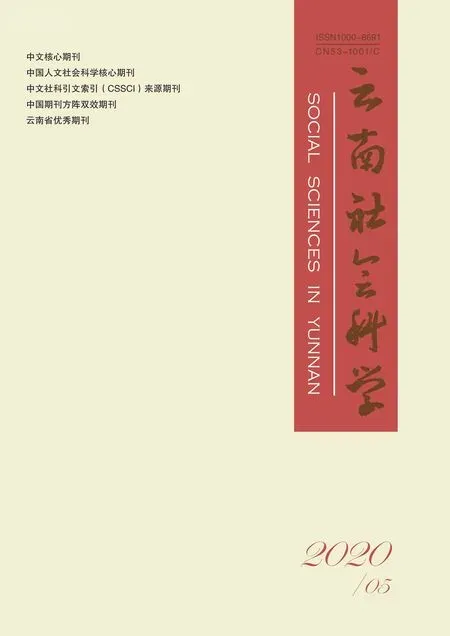何谓现代性:马克思的本质解答及其意义
2020-02-20毛勒堂
毛勒堂 杨 园
现代性是人类身居其中的现时代之根本属性,是现代之为现代的本质规定和核心标识,也是现代世界问题之所在的中心。而与此相应的是,现代性作为一种流行的话语充斥于当今之思想界、理论界乃至大众生活。然而,在众多的现代性话语中,对于现代性本质、现代性风格以及对现代性的态度等问题上,人们之间仍存在着莫衷一是的纷争,现代性问题依然是一个有待深究的时代课题和理论任务。那么,马克思哲学作为“现世智慧”和“时代精神之精华”,作为现代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自我解放意识和思想表达,其对现代性秉持何种态度?对现代性给予了怎样的本质规定和解答?而这种解答在今天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和启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思考,对于深入透视和把握现代性的本质以及确立对现代性的辩证态度,进而创造性地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何谓现代性:不同的话语路数
在当今国内外的思想界和学术界,现代性作为一种广泛的话语而为学者们普遍探讨和极大关注,而其中也存在不尽一致的分歧和纷争,从而产生不同的叙事路数和策略。
(一)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顾名思义,就是对现代性作了哲学性规定,其实质则是一种理性形而上学话语。在这种现代性的哲学叙事话语中,现代性的本质、基础和根源被置放到理性之中,从而以理性规定现代性的本质,视理性为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根由,将理性、启蒙等作为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和标识,并对理性持积极和乐观的态度,深信理性必将为人类带来自由、平等、博爱和美好生活。在这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现代性被规定为是对前现代传统社会的瓦解和超越过程中形成的现时代之特质即理性,从而现代被高度概括为“理性的时代”。
与此相反,前现代社会则被视为是一个充斥着神性、无知、禁欲的时代,是一个由浓厚的“神魅”包裹着的存在世界。在那里,信仰扮演真理,神性主宰人性,教条充当法则,人们置身在一个神性高扬、理性黯然的时代,从而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个理性代替信仰、人性代替神性的世俗化、理性化、去魅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在此过程中,理性主体得以全面崛起并获得内在巩固,理性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利和地位,以君临一切的气势俯瞰世间万物之存在,从而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身的存在合法性提供依据或辩护。由此,确立了一个由理性主导和支配的现时代,建构起以理性为根基和原则的现代世界。所以,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现代性作为现代之本质特性,是以理性作为其根本原则和核心标识的,并依据理性原则阐明现代世界的优越与危机、进步与异化、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凭借理性标识出与前现代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概言之,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将理性视为现代性的本质根据和核心标识,从而对现代性做了理性的本质规定和核心命名。
(二)现代性的社会学话语
社会学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层面展开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群体的研究。现代性的社会学话语,实际上是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和社会组织的层面审视和规定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从而对现代性作了制度性诊断和制度性规定,进而从社会制度和秩序方面考察现代性的生成,揭示现代性的动力,解析现代性的本质,确立对现代性的态度。譬如,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必须从制度层面来理解现代性,因为“就其动力、就其侵蚀传统风俗习惯的程度及其全球性的影响而言,现代制度与以前所有形式的社会秩序迥然有别”①[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1 页。,“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②[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年,第1 页。,它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③[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16 页。。可见,在这样的现代性社会学话语中,现代性是作为一种与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秩序有显著区别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和秩序被理解和规定的。
在这样的现代性社会学叙事中,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工业主义”“科层制”以及民族—国家体系等制度方面。“工业主义”作为一种以机械化操作方式规范化订制人工产品的生产体制,实施了对物质世界的“图像化”和切割组装,并通过对自然的大力开发,最大限度地去满足人类的需要乃至无度的欲望,从而与前现代传统社会那种“靠天吃饭”的农耕文明秩序存在显著区别。“科层制”由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它是一种以严密的规则为主体的管理体制,处于体制中的每个人职责分明,权责清晰,体制内部具有自上而下的办事程序和自下而上的反馈系统,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程序化和系统化的组织形式,从而其与前现代传统社会依靠感情、凭借习俗以组织和管理社会具有了实质上的不同。这正如美国学者卡洪所指出:“现代性展示了社会生活的循序渐进的理性化和管理的官僚机构化,这就一点一滴地克服了作为逝去的岁月主要特征的神话般的非理性的组织模式。”④[美]卡洪:《现代性的困境》,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3 页。在现代性的社会学话语看来,民族—国家既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显著标志。“作为社会实体,民族—国家与大多数传统的秩序形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具有特定形式的领土性和监控能力,并对暴力手段的有效控制实行垄断”⑤[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16 页。,从而与传统的帝国体制具有原则差别。可见,现代性的社会学话语,对现代性作了制度性的规定和阐释,从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层面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特质,规定了现代性的本质。
(三)现代性的美学话语
现代性的美学话语,把现代性置于审美批判领域加以叙述,视其为审美体验和内心感应,从而对现代性做了审美现代性或体验现代性的诊断和规定。譬如,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哈贝马斯从审美现代性问题入手来探讨现代性问题。他在书中指出,若遵循概念史来考察“现代”一词就会发现,现代首先是在审美批判领域力求明确自己的规定。
在18 世纪法国发生的著名的“古今之争”中,主张现代的一派反对法国古典派的自我理解,并从历史批判论的角度对模仿古代范本的意义加以质疑,用一种有时代局限的相对美的标准去反对那种超越时代的绝对美的规范,从而把法国启蒙运动的自我理解说成是一个划时代的开端。因而,“modernity”一词至今仍然具有审美的本质含义,并集中表现在先锋派艺术的自我理解中。①[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年,第9—10 页。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这个概念是和美学或艺术实践具有紧密关联性,并包含着主体的内心体验维度。事实上,不少学者从主体的审美体验、心理感应的层面刻画了不同于传统的现代性画面,如鲍曼之“流动的现代性”、波德莱尔之“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现代性。与此相一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一种心理主义,是依据人们内心生活的反应,实际上是作为内在世界,来体验和解释世界,在心灵流动因素中固定内容瓦解了,由此一切本质性的东西都被过滤掉了,其形式仅仅是运动的形式而已。②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66—67 页。如此可见,在这种审美现代性或心理体验现代性的话语中,现代性意味着一种与传统的断裂,意味着一种碎片化、躁动不安、不确定和社会生活急剧变迁的心理体验,从而与那种稳固牢靠、确定不变以及由传统纽带链接在一起的前现代社会作了本质划界。
以上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社会学话语和美学话语作了概要阐述,但必须指出的是,现代性的叙事话语远不止于如上所述,还有很多不同的叙事路数,如政治现代性、经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技术现代性等等。就上述的三种现代性话语而言,公允地说,它们从某一定角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性的某些属性和面相给予了揭示和阐述,这对于认识和理解现代性是有助益的。但是,对于这些话语,仍需要进一步追问。譬如,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其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话语,是一种基于观念论的现代性批判,由此就要追问:理性何以能在现代世界异军突起?理性主体为何能在现代社会突显?循着这样的追问,现代性的批判就会被引导到“历史的本质一度”中加以求索。
对于现代性的社会学话语,若现代社会的制度和秩序不是天然存在和与生俱来的话,那么其来历和根据又何在?在这样的追问中,对现代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求解就会深入到对其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之来历的考察。同样,面对现代性的美学或心理学话语,需要追问的是,主体的审美或心理体验是现代性的本质属性吗?这样的话语是否深入到了现代性的核心本质和本体层面?事实上,作为一种主体的现代审美体验或心理体验,它在根本上是由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和现代生活的内容所引发的,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情感体验和心理反应。由此要求穿透现代性的审美体验表象以把握现代性的实体性内容。可见,在对上述现代性话语的批判性追问和检审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就会呈现出来。
二、资本现代性: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本质规定和核心命名
由于现代性是现代之为现代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现时代的本质属性,所以要理解和把握现代性,首先需要了解马克思语境中的现代概念。不同于以理性命名现代的现代性哲学话语,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根本处对现代性做了历史存在论的批判揭示和本质规定,以资本命名现代,将资本逻辑视为现代社会的本质逻辑。马克思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98 页。,“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6 页。由此,马克思以资本对现代性作了本质的规定和命名,从而在何谓现代性的问题上,马克思以资本现代性作了本质的回答。事实上,马克思从资本及其逻辑的视角对现代性的生成、现代性的延展、现代性的悖论、现代性的终结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批判和论析,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资本降世与现代性的生成
由于马克思在总体上把现代性纳入到资本视阈中加以审视,因而在检视现代性的生成问题上,把现代性的生成与资本降世紧密结合在一起,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把现代性的生成与资本降世的历史视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从而把资本来到世间的历史过程视为现代性的生成和出场过程。由此,对现代性生成历史的检视,就可以置换成对现代资本诞生和降世过程的历史考察。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一个产生、存在并将消亡的现代社会生产关系,并不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们所宣扬的那样,是一个与生俱来、天然永恒的圣神存在,相反,资本来到这个世界经历了一个漫长且伴随着血腥和刀剑的历史过程,它“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第822 页。,从而“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的历史起源的本质,就是直接生产者被剥夺,是以所有者的个人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解体。”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825 页。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降世的历史有更为清晰的认识,认为资本并非无中生有,而是由货币羽化而来的,所以资本不过是能够带来货币的货币。然而,货币也不是天然存在的,它本身又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马克思认为,货币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是商品交换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一般等价物,因而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没有货币,就不会存在资本。因此商品经济是资本存在的前提,而其中最为本质的是,不仅劳动产品商品化,更关键的是劳动力本身商品化。正是由于劳动力商品化,才使得货币能够在市场上购买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为货币带来更多的货币,从而使得货币羽化资本成为可能。马克思又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沦为商品的成因,认为劳动力商品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使然,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劳动者和劳动资料遭遇痛苦而深刻的分裂,另一方面货币资本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劳动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生,忍受货币拥有者的统治和剥夺。当然,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考察,在根本上是从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中加以分析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从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基础上,剖析了现代资本的来历及其降世过程,在此基础上描绘了资本时代、资本世界、资本社会不同于中世纪社会的时代属性和特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现代性有许多生动的描述,指出在资本时代“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同时,资本时代表现出急剧的不稳定特性,“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 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第34—35 页。概言之,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生成与资本降世这一世界历史事件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资本降世本质地构成现代性的生成因,从而深刻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来历。
(二)资本逐利与现代性的延展
正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是在欧洲出现并逐渐在全球扩展一样,作为资本的伴生物,资本现代性是从欧洲逐渐延伸至北美再到东亚,并逐渐布展至世界各地,从一种地方性的存在逐渐转变为全球性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现代性之所以能够从其源生地西欧逐渐延展至全球,其根本动力乃植根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及其无限度扩展的增值逻辑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其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生产和追逐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实现交换价值。因而资本带着贪婪的野心攻城略池,不断追求自我增值,拓展自己的疆域和领地,并把自己的增值逻辑强力推广至全球,把资本原则布展至世界遥远的边际。
事实上,资本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自己的全球布展计划和贯彻行动。马克思认为,资本为了实现逐利和自我增值的目的,不停地奔走于世界各地以开拓世界市场,而为了输送商品至世界各地,就必须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和交通条件,进而把一切民族乃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资本的体系中来,世界也因为资本的中介而联结在一起,从而开创了资本的世界历史。所以,马克思指出,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而“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第35 页。因此,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以资本为核心标识的现代性,其所以能在全球延伸和布展,源于资本的逐利活动和增值驱动,正是资本的全球逐利行动和全球征服活动使得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布展成为现实可能。
由此,马克思以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增值逻辑深入揭示了现代性由地方性存在转化为世界性存在的根本动力和深层根源。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不仅现代性的生成与资本紧密相关,而且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与资本逻辑在全球的演绎具有本质关联,正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增值逻辑现实地推动现代性在全球的延展。
(三)资本“二重性”与“现代性悖论”
资本现代性生成并主导现代社会以来,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抛离了旧有的社会秩序和生活轨道,从而步入了以“现代性断裂”为条件而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生活之中。在其中,现代人一方面因摆脱传统的各种禁锢而使自我的主体意识得以极大张扬和释放,带来了心智上的启蒙和前所未有的物质富足、便捷的交往生活以及乐观的期待,从而沐浴在现代文明的光辉里。而与此相对的另一极是,现代人因遭遇“上帝已死”的存在境遇而陷于浮萍般的无根精神生活状态,并在贪婪的物欲支配下深陷沉重的物化生活而不能自拔,从而现代性的布景上出现了巨大的阴影,并产生了现代性的“悖论”:富足与贫困共生、安全与危险并存、文明与野蛮交织、光明与阴暗同现、进步与倒退并行。这一切引发了人们的深度“现代性之隐忧”。事实上,现代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且自相矛盾的时代,诚如英国学者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它在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的同时,其自身也有阴暗面,而且在今天变得越来越明显。②[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6 页。
对于现代社会所具有的这种自相矛盾和悖论性质,马克思早已具有了深度的体察并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 毋庸争辩的事实。”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第580 页。马克思不仅生动描述了现代性的悖论现象,而且对于其成因和根源也进行了深入分析。在马克思看来,由于现代性本质上是资本现代性,资本原则本质地构成现代性的核心原则,因而现代性悖论植根于资本之中,源生于资本的“二重性”。马克思认为,资本本身就是矛盾体,是集“文明”与“野蛮”于一身的存在。一方面,资本具有促进生产、创造财富、扩大交往、传播文明等文明的一面,从而资本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资本是以自我增值为根本存在,因而具有无限贪婪、无度扩展、无视尊严、极限压榨的一面,从而引发诸如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意义危机等动荡不安的殖民化生活世界。正是资本本身所固有的“二重性”,使得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现时代,呈现出自我存在的“悖谬性”。对此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许多深刻而丰富的指认: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劳动现实化表现为工人到饿死的程度;物的世界的增殖则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动物的机能成为人的最高追求,而真正的人的机能则降格为动物的机能;活动是受动;生殖是去势;等等。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56—160 页。如此可见,马克思立足资本“二重性”视角,分析了现代性的自相矛盾及其“悖论”的成因和根由,为破解“现代性悖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四)资本自反性与“现代性的终结”
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其将会呈现一种怎样的存在前景?这是在反思和研究现代性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人们之间是存在分歧的。有的人认为,现代性是有史以来人类伟大的发明并具有最高的价值善,从而现代性是“历史的终结”。有人主张,现代性虽蕴含进步、启蒙、解放等可贵的现代价值,但其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矛盾和不足,因而需求对其进行不断的修补和完善,以保持现代性的伟力,从而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也有人声称,现代性犹如流动的液态物和飘忽不定的存在,无法捉摸并难以把握。也有人认为现代性罪恶多端,引发了现代世界极度残忍的“大屠杀”,从而是不可饶恕的对象。由此,人们在不断思考现代性的未来前景,寻求现代性的拯救力量,探索现代性的终结之路和替代方案,并给予了不同的诊断和药方。如试图将现代性拉回到前现代田园牧歌式年代的浪漫主义方案,以激进、暴躁、极端反现代性面目出现的各种后现代主义方案等。
对于现代性的发展前景、终结道路及其替代方案,马克思曾以辩证的眼光和历史的态度给予了深刻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现代性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存在,它有自身的来历和存在合理性,也有其存在的限度和边界,并把这一切都置放在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中加以审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现代性的终结力量内在于资本的自我否定性,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推动资本的发展,也在其中形成瓦解资本的力量,并最终实现自我消亡。所以,马克思论述道:“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78 页。,“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91 页。。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产生出自反性力量,为超越资本现代性创造出物质前提。而在此过程中,共产主义将历史地出场,并实现对资本现代性的积极扬弃和终结。所以,马克思以资本的自反性辩证法深刻解答了关于“现代性终结”和超越的问题。
上述可见,马克思基于生产方式的存在论根基,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从资本与现代性的本质关联中,深刻解析了现代性的生成根据、延展动力以及“现代性悖论”和“现代性终结”等问题,从而在根本上以资本规定和命名现代性,对现代性做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解答。
三、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意义和启示
前文述及,马克思立足资本及其逻辑的视角,对现代性作了本质回答和核心规定,并从资本降世与现代性的生成、资本逐利与现代性的延展、资本“二重性”与“现代性悖论”、资本自反性与“现代性终结”等方面,对现代性的生成、发展、面貌和走向,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和批判。而马克思对现代性所做的这些深度解析和阐释,在今天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一,开创了现代性批判的全新路向。“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流行语,也是现代社会道不尽的话题。而在现代性的言说中,因学科视野、认识基础、所处环境等差异,导致不同的叙事风格。譬如,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把理性作为现代性叙事的轴心,从而对现代性作了理性形而上学的本质规定。现代性的社会学话语,围绕社会制度和秩序展开对现代性的分析,把现代性视为是一个社会“去魅”化、“合理化”和“科层制”化的过程。现代性的美学话语,则围绕着主体的审美体验和心理感受求解现代性的核心。现代性的工艺学话语,则以技术的现代化规定现代性的本质和核心,从而对现代性作了技术主义的解答。上述现代性话语,尽管在现代性叙事方面存在一定的侧重点,但总体上依然停留在对现代性的形而上学解答。无论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社会学话语,还是美学话语、心理学话语,乃至技术现代性话语,基本停留在理性主义批判或意识形态批判的层面,从而可以视之为是一种观念论的现代性批判路向。与此不同,马克思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视野和方法论原则,把自己的现代性批判深入到社会历史的生产方式中,将现代性批判奠基于对现代资本生产的深入批判,对现代性采取了资本现代性的核心命名并予以本质规定和深入阐述,从而将现代性的批判推进到其“历史的本质一度”中,本质性地超越了现代性的观念论批判 路径,开创了现代性批判的全新路向即历史存在论批判路向,从而深刻揭示了现代性的实体性内容及其存在根基,深度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真理。
其二,实施了对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历史终结论”由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这种论断在某种意义上是关于资本永恒的神话。事实上,类似“历史终结论”的话语在阶级社会中从不绝于耳,它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话语,其实质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在观念上的反射,是物质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表达。譬如,在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历史终结论”是以上帝永恒神圣的教条形式出现的,其为封建社会的永恒性做注解,为教会的统治做辩护,声称封建社会乃上帝善良意志在人间的体现,因而是“历史的终结”。在资本主义时代,“历史终结论”则以资本天然存在、资本永恒神圣的话语呈现,声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历史上最为进步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且其只存在内部自我完善的问题,而不存在被超越的可能,历史因此而终结。在资本时代,“历史终结论”也不过是一种典型的资本意识形态话语,直接而露骨地为资本永恒、资本正义做无批判的辩护,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典型形式。而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则将资本及其生产关系置于宏阔的历史视野中加以审视,对资本及其生产关系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析,认为其是在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中历史地产生、历史地存在并历史地消亡的,因而资本是一个过程性的存在。所以,在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语境中,资本既不是历史的起点,也不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不过是社会历史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而已。不仅资本不能终结历史,而且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历史就不会终结,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是人们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总之,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揭穿了关于资本天然神圣的谎言,破除了资本永恒、资本终结历史的神话,从而实施了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其三,提供了检审现代性的辩证视野。由于资本现代性是一个集进步与倒退、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阴暗、危机与生机于一身的悖论性存在,因而自现代性生成开始,人们就围绕现代性的是与非、功与过、福与祸等问题展开了各种论争,进而对现代性持有不尽一致乃至尖锐对立的认识和态度,这一情状在今天依然如故。历史地看,围绕如何认识和对待现代性的这种纷争既存在于现代性初现的早期,也存在于现代性兴盛的当代。在如何认识和对待现代性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话语,一种把现代性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正是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导致了现代世界的深刻危机,引发了现代人的存在焦虑,因而现代性是现代世界阴暗的根由,从而对现代性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道德控诉和伦理批判,进而对现代性采取大拒斥的态度。而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现代性冲破了旧时代愚昧、狭隘、专制、禁欲的禁锢和牢笼,极大地释放了生命的自由存在本性和精神世界的青春活力,并因此带来了现代世界自由、平等和美好,因而现代性是一个合乎人性的解放事业,值得人们无限眷恋和誓死捍卫,从而对现代性采取了无批判的拥抱态度。然而,无论是全面拒斥现代性还是全情投入拥抱现代性,二者在认识和对待现代性问题上,都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立场和片面认识。
马克思则不同,他以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视野,从资本的历史辩证运动方面,深入揭示了资本现代性的辩证性,认为现代性的出现有其历史的根源,现代性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基础,现代性的发展有其历史的限度,因而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价值层面来审视,现代性都是一个辩证合理的历史性过程,从而现代性既不是一无是处的邪恶化身,也不是满身光明的至善大全。在马克思看来,既不能以浪漫主义的天真全面拒斥现代性,也不能以无批判的态度全情拥抱现代性,而是既要辩证认识现代性,更要辩证对待现代性,从而在批判中扬弃现代性,以创建更加合乎人性的美好世界。可见,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超越了在现代性问题上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认识片面性,为人们提供了辩证认识和对待现代性的科学态度。
其四,指引着中国现代性的创造性建构。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属性,是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显著特征。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从而现代性是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存在问题。因而如何直面并回应现代性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现实挑战。中国在发展自己的现代性实践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因为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又具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和传统势力,还面临当今后现代性力量的挑战。因此,在古今中西力量交错中的当代中国,如何创造性地建构自己的现代性,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之路,从而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成为当代中国迫切而重大的思想课题和历史任务。在此过程中,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思想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智慧和价值航标。
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语境中,现代性是由资本奠基、由资本命名的,从而资本现代性是现代性的本质内核,因而无论是对现代性的言说还是对现代性的实践和建构,皆不能无视资本及其逻辑在现代社会的主导力量和现实运作,因此中国现代性的实践和建构不能绝缘于资本文明,而是要大胆利用和借鉴资本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实上,利用资本文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重要内容。另外,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其根本的价值旨趣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指针要求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价值取向,坚定不移的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实上,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结合中国实情,创造性的探索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之路,并在其中自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旨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和谐献智慧。可见,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中国现代性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智慧和价值指引。
总之,现代性是现代之为现代的本质属性,是现代社会所谓问题所在的中心,并引发不尽一致的诸多现代性话语。马克思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从社会生产方式出发,对现代性进行了资本的本质规定和核心命名,并从资本与现代性的本质关联处深度揭示了现代性的生成根源、现代性的延展动力、现代性悖论现象以及现代性终结之路。置身于当今现代性的存在境遇,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依然散发出强大的思想魅力和现实启迪,是今天检审和应对现代性时不可错失的思想坐标和价值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