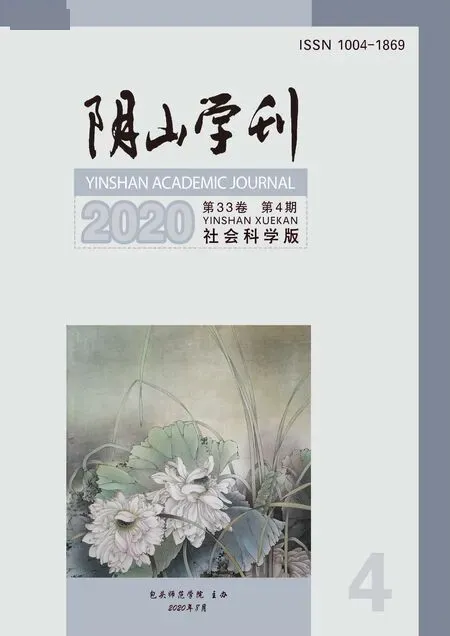论刘震云小说中底层民众的语言暴力书写
2020-02-20张明
张 明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人作为会说话的动物,语言可谓是人类最基本的存在形式。正是通过语言,人类将实践中习得的文明代代相承下去。它不仅是人交流沟通的工具,更担负着特定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思想价值理念与情感心理模式。换句话说,“语言是社会群体的资产,群体的价值和思想模式都隐寓在语言之中”[1],个人化的表达中必然会附带社会性意义。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文学作品中暴力的书写并不少见。但大多数读者对于具有文学暴力现象的作家认知却往往放置或着眼于先锋作家的笔下,余华、莫言、苏童、残雪……,暴力成为他们写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或某一阶段的标签,这已然是学界普遍性的共识。相比之下,刘震云作品中的暴力,尤其是语言形态的暴力却在有意无意中被搁置与忽略。实际上,刘震云在文学创作上一直表现出一种执着的沉潜于故土的民间文学的自觉求索,以颇为“顽固”的姿态表达着“民间立场”,鲜明地凸显着不同形态下底层民众固有的暴力文化特性。正如摩罗所说:“中国文化极其冷酷无情,极乏人文气息。无论是就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而言,还是就日常生活形态而言,内中深藏着对于生命尊严的漠视和对于人性的敌意”[2]。因而,在社会生活以及内在的意识形态中普遍存在着暴力的倾向。可以说,正是如此,构成了民众一脉相承的精神链条。由此,刘震云作为知识分子,按照作家的固有方式——文字的形态一直在实践这种映照,自在地表达着这种文化理念和生存方式。
一、语言暴力的文本呈现
“所谓语言暴力,就是用语不合逻辑和法律规范,欲通过不讲逻辑、不守法度的语言风暴,从而以语言霸权的形式,孤立和剥夺他人的某种权利,对他人造成伤害”[3],在此涵义范畴内,暴力的施行手段抑或工具载体正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纵观刘震云的文学创作,语言暴力在其文本编织中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取向。
一是直白的身体器官性的恶语咒骂。像“他妈的”“狗日的”“××巴”等粗俗口语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塔铺》中因舍友“磨桌”在宿舍“呜呜”大哭,“耗子”向其发火道:“你别他妈在这号丧好不好……”[4]3;因为“耗子”开“我”和李爱莲的玩笑,“我愤怒地将馍袋向他头上砸去,并骂道:‘去你妈的!……’”[4]4《头人》中的三姥爷顿着手中的粪叉对保丁小路说:“我×宋家掌柜他妈!……”[4]93《官场》中,皮县县委书记老周因食物不满大发牢骚骂道:“妈的,他们到县上来,咱们桌上桌下招待;咱们到他们这开个会,他们顿顿让咱们吃大锅菜!”[5]193因自己以前的办公室主任被现任县长小毛给撤了,金全礼在心里骂道:“妈的,你小毛也太胆子大,太岁头上就这么动了刀子”[5]222。《单位》中局里要搞民意测验选举处长,老何认为这是正常的,老孙却反驳道:“别听他妈的胡扯”[4]122;对于老何告知自己老张搬家的消息,老孙鄙视地骂道:“你他妈懂什么!要不说你永远是个科员,拉上你真他妈的倒霉!”[4]136《官人》中副局长老方更是多次骂出“妈拉个×”,言语的暴力充斥在整个人物的塑造中。在其他的《温故一九四二》《一腔废话》《故乡相处流传》《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等作品中,这种类型的语言暴力可以说遍布刘震云的小说文本,因此不再展开赘述。
如果说这些暴力的展示更多的是人遇到愤事的过激反应的话,那么在《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中多次出现的杀人行为则明显带有暴力渲染的成分。当然,刘震云作品中杀人这一行为并没有完全真正落实到实处,只是作为一个话语要素推动文学叙事的进展,同时也带来了语言暴力的残酷想象。这便是第二种类型:突破道德化的伦理批判。
在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上部“出延津记”中,老裴因和老婆老蔡闹矛盾,牵扯到老蔡娘家哥,便怒火中烧,拿起砍刀要去杀她娘家哥蔡宝林;因赶车的老马去茅房吐了一口痰,使得在茅房垫土的杨百顺追根溯源起“延津新学”和抓阄的事,再加上酒精的作用,杨百顺便恶向胆边生,遂抄起自己的杀猪刀去马家庄杀老马;吴摩西(杨百顺)拿一把牛耳尖刀去找姜龙姜狗两兄弟算账,虚张声势地想要杀人;吴摩西发现自己妻子吴香香和隔壁老高偷情,拿起上回的牛耳尖刀冲了上去准备杀了这对狗男女。在下部“回延津记”中,当曹青娥不愿和丈夫牛书道过日子的时候,“我光想杀人,刀子都准备好了”[6]267;当牛爱国看到小蒋一家三口依旧和好如初,便拍胸瞪眼的要杀人,“杀他们家的儿子,让他一辈子不得安生”[6]288。在《一句顶一万句》中真正完成的杀人行为是高个子山东人捅杀姜虎。姜虎在与人打架争执的过程中,被随身携带着刀的高个子山东人捅了胸腔而毙命,“血呼的一下,喷了一墙”[6]130。此外,老汪他爹临死前老汪道出了杀人的内在逻辑,“让你去当杀人放火的强盗,一来你也不挨打了,二来家里的仇早报了”[6]24。杀人行为可以说是一种“恶魔的私语”[6]178,体现着人内心被规训的暴力。
《我不是潘金莲》这部小说开篇“序言:那一年”,李雪莲为离婚一事找王公道,提到如若王公道不管,她就要回去杀了秦玉河。听到此话,王公道吃了一惊。吃了一惊应是“杀人”这一暴力词语对王公道所产生的冲击。在来之前,李雪莲最初的想法就是“快刀斩乱麻,一刀杀了秦玉河了事”[7]7。凸显了杀人可以省去一切麻烦,简单快捷地达到解决仇恨的目的。但正如李雪莲娘家弟弟李英勇所说:“杀人容易,杀了人,自个儿也得挨枪子儿呀”[7]8。挨枪子在现今的理性社会,所代表的是外在人人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具体来说就是法律效力,而不是意气用事的侠义精神。后来,听了看厕所妇女的话,觉得“杀人不过头点地,一时三刻事儿就完了”[7]16,如此这般太便宜秦玉河了,最好的惩罚办法是跟秦玉河闹,“也闹他个天翻地覆,也闹他个妻离子散”[7]16。李雪莲认同了这个比杀人“更好的办法”,因而选择放弃杀人去诉诸法律。走向法律这条路径之后,谁知绕了一圈,问题没有解决,李雪莲还被拘留了七天。出来之后李雪莲再次想到的是“杀人”,这次不仅仅是杀秦玉河一人,杀人名单上更是增添了市长蔡富邦、县长史为民、法院院长荀正义、法院专委董宪法、法院法官王公道等五人。在近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牛小丽对着母亲的背影喊道她再回来,就要杀了她,张大进他妈也说要拿刀杀了这对偷情男女。
杀人是一件残忍暴力的行为,通常认知习惯中杀人者都是一些土匪、流氓、恶霸等负面人物。杀人虽然能给予对方致命一击,但在毁灭对方的同时,自己也要相应地付出毁灭的代价,正所谓“杀人偿命”是也。因此,这些人物口中愤愤然喊出的“杀人”就是一种善良弱者不断以不可能落实的语言虚拟暴力上演的一出出悲剧。即使是刘震云那些纯属虚构、子虚乌有的“故乡”系列小说,也弥漫着不可遏制的暴力,但这种暴力当然也是一种生活的与历史本身的存在。杀人的心理动机,虽然各异,但是当民众遇到无法解决的事情时,不是诉诸法律去讨回公道、伸张正义,而是依靠最原始的本能冲动,想要通过暴力的手段用最直截了当的形式杀人一解心头之恨。
从刘震云小说人物的这些语言中,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对压抑和淤积已久的精神苦痛的宣泄与释放。实际上,更表达的是这种暴力心态、暴力情绪与暴力倾向在国民集体无意识层面的浸染以及如何通过他们的平常生活语言体认“他者”和理解外在世界。正如五四的“书面语言的变革不只是文学形式问题,它在强有力地动摇着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8]44。值得肯定的是,刘震云作品中的语言暴力并不是毫无节制地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审美状态去客观呈现,而是在自我无意识中恰如其分地随着人物的特定身份与心理需要自然的流露,令语言暴力的使用获得了天然与历史的双重合理性。而今,需要深究的是民众语言暴力形式背后所受制的思维模式,这是有待于揭示的。
二、语言暴力潜在产生缘由:底层民众的心理图式症候
自“五四”以降,虽然数千年的农业小生产在新的时代潮流中已经开始走向重大变化,以往赖以生存的根基已极大动摇。但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的变革仍是需要探索深思的问题。在汪曾祺的文学观念中,语言不仅只是形式,本身更具有内容的意义。不仅如此,更进一步的认识到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可以说刘震云笔下的叙述语言是与人物相协调的,具体到写农民人物,所体现出来的叙述语言就是鲜活的农民语言。
人是一种“言说的动物”,语言暴力是一种手段,也是目的。借助于日常生活中的言语暴力,可以施加给对方人格的凌辱与精神的创伤,可以窥见和挖掘人性深处所背负的负累以及找回被否定的尊严。语言暴力显现出的深层文化与心理,有着坚实的“文化心理积淀”。在我们民族长期的封建集权与专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逐渐生成,沉积在人的意识、潜意识之中,成为一种民众暴力心理的普遍化存在。“根植于中国乡村的仇恨意识形态,散布在每一个细微的生活细节里,它并没有受到政治制度的直接鼓励,却为历史上悠久的流氓暴力传统提供了深厚而广阔的基础”[9]。正如胡适提出研究中国文学的语言来究诘民族心理,话语暴力这一行为模式背后所支配的是观念意识的传统性,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心理结构和意识形态。这正是通过暴力形式的语言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虽然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似乎在不言而喻地表明某些沿袭千百年之久的陈规陋习被涤除殆尽,但是封建的传统的小生产意识形态依旧在乔装改扮后悄然存在,并未得以彻底清理。“儒家孔学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学说、理论、思想,而是融化浸透在人们生活和心理之中,成了这一民族心理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8]37。可以说底层民众深受民间文化影响,尤其是与中国传统“侠士”文化中的“尚武”质子有着内在联系,既有“杀身成仁”,又有“舍生取义”,恰似《水浒传》中绿林好汉的侠匪气质与品性。
弗洛伊德于1900年发表的《梦的解析》一文中,则另外一个层面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启发性和说服力的理论性依据。他认为,人的意识结构是一个由意识、潜意识、无意识共同构成的由浅入深的多层次动态。弗洛伊德将其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部分进行描述。其中,“本我”是人的无意识领域各种原始本能、欲望和冲动的总和,“自我”和“超我”则起到对“本我”的控制和监督作用。而梦所需要做的恰恰就是使被压抑的“本我”在梦境中逃逸出来并得到某种满足,“梦是一个(受压制的或被压抑的)欲望的(伪装的)满足”[10]。在语言的暴力中非理性的“本我”暂时冲破“自我”的现实管束,使长期受压抑的人能将其内心最原始的生物性本能得以宣泄、转移,显示其尊严与力量,从而获得一种“本我”满足性的快感。反之,如果过度的抑制而无法控制,则往往会导致人心理扭曲、变态,甚至变成疯子。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去看,“杀人”的非理性暴力生命状态,充满了狂躁、愤怒乃至随之而来的恐惧最具有威慑力,以生命作为赌注,彰显了底层民众的无助与可怜。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生命是一切之根本,正如“未知生,焉知死”一般,人们注重有生之年。生之意义如此重大,不可儿戏。但是,“杀人”的情形毫无疑问地说明事态已经达到了抛弃所有的无法挽回的决绝地步。在此,传统民间形态的文化作为一种“客体”被存留,具有审美性的观照,也可以看出乡村短暂的时间性记忆确实蕴含着对刘震云异常生动的影响内容。这应该说并非是文学的工具理念属性,而多是一种文化心态的流露,真切地展现民众的思想方式、行动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些主人公的挣扎,他们的愚昧、狭隘、懦弱与暴力,凸显出的是关于弱势群体本色式还原的真实记录,是对民间的退却与坚守。
刘震云笔下的暴力形式与姿态又有很大的个人特点。他的文本既没有“文革”题材的政治灾难下的迫害景象,也没有先锋小说作家对鲜血淋漓的死亡与暴力场景的迷恋,更没有莫言文本世界中逼真残忍的酷刑与杀戮的极端魔化,而是一种最本真的原始暴力的张扬、显现,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的真实。这种行为方式背后隐含的运行逻辑,折射的是千百年来所积淀形成的文化心理积习。“我们从这样一种声响中得到这些令人惊异的语义属性,它不仅包括修辞学的和语言学的现象,而且甚至包括政治的、文学的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现象”[11]。这种话语现象背后的深层意蕴是当底层民众遭遇不幸时,文本中暴力书写所张扬的血性、以恶治恶的反抗方式便有了大快人心的认同感,也以此来体认和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
语言暴力景观是一种“非肉体”的刑罚,且在这种情形下已然转变为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作为在与其对话的对象的意识形态层面上达到征服状态的工具。由于伦理道德的知识体系,造就了语言话语的“现实——指涉”意义的扩大与强化,催化在人们的心理结构和心理秩序上,形成我们这个民族的认知和情感结构并演变为久远的历史传统。
三、语言暴力的文化反思与意义
这些看似日常生活的言语组织,却有着某种历史维度的现实指涉。正如福柯将话语与权力扭结在一起,强调话语乃至话语的实践中等值着权力的压迫与命令,体现着广义的支配力、控制力。“只有话语才能行之有效地贯彻权力意图,权力隐藏于话语之中,话语经由权力发送,它挟带着权力的弹药进行争斗和掠夺”[12]。既然如此,在民间话语的想象之下,人通过话语便“言而喻”地向外在他者证明了自己的存在。这是一个真正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民间社会、民间权力的确立。
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中,他们身上所呈现出的政治或文化背后现实的生活境遇不能不让人唏嘘、哀叹。不可否认,语言暴力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它所导向的精神暴力具有复杂的深层次构成,有着巨大而深刻的文学价值和思想意义。刘震云所关注和展现的不仅仅是底层外部的物质的观照,可以说是真正走进内部对他们的精神层面进行透视、把捉与体察。这种语言暴力既是一种复杂的审美现象,也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刘震云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乡土性的一面,受到不自觉的语言暴力记忆的牵制去用具体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这一点上来说,刘震云的文学语言是真正的底层人的语言。如果说在其他作家的笔下,语言的暴力书写呈现的是一种变相的刺激与伤害,那么在刘震云这里则是通过语言暴力建构出一个真实的民间图景,实现了把握叙述者的生命律动乃至诗性审美的回归。当然,这些作品中叙述者所使用的暴力性的语言对阅读者也产生了无法抗拒的精神暴力。
“暴力是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部分,是深藏于人性深处的罪恶和痛苦。它是最可诅咒的,同时也是需要我们理解与悲悯的。因为它是人性痛苦的一部分,是人类苦难的一部分”[13],需要施之以人文关怀。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非理性行为的暴力现象便形影不离的存在着。其中,肢体行动上的暴力无疑代表着强悍野蛮和杀伤性力量。而语言的暴力则是话语体系中体现暴力的一种独特形式,具有心理上的无形侵犯性,因而表现出不同于肢体暴力的鲜明特征。在暴力中,如果暴力的使用者是为了反抗非正义的侵害行为,则无疑有着充分的伦理或道德层面的支持依据。在文学作品中,将语言暴力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就具有了不可替代的美学意义。刘震云作品中的人物语言,暴力的合理灌注与渗透,增强了感染力与激荡力的成分。但是,由于人物身份的特殊性同时体现了中国的农民,尤其是底层民众,在深厚的封建与专制的统治下,一直处于一种压抑与服从的生存状态,肢体的行动暴力无法实施,只能通过语言上的暴力去排遣和释放压力,这便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被一代代的传承。当问题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得到解决,以暴制暴就成为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似乎暴力崇拜的心理。“这样的心理和思维虽然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兑现的机会,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消失了,不存在了。作为人性的暗流,它仍隐藏在心底深处,并时时会蠢蠢欲动”[14]。
在这些人物身上通过语言所展现出来的前现代性,与其说是刘震云的一种文化批判,不如说是一种无意识情况下潜意识的展露,这当然与刘震云本人来自乡村的作家身份有着不可脱离的关系。乡村的前现代性理所当然的与所谓的现代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乡土本性。从现代性的视域对乡村予以观照,便会发现启蒙的无效性与苍白无力。乡土继续延续了传统,并造就孕育了与之相适的乡土性的文化心理结构,使这些底层人物遭受的物质、精神乃至伦理层面所承受的痛苦状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显现,可以看到刘震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身上应有的批判坚守与人格良知,尽管刘震云本人对此可能并没有明确的意识。质言之,这种话语暴力的叙事路径,是前现代社会中国民内心深处无意识情结被控制被戕害的文本注解,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这种禀性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深刻地参与到中国底层文化心理结构。应该指出的是,在这种语言暴力形态的背后的建造之中,实际上还有一种苦难意识。
由此观之,底层民众思想观念所背负的意识批判仍然需要进一步延展强化,这既要求敢于抵抗当下时代环境所规定的种种生产模式及其滋生的价值观念,更要从文化心理的维度上进行彻底的反思。与此同时,这也是一场新的思想启蒙,需要有冲决罗网式的勇气和经历一场漫长的历史过渡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