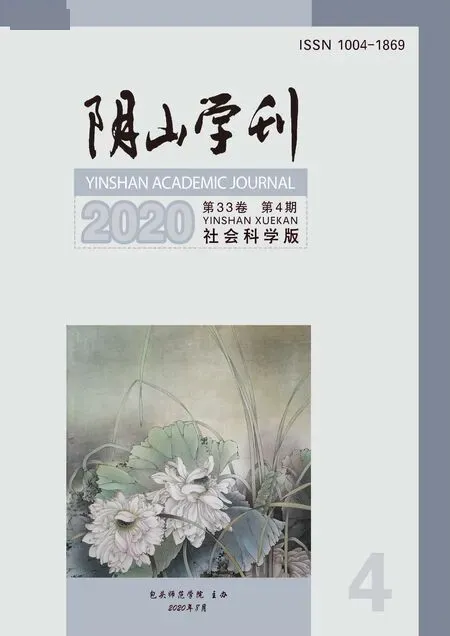严虞惇《读诗质疑》研究
2020-02-20冉金娥
冉 金 娥
(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诗经》在当代首先被作为文学总集而加以研究,而近年来经学研究的再次兴起使它被重新审视。《诗经》在历代的注疏成为《诗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注疏本身与时代学术的关系、在《诗经》学内部的地位、对《诗经》的阐发是研究所要探究的主要问题。以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宋代以前的《诗经》学研究的焦点是《毛诗注疏》,宋代《诗经》学研究最耀眼的是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其余涉及王安石、苏辙、吕祖谦、严粲等。元代除了朱熹《诗集传》盛极一时外,“《诗》学著作较少,《四库全书》收录的仅有七家:许谦、刘瑾、梁益、朱公迁、朱倬、刘玉汝、梁寅”[1]411。明代诗经学早期以朱熹《诗集传》为主,胡广编撰的《诗经大全》促使朱学成为主流;中期兴复古之风,成为清代诗学复宗毛、郑之渊源之一;晚期《诗》学为科举所用,形式僵化。[1]421清代经学注重训诂,出现了陈启源、段玉裁、陈奂、马瑞臣等名家,在名物研究、制度研究、天文研究、地理研究等专题研究方面成果突出。明末清初正是由“《诗经》宋学”逐渐过渡到“《诗经》清学”的时期,是学术转变的时期,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无疑会加深我们对学术演变的内在理路的认识。
明末清初以《诗经》名家的人不多,严虞惇是其中之一。其《诗经》学著作《读诗质疑》无论是篇幅还是体例都吸引着笔者。正如文学史是由突出的几位大家加上无数小作家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学体系一样,《读诗质疑》不仅本身具有研究价值,而且作为《诗经》学史上由明中后期到清前期的宋学式微到清学逐渐形成的重要一环,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四库》馆臣评《读诗质疑》曰:“大致皆平心静气,玩味研求,于毛、朱两家择长弃短,非惟不存门户之心,亦并不涉调停之见,核其所得,乃较诸家为多焉”[2]134,可谓好评。但馆臣又云:“大旨以《小序》为宗,而参以《集传》,其从《序》者十之七八,从《集传》者十之二三”[2]134,即馆臣又认为其汉学重于宋学。众所周知,《四库提要》有汉学倾向,而馆臣对有汉学倾向的《读诗质疑》给予好评,就让我们心生疑窦:一是馆臣对《读诗质疑》汉学重于宋学的判断是不是实情,二是馆臣对《读诗质疑》“其所得较诸家为多”的评语是否恰当。这也促使我们探究《读诗质疑》。
一、严虞惇的生平与《读诗质疑》的创作
严虞惇(1650—1713),字宝成,号思庵,江苏常熟人,生于顺治庚寅五月二日,卒于康熙癸巳三月二日,享年六十四岁。或云“一字思庵”[3]294。严虞惇学习佛法,以僧人为师,其《题苏州半塘寺血书〈华严经〉后》云“思庵居士严虞惇法名开良敬书”[3]264,可知思庵为虞惇之号。虞惇高祖讷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曾祖泽为中书舍人;祖栻为崇祯年间进士;父熊,著有《严白云诗集》。严氏大抵以诗书传家,故虞惇自少得以读经研史。严虞惇“入籍华亭,补博士弟子”[3]295,此时已声名甚著。丁卯年(1687年)中副车,入京师,昆山徐健庵招之预修《明史》,丁丑年(1697年)高中。严虞惇以家世得康熙拔擢,据《墓表》云:“殿试日,京江相国张文贞公读卷,以第三人进呈,而长州大宗伯韩公复奏先生家世籍贯,上亦素闻先生名”[3]295,遂以之为榜眼,授职编修。虞惇擅长古文,故当时馆阁文字多出其手,颇受重视。己卯(1699年)科考,其次子严密、从子严亨裔中于北闱,两主司皆严虞惇同年,遭受非议,官镌二级。
康熙南巡,严虞惇受到诏对,是岁之冬起补国子监丞,又转为大理寺寺副。其任寺副期间尽职尽责,不畏权贵。“有徐天荣者,馆内务府二格家。二格杀人而欲蔽其罪于徐,徐力不能脱,又口吃无以自明,已定谳矣。先生独心疑其冤,时方移疾且秩满,或劝先生稍缓即量移,此事勿与也。先生不听,力疾起视事。密擒二格讯之,二格服辜,天荣得释。”[3]295此事影响甚大,京师内外“咸惊叹以为神”,因此事得罪权贵,虞惇并未得到升迁。其《与沈位山书》云:“仆自少有此志,欲作一亲民之官,好作条教,少立名迹”[3]261,但是现在“向背俱触,不得不杀人、诈人以媚人矣。”[3]261可见其官场不如意,内心亦极痛苦。严虞惇毕竟受到康熙赏识,曾在两月之内三迁其官,由鸿胪寺少卿转通政司右参议,又迁太仆寺少卿。又曾掌四川、湖广乡试,于湖广乡试出闱未十日而卒。
严虞惇仕途不达,故倾心著作。有《文献通考详节》二十四卷,有未成卷帙的《易经》及《通鉴提要》。又《严太仆先生集》十二卷,杨绳武评价其文章曰:“制义既已风行海内,衣被后学,而古文辞尤度越于俗,卓然名其家”[3]296,甚至将其与明代归有光相提并论。严虞惇深指其时学风之弊,学者所习之经大多为割截之作,因此总结前代之作,著成《读诗质疑》三十余卷、附录十五卷,凡六易稿始定。该书主要有严有禧刊本和《四库全书》本。
“经经纬史”是严虞惇创作《读诗质疑》的重要指导思想。经、史作为中国两大因源颇深的显学,其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经史未分,汉代出现大量的史学著作,但从《七略》来看,史学并没有类目,直到《中经》《晋中经簿》单独分出其类,《隋书·经籍志》正式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定型,随着目录学四部定型,可以看出史学地位越来越高,但是尽管史学著作庞大,其地位仍居于经学之下。清初,史学进入了大总结时期,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史学影响巨大。严虞惇在《读诗质疑》中大量引用史学著作进行论证,据笔者统计引用《史记》达六十余次,《汉书》《后汉书》共一百六十余次,达到以史证经的目的。严虞惇主持乡闱,曾自述其选材标准云:
臣惟人才之淑系文章之高下,而文章之高下系取士之贤否……,取实学不取虚声也,取才地不取门阀也,取寒畯不取势家富族也。又其甄别也必明,理取正大不取险僻,词取典雅不取纤缛也,气取宏达不取卑琐庸弱也。[3]238
因此要“示之以经经纬史之法”[3]237。他认为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辞胜,经、史各有其特点,但其功用面向是一致的:经世致用。科举之弊,“自近世妄庸者,流专之务速化之术,盖束经史于高阁,而奉坊刻程墨试牍为圣书,其所习之一经亦大率割截,记诵剽贼而已,不复能究其全”[3]241。把经当作进入仕途的工具,无疑损害了经的神圣性,也削弱了经的实用性。这也是严虞惇强调经史文章及经世致用的现实原因。
二、《读诗质疑》卷首内容与其解经体例
严虞惇《读诗质疑》分为两部分,卷首十五卷,正文三十一卷。卷首十五卷为此书纲领,为严虞惇对《诗经》基本问题之见解,故择其可观者述之于下,并略言其与前代著作之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首为《列国世谱》,次《国风世表》,次《诗指举要》,次《读诗纲领》,次《删次》,次《六义》,次《大小序》,次《诗乐》,次《章句音韵》,次《诂训传授》,次《经传逸诗》,次《三家遗说》,次《经传杂说》,次《诗韵正音》,次《经文考异》,每一类为一卷,皆附录编首,不入卷数。其正经则《国风》为十五卷,《小雅》为八卷,《大雅》为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颂》为五卷。[2]134
所谓《列国世谱》即周、卫、郑、齐、魏、唐、秦、陈、桧、曹、鲁、商之继承世系。各国排列次序与《诗经》次序相同,略述其王位之继承与国运兴衰。唯魏国世次无考,略断其诗当在平恒之间;桧亦世次无考,诗当在厉、幽之间。《国风世表》即《诗经·国风》之系代,大部分从《诗序》之说。《诗指举要》即各诗之解题,大抵依据《诗序》,参以毛《传》、郑《笺》、朱《注》,取一说而注明异同。如《绵蛮》“大臣遗忘微贱,《注》异”[4]70,又如《白华》“下国弃妻自伤,《传》《笺》《注》小异”[4]70。《读诗纲领》即摘录《尚书》《论语》《孟子》等书论《诗》的言语,另加按语阐发之。按语详略不一,或考证,或阐发,可见其治《诗》之一端。如引《尚书》之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其按语云:
经典言诗,无先于此者。《吕氏春秋》云“葛天氏歌八阕”;《隋·乐志》云“伏羲有网罟之咏”;《楚辞·大招》云“伏羲驾辨”,注云“伏羲作琴,始造此曲”也;夏侯玄《辨乐论》又云神农有《丰年》之歌,然皆不见于经。惟“帝庸作歌”,皋陶“赓载”,见于《虞书》;“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见于《礼记》;而《家语》亦云“舜造《南风》之诗”,是则五帝以前已有歌曲,而不名诗。诗之名盖自唐虞始矣。[4]73
严虞惇此按语主要论证唐虞前歌、诗合一,歌之名早而诗之名迟,在唐虞时始有诗之名。
其《删次》论诗歌次第,《诗乐》则言诗与音乐之关系,《诂训传授》主要论四家诗传授源流,《经传逸诗》则辑录诸书所见逸诗,《三家遗说》则勾稽齐鲁韩三家诗论以备采纳。《经传杂说》则是广辑群书,凡用《诗》引《诗》有可观者,皆采录以备一说。《经文考异》则广录《诗经》异文,以备训诂之用。此皆研究《诗经》之基本工作,对习《诗》者而言,亦是入门之道,故列之于首。此亦渊源有自。朱熹《诗集传》前有《诗传纲领》,严虞惇《读诗纲领》与之略同,而朱熹取宋人说多,严虞惇于宋人一条未取。元刘瑾《诗传通释》卷首有《列国世次图》《诗源流》《诗乐》《删次》。《列国世次图》只列主王公名,依次排列,比《列国世谱》简单,其余与严虞惇之《诗乐》《删次》亦大略相同。而严虞惇《诗韵正音》《章句音韵》意在反对朱熹叶韵说,《诂训传授》《经传逸诗》《三家遗说》《经传杂说》则意在表彰汉唐先儒之《诗》说。盖天水以后,宋学天下,《诂训传授》《经传逸诗》等标目乃严虞惇有意表彰汉学使然。故其研究《诗经》之法虽沿袭宋元,然其倾向已在汉学。
读经不可不明其体例。《读诗质疑》按语云:
自孔子删诗,而后遭秦灭学,六义散亡。汉兴,至于孝文,《诗》始萌芽。建元之间分为四,齐、鲁、韩、毛各仞师说。其后毛氏孤行,三家渐亡,郑《笺》、孔《疏》递相祖述。宋朱熹《集注》出而毛、郑空存,无有习其读而问其传者,盖汉唐儒者穷经之学至是而尽废。然而残编蠧简、遗文杂记往往而在,未必尽泯没于士大夫之口。故余于三家之说既略为掇拾,复旁采经传杂说别为一编以附其后,使学者知朱子之外未尝无毛、郑,毛、郑之外未尝无三家,而三家、毛、郑、孔、朱之外,又未尝无汉唐宋元诸儒之说,于以广异闻、扶微学。《传》不云乎“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小子何莫学夫《诗》”,其以是编为博依可矣。[4]135
依著者之意,《读诗质疑》于三家、毛、郑、孔、朱之外,博采汉唐宋元诸儒之说,以扶继微学。如此,此书乃集注或集解体。据笔者统计,《读诗质疑》全书引用前人解《诗》之说三十余种,又杂采经史及其他著述五十余种,上至先秦,下至与之同时代之钱澄之,确属集注之体。严虞惇名之曰“质疑”,谦辞而已。严虞惇引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近五十次,其体例亦继承之[5]67,举一例以明之: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兴也。孔氏曰:参差,不齐也。毛《传》:荇,接余也。郑《笺》:左右,助也。毛《传》:流,求也。寤,觉。寐,寝也。朱《注》:服,犹怀也。王氏曰:悠者,思之长也。郑《笺》:卧而不周曰“辗”。朱《注》:“辗”者“转”之半,“转”者“辗”之周,“反”者“辗”之过,“侧”者“转”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毛《传》:后妃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郑《笺》:后妃将共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是以觉寐之中常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己职也。[4]169
严虞惇解诗先引诸家之说以疏通训诂,训诂之后诠释大意,之后若有补充辨明必以“虞惇按”三字标出。解释依正文次序,故一家之说前后分割,殊感繁复。
三、严虞惇《读诗质疑》之见解
严虞惇此书有自己的见解,且兼采古今数家之长。这首先体现在对《诗经》韵例的讨论。《诗经》用韵,自有韵例。严虞惇认为“诗无不用韵,而用韵之法,古今不同,古韵宽而今韵严”[4]106,不能以今韵论古韵。认为“诗人用韵,错综不同。如熊氏及二顾氏之说,略见大端”[4]105,熊氏即熊朋来,其论《诗经》用韵云:
《赓歌》,虞诗也,每句有韵。《五子之歌》,夏诗也,隔句有韵,其四章两韵一换。《商颂》,商人之诗也,诗韵之例,尽在是矣。《那》之首章隔句用韵,两韵一换,至“绥我思成”下,又每句有韵,篇末别出尝、将二韵结之。《烈祖》以祖、祜、所三韵起,中间“申锡无疆”开下文连句之韵,似以三“无疆”为之节,后人交互用韵始此。《商颂》多每句用韵,《玄鸟》《长发》《殷武》皆然。《玄鸟》六换韵,《长发》前六章皆每句有韵,惟卒章两韵一换。《殷武》每句有韵,惟第四章交互相韵,其末别出国、福二韵结之,五章以翼、极二韵起,而下文连句有韵,卒章又通章连句用韵。自后作诗者,用韵皆以《商颂》为格例。[4]105
熊朋来的观点可归纳为句句韵、隔句韵、换韵、交韵四种,并且认为代表不同时代的诗歌。顾大韶又提出末句不入韵、首二句不入韵、有首句与末句押韵而中二句押韵、有通章不押韵的《诗经》用韵方式。顾炎武进一步归纳为三种用韵方法: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末句用韵、句句韵、上下各自为韵(换韵),并认为上下各自为韵为《诗》之变格。
严虞惇在赞同熊朋来及二顾氏所阐明用韵之例外,又加以补充,云:
此外更有一句中自为韵,如《柏舟》“日居月诸”,《北风》“其虚其邪”,《商颂》“猗与那与”之类。有一句两韵,二句中各自为韵,如《匏有苦叶》之次章,弥与鷕韵、盈与鸣韵之类。有三句一韵,如《采芑》前三章之类。亦有三句一韵,而三句中又叠用韵,如《采芑》二章、三章、后六句之类。有上下总一韵,而中间复自为韵,如《大雅·思齐》二章之类。有下三句各与上三句为韵,如《桑柔》卒章之类,《麟趾》《驺虞》末句不用韵,而合三章为韵,《瞻彼洛矣》起句不用韵,而合三章为韵。更有后三章复承前三章为韵,如《鱼丽》之类。更有合全篇为一韵,如《泂酌》三章之类。皆变化因心,自然合节,《乐记》所谓“声成文谓之音”,举一反三可以类推也。[4]106
“有一句两韵,二句中各自为韵”,所用《匏有苦叶》之例乃是元戴侗之说。“一句中自为韵”,以所举《柏舟》《北风》之例言,即四句诗中首句第二四字自为韵。“三句中又叠用韵”其实就是换韵。其后所论大致皆可归入熊氏及二顾氏所论之中,不同者乃是严虞惇所举皆三句一韵或三章为韵。
严虞惇极力批评叶韵说。时有更革,音有转移,《诗经》古韵以今音读之,多有不叶,后世遂创叶韵之说。宋吴才老《韵补》之叶韵为朱熹《诗集传》所用,后人颇有遵之者。明杨慎已论其失,陈第《毛诗古音考》深掘其非,顾炎武《诗本音》又“主陈第诗无叶韵之说”而正古音韵读,叶韵之论自后不信于人。严虞惇云:“朱子泥于今韵,遂创为叶韵之法。凡诗之不合于今韵者,俱从而叶之,就其所叶之韵亦多有未可通者。”[4]106又云:“古人四声通用,诗为乐歌,抑扬抗坠,本自相协,不必强而叶之。朱子《诗集注》几于无句不叶,殊失声”[4]107,又云:“朱子于诗多用叶韵,大约本吴棫才老《韵补》,然其中舛误弘多”[4]184。对朱熹《诗集传》叶韵之说又以“不可晓”批评之。如“否,房以反。友音以。《集注》子、否、友俱从叶,不可晓。”[4]216又如“母,满以反。有音以。不从叶。《集注》一章俱叶,不可晓。”又总纳前人之说,论叶韵之非者四:
有韵本通而亦叶者,如《葛覃》之萋、飞、喈,《卷耳》之嵬、隤、垒、怀是也;有本同一韵而亦叶者,如《殷其雷》之侧、息,《卷耳》之筐、行,《麟之趾》之趾、子是也。亦有不宜叶而叶者,如《旄邱》“叔兮伯兮”之伯,《小戎》“骐骝是中”之中、“秩秩徳音”之音是也;亦有同一字而一章叶两音者,如《驺虞》之“于嗟乎驺虞”,《行露》之“谁谓女无家”是也。[4]184
严虞惇进而“于朱子之不必叶而叶者,概从删削,以省学者支离烦碎之病”[4]184。于诗句之下必标“不从叶”“不必叶”。“不从叶”者,如《关雎》第二章注云:“友,古音以,后并同。采,今贿韵,与友通,不从叶。”[4]169又如《草虫》首章注云:“降,古户工反,后并同,不从叶。”[4]187此皆同韵者,故“不从叶”。“不必叶”者,如《鹊巢》首章注云:“居、御,平去通韵,不必叶。”[4]284又如“佩,队韵;思,支韵;来,灰韵。平去通韵,不必叶。”[4]186此皆属四声通用者,虽音调不同,亦可同韵,故“不必叶”。
严虞惇所定音韵,辨择诸家,间有考证。取王应麟、杨慎、陈第等诸家之说,而“顾炎武《诗本音》极论古音通用、四声通用之说”更为严虞惇所崇奉,故“略采其说”,“更以鄙见参之”。[4]185其考证,如《新台》“籧篨不鲜”之“鲜”,古音“犀”,按语云:
《汉书·匈奴传》“黄金犀毗一”,师古曰“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尔雅·释畜》疏引魏时“西卑献千里马”,西卑即鲜卑也。《诗》“有兔斯首”,《笺》云:“斯,白也。今俗语‘斯白’之字(一作斯)作鲜,齐鲁之间声近斯。”《尚书大传》“西方者何?鲜方也。”[4]523
犀毗、鲜卑同是一物,故鲜、犀同音。又有西卑即鲜卑,亦可证西、鲜音同。又引郑《笺》《尚书大传》旁证,殆无疑议。吴玉搢《别雅》云:“西有先音,历历可证,故西施亦称先施也。至西之所以得与先通,则其理不可考矣。”[6]亦可旁证鲜、犀同音。严虞惇发明《诗经》韵例,不信叶韵,虽沿袭多而考证少,然亦不为无取也。自明兴考订之风[7],清儒延宕其波,虞惇有与焉。
严虞惇对《诗经》的赋、比、兴也有自己的见解。对于赋、比、兴在《诗经》中的具体运用,严虞惇主要是以朱熹对赋、比、兴的认识为基础的。其一便是对于赋的判断,严虞惇主要从朱熹纠正汉儒之说,其云:“‘手如柔荑’‘如山如阜’,既谓之‘如’,则赋矣,非比也。汉儒多以此类为比,黄氏亦沿汉儒之误,此义至朱子而后明。”[4]86他认为“既谓之‘如’”这一类,汉儒把《诗经》中“赋”误判为“比”,当以朱熹之说纠正。但严虞惇并不是对朱熹所判为赋的具体结论都一概从之,而是有所辨证,比如:
朱子于《衡门》《蒹葭》皆谓之赋,而《匏有苦叶》之三章亦谓之赋,不知《衡门》《蒹葭》乃借彼以喻此,而“雝雝鸣雁”是即小以讽大,非赋也。《周南》之《螽斯》、《卫》之《有狐》、《曹》之《蜉蝣》、《齐》之《甫田》,朱子以为通篇皆比而不正言其事。《郐》之《隰有苌楚》则注虽曰赋,而以乐子之子指苌楚,是亦通篇皆比,而不正言其事矣。窃思狐与苌楚不可以言子,螽斯不可以言尔,忧《有狐》之无衣裳,乐《苌楚》之无家室,《螽斯》则美其子孙,《蜉蝣》则欲其归,说不惟诗义全失,而文理亦未可通。《甫田》正兴思远人,而概以为比,则未知所比者何事。他如“厌浥行露”比女子之守,而直以为赋;“凯风自南”兴母氏之劬劳,而混以为比。如此之类,舛误弘多,未敢时然亦然而曲狥之也。[4]86
其实他的意见主要是汉儒“赋”误判为“比”当以朱熹之说纠正,而朱熹又有以“比”为“赋”的,则严虞惇纠正之。
严虞惇延续朱熹赋、比、兴兼义的理论,认为《诗经》中每一首诗以及每一句不能被截然划分为赋、比、兴,其云:
《集注》亦有赋而兴也、兴而比也、赋而兴又比也之例,然其所云乃是一章之中,既赋复兴,既兴复比,如《小弁》之“君子信谗”“莫高匪山”,《巧言》之“奕奕寝庙”及《汉广》三章、《椒聊》三章、《頍弁》三章之类,非谓一句中赋而兼兴,兴而兼比者也。间有赋其事以起兴,如“彼黍离离”“溱与洧”“野有蔓草”之类,亦云赋而兴也,此则朱子之变例,通经唯三四见而已。六义虽有赋、比、兴之分,然亦难截然判隔,往往赋之中有兴,兴之中有比。今所云赋也、兴也、比也,亦止据章首二句为言。其实一章之中或比、或兴,一句之中有兴、有比,不能尽拘,必欲判何句属兴、何句属比,亦未免蹈“固哉高子”之讥,读者以意逆志,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得之矣。[4]174
朱熹突破汉儒说《诗》每一首只有一体的看法,认为“一章之中,既赋复兴,既兴复比”。严虞惇沿袭朱熹的意见,进而认为不仅一章之中赋、比、兴可以兼有,而且“一句之中有兴、有比”,亦“不能尽拘”。
严虞惇在此思路之下,又着重讨论了比、兴兼义的问题,他认为:
比之与兴,义本相通。然有兴可通比者,有兴不可通比者。《关雎》《桃夭》,兴也。而《雎鸠》之和鸣,《桃夭》之少盛,亦为比,此兴之通比者也。《葛覃》之因时感事,《殷雷》之触景怀人,兴也。以葛覃喻形体浸长,以殷雷喻号令四方,误以为比则失之,此兴之不兼比者也。兴之兼比,而比轻于兴者,则直谓之兴,《关雎》《桃夭》之类是也。兴之兼比,兴意多,而比亦不可略者,则谓之兴而比,或谓之比而兴,《螽斯》《摽有梅》之类是也。亦有即以所赋之物为兴,所举之事为比者,谓之赋而兴,赋而比,《葛覃》《兔罝》《北门》之类是也。以物比事,而事在言外,谓之比,则“厌浥行露”不得谓之赋,“园有桃”不得谓之兴。以物起事,而事在下文,谓之兴,则“喓喓草虫”不得谓之赋,“凯风自南”不得谓之比。[4]87
兴兼比,“则谓之兴而比,或谓之比而兴”,不可认为“比而兴”是比为主,兴为次。严虞惇认为比不可兼兴,《关雎》之按语云:“此诗以雎鸠兴淑女,故毛公《传》曰‘兴’,而朱子从之,其实兴之中有比,雎鸠之挚而有别,即比也。兴中有比,而兴之意多于比,故仍以兴表之,所谓兴可兼比,比不可兼兴者也。”[4]174《关雎》之按语以毛《传》为主、朱熹次之,“兴中有比,而兴之意多于比,故仍以兴表之”以弥合自己与毛、朱之分歧,“兴可兼比”之论亦有牵强古人之嫌。此种看法实际上削弱了兴独立存在的意义。严虞惇认为“大抵毛、郑于比、兴求之过深,而朱熹于比、兴取之太简,毛、郑多以比为兴,朱子多以兴为赋,学者当知所别择云。”[4]87表明自己在赋、比、兴判定上对汉宋皆有所批评,取汉宋之间而成己说也。
严虞惇全面反对朱熹“淫诗说”。朱熹以《风雨》为淫奔之诗,《子衿》“亦辞气儇薄”,严虞惇认为此乃“说《诗》而以辞害志”,并且说道“愚之于朱子不敢以苟同者如此”。[4]284严虞惇曾推测朱熹“淫诗说”之由来,云:
朱《注》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不翅七之五。今按:《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风雨》《出其东门》《子衿》《扬之水》皆各指一事,而注皆以为淫奔之诗。《东门之墠》《溱洧》皆刺淫之诗,而注皆以为淫奔者所自作。盖其意泥于“郑声淫”之一言,遂若郑国之俗,无一人之不淫,而郑国之诗无一篇不为淫奔而作者,恐亦不免于“固哉高子”之为诗也。[4]288
严虞惇将朱熹所定“淫诗”分为两类,一是有本事与“淫”无关者,二是与“淫”相关的刺淫之诗,否定了朱熹“淫诗”的判定。
朱熹提出淫诗二十四,而王柏扩充至三十二,并主张删淫诗。严虞惇极力反对,云:
鲁斋王柏氏祖述朱子之说,既以《郑》《卫风》为淫奔之诗,而又以圣人明言“放郑声”,决无存淫奔之诗之理,于是谓秦人焚书之后,《诗》决不能独全。夫子删去之诗,容有存于闾巷浮薄之口者,汉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撺杂之,以足三百之数,莫若尽举而削去之。《召南》之《野有死麕》……共三十有二篇,皆王氏之所削也。窃意六经经圣人手定,学者即有所疑,亦当谨而存之,以附于不知而阙之义,何乃公肆狂悖,奋笔刊削,自用自专,“非圣无法”斯之谓矣。[4]289
《四库全书总目》对王柏删淫诗之看法与严虞惇极其相似。
二者皆反对王柏删淫诗的做法。而且通过文字的对比,二者如此雷同,《诗疑》提要或是取自严虞惇之论也。
严虞惇反对朱熹“淫诗”说主要是根据《诗序》,因此反对“淫诗说”的同时重申《诗序》之说。其云:
虞惇按:朱子以《论语》有“郑声淫”之语,故于郑国风大半以为淫诗,如此诗(《将仲子》)引莆田郑氏曰“此淫奔者之辞也”。今按《春秋传》,郑伯为卫侯故如晋,子展赋“将仲子兮”;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齹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此六诗,朱子皆以为淫奔之诗,而当时皆见美于叔向、赵孟、韩宣子。而伯有赋《鹑之奔奔》,则赵孟讥之,以为床笫之言不踰阈。则知淫诗固不可赋于宴飨之时,而此六诗绝非淫奔之诗也,然则小《序》之言信矣。[4]272
严虞惇以史事证小《序》,反对“淫诗”,并且自为设辞为自己辩证以驳斥朱熹,其云:
或曰:“文公之说谓《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事变之实而垂鉴于后世,故不得已而存之于诗,亦犹是也。”愚以为不然。夫《春秋》,史也。《诗》,文辞也。史所以记事,固不容存禹、汤而废桀、纣,录文、武而弃幽、厉也。至于文辞,则其淫哇不经者直削之而已,而夫子犹存之,则必其意不出于此,而《序》者之说是也。[4]94
驳斥之结果还是在以《序》为主。
严虞惇主张以《序》为主的另一个理由是此乃孔子删后之诗,不是“淫诗”,其云:
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指为男女淫奔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篇。《桑中》《东门之墠》《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序》以为刺淫。《狡童》《褰裳》“子之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为放荡无耻之辞,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4]94
其实,主要是朱熹反对“刺”,严虞惇则主张《诗序》美刺之说。《野有蔓草》之序未云“刺乱”,而云“思遇时也”,即表明此乃男女情诗,依古人道德,自是“淫诗”。而严虞惇为反对朱熹之说,辩解道: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犹未至于淫奔也,故序不曰刺乱。从《序》之首句云“刺乱”的还有《大东》《绵蛮》。
至于《丰》究竟是“刺”还是“本别指他事”,严虞惇自己的观点并未一贯。其《郑风·出其东门》按语云:
《郑风》刺乱之诗,《丰》《东门之墠》《出其东门》《溱洧》,凡四篇。此篇《序》云“闵乱也”,余三篇皆曰“刺乱也”。所谓“乱”者,乃淫乱之乱,非丧乱也。故班固《地理志》引此诗“出其东门,有女如云”,以为男女聚会之证,后世讲师不达此旨,误以为闵丧乱,遂附益兵革不息、民人相弃、思保其室家等语,于是全诗之义俱失。凡此类,皆当以《序》之首句为定,余俱削之可也。[4]286
他认为《丰》应与《出其东门》《溱洧》等为一类,是“刺”,而前面之观点云《丰》与《风雨》《子衿》等为一类“本别指他事”。其余,如认为《氓》乃“刺时”之诗,又以为“正刺淫佚也”,大致如此。严虞惇认为当“以《序》之首句为定”[4]282,朱熹认为“直谓序之首句已不得诗人之本意”[4]97,故而严虞惇批评朱熹“肆为妄说”,“未敢以为信然矣。”[4]97从明代中期以后,主张《序》说,反对朱熹“淫诗”说的人不在少数,因此这并不是严虞惇的个人创见或者独特主张。只不过,在清代走向汉学的途中,严虞惇此举正是预学术之流。至于其以史事论诗及夫子删诗的证明方法亦是承自前人。四库馆臣认为其“从《序》者十之七八,从《集传》者十之二三”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但“其所得较诸家为多”恐怕有溢美之嫌。
四、《读诗质疑》之缺点
严虞惇《读诗质疑》未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读诗质疑》本身存在缺点。《读诗质疑》的缺点之一就是信伪造之《申培诗说》。四库馆臣批评云:“《申培诗说》出自丰坊,其中多剽朱《传》之义,而虞惇反谓朱《传》多引申培,亦殊失考。”[2]134严虞惇并非不知道《申公诗说》出于伪造,其云:“《申公诗说》盖出于后人伪撰。”[4]124又云:“今世所传《申培公诗说》盖后人伪托也。”[4]112又云:“《子贡诗传》《申公诗说》皆后人伪撰。”[4]176但他同时认为“其流传既久,其间亦有足与《序》相发明者,朱熹《集注》多采用申说,故亦间录其一二”[4]176,盖以为伪造之时尚在朱熹之前,其实它不过是明代的产物。“与《序》相发明”,亦可见严虞惇倾向汉学之态度,此盖误判之因由。
《读诗质疑》常取《申培诗说》羽翼汉学。如《北门》,《序》云:“刺仕不得志也”[4]225。其引之云:“《申公说》:之仕者,处危国事乱君,因征役而出北门,赋之以自叹。”[4]225以相发明。又如《鹑之奔奔》,“刺卫宣姜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若也”[4]238。《申公诗说》云:“刺宣姜与公子顽之诗”[4]238,其又引之。如此者不下二三十处。还有阐明者,如《还》之按语云:“《申公说》:‘齐俗好田,君子刺之,而其篇名谓之营,营,营邱也。’盖指其通国之俗而言也。”[4]293严虞惇以“盖指其通国之俗而言”阐明“齐俗好田”。严虞惇对《申公诗说》亦有直接批评。比如《申公诗说》“文王闻太颠、闳天、散宜生皆贤人而举之,《国史》咏其事而美之”[4]180,严虞惇批评其为附会之语。又比如《隰有苌楚》之按语云:“朱《注》: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叹不如草木之无知,盖本《申培说》也;又云……皆未可通,今取吕氏说。”[4]335因为严虞惇本身的出发点是“与《序》相发明”,且抛开他对史实的错误判断,就《申培诗说》本身来说,它亦是解《诗》者的一家之言,当有可取之处。因此信伪造之《申培诗说》对《读诗质疑》来说,只是产生了史实的错误判断,即诸说先后继承关系的错误判断,对严虞惇解说《诗经》的理论及方法并没有多大影响,但是这确实成了《读诗质疑》的缺点。
《读诗质疑》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缺点是略名物训诂。虽然上文提及其《读诗质疑》有所考辨,但总体而言,基本上还是沿袭多而考证少。比如解释《关雎》之“雎鸠”,严虞惇云:“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4]347此系朱熹之“雎鸠,王雎,鸟之挚者也。物之挚者不淫。”[8]朱熹于名物训解从略,后人补其不足,云:“雎鸠,水鸟,一名王雎,状类凫鹥,今江淮之间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9]74以“王雎”释“雎鸠”,依然不知“雎鸠”为何物,后人补注则知其类属、形状、情性。此可见严虞惇所释之语甚为简略。又比如《螽斯》。螽斯,严虞惇引毛《传》云:“螽斯,蚣蝑也”[4]167,又引苏氏之言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4]167。然于螽斯之情貌不置一言。《诗集传名物钞音释纂辑》释“螽斯”云:“螽斯,蝗属,长而青,长角长股,能以股相切作声,一生九十九子。”[9]79严虞惇所引或不如《诗集传名物钞音释纂辑》,而且琐碎。又“九十九子”与“八十一子”数目不同,数目不同要皆言其多,非为一定数值,而严虞惇亦无一语及之。
至于词语之训诂,严虞惇亦多承前人。比如“具赘卒荒”(《柔桑》)承毛《传》之说,云:“赘,属。荒,虚也”[4]607。“我居圉卒荒”(《召旻》),引苏氏之说曰:“居,国中也。圉,边陲也”[4]633,又引郑《笺》云:“荒,虚也”[4]633。于省吾用训诂学的方法,得出“具赘卒荒”即“具敖卒荒”,“我居圉卒荒”即“我具吴卒荒”。“具吴”即“具赘”,为娱乐之意。“荒”与“幠”通,“幠”与“敖”在《大戴礼记》为对文,意思相近。“具敖卒荒”言“国人俱敖戏而尽荒乐”,并且批评“《传》《笺》曲为系属荒虚边陲之训,词乖意舛”[10]。于省吾之说较为合理,严虞惇并未考订。
引文出处混乱也是其缺点之一。严虞惇引用前人解《诗》之说,除毛《传》、郑《笺》、孔《疏》、朱《注》外,其余于文中皆只标“某氏曰”。一般而言,首次出现皆出全称,而严虞惇皆只标“某氏”,不标其全称。书前亦无引用诸家之列表,故于行文之中极易混淆,不便阅读。比如严虞惇引朱氏一百三十五条之多,此朱氏非一人。其一为《诗传遗说》之作者朱鉴。其引文云:“朱氏曰:言才徳相合也。”[4]180《诗传遗说》作“言其才徳相合,处公侯腹心”。《读诗质疑》中又有一条为“朱氏曰:闻椓杙之声而视其人甚勇,可为干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见贤人之众多矣。”[4]179此条见于元人刘谨之《诗传通释》,又见于元人朱公迁之《诗经疏义》,言此乃朱熹之说,但不见于朱熹《诗集传》。又有一条云:“朱氏曰:卫首灭邶墉,故邶墉之诗皆为卫作,而犹存邶墉之名者,不与卫之灭国也。”[4]203此朱氏非前二者,乃《诗经疑问》之作者元人朱倬。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汉广》引文云:“朱氏曰:其幽闲贞静之度,见者自无狎昵之心,决知其不可求也。”[4]181此条转引自宋吕祖谦撰《吕氏家塾读诗记》。其原文为“朱氏曰:其幽间贞静之女,见者自无狎昵之心,决知其不可求也”[5]217。依《吕氏家塾读诗记》引用之例,朱氏指朱熹。盖严虞惇转引之文即依原书作“朱氏曰”,而所引之书多,所云“朱氏曰”于原书各有所指,集于《读诗质疑》却未加分辨,以致混淆难明,此其定例不严之过。严虞惇集数十年之力,删成此编,“以是编为博依”,盖为初学入门之用,但后学非遍览诸家,不知其“某氏”为何人。
总体而言,《读诗质疑》对宋元治《诗经》之法亦颇有继承,但主要倾向在汉学,而且,严虞惇反对朱熹叶韵说、“淫诗”说,主张《序》说,使其汉学倾向更加突出。严虞惇虽欲集前人之大成,但问题尚多,加之又不及乾嘉考据之精深,故不为后世所重,然其学术及学术史意义亦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