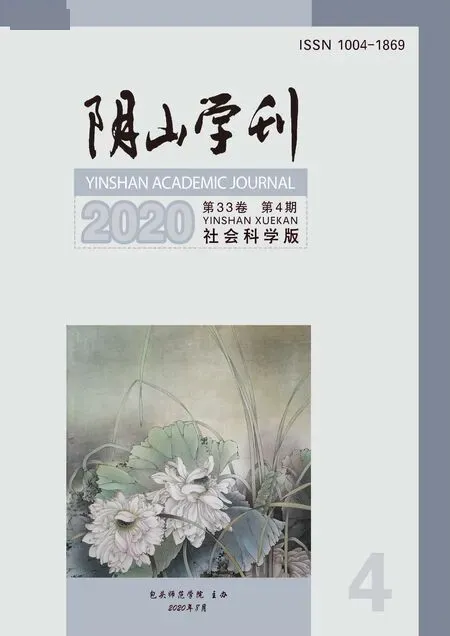林逋《山园小梅·其一》的传播与接受
2020-02-20陈莜烨
陈 莜 烨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林逋《山园小梅·其一》(以下简称《山园小梅》)为宋诗经典中经典。有研究者定量统计出《山园小梅》位列宋诗一百首经典篇目第二位,次于陆游《示儿》。[1]12宋元以降,对该诗篇研究述评者众多。学术界对这一诗作研究,暂停留于作品鉴赏、考证以及意义探寻上,涉及《山园小梅》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仅四篇:王骞博士论文《宋诗经典及其经典化研究》,较为客观地统计各个时代选本、评论纪事资料、网络链接等数据,将《山园小梅》归入“恒定型经典”,当代名次有所下滑;王玉立硕士论文《林逋诗作及其在日本的影响》,以及潘晓颖硕士论文《林和靖意象在日本文化中的流播与变异》,注重“跨国”研究,前者以《山园小梅》为中心,探讨五山文学诗作对此诗的引用、演绎[3],后者将《山园小梅》作为林逋意象四要素之一,介绍其在日本文化的发展与异变[3],此二篇打开了笔者视野;高燕《林逋〈山园小梅〉的被赞赏与被批判》,更多从诗歌批评角度,梳理历代诗话[4]。由于角度不同,这四篇论文都未专题研究《山园小梅》传播与接受,诗歌经典化路径全面性和深入性尚待挖掘。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选本、后人模仿、评论、跨体、跨国、跨学科等角度切入,研究该诗的传播路径与接受情况,并探究其广为流传的原因。
一
林逋诗歌传播有不同方式,如刊刻、传抄、选录、评论等。他作诗从不留存,随写随弃。但有宋以来,其诗歌经后人不断整理、刊刻,流传于世。据夏汉宁先生考证,北宋时其侄孙林大年将林逋诗歌编辑成集,且有刻本或抄本流传,在南宋时有过重刻本;明代刊刻较多,大致有正统间陈贽重编刻本、正德间韩士英刊刻本、万历间何养纯刻本、万历间潘是仁刊刻本、正德或嘉靖间林逋后裔刊刻本等;至清代刻本数量增加,林集刻本有康熙间吴调元刻本,同治间朱孔章刻本,乾隆间深柳读书堂刻本,汪安、汪定古香楼刻本等,晚清还有不少刻本流传。[5]
作品取舍与时代文学风尚、选者诗学主张、选本体例限制等有关,一定程度上选者青睐会推动经典传播。历代选者文学观念不同,心中的经典也不同。笔者从王骞博士论文《宋诗经典及其经典化研究》附录表一“选本数据来源书目”与附录表二“诗歌篇十大经典名篇原始选本数据”,粗略统计得《山园小梅》历代选本名目:宋代,选本有谢枋得《重定千家诗》、吕祖谦《宋文鉴》2种;元代,正统诗文不受重视,仅方回《瀛奎律髓》选录;明代,“诗必盛唐”论滥觞,宗唐者占据话语霸权地位,仅汤显祖《槐轩名家诗》选录;清代,融通唐宋,不拘一家,选本明显增多,有吴之振《宋诗钞》,邵暠《宋诗删》,陆次云《宋诗善鸣集》,汪景龙、姚壎《宋诗略》,侯廷铨《宋诗选粹》,许耀《宋诗三百首》,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宋诗别裁集》,章薇《历朝诗选简金集》,柴友诚《历朝古体近体诗笺评自知集》,朱梓、冷昌言《宋元明诗三百首》等10种;民国有陈衍《宋诗精华录》、陈幼璞《宋诗选》2种选本;到了近代,约65种以上,多数为中国文学史及诗歌鉴赏辞典。[1]264-279
当世人评价,是“原生态”评价,应充分重视。据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卷八记载,当时人称赞“疏影”一联“曲尽梅之体态”[6]。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记载了品诗者的高度赞誉:“评诗者谓:‘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7]周紫芝《竹坡诗话》曰:“林和靖赋《梅花诗》,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语,脍炙天下殆二百年。”[8]347可见,《山园小梅》在咏梅诗中获得高度的艺术地位,被视为梅花诗之“绝唱”,传播盛广。
后代和作诗多,如胡铨《和和靖八梅》直接以唱和诗形式制题。以诗为韵的,如赵时韶以“疏影”一联十四字逐字为韵作七绝组诗《山园小梅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十四诗》。吊挽作中提及《山园小梅》的,如朱彝尊《孤山拜林和靖墓》曰:“剩水残山悲往事,暗香疏影欲销魂”等[9]276。“暗香”“疏影”成为梅花代名词,如陈著《代弟茝咏梅画十景·古枝》曰:“惆怅西湖人不见,暗香依旧月黄昏。”[10]40138柳如是《次韵永兴寺看绿萼梅作》曰:“折赠可怜疏影好,低回应惜薄寒赊”等[9]275。后代文人也点化《山园小梅》诗意,如陆游《缃梅》曰:“疏影横斜事已非,小园日暮锁芳菲”等[11]1871。词作中亦有,如周邦彦《花犯·小石梅花》曰:“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12]晏几道《胡捣练》(小亭初报一枝梅)曰:“遥想玉溪风景,水漾横斜影”等[13]。可见,《山园小梅》的魅力永久不衰。
林逋咏梅诗数量虽不多,仅八首,但他对宋诗题材的开拓做出了贡献,开宋代梅花诗创作之先,带动咏梅题材创作风潮。而《山园小梅》咏梅范式也成为文人模仿、学习的对象。程杰先生《林逋咏梅在梅花审美认识史上的意义》总结了林逋发现梅花审美三大方面:枝影美,水、月、梅的组合和隐士心性咏梅。[14]林逋稍后的诗人也开始关注枝、影描写,如陆游《别梅》曰:“影横月处愁空绝,子满枝时事更非。”[11]1307范成大《再题瓶中梅花》曰:“园林疏落冻芳尘,南北枝间玉蕊皴。风袂挽香虽淡薄,月窗横影已精神”等[15]。也有模仿“水月衬梅”形式,如梅尧臣《依韵和正仲重台梅花》曰:“月光临更好,溪水照偏能。”[16]苏辙《次韵王适梅花》曰:“江梅似欲竞新年,照水窥林态愈妍。霜重清香浑欲滴,月明素质自生烟”等[17]。
模仿者虽众,但少有人能真正超过林逋,可见《山园小梅》艺术地位之高。方回《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曰:“和靖八梅未出,犹为易题。‘疏影’‘暗香’,一经此老之后,人难措手矣。近世诸人为梅诗,一切蹈袭,殊无佳语。甚者搜奇抉隐,组织千百,去梅愈远。”[18]811《山园小梅》,尤其是“疏影”一联,被历代不断模仿。一方面,催生了大量仿作,构成独特咏梅文化景观;另一方面,经典确立后,成为后人模拟对象,趋于模式化、程序化。南宋洪皓《江梅引·忆江梅》小序云:“如‘暗香’‘疏影’‘相思’等语,虽甚奇,经前人用者众,嫌其一律,故辄略之。”[19]新意落为俗套,阻滞文学发展,但不可将此过归于原创者。
二
在文学接受活动中,批评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作品价值进行再创造。《山园小梅》传播得益于“诗家多推崇之”[20]。黄彻《巩溪诗话》卷六曰:“西湖‘横斜’‘浮动’之句,屡为前辈击节。”[21]其中,欧阳修就激赏此句,许顗《彦周诗话》曰:“林和靖《梅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大为欧阳文忠公称赏。”[8]390《王直方诗话》卷九中还记载苏轼在宴会上对此诗的随性评点,认为“杏李花不敢承担”[22]。为何“疏影”句所咏的花卉一定是梅花,而不能是杏花、桃李花呢?梅花的香气与杏李花不同。它是浮动着的无形的“暗香”,尤其在“月黄昏”的朦胧视觉效果下,嗅觉感官被充分调动,轻微的若有若无的香气,可近而又不可玩。苏轼《红梅三首·其一》曰:“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23]这是针对石曼卿《红梅》中的“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10]2005而提。苏轼认为辨别梅与桃杏的关键非外在的绿叶、青枝,而是内在的气格。梅花孤傲独立的人格象征也是杏李花无法承载的。林逋可谓颇具写物之功,从形似上捕捉到梅花的独特处,同时又把握住梅花的内在精神。两代文坛盟主的高度评价加之轶闻趣事的广为流传,《山园小梅》也被更多读者所熟知。
历代学者对《山园小梅》的讨论,也推动了它的传播。评论多集中于“疏影”一联。称赏者多,如宋代张端义《贵耳集》视此联为“孤梅八首”之“绝唱”[24]。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曰:“恨不使唐人专咏之耳。”[25]清代爱新觉罗·弘历曰:“两句千古,谁不倾倒。”[26]至明代,才有人提及“疏影”一联并非林逋自创。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曰:“江为诗:‘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林君复改二字为‘疏影’‘暗香’以咏梅,遂成千古绝调。”[27]虽指出事实,但仍高度赞扬林逋用字贴切之功。竹子秀丽挺拔,与“横斜”的活泼矛盾;桂香浓郁扑鼻,与“浮动”所强调的隐约感冲突。林逋只改二字,以“疏”换“竹”,以“暗”换“桂”,贴切地写出梅的淡雅。“暗香”也成为梅花代称,凝结为梅花品格特征。该联终成千古绝唱,改写之妙使人忽视诗句的原创性。
不同批评家的诗学主张与标准不同,对诗歌的看法也就互异。在诸多赞赏声中,亦存少数异声。宋代逆主流之声者,如陈辅《陈辅之诗话》曰:“近似野蔷薇也。”[28]189但这种看法很快受到反驳,费衮《梁溪漫志》卷七曰:
陈辅之云:“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殆似野蔷薇。”是未为知诗者。予尝踏月水边,见梅影在地,疏瘦清绝,熟味此诗,真能与梅传神也。野蔷薇丛生,初无疏影,花阴散漫,乌得横斜也哉?[29]
到了明代,获李东阳“绝唱”之称,“恨不使唐人专咏之耳”[25]。但王世贞举盛唐高标,将此诗归入晚唐水平,认为是“许浑至语”,“非开元、大历人语”[30]。胡应麟是格调派诗学重要人物,他主张“格以代降”,评价此诗:“然其格卑,其调涩,其语苦,未足大方也。”[31]谢肇制曰:“《梅花》诗,‘暗香’‘疏影’两语,自是擅场,所微乏者,气格耳。”[32]褒贬不一的批评现象背后牵扯着唐宋诗之争这一更大的文学话题。但总的来看,称赏“疏影”一联者仍居主位。
对诗中的“黄昏”释义也有不同看法,如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上曰:
林和靖《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议者以“黄昏”难对“清浅”。杨升庵《丹铅续录》云:“黄昏,谓夜深香动月之黄而昏,非谓人定时也。”余意二说皆非,岂诗人之固哉?梅花诗往往多用“月落参横”字,但冬半黄昏时参横已见,至丁夜则西没矣。和靖得此意乎?[33]
到了当代,仍有学者讨论这个问题。郑绍昌认为“日黄昏”还不曾出现朦胧的月色,此时之月本身还是“落日余晖映照的对象”,林逋“绝不可能从日黄昏之月色中去研求”[34]。白灵阶以古典诗歌为例说明黄昏的时间以及双重含义,最后考证此为古典诗歌中的“月黄昏”,即“黄昏时朦胧的月色和月光”[35]。黄昏是昼与夜的分割界,暮色苍茫,月光朦胧,梅花少了白日的明艳,渲染出雅净的氛围。从诗歌意境角度而言,“月黄昏”解释为“黄昏时的月色和月光”更为贴切。
除了“疏影”一联的讨论外,历代焦点还落于对整首诗评价上,即“有句无篇”问题。吴沆曰:“好诗但一篇亦难……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亦只是一联得名,多少惊天动地。诗岂易得哉!”[36]蔡启曰:“‘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则与上联气格,全不相类,若出两人。乃知诗全篇佳者诚难得,唐人多摘句为图,盖以此。”[28]189颈联与颔联气格不合。清代纪昀曰:“冯云:‘首句非梅’不知次句‘占尽风情’四字亦不似梅。三、四及前一联皆名句,然全篇俱不称,前人已言之。五、六浅近,结亦滑调。”[18]786从整首诗看,颔联塑造的是淡雅之梅,用笔含蓄,意在言外。首联言梅不畏寒冬,独立于小园中,“暄妍”色彩浓烈,“占尽”一词直露。颈联“以物观物”,从“霜禽”的“偷眼”和“粉蝶”的“断魂”侧面写出梅之色香对生物的吸引,画面富有色彩与动态,但“断魂”略显夸张。尾联诗人直抒喜爱之情,以“微吟”的高雅与“檀板”“金樽”的低俗对比,反衬梅之高贵,但诗思落于常态,未见出新,且“狎”字又失之于庄重。因而,该诗的其他三句断裂了颔联的意蕴,破坏了淡雅的意境,确是“有句无篇”。
经典的形成还包括对经典的解构或追认。历代论者也将该诗与林逋其他梅花诗进行比较,分出优劣高下。历代推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以欧阳修为代表,激赏“疏影”句,此种占大多数。如许顗《彦周诗话》曰:“林和靖《梅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大为欧阳文忠公称赏。大凡《和靖集》中,梅诗最好,梅花诗中此两句尤奇丽”[8]390,这从体物之工角度称赞;第二种以黄庭坚为代表,赞林逋《梅花》诗中“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句,如黄庭坚《书林和靖诗》云:“欧阳文忠公极赏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别有《咏梅》一联云:‘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似胜前句”[37]。王义山《刘梅南诗集序》认为“雪后”一联,“风味不减。逋与梅相似,清哉吾逋也”[38]。将梅的清逸出尘与林逋的清雅高洁相提并论;第三种,以王直方为代表,认为林逋另一首《梅花》中“池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可与“疏影”“雪后”二联相伯仲,而胡仔评论道:“余观此句,略无佳处,直方何为喜之,真所谓一解不如一解也。”[28]188-189每位评论家评价标准不同,偏好也有所差异。但从接受史上看,更多的人认为此诗更胜一筹。艺术欣赏无定论,也无需有定论。
三
除了作品自身审美价值以及批评家讨论外,诗人人格形象也是它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梅花”作为一种符号,被视为林逋文化人格象征。林逋《山园小梅》捕捉梅花外在曲干、暗香的特点,以梅花的幽独雅致展示隐者的闲静淡泊,为后代诗人赋予梅花士大夫人格奠定了基础。苏轼提出“梅格”观念成为梅花象征化关键因素。苏轼《荷花媚·荷花》一词以“别是风流标格”形容荷花的风姿。“标格”为风范之意,可形容一切带有风度的人或事物。而“梅格”在“标格”基础上,加上“梅”字,凝结成一个特定词组,笔者还未发现其他“植物+格”的词组,可见其独一无二。“标格”可标举普遍的事物,而“梅格”只能用于梅花一物。苏轼经历“乌台诗案”波折后,开始大量创作咏梅作品,其中,咏梅诗有40多首,咏梅词为5首。他融自己的仕宦遭遇与人生体悟于梅花中,梅花成为他的人生际遇与精神品格的代言物。随着理学的兴起,格物究理意识的流行,梅花被赋予了儒家伦理中的君子品格,获得“比德”的深厚内涵。程杰先生提出“林逋首明其‘清’,北宋中期以来强调其‘贞’。”[39]陆游也推崇梅花的道德品质,诗《十二月初一日得梅一枝绝奇戏作长句今年于是四赋此花矣》曰:“高标已压万花群,尚恐娇春习气存。”[11]385梅花“恐娇”的高标精神气质压倒众芳。南宋中后期,面对北方夷狄政权的威胁,士人对于华夷之辨的观念愈加强烈。国家可以灭亡,但道统不可中断,华夏文明不可消失。这个时期多刻画雪中之梅,突出梅花在严苛环境中的斗争精神与坚守的慎独品格。理学家在梅花身上找到了象征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图腾。因而,在梅花与品格联系紧密的南宋时期,辛弃疾《浣溪沙·种梅菊》曰:“若无和靖即无梅。”[40]梅花与林逋成为固定意象,提起其中一个,必定联想到另一个。如吴锡畴《林和靖墓》曰:“清风千载梅花共,说著梅花定说君。”[10]40400吴龙翰《拜林和靖墓》曰:“清风千古镇长在,见著梅花如见君”等[10]42895。后人也将林逋咏梅诗与陶渊明咏菊诗并提,以扬隐士高风亮节人格,如黄庚《杂咏》云:“人非陶令空看菊,诗不林逋漫咏梅。晋宋后来爱菊者,输他高节与高才。”[10]15008文以人传,人以文传,林逋之梅成为隐士的高洁闲雅的象征。
其他“非文学”因素也会影响作品的传播,如时代风尚。宋代梅花审美文化兴盛,圃艺之风推动经典的传播。北宋前期,园林多以牡丹、松竹为主;北宋中期以后,出现梅景布置;南宋圃艺蔚然成风,范成大《梅谱》云:“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轻重。”[41]地理因素也是《山园小梅》成为经典的助力器。钟婴《孤山景区与林和靖》一文认为林逋是“孤山景点的开拓者”,“林逋和梅花是孤山独特的人文景观”[42]。西湖孤山是古代梅花名胜,不少人游览后都有创作,进而推动了原诗传播,如刘黻《访西湖》云:“惟欠数间茅屋在,种梅花处伴林逋。”[10]40728姚勉《题小西湖》曰:“待种梅花三百本,请君雪里访林逋”等[10]40440。这与历代岳阳楼、黄鹤楼、醉翁亭的诗文创作现象相似。
“跨体接受”现象是经典传播与接受广泛性的体现。《山园小梅》不仅仅影响诗歌创作,还影响其他文体。词中化用诗意的例子上面已论。“暗香”“疏影”语词以词调名、乐曲名方式流传。姜夔自度曲,“暗香”“疏影”成为词牌名。张炎《词源》卷下《杂论》曰:“诗之赋梅,惟和靖一联而已。世非无诗,不能与之齐驱耳。词之赋梅,惟姜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43]张肯在《暗香》《疏影》调的基础上,自度曲作《暗香疏影》(冰肌莹洁)。楼俨《书姜夔〈疏影〉词后》曰:“按元张肯有《暗香》《疏影》词,第一段《暗香》,第二段《疏影》,自注夹钟宫,押入声九屑韵,亦商音也。”[44]另外,吴文英《暗香疏影·夹钟宫赋墨梅》以“暗香疏影”为词牌名。张岱小品文《补孤山种梅序》中“疏影横斜,远映西湖清浅;暗香浮动,长陪夜月黄昏”[45]也借鉴此诗。
《山园小梅》还“跨学科”传播。林逋与“暗香疏影”之致影响了绘画创作。“疏影”梅的主次分明以及“临水”梅的情景设置启示了绘画技巧,梅以疏枝横斜的姿态出现。此现象可从题画诗词中窥见,如王柏《和遯泽韵取临江叔父墨梅》曰:“疏影暗香浮戏墨,光风霁月惠仙姿。只疑和靖旧争长,纵是逃禅甘伏雌”等[10]38071。李开林《林逋的绘画史意义——以宋、元墨梅诗画创作为中心》,提出了林逋对墨梅画意境风格和思想主旨的影响问题,足可见林逋之于绘画史的重要意义。[46]“林逋与梅花”也成了绘画的本身,如明谢时臣《选梅接枝图》[47],以折扇为载体作画,画中林逋立于梅前,家仆修剪枝条。林逋与梅花整体墨浓,而家仆与梅墨淡,浓淡对比可见画的主体所在。梅与水、月的搭配在园林造景中也广为使用,薛芸《中国梅文化及梅花在园林造景中的应用》一文,提到了“疏影”一联“堪称梅水配置的最佳描述”,梅与月的结合更能提高园林审美情趣。遒劲横斜的枝干也在盆景中随处可见,一系列品题如“水边梅”“暗香”“疏影”等均脱胎于《山园小梅》。[48]
《山园小梅》亦“跨国”传播,尤其是日本。“现在可查的日本林逋诗集最早刊印于日本江户时期(贞亨三年),其后亦有刊刻本。”[2]1在诗集刊印前,《山园小梅》的“疏影”一联,被日本室町时代的五山诗林广为接受与喜爱。经王玉立统计,《五山文学全集》中引用“疏影”一联达29首,占所有咏梅诗的约14%,引用“暗香”“疏影”典故的咏梅诗,共10首,占所有咏梅诗的约5%。[2]48同时代的一休宗纯《狂云集》中咏梅诗引“疏影”一句达6首。[3]27由于接受者身份、当地本土审美方式等影响,日本的解读加入了禅宗色彩,且更关注林逋的隐逸行为,与中国传统理解有所差异。宇野哲人曾游历放鹤亭,其《中国文明记》中描述:“亭侧多古梅,花影倒映于湖水之中。和靖先生笔下有联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古来咏梅者甚多,然未有及此一联者。今伫立于此亭前,亲见此梅此水,吟诵起此联,顿觉其中诗趣津津。”[49]赞赏之情充溢于心。许渊冲将《山园小梅》翻译为英文,益于诗歌从东方传至欧美,对传播中华经典做出贡献。
《山园小梅》之所以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得益于诗集流传、选者青睐、后人模仿、批评家讨论、诗人人格、时代风尚、地理文化等,还有很多影响价值评判的因素待继续探究。《山园小梅》不仅堪称咏梅诗典范之作,而且对其他文体、学科乃至国家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小觑。经典的价值是经过世代不断挖掘、累加的,除了文学因素外,“非文学”原因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经得起“再经典化”以及时间的考证。本文主张不应静止地看待经典,而需动态考察,并且打破文体、学科、国别界限,以更广阔的视野重审经典的影响。经典作品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亟待更多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