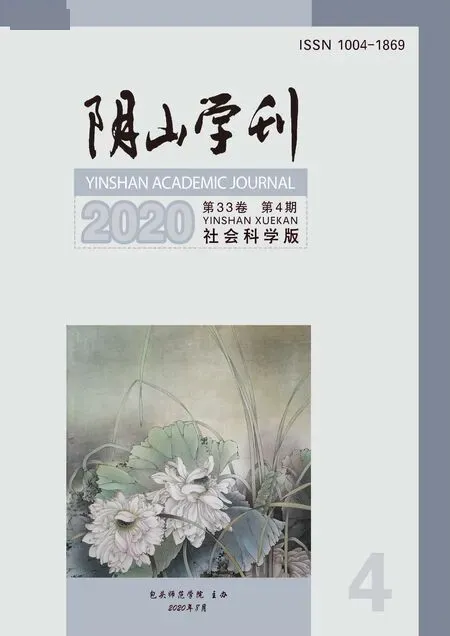儒学与东汉中后期的婞直之风
2020-02-20周尔祥
周 尔 祥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婞直是一种带有强烈个人情感的耿直性格,表达的是一种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东汉中后期儒家士人群体首登政治舞台,以其群体的婞直之举,演绎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婞直之风。它是在东汉中后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深受儒学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士风,体现的是具有忧患意识的儒家士大夫要求驱除戚宦、政归士人的政治诉求,其以“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为主要表现形式,是东汉士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着重探讨的就是儒学与东汉中后期婞直之风的关系。
一、何谓婞直之风
何谓婞直?《说文解字》云:“婞,很也。”[1]婞直,则是指倔强、刚直的性格。据考证,“婞直”二字最先出自屈原的作品,其《离骚》有“鲧婞直以亡身兮”之语,其《惜诵》亦有“行婞直而不豫兮”之说。婞直实际是一种带有强烈个人情感的耿直性格,表达的是一种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或许是受屈原这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用“婞直”一词来描述后汉士人。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东汉中后期特别是桓灵之际的东汉士人正如屈子一样,因报国无门而产生义愤填膺的愤懑之情,他们为了挽救日趋黑暗的政局,同样是“虽九死其犹未悔”。
不可否认,东汉初年不乏婞直之士,桓谭就是典例,他有着鲜明的学术立场和政治个性。光武帝笃信谶纬,桓谭称谶纬“奇怪荒诞”,在光武帝“不悦”之后,桓谭仍然反对谶纬决事。光武帝打算用谶纬来决定建灵台的位置,“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2]961耿直狷介的桓谭可谓东汉初年婞直之士的典型代表。但总体来说东汉初“光武明章之治”政治比较清明,对儒学也颇为重视,因缺乏婞直之风的酿成因子,故而那时婞直之风没有形成。
而到了东汉中后期,士人群体不断壮大,仅太学生就达三万余人,扎根于他们内心深处的儒家“致君尧舜”政治理想因朝政渐趋黑暗而得不到实现,他们义愤填膺,为明政治而不畏奸邪乃至弃生死于不顾,终于在桓灵之际形成一股强大的士林风气,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婞直之风。朝野士大夫以“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方式,主动向宦官发起攻击。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2]2185
范晔认为,婞直之风盛行于桓灵之际。原因在于桓灵时期宦官干预、把持朝政局面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致使“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婞直之风主要表现在“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两个方面,婞直的矛头直指“阉寺”,也就是权宦。据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所云,“党议”之称始自桓帝继位初期任命周福为尚书一事。
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2]2185-2186
尚书周福与河南尹房植同是当朝有名的甘陵人。两人的门生,各树朋徒,褒扬其师,渐成尤隙,并传以歌谣,这是党议的开始。后此种方式传入京师太学,经太学生与李膺、陈蕃等人的相互褒扬发展成风气,并出现了“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等歌谣。范晔因此认为,婞直之风由发展到兴盛是自桓帝初期“党人之议”到灵帝继位后第二次党锢之祸这段时期,“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2]2189第二次党锢之祸后,婞直之风开始发生转变。再看袁宏《后汉纪》所论的婞直之风:
自兹(和帝)以降,主失其权,阉竖当朝,佞邪在位,忠义之士发愤忘难,以明邪正之道,而肆直之风盛矣。[3]
此处的肆直之风即是指婞直之风。袁宏将婞直之风追溯至和帝,不无道理。东汉自和帝始进入王朝中后期。自汉和帝刘肇起到汉献帝刘协,其间皇帝平均登基年龄不超过10岁,最大的不过17岁,最小的则身在襁褓之中,驾崩平均年龄不到21岁。和帝10岁继位,外戚登上政治舞台把持朝政,此后出现外戚宦官轮番执政的局面,即阉竖当朝,佞邪在位。据袁宏把婞直之风追溯到和帝,可知其婞直矛头指向的是戚宦,但那时的婞直之风只是处于酝酿和发展阶段,远没有桓灵之际盛行。范晔所论婞直之风,则专指桓灵之际党人的婞直之举,“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埶,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概,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2]2207此时,崛起于和帝时期的肆直之风臻于鼎盛,其矛头直指宦官。因为在桓灵之际,权宦势力达到顶峰,清流们抗击的对象也从原来的戚宦,变成了联合外戚打击宦官。[4]
范晔将婞直之风概括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两个方面。袁宏将“忠义之士发愤忘难,以明邪正之道”的做法称作肆直。综合起来看,东汉中后期的婞直之风主要指“忠义之士”的士大夫群体通过“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做法以明正邪之道,尤以桓灵之际的婞直之风最甚,而其“道”,即是指儒家的道。“激扬名声,互相题拂”是士人们的相互标榜,尤其表现为以传歌谣、上称号的方式题拂名士,“品核公卿”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清议”,而“裁量执政”则是儒士官吏运用手中权力对戚宦势力给予打击,以上是婞直之风的具体表现。无论是将婞直之风的渐盛追溯到和帝还是桓灵之际,其时为东汉中后期无疑。婞直之风的渐盛是由戚宦轮番掌权而始,到第二次党锢之祸前后极盛。其矛头起先是戚宦二者兼指,后期则是主要针对官宦。
二、儒学对婞直之风的影响
婞直之风日臻兴盛于桓灵之际,与儒家政治理想因朝政日益黑暗而得不到实现密切相关。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5]81,朝政虽渐趋黑暗,但在具有强烈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儒家士人看来,朝政仍然有挽回的余地,故而他们不但不甘于“隐”,还要“见”,出来力挽狂澜,挽救危局。他们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更抱共同之政治理想,通过相互声援,产生出了强大的合力和凝聚力,激励他们勇于同宦官作斗争。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使即将变为“无道”的天下向“有道”转变,抑或是为了“有道”的实现去做一番努力。正是基于家国天下的政治理念和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才有了他们的婞直之举。为了实现共同之儒家政治理想,有些士大夫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朱熹所云:“某谓三代而下,惟东汉人才大义根于其心,不顾利害生死,不变其节”[6]。
那么,日益壮大的士大夫群体为何将婞直的矛头指向戚宦呢?在士人眼中,戚宦干政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外戚以裙带关系辅政,在以道德、学问相尚的士人看来,外戚的入仕途径轻贱而可卑。[7]至于宦官,原因不仅在于“关西孔子”杨震之子杨秉所说的“案国旧典,宦竖之官,本在给使省闼,司昏守夜,而今猥受过宠,执政操权”[2]1774,典章中宦官从来就没有被宠幸甚至参与朝政的先例,而且宦官中的绝大多数并不通经,不符合正常入仕途径,他们“傅近房卧之内,交错妇人之间”,因此宦官无资格把持朝政。宦官深受士人摒弃的原因更在于其是“天刑之人,刀锯之余”,在以孝治国、深受正统儒家观念影响的东汉社会,中断血脉世系传承的“不孝”之宦官参政本身就是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故而士人“羞”与宦官为伍。但现实恰是这些深受厌弃的宦竖,其权力与日俱增,如日中天,给社会带来深重灾难,致使“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因而戚宦,尤其是宦官成为他们主要声讨的对象。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形成相互标榜的风气;同时品评公卿,议论时政得失,形成清议之风,给当朝造成舆论压力。他们要求权去旁门,政归皇帝,选贤举能,官得其人,抚恤民众,安定社会。[8]
婞直之风的产生,在以经治国的东汉社会,与通经入仕的渠道受阻不无关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通经入仕逐渐成为重要做官渠道,在东汉前中期这一渠道成为官吏选举与晋升的主要来源,真正达到了以经治国。士子们之所以研习儒家经典,最重要的就是运用所学经典走入仕途,尽可能做到通经致用,一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积极入世,然而戚宦掌权阻碍了他们通经入仕进而济世救民的理想。以戚宦为代表的浊流置儒家道德于不顾,轮番把持朝政,造成政府失序,选官体系紊乱,莘莘学子学而优却不能仕,破坏了东汉社会阶层流动的均衡态势。[9]128戚宦群体,特别是宦官们,在经学兴盛的时代不通晓经典,文化素养低,毫无政治追求,一味地“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2]1657。而东汉中后期太学生群体日益庞大,看似再正常不过的入仕途径随着戚宦的专权而日益坎坷,这令以太学生为主体的广大士人甚为不满,在朝在野的士人们逐渐合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向戚宦发起攻击。
“激扬名声,互相题拂”是婞直之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相互标榜的标准为儒家道德伦理。东汉时期士人对经术、德行的风摇式品题十分流行,德才兼优者迅速流誉天下,儒家观念成为士人自觉的意识形态。[10]所以士人大都特别注意道德操守,其道德标准大体就是儒家所讲求的孝悌、仁义、廉洁、轻财等,他们如此注重名节,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名声,抬高身价,通过举孝廉入仕途。而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标榜之风更加激进,政治色彩更加浓厚,且掺杂有相当大的愤懑情绪,士人们不再把通过相互标榜以便走入仕途谋求官禄作为婞直的主要目的,而是以此来表达对朝廷和宦官势力的强烈不满,希冀通过标榜天下名士,荡涤朝政,以致标榜达到了给名士上称号的程度,“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摽搒,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2]2187。无论标榜之风在党祸前后如何变化,题拂之准绳始终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他们标榜的都是儒家所说的正人君子。此时的士大夫不仅具有共同的文化规范,更是将仁义气节视为行为标准,为加强同戚宦的斗争力量,更是借助儒家仁义气节观相互标榜。如“三君”“八俊”“八顾”“八厨”等美称皆属儒家范畴。君,体现的是儒家所推崇的君子形象;俊,则是人之英杰的代表,孟子曾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君子的三大乐事之一;顾,是德行高尚的体现;厨,则体现的是儒家重义轻财理念。诚如庞天佑所说,东汉中后期士人群体的凝聚是建立在儒家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基础上的。[11]
对当权者和朝政作出一定的评论是儒家关怀现实的重要体现。儒家自产生之时起,就以关怀政治与现实为己任,儒者的重要职责就是对历史和当朝政治人物及朝政进行议论以敦促统治者实行仁政。孔子“爱人”,更喜欢品藻人物,孔子一生品藻过八十余位人物,而且涉及范围很广,既有历史的,也有同时期的。[12]比如孔子对历史上管仲和令尹子文的褒贬,对同时期季氏僭越礼制的批判,对晏平仲、宁武子、孟之反等人的人格褒扬。孔子人物品藻之目的在于举贤人、行德政,他的这一行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东汉士人品核公卿的做法无疑是对孔子人物品藻的继承与发展,他们关怀现实、积极仕进,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意识。在那个时期,君权旁落,仁政无从谈起,士大夫通过“清议”品评当朝公卿大夫,议论朝政得失,褒扬贤能之人,贬低权宦和江河日下的政局,希冀朝政有所改善。何童认为在吏治混乱、仕进之路被阻隔的背景下,人物品评到桓灵前后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现象和士人风尚。[13]东汉士人对公卿和名士进行品核与品藻仅是一种追求仁政的辅助性手段,其目的是通过评判公卿和时政来影射日趋黑暗的政局,以匡正纲纪。如汝南许氏兄弟以“月旦评”的方式定期品评士人、议论时政。实际上,士人品核之范围也不仅仅局限对公卿名士和当朝政治,有的士人甚至直接谏言皇帝。如桓帝延熹二年(159年),中常侍单超等五人封侯,白马令李云上奏:“孔子曰:‘帝者,禘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不欲禘乎?”[2]1852士大夫用儒家学说谏言皇帝,言辞激烈,直陈最高统治者决策失误,可谓是婞直之风的极端体现。
运用儒家学说“裁量执政”,以儒学作为抨击宦官势力的重要手段。与口头上的清议相比,一些在任的清流士大夫则能够利用手中的职权“裁量执政”,给宦官势力造成冲击。而支撑他们不畏艰险伸张正义的正是儒家的道义,他们“裁量”的标准也是儒家的理念。李膺在任司隶校尉时,将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打死。桓帝责问李膺为何不请示就将张朔治重罪时,李膺用儒家经典来为自己辩护:“昔晋文公执卫成公归于京师,《春秋》是焉。《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2]2194再如范滂,“滂在职,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埽迹斥逐,不与共朝。”[2]2205《论语》载:“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5]2,儒家将孝悌看作人之根本,而仁义又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这正是范滂所推崇的。当范滂被投入监狱,王甫诘问他为何相互标榜、评判朝廷时,范滂又是引孔子语:“臣闻仲尼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2]2205-2206这种儒家气节使王甫为之动容。杨秉任河南尹在深查单超之弟单匡贪污罪时被尚书责问,杨秉引经说:“《春秋》不诛黎比而鲁盗多,方等无状,衅由单匡”[2]1771,这明显带有西汉“春秋决狱”的影子。后杨秉在太尉任上又弹劾宦官侯览之弟侯参,并上书说:“虽季氏专鲁,穰侯擅秦,何以尚兹!……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夺阎职之妻,而使二人参乘,卒有竹中之难,《春秋》书之,以为至戒。……盖郑詹来而国乱,四佞放而众服。”[2]1774可以说,在政局逐渐败坏的情况下他们不仅用儒家伦理来“裁量执政”,打击宦官势力,甚至在生命的紧要关头,他们仍然是用最为崇尚的儒家理念为自己辩白。正是基于深深植根于他们内心的儒家思想的支撑,才造就了他们的婞直之举。
儒学对东汉中后期士人婞直之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戚宦专权与士人从政理想背道而驰的同时,也使正常的通经入仕渠道受阻,这俨然挑战了儒家伦理的权威性。清流儒士奋起而捍卫自己服膺的信仰,他们以儒家道德伦理相互标榜,运用儒家学说“裁量执政”,用儒学作为抨击宦官势力的重要手段。可以说,东汉中后期的婞直之风是特定政局与儒学综合作用的产物,是在戚宦专政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儒家清流士大夫以儒家思想为“武器”与戚宦进行斗争的不畏强权之举。
三、婞直之风的分途及其对儒学的影响
党祸后士人群体遭受严重打击,士人群体的中坚力量或失去性命,或被禁锢、流放,士大夫群体元气大伤,名士凋零。政治压力促使在党锢之祸中存活下来的士人看清政治现实,他们已认识到汉王朝大厦将倾,与其从容赴死不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他们已经处于孔子所说的“无道”社会中。始料不及的政治冲击,也使婞直之风发生分途,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大批士人由“显于朝”开始向“隐于野”转变。有的士人讲求权谋与策略,甚至暂时向宦官妥协。比如党锢之祸后袁绍隐居洛阳,其“爱士养名”“非海内名士不得相见”的做法引起宦官警觉,其叔父太傅袁隗怒斥袁绍“汝且破我家”,向宦官表示妥协。袁隗之所以这样做,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在激烈的生死斗争中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后来袁隗与何进一同辅政,袁绍铲除了宦官势力。如王克奇所说,党祸后士人集团遭到残酷镇压,当他们不能通过正常手段和途径实现自身价值时,只有诉诸武力,最终走上汉末武装割据的道路。[14]
党锢之祸后名士之间“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之风仍然盛行,但是“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现象则几乎消失了,“品核公卿”变成了人物品藻,形式也由原来兼济天下的清议变为独善其身的清谈。党锢之祸后名士的互相题拂、人物品评缺少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激浊扬清的政治情怀,完全陶醉于个人名声而无法自拔,如汉末的孔融、祢衡相互扬名,祢衡称孔融“仲尼不死”,孔融赞祢衡“颜回复生”,这种缺少了儒家情怀的名士品题之风与婞直之风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追求虚名,崇尚清谈进而玄谈,透露出了由儒而玄的气象。东汉中后期尤其是桓灵之际的婞直之风体现了儒家士人在困难面前英勇不屈的名节,不向奸邪低头的骨气,他们激浊扬清,对当时黑暗的政局起到了净化作用,赢得了士林的广泛赞誉。虽然在党锢之祸中遭遇劫难,但对研习儒家经典的士人来说,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在他们心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入仕有为是士大夫难以割舍的政治情怀。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形成的婞直之风因过于激进而促成了党锢之祸,党锢之祸是士大夫们用生死来演绎婞直的最终结果。东汉时期,多以儒术进仕为官的儒士坚定践行儒家学说,他们的罹难必然使儒学遭受沉重打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5]79孟子也有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人乎者也。”[15]东汉士大夫群体自觉承担起弘毅之责,以身殉道。不可否认的是,党锢之祸促使幸存下来的士大夫群体认清政治现实,他们不再奉行婞直之举,而是转向更为安全的方式,或是退隐,或是讲求权谋,或是清谈,或是向宦官屈服。这说明士大夫群体在党锢之祸后随着“善士”的逝去而发生了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道玄思想抬头,这对儒家学说产生了冲击。汉末士大夫由慷慨激昂、匹夫抗愤、舍身为国的儒家风尚转向自任性情、避祸保身、持家忘国的道家风貌。[9]133
就整个思想文化史而言,东汉中后期清流士大夫在与戚宦对抗过程中彰显的不畏强权之风和舍生取义的精神无疑是对儒家气节观的坚守和传承,影响了历代知识分子和读书人。余英时先生认为李膺、陈蕃、范滂等党魁皆有儒家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之气象,他们身上体现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之精神传统“上承先秦之士风,下开宋明儒者之襟袍”[16]257,陈建林认为北宋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与党锢名士趋死不避的名节观一脉相承,宋明理学乃至近代民主革命皆受到东汉士人精神的影响。[17]就东汉后期儒学的发展倾向而言,党锢之祸后儒学的发展则受到冲击。第二次党锢之祸后,“隐”成为士人看清政治现实后不得不做出的重要选择。作为儒生的隐士退隐后心中仍然难以割舍儒学情缘,虽上不能立德、立功,唯求立言,故著书立说,传授以经学为主的儒家学说,或成一代大儒。如荀爽“后遭党锢,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以著述为事,遂称为硕儒。”郑玄“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党锢之祸后士人退而著书者尤多,率有所愤而发,[18]如因党锢之祸退隐的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张奂著《尚书记难》三十万余言,陈纪发愤著书数万言,号《陈子》。他们自觉承担起传播儒家文化的重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末的私家讲学之风。但是,党锢之祸后大批士人不再“清议”朝政,而是注重品藻人物和陶醉于个人名声,他们崇尚空谈,开魏晋士风,如上文所述孔融、祢衡,他们的行为即可证明。余英时先生认为汉末孔融所经历的时代正值儒家的名教或礼法流入高度形式化、虚伪化的阶段,汉末儒家的君臣关系、家族伦理出现危机,儒家的礼亦受到“情”的冲击。[16]369-371作为经学大师的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然“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前授生徒,后列女乐”[2]1972;东汉后期名士仲长统“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弋高鸿,……思老氏之玄虚”以求“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2]1644,似乎不再留恋儒家的人生价值,而是奔向道家的养生和逍遥。马融、仲长统等人之所以表现出违背儒家礼法的行为,与东汉中后期政局复杂多变不无关系,他们求“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2]1644。东汉中叶以后,地方名士除信奉儒家道德主义之外,对老庄道学的逍遥自由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具有“清”“异”“逸”等儒玄双修矛盾情结的儒家式道家人物大量涌现。[9]133-134
东汉中后期儒家士人群体首登政治舞台,其以群体的婞直之举,演绎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婞直之风。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深受儒学影响而形成的婞直之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党锢之祸的发生。党锢之祸后,婞直之风发生分途,又对儒学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东汉中后期,在婞直之风不断酝酿并走向极盛的同时,儒家学风已由学术转向政治。党锢之祸后尽管有大批归隐士人继续承担注经、讲学的任务,儒学部分实现了由政治向学术的回归,但随着东汉中后期作为儒学践履和传播载体的大批“善士”被处死、禁锢、流放,道玄思想在士人之间亦有异军突起之势,儒学走向衰落已成历史必然。因此,党祸后婞直之风的分途给儒学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