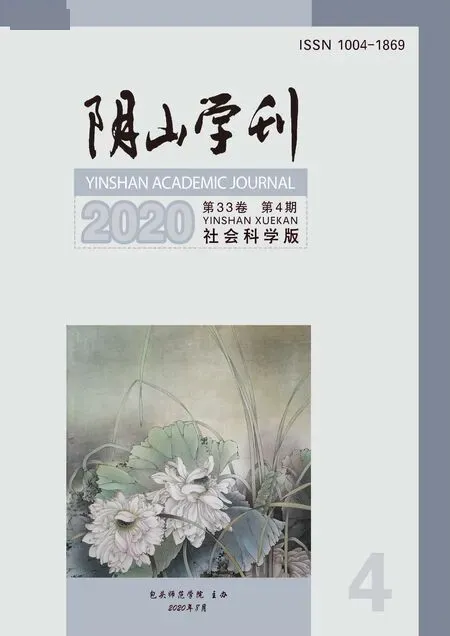俯瞰视角下的几种后现代文化表征
2020-02-20李弋文
李 弋 文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男爵》无疑是对现代社会的隐喻。柯希莫在树上生活、学习、思考,可谓是“诗意的栖居”,脱离了一般人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在树上(或言空中)这个平行于地面世界的乌托邦里,找到了心灵的居所与永恒的自由。同时,由于跳出了现代社群,远离了人类社会,柯希莫以一种局外人的视角俯瞰着人间,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与个人挣扎暴露无遗,从而使他的思考转入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带有某种后现代的色彩。
诚然,观察视角的转换往往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判断。置身于广场中央与从高楼上俯视广场看到的景象迥然不同,因此而引发的联想自然各异。本雅明在其未完成的拱廊街研究计划之中,以“闲逛者”的视角,揭示了现代人置身于大都市之中所面临的生存状态,作为其现代性批判的蓝本。那么,当我们抽身于人群,将观察视角置于上空,以一种俯瞰的眼光来观照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后现代社会种种文化、艺术作品与现象,我们将会看到更为鲜明的后现代文化表征。
一、绝对阐释的消解与多元阐释的诞生
当我们站在天桥之上向下望去,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以及植物、建筑等等城市景观,直接铺展在我们面前。立体的、多面的事物,在俯瞰的视角之下,被压缩成一个个平面的画面。在我们尚且加入这些城市图画的时候,事物仍然以一种平等而交互的方式进入我们。我们平视着世界,看到每个人脸上的神情、每辆车的车牌号、商场玻璃展厅中琳琅满目的商品等等可以称之为细节与构成的因素,以及事物间相区别的特征。我们不会把随机两个路人看成同一人,因为他们的长相完全不同——这是我们观察时双眼告诉自己的经验。然而,当我们回到天桥上,以俯瞰的视角观察同一段区域时,原先的经验就靠不住了:所有的人似乎都是相同的,轿车也分不出区别,这座喷泉与那座喷泉都呈现辐射式的喷水——雕在喷泉上的装饰被压入平面而不见了。那些我们用以判别的细节特征,由于视角的转变而消失,三维的世界在俯瞰视角之下成为二维的图画。
随着细节消失的是深度。我们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欣赏艺术的习惯:站定在艺术作品前,细细观察、体悟,画家对于画面结构的布局、色彩的运用、特殊人物描绘的用意,或是雕塑家为形成某种美感而作的刻意安排,都是能够使观赏者联系相关的经验与知识,对艺术品背后隐含的真理作出一番阐释,而这种阐释往往是具有相关领域权威认证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对艺术品进行某种阐释,正是因为这样的艺术品包涵了可能的深度,或者说,现代艺术品的完整性,是建立在以背后的深度来诱导观赏者做出阐释的基础上的。后现代的艺术似乎是关于俯瞰的寓言,由于细节的消失,人们失去了赖以阐释的文本来源,于是,一切归于平面与无深度,“一种崭新的平面而无深度的感觉,正是后现代文化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特征,说穿了这种全新的表面感,也就给人那样的感觉——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1]440正如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比较的两双鞋,即凡·高的画《农鞋》和安迪·沃霍尔的《钻石灰尘鞋》[1]434-441。前者属于现代艺术的杰作,其中仍有着意义的深度模式。在詹姆逊看来,凡·高的这幅作品是可阐释的,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所做的解读就是一种典型的存在主义的深度阐释。而面对一个平面的无深度的世界,这种深度阐释模式就会显得不知所措。安迪·沃霍尔的《钻石灰尘鞋》展示给人们的就是这样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景观。它以精致然而毫无生气的姿态颠覆了现代主义式的乌托邦。
但是,这种深度的消失并非无积极意义。现代主义对于深度的阐释,首先是集中于某一些权威手中。他们把握了阐释的话语权力,并通过诱导、恐吓、孤立等方式,排除异己,将同一领域的解释权进一步集中。当阐释领域呈现一种声音之时,有多少人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造成这种矛盾的重要原因便是传统研究视角的禁锢。当人们将权威阐释视为理所应当,无可逾越,那么就难以产生反抗的兴趣。后现代的非阐释模式,则是以俯瞰的视角,观照一切理论的产生过程,“那些想当然地被看作是一般的、永恒的和必然的东西,其实都是有一个历史的,也就是说是有开始的,因而也就是有结束的。”[2]11其次,现代主义的阐释是以传统二分法为基础的。詹姆逊认为,至少存在五种现代阐释模式,内外二分法、以表里二分模式为基础的辩证法、以意识表层与深层为分野的精神分析理论、以真确性与非真确性为基础的存在主义和以意符、意念为本的符号学理论,而这些理论的模式,都受到了后现代理论家们的批判,因为二分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形而上的固定性质的,是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的。人们渴望从二分法中辨析真理,然而真理在后现代理论家眼中却不是一个多么确定的客观存在。
既然一切阐释理论皆有历史,而真理并不总是靠得住,那么就不存在绝对而唯一的阐释,现代社会的理论权威被重新审视。后现代是理论的时代,而种种理论又以反传统阐释作为其特征。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每一种理论与思想,出于论者的不同视角,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真实。现代阐释领域的一元论被推翻、消解了,后现代“多元”“平等”的概念越来越得到认同。理论的对话,现在与过去、解释者与文本、解释者与接受者,从历史的广阔的俯瞰视角之下,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同时,宏大叙事的理论框架再难以吸引后现代理论家们了。人们不再执着于构建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式的融哲学、美学、政治、文化等元素于一体的宏大理论体系,而是各执一端,从多元领域入手,提出独具创造性的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霍伊的系谱学、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家将着眼点从形而上的哲性思考,转入对当下社会的调研,这些理论也就呈现出强大的实践性与现实关怀。
二、实体与影子:阴影弥漫的后现代社会
让我们回到天桥之上。阳光普照大地,投射在每个事物上:人、车辆、建筑,都在支持其运动的大地上留下了影子。影子有时很长,有时很短,视太阳与被照者的角度而定。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确然无误地分辨出事物的实体与其影子——两者根本不在一个平面上。但是,当我们以俯瞰的视角观察事物时,却难以如此自信:立体的世界在我们看来是平面的图画,事物的实体与阴影并存于同一平面,投射在我们眼中,造成了某种视觉错位。我们似乎分辨不清实体与阴影的界线在哪里——除了色彩与明暗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也许是某位画家刻意为之。我们还看到,有些影子格外的长而大,甚至盖过了实体在我们眼中的位置。
在后现代的世界里,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影子,尤其是当它以符号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各式各样的物品包围着社会,物资前所未有地丰富。在满足了生存之需求之后,物本身的光芒愈发地黯淡,而其背后的影子越拉越长,以至于在与物自身的斗争中占据上风。这种现象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描述的那样,物的符号意义全然取代了实用意义,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其目的需求“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的满足首先具有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3]59也就是说,这种被制造出来的符号的象征性意义使得人们不再关注物品本身。在如今的资本主义消费过程中,物品通过华丽、刻意、无所不在的焦点凸出性展示,包装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美学、心理学技巧广告之中,在隐含兆示着品位、地位、权力等所谓的成功要素的诱惑之下,物背后的阴影渐渐统治与支配了人们深层心理结构的潜意识,符号制造了意义和象征,操纵着人们日常的消费。更为关键的是,如同阳光下一连串重叠的影子,这种阴影的支配已经成为一种商品之间环环相扣的锁链式的控制:“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3]3一套高档的西装需要一条昂贵的领带、腰带与一双名牌的皮鞋搭配才能显示出所谓的身份与品位。在当下的条件下,有幸获得的高档消费品往往预示着无限而强制性的消费意义链条。无止境的消费符号意义成了后现代社会消费领域的主要追求,而物品实体的价值却不值一提了。
这种虚影弥漫在社会各处。随处可见的广告、新闻、故事、访谈等等传媒方式,将每个人身后的虚影无限放大,建立起一种所谓的明星效应。当摄像机对准某个人的时候,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对其人浮光掠影的一瞥和他背后巨大的影子:我们往往与他的时空与心理距离太过遥远,根本无从了解其真实情况,只有通过镜头的投射,被动地接受着刻意构建与传递的某些信息,就像从天桥上俯瞰地面,人的真面目模糊不清,其身后的影子引人注目。这影子如同明星所谓的“人设”,成了大众评价的核心标准。而这一标准,与消费社会的消费商品通过广告潜移默化地构建其背后的意义与价值一般,也是裹在一系列欺骗性的包装之中的。在机械复制的时代,旧的光韵在艺术品的背后消散了,而新的阴影却取代了光韵的位置,并通过新媒介的放大与聚焦,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接受与承认。
在日复一日的欺骗中,也有人意识到了阴影的禁锢,并发起了对阴影的反抗。人们开始渴望触碰到阴影之前的实体,以及由此引发对真实价值的讨论。例如,风靡一时的“真人秀”类节目,使得人们以为他们终于窥见了真实,将明星从其背后的阴影中分离出来,重新置身于群众的围观之中。然而,荒谬的事实却是,这种自以为是的真实实则是更深层次的欺骗,这是一场名为“真实”的表演,阴影不出现在事物背后,而是覆盖了其自身,并通过剧本、画面剪辑等技术上的实现,制造其不在场性。观众无可避免地陷入又一轮阴影的笼罩之中。
三、个人主义的消散
本雅明在其“拱廊街计划”中提出了“惊颤”的体验,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面临突发事件,现代人需要快速地做出反应:现代化的进程将个体置入了一个别无选择的必须快速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现象的境地。这种快速反应的心理机制,是建立在个体对个人化独立地位的认识基础上的。每个人是独立的个体,人与他人和他物的联系是外在、偶然而陌生的,因此,惊颤构成了遭遇突发事件时的第一层心理保护机制,阻隔他我两者的突然碰撞。这是一种“正看”时的体验。
当我们以广阔的俯瞰视角观察一片区域时,自然而然地会将关注点从个人转向这一片社群。每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并且从未如此紧密过:一个人位置的改变取决于他者的运动。同时,人与支持其成立的大地之间也加深了联系——一般视角下凸显于大地之上的人在俯瞰之中成为大地的一部分,个人强力的奔跑、跳跃,群体的运动在大地的蕴含之中显得微不足道。
现代社会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精神,在后现代社会中逐渐消散。那种把社会理解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自愿地结合到一起的独立的个人的聚合体的看法,受到后现代理论家的普遍质疑。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秩序与哲学理论为个人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成立基础,而这一基础在全新的、变革的世界里被不断摧毁与重构。大卫·格里芬在《后现代精神》一书中认为,后现代精神以强调内在关系的实在性为特征,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个体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他(她)只是借助这些属性同其他事物发生表面上的相互作用,而这些事物并不影响他(她)的本质。相反,个体与其躯体的关系、他(她)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其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2]38这种联系观使得个人与其周边的关系异常的紧密,最为显著的改变就是人们对于自然的态度,格里芬将其概括为“有机主义”:“后现代人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后现代人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2]38-39如同俯瞰之下的人群的状态,人们积极拥抱着与大地、与他物及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当独立的单一的个体昂首面向世界、冲破自然的约束之时,群体的集合的人们则更多俯视自我与大地的关系,思考生命与生命、世界的价值。
个人主义的消逝,我们也可从当代众多小说主题的嬗变中看到端倪。现代社会的那种描写个人的意志、力量、追求及在困境中的挣扎与思考,总而言之,为突出大写的人的主题,在当下时代渐渐退位了。我们很难再见到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的英雄,那样的痛苦与强大的精神,在现代文学中颇受青睐的人物传记体裁在当下也难以再现辉煌。取而代之的,是跳出正对人物、事无巨细地单一刻画,而采用广阔的俯瞰视角,描写出属于众多人的平凡的世界。后现代世界的深度的消失,以及人的存在取决于构成他的关系,使得在当下再难以出现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英雄坠入凡间,成为俯瞰视角下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例如,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避开了宏大叙事与重大矛盾冲突,竭力淡化社会政治关系,致力于描写生活琐事与群体生命状态。
四、结语
总体而论,后现代文化是对现代社会的反叛与思考,其文化表征与社会精神在变革之下,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特质。当我们跳出传统视角,而以俯瞰的视角探究后现代社会文化时,后现代阐释理论的变异、事物符号价值的主导及个人主义消逝这些文化表征将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对于我国当下的社会阶段性发展无疑是一种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