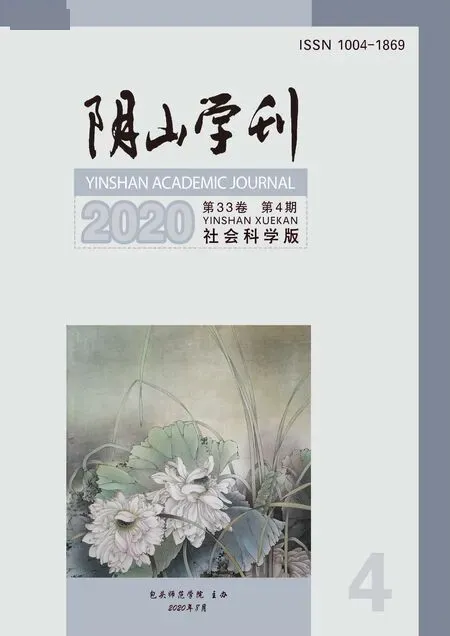视觉景观语境下身体的突围与沉溺
2020-02-20赵郭东
赵 郭 东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身体”这一术语,近年来已经成为当代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向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理查德·舒斯特曼,在他的专著和学术会议中,抛出了以身体研究为中心的实用主义身体训练美学,期望通过打破身体与意识的二元对立,实现一种新的美学思维和实践。媒介和技术爆棚,身体转向进入了空间和视觉社会的中心,身体感官第一体验全是来自视觉带来的绚丽,景观化的身体成了一个隐喻和文化象征,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正在以技术和消费品塑造没有特点的身体,所有电子媒介和实体空间的身体,失去了自我理性自查,变成了色情、社会关系的壁垒,互联网时代的商品景观全都为身体赋予了绝对感性魅力,身体的在场表现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隐藏的大众消费文化,如何对待视觉空间身体的中心化是人文学科研究避不开的地方。
一、身体的历史地图
身体审美的艺术理念在历史时间轴上一直是个醒目的存在,如古希腊的绘画和造型艺术都非常注重模仿再现人的身体,《穿披肩的少女》[1]就是对女性身体外形的塑造,艺术领域里身体的在场证明了视觉感性美学对人自身存在的关注,身体作为客观的存在始终占据着艺术表现的中心。但是,国家体制的建立和宗教神学思想的遍布形成一套完整的政治和神学话语统治,身体被标识为如同一具槁木,神学将灵魂解释为人永恒存在的本真,柏拉图就是灵魂至上的虔诚信徒,强调美在“理念”,精神是存在的本质,可视化真实存在的身体却遭遇了极大的贬低,“我们岂不相信死就是脱离肉体,死的状态就是肉体脱离单独存在的状态,以及灵魂脱离肉体单独存在的状态?死岂不是就是这样?他说:就是这样的。”[2]相信永恒不灭的洁净灵魂而摒弃身体形体美,追求像空气般虚幻的精神之美。真实在场的身体从文明起源就失去了话语权的表达,身体话语权的缺席开启了精神审美的绝对权威,妖魔化身体陷入高尚道德的对立面,身体失语的情况被表征为释放一切罪恶的潘多拉魔盒。
及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人文思潮的涌现和宗教自身的分裂,人的主体反思性从神学欺瞒中挣脱出来,身体审美不再是人们思想意识的禁区,艺术运用和生活实践证实了身体存在的合法性,身体解放彻底宣告了宗教彼岸世界幻想的破灭,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身体由被压抑的在场变为合法的在场过程。科学和理性的进步使人丢弃了身体妖魔化的观念,盛行的身体享乐成了人的自我身份认同——“身体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而根本的维度。身体形成了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最初视角,或者说,它形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的融合模式。”[3]13身体是人自我指认和区别于他人的第一方法,没有人通过灵魂面对面的交流辨认一切,人开始正视身体感官的欲望。但是,身体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并没有将自身缺席的话语权夺回,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还有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就是精神崇高的最佳佐证。一直以来,宗教学说宣扬隐形的灵魂是人终生的归宿让位于唯心主义的理性,这时身体所取得的解放只是对人生活中原有欲望的认可和公共关系里彼此身份权利平等的正视,也只能看作是身体外部的一些权力,表达身体存在的话语权依然滞留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里,这在鲁迅小说《祝福》中有所体现,祥林嫂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在爆竹声中,新年献祭的鲁四老爷私下偷偷对四婶叮嘱:“这种人虽然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4]祥林嫂为了谋生而做工于地主家庭,虽然可以通过劳动获取自己的工钱,但这个丧夫丧子的不幸女人身体却背上扫把星、淫秽的文化恶习;文学中的祥林嫂去除历史背景就仅仅是一个获得身份认同的身体,但却无法言说和申述。
尼采的一句“上帝死了”推倒统治千年的形而上身体观,身体哲学转向赋予了身体缺席已久的话语权,主体的消亡、作家已死、互文等解构主义思潮作为身体哲学话语转向的先锋,推倒了精英主义的理性象牙塔。与此同时,实用主义学派开始强调身心一元论的身体美学,理查德·舒斯特曼将身体定义为:“‘身体’这个术语所表达的是一种充满生命和情感、感觉灵敏的身体,而不是一个缺乏生命和感觉的、单纯的物质性肉体”,[3]11身体转向是身体和意识一次融合,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在身体话语回归后赢得很大认可,他结合了杜威实用主义身体训练法和威廉·詹姆斯身体中心论,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受实用主义美学思想的启发和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阴阳两极”等对立互补的结构主义观念影响,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强调“身心一元论”的“亚历山大技法”,亚历山大认为人的习惯会压制人的意志,身体将埋没在舒适的习惯环境里,失去自我,个体通过参加瑜伽练习和习惯养成等,以达到身体治疗的目的。身体和意识作为两个被分割的部分,只有在实践环境下将理性反思和生理欲望相结合,才是舒斯特曼所说“身体一元论”,身体一元论的出发点必须对自我身体进行训练和反思。虽然文艺复兴使世俗化的身体获得与主体意识暂时的力量平衡,但脱离宗教的身体并没有能够与意识主体休戚与共,景观社会下开始了一场感性身体革命(身体美容、拍照、时尚包装、明星代言),世俗化的身体就像万有引力潜移默化的操控着每一个躯壳去狂欢,消耗自己,身体失去了自我变为一个符号和文化建构的他者,一个以身体为中心的风暴席卷了主体意识,下文将重点论述视觉景观下突围出的身体如何深陷景观的围城。
二、身体的狂欢
现代性的理性大厦倒塌后,肉欲化的身体在商品消费景观社会中由唯灵论主义压抑的边缘地位走向可视空间的中心。当现代性引以为自豪的理性井然有序的改造这个任人宰割的自然世界时,人自我建构秩序和生物链毁在了惨无人性的世界大战,战争彻底摧毁了资本主义社会精英构想的社会蓝图,面对战后残垣断壁的废墟和美苏争霸的威胁,希望的灯塔在迷惘的一代生活中从未发光,对这群没有理想未来的愤青来说,身体的狂欢变成了他们存在的最后意义,用身体反抗启蒙理性虚伪的面孔。失望的年青一代开始走向高雅文化的反面——吸毒、蔑视法纪、同性恋、玩说唱乐,用精英社会贬低和妖魔化的身体作为反抗手段。身体存在所拥有的意义在人繁衍的过程中不断地在增加,虽然这些诋毁身体生理性的文化观念包袱一直使其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但是这些无可名状的罪名却在媒介社会下成了年青一代解构理性至上幌子的最佳方式,媒介的综合和扩散效应把身体散发的魅力动态拟真化,“媒介并不是把我们与‘真实的’旧世界联系起来;它们就是真实的世界,它们为所欲为的重新塑造旧世界遗存的东西。”[5]现代媒介像电脑、电视、广告都成了视觉传达信息,取消了人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媒介载体上的视觉将所有隐含的意识都掩藏了起来,图像呈现的是四处游玩的身体,无意识的媒介将大众文化所带有的搞笑、戏仿、色情都通过身体视觉化了,光怪陆离图影全是在开发和引诱身体展示自己。
全球化的消费环境和电子网络信息媒介的形成将疲于应付的身体推到舞台的聚光灯下,“外貌崇拜意味着对自我身体施加一种不知疲倦的雕琢。为了塑造出美好的体貌,当代社会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节食、饮食治疗、健身、美容产品、整容手术、瘦身药物、抗结缔组织药物等。”[6]身体大有吞并高傲在上的主体意识,身体通过无所不在的媒介将自己放置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广告、报纸、电视等传播媒介还有广场、商场、酒店这些实体空间都成为身体的背景和修饰。身体集中能量的全面突围,给予视觉感官“惊颤”性的体验,个体的自我意识保持独立的空间越来越少,身体的娱乐化和狂欢化通过呐喊、跳跃、购物这些无意识的行为获得极大的快感,感官的体验乐趣为身体的沉迷赢得坚硬的支撑,郁达夫的《沉沦》里不光是一群看不着未来的失落青年,也是沉溺于偷窥的视觉狂化而放弃了思考和面对现实。
消费营造出了满足个人身体欲望的不散视觉盛宴,身体是这一匠心之作的主角也是自乐其中的囚禁者。身体在现代性的科技进步中获得在场的身份,又跳进了没有痛苦的视觉囹圄,“世界只是对于认知理智才作为‘世界’而存在,而且主体的精神活动决定着世界的表现形式。”[7]身体陷入疯狂的“偶像”“包袱”世界,主体的自我意识失去警示作用,想象的狂欢引诱者贪婪的身体盲目行动,身体的体验是一场没有凶手的审美意识营销,资本意识正在为疯狂的消费者建一座只有梦没有痛的迪士尼监狱,完全乌托邦式的理想乐园,身体处其中就像是实现了人生意义的最大化,刘成纪曾言:“当代大众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围绕着身体建构的文化,其主题是欲望,其价值是身体性愉快,其实践是按照美的规律对人体进行的技术再造和改装。”[8]身体反抗变成了自我沉醉,解放意义也被欲望化体验消解,身体的解放成为诙谐的反讽。身体的获释是否像舒斯特曼所言,必须将身体与意识看成完整的一体?显然,当前丰富多彩的大众视觉文化不可能成为身心一元化实践土壤。
三、身体消费景观的符号化
消费大众的审美视觉在信息媒介转译和编码下,批判深思的锐目就仅仅剩下流涎贪婪的窥视。视觉器官在生理功能上承担了镜子的作用,将一切图像通过成像原理传达给脑中枢,但其文化功能——明辨是非——反而长久以来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当照相机出现和摄影商业化后,屏幕景观的复制给了人记录和创造的机会,所有的生活元素都可以进入屏幕来供人欣赏。技术的进步实现了电影和电视的彩色化,仿真的技术达到至真至幻的境地,“拟仿不再是版图、某个指涉物或实体的拟仿。它是通过一种没有本源或真实性的实现模型来产生的,它是一种超现实。”[9]技术的加持下真实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相对化,再造景象与自然景观的融合使得视觉窗口的非理性窥视常态化,视觉感官的文化批判功能正是在无意识的景观社会温存里,剩下了一幅没有筛选的洞孔。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说:“在现代生产条件下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积。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10]3庞杂的视觉画面和刺激给予了消费大众更为直接身体感官体验,理性意识——主体获得身体快感的最大阻碍——被放逐,不管是自然景观还是人造景观,两者的真实性不再成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实现这一差异的消失正是两种视觉空间里同质化的生活元素,最为重要的就人(身体)在两种空间里的出现将隔着的镜片消融。身体如何能占据视觉的中心呢?这与它的文化属性相关,身体的文化含义以及技术赋予它特有的功能属性,一切的视觉空间体验的中心最后都落在了身体上。
当消费变为一种视觉的体验和文化意义上的买卖时,身体审美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一形态的中心。后现代话语下的消费已经不再是柴米油盐这层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而是生存无虑的前提下可有可无的奢侈消费。所以,这种消费是特殊的狭义概念,有特定消费观念在起推动作用,当消费者身处其中时,并不会去刻意遏制自己消费行为,这背后的影响因子就是社交网的绵延不绝,没人能逃脱消费编制的虚拟网套。身体在消费的环境中延伸了自身的功能和意义,可视化的身体摆脱了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神学意义上的亵渎,获得消费者疯狂的崇拜。差异化的身体形态在商业审美意识的裹挟下,同化为单一的“偶像”身形,明星和时尚绑在了一起,精英引领的理性生活观跌地破碎不堪,先天的基因造就的身体被技术加工改造,数学中“黄金分割点”成了美容群体重塑自己的起点,除身体的美容,就连衣服的搭配和外露都成了一股风,明星的效应以及大众跟随表面是一种时尚的扩散,最根本的还是资本意识形态下能指符号的窥视和消费,大众需要自我社交网中的接受和认可,明星也是他们实现自我视觉体验和拥有同质化群体接纳的一个消费能指,真正明星个体离开了消费需求的能指符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身体符号化在消费语境中,慢慢演化成一种符号的暴力,形成了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快感和欲望经由编码成为时代的关键词,这意味着一种新的神话开始形成,并宰制了身体的其他维度。”[11]身体卸去肉体躯干的真实存在而完全符号化,编码的符号获得主体的绝对掌控权,没有所指意义的能指符号统摄着消费受众的视角,身体也变成多种姿态的在场。
身体空间场域的符号化是以隐喻和象征的方式显现,去中心化后的身体留下的只是一个众人追逐的虚幻,身体幻化为一个欲望的机器不断地运行获取视觉和感官体验。在寻找满足视觉欲的过程中女性身体变成了可消费的商品,当然,商品自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是联系在一起,商家和消费者只能拥有其中一个,身体的符号化使得自己变成了可标价的商品,这主要出现在女性身体的商品化,男性和女性在消费环境下形成了一种捕猎与被捕猎的关系,根由在于大量的男性消费者的存在,还有女性作为消费景观的文化观念根深蒂固的存在,女性在倡导女权的过程中将身体作为武器,反而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再一次将女性自我受压抑的负面形象(由男权建构私有财产和自由买卖)送进了消费大众的欲望视野。“身体写作”实践最终变为一种色情的消费,女性在开发身体上的有意展露和所谓的健康身形,都是男性消费意识观念规训和女性自身被窥视的自恋,吸引异性的眼球以获取心理上的满足和存在感,身体的本我形态被解构,建构了一种感性符号的身体景观,居伊·德波说道:“景观是一场永久性的鸦片战争,是一场根据自己的法则不断扩张的、精新设计的、强迫人们把货物等同于商品,把满足等同于生存的鸦片战争。”[10]15身体丢掉了基本存在的意义,已经完全景观化。
四、文化观念的认同:身体的他者化
技术和媒介是身体实现景观化的手段,媒介的无意识性松弛了视觉接受者的警惕。精湛的技术实现了对景象的复制和美化,摄影者和对象两者都是可调整的变体,摆拍、美颜不但让身体得到了复制,还处理和美化了对象所焦虑的部分。一旦成像后,呈现在屏幕观众眼前的身体完全理想化,镜框里的身体传递一切信息(穿衣、化妆、讲话、姿态)都成了标准化的公式,动态的画面删减和剔除很多空白点,留下的全是文化观念里早已潜移默化的形象,本雅明在《摄影小史》里说:“任何人都会发现欣赏一件美术作品,特别是雕塑或建筑,看摄影复制品要比观看实物容易理解得多。”[12]屏幕里的景观是审美意识形态过滤后,而彰显的共同文化观念,接受者不需要二次重新品味和翻译,语言艺术的作品恰恰是需要读者进入其中,填补一些不确定的信息,媒介呈现的视觉影像能够运用技术把所有阻碍观众接受的信息加工处理,影视观众根本不需要自己去连贯屏幕中信息,直观的景象整体性塞进大脑。当屏幕成为日常大众获取信息和休闲的中介后,身体这一独特景观迅速实现霸屏,偶像剧最为凸出之处就是消费者审美盲视和呆滞,只要有高颜值,演员的演技没人在乎;手机短视频像抖音、西瓜视频这些软件,全是卖弄身体获取浏览量,资本意识的营造,线上线下都流露着腐朽的身体买卖,网红女性为代表的群体,利用身体的获得流量和金钱,大众通过视觉观看获得视觉的体验,这种屏幕化的“看与被看”关系牢不可破,资本意识牢牢地将消费大众掌控在手中。
后现代以来以美国“垮掉一代”为代表青年通过不合作、反讽、低俗等手段和方式,扛起了反抗精英知识分子用心维护的理性秩序,把涂鸦、嘻哈、扮丑引入审美领域,在权利和秩序无法触及的空间,宣誓自我、冲击美学理念。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一代喜闻乐见的是视觉、听觉和身体的刺激,审美异化为一种肉体的欲望追求,美腐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视觉暴力,展览者让渡性感肉体与接受者支付流量和金钱,大众的审美下的身体异化为没有思维人造僵尸,伊格尔顿这样描述后现代文化中的身体:“身体是一种文化的构想,是如同男按摩师手中拍打的东西一样的充满想象的解释者手中的黏土。”[13]人造景观里的身体是意识形态操控下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回归,模特的走秀、美容手术、疯狂的减肥这些无处不在的观念正在塑造着统一的身体外形,身体的美有了可参考的标准,主体身体审美在景观社会失去了多样的差异美。景观社会里的身体超越了肉眼视线的瑕疵,滤镜修饰过的身体慰藉了主体现实生活的遗憾,技术宽解了身体幻想的个体,也消解了理性的身体意识,“你的身体不是它自己。而且,我的也不是。它正处在医药、运动、营养、减脂、卡路里计算这些后现代控制论力量的围攻之下。”[14]身体变成了他者的想象。
五、结语
视觉时代的人对自我身体进行了最大化的开发,人造景观中身体的实践丢弃了能动理性思维。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记录和界清一切的功能被视觉空间超现实的仿真消弭殆尽,摄影技术的进步通过镜头将身体拉近、特写、补光,呈现在镜框中身体获得了最为诱人的魅力,媒介包裹下的身体吞噬了主体的自反意识,多种媒介延伸了身体能指的象征意义,宗教贬低的肉体在消费时尚观念的包装下以感性和青春活力潜移默化地固化着身体自恋者非理性的可悲奢望。舒斯特曼对身体的定义:“身体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而根本的维度。身体形成了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最初视角,或者说,它形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融合的模式。”[3]13他所开辟身心一元的身体美学,面对视觉时代身体异化为一种能指符号的欲望化,理论高瞻远瞩与实践随波逐流大异其趣,人造景观中的身体放大了主体非理性的欲望,身体不再是作为一个因会劳动而区别于地球上的生命体,失去了特有的种类区分的人所拥有的只是不断获取视觉享受,身体就像一座水塔供养人类不是甘霖而是无感情的生物欲,景观境况下的身体拥有统一漂亮而没有言语的皮囊,图像定格了性感的身体,但却失真了主体身份,互联网和消费文化的崛起给了身体无限自由,同时,也将身体和意识二元对立关系打破,身体景观的强势吸睛正在营造一种快乐致幻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