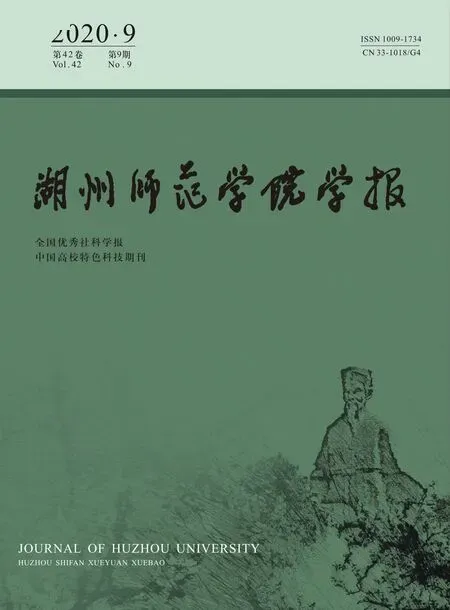“记言”“编言”与“撰言”*
——早期语类文献生成及文体嬗变述略
2020-01-18夏德靠
夏德靠
(湖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语”是早期社会十分重要的一种文类,“过去我们的印象,古代史书,‘春秋’最重要,但从出土发现看,‘语’的重要性更大。……它和它所记的‘事’和‘语’都已拉开一定距离,思想最活跃,内容最丰富,出土发现也非常多。”[1]202目前人们多从记言的角度去思考早期语类文献的生成与文体特征,并且也取得很好的实绩。然而,就早期语类文献生成,特别是其文体演进而言,仅仅重视“记言”是不够的,还必须分析“编言”与“撰言”行为。事实上,只有将这些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比较全面地揭示早期语类文献的生成与文体特征。
一、“记言”“编言”与“撰言”
在先秦时期,人们似乎对言语现象已经显露出极大地关注,可以说那个时代业已形成重言之风尚。人们如此重视言语,意味着人们已经认识到有意义的言论对于社会实践、道德修养所发挥的指导作用。《诗经·大雅·行苇》序云:“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耉,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2]1079“养老”是当时一种重要的仪式,《礼记·王制》孔疏分析说:“皇氏云:‘人君养老有四种:一是养三老五更;二是子孙为国难而死,王养死者父祖;三是养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养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视学之年,养老一岁有七。’谓四时皆养老。故郑此注‘凡饮养阳气,凡食养阴气,阳用春夏,阴用秋冬’,是四时凡四也。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乐,必遂养老。’注云:‘大合乐,谓春入学,舍菜合舞。秋,颁学合声。’通前为六。又季春大合乐,天子视学亦养老,《世子》云凡视学,必遂养老,是总为七也。”[3]420重视“养老乞言”,其用意在于“法其德行善言”,为实际的政治生活提供借资。毛传说:“乞言,从求善言,可以为政者。”[2]1079即通过“乞言”的方式所取得的“善言”,其目的是“为政”。其实,先秦时期重视言论的现象还有很多,在“乞言”之外,还存在规谏、咨询等情况。《国语·晋语八》记载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叔向对范宣子说:“吾闻国家有大事,必顺于典刑,而访咨于耉老,而后行之。”[4]45叔向向范宣子推荐訾祏,于是在訾祏的建议之下圆满解决这个困扰的争端。《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一种大型的咨政仪式:“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5]2762-2763这就是说,每当国家面临兵寇之难、徙都改邑及国君遴选这些重大疑难问题时,往往由小司寇负责集结万民来讨论。《国语·晋语三》载晋惠公为秦所囚,听说即将恢复自由时,立即派大夫郤乞转告吕甥,于是出现询立君的场面。[4]330又如当兵败栖居会稽时,勾践召集三军寻求纾解兵寇之难。[4]631需注意的是,先秦社会还存在“赠言”现象,刘向编纂的《说苑》载录几则先秦社会赠言的事例:
魏公子牟东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将去冉之山东矣,独无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几忘语君,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6]440
子路将行,辞于仲尼,曰:“赠汝以车乎?以言乎?”子路曰:“请以言。”仲尼曰:“不强不远,不劳无功,不忠无亲,不信无复,不恭无礼。慎此五者,可以长久矣。”[6]742
曾子从孔子于齐,齐景公以下卿礼聘曾子,曾子固辞,将行,晏子送之,曰:“吾闻君子赠人以财,不若以言。今夫兰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则易以匹马。非兰本美也,愿子详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闻君子居必择处,游必择士。居必择处,所以求士也;游必择士,所以修道也。吾闻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6]742
上述几则事例要么是送者要求被送者赠言,要么是送者赠言给被送者。这些“赠言”在内容上都呈现一种教益性质,例如在送别子路时孔子说道,人只有坚强才能致远,勤劳才会成功,忠诚才会有亲近的人,诚信才会有回报,恭敬才会有礼。这些格言式的话语蕴含深刻的意义。因此,从这些“赠言”行为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当时人们对言论的重视。
当然,这种重言传统的建构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即重视言论的载录,也就是所谓的“记言”。《汉书·艺文志》指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7]1715《汉志》认为历代王朝均设置左史以专门负责记言。当然,《汉志》“左史记言”的提法也引起人们的非议,清代的章学诚就曾经质疑说:“《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8]8我们认为,左史与记言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左史的有无事实上并不必然影响记言制度的存在。章学诚指责《周礼》没有“左史”的说法,可是《汉志》所说的“君举必书”无疑有文献依据。《国语·鲁语上》记载鲁庄公准备到齐国观社,曹刿在规谏中提及:“臣不闻诸侯相会祀也,祀又不法。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4]153这个说法也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三年》,韦昭对“君举必书”做了这样的解释:“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4]154韦氏的注释采自《礼记·玉藻》,这个说法虽然与《汉志》有些差异,但也肯定记言制度的存在。事实上,早期文献确实在很多地方出现描述记言的现象,而且也并不限于君主的言论。《大戴礼记·保傅篇》说:“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有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必书之。”[9]52这里的“过”恐怕不仅指行为的过错,应该包括言论。《鲁语上》记载臧文仲准备祭祀爰居,被展禽谏止,事后臧文仲说:“‘信吾过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书以为三筴。”[4]170“筴”即简书,《礼记·王制》说:“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郑《注》:“简记,策书也。”孔《疏》谓:“此一经论大史之官典掌礼事,国之得失,是其所掌,执此简记策书,奉其讳恶之事。”[2]418可见展禽对于臧文仲的一番谏辞当时即被史官用简书记录下来。《吕氏春秋·重言》篇载: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10]1156
这个事件也见于《史记·晋世家》,叙述有些出入,但均强调史官记言之职责。又《骄恣》篇载齐宣王为大室,春居谏之,宣王召掌书“书之”。[10]1405这些例证均说明当时社会存在记言的现象。
正是基于重言、记言这种风尚,于是形成记言文献。《礼记·内则》说:“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2]855这里谈到惇史的记录现象。对于“惇史”,郑《注》说:“惇史,史惇厚是也。”孔《疏》解释说:“惇,厚也。言老人有善德行,则记录之,使众人法,则为惇厚之史。”[2]855也就是说,史官记录的是善言善行,而这些善言善行能够为别人取法,因此,这些善言善行就成为一部“惇史”。《尚书·皋陶谟》述及“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孔疏指出:“天叙有典,有此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此皆出天然,是为天次叙之。天意既然,人君当顺天之意,敕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11]107-109柳诒徵对此做了这样的分析:“《皋陶谟》所谓五典五惇,殆即惇史所记善言善行可为世范者。故历世尊藏,谓之五典五惇。惇史所记,谓之五惇。”[12]3这个理解与《礼记》孔疏有一致之处,即将惇史理解为文献,不同的是,柳氏也将惇史视为史官的名称。
据此可知,先秦社会很早以来就出现重言风尚与记言传统,由此记言文献也得以形成。不过,就早期语类文献而言,其生成方式是多元的,除了“记言”之外,还存在其它的形式。比如《国语》,韦昭在《国语解序》中说:“(左丘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4]661按照韦昭的认识,《国语》显然是出自左丘明的编撰,事实也正是如此。又如《论语》,《汉书·艺文志》谓:“《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7]1717这同样表明《论语》也出自编撰。像《国语》《论语》这样典型的语类文献,单单用“记言”是难以说明其形成的,只有结合“编言”才能更好地阐释其生成过程。当然,早期语类文献的生成还有一种形式,比如《法言》,尽管这部文献是扬雄效仿《论语》而成,但是,它毕竟是扬雄撰写的。《法言》的生成,显然不是出自“记言”“编言”,而是“撰言”的结果。同样,汉代开始盛行的奏疏文献也出自“撰言”。因此,就早期语类文献的生成方式来说,大抵存在“记言”“编言”“撰言”三种形式。
早期语类文献存在的“记言”“编言”“撰言”三种生成方式,从发生角度来看,以“记言”为最早,其次“编言”,再其次“撰言”。然而,就早期语类文献生成而言,三者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混融,一般来说,混融的情形更为常见。比如《国语》《论语》,如上所言,是“记言”与“编言”的结合,而《新语》则是“撰言”与“编言”的结合,《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3]959
陆贾撰写十二篇奏文,刘邦及其大臣们是非常满意的,将这些篇章统合起来,名之曰“新语”。又如《新书》,它由《事势》《连语》《杂事》三部分组成,《事势》出自贾谊本人撰写,《连语》《杂事》的生成大体有四种方式:一是贾谊亲自撰写;二是就某一具体篇目而言,一部分源自编纂,一部分可能是贾谊撰写的;三是贾谊纯粹采用编纂方式完成的;四是出自门人的编纂。[14]可见《新书》的生成综合“记言”“编言”“撰言”三种形式。
二、“编言”的存在方式
作为语类文献的三种生成方式,“记言”“编言”与“撰言”的存在形态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记言”的存在方式比较单一,通常只是对人物言论的载录。比如“乞言”仪式,人们向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请益,而惇史负责载录的只是老人的言论,并不涉及其它因素。颇为遗憾的是,虽然文献提及先秦时期的“乞言”,但对于其具体过程则没有记载。不过,“乞言”仪式在后世仍然继续流行,举例来说,《三国志·魏志》卷四载:“(高贵乡公)诏曰:‘夫养老兴教,三代所以树风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纳诲,著在惇史,然后六合承流,下观而化。……其以祥为三老,小同为五更。’车驾亲率群司,躬行古礼焉。”[15]62高贵乡公躬行“乞言”仪式,任命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云:“帝乞言于祥,祥对曰:‘昔者明王礼乐既备,加之以忠诚,忠诚之发,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动乎天地,天且弗违,况于人乎?’”[15]62当高贵乡公向王祥乞言时,王祥对之进行训诫,史官将训诫之语载录下来。从这一例证来看,“记言”着重的只是人物的言论,这就表明“记言”的存在形式很单一。正是由于存在形式比较单一,“记言”对于语类文体生成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格言与对话体方面。王祥的言论体现格言的特征,至于对话体,《国语》《论语》中的一些对话也是单纯“记言”的结果,比如《论语·为政篇》载: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16]117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16]119
上述两则文本只是载录鲁哀公与孔子、季康子与孔子之间的对话,它们应该是单纯“记言”所形成的文本。
“撰言”对于语类文体生成的影响较“记言”要广泛。“记言”行为大都是被动的,往往只是对他人言论的载录,而“撰言”则不一样,它是主体对自身言论的载录。因此,由“记言”行为而形成的文献通常只是作为档案存在;相反,由“撰言”行为而形成的文献则往往表现为撰述。由于“撰言”行为出于主体的自由意志,那么,它对语类文体生成的影响就较“记言”行为广泛。在“记言”场合中,“记者”需依据他人言说方式而决定所采纳的“记言”体式,比如“乞言”仪式中重点关注的是三老五更的言论,因此,其结果呈现为格言的体式;倘若“记者”面对的是二人或多人的谈话,那么,他通常采取对话的“记言”体式。“撰言”行为则不受这些限制,撰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或实际需要而采取灵活的方式,比如陆贾撰写《新语》时采用专论体形式,而扬雄效仿《论语》而撰写《法言》,《法言》在很大程度上具备《论语》的文体特征,如对话、格言、言行两录等。尽管“撰言”与“记言”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就存在方式而言,与“记言”一样,也是比较单一的。比较起来,“编言”则复杂得多,或者说,其存在形式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原文移录、添加、合并、删改等,因此,它对语类文体的生成所起到的作用更为深远。下面从两个方面尝试论之。
三、“编言”与篇章“语体”
早期语类文献作为一种复杂的文类,其内部蕴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专论体,以及国别体、语录体、纪传体、世说体这些次生态文体。其中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专论体这些文体是基于篇章而言的,至于国别体、语录体、纪传体、世说体这些文体则是基于专书而言的。这些次生态文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编言”行为相关。因此,讨论早期语类文体的生成,就离不开对“编言”行为的分析。
《汉书·艺文志》提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7]1715在此基础上,刘知几指出先秦史官的传史方式经历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的演变,“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缺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17]8《汉志》“言为《尚书》”之说,以及刘知几言事相兼的主张,无疑涉及“编言”行为。尽管言事相兼的主张比起《汉志》的说法已经前进一大步,并且也能够较好地解释早期语类文献的演进。但是,相对于早期语类文献内部复杂的次生态文体而言,言事相兼的说法由于太过笼统而难以满足需要。因此,我们对“编言”行为需要做出尽可能详细的分析,以便更好地揭示上述次生态文体的生成。
早期格言大抵存在散见式与汇编式两种形式,散见式格言多见于人们日常谈话中的引用,这种引用一般不会改变其外在形态。汇编式格言与“编言”行为密切相关,其中又可分为:其一,汇集某一具体人物的言论;其二,主要汇集无主名的言辞。史佚是周初有影响的史官,《左传》《国语》多次征引其言论,这些言论大都具备格言的性质。然而,《左传》有的地方引用《史佚之志》,倘若综合考虑《左传》《国语》所引述的史佚言论,那么,《史佚之志》应该是史佚格言的汇编。同样,《左传》所引《仲虺之志》也当为汇集仲虺的格言。无论是《史佚之志》还是《仲虺之志》,人们是如何汇集、编纂这两部文献的,随着它们的失传,其详情不可得知。不过《论语》也汇集孔子及其弟子很多格言,此点后文还有细论。至于汇集无主名的言辞,据现有文献,人们进行这一工作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原有格言的体式。《逸周书》之《周祝》《王佩》两篇是汇合格言组成的文章,不同于一般的格言汇编,《周祝》通过对格言的整合,使之形成一篇专论。[18]同样,《王佩》紧紧围绕明德、治乱的思路而遴选相关格言,也表现为专论。《淮南子》之《说山训》《说林训》两篇也值得注意,《说林训》在收集的基础上又对所收集的格言进行编排,使之成为一篇独立的文章。《说山训》整体上是由格言组成的,不过还有其它一些成分,因此不能算是纯粹的格言专论体。在出土文献中,《为吏之道》不仅具备格言集锦的特征,也具有独立成篇的形式。《语丛》四篇作为格言集,其中《语丛》一、二、三还只是格言汇编,不过有共同的主题;而《语丛四》则已是一篇独立的文章。当然,前三篇结合起来表现一个相对完整的主题,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专论的特性,从而与一般的汇编有着差异。除此之外,《老子》是一部散韵结合的格言体,综合简本、帛本及通行本来看,《老子》81章主要呈现“核心文本+附加文本”的结构模式,它具有格言、解释及训诫三个基本元素,由此形成四种结构形态:①只有一个或多个格言;②格言+解释;③格言+训诫;④格言+解释+训诫。[19]209-211格言是四种结构的共同部分,显然属于《老子》的核心文本。有的学者根据这种现象曾做出如下推测:“《老子》文本的最早形式可能只是一些十分精炼而短小之文句,这些精炼化之语言乃是由‘一批’不知名但对当代政治社会有所反思之思考者所创发,就形成了《老子》之文本。形成文本之后,继续流传,而在流传之中再辅以口说,因此某些借着口说而阐释文本之观念乃转化成文字而加入以形成新的文本。”[20]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由此可见《老子》文本虽然也是出于对格言的整合,但与上述整合路径稍有差异,同时还存在对格言的阐释。这种对格言进行阐释的做法并不限于《老子》,比如《逸周书·史记》往往“先写警句训语名言,然后印证历史事实”,[21]199也就是说,《史记》篇中每一条格言之后都遴选史实加以说明,表面上看来,该篇似乎不能视为纯粹的格言汇编。然而,倘若从整体上来加以考察,这一模式其实建构了一个格言群。[22]
当然,“编言”行为并不限于格言。比如,《论语·卫灵公》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16]1065-1066据此,子张在绅带上书写的只能是孔子的言论,但是,在《论语》的实际文本中,除了孔子的言论之外,还存在“子张问行”“子张书诸绅”这样的成分。那么,很清楚,“子张问行”“子张书诸绅”应该是后来添加上去的。正是通过这种添加、补充,不仅交待孔子言论的来源,同时也凸显孔子言论的意义。当然,这一行为也改变整个文本的文体特征,即由原来的单纯记言转化为言事相兼的“事语”。又如《鲁语上》载:
莒太子仆弑纪公,以其宝来奔。宣公使仆人以书命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惮以吾故杀其君,而以其宝来,其爱我甚矣。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无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书曰:“夫莒太子杀其君而窃其宝来,不识穷固又求自迩,为我流之于夷。今日必通,无逆命矣。”明日,有司复命,公诘之,仆人以里革对。公执之,曰:“违君命者,女亦闻之乎?”对曰:“臣以死奋笔,奚啻其闻之也!臣闻之曰:‘毁则者为贼,掩贼者为藏,窃宝者为宄,用宄之财者为奸’,使君为藏奸者,不可不去也。臣违君命者,亦不可不杀也。”公曰:“寡人实贪,非子之罪。”乃舍之。[4]176
宣公告诉季文子说,莒太子为了我不惜杀掉自己的君父,替我赏赐莒太子城邑。不过,这番话并不是鲁宣公直接告诉季文子的,而是通过仆人转告的。可是仆人转告的是鲁宣公的书信,这样,文中的对话其实是对书信的引述。当仆人准备将这封书信送给季文子的时候,在路上遇到里革,里革将书信的内容做了更改。里革的这个行为既可视为鲁宣公与季文子之间对话行为的实现,也是本文的第二次对话。这次对话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提示鲁宣公与季文子之间的对话其实并未发生,亦即包含鲁宣公真实想法的对话并未发生;二是鲁宣公与季文子之间借助书信毕竟发生实质性的对话,季文子按照书信的指示驱逐了莒太子,不过这封书信是里革篡改过了的;三是鲁宣公与季文子之间的对话不但经过仆人这个环节,也经过里革这个环节,仆人环节只是促进对话的实现,而里革则确实参与这次对话。里革篡改书信,一方面可理解为是里革与鲁宣公的对话,里革通过篡改这一行为其实是对鲁宣公的看法表示反对;一方面可视为里革与季文子的对话,因为经过篡改的书信基本上代表的是里革的意思,而不是鲁宣公的意思。因此,就文中第一、二层次的对话而言,鲁宣公与季文子之间的对话只是表面上的,本质上是里革、鲁宣公之间的对话与里革、季文子之间的对话。但是文本给人的感觉则是鲁宣公与季文子之间的对话,这纯粹是编撰的结果。第三层次的对话是有司与鲁宣公之间,以及鲁宣公与仆人之间,只不过这一层次的对话被省略了。第四层次的对话又在里革与鲁宣公之间展开,这一对话应该是当面进行的,也是此文本真正实质意义上的对话。不过,就整个文本而言,虽然存在四个层次的对话,但真正意义的对话只存在于第四层次,至于第一、二层次的对话则是对书信的改造,其实是编言的结果。又如《论语·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陪孔子坐着,孔子希望他们谈谈自己的理想。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依次谈了自己的想法,孔子听后很赞同曾皙的看法,这是第一回合的对话。在这个回合中,孔子依次询问四个学生的理想,他们对自己的理想都做了表述。当子路、冉有、公西华离开之后,曾皙与孔子之间又进行第二回合的对话。曾皙希望孔子谈谈对子路、冉有、公西华他们言论的看法,孔子发表了自己的评论。[16]797-814整篇文本由师生之间的对话构成,就文本表面来看,我们觉得此次对话是自由的、随意的,很难说是出于有意的安排。然而,张履祥《备忘录》分析说:“四子侍坐,固各言其志,然于治道亦有次第。祸乱勘定,而后可施政教。初时师旅饥馑,子路之使有勇知方,所以勘定祸乱也。乱之既定,则宜阜俗,冉有之足民,所以阜俗也。俗之既阜,则宜继以教化,子华之宗庙会同,所以化民成俗也。化行俗美,民生和乐,熙熙然游于唐虞三代之世矣,曾皙之春风沂水,有其象矣。夫子志乎三代之英,能不喟然兴叹。”[16]816张氏的分析表明这个文本是经过缜密编排的,因为我们很难设想一次随意的对话在逻辑上会显现如此清晰的条理性。[23]156-159
在篇章“语体”中,“事语体”的形成与“编言”行为的联系更为密切。所谓“事语”,其根本特征在于“既叙事,又记言”。[24]这种“事”与“言”的结合,按照刘知几的说法,显然是出于言事相兼的“编言”行为。然而,就早期“事语体”而言,其内部形态也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在言事相兼的传史方式下,其具体的“编言”行为也是灵活多变的。据我们的考察,早期“事语体”包含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三种次生样式。[25]这些样式的存在,自然是“编言”行为引起的。前面已经提及《论语》“子张问行”章,这一章的中心无疑是孔子的言论,至于“子张问行”“子张书诸绅”是附加上去的,尽管这些成分也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改变不了孔子的言论在整个文本中的核心地位,因此,这一文本属于“事语体”言显事隐模式。当然,“子张问行”章是孔门弟子有意识编撰的。至于“言隐事显”与“言事并重”的形成,也自然出于“编言”行为,然而有时这种“编言”并不排除虚饰的因素,比如《国语·晋语五》载:
灵公虐,赵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则寝门辟矣,盛服将朝,早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赵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镇也。贼国之镇不忠,受命而废之不信,享一名于此,不如死。”触庭之槐而死。灵公将杀赵盾,不克。赵穿攻公于桃园,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实为成公。[4]399
钱钟书先生指出:“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咳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26]164-166《左传》记言是否都出自拟言、代言,此问题暂可毋论。然而就晋灵公派鉏麑刺杀赵盾这一文本而言,史官参与拟言,甚至是代言。这一文本有“晨往,则寝门辟矣,盛服将朝,早而假寐”的描述,这是鉏麑临终前所观察到景象,正是这一景象使得鉏麑陷于两难境地而最终选择自杀,但这一景象他人应该无法从鉏麑这儿获取的。也就是说,此段描述显然出于史官的想象。因此,在上述事件中,真正能确认为史实的是晋灵公派鉏麑刺杀赵盾以及鉏麑触槐而死,至于鉏麑所见所言,应该是出于史官的揣摩。但在整个叙述中,史官不但设想鉏麑的所见,而且也构拟鉏麑的所想,这样,整个文本的结构就非常完整。当然,使文本完整的方式有很多,史官之所以特意构拟鉏麑的言论,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史官记言职责的本能,更为重要的,通过鉏麑的言论,使整个情节发展变得非常自然。
因此,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这些篇章“语体”,并非都单纯出于记言传统,而是与“编言”行为密切相关。不过专论体的情况要复杂一些,有的出自“编言”行为,如《周祝》《王佩》等;有的则出自“撰言”,如汉代盛行的奏疏。总体来说,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专论体这些多元篇章“语体”的生成与“编言”行为紧密相关。
四、“编言”与专书“语体”
“编言”行为除了存在于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专论体这些篇章“语体”之中外,其实在国别体、语录体、纪传体、世说体这些专书“语体”中也得到体现。
“国别”一词似乎最早见于刘向撰写的《战国策书录》,但“国别体”显然是由《国语》奠基的。《国语》的成书大致经历三个过程:首先,先秦史官存在分职载录的职能,形成一个记言传统;同时史官经历了由王朝而侯国而卿大夫家的下移过程,这样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语”文献。这是最原始的文献,在本质上可视为一种档案式的记言文献。其次,周代非常重视文献的编纂、整理工作,各国史官对于本国的那些属于档案的“语”文献也进行整理、编纂的工作,由此产生各国之“语”。最后,左丘明在收集、讽诵各国之语时,对手中的“语”文献进行整理、遴选,最终按照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排序而编纂为《国语》这部文献。《国语》的形成最终奠定“国别体”,然而讨论《国语》文体的生成,仅仅止步于此是不够的。以“国别体”指称《国语》文体,只是立足于专书的角度。其实《国语》文体显然还蕴含篇章文体这一层内容。从篇章文体来看,《国语》一个显著特征在于“三段式”。《国语》中的人物对话大抵源于规谏活动,因而谏辞文献属于《国语》的核心文本。一般来说,史官载录的主要就是这部分文献,然而我们现在接触的《国语》文本往往是“起因+谏辞文献+附加文本”或“起因+谏辞文献”。在谏辞这样的核心文本之外,无论是“起因”还是“附加文本”,它们大抵是后来编撰的。比如,《国语·周语》“恭王灭密”章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这句话叙述事件的缘起,接着载录一段记言,这是密康公的母亲针对儿子的行为所提出的规谏,最后记录后果。“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这个结果实际上又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康公不献”,二是“王灭密”。“康公不献”针对其母的规谏来说可以说是一种结果,而两个次结果之间又形成一种因果关系,“不献”的行为引发“灭”的后果。从编纂的角度来看,“恭王灭密”这个文本显然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一年”这个用词提示“恭王灭密”文本至少经过两次编纂。正是由于“三段式”的存在,《国语》很多文本就呈现“事语”的特征。
《汉书·艺文志》认为《论语》是门人依据孔门笔记而编纂的,此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论语》文本的形成过程。而按照这个说法,就需要分析孔门笔记的文本样式及门人如何利用这些笔记的问题。即使从有限的资料出发,孔门笔记的存在是用不着怀疑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笔记的存在样式。依据《论语》所载“子张书诸绅”来看,子张书写的只能是孔子的言论,那么,可以想见孔门笔记大抵以载录孔子言论为主。这一点还可以从其他一些资料得到印证,比如《孔子家语·弟子行》篇载孔子与子贡讨论“知人”,孔子依次评论伯夷、叔齐、赵文子、随武子等人行为,子贡“退而记之”;又《入官》篇载子张向孔子请教入仕之道,孔子详细解释“安身取誉”,子张“遂退而记之”,这些记载表明弟子注重记录的仍然是孔子的言语。由此,可以基本推定孔门笔记主要以载录孔子言论为主。然而,《论语》文本虽然以记言为主,但同时还存在记行与记言杂糅,甚至单纯记行的文本。这样看来,孔门弟子在编纂过程中显然对笔记进行重组。这种重组行为,据分析,大约有粘合、扩充、原文迻录、改造等形式,例如粘合,《为政篇》载: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6]79
这一文本首先叙述孟懿子向孔子询问“孝”,孔子以“无违”作答;接着孔子对樊迟转述孟懿子向他请教的事实,樊迟追问具体所指,孔子详细对他加以解说。可见此章前后两个部分是相对独立的文本,存在两个主题,即懿子问“孝”一节构成自足的一个层次;孔子告樊迟是另一层次。这两部分原本属于不同语境下的对话,它们聚合在一起显然是编纂的结果。因此,从孔门笔记到《论语》,固然存在原文迻录的现象,但还存在其它编纂形式,而正是这些编纂形式最终奠定《论语》多元的文体形态。一般认为《论语》开启语录体这一语类文献体式,而根据相关的考察,语录体呈现言行两录的特征。据统计,《论语》20篇可分为512章,其中纯粹记行的为46章,记言的为405章,记行与记言杂糅的为61章。这些数据不但表明《论语》确实存在单纯记行的文本,同时也显示记言占据主要地位。至于《论语》中的记言文本,又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格言体,为267章;二是问对体,为138章。格言成为《论语》的主流形态,这种情形不难理解,孔门笔记原本就重在记录孔子言论,《论语》自然也承继这种特征。至于《论语》的问对体,一般表现为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对话,但在有的问对体中,不仅仅载录双方或多方的对话,同时还涉及一些基本情节的描绘,于是出现事语体。《论语》中的问对体与事语体,基本上出于“编言”行为。
纪传体是否来自司马迁的创制,历来存在很大的争议,我们以为五体出于司马迁的创制。[27]白寿彝先生指出:“《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记言和记事的综合。”又说:“《史记》里最大量的篇幅都是把记事和记言综合在一起。记事和记言相结合,如果以人物为中心,就成为人物的传记。纪传体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中心,是记言和记事相结合的必然产物。”[28]78-79记言和记事的综合,其实就是言事相兼传史方式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纪传体不仅可以纳入语类文献的范畴,同时也意味着纪传体的书写也存在“编言”行为。一般而言,本纪、世家大抵采取编年的形式,但就《史记》而言,情形颇为复杂。以本纪为例,《史记》十二本纪呈现为以王朝和以帝王为单位两种形式,亦即王朝本纪与帝王本纪的混合。《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大体可归于王朝本纪行列,其中《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属于严格的王朝本纪,然而《五帝本纪》载录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传说帝王的事迹,他们并不属于同一王朝;至于《秦本纪》叙述的主要是秦国的历史,也不是一个王朝。司马迁之所以采取“王朝本纪”的形式,大约受到《尚书》《国语》的影响。《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个朝代,《国语》包括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这种以朝代或国别为单位的编纂方式很可能启发司马迁设置“王朝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七篇属于“帝王本纪”,它们是专为某一帝王设立的。不过,《秦始皇本纪》并不纯粹载录秦始皇事迹,同时还载录二世及子婴二代史实,实质上涵盖整个秦王朝,似应归入“王朝本纪”系列。至于项羽与吕太后,二人并非帝王,但司马迁还是将他们立为本纪。由于《史记》本纪书写对象存在这些差异,因此,《史记》本纪并不严格采取编年的形式。这样,《史记》本纪叙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如《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以及《项羽本纪》(包括部分《周本纪》),它们没有或无法有确切的编年,这样只能叙述各帝(王)的事迹,主要表现为言行的载录。从文体的角度来看,这些本纪的书写很接近《尚书》《国语》;二是有比较明确的编年,“帝王本纪”主要属于这种情形,不过章学诚说:“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8]8也就是说,《史记》“帝王本纪”虽然效法《春秋》编年体形式,可是同时又将典谟之类文献写入其中。因此,《史记》本纪的整体叙事与《春秋》并不一样,它更多地与《国语》《左传》相似。整体言之,在无法确切编年的情况下,只有依据世系编排史事,于是采取《国语》的叙事方式;倘若有确切的编年,则采取《左传》的叙事方式。世家的体例与本纪相似,大抵取法《左传》,间或也采取《国语》的书写方式。至于列传,由于没有编年的限制,其叙事显得灵活自由,它重在叙述人物的言行,因此同《国语》接近。不过,纪传体对于人物言论的采录,有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原文迻录。比如司马迁在采用《尚书》时,通常会做一些“翻译”的工作,这是人们所熟知的。又如《汉书》中的《陈政事疏》,此篇与《新书·事势》有着紧密联系。班固在撰写《贾谊传》时对《事势》进行了整合,主要采取舍弃、改写、添加这些编纂手法。《新书》之《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五美》《制不定》《俗激》《时变》《孽产子》《亲疏危乱》《解县》《威不信》《势卑》《保傅》《礼察》这些篇目参与《陈政事疏》的建构,不过,班固在书写过程中并不按照这些篇目在《新书》中的顺序来组篇,而是打乱了这个次序。具体到每一篇,班固又根据实际需要对它们进行遴选、摘录、改写等工作。[14]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陈政事疏》应该是贾谊与班固合作完成的。
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卷十三“唐语林”条明确将《世说新语》命名为“世说体”,在他看来,“世说体”的特征在于分门记载人物言论。[29]559应该说,晁公武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世说体”的本质。倘若做进一步的考察,不难发现《世说新语》基本上继承了《论语》的各种文体形态,正是在以《论语》为代表的“语录体”之基础上,通过门类的设置,最终完成“世说体”的创制工作。前面已经指出,《论语》是孔门弟子通过对孔门笔记采取粘合、扩充、原文迻录、改造等形式而完成的,而《世说新语》的生成事实上也经历类似的过程。首先从材料的渊源来看,王能宪分析说:“刘义庆编撰《世说》的材料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类是与《世说》同一类型的记载人物言行的轶事小说,如西晋郭颁的《魏晋世语》,东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第二类是当时的史书,据叶德辉编《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刘注中引用有关魏晋的史书大约五十种,如《魏书》、《魏略》、《蜀志》、《吴书》、《晋阳秋》、《续晋阳秋》,以及多种《晋纪》和《晋书》等,这些虽说是刘注所引之书,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亦当为义庆采录之书。第三类是当时的杂史,叶德辉《引用书目》‘杂传部’列有各类人物杂传等120余种,如各种《名士传》、《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以及一些名门大族的《别传》、《家传》、《世谱》,乃至有关释道的《高僧传》、《仙列传》等等,这些也应当在刘义庆所采录的范围之内。”[30]45-46这个分析大体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刘义庆在编撰《世说新语》时所引述的材料主要是《魏晋世语》《语林》《郭子》及各种别传、家史、家传,比如现存《语林》185条中有80条见于《世说新语》,而现存《郭子》佚文84则,其中77条见于《世说新语》,从这些数据来看,可以想见《语林》《郭子》在《世说新语》编撰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那么,刘义庆又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料的呢?王能宪分析说:“义庆纂缉编撰之法有三:一为简化;二为增添;三是个别字词的润饰。”[30]61范子烨指出“《世说》编者之纂缉旧文,通常用五种方法”,即简择法、增益法、拆分法、兼存法及附注法。[31]13-23尽管提法各异,但有些是相通的。比如简择法相当于“简化”,而所谓“增益法”也大致相当于添加增润。对于“简化”,王能宪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省去原文中字里仕历等介绍,径直进入叙述人物故事”,二是“糅合浓缩原文”,三是“截取原文中最具特色的秀句丽词”。举例来说,《世说新语·识鉴篇》载:“褚期生少时,谢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仆不复相士。’”[32]481刘《注》引《续晋阳秋》曰:
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孙,秘书监韶之子。太傅谢安见其少时,叹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复论士。”及长,果俊迈有风气。好老、庄之言,当世荣誉,弗之屑也。唯与殷仲堪善。累迁中书郎、义兴太守。女为恭帝皇后。[32]481
重视人物家世、郡望、履历的记载,这是魏晋史传文献的通例,也是门阀制度的体现。然而,刘义庆只是关心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言行,并将这部分内容截取出来,这就是简化的手法。当然,对于被截取的内容,刘义庆又再度加工,如将“太傅谢安见其少时”改为“褚期生少时,谢公甚知之”,通过这种更改,表明谢安很了解褚期生,《续晋阳秋》中的“叹曰”被改为“恒云”,可见谢安对褚期生的一种关爱,同时也对自己相士的自信。据《续晋阳秋》的记载,褚期生后来的发展确实印证谢安的判断。又如《赏誉》载:“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刘《注》引虞预《晋书》曰:
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人。父潜,魏太常。秀有风操,八岁能著文。叔父徽,有声名。秀年十余岁,有宾客诣徽,出则过秀。时人为之语曰:‘后进领袖有裴秀。’大将军辟为掾。父终,推财与兄。年二十五,迁黄门侍郎。晋受禅,封钜鹿公。后累迁左光禄、司空。四十八薨,谥元公,配食宗庙。[32]499
据虞预《晋书》,上引《世说》的“谚曰”其实是时人对年幼裴秀的评价,属于一条人物品评。虞预还详细交待裴秀的家世、生平,通过这种叙述,使人明白这条评论出现的缘由。可是,刘义庆并不关心这一过程,他注重的是品评的结果。至于“兼存法”,有同条兼存与异条兼存,所谓“同条兼存”,是指“某一条在记述某一故事或某种言语之时,标示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说法”,[31]16按照范子烨所举例证来看,“同条兼存”即“或云”,而“异条兼存”则相当于“存疑”。所谓“拆分法”,就是“将旧文之某一条拆开,而裂为多条”,[31]15如《规箴篇》第八、九则:
王夷甫妇郭泰宁女,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预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都大侠,犹汉之楼护,郭氏惮之。夷甫骤谏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卿不可。”郭氏为之小损。
王夷甫雅尚玄远,常疾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令婢曰:“举却阿堵物。”[32]651-658
按《太平御览》引《郭子》云:“王夷甫雅尚玄远,又疾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妇欲试之,夜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阅之,令婢举阿堵物。妇,郭太宁女,才拙性刚,聚敛无厌,夷甫患之。”[33]1050据《太平御览》,《郭子》的这些内容是作为整体存在的,而刘义庆在编撰时却将其析为两条。整体言之,刘义庆对所辑录的材料进行简化、增益、移录、兼存、附注等工作,基本上完成文本的整理。在此过程中,虽然不排斥刘义庆自行创造条目的可能,但绝大多数属于纂辑旧文。
因此,就语类文献而言,由于早期社会的重言风尚与记言传统的存在,最终催生一批记言文献。从文体的角度来看,这些记言文献载录的主要是人物言论。可是,早期语类文献尽管以记言为其根本特征,但同时还包含其他因素。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文类,早期语类文献其实有着多元的次生文体,不仅存在篇章意义上的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专论体,而且还存在专书意义上的国别体、语录体、纪传体、世说体。这些次生文体的形成,与“编言”行为密切相关。正是不同的“编言”样式,从而导致不同次生语体的生成。当然,一般而言,篇章语体先于专书语体存在,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有时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是相伴而生的,此点是不难从前面的分析中领会到的。总而言之,我们只有将“记言”与“编言”“撰言”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比较好地揭示、解释早期语类文献的生成与文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