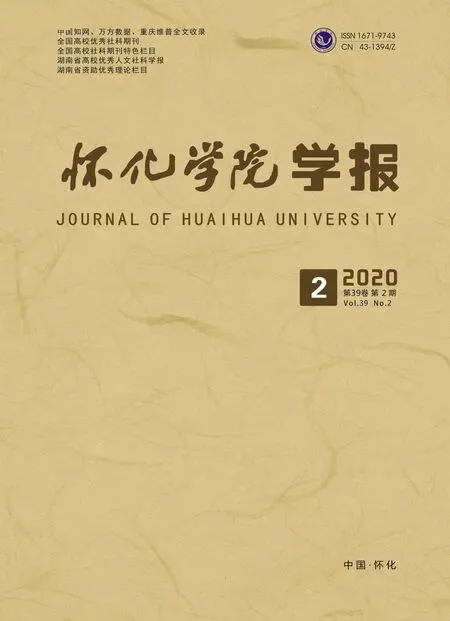《疯癫亚当》三部曲的动物伦理思想
2020-01-18郑婷婷
郑婷婷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福建福州350117)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获得过世界文坛众多重量级大奖。阿特伍德十分关注加拿大的民族、女性、人权、自然的现状与发展,通过文学作品对滥用科技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灾难表示担忧,是一位极具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疯癫亚当》三部曲,也称为末世三部曲,包括出版于2003年的《羚羊与秧鸡》、2009年的《洪水之年》和2013年的《疯癫亚当》三部小说。阿特伍德为读者描述了一个被科学技术摧毁的未来世界里人类幸存者带领着一个新物种艰难前行的故事,表现了对人类现实的严肃思考以及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在三部曲中,动物成为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动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动物,而是科学技术、消费社会的产物。例如,专为人体器官移植设计的转基因猪,没有眼睛没有大脑只有嘴巴的鸡肉球,狼犬兽、魔发羊、狮羊、浣鼬等都是基因工程的产物。科技天才秧鸡还创造了理想人类“秧鸡人”。这个新物种在一场“无水的洪水”瘟疫后取代人类在地球上生活。阿特伍德通过生态预警小说警示人类无视自然规律、滥用生物技术导致的生态伦理危机,并提出面对这样的未来,人类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处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本文以《疯癫亚当》三部曲为研究对象,以动物伦理为研究视角,挖掘小说中不同的动物伦理思想,反思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揭示深远的生态内涵。
一、人性与动物性二元对立
西方人对待动物的态度主要源于犹太教和古希腊文化两个传统。《圣经·创世记》宣称,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只有人类有灵魂,上帝希望人类管理和支配其他的动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人与动物之间建立了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植物就是为了动物的缘故而存在的,而其他动物又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大自然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创造了所有的动物”[1]23,动物低于人类,人类可以随意利用和处置动物。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动物是机器”“无机的自然界是机械的,有机的植物界也是机械的,连动物界都是机械的”[2]27,认为动物与时钟一样无法享受快乐、体验痛苦或其他感觉。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是动物机器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都认为动物没有理性,不具有道德地位,对人类只有工具价值,人类对动物不负有道德义务。动物机器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否定了自己的动物性,夸大了人性中的理性,将人性与动物性对立起来。《疯癫亚当》三部曲中动物大灭绝现象以及大院精英和废市民众对动物的态度体现了人性与动物性的二元对立。
(一)大院与基因动物
小说里的未来世界被一群资金雄厚的高科技生物大公司控制,各大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大院,大院里住的全都是科技精英,他们崇尚科学技术。为了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或满足科学幻想,科技精英们热衷于创造动物,他们觉得“创造一种动物是如此的有趣,它让你觉得你像是个上帝”[3]53。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需求,科技精英们致力于发掘动物的新用途,利用生物基因技术将动物改造得面目全非,并用基因动物进行实验。吉米的父亲是奥根农场的基因研究专家,负责开发器官猪项目——专为人体器官移植设计的转基因猪。器官猪体内长着可以移植给人类的组织器官,“一只器官猪身上一次长五六个肾”[3]24,这使得器官移植操作起来简单廉价多了,而且可以避免排异反应。科技的运用划分了人与动物的等级。在经济利益面前,基因动物沦为商品和机器,对人类只有工具价值。
吉米长大后,受好友秧鸡邀请参观沃特森·克里克学院最新的研究项目——鸡肉球,“一个像大皮球的物件……里面伸出二十根肉质粗管,每根管子末端各有一个球状物在生长,一个生长单位可以长十二份”[3]209。鸡肉球被去除了眼睛、大脑等与消化吸收无关的器官,只留下所谓的嘴巴,其实就是倒入营养素的口。鸡肉球生长速度惊人,并根据人类不同的需求,两周内长出鸡胸脯、鸡腿肉等不同产品,这样的生物怪物迅速垄断了肉食品市场,缓解了人类的消费需求。小说中人类按照自己意愿改造的自然物种很多。例如,浣鼬、浣熊和臭鼬的结合体,没有浣熊的攻击性,没有臭鼬的臭味,乖巧可爱,是完美的宠物选择;狼犬兽,外表像狗一样可爱,见了人尾巴摇个不停,可一旦去拍它,便将人的手一口咬下。
阿特伍德看到人类滥用生物技术随心所欲地改造物种,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我是上帝,我会很不安。他创造了一切,并且认为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现在人们正在这件艺术品上到处胡乱涂改。”[4]429创造这些异化动物的内在驱动力是人类的消费需求,异化动物丧失了自然赋予它们的动物性,使动物呈现出物化的状态,丧失了动物生命的尊严。
(二)废市与珍稀动物
小说里的废市是下层民众生活的地方,治安混乱,破败不堪;民众自私冷漠,尔虞我诈,生活在贫困无助中。废市民众贪图享乐,倒卖珍稀动物的皮革,以食用珍稀动物为乐。托比租住的房间楼下就是一家以稀有动物的毛皮做原料的高档女装作坊。顾客们以穿着的毛皮大衣作为炫富的资本,因此希望动物毛皮是货真价实的;而服装店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在密室里现杀现卖。“他们在柜台上出售万圣节的道具服……转身回到密室熏制兽皮……偶尔还会听见动物的咆哮和哀号……他们剥皮的畜肉统统卖给一家名叫‘生珍’的美食连锁餐厅……但是在私人宴会厅里,你可以吃到濒临绝种的动物。”[5]32-33
遗迹公园北面边界处的停车场举办了一场“生命之树”自然物材交易会,吸引了很多赶时髦的上层人士。“上帝的园丁”摊位边上有很多披着厚重昂贵皮革的阔佬富婆路过,让瑞恩好奇的是“穿戴这些皮具的人对另一个生命的皮肤紧贴着自己的肌肤有何感觉”[5]145,然而阔佬富婆们却表现出不以为然的表情,反正动物又不是他们杀的,何必浪费动物的毛皮呢!
本该与人类和谐共生的珍稀动物成为商品,被残忍杀害,血肉成为人类的盘中餐,皮毛成为人类炫富的资本,满足了上层阶级的时尚需求,生命的尊严被践踏。
二、人性与动物性的统一
传统的动物伦理思想将人的人性与动物性二元对立起来,语言、理性、道德成为区别两者的判断标准,对理性的崇拜推高了人性,贬低了动物性。人类和动物的基因排序有极高的相似性。人类是由动物进化来的。由于本能的需要,人类仍然拥有自然性,我们称为动物性,如食欲、性欲等一般动物性行为。
阿特伍德认为,动物性是人性的基础,人是人性和动物性的统一体。“亚当第一”在布道时重申了人类的灵长类血统,即使傲慢的人类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但人类的胃口、欲望和情绪都具有灵长类的本性,这是无法否认的,科学证明了这一点,DNA使人类与动物紧紧相连。在赞美诗中,“亚当第一”请求上帝去除人类心中的骄傲,警告人类谨记动物内在,不要以动物性为耻辱。阿特伍德指出,“我们所怀有的种种信念和想法,到了其他动物那里就成了与生俱来的本能”[5]240。
性欲是人类内在的动物性。小说提到了吉米和秧鸡无法控制自己的性冲动,与女性性交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喜福多”药片表面上是为了解决人类纵欲的后顾之忧而研发出来的。这种药不仅可以抵抗性病,提高性欲,还具有控制生育、延长青春的功效。“喜福多”给人类带来高质量的性生活,又是一种安全可靠的节育产品,因此,一经问世就炙手可热。正因为如此,秧鸡在设计新人类的时候将性设计成不再受到荷尔蒙和冲动的驱使,而是一种机械性的交配行为。食欲也是人类内在的动物性。“无水的洪水”爆发后,人类灭绝,吉米带领秧鸡人在一片废墟中觅食,还得警惕四周器官猪、狼犬兽这些基因动物的攻击。面对饥饿,人类的文明与理性原则毫无意义,生存才是最基本的需求。吉米身上更多体现出人性中的动物性,而秧鸡是理性工具的代表,他们对待动物的态度截然不同。吉米小时候看到焚烧动物,不断地问父亲焚烧动物的原因。父亲告诉他这些动物被感染了,吉米为无法拯救动物而感到内疚。虽然奥根农场承诺器官猪死后不会被做成腌肉或香肠,但在肉类稀缺的背景下,猪肉制成的各种食物仍然频繁出现在员工餐厅的菜单上。吃饭的时候,大家会开玩笑说又吃器官猪馅饼了。吉米食不下咽,因为他认为器官猪是和他一样的生物。吉米视动物为伙伴,对变异动物表示同情,认为人对动物负有责任;而秧鸡视动物为实验品,根据消费需求像机器零件一样对动物进行重组。阿特伍德选择吉米带领“秧鸡人”在新世界重生说明了他认为人类最本质的特征是动物性,人类应该尊重动物权利,保持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关系。
三、反思人类与动物的关系
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从人的角度论证动物的伦理地位,认为动物能感受痛苦,人类对动物负有直接义务。20世纪上半叶,德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在《文化与伦理》中提出了敬畏生命伦理,即不仅要敬畏人的生命,而且要敬畏动物和植物的生命,生命没有高低和贵贱之分。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了大地伦理学说,即大地是由土壤、水、植物和动物等组成的相互依赖的生态共同体,人类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员。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污染,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人类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彼得·辛格在边沁功利主义基础上提出了动物解放论——所有动物一律平等,认为动物是有感知力的,进一步论证人应该增加动物的利益,把道德关怀从人类扩展到动物。辛格关于动物解放的观点集中在《动物解放》一书中,这本书被称为“动物保护运动的圣经”。后来,美国动物权利理论研究专家汤姆·雷根出版了《动物权利的理由》,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动物的权利。雷根认为,动物也有意识和情绪,与人类一样都是生命的主体,具有自身所固有的价值,与人类一样具有道德权利。西方动物伦理思想递进式的发展体现了人类道德的进步和文明的提升。20世纪70年代,环境伦理体系逐渐成熟,动物伦理成为环境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特伍德的动物伦理思想是通过小说中的环保宗教组织“上帝的园丁”表现出来的。“上帝的园丁”有自己的圣人、宗教节日和教义,批判人性与动物性二元对立,倡导动物与人类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思想。基于洪水之后上帝与所有生物立约,“上帝的园丁”认为“动物不是毫无感觉的物体,也不是切碎的肉块”[5]93。动物和人类一样拥有对生命的平等权利,动物不为人类而存在,它们拥有属于自己的固有价值和权利。“上帝的园丁”有许多宗教节日是以动物的名称命名的,如鼹鼠日,通过庆祝鼹鼠节,引起人类对动物界边缘物种的重视;四月鱼节,借此呼吁人类对海洋动物的关爱;狡蛇节,借蛇的智慧,希望人类认识到动物性是人性的基础,顺应自然本能,遵循自然规律。园丁们遵循自然的生活方式,平时吃素食,养殖蜜蜂,培植菌类,用蛆虫疗伤。皮拉是“上帝的园丁”的成员,养殖蜜蜂和培植菌菇是她的专长,并把本领授予托比。皮拉说:“你永远可以向蜜蜂倾诉你的烦恼。”[5]102皮拉死后,托比常与蜜蜂对话,视蜜蜂为朋友,认为蜜蜂有灵性,是连接生者与死者、往返于现在与未来的信使。“亚当第一”在布道中庆祝鼹鼠节,庆祝地底下的生活,赞美了被人们轻视的不受欢迎的存在。人们很容易轻视那些边缘的物种,觉得他们可有可无。但事实是,离开它们人类将无法生存。“亚当第一”列举了眉毛虫、钩虫、阴虱、蜱虫这些不受欢迎的存在,它们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执行着任务。腐尸甲虫和细菌将腐烂的肉体分解,回归自然,滋养万物。如果没有蚯蚓、线虫、蚂蚁不停地翻弄土壤,大地就会变成像水泥一样杂乱坚硬,生物将要灭绝。“想想蛆虫和各种霉菌的抗菌特性,想想蜜蜂酿造的蜂蜜,还有蜘蛛结成的网,对伤口的止血特别有效”[5]166,这些是大自然为各种疾病准备的解药。“亚当第一”认为各个物种对地球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肯定了不同物种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人类和其他物种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与动物是互为主体的关系,是共生的关系。
加拿大特有的自然地貌以及阿特伍德童年经常跟随身为生物学家的父亲丛林旅行的经历,使得阿特伍德创作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动物伦理思想,折射出作家的动物观,并加深了作品的生态内涵。人类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加剧了动物的商业性捕杀,许多物种濒临灭绝,破坏了生态平衡,不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预警小说,《疯癫亚当》三部曲意在揭示人类对动物灭绝的漠视、对生物科技力量的过度崇拜和滥用以及贪图享受、唯利是图。三部曲并非科幻小说。阿特伍德创造了一个与现实生活近乎平行的另一个世界,深入挖掘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警示人类必须认识到自己人性与动物性的统一以及人与自然与生态系统的统一,同时预警盲目崇拜科技导致的生态伦理危机,批判大院和废市体现的人性与动物性二元对立的思想,并通过环保宗教组织“上帝的园丁”表达人与动物同为生命主体、人与动物共生、人性与动物性统一的生态伦理思想。阿特伍德通过三部曲小说呼吁人类关注动物的生存状况,反对虐待和捕杀动物,倡议客观平等地对待一切动物,构建理想的动物伦理思想,促进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