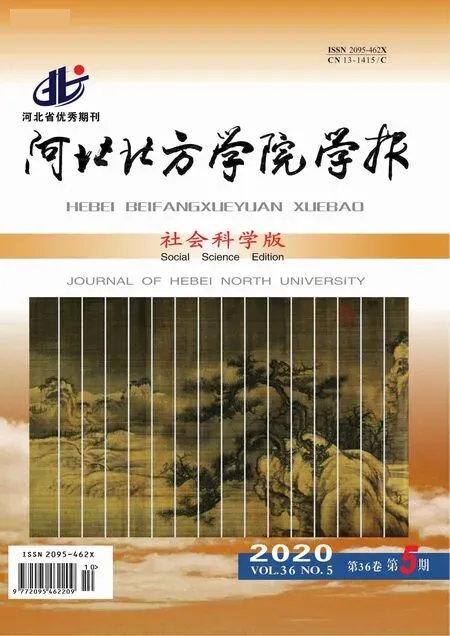薛瑄主敬修养论及其实践之学
2020-01-18龚瑞
龚 瑞
(新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薛瑄(1389—1464),明初著名理学家,“河东学派”开创者,其思想特色主要在于对理的内化与实践,因而被世人称为“明初理学之冠”与“实践之儒”。他注重“践履”的特色代表了“河东学派”的发展方向,也是推动河东学派后期掀起为学之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明初朱学独尊和趋向僵化的思想环境下,薛瑄以“复性”为宗旨,注重“躬行践履”,强调在具体的修养过程中进行主体性的内向探索,矫救朱学繁琐僵化之蔽。在此过程中,薛瑄主张以“敬”涵养身心,并将之作为“学以至圣”的重要途径,试图在实现“复性”境界的进程中涵养心体,培育内在的道德意识。
一、心肃容庄
作为一种修养方法,“敬”在宋明时代理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中有较大影响。理学重要代表人物程颢、程颐和朱熹皆把“敬”作为自身的修养工夫。程颢把“敬”与“诚”相联系,偏重于“诚敬”的修养方法,主张以“诚敬”存养身心[1]81。程颐则以“敬”论“静”,更加注重内心的平静与外貌举止端正的双重作用[1]81。朱熹在继承二程思想的基础上把“敬”的思想“具体化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2]21,这种观点也是其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一向推崇程朱理学的薛瑄也承继了程朱以“敬”为主的修养工夫论,但他并不只是完全承袭程朱关于“敬”的思想,而是将“敬”落到具体的实际行动中反求诸己,注重培养善的道德本心,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醇儒”。
薛瑄关于“敬”的表述有“居敬”“持敬”“主敬”“恭敬”“敬身”“诚敬”“敬慎”“敬德”“笃敬”“敬谨”“心敬”和“自敬”等。他没有特意区分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但从其所阐述的“敬”的不同侧面及使用“敬”字的语境差异中,可以把握他所指向的精神脉络。
“敬”是修养心性的枢要与根本。薛瑄认为,“是知‘敬’之一字,乃直内之枢机,养性之本根”[3]625,“敬”的修养工夫始终提醒着主体要收敛身心,通过心体的涵养操持具体事务,而“敬”之所以为修养心性的根本就在于“敬”对心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主敬则天理存而心实,外患自不能入”[3]889。做到了“主敬”,此心就实现了“存天理”的目的,心就不能容纳外物,也不会被外物所侵扰,而是被“敬”彰显出来的人的道德品德所充满。他主张以“敬”存养内在的心性,而持敬之心的目的就是要行敬之事,在行为上将“敬”发挥出来。薛瑄将“敬”和修养心性结合起来,使“敬”和“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并作用于外在的具体行为,突出实践意义。所以,“敬”是个人修养身心和立身行事的根本,必须“笃敬念之不忘”[3]942,不能有丝毫间断。
“敬”是德性与德行的集中体现。薛瑄认为,“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3]763,从人的内心之敬出发来认识由“敬”凝聚在人内心或者样貌之上的德性与德行。在他看来,“敬”有德行,阐释为“心敬”,德性就凝聚在心中;“貌敬”,德行就体现在举止上。所以,耳、目、口和鼻等器官的外在表现实际上是对“敬”的相应表达。他对于“敬”的重视可以从其对“不敬”的表述中看出,“或有不敬,则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体懈弛而物则废,虽曰有人之形,其实块然血气之躯,与物无以异矣”[3]763。“敬”是人内在德性的一个方面,是主体发自内心矫正外在行为的主要表现。因此,在修养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心敬”,以“敬”加强内在德性的修养与外在德行的规范。“敬”的修养方法具体表现为“心肃容庄”,即从人的内在修养与外在涵养两处同时下工夫。
在人的内在修养中,薛瑄记为“敬”的修养方法主要表现为人在向内反观自身的过程中,使内心时时事事处于一种“敬慎”和“敬谨”的状态。他在阐述“笃敬”时强调,要在未发与已发之间时刻省察自己的内心,不让内心被外界事物遮蔽,这种方法就是“敬慎”与“敬谨”。“人之为人,其理有木、火、土、金、水之神,其体有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其事有五伦、百行之备,故内焉而敬不笃,则心官味而天理亡”[3]532,人对物欲的放纵会使物欲遮蔽天理,进而导致心被外部环境牵引并为物所扰乱。因此,要以“敬”涵养身心,从而达到“心肃”的境界,摆脱外物对内心的干扰。这种“心敬”具体表现为3种心:
敬天之心。薛瑄非常重视天人合一,一生也在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在他看来,天和人是相通的。他对“性天通”的阐述源于孟子,孟子认为“性”虽然表现在心上,却是来源于天的。所以,薛瑄对天是十分敬重的,“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怠”[3]759,正是这种“敬天之心”为“敬”其他人或物提供基础,也突出个人内在修养的重要性。张岱年说:“他(薛瑄)在平日进行道德修养的过程中,有时已有‘心与天地同其广大’的体验,如说:‘湖南靖州读《论语》,久坐假寐,既觉,神气清甚,心体浩然,若天地之广大。’又说:‘心虚有内外合一之气象。’此心虚湛,便有内外合一的气象。内外合一即是天人合一。”[4]1由此,敬天之心是心“敬”的基础,一方面也体现着敬天之心存在于“敬”人之心中。对天的恭敬之心体现在人身上就是对人的恭敬之心。但只有“敬天之心”是远远不够的,“敬天,当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谓能敬天者,妄也”[3]732,而“吾心”则从公正之心开始说起。
公正之心。在薛瑄的思想体系中,“敬”是使内心处于一种“公正”的状态,他指出:“敬,则都是一片公正的心;不敬,则无限私窃的心生矣。”[3]705他将“敬”视作公正之心的前提,只为自己考虑不是薛瑄所讲的“敬”,对他人有成见也不是薛瑄所讲的“敬”,这里的“敬”不只是内心的或者理论上的,而应该是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的各种状态,在表现的过程中,“敬”之心使人愈加“卓然”“光明”。这种“公正”的状态使他在为学和从政的道路上能够摒弃个人之私,保持近乎于圣的美德。
诚敬之心。薛瑄以诚敬之心作为自身待人接物的原则,并且认为“诚敬之心”是圣人所具有的重要品性。他讲道:“观《师冕见》一章,可见圣人接物之诚心;若常人之于瞽者,鲜不忽易而欺绐之。于此亦可以观圣人之气象。”[3]759同时,他还指出待人接物有无诚敬之心是区分“圣人”与“常人”的重要标志,因为“常人见贵人则加敬,见敌者则敬稍衰,于下人则慢之而已;圣人于上、下、人、己之间,皆一诚敬之心”[1]759。“圣人”怀“诚敬之心”与人相处,对敌、对上和对下没有任何差别。“虽三尺童子,亦当以诚心爱之,不可侮慢也。”[3]951圣人对年幼孩童也以诚敬爱,更何况是对待地位低的人呢?“于人之微践,皆当以诚敬待之,不可忽慢”[3]951,圣人也以无差等的“诚敬之心”对待地位低下的人。“诚”和“敬”一样,是圣人所具有的至善品性,薛瑄认为这也是为学作圣人所要追寻的重要品德,且并不是不可达到的。
在薛瑄看来,“敬”的涵义十分丰富,“敬”的修养方法不仅要从内在精神层面体现,还要从外在的言谈举止中彰显。他认为,“外则肃乎其容,不使有一体之惰,以至接乎物,则必主于一”[3]532,衣冠和容貌的端庄也能约束规范内在。外在庄重,内在自然也会“敬”,正如他所言:“外焉而敬不笃,则众欲攻而百体肆。”[3]532“其曰‘整齐严肃’者,欲人必极其庄,而不失于怠隳。”[3]625若是忽视对外在言谈举止的关注,长此以往,内在的品性也会受到影响。在薛瑄“敬”的修养方法里,内在修养与外在涵养是相互作用的。外在涵养由内在修养决定,内心的敬促使自身与他人交流时严肃端庄,充满敬意;内在修养在外在涵养中得到彰显,内心不敬的人外表上也会是衣冠不整和举止轻浮。外在涵养同样需要以“敬”来修养,因为外在的礼仪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需要经常磨炼,才可养成举手投足间的良好习惯,作用到内心才会“恭敬”。薛瑄用“日益之效”和“积土为山”等词形容“敬”是由点滴积累而来,强调“敬”须在日用之间慢慢存养,他说道:“积土为山,而不觉其山之高;浚源为流,而不觉其流之长。其自得之妙,又有非言语所及者矣。”[3]532
薛瑄将“敬”概括为由内向外和从外到内的双向过程,归根结底还是强调“敬”在内在修养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心肃”是敬的出发点,“容庄”是敬的外在表现,两者相互影响。在他看来,要达到“成圣成贤”的境界,“敬”的修养是必不可缺的方法。薛瑄在为学的进程中以“敬”教人,从日常生活到为官的过程中践行“敬”的道德原则,不仅关注人的外在,更希望人从外而内和由内而外成为真正品德高尚的人。
二、以敬立心
“敬”被薛瑄视作进德修身和整饬身心的修养之法,这种修养主要通过外在的端庄和内在的庄严两个方面实现。在薛瑄看来,以敬立心讲求的就是“知性”“尽性”和“穷理”,并将其作为“学以至圣”的重要途径。这种观点与他在追求个人道德完善的过程中注重培养成德成圣的根本及其追求“复性”的宗旨密切相关。
薛瑄以“敬”立心是圣贤所具有的高尚品德。他从“居敬”这一概念展开,认为“居敬”是“穷理”的根本所在,通过“居敬”可以去除物欲,回复至善至纯的本然之性与圣人般的精神风貌和品格,最终达到“内圣”的精神境界。他指出:“程子论‘恭敬’曰:‘聪明睿智,皆由此出。’盖人能恭敬,则心肃容庄,视明听聪,乃可以穷众理之妙;不敬,则志气昏逸,四体放肆,虽粗浅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况精微之理乎!以是知‘居敬’‘穷理’二者不可偏废,而‘居敬’又‘穷理’之本也。”[3]802他把“居敬”和“穷理”结合起来,认为“居敬”就是使心“专一”于天理,不受外界扰乱,不被外物引诱,立住本心。他认为,事物有大小之分,但理无大小之别,谨慎地对待大事而对小事不在乎的作法必然会在天理层面有所欠缺。所以,无论事大事小都必须以“敬”的态度去对待,才能达到存天理的境界。当然,薛瑄并不认为只要存有“敬”之心就能明天理。他以“镜”作喻,认为心“敬”的程度与明天理的状况具有一致性。他言道,“心如镜,敬如磨镜”[3]789,人们先在心中存有了“敬”心,才能通过修养将人欲和物欲等外在表现慢慢褪去,天理才会越来越明晰,就像磨镜子那般越磨越亮。反之,不主敬,“中无主而天理不存,外物皆得以入,故曰‘实’,实即物来填塞于中”[3]889。向更深层次求索,薛瑄主张“居敬”的目的不仅在于明天理,更重要的是察天理。他在为学之初,“见‘居敬’‘穷理’为二事”[3]736,为学日久便能“见得‘居敬’时敬以存此理,‘穷理’时敬以察此理,虽若二事而实则一矣”[3]736。简而言之,以“敬”存养“理”,“敬”的工夫日益精进了,便能穷得“理”,在穷“理”的同时也能操存体察“理”。正所谓“居敬有力,则穷理愈精;穷理有得,则居敬愈固”[3]1056,两者是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否则“一于居敬而不穷理,则有枯寂之病;一于穷理而不居敬,则有纷扰之患”[3]1047。事实上,薛瑄也是这样作的。他把“敬”作为圣贤修己之要,还特意写了《持敬箴》和《笃敬齐记》,以此勉励警示自己将“敬”存于心中,时常“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3]874。他所讲的“居敬”“穷理”与他的知行观也是相通的,“‘居敬’以立本,‘穷理’以达用”[3]736正体现了他“以行为本”的知行观[5]274。他认为,在他所处时代儒家的教诲已经非常清楚了,不再需要解释,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躬行践履,将圣贤所具有的道德内化到自己身上,丰盈自己的精神生命。而“敬”正是他所主张的可以通往圣贤之道的路径。
薛瑄以“敬”立心求的是知性、明性和尽性,试图通过“敬”的修养方法呈现人的本然之性,以达到复性的目的。他指出:“《小学》只一‘性’字贯之。‘立教’者,所以教此也;‘明伦’者,所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3]816从“敬身”来看敬“性”,人必须先向内反观自身,如此才能将“敬”发挥到“性”的活动中,使“敬”得以贯穿“性”。在这个意义上,他所讲的“敬”是不能脱离“性”的。薛瑄将“性”理解为受之于理的至纯至善的本然之性和与气质相结合后产生的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所以,他非常重视在日常生活与为学过程中主动改变被遮蔽的渣滓之气,“才敬,便渣滓融化,而不胜其大;不敬,则鄙吝即萌,而不胜其小矣”[3]720。在回复至善的路径中,薛瑄提出“用敬”的修养方法,通过对“敬”的具体实践,形成了一套较完备的自我修养体系,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实践之儒”。
薛瑄持“敬”的目的不仅在于立己之心,注重个人修养方面的“复性”与“成善”,还在于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反思,立天下人之心。“《书》言‘敬’者最多,敬乃治天下之本。”[3]946“治乱之原,皆原于敬、怠,故唐、虞君臣恳恳言敬而不已,三代圣人亦然。”[3]946他将“敬”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认为天下人皆持敬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他看来,舜、禹、汤和文王等圣人都是因为持有“敬”之心,才能作出圣人之治的。他说道:“《中庸》曰‘笃恭而天下平’。”[3]947“开示群迷,敬为要约。”[3]625“敬,礼之兴也;不敬,则礼不行。”[6]289“左氏论‘敬’处多,亦是先王之教有未泯者。”[3]825这些言语均强调统治者要像圣贤尧舜那样以“敬”治理国家,以“敬”教化百姓,这样百姓才会有礼有节,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就他自身而言,他在为官过程中注重将“敬”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品质,时刻不忘以“敬”修养自己,以“诚敬之心”对待百姓。他言道:“作官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3]735,认为为官者就是要秉承“和而敬,敬而和,处众之道”[3]700,以“敬”对待百姓,敬民和爱民,并且在“处己、事上、接下,皆当以诚敬为主”[3]889,对百姓持谦让态度,从不怠慢,以百姓心为己心。薛瑄将自己的为官之道概括为:“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此居官之七要也。”[3]1072
在薛瑄看来,“敬”不单是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概念,更重要的,“敬”还由内而外地作用于道德实践。在朱学日渐僵化的背景下,薛瑄由“敬”立心的目的就在于将内在修养转为追求“圣人之法”,以探求“复性”的道路,这种追求就体现为其以“敬”为核心的实践之学。因此,他在言“敬”时虽然也讲精神性的道德作用,但更加强调的是以“敬”贯穿知与行,贯穿实践。
三、致用之学
薛瑄主张用“敬”的修养方法,旨在通过主“敬”以解词章之学的弊端。他关注到当时社会不注重“实行”的弊端,提出将“敬”落入实践,使“敬”作为“千古为学要法”[3]796,从而使他的修养方法具备了“实学”色彩。
薛瑄认为,人“虽有‘仁’‘敬’‘孝’‘慈’‘信’之分”[3]985,但是“皆以‘敬’为主”[3]985,“敬”作为人的一种修养方法,它的层次是高于“仁”“孝”“慈”与“信”等品质的。他沿用《左传》的说法,认为“敬”乃“身之基”[3]907,即“敬”不仅是身体的根基和行动的根本,还是人立世处事的基础。因此,“敬”必须有所着落,才能为其他的道德品质提供存在的空间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给其他的修养方法地提供依据。薛瑄之所以以“敬”为主宰,就是要在心中确立起道德原则,并通过内在的道德依据克服外在的私欲,使心神不被干扰,进而使其他的道德品质得以被更好地彰显。
薛瑄吸取了程颐“主一无适”的思想,对“敬”“只是内”作了新的阐释,即把“敬”付诸于实践,认为“心在此事上”人便具有了“敬”。他将“敬”的实现过程解释为:“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无不如此,所谓‘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五步之外,即非敬矣。至若写字处事,无不皆然。写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为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专一,便是敬。”[3]1057他认为,做事时专心收敛身心于此件事上,使自身不被其他事情干扰,如此这般才能作到“敬”。显然,这里的“敬”不仅是一个意识问题,而是同“理”与“气”一样,都是客观实在的一种身心实学。薛瑄强调行与心的结合,提倡心神不能漫无目的地四处飘散,而应当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一心一意去做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敬”的实现应当“专一”,即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做事情,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当人的内心具备“敬”这一道德自觉后,还应当坚持不懈地保持这一道德修养,因为“敬”的修养本身就是一个辛勤且持之以恒的反躬自省过程。个人必须不畏艰难地去为学,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求知,还要不停地知性和明性,改变自身的浊气。更重要的是,个人还要有坚守道德原则的决心,不为任何事物所动摇,这样才具有了“敬”的内在活力。
薛瑄还意识到,仅在当下存“敬”是不够的,这样容易使“敬”流于形式,无法在人们的内心立足。所以,他还关注“敬”在修己之道过程中的具体贯彻和应用。他认为“持敬”与“私欲”密切相关,“‘敬’字、‘一’字、无‘欲’字”[3]787,把“敬”视作去欲的过程,强调只有遏私欲人才能持敬。这种观点与薛瑄对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论述具有内在一致性。他认为,人的本然之性都是好的,只是因为被私欲遮蔽才使善的本性不能呈现,因而表现出有善有恶之性。当私欲破坏了人的内在本质,“敬”作为向内涵养心性的工夫就有了重要意义。薛瑄把来自内心的“敬”看作是一个人心志越来越清明的内生动力。他说道:“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养气。”[3]740“不轻妄则重厚,不昏塞则虚明,其要在‘主敬’。”[3]1008这是因为“主敬”可以使人们内心宁静纯一,不受私欲的影响,坚定不移地在为学的道路上勇毅笃行。相反地,若心中不存有“敬”,心便没有凭借,没有支撑思想的基础,嗜欲会被无限释放,造成人欲横流的现象。只有“主敬”“持敬”和“居敬”,才能“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动,一身皆天理。事不妄为,事事皆天理”[3]761。
“敬”是薛瑄的致用之学,这种致用之学彰显着他的为学宗旨,强调为学来自于他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薛瑄非常重视学,并将“敬”视作为学的重要方法,他说道:“千古为学要法无过于‘敬’,敬则心有主而诸事可为。”[3]796“程子挈‘敬’之一字,示万世为学之要。”[3]784他强调为学要用“敬”,可以通过为学去除物欲,回复至善之性。薛瑄为学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获取理论知识层面,而是想要“实得而力践之”[3]1029,即把所学到的知识应用于现实生活,为现实生活服务。他的这番主张源自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明初统治者为了禁锢国民的思想推行文化专制,学者只能按照官方所列书目和规定的解释习作和背诵词章,不能发表自己的见解。薛瑄反对这种“只是讲说,不曾实行”[3]761的学风,批判人们“尚溺于语言文字,不知主敬以救其弊”[3]532。他提出“主敬”以挽救空谈和不求实际的学习之风,这也为明中叶“实学”的发展输送了理论资源。
薛瑄所展现的“敬”,立足于程朱对“敬”的阐释,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这不仅是一种具体的修养方法,更是结合实践为人们探求礼的规范与道德修养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用“敬”修养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除私欲以保持内心的明晰,回复本性,从而涵养出较为完备的道德修养体系。由此而言,“主敬”“持敬”和“居敬”等对“敬”的描述既是个人修养立心的根本,也是经世立学的门径。这番对“敬”的阐释不仅是薛瑄对空谈无实学风的批判,更是他针对当时思想僵化的社会环境提出的有力措施,也为“敬”的新进路提供了可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