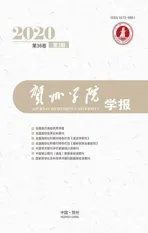怀疑—悬置—还原的“混沌”诗学模型
——评余怒诗集《蜗牛》
2020-01-18李光耀
李光耀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面对强大的汉诗传统——既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指涉亦包含“五四”至“十七年”时期的经典诗歌——每一个自觉的当代诗人,都必然会遭遇一个“诗是什么”以及“诗如何写”的问题。对此,“朦胧”诗人及其后的“第三代”都以或文本或姿态的形式,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而与“第三代”同时期或稍后①的余怒所面临写作局面的复杂程度与革新阻力更是前所未有。一方面是对传统突破的艰险,另一方面是对同时代业已成型的诗歌“范式” 的警惕;此外,更有对自身诗学探索的犹疑与焦虑。纵观余怒自1992年《守夜人》以来的诗歌创作,尽管几经变革②, 但其写作之初便自觉倡导的那些诗学基质却始终只是被扩充、生发和完善,而从未失却其底色,建构起一个以“怀疑—悬置—还原”为轴承的“混沌”诗学模型。下面我们试以其最新诗集《蜗牛》为例,对此范式一探究竟。
一、怀疑:解除语言封印
余怒诗歌中有一种普遍的否定与怀疑论气质,首要指向便是对语言的警惕。在诗歌与理论的具体建构中,这种行动既体现在对“陈词滥调”的清洗上,也昭彰于对语言作为认知与描述世界工具的本体性神话解构中。前一个层面是更基础的工作,亦即所有有志确立自己独一性身份标识的当代诗人所必践之旅——是要通过对“传统”的悖论来揭示存在之深。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陈词滥调、日常语言和循规蹈矩有一种众所周知地把我们隔离于现实的作用,即隔离于所有事件和事实由于其存在而使我们思考它们的要求”[1]131。但这还只是浅层的,只是对一种借助前人的“望远镜”看世界的不满与愤怒,是独立地看,而未必得“见”的。后一层对语言本质的怀疑则是余怒独属的,也困难得多,他要使存在之“真”切实地呈现于文本间。
语言与世界以及诗歌的关系是暧昧的。一方面,语言点亮鸿蒙,使沉默幽暗之物通过被命名得以进入我们的认识;另一方面,基于主体的主观参与,意义、价值、知识等文化负累也在此过程中不断繁殖、堆叠,在逻辑作用下将“如其所是”的事物变为“如其应是”或“如其所愿”——语言似乎成为事物唯一的栖身之所,真正的存在却被蔽覆其下。相比语言与世界(存在)之关系,语言及诗歌之间的纠缠则更为复杂。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必须借助语词、语句和语段等介质得以立身。但又因语言本身的过于确定(隐喻、象征与多义性在本质上也是某种确定), 人在世界中难以量化与具身化的丰富微妙感觉是很难得到真实与准确表述的,更遑论为其存在提供居所的世界本身的混沌苍茫。余怒准确把握了这一点——“世界本身的混沌性、 物种认知的差异以及语言描述的局限使这种愿望的实现一再陷入尴尬。”“人对世界的认识和解说是一个单方面的赋意过程。”“语言作为人认识世界的工具实际上是对世界的‘二度扭曲’”[2]190。余怒是不相信语言的, 这种警惕与自觉时时刻刻闪现在他的诗句中,如一切都在抖动中显示出极度不稳定的《互相确定》:“正在消逝的部分/有一个窗口向外/我确定我醒着并且还在这里/我喊起同室的伙伴, 互相/确定。然后我们来到屋顶上/很多建筑,高过/我们的屋顶,被雪覆盖/吱吱嘎嘎摇晃;共振的还有/香樟树、华椴树、刺槐/这时,我们可以用任何名称/称呼任何事物, 不会因/一时找不到相称之处而恼怒”[3]13。一些东西已经消逝,还有一些正在消逝,一切都值得怀疑,一切都极不稳定。就连“我”的存在也成为不确定的或然事件。“我”与“他”——自我与他者——同处于一个强溶蚀性的荒诞环境里,须得通过“喊”(语言)来互相确定与彼此唤醒。在这个一切都不可靠的世界里,似乎只有语言为我们的存在(活)提供了一丝佐证。语言也借此成为勾连人与世界的那个“窗口”。如若只是写到这里,语言的救赎功用便会被强调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这显然与余怒“希求以其来还原实在世界只是一个梦想”[2]190的诗学追求相悖拗。只要耐心往下一读,我们就会发现,诗人此处只是欲抑先扬,借一种暂时的肯定以抽身出去,制造一个更为彻底的否定现场。当我们借助语言的爬杆来到“外”面,升至“屋顶”之时,被语言命名过的一切——建筑、香樟树、华椴树、刺槐,以致任何事物——都摇晃与振动起来,整个世界顿时陷入一场更大的不确定性灾难当中。覆于事物之上的语言外壳被彻底抖落, 世界焕然为“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4]86,我们也不必再受语言牵累,“可以用任何名称/称呼任何事物”[3]13。
语言对事物的命名是可疑的。事物之存在,无所谓必然或应然如何, 具有自我呈现的无限可能性。直到语言的到来,其每为某一事物扣定一个名称,那事物便“失去了一种被给予的方式”[5]47。余怒十分擅长在诗歌中制造某种偶然的时机, 让事物(存在)的粗粝与混沌逼迫语言自惭形秽地退场,让一切不属于存在本身的东西被悬置起来,以获取一种混沌性还原。在《在什么的边缘》中,是借助对不知道“什么是”而又“不能没有名称”的“时间”的突然发问;在《分享》中,是对“站在橘树下/摘一颗橘子,拿在手中”时“用众所周知的语言谈手中的感觉”的考量,是对“坐在石凳上,左手/握住右手,保持住沉默”的时刻的信任和依赖③。这些都成为余怒叩问语言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有效的钥匙,存在的大门也借此缓缓被推开。当然,对语言的怀疑还只是余怒诗歌的发起点与诗学模型的石柱础。在对语言的本质审慎与“混沌”诗学的终极殿檐之间,还有诸多杂质及诗人对杂质的涤除有待我们进一步考量。
二、悬置:必要的悬搁术
悬置与还原本都是现象学的概念,却能与余怒诗学理念在相当程度上完美契合(这倒不是说余怒必定从现象学那里得到了些什么,只是基于二者相向之处的一种考量)。借助此组概念的探镜,能够帮助我们达至对余怒诗歌文本的另一种通透。发轫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一门关于还原的哲学。尽管来源多样,在理论与流派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多向播撒态势,但其通过悬置的方法来实现对存在真理和明见性寻求——“面向事物本身”——的本质是得到普遍承认的。现象学否认任何知觉或知觉主体的优先地位,强调让现象本身“呈现”,是一种“练习悬置、冲刷、化约那些阻碍我们与生活现实最初的具体性进行原始接触的事物”[6]34的方法。悬置,即搁置或移除, 是将某些东西暂时冻结在一边不予考虑, 而让另外一些更清晰地现身——“现象学一定要惊奇于事物的物性”[6]48。这就涉及一些具体的悬置与化约活动。首先,现象学要将一切建立在周遭世界基础上的价值判断、道德指认等非存在问题悬置起来(并非否认其存在,只是暂时不予考虑);其次,要将概念、假设、前提、投射和语言方式等诠释性成分驱逐出去;最后,对所有由质性研究导递而来的理论或者理论性质的意义也要加上括号。以开放性的姿态唤入鲜活的存在经验——而这种“经验”,特指“那些直接呈现其自身的”[4]282。总而言之,现象学的悬置态度,即将意识中的经验因素搁置一旁, 暂时远离科学世界及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放弃对世界采取的自然态度,以“挺身于世界”的姿态去迎接现象的自“呈”。
余怒诗学也呈现出一种对于悬置或悬停的自觉,即其自己所说的“接受某种停顿”。这种悬置是与我们在上文中所探讨对语言依赖的“拒绝”相匹配的。对常规言说和语言遮蔽的悖论,本身就是一种悬置。具体来看,余怒诗学中所涉及的悬置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对诗歌中“意义”的悬置
关于这一点,余怒在自己的诗学论文中已经说了很多,“我们通常所言的意义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涵, 一是作为主体理想和观念的体现的价值,一是用以表述事物之间逻辑关系的意思”[2]188。受强大的传统阅读意趣的诱引,读者在面对一个既定文本时所抱有的,也往往是一种封闭性的既定态度。我们最关心的并非“诗性”所在,而是这首诗究竟隐含着一个怎样的“标准”题旨,表达了一些怎样的思想感情, 并将此二者在诗中呈现的饱满度与抵达度作为评判诗歌的不二标准。余怒对此是犹疑的,他的诗歌明确悬置了对某种特定价值的展览,让读者面对文本时变得手足无措,真正经验到他者的他者性。
余怒擅长从两个方面去处理这样一种悬置:一是事物的无序展列, 一是诗歌上下文的不断互否。前者如《在振风塔上》:“我来到塔上/没有一个游客/对岸的芦苇丛/突突驶过的拖船/觅食的绿头鸟/这是由黄昏弯曲而成的世界/其中,斜坡屋顶、折腰屋顶/一座塔: 它被我置身的空/这些可用以解释梦境/我们是时间性的动物/又有着间歇性,同时/并存,是行星也是流星。”[3]35可以试想,在从未了解过(事实证明,即使了解过甚至熟知也不一定会好到哪儿去)余怒诗学理念的普通读者那里,初次面对这样一首诗时会做些怎样的“规定动作”? 看形式(长短、字数、是否分行排列),找意象,问主旨,下判断。对这一切读者所期望能从诗歌中顺利(尽管也有不太顺利的时候,但多数情况下还是能令自己满意)获得的东西,余怒都要予以搁置。在这首诗中,除了第一句“我来到塔上”交代了时间主客体外,往下几句都是对我在塔上“看”到的东西的客观呈现,这一切也都只是不带任何价值蕴含与情感起伏的黄昏世界的一部分。即使警句式的第八句“一座塔:它被我置身的空”也迅速止于对事实的描述,至于“我”和“塔”的这种实与“空”,诗人没再进一步言说。而后面呓语般的一句“这些可以解释梦境”更让我们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其与前文有何关联。但再细细一想,大千世界因缘和合又岂是三两句诗歌能够讲得清楚的,这“塔”这“人”这“空”又何尝不与“梦境”中的它们(或别的什么)相一致呢,于是我们又陷入一个“庄生梦蝶”式的漩涡之中。而且都是不确定的,“我们是时间性的动物,/又有着间歇性”,“是行星也是流星”。没有一个句子是深奥的,都是事实性的陈述,但我们又似乎真的从这些陈述中抓住了些什么,是什么呢? 大概就是悬置了诸般障碍之后乍然蹦出的“诗性”吧。
我们再来看一则通过上下文互否以实现悬置的例子:“夏日傍晚/我去观察地平线/那儿, 一会儿,有东西跳出来/再过一会儿,又有东西跳出来/仿佛是为了这里的平衡/不是太阳月亮星星/不知道该叫它们什么/在江堤上, 我躺下来/这么多年不停地衰老是值得的/这么多年没有任何东西出现消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惊喜/地平线从来没有抖动过。”[3]3对地平线的打量是一个文学与哲学的老话题,对这一主题的选择与写作是极其危险也极有难度的,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一个有限无限或死生循环的旧圈套里。诗人在一个“夏日傍晚”“去观察地平线”,那里反复“跳出来”的东西使他有所获也有所惑。那不断跳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这是一般读者读到这里最迫切想知道的,是太阳、月亮、星星,还是别的些什么? 诗人也顺应了我们的意愿,只不过是一种拒绝式的顺应,明确告诉我们“不是太阳月亮星星”,也“不知道该叫它们什么”。读者更着急了,阅读受阻、理解被驳回,甚至有了一些不满的愤怒。作者的初步意愿达成了,也借助这次沟通失效的“停顿”,又把读者诱入第二个话题场域——由神秘的远方转至当下存在的现场——“在江堤上,我躺下来”,诗人自己构成了另一条“地平线”,说出了生命的秘密——“这么多年不停地衰老是值得的”。这里,诗人引进了一条价值判断“不停地衰老”是“值得的”。对于这样一种价值观,读者可能一开始不会接受,衰老真的值得吗? 值与不值牵涉着一系列的关于得与失的考量,一些东西出现,一些东西消失,这不正像那条自然的“地平线”吗? 仔细思考之后读者可能会慢慢体悟到作者这种断言的妙处,于是在读者心里,此前的那种愤怒被一种恍然大悟般的欣喜所替换, 认为自己与作者达成了默契,读“懂”了这首诗。但余怒的厉害之处就在这里,他又一次违拗了读者的意愿,大声宣布“这么多年没有任何东西出现消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惊喜”。人生与世界都重新回到其荒诞的原点,那只是一条不承载任何意义的天地交合而成的直线(也不一定就是直线),它也“从来没有抖动过”。读者读到这里彻底崩溃了,前面历尽千难万险,跋涉而成的所有都成了一种必然失败的“单恋”。
(二)对诗歌中“文化依附”的悬置
余怒认为,诗歌一定要言说当下,触及存在,反对那种假大空而不及“物”的“文化”复述。他尽可能剔除词语与诗句中已高度凝固的文化内涵,力图更新汉语诗歌的词汇系统及语境系统——望月不一定怀人、登高不一定思远、秋天也未必就悲凉。且看《雪霁日》 一诗:“天亮时雪停了/有突然挣脱之感/桥那边,一个人/慢慢倒向冰面/冰窟窿里的冰碴/地球停转般的死/ 冰柱融空般的死/ 倘若说正在死,或/自我完成:扑腾或游动/我时常觉得自己/是个回忆型病人/还记得那么多失败。”[3]41历史上曾有过太多书写雪霁情景的诗歌,“雪霁万里月,云开九江春。”[7]427(李白《避地司空原言怀》)“绮陌敛香尘,雪霁前村。东君用意不辞辛。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8]191(苏轼《浪淘沙·探春》)这些诗句虽不尽然但大抵都展现了雪霁日的美与欣悦。虽偶有像郑燮“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檐流未滴梅花冻,一种清孤不等闲”[9]65(《山中雪后》)这类吟咏一己之怀的孤清之词,但毕竟少数。在历代文人纷繁书写之后,“雪霁”这一景象及其所关涉的情感情趣已被固定甚或“规定”成型。余怒则对附着在现象本体之上的种种文化属性表示怀疑,在自己的诗歌中将它们通通悬置起来。“天亮时雪停了,/突然有种挣脱之感”这一句起手到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是一种公共感受(体验而非经验)的传达;“桥那边,一个人/慢慢倒向冰面”,这一句完成了对基调的转换,一些阴郁的情景迅速挤进画框。如不细品,却也觉不出什么异常:一个雪后初晴的清晨,桥边上一个人或因为疾病或因为失足或别的什么原因而倒向了冰面,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日常。但再仔细一读“慢慢”这两个字,我们可能就不那么淡定了。在一个迅疾失去重心的时刻,他不应该是急速倒下去吗? 那么又是什么力量在拖衬着他? 他是自觉(愿)倒下的吗? 刚刚获得一种“挣脱”便又迅疾扑向另一种吞噬,此前的“挣脱”也被悬置半空,成了一个有待重新审视的现象。“倘若说正在死,或/自我完成:扑腾或游动”,死亡在这里成了一个持续性动作,死亡者扑向死亡的行动也附着了自我完成的性质。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自我完成呢,与那次“挣脱”又有怎样的关系? 对于万众瞩目的那份真相,诗人并未作答, 只是回到一种低低的自语——“我时常觉得自己/ 是个回忆型病人,/ 还记得那么多失败。”
三、还原:混沌的呈示
余怒经由对语言的怀疑和对诸般“非存在”的悬置,通达了一个现象重生、万感交错、混沌而不混乱的诗歌世界,其混沌诗学的基本模型也在此慢慢建立起来。“混沌”是个缘起甚早而又运用颇广的跨学科概念。从宇宙鸿蒙的先民想象,到庄子《内篇·应帝王》中对“混沌”的人格化,再到现代非线性理论,关于“混沌”的探讨从未中断过。余怒在1990年代就曾提出“混沌”诗学概念,其后在《诗观十六条》等论著中又反复重申,“混沌,但不混乱。混沌是世界(存在)的本来面目。诗人的任务就在于使这种混沌呈现出来,而不是枉用模糊混乱的笔法去书写诗歌,诗歌的混沌与笔法的混沌根本上是两回事”[10]472。“混沌”是余怒诗学的一种自觉追求,也是其建基于对语言的怀疑及“非存在”的悬置之上,所要还原而出的理想诗学效果。这种还原生成后的“混沌”性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窥见一斑。
(一)理性时空隐没,感受瞬间入镜
出于对语言的不信任,被时间包裹着的种种关于时空的概念界说和逻辑公式在余怒诗歌中也失去了稳定性。相比前人对永恒时空的理解和执着,余怒更关注一个又一个偶然闪现的瞬间,而且在这样的瞬间中,既往的一切价值判断和道德界定等因素也被过滤得一干二净。其描述的效度是瞬间的、局部的,如《更遥远的》一诗:“不知道‘同一’/‘现在’‘永恒’ 所由来/那是象牙雕刻的/刚出生一天的婴儿/啼哭着,找寻乳头/孤寂和依恋所由来/恒星正在变成白矮星/绝对的金字塔和关于它的物理学/我知道另一个星球上/的很多事,却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茫茫中/接受某种停顿。固态火。冰冻鳕鱼。”[3]5不知道“同一”“现在”“永恒”所由来,这些也并未使我迷惑与受束。因为,我明白那些都“是象牙雕刻的”,不触及存在之本,只是人与语言合谋的产物。我所感兴趣的与婴儿感兴趣的有某些共同之处, 尽管我比婴儿拥有更多的知识——“知道另一个星球上/的很多事”,“却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些才是我之困惑所在。我对“巨大”、对“茫茫”感兴趣,但那些远不是我所能够把握的。我所切实拥有的, 只是在思索这些时的那个瞬间,那种“停顿”,我的迷茫、我的慨叹是真实被我体验到并击中我的。
(二)对中间态不确定性事物的发掘
世界并非由单纯的两极所构成, 在大是大非、纯黑纯白之间,还有着广阔的中间区域。它们或因语言难以命名或因界限模糊被长期遮蔽。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11]20余怒正是要说出那些不能谈论的部分。在《新世界观》中,是对“有一种东西/专门吸收蓝色/你说它是梦吧又不是/天那么蓝而天那么蓝”[3]27中那种“东西”的呈示;在《低语》中,是对一条正在桥下游泳的“蛇”“脑袋昂起,凝视我数秒钟/我觉得它传递给我/一种信息(这完全不可能)/但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3]26里那个“什么”的给予。在诗人看来,这些处于中间状态的模糊事物,也拥有(占据)着某个时候的我(反之也对),“我”被它们以另外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三)逻辑毁断,“世界”失效
余怒对于混沌性的追求还体现在对传统诗歌逻辑的毁断与大量的歧义呈现上。余怒强调感受而非表达,这种歧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主客体相接触的那一个瞬间所生成的,而诗人只是做一个“供述”(余怒语)性的工作。“在方式上它属于描述,但不是‘本义描述’, 而是不带有理性认识和理解的‘歧义’的描述”[2]195。此种意义上的歧义,既包括本节第一点我们所谈的瞬间感受的错位,也包括语词本身的本义、引申义等。《柳叶湖上(一)》中有典型的体现:“坐在船舷边我谈起/诗的结构/水和波浪的关系:心情结构/湖面上有风/船载着我们滑行/几个小岛、 迷茫忧郁/各种水鸟的各种声音/远和近之间的穿梭相见/如同钻石的琢面/横竖线条的茫然抽搐——/扩展了我的诗——来自/左右方向的反向力”[3]85。在一种独特氛围的笼罩下,几个小岛显出“迷茫忧郁”的色调,远处与近处各种水鸟叫声交杂不已。在那一瞬间,我“看”到它们像“钻石的琢面”般,“横竖线条”“茫然抽搐”。这些景象,在寻常情况下定然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但我们无法否认有那么一个(些)瞬间,理性退场,逻辑断带,错位与混乱发生,想象与现实交叠。更重要的——这些都“扩展了我的诗”。
(四)纯然感受性的“我”
进入到混沌诗学世界中的“我”,是一个不为经验逻辑左右、 道德条框约束、 知识理性驱策的人。“我”的感官全部打开并融贯一体,与万物共呼吸,与感受同命运。语言不再成为我的负累,因为“雨中的仙人掌”成了“‘沉默’的替代品”。“对语言而言,沉默是一种自然,一个休息,一片未开发的原野。语言因沉默而获得生气勃勃。语言因沉默摆脱了语言自身的暴虐性,而洁身自好。语言可在沉默之中喘口气,然后用根源性的力量重新充实自己”[12]23。在被万物的“物性”击中时,语言退场,沉默出现,那些长期被遮蔽的东西以自身的方式“降临”到我的身上,感受充盈着“我”。当语言历经感受的洗礼,重新出场时,便会生机勃勃,洁白少瑕。
结 语
正如众多评论家所言,想要准确地用语言去评述余怒的诗是困难的, 想要用某一个诗学模型去“罩住”诗人的所有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更近乎是一种虚妄。既是基于余怒自身对语言的谨慎和创造性使用已达至一种纯熟之境, 也是因为其作品众多,变化多端且仍在持续自我悖反,自我革新中。这也是当代诗学(文学)批评固有的难点之一。但对其诗歌及诗学体系的整体把握仍是必要的,这是批评职责之所在,也是对诗人的致敬与对话切磋。
注释:
①也有论者将余怒归入“第三代”诗人,如董迎春.身体超验与诗学探索——以20世纪90年代余怒诗歌作例的考察[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8(4):1-7。“余怒作为第三代诗人中较晚成名的一个诗人”;余怒曾参加“甲申风暴·21世纪中国诗歌大展”,参见李佳璇.破碎与真实——余怒的诗歌写作[J].写作,2018(7):84-89.基于此点,诗人或对自己的代际归属有一定体认,但也不一定,这种代际划分本就疑点众多;
②余怒曾总结过自己诗歌创作的三次变化,“我的写作经历了几次变化,第一次是《守夜人》《剧情》时期,第二次是《这一分钟》《众所周知的立方体》时期,第三次是《个人史》《主与客》时期。这三次变化可能与我的年龄有关(也可能无关)。第一次是‘我’与世界的对抗;第二次是‘我’的隐匿,主体被客观化,‘我’只作为一个旁观者环顾着周围的世界;第三次是‘我’的重现,乐于置身‘与你谈话,很快活’(《主与客》)的世俗乐趣中。”参见余怒.主与客[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16 页。
③本段几处诗句皆摘自《蜗牛》。参见余怒.蜗牛[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