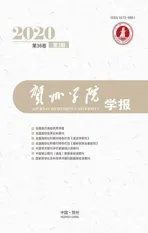黄独峰的现代绘画观与实践
2020-01-18赵嘉
赵 嘉
(广西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北京 100084)
黄独峰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发生着一系列巨大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引发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否定、破坏,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开始了试图改变落后文化的“文化革命”。至此,中国从物质、制度、文化层面开始探索走向现代化的路径。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也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展开:在“革命”“进化”“创新”的思想引导下,艺术的“发展”成为首要问题。中西方艺术交流和碰撞,旧的文化价值被破坏,新的文化形态尚未出现。一时间,各种艺术思想交锋争鸣,人人都在为国画的发展寻找新的可能性。摆在艺术家面前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具体在创作中就是,如何协调时代性、民族性和个性的问题。
因此,对黄独峰艺术观念及其创作的思考不能孤立地局限在单纯的风格分析和技法研究上。只有将艺术家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情景中,我们才能看到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 社会文化思潮、师承关系、个人的境遇和艺术家艺术创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那样的一个矛盾、冲突、混乱的时代,黄独峰学任伯年派,入岭南,其后又东渡日本留学,在香港转投张大千门下,这样的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个人性情如何与时代交错共同构成艺术家的艺术观念? 又对其艺术创作和风格的形成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纵观黄独峰的艺术生涯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是,1939年在香港进行的一系列艺术活动;二是,1960年从印度尼西亚回国, 任教于广西艺术学院。
1938年黄独峰在香港创办了《现代艺术月刊》。1939年与方人定、黎葛民、李扶虹、司徒奇等同学组织了“再造社”。在方人定留美回国后,举行第一次社展,编辑了画展特刊,除了刊登作品外,还收录了社员的相关论文。黄独峰发表了《中国绘画和西洋画的倾向》一文。关于成立“再造社”的宗旨,方人定曾在自己的手稿中写道“我们本着中华的国民性,站在时代艺术前线上, 再辟国画的新路为宗旨,我们联合个性坚强,思想前进的艺术同志,共同研究,绝无阶级观念,我们把身心寄托艺术,决不为外物摇动,不做虚伪的宣传”[1]129。方人定后来又回忆说“再造社,是一个画社组织,都是高剑父的学生,因不满高剑父的家长制,组织起来反对他,但不久被他逐个收买,各个击破,又因香港沦陷,个人散了,再造社散了”[1]129。我们不知道这一说法的可靠程度有多少,但是师生之间在艺术主张上的分歧却已出现。这一点也在体现在《中国绘画和西洋画的倾向》一文中。可见,1939年是黄独峰在跟随高剑父入“春睡画院”学习,又去日本留学后,开始在艺术观念上逐渐走向成熟,并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时期。
在《中国绘画与西洋画的倾向》一文中,黄独峰阐明了自己对东方和西方艺术的理解, 并试图从“表现主义”的角度来调和在美术界当时关于的“科学与艺术”“东方与西方”的争论与矛盾,为新国画的发展寻找道路。文章开篇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的绘画,最重六法,六法者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傅彩,经营位置, 传移模写的六种。而尤以气韵生动最为重要,……”[2]299,在列举古人对气韵和笔墨、气韵和人品的讨论之后, 黄独峰否定了气韵来自天性的说法,并得出以下结论“纵观以上论列,可见用笔之重要,中国绘画且与画法息息相关。向称书画同源,绘画因极注重笔法和调子,写字亦是一样,所以写字除传达字的意义之外,还要传达出精神的情绪来”[2]300。并进一步对气韵进行了界定:“……若字和字之间,行与行之间,能偃仰顾盼,阴阳起伏,先后相承,这一幅字就成为有生命流动;此种生命的流动,就是气韵,……中国绘画不是自然界的附属品,而以生动的内容为主体。所以历朝作家虽有南北二宗之分,都是注重自我的表现,即是描写事物表现而直接心理感应发展到画面上去的。故桥本关雪说‘中国画非写实主义,亦非印象主义,实表现主义。有人借物体而吹入自己的灵魂,从内向外自己的表现。”[2]301无论是“生命的流动”也好,“生动的内容”也好,说到底就是“内在的生命意识”。这成为打通中西方绘画差异和矛盾的关键。黄独峰进一步研究了西方的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新古典主义等艺术流派的艺术主张和视觉形式后,总结到“以上所说的西洋现代的绘画,各种主义,均倾向于表现的主义,在色彩与线条上大都有共同点,不过表现的思想与技巧上不同而已。这种表现主义是受到了中国绘画上的影响,在现阶段的中西绘画可说是在共同的目标上努力了。”[2]304可见,黄独峰还是站在中国的立场看待西方,认为在古典的写实主义之后兴起的西方现代艺术诸流派,并不拘泥于“客观的形似”,而是进入感情和“内在精神”的表现,是主客观合一的艺术。因此,在艺术观念上和注重形式构成主观表达的中国文人画体系有着相似之处,从而中国的传统艺术也就具备了现代品质,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毫无疑问,这一结论是黄独峰对西方现代艺术“误读”的结果,但这种误读在当时的美术界是一个普遍现象。随着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对西方现代表现主义的介绍和引进,并最终促使了“新美术运动” 中对表现主义的探索。“当又一股更为革命的西潮到来时, 许多画家选择了一种很巧妙的中西融合方式,即以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意象创作心理迎合西方现代的抽象创作心理,以稚拙的天真对应无意的真切,以最便捷的方式扯起新美术的旗帜,这是在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相对撞时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3]53
黄独峰对中国画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岭南派是一致的,肯定中西融合的思路和倾向,坚持文化发展的民族同一性, 坚持历史和艺术形态的同一,认为现代艺术是由古代演进发展而来。只不过,在对东西方艺术的认识和角度上,以及对中国艺术现代性的出路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对比一下高剑父写于抗战时期的《我的现代绘画观》就能看到其不同之处。
对东西方艺术认识的不同。在《我的现代绘画观》中,高剑父论及西方艺术时说“这五十年间,欧洲画坛的动荡已起了不少大变化,新之又新、变之又变。即前次之世界大战,至此次世界大战,在人类大屠杀之过程中,世界画坛之异军突起,已指不胜屈。说起来惭愧极了,难道我们的国画就神圣到千年、万年都不要变、都不能变吗?”[4]47在谈到具体的西方现代艺术流派时,高剑父认为“我在外国曾看过两个画展:一个是‘超现实主义’的,其中真是光怪陆离,不可思议;又一个是‘未来派’的,场内虽有二人说明,但总是莫测高深,殊难索解,即使说明之人,也不能自圆其说。派别虽多,未必派派能发展,有的渐渐削弱,归于失败。”[4]47可见高剑父对西方现代艺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艺术主张缺乏充分的了解,也并不认可在超越古典写实主义之后,西方出现的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西方现代艺术吸引他的是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西方现代艺术流派更迭所显示出的“革命性”——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和超越。高剑父以此来否定当时国画界的因循守旧。这一观念无疑是“文化进化论”的产物。二是,在“务实”“科学”的思想指导下,借鉴西方的写实主义,否定晚清以来的文人的程式语言,用西方的写实性化解中国的写意性。而对于黄独峰而言,西方现代艺术意义并不在革命的文化姿态上,而是需要在实践中具体的找到西方现代艺术在形态上和中国传统艺术相融合的切入点。他试图在东西对照下,重新阐释传统美学,寻找能和时代和西方沟通的“表现主义”传统,为国画的现代化提供本土文化的历史依据。以此反拨了岭南派秉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艺术造成的负面影响。用东方的写意性来化解西方的写实性。在《中国绘画与西洋画的倾向》中显示了艺术家的这种尝试和努力。虽然,在理论逻辑上颇为跳跃,在具体的问题上——诸如形似、空间等问题上语焉不详,含混模糊。
基于以上的分歧,两人向中国传统艺术学习借鉴的方向也不同。高剑父对中国艺术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过于玄妙,缺乏实际。并重新评价明清之际被忽略的职业绘画,推崇宋画,认为“宋代的画风,诸法具备,精深善妙,可为我国画之黄金时代”。黄独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是落脚在外在的语言和形式,而是再次将传统绘画的精神和意识置于优越位置上,提倡“六法”,专心研究文人画,强调笔墨,追求“物我两忘”的境界。
高黄二人在艺术观念上的差异,向我们显示了中西艺术融会贯通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同样是中西融合的思路,高剑父带着更多“西化派”的色彩,而黄独峰则和“国粹派”更为接近。高剑父针对明清文人画程式化的问题,用西方的写实性化解中国的写意性,成为“新艺术运动”中写实主义倾向的实践者和代表。而黄独峰则是反驳以科学主义改造中国画的艺术观念。用东方的写意性来化解西方的写实性。在艺术主张上倾向于表现主义。20世纪30年代中西方的艺术语境都在发生变化。由于西方对古典传统的反思和叛逆, 导致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也促使了中国艺术家重新评估西方艺术和中国传统。时代语境与文化语境的变迁,旧理念和新知识的碰撞,黄独峰的绘画观念逐渐和“岭南派”拉开距离,开始了自己独立探索的道路。这也就不难理解1950年黄独峰转投张大千门下的选择了。
黄独峰艺术生涯的第二转折点是1960年从印度尼西亚回国。这时的中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另一场“新美术运动”。
1950年后,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的新美术运动兴起。新一轮对文化的改造和现代化进程拉开了序幕。学者陈履生写到“一部中国美术史发展到20世纪中叶,因为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相应的美术也与前朝大相径庭。没有哪个时代这么看重美术的济世功能, 也没有哪个时代这么大张旗鼓地要求美术为社会服务。运动式、全民性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极其显著的特征。在这个时期内,不管是具有千年文化传统的国画,还是引进不到百年的西画,都遵循着一个方向为执政党的文艺方针服务,行使着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职能。”[5]2
在完成了对年画的改造和创新后,“革新中国画”的问题也随之被提出来。中国画是否能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成了首要问题。中国画从艺术功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艺术风格(唯“现实主义”独尊)、创作方法(“深入生活,反映现实”)开始了全方位的革新。在这一过程中,“写生”成为新国画的改造革新的基本途径和手段。1953年,艾青提出了“画山水必须画真山水”,“画风景的必须到野外写生”的观点。由于艾青在美术界的领导身份,无疑成为官方对国画改造发出的指导意义的号召。一时间, 在全国国画界兴起了大规模的山水写生活动。以写生来促使艺术家走出书斋画室,走向社会和自然,改变传统山水重笔墨轻造化,借助程式化手段来结景造景的创作方法,并最终完成对艺术家世界观和审美思想改造,让中国画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成为当时写生运动的宗旨。
具体到黄独峰的艺术创作中,“写生”常常被作为其创作方法和特点提出来, 强调其写生能力强,并认为黄独峰对写生的推崇有一定的师学渊源,是受到了“岭南画派”强调户外写生的影响。但是若是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实际情况会更复杂一些。“写生”是中西方艺术实践中都使用的方法。中国古代就有人提倡“收尽奇峰打草稿”的写生,强调的是“师法自然”的创作理念和方法;而西方的写生则建立在定点透视基础上,强调科学、客观的观察方式,带有认识论的色彩。在中西文化交融的20世纪早期,“写生”的概念在被美术界广泛使用,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守成派都提倡“写生”。在不同的文化立场和语境中,其内涵和意义也有所不同。“写生”作为一种创作手段,并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还和文化、社会等层面的因素相关。
在黄独峰的创作实践中,“写生” 是随着中国画的现代化进程,为了建立“新国画”而使用的创作手段,在不同的阶段,其意义和作用也在发生着变化。
20世纪30年代,黄独峰对写生的强调,有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和作用。一是,通过写生来解决当时画坛上模仿因袭,缺乏创造性的问题。“我自从走进艺术的途程,十余年来都抱着董香夫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法艺”“……每到一家,便有一次不同的感觉,艺术上亦跟着变化,新的事物就是新之资料,现代的艺术,正需要新的生命,新的创造,闭门造车,推残守缺,有如向人死尸古董,没有新的表现,这些只有走的没落的道路,在现阶段的艺术,是要不得。”[6]104二是,受“科学”“求真”的影响,形成观察实物的新眼光,成为训练造型能力的手段。“几十年来,我是把写生作为提高技艺、丰富作品题材的手段,我把‘搜尽奇峰打草稿’作为治艺的座右铭”[7]201。“写生” 对黄独峰而言既意味着对山水画师造化的传统的继承,提高艺术家的创造力;又意味西方写生观念对艺术家的观察方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艺术家对写生的理解。
回国后,黄独峰并未像很多同时代的国画家那样感到不适应,一贯注重“写生”,表现现实生活的他驾轻就熟地投入到当时艺术潮流中。20世纪初革新运动中作为写实主义基础的写生,在“启蒙”“救亡”的时代主题下所产生的人文主义追求和政教功能与新中国的文艺诉求在此完成了同构和转化。以至于,在看了黄独峰在回国前的画展后,有人评论到“黄先生所绘的题材是多样的,有花鸟虫鱼,也有巨幅山水,更多的是实地写生。这是一改旧国画的旧作风,使人可从这些国画里,嗅到时代的气息,更能闻到印尼泥土的香味,这是说明了我们海外的中国画家们,也和祖国进步的画家们一样,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正确道路”[8]141。在新的语境下,写生直接表现了现实生活,是现实主义。哪怕视觉效果上还是传统山水差别并不大,也不再是闲逸适性的传统山水画了。
相比徐悲鸿以室内写生为基础,进行主题创作的学院思路, 黄独峰的创作继承了岭南画派的思路,走向大自然。用水墨对景写生、对景创作。写生就是创作,创作就是写生。这一时期的作品有《桂林写生册页》《桂西春晓》《黄山写生》《黄土高原写生》《苏州写生》《西津水电站》等。在技法上,艺术家以古人的笔法写生自然,保持中国画特色;在视觉效果上,注重画面写实性和大众化经营;题材上,出现了工农建设、城乡新貌等题材,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