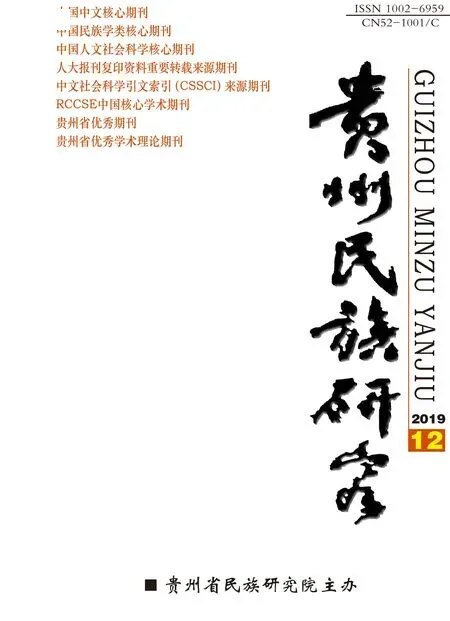贵州望谟布依族“三月三”文化节变迁与重构
2020-01-14鄂启科
鄂启科
(贵州省地方海事局,贵州·贵阳 550003)
一、问题的提出
南北盘江和红水河流域是布依族重要的栖息地,地处红水河畔的望谟县是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全县国土面积3018平方公里,辖12个乡镇3个街道,161个行政村4个社区,居住着布依族、苗族、瑶族等19个少数民族。截止2018年,全县总人口32.6万人,其中布依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62.8%。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布依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有自己灿烂的民族文化、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其中“三月三”是望谟县布依族重要的民族节庆之一,并以其特有的节日仪式、文化内涵保持了布依族传统的集体记忆,使得布依族集体成员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日共享了一场“民族文化盛宴”。布依族“三月三”民俗节庆是布依族“集体成员文化共享与记忆延续的有利时期”[1](P43),独特的仪式和活动,凝聚着布依族的团结和族群认同。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认为:“民族是被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不过民族成员彼此之间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心中。”[2](P6)望谟布依族“三月三”民俗节庆,正是这种“联结的意象”,让布依族世世代代的族群成员维持本民族的集体记忆。望谟布依族“三月三”已然从内容到仪式,均发生了明显变迁。表面上看,这是政府利用民族民俗节庆推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作出的一项重要举措所导致的文化变迁。但深层次看,笔者认为,这种变迁来自于内外矛盾的推动:一是国家民族政策外部力量的推动;二是望谟布依族“三月三”民俗节庆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所作的自我调适,国家民族政策的推动是主要的因素。
传统意义上的“三月三”民俗节庆已经华丽转身,被改造包装成“中国布依三月三文化节”。民俗节庆“蕴含了民族成员的生活理念、价值观念、群体情感、宗教信仰、社会交往、民族心理、生产器物、行为方式、饮食风俗、服饰文化、歌舞艺术等民俗事象”[3],这些事象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但是共同记忆只有建构在共同历史传说和祖先故事之中,才能真正构建起“民族想象”,才能联结起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才会成为可能。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民俗节庆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民俗节庆的变迁,反映着该民族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变化。因此,研究民俗节庆历来成为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法国葛兰言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借助中国古代文献所保留的歌谣、节庆,来阐释和分析中国古代的宗教习俗和民族信仰,为后来学者研究民俗节庆作出了经典示范。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民俗节庆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出新,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就。目前,对民俗节庆、传统节日研究,大致有四个方面进路:第一,从仪式功能角度,关注民族传统节庆的变迁和重构。比如,黄彩文通过对云南耿马佤族青苗节祭祀仪式的研究,发现由政府主导的青苗节在仪式场域、祭祀内容和社会功能等方面逐渐发生了流变[4]。林慧则把视野扩大到中国传统节日仪式,林慧认为在当代,由于历史、社会等诸多原因,节日中的仪式变得越来越简化,有的甚至遗失,通过研究,林慧提出了仪式重建的当代意义以及仪式重建的途径[5]。第二,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角度,研究民俗节庆。比如,李凌霞通过对湘西田家洞村舍巴节的土王祭祀研究,揭示土司时代以来田家洞地区土王祭祀活动的变化。第三,从民族文化传承角度,关注传统节日、民族节日的变迁和未来走向。比如,刘从水基于云南民族传统节日变迁的研究,认为传统节日的舞台化、法定化、市场化,创造了节日文化传承舞台,发明了节日文化传承方式[3]。萧放以当代中国节日为例(不含少数民族传统节日),考察了中国民族节日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了其面临的挑战与未来走向。[7]第四,从节日公共文化空间的角度,探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秩序建构。如,李志农通过对云南迪庆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的个案研究,阐释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路径的思考[8]。
对布依族“三月三”民俗节庆的研究,根据笔者所见,为数不多。一是从文化角度研究,比如毛天松对布依族“三月三”的历史渊源、活动内容、节日特征及其价值方面的研究,认为“三月三”节日传承着布依族的习俗和文化,反映了远古时期布依族先民质朴的人与自然的观念,从而形成了一种集宗教、生产、娱乐为一体的节日文化现象[9]。罗茹、龙青松关于布依族节日的名称、内涵和主体的研究认为,人民是节日的主体,尊重文化是开发的前提,保护布依族文化生态系统是举办民俗节的基础,特别是要保护好布依族的社会环境[10]。二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比如徐倩通过对望谟县“三月三”布依文化节的研究,提出了传统节庆文化传播推广策略的思考。[11]
在布依族“三月三”民俗节庆研究方面,学者们也开始投入了关注的目光,并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为人们了解布依族民族文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但是从已有的研究文献中,笔者发现,对布依族民俗节庆关注度不够,从民族政策的角度对民俗节庆变迁与重构进行深入的研究尚不充分。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党中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70年来,民俗节庆的保护、传承、发展,离不开国家民族政策的大力支持和资金保障。因此,从民族政策的角度,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民俗节庆,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
三、传统村寨祭祀仪式:布依族“三月三”的历史渊源
关于布依族“三月三”节庆,专家学者引用最多、最早的历史文献是清朝乾隆年间李其昌《南笼府志·地理志》,兹录如下:
……每年三月三宰牛祭山,各聚分肉,男妇筛酒,食花糯米饭,……,三、四两日,各寨不通往来,误者罚之。
再往前从清代雍正上溯至汉唐时期,均无文献对该节日的详细记载
在当代的各种志书中,关于布依族“三月三”的记载,有三种:一是毛公宁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志》,该书记载:“布依族“三月三”主要是祭山神、灶神、扫寨、赶鬼、预祝丰收的节日。”[12](P341)二是黄义仁在《布依族史》中说:“罗甸望谟一带过三月三日,把它当着清明节一样看待,杀猪宰牛,上坟挂青,吃三色糯饭。”[13](P294)三是2000年出版的《望谟县志》记载:“农历三月初三日,是祭社神、山神的节日。乡间的三月初三日,各家上坟扫墓。”[14](P184)以上文献记载,尽管文字不多,但可以看出传统布依族“三月三”节日功能,一方面是祭神,以祈求丰收;另一个方面是上坟扫墓,怀念先人。在祭祀物品方面,要杀猪宰牛,吃花糯饭。这与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对节日的描述也相对一致。望谟县新屯街道办油腊寨摩师岑英能说:“三月初二,各寨子杀猪或杀牛祭祀神,每个寨子都有一个保佑本寨五谷丰登的神。祭神,是为了祈求保佑风调雨顺,保佑本寨人人健康成长、吉祥如意。”笔者在调查中,每寨所祭祀的“神”,叫法不一致,有的叫“xiex suc(谐苏)”,有的叫“xiex mbaanx(谐瞒)”,有的神还有名字,如新屯街道办纳交寨的寨神,一共有三兄弟。这三兄弟原来住在纳交寨对门山坡上的山腰处,纳交寨请来到寨中,保佑寨子和顺安宁。纳交寨每年农历正月初三、三月初二、六月初五都要进行祭祀。至于如寨上有人梦见神已经回到山上去,则必须要举行“迎神”仪式,用布依话说叫“xuex xiex”。说到是否三月三对山歌,岑英能摩师说,没有对唱。他还用一首布依族歌来作为反证,他说,有一首歌这样唱:“xunz xih xunz ndianl xiangl,guas ndianl ngih ndianl saaml bail nac,bux laez weanl nac rih”,意思是说,我们要玩就趁正月农闲时间玩,到了二月、三月,还有谁会和你在山地上对唱山歌呢?农历二月、三月,正是春耕的时候,男女青年一般很少往来,何况大家都在忙耕种,谁还有闲心来对唱山歌呢?
谈到具体的祭祀仪式,望谟县新屯街道办纳交寨的罗凤熬说道:祭神时,用一张八仙桌,一卷白布捆成枕头样子,置于桌子北面边缘,用五个酒杯,五双筷子,间隔摆好,靠在布上,然后用煮好的猪头或牛头摆在桌子上,再放一块刀头肉,一碗米。点香,斟酒。由村寨中德高望重的摩师或村寨中的寨老主持祭祀,并斟酒,初敬酒时,一边斟酒,口中一边祈求保佑,念毕,躬身退出。过了一刻钟之后,再斟第二巡酒,三巡酒后,礼毕,烧纸,收拾贡品。集体就餐,分肉。如果村寨中有什么事要讨论决定,饭后就一并开会议定。第二天,三月初三日,各家上坟扫墓,祭祀先辈祖宗亲人,缅怀哀思。
关于“扫寨”“赶鬼”,不一定要在“三月三”,也可以在正月初三以后,也可以在二月、三月,时间不限,只要认为寨子上不干净、有晦气了,就要请人来扫了。另外,在农村,以前都是住木房子,一到春天之后,风大,怕火烧房子。岑英能是附近有名的摩师,他为很多寨子扫寨过,他说:“到了二三月份,风大,怕火烧房子,怕各种瘟疫降临,所以要扫寨”“扫寨、赶鬼,一般选择的日子是春天寅、午、戌日,布依话叫‘ngonz baiz os’ (除日),送的神是meeh luangz ruc、bux luangz fiz(这两个神一旦来到民间,就喜欢放火烧房子)、天瘟、地瘟、猪瘟、牛瘟、鸡瘟等瘟神”。通过一定的仪式把瘟神送出村寨之后,所有的路口都要画符、念咒语、“封寨”,不让外来人进入村寨,以免把晦气带入。
综上,可以看出,生活中的布依族“三月三”的原始表达只是传统村寨的祭祀仪式。从仪式内容、仪式功能看,比较简单,其目的是祈求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至于扫寨、赶鬼,也是为了驱除村寨的晦气,让各方面都能够顺顺利利。
四、现代机构活动展演:变迁的布依族“三月三”
望谟县布依族“三月三”文化节,自从2011年举办至今,已有九届,在传承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展示地方特色、推动旅游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特别是2012年,修订后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明确规定:“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布依族、苗族的传统节日,全州放假1天。”当然,布依族“三月三”作为民族法定节日也包含在其中。2017年3月,望谟县布依族“三月三”文化节,被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节庆专委会授予“中国品牌节庆示范基地”称号。这表明传统村寨的祭祀仪式已经变为机构组织的活动展演,在仪式内容、仪式场所、参与人数、功能等方面均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了更客观地反映望谟县布依族“三月三”民俗节庆的变迁,笔者对2016年至2019年4届望谟布依族“三月三”文化节进行了梳理(具体如下表):

时 间 活动主题 活动地点 活动内容 参与人员2016年农历三月初三日开始布依山水·温暖望谟;三月三·同昂央望谟县城王母广场、迎宾大道及县内其他乡镇(街道)、村寨、景区和区域第二届国际山地旅游大会·望谟“三月三”布依文化节民族风情巡游展演、开幕式及文艺演出;第二届国际山地旅游大会·望谟“三月三”布依文化节纺织技艺展示和比赛;第二届国际山地旅游大会·望谟“三月三”布依文化节布依纺织文化研讨会。除此外,特色文化展示(沉香、奇石、特色农产品展销及诗词、书法、绘画、摄影展),民族美食大赛,“山地旅游·万人踏青”体验活动等配套活动。除本地布依族、苗族、汉族等同胞参加外;邀请了各级党政领导;各级政府部门领导;院校及科研院所;知名专家学者、文化人;各级新闻媒体;部分纺织企业和旅游企业代表;布依学会人士。2017年农历三月初三日开始感恩行·糠包情——民族团结同昂央和谐繁荣丽甲习望谟县城王母广场、迎宾大道及县内其他乡镇(街道)、村寨、景区和区域沿袭2017年。走进新时代·相约三月三·建设新望谟民族团结同昂央·社会和谐丽甲习望谟县城王母文化广场、迎宾大道、余姚大道、天马大道及县内有关乡镇(街道)、村寨、景区。全球布依感恩大典;开幕式、颁奖、文艺演出;布依糠包万人舞活动;中华布依服饰盛装巡展。配套活动:“布依情”—中华布依糠包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布依境”—中国布依民俗摄影大展;“布依韵”—中华布依原生态服饰盛装展;“布依味”—首届中华布依美食大赛;“布依奇”—民族奇特商品展;“布依美”—“同昂央”民族团结文艺展演。2019年农历三月初三日开始2018年农历三月初三日开始望谟县城王母文化广场、迎宾大道、余姚大道、天马大道及县内有关乡镇(街道)、村寨、景区。布依感恩大典;布依糠包万人舞;“民族团结同昂央·社会和谐丽甲习”文艺汇演及“王母传说”原生态歌舞晚会;民族方队巡演。配套活动:布依宝—“户外嘉年华·寻宝三月三”大型户外运动;布依俏—“王母之星”选秀大赛;布依美—“锦绣布依”布依族服饰设计大赛;布依韵—“天籁布依”古歌展唱;布依欢—“激情布依”民族体育竞技体验;布依味—“原汁布依”特色商品展销。布依族美——“锦绣布依”民族服饰设计展演;脱贫攻坚宣传巡游;布依感恩大典;布依文化节开幕式;布依欢——“民族团结同昂央·社会和谐丽甲习”民族大舞台;“感恩·奋进”民族文化展演;布依情——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展销。分会场,还有“神秘布依”麒麟扫寨、原生态祭祀活动;“多彩布依”布依土法染织展演;“天籁布依”布依古歌、饶、布依说唱表演;“快乐布依”民俗活动体验;“恋恋布依”乡愁集市体验;“风味布依”酒桌宴体验;除与2016年邀请人士一样外,2017年,还增加了邀请东南亚国家布依人和贵州、四川、云南等省级布依学会及省内各市州及相关县布依学会。沿袭2018年。
通过梳理,不难发现其中变迁的轨辙。
(一)仪式多样化。从表中,可以看出望谟布依族“三月三”文化节仪式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村寨仪式。从活动内容上看,有传统的祭祀仪式——感恩大典和赶鬼——麒麟扫寨,但更多的是充满现代色彩的开幕式、文艺演出、古歌展唱、服装设计展演、商品展销、书画摄影展、奇石展、民俗体验、体育竞技等等,并且活动内容一年比一年丰富,仪式越来越多样化。正如学者指出:“祭祀是‘三月三’最重要的文化特征,唱歌、跳舞等是衍生的产物”[10]。
(二)俗民多样化。所谓“俗民”,就是民俗行为的主体,是各种民俗事象的具体践行者。按照潘文焰、仲富兰两位先生的观点,“俗民是民俗文化系统发展与演变的直接动力,俗民群体的发展变化将直接影响整个民俗(文化)系统的改变”[15]。传统的布依族“三月三”民俗仅仅是在布依族群众内部,没有扩大到其他民族。而政府机构主导下的望谟县布依族“三月三”文化节,从参与人员身份、族群成分看,显然已经超出了布依族族群的范围,有苗族、汉族等其他民族成员,也有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民族精英,更有东南亚国家的其他民族人士,大家都纷纷参与并加入其中,与布依族成员一起,共享一场布依族节日的文化盛宴。一份来自贵州移动黔西南分公司的大数据分析,2018年望谟布依族“三月三”文化节当天,4.3万人,本地布依族人参与最多,黔西南本地游客2.9万人,贵州省内游客0.9万人,外省游客0.5万人,36岁以上的中年人约占到48%。
从表中所列四届的“三月三”文化节主题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关键词有“同昂央”“民族团结”“建设新望谟”。其中“同昂央”,这是布依语音译而来,布依文是“dongq aangs yaangh”,意思是“大家一起高高兴兴”。由此看出,这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参与、庆祝的节日,充分彰显了民族大团结、社会和谐的浓厚氛围。
(三)场所现代化。传统仪式的布依族“三月三”,祭祀的场所一般是布依族村寨社神所在地点。社神或山神一般建在寨子上方或村寨周边,以木石建墙、盖瓦,大小不一,没有统一标准。有的建在大树下,用三块石板围成三面墙,上面再用一块石板盖起,就成为山神或社神的房子。逢年过节,如“三月三”,则全村寨各户家长自带碗筷、三柱香、纸钱等,到山神前集中,由寨老或德高望重的摩师主持祭祀活动。从政府主导的文化节开始,祭祀场所离开了原生环境,已经从村寨神前转移到现代化的广场上,有音响、有祭文,甚至连参与祭祀的摩师服装都充满着戏剧化,舞台气息浓厚。所祭祀之神,并非社神、灶神,祭祀的是布依族人文始祖——布罗陀,更有民族的人文意义和民族信仰。当然,每个布依族村寨也仍然维持着原始的祭祀仪式,在本村寨中举行,与政府主导的“三月三”文化节的祭祀仪式、感恩大典没有任何关系。
(四)功能多元化。望谟布依族“三月三”的原始功能就是祭祀,一是祭祀神,二是祭祀自己列祖列宗。但是,自从“三月三”变成文化节后,其节日的功能已经从原生的祭祀功能——宗教功能、教育功能变成了集娱乐功能和招商引资、旅游推介等经济功能于一体的多元功能的民俗节庆。从上表中,我们看出,活动的内容有服装走秀、商品展销、山地旅游等浓厚的现代气息,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以祭祀为主的民俗节庆。
五、布依族“三月三”变迁动因分析
潘文焰、仲富兰提出构建节日民俗系统的四个维度,即依存载体、行为主体、运作介体、表现客体。在这个系统之内,文化生态是节日文化的依存载体,俗民是节日文化的行为主体,节日习俗是节日文化的表现客体,节日运作者的各种社会机构是节日民俗的介体[15]。于此,笔者借鉴该节日民俗系统的逻辑框架和理论,从民族政策的角度,分析讨论布依族“三月三”变迁的动因。
一是民族政策为节庆变迁提供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是民俗节日的载体,是民俗节日依存的土壤。在这块土壤上,文化(包含节日文化)一方面,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又互相影响着彼此。正如斯图尔德认为的一样:“在物质环境和人类活动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系列知识与信仰,即文化模式。文化模式之集合的文化圈,如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圈层一样,也是一个相对独立又与其他圈层联系着的进化系统。”[1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坚持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专门法律,内容包含有少数民族成员的人身自由与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以及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等多方面。可以说,一系列成功的民族政策的实施,为民俗节庆的变迁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并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政策的鼓舞之下,也为地方政府在民俗节庆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找到一个新的结合点。
二是民族政策为节庆变迁提供坚强的政策保障。从2011年到2019年,望谟布依族“三月三”文化节已经连续举办九届,当地政府各级部门和人民群众都以极大的热情和满怀的期待,从农历二月份开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即将到来的“三月三”文化节隆重召开做好充分准备。政府部门要认真制订详细方案,明确组织领导机构、活动内容、活动意义、经费筹措、保障措施等,可见地方人民政府对布依族“三月三”文化节的重视程度。田野调查中,望谟县实验高中的黄高堂老师告诉笔者,“‘三月三’布依族文化节已经成为望谟县、黔西南州乃至贵州省一张亮丽的民族文化品牌。”在望谟县,没有哪个民族节日如此隆重,如此受到各民族同胞的欢迎,当地人民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举办这样一年一度盛大的民族节日,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振干部群众志气,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但这里,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动员各方、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举办“三月三”民族节日,主要原因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支持保障。
三是民族政策为族群文化意识觉醒提供内生动能。望谟布依族“三月三”文化节从2011年举办以来,布依族同胞男女老少都要穿上布依族服装,活动当天大街小巷,目光所及都是穿着布依族服装的民族同胞。已经在望谟县经营民族服装缝制八年的鄂启姹告诉笔者,她从事民族服装制作的这几年中,每年的“三月三”是她最忙的时候,订制布依族传统服装的大概要在300多套以上,大街小巷男女老幼都喜欢在“三月三”节日期间穿民族服装。在望谟县经营少数民族服装缝制的,有近十家左右。“以前我们都认为穿布依族服装很土,都喜欢买街上很流行很现代的服装穿过年过节。但现在我们又重新喜欢自己的民族服装,男女老少大家都很喜欢,觉得很漂亮。”望谟县一位女青年王燕这样告诉笔者。她还说,2019年布依族“三月三”文化节时,广东来的一个朋友也和她一样,穿上了布依族的民族服装。从这个角度上讲,望谟县布依族“三月三”文化节同时也是民族服装的一次大展演。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在布依族历史上,民族服饰始终与民族文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布依族服饰积淀了民族文化精髓,体现了布依族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思维以及民族审美等多方面内容。从民族政策的角度分析讨论,全体成员身着民族服装盛装过节的景象,显然离不开党和国家大力支持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离不开党和国家制定出台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由此形成的良好的社会氛围。从民族意识角度看,全体族群成员自觉穿民族服装过年过节的现象,实则是族群文化意识的觉醒,激发了少数民族同胞极大的热情,让少数民族同胞在民族节庆中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了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这种族群意识觉醒和文化认同,为“三月三”民族节庆的变迁提供了强有力的内生动力。
六、布依族“三月三”民俗节庆保护与传承的政策路径
一是立法保护,规范传承。彭兆荣指出:“文化传承表现出多种维度,包括传承的主体、传承的权利、传承的保障、传承的对象、传承的制度、传承的范围、传承的方式等等”,[17](P73)对布依族“三月三”节庆的传承,自然无需讨论,不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族群成员,传承已经成为共识,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如何从制度层面,去保障、并规范传承。目前为止,对民族文化的政策保护,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配套出台《民族自治区域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及各民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各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法律法规体系,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但是,对当前传统节日、乃至少数民族民俗节庆的传承保护,尚未出台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8](P32)传统节日、民俗节庆是民族文化记忆传承的载体、是民族集体意识的表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传统节日不仅给人们带来休闲和娱乐,更重要的是,通过集体性的仪式或庆祝活动,通过大众的参与,来建立公共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进而强化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5]。因此,立法保护民俗节庆,从民俗节庆的内容、仪式、传承方式、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规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立法方式,可以从国家层面,统一制定一部专门的节日传承保护法规,也可以通过修订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达成,还可以由民族自治地区修订完善本区域自治条例,予以专章明确。
二是文化为主,适度发明。“如果说传承是保障文化得以经久性地进行代际传递的话,那么传承方式便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它是真正使得文化遗产可以按照良好的意愿薪火相传的有效途径和手段。”[17](P73)从望谟县政府主导布依族“三月三”文化节以来,我们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传承民族文化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但从另一方面看,自从政府主导的望谟县布依族“三月三”文化节以来,一年一度的节日打造,从形式到内容都进行了精心的包装,“成为了民间社会和政府部门同心同德同喜同贺的象征符号,也成为了一种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意愿的现代政治表达。”[3]“三月三”作为一个传统的民族节庆,既存在着节日所蕴含的精神文化的内涵因素,又体现这些精神文化内涵的符号与仪式的外在形式与物化的载体。因此,对于节日“发明”的度,要充分尊重节日的传统文化内涵,然后再进行适度发明,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传承保护民俗节庆的目的,不是经济、旅游等方面的现实利益,而是唤醒族群成员的集体意识和归属感,增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从而实现国家认同。再者,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旦失去了节日的民族性、地域性等特征,节日的传承与保护自然无从谈起。
三是立足教育,凝聚认同。望谟县布依族“三月三”源自祭祀仪式,实则是布依族民间信仰。既然作为一种信仰,就必然具有提供精神家园的功能。人们在“三月三”,祭祀社神、灶神,就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祭祀祖宗先辈,则是缅怀思念,“感恩”“向善”。所以,传承和保护民族传统节庆,首先,要通过民俗节庆的文化内涵,普及民族文化知识,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凝聚民族共识,实现国家认同;其次,要立足于节日本身文化内涵、仪式等内容,教育族群成员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再次,要着力培养少数民族精英,“文化政策的本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知识分子政策,传统文化保护和民族发展都离不开民族知识分子精英的参与”[19](P21),他们是“联系国家与草根社会的渠道,并带动草根社会直接参与文化保护工作”[19](P21),因此,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精英,是传承、保护民俗节庆政策路径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
七、结语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民俗节庆的变迁自然在所难免。深入探究变迁的动因,以寻求保护和传承的路径,应该成为学界共同思考的问题。本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从民族政策的角度,认为民俗节庆的繁荣发展以及变迁,离不开党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保障。在民族政策的背景下,对变迁的动因进行分析,提出保护和传承布依族“三月三”民俗节庆的政策路径,希望能对我国其他民族的传统节庆的保护和传承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