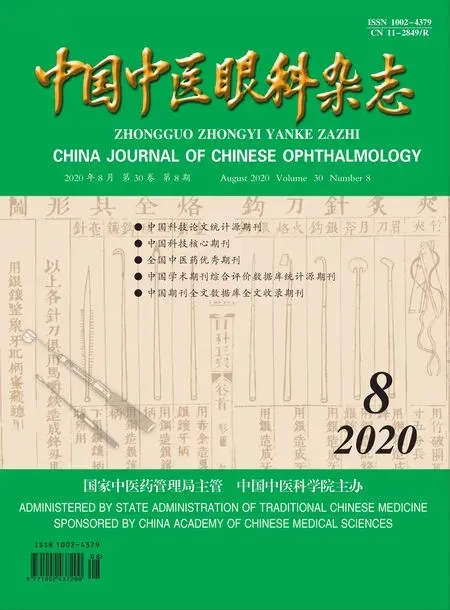中医眼科用药特色
2020-01-10庄曾渊盛倩杨永升
庄曾渊,盛倩,杨永升
自北宋眼科成为独立的专科以来,中医眼科的基础理论和临床技术都得到了长足进步。其间五轮学说、八廓学说逐步完善成熟,治法方药更加丰富,特别是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思想对眼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完素[1]提出:“论目昏赤肿翳膜皆属于热”“眼病在腑为表,当除风散热。在脏为里,当养血安神。”张从正[2]谓:“目不因火则不病”“能治火者,一句可了”。李东垣[3]强调:“脾胃虚则九窍不通”“凡医者不理脾胃及养血安神,治标不治本,是不明正理也。”朱丹溪[4]谓:“眼疾所因,不过虚实二者而已。虚则眼目昏花,肾经真水之微也。实则眼目肿痛,肝经风热之感也。实则散其风热,虚则滋其真阴。虚实相因则散热滋阴兼之,此内治之法也。”上述学术思想在元末明初的眼科专著《原机启微》中被吸纳应用。《原机启微》[5]以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理论为指导分析病机,归纳病证,立法处方,为后世推崇,起到了上承唐宋,下启明清的作用。
明代《审视瑶函》[6]曰:“眼乃至清至虚之府,以酷烈之药攻之,翳虽即去,日后有无穷之遗害焉……惟以宽中开郁,顺气消痰,滋阴降火,补肾疏风为主。”清代《眼科金镜》[7]云:“目病虽多,不外风寒虚实之候,治亦不离清散补泻之法。补不可过用参、术以助其火,惟用清和滋润之类。泻不可过用硝、黄、龙胆草之类以凝其血,惟用发散消滞之类。”
梳理古人眼科用药经验,基于眼生理、病理的特殊性和治疗病种的差别,眼科在治法方药上亦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色[8]。其特色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宜轻升,忌沉寒
轻升和寒沉是对中药性能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而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9]将中药性味分阴阳,谓:“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素问·至真要大论》[9]提出五味的阴阳属性和作用,谓:“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为临证利用药物的特性论治脏气不平出现的病证打下了理论基础。张元素宗《内经》原旨,十分重视药物气味厚薄,升降浮沉及其辨证关系。《医学启源·药类法象》[10]将药物区分为:“风生升、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类。轻升即指风生升类,沉寒即相应于寒沉藏类。
眼位居高位,因风邪致病者十分常见,又因目为肝之外候,肝为风木之脏,易生风化热,同气相求,内外合邪。外障眼病,外感风邪或风热不制是多发病证。因而辛散疏解是常用治法,或辛凉透热,或辛温发散,均以发散风邪,驱邪外出为治疗目的。所用荆芥、防风、羌活、独活、白芷、细辛、柴胡、前胡、桔梗、薄荷、秦艽、蔓荆子、麻黄、葛根等均有发散表邪,疏风通络作用[11]。常用方有羌活胜风汤、金液汤等,挟热则有芍药清肝散。
角膜翳的治疗,自始至终离不开疏风宣散。新翳多数风热壅盛,当疏风清热。宿翳风热已减,气血凝滞,当祛风退翳,活血明目,常用木贼、白蒺藜、决明子、青葙子、密蒙花、蝉蜕、谷精草,均能辛散。退翳药中忌过用寒凉,以免引起气血寒凝,翳膜难退,如龙胆草、黄柏、知母、黄芩、黄连、汉防己,玄参、牡蛎等苦寒泄热坚阴之品。
李东垣创益气升阳,升阳散火,引经报使学说。升散药在眼科应用更加广泛。
升发阳气:中气不足,清阳不升,九窍不通。助阳活血汤用蔓荆子、防风、升麻、柴胡使阳气升而九窍通利,治服寒药太过,其气不能通九窍,眼睫无力,常欲垂闭,隐涩难开诸症。
发散郁火:元气不足,阴火亢盛,火乘土位。冲和养胃汤用升麻、柴胡、葛根升阳,羌活、防风散下焦郁遏之火,发散以伸阳气,治圆翳内障。
引药上行:羌活、防风之类辛散轻扬。李时珍[12]谓:“酸咸无升,辛甘无降,寒无浮,热无沉”。羌活、防风之类不但自身归经走头目,而且能引药上行。当归养荣汤用白芷、羌活、防风引药入胃经、膀胱经,治眼珠痛不可忍。
治外障眼病,滋腻性药物亦应慎用,意在防外邪不得发散,入里化热,加重病情。
2 宜清润,忌助火
基于中医眼科以目内包黑稠神膏,膏外有粘稠神水,血以滋水,水以滋膏的认识,以及一肾水配五脏火,是火太有余,水常不足的理论,目中肾水亏者多,盈者少。《审视瑶函》[6]指出:“水衰则有火盛燥暴之患,水竭则有目轮大小之疾,耗涩则有昏渺之危。”阴虚在眼病表现为视瞻昏渺,干涩磨痛,眼表无光彩,目赤,目劄,并可伴见口渴喜饮,唇红干裂,头晕耳鸣,烦躁易怒,大便干结,小便短赤等症。舌象尤为重要,一般为舌红苔薄少津,或有裂纹,甚则无苔。舌红干瘦无津,光剥暗紫如猪肝,属肝肾阴虚,脏腑燥热,治当滋补肝肾,壮水制火。肾阴充则五脏得濡,主要方剂有一贯煎、六味地黄丸、左归丸等。滋阴药一般偏于滋腻,故应用时要注意行气。一贯煎养阴药中配川楝子,使肝阴得养又肝气调达。六味地黄丸三补配三泻,补中寓泻,通调水道,补而不滞。基于阴阳互根的原理,左归丸滋补阴精配鹿角胶温补填精,使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
《审视瑶函》[6]提出“补不可过用参、术以助其火”,关键在于“不可过用”。所谓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热,心烦口渴,牙龈肿胀。二为升,眩晕耳鸣,步态不稳。可用玄参、天花粉、黄连、炒知母佐制参、芪之热。用牛膝、黄柏制约参、芪之升。益气聪明汤中应用黄柏即是实例。为制约八味丸中附子、肉桂伤阴,《一草亭目科全书》[13]温阳剂中不用八味丸而用还少丹代之,谓滋补肾水,温养少火,寓有深意。
另有名方石斛夜光丸有25 味药物组成,看似庞杂,不易分析方义。然而仔细品读斟酌,从滋养肝肾着眼便易理解。目病肾水亏多盈少,肝肾同源。肝脏阴血不足,故方中生地黄、天冬、麦冬、五味子,石斛养阴滋水以滋补肝肾。枸杞子、熟地黄补肝肾、养阴血。肉苁蓉、菟丝子补肾益精、从阳化阴,使肝血充沛为治本。人参、山药、茯苓、甘草健脾益气,后天之本滋生化源。犀角、羚羊角、黄连解气血郁热。菊花、青葙子、决明子、白蒺藜平肝熄风。郁热、肝风皆因肝血不足、肝气郁滞而生,此治标。牛膝、川芎、杏仁、枳壳、防风调畅气血既为佐使治已病,亦能防止气血郁滞而治未病。所以配伍周正,保证了本方补益肝肾、滋阴养血的主要功能。并且对主证衍生的其他病症亦能兼顾,成为眼科应用最广的方剂之一。本方亦是眼病宜清润、忌助火思想的又一例证。
3 宜消散,忌克伐
宜消散,忌克伐是针对积滞而言。眼科多见因气、血、痰、水运行不畅,日久结聚而继发的病证。因眼的结构精细,慢性内障眼病虚实夹杂,治疗宜渐消缓散,不宜过烈泻下逐水以免伤正难复,需突破投鼠忌器之思维。
眼科有形之积,大致见于肿块、翳膜、瘢痕增生等,均适用消法。消法意味消癥散结,而这种方法都是通过祛除郁结之邪气和疏通阻滞之气血来实现的,所以消法实际是行气、活血、清热、化痰、利湿诸多具体治法的综合运用。比如,胞生痰核,表现为胞睑皮下痰核隆起,或有红肿,上睑沉重,系痰火郁滞所致,治宜清热化痰,方用化坚二陈汤合清胃散。特发性黄斑视网膜前膜,为视网膜内表面增生的纤维细胞膜,好发于老年人,其病机为正气不足,络虚血瘀,水停热郁。补消结合,治以益气健脾,活血化瘀,化痰散结,予炙黄芪、炙甘草、当归、丹参、莪术、醋鳖甲、柴胡、赤芍、苍术、土茯苓等。视网膜瘢痕增生,可因曾经出血或渗出引发,如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病理性近视黄斑病变均属本虚标实。老年人阴血常亏,病理性近视脉络失养,气血不足,分别应在补益肝肾或益气养血的基础上软坚散积,加片姜黄、炒蒲黄、连翘、浙贝母、三七粉等。
血有形,凝而成积宜消。气无形,聚而为结宜散。“肝气通于目”,肝气从肝胆发源,通过脉络孔窍到目中,成为目经络中往来之真气。若情志不遂,肝气不畅,疏泄失职,引起气机郁结,又可继发火郁、痰郁、血郁。如Graves 眼病,临床表现眼部酸胀、眼睑水肿、回缩迟落、眼球突出,好发于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的青年女性,常有情绪抑郁,焦虑忧思,劳倦过度等诱因,致肝脾不调,气机不畅,聚湿成痰,气液失调,阻于络脉,郁久生热,结膜充血。宜行气解郁,化痰散结。予逍遥散加夏枯草、玄参、生牡蛎、浙贝母、川芎、香附,有热加牡丹皮、栀子。《证治准绳·目肿胀》[14]曰:“大凡目珠觉胀急而不赤者,火尚微,在气分之间。痛者重,重则变赤,痛胀急重者,有瘀塞之患。疼滞甚而胀急,珠觉起者,防鹘眼之祸。”本病轻症相当于中医神珠自胀,其重症即鹘眼凝睛。
偏头痛、血管神经性头痛致目痛,往往情绪紧张,精神刺激能诱发其发作,中医谓气眼证。《证治准绳·目痛》[14]云:“才怒气则目疼”。怒则气上,动火生痰,气不宣畅,气滞而痛,治以复元通气散:石决明、决明子、楮实子、香附、木贼、蝉蜕、川芎平肝行气,活血通络。
4 宜通调,忌瘀塞
目得血而能视。《审视瑶函》[6]云:“目之有血,为养目之源,充和则有发生长养之功,而目不病;少有亏滞,目病生矣。”亏即气血亏虚,滞即脉络瘀塞,气血不能上荣于目。《审视瑶函》[6]又论述了脉络瘀塞的病机,谓:“目属肝,肝主怒,怒则火动痰生,痰火阻隔肝胆脉道,则通光之窍遂蔽。”将肝胆脉道瘀塞的机制剖析为气、火、痰、瘀四个环节。七情刺激引起的肝胆脉道瘀塞多引发内障眼病,不同于外感六淫继发的脉络瘀阻,治疗这类肝胆脉道瘀塞所致的内障眼病当以调气活血为根本,结合病位和病性,采用疏肝通脉、清肝通脉、化痰通脉和活血通脉。
4.1 疏肝通脉
肝气郁结郁于本经,引起血行不畅,脉道瘀滞。如青风内障(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若因过劳思虑以致眼胀眼痛,视物日渐昏曚,情志抑郁,胸胁胀满,女子乳房胀痛,月经不调,用柴胡疏肝散,效仿叶天士提出的“辛润通络法”[15],以辛味发散通气机、行津液、润血燥,加蔓荆子、羌活、防风、当归、桃仁、柏子仁等在疏肝理气同时又活血通脉,在气的推动下,顺畅血脉,所用药物药性平稳,对于慢性眼病之久病入络者,比较合适。
4.2 清肝通脉
肝气郁滞,郁久化火,血液受灼,滞于脉络,如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若素有肝阳上亢,复因情志不舒,突发视力下降或视野缺损,头晕头胀,口干口苦,心烦燥热,大便干结,宜清化肝热和活血通络同用。夏枯草、黄芩、山栀、决明子、茺蔚子、当归、红花、怀牛膝、鸡血藤、丹参、郁金、陈皮,较单用桃红四物汤活血化瘀,改善视力、视野更有效。张景岳用化肝煎[16](青皮、陈皮、芍药、牡丹皮、栀子、泽泻、土贝母)清化肝经郁热,配活血药可使血行流畅。若因血热妄行引起血灌瞳神等症,可配合凉血散血的生地黄、玄参、槐花、旱莲草、大黄炭等,遵肝为血海,热去血宁之意。
4.3 化痰通脉
痰湿之体或肝气横逆克制脾土,脾失健运,痰浊内生,脉络瘀滞。如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症,眼胀头沉、视力昏矇、虹视、隐涩畏光、胸闷痞满或有呕恶、眼压高、角膜后壁大小不等灰白色沉着物,宜清化痰热,活血通络,予解郁逍遥散加减。疏肝使气机流畅,辅以清肝,解化火生痰之虑,行气使升降有序,助力半夏、浙贝母消积聚之痰,通调脉络。若目赤、咽干、尿黄、热象偏重,加牡丹皮、栀子、夏枯草、菊花;若头痛、眉棱骨痛,兼见风邪,加蔓荆子、白芷、僵蚕、天麻。津血同源,全程配伍适量活血药如茺蔚子、泽兰、川牛膝等有利于促津液偱行,痰化而脉通。又如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见视网膜神经上皮脱离、色素上皮脱离,视物变形、口苦咽干、胸闷心烦,是肝胆气机郁滞,血行不利,津液停滞所致,应用柴芍汤调畅气机,活血行水。
4.4 活血通脉
气滞、火郁及痰阻均能引起脉络瘀阻[17]。内障眼病表现为视力下降和形觉异常,如视直如曲、视大为小、云雾移睛等。活血通脉须辨虚实寒热。
气虚血瘀:肝气甚而中气虚,情绪紧张,脉络拙急,经气不足。王清任言[18]:“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补阳还五汤加茺蔚子、天麻、怀牛膝,益气活血兼平肝舒络。
气滞血瘀:肝气郁结,气机不利,血行瘀塞,血府逐瘀汤主之。血不利则化为水,视网膜渗出、水肿明显者加茯苓、泽泻、生白术(相当于和当归芍药散合方)活血利水。
热结血瘀:肝热蕴蒸,郁于血分,血受热熬成瘀,热与血结,脉道不通,选四妙勇安汤、犀角地黄汤合方加桃仁、熟大黄、栀子、紫草、大青叶清解热毒、凉血散血。
寒凝血瘀:肝气虚甚致肝阳虚,温煦不足,血流凝集,脉道瘀阻。当归四逆汤合桃红四物汤加黄芪、吴茱萸温肝散寒、活血通脉。阳化气,阴成形,温阳通脉可散阴寒凝结的包块,必要时加化痰散结的半夏、胆南星等,作用更加全面。
5 总结
宜和忌,“忌”更多的是具有“慎”的意思,而非废而不用。其实质在于提示在组方用药时,在辨证基础上,一是要注意眼病的发病特点,二是要注意药物性味和治法病机相对应。古代外障眼病,尤其是感染性外障眼病是多发病,常见外眼红、肿、疱疹、疮疖、翳膜,以疼痛、畏光、流泪、干涩、刺痒为主症。历代医家皆从风、火立论。又因肝开窍于目,肝木主风,火眼皆由风引动,风动火烈,风火交煽,病势益重。因此,出现了诸多清肝、泻心、清脾、泻肺、通腑泄热的方药,尤以清肝泻火、清肝利湿最甚。祛风清热、清热解毒、清热利湿成了外障眼病的主要治法。即使是内障也常用清热解郁治法。宋元期间寒凉派是眼科主流。后来《一草亭目科全书》[13]概括为:“外障者风凝热结血滞也,法当除风散热活血明目”“内障者血少神劳肾虚也,法当养血补阴安神明目。”此论有临床依据,得到业内普遍认可。然而,明清时期,受温热派赵献可、张景岳等命门学说的影响,针对滥用寒凉出现的一些弊端,业内出现了争论。《目科捷径》[19]立专篇“以儆独用古方清凉之弊”倡气血虚实阴阳寒热辨证,提出“凡治外障者总以散寒去滞为主”“若内障必须温散加以补剂”,寒热之间南辕北辙。后者的提出亦出自临床,亦是经验之谈,各有所长,各有所取,有利于完善眼科治法体系。近代中医眼科在退行性眼底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疑难性眼病的治疗上显现出一定的优势,丰富适宜的治疗方法是保证疗效的重要手段。各科因为病因、病位、病性的不同,在治法上存在学科特点,专科特色是中医诊疗原则在各科的发展创新,在临证中可以会有偏重,不能偏执[20]。
重权衡,即以阴平阳秘,气血平和为目标。临证中判断病机的动态变化,要点是寒热、虚实和气火的变化,及时评估治疗的得失,并按规律对治则治法作必要的调整。
寒热和病邪的性质和患者体质有关。例如外障红肿睁不开,疼痛难忍,羞明怕日,恶寒头痛鼻塞为风寒外袭,用四味大发散。若病起突然,暴发火眼,目赤肿胀,目痛而无头痛鼻塞等症,为风火攻目,伤于气血,气滞血凝所致,选用羌活胜风汤,菊花通圣散等加减。又有寒热错杂的证例,要注意主次有别,针对主病主证,同时注意兼病兼证,复合组方兼顾并治。
虚实反映邪正斗争的态势,在病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年老体衰,脏气虚损,气血不足是基本病机,但随着病程进展出现神经上皮、色素上皮浆液性脱离,脉络膜新生血管,视网膜出血、渗出形成痰湿、瘀血和积热。病理产物又成为新的病邪。病机转变为本虚标实。治法也随之改变。由补益肝肾,益气养血,转变为扶正祛邪,活血化瘀等。若失察病机转化则不能随机变化致治疗失当[21]。
气火平衡是整体自稳,调控能力的反映。自身免疫性眼病,往往表现为气火失调,正气不足,调控失司,贼火乘之。“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气虚证在应用补气药时,在用药配伍和药物用量上要度量、权衡。气虚兼阳虚者适当辅以温阳稍加肉桂、姜、附,“少火生气”有临床意义。但用量过大,过久引起火盛反而伤气,即“壮火食气”。所以用药期间审视病机,权衡利弊,用药合乎法度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