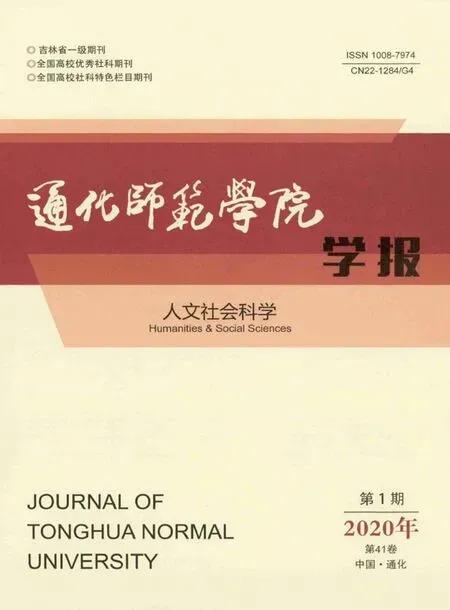代孕生育中的亲子关系认定规则研究
2020-01-09赵朝霞
赵朝霞,吴 健
一、代孕的内涵、法律认定及禁而不止之原因
(一)代孕的内涵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法》是我国卫生部发布的为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和管理的部门规章。在该办法中使用了代孕这一术语,但对于代孕的内涵未做出明确界定。
依据胎儿与代孕母亲是否具有血缘关系,代孕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他人的精子卵子进行体外受精后,将受精卵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此时代孕母亲仅仅提供自己的子宫,其妊娠出的胎儿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此类代孕称为完全代孕;另外一种情形则是代孕母亲利用自己的卵子进行人工授精,在此种情形下代孕母亲不仅要提供子宫,还要提供具有自己遗传物质的卵子,此种方式出生的胎儿与代孕母亲具有血缘关系,此种代孕称为部分代孕[1]。
在司法实践中,第一种情形更为普遍,并且第一种情形下的亲子关系法律认定更为复杂,因此本文着重于探讨第一种情形,即完全代孕情形下的亲子关系法律认定问题。
(二)代孕在我国的法律认定及地下产业存在的原因
我国在2016年1月1日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将草案中的“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一条删除,因此现如今我国对于代孕仍然依据上文所提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的“任何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条款对代孕进行禁止。
但是在现实中,代孕却禁而不止,地下代孕交易已形成产业,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先天身体机能缺陷导致部分人群生育艰难或者丧失生育能力,加之中国自古以来的传宗接代思想的根深蒂固[2],当生物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这类群体能够通过代孕来解决人生一大难题时,即使有法律加以禁止,他们仍然会铤而走险进行代孕。
第二,随着社会发展以及公民思想的开放,特别是当前女权主义的盛行,越来越多女性认识到妊娠既是女性一种神圣的特权,也是沉重的枷锁。她们不愿再囿于家庭生儿育女,相夫教子,而是更希望在职场与男性比肩,这时候怀孕生子就成为一种负担。因此这类女性会为了实现事业上的自我价值而不愿去在怀胎十月的同时还要承担分娩时的生命危险,在面对家庭和社会所给予的生育压力时,她们会选择通过代孕来转嫁风险与压力。
第三,我国目前失独老人的数量也在逐年攀升,他们承受着老年丧子巨大痛苦的同时,还怀有着老无所养的巨大恐惧[2]。在此情形下,部分失独老人在精子卵子仍然机能正常的情况下会选择代孕,来弥补丧子的心灵创伤,获得晚年生活的保障。
因此即使国家公权力对代孕加以禁止,仍然无法阻止代孕产业的发展壮大。一旦产业与市场逐渐形成,因代孕而产生的纠纷也会急剧增加,再也无法隐匿于黑暗之中。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年所判的全国首例代孕子女监护权案。通过此案,代孕的亲子关系认定问题高度暴露于司法实践中。我们已然可以预见,在代孕不断发展的将来,有多少类似的纠纷将会出现,因此代孕行为虽然禁止,但是与代孕相关的法理研究与论证却刻不容缓。从婚姻家庭法的角度来讲,首先要明确的就是代孕中的亲子关系究竟如何认定。
二、当前我国亲子关系认定规则
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中,亲子关系主要有两种: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
(一)自然血亲
自然血亲的依据是子女出生这一法律事实,其强调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生物学上的遗传与联系。在自然血亲中,子女的基因中往往包含父母的遗传物质,可进一步划分为婚生的父母子女关系以及非婚生的父母子女关系。在生物父母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受胎或者出生的为婚生子女,反之则为非婚生子女。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只能因送养或者父母子女一方的死亡而解除。
(二)拟制血亲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拟制血亲的形成主要来源于收养或者生物学父母再婚的法律行为。具体表现为养父母与养子女的亲子关系、尽到抚养教育责任义务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的亲子关系。与自然血亲不同,拟制血亲是可以通过解除收养关系以及继父母与生父母的离异而解除的。
对于拟制血亲父母双方的认定,自然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而对于自然血亲而言,我国传统上是采用“分娩说”,即娩出者为母这一原则来认定母亲;[3]137对于父亲的认定,我国法律尚未有明确规定,但也借鉴国外的“婚生推定+否认”这一模式。
然而在代孕的亲子关系认定中,当传统情形下的分娩母亲和生物遗传母亲为同一人的规则被打破时,采用传统的“分娩说”无疑会陷入窘境[4]。以本文所要讨论完全代孕的情况为例:代孕母亲将一对夫妻的受精卵植入子宫内,十月怀胎后娩出胎儿,此时若采用传统分娩说,则代孕母成为了胎儿的母亲,婚生推定使得代孕母亲的丈夫成为胎儿的法律父亲。提供卵子以及遗传物质的委托母亲此时既不能依据代孕协议取得母亲身份,也不能依据血缘关系进行主张。然而提供精子的委托父亲,却可以依据血缘关系对非婚生子女主张父子关系成立。在此情形下,就陷入了“父为父,母不为母”的尴尬境地。
因此在代孕的亲子关系认定中,采取传统的认定方式是行不通的,必须针对代孕中的亲子关系认定问题,提出一套新的可行方案。
三、我国关于代孕中亲子关系认定的学说
目前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对于代孕中的亲子关系认定问题,颇有百家争鸣之态,但主流学说仍是以下四种:分娩说、基因说、契约说以及子女最佳利益说。
(一)分娩说
分娩说即前文提到的我国对于自然血亲的传统认定原则——娩出者为母原则。通俗来讲,就是谁十月怀胎生下孩子谁就是孩子的母亲。这一传统学说放到代孕亲子关系认定的情境中仍有许多拥趸也是不无道理的:第一,这一认定方式最为简单直接,其认定无需其他任何外部条件,从法律角度来讲,具有无可比拟的确定性;第二,无论是从心理还是生理角度,代孕母亲在妊娠期间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及无可挽回的身体机能的损害,分娩原则将其认定为法律母亲不失为对其的一种补偿[5];第三,我国到目前为止对于代孕仍然是持反对态度并加以禁止,采用分娩说将代孕母亲认定为胎儿的法律母亲,无疑是与代孕关系中双方的初衷背道而驰,在此情形下,采用分娩说成为一种有效的打击代孕的手段。但是这也违背了代孕生殖技术的目的,不符合人类医学发展的要求。
(二)基因说
基因说与分娩说恰恰相反。基因说依据生物学上的遗传原则,认为谁提供的带有遗传物质的精子和卵子,谁就是娩出婴儿的法律意义上的父母。在本文讨论的代孕情形下,即委托母亲为法律母亲。这一学说在某些角度亦是言之有理:第一,无论由谁娩出,婴儿的容貌、血型乃至性格,都摆脱不掉委托母亲基因的影响,娩出只是一时的,但基因却是伴随一生的烙印;第二,基于基因认定亲子关系,也是自古而有之的。古有滴血认亲,而现代法律中的“婚生推定+否认”原则中否认的依据亦是亲子鉴定——对基因的检测。但是采纳基因说满足代孕母亲的愿望,也会直接加剧代孕母亲子宫的物化,间接导致更多的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
(三)契约说
契约说是完全遵循《私法领域》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认为委托母亲与代孕母亲双方协商签订代孕协议,对法律母亲这一身份归属作出约定,当胎儿娩出时,完全按照协议的约定来认定婴儿的法律母亲。在实践中,代孕协议往往约定委托母亲作为娩出婴儿的母亲。波斯纳曾说过:“正是委托夫妻人工生殖的意愿,才使得这个孩子的出生成为可能。”[2]这充分表明了契约说的本质:不能生育或者不愿生育的委托母亲基于强烈的想要拥有孩子的意愿,找到代孕母亲并与其签订协议,约定代孕母亲放弃亲权,由委托母亲取得亲权。然而与前述两种学说不同,契约说的成立有一个必要的前提——代孕协议合法有效。然而在我国,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并不受《合同法》调整,因此契约说在我国只能是空中楼阁,并无实际运用的可能。
(四)子女最佳利益说
如果说将前述三种学说类比为法律规则,那么最后一条子女最佳利益说就相当于法律原则——适用范围广,起补充兜底的作用。
顾名思义,子女最佳利益就是将子女的利益放在首位,将其成长发展作为判定亲权归属的第一标准。子女的事务并不是简单的父母事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子女从一出生就处于弱势一方,需要公权力介入加以保护。委托母亲与代孕母亲双方谁的生活环境、经济能力、个性品格更适合抚养子女,更有利于子女的成长发展,谁就是子女的法律父母[6]。在子女最佳利益学说中,法官拥有较大裁量权,需要根据个案情形进行判定[8]。然而当国家法律放开对代孕的管制时,这一情形无疑会成为司法的沉重负担。从另一角度讲,法官所做判决真的是对于法律父母身份的确认吗?仔细想想其实不然。法官只是按照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判定了抚养权属于谁,然而法律父母的身份的认定却不能如此简单地套用。
四、我国代孕生育中亲子关系认定规则的构建
目前理论界存在的上述四种学说各有利弊,我们在构建代孕生育中的亲子关系认定规则时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全然否定,而应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一)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我国于1990 年缔结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就对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有所规定:所有和儿童有关的举措,都应当把保护儿童的最佳利益作为第一要务考虑。显而易见,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公认的处理父母子女关系的重要原则。在代孕亲子关系认定中,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往往能够突破认定标准的局限性,对其的解释和运用,能够填补规则的空白。实践中往往委托母亲一方经济状况以及生活环境较好,对代孕子女亲权自始存在着强烈的归属要求,而许多代孕母亲是因为金钱的诱惑而违法代孕,经济、所受教育以及生活水平相较而言更低,其自身也根本没有抚养孩子的意愿。在此情形下,按照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代孕所生子女的亲权往往归属于委托母亲一方。不仅如此,按照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代孕所生子女还应与婚生子女地位平等,不得歧视。司法实践中,即使我国禁止代孕,但是对于代孕产生的纠纷仍然适用了这一原则。在全国首例代孕引发的监护权案中,二审法院正是将此原则作为重要理由,进而将监护权判归陈某。
(二)符合代孕生殖目的原则
之所以代孕禁而不止,最主要是因为缺乏生育能力的家庭渴望拥有孩子。委托母亲找到代孕母亲签订代孕协议,约定代孕母亲娩出婴儿后,委托母亲获得亲权,代孕母亲获得报酬。显而易见,代孕发生的初衷就是委托母亲为了成为孩子母亲,代孕母亲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不欲抚养孩子[9]。若不顾代孕双方的主观目的,而依据其他原则例如分娩说一味判定子女归属代孕母亲,既会使得委托母亲人财两失,也会加重代孕母亲的负担,最重要的是对子女日后的成长发展存在极大不利。同时,代孕生殖技术发展到今日对于人类最大的价值就是为无法生育的人群提供拥有自己子女的机会,因此在认定代孕亲子关系中,不可一味采用其他学说,忽视代孕双方的主观目的以及代孕生殖目的。
(三)有限使用原则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遵循着自然生殖的繁衍规律,代孕技术发展至今,我们仍不能摈弃这一规律。代孕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只能作为对人类生活发展的辅助,而不能成为人类任意创造生命、改造生命的工具。因此对于代孕技术,必须限制其使用的条件与范围。只有当不孕家庭穷尽其他所有救济方式仍不能走出困境时,才能将代孕作为最后的救济途径。
(四)禁止商业代孕原则
如今我国代孕的发展主要是商业代孕市场的发展。中介一边以金钱诱惑刚进入社会的年轻女性,说服其作为代孕母亲,另一边瞄准具有经济实力却苦于不能生育的家庭,高价收取委托母亲一方的费用,低价支付给代孕母亲,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商业代孕使得想要不劳而获的女性找到另外一种出卖自己身体的方式,将会加剧社会上的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同时在商业代孕的情形下,女性子宫成为一种用来孕育孩子的工具,成为可以买卖的物品,这既是几百年来女权主义发展的倒退,也违背了伦理。更有甚者,当中介找不到合适的代孕母亲时,拐卖妇女的犯罪团体必然会和违法的代孕中介相结合,拐卖妇女并强迫其代孕,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因此,即使未来国家逐步放宽对代孕的管制,在初期也必须禁止商业代孕,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在禁止商业代孕的情形下,可以允许亲属或者社会上志愿者的公益代孕,作为对禁止商业代孕的补充。区别商业代孕与公益代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是否存在报酬。公益代孕中,委托夫妇应被禁止向代孕母亲支付额外报酬,但是为了维护代孕母亲的合理权益,相关误工费、营养费、身体受损医疗费以及必要的精神补偿金等费用必须由委托夫妇支付给代孕母亲[10]。
(五)公权力介入原则
代孕目前在我国仍处于管制之中,未来如若放开管制,切不可过于急切地完全依靠当事人订立的代孕协议意思自治,公权力不仅要履行总体的监管职责,更要对代孕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把控,包括委托家庭的确认、委托母亲的资格和代孕母亲的资格的审核、代孕协议的审查、代孕机构的管理等等[6,9]。
总体而言,我国在处理代孕生育中的亲子关系认定问题时必须以上述几点作为基本原则加以把握。从具体认定标准角度来讲,宜采用“有条件的契约说”——以代孕协议为基础,辅之以子女最佳利益的考量,尊重意思自治的同时又将代孕置于公权力的监管之下。
前文已经阐明,未来我国放开代孕管制的初期,对于完全代孕的情形,要禁止商业代孕,以亲属以及志愿者的公益代孕为补充。然而即使是公益代孕,也口说无凭,双方也不可能完全避免纠纷的发生,因此公益代孕的代孕活动也必须签订代孕协议。双方对于娩出婴儿的亲权或者对于代孕母亲探视权利所作的约定,对于代孕母亲营养费、误工费等必要费用的约定,在得到相关机构审核通过后合法有效,当发生相关争议纠纷时,法院作出审判必须以经过公权力机关审核的代孕协议为基础。例如娩出的孩子存在先天缺陷或者患有重大疾病,此时委托父母以及代孕母亲双方都不愿抚养孩子,法院可依据所签订的代孕协议确认亲子关系,若双方在协议中对于孩子抚养存在约定,也可依据双方约定判定实际抚养权。
代孕本来就是委托父母与代孕母亲双方的决定,无论合法与否、合理与否,都不可将不利后果由无辜的婴儿承担。因此将代孕协议作为基础的同时,子女最佳利益的考量必不可少。例如婴儿娩出后,代孕母亲对婴儿提出亲权要求,此时委托母亲一方恰好家庭遭遇变故或者有其他不利情形发生,此时法院不可一味按照代孕协议进行判定,而应考虑实际情况,衡量委托父母与代孕母亲双方哪一方的生理情况、心理状态以及经济水平更有利于子女的成长与发展。虽说以代孕协议为基础,子女最佳利益的考量作为补充,但当特殊情形出现时,也可将子女最佳利益作为主要判决依据。
代孕作为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给许多不孕家庭带来了希望,帮助他们完成家庭圆满的心愿。与此同时,代孕所引发的问题与纠纷也层出不穷,其中最主要的难题就是由代孕引发的亲子关系认定问题。在亲子关系的认定中,应当在基本遵循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符合代孕生殖目的原则、有限使用原则、禁止商业代孕原则以及公权力介入原则的基础上,采用“有条件的契约说”,以公益代孕协议为基础,以子女最佳利益为考量,切实保护代孕子女、委托母亲以及代孕母亲的合法权益。
总之,对于代孕,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这样只能助长地下不法代孕、拐卖等黑色产业链的发展。相反国家以及司法工作人员应该正视问题,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逐步放开代孕管制,并丰富法学理论研究以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只有这样,代孕生殖技术才会真正发挥其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