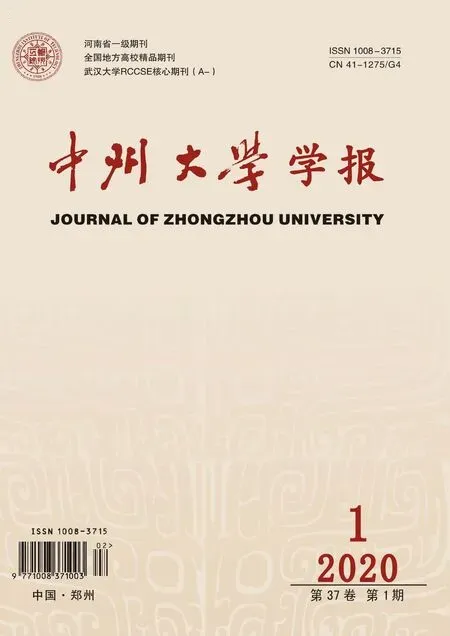历史延展中的人性呈现
——谈田中禾长篇小说《模糊》中的人性叙述
2020-01-07刘宏志
刘宏志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田中禾的长篇新作《模糊》[1]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结构方式——小说是由一部小说手稿和叙事者对小说手稿书写地方的实地探访组成。故事中套故事,这种写作模式并不稀奇。《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佐德就是用这种方式让她的故事无限期地延宕下去的。田中禾这部小说的有趣之处在于,利用这种结构方式,建构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从而给人性的呈现提供了一个更为阔大的舞台。
一、拉开的历史时空与真实人性之问
《模糊》的第一部分是一部小说手稿。叙事者某天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这个包裹中就是一部小说手稿。而且,有趣的是,这部小说手稿中的主人公章明,显然就是叙事者失踪的二哥张书铭。这部小说手稿,就讲述了章明离开家乡之后的几十年的详细经历。小说手稿是从章明来到库尔喀拉开始故事叙述的。此时的章明,也已经是犯了错误的人,是被下放到库尔喀拉的。但是,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显然还没有伤害到他。他依然还是风度翩翩,在工作上,也是技术骨干。此时的章明,除了在家乡有一个妻子,在库尔喀拉还有几个不同的女孩在喜欢他。接下来,章明开始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在遭受政治打击的过程中,他的妻子也反戈一击,检举揭发了他,而且嫁给了主持打击他的领导老耿。喜欢他的女孩,或者被迫离开,或者受到牵连自杀。不断被朋友欺骗、被劳改的章明,依然被女孩子喜欢。老家的姑娘小六,千里迢迢来到边疆,嫁给了章明,并且给章明生了两个孩子。但是,在章明被通知解除“右派”身份的当天,他却发现了小六和一个盲流的奸情。这直接导致了他婚姻的破裂。之后,蹉跎半生的章明,显然已经不再有当年的锐气,在又一次婚恋无果之后,从单位神秘地消失了。
小说的第二部分是叙事者“我”对二哥的寻找。“我”读到小说手稿后,立刻意识到小说中的章明,就是自己的二哥——“我”的二哥也是神秘失踪的。于是,“我”立刻踏上了去库尔喀拉的道路,去寻找二哥。在这一部分,小说叙述了“我”对上半部中涉及的一些关键人物的探访,如对二哥的两任妻子的探访,对二哥当年同学的探访,等等。
从小说叙事来看,这个小说很容易被理解成是一部对特定历史年代反思的作品,而且,毋庸置疑,小说的第一部分即手稿部分,关于章明的命运的叙述和呈现,也的确非常精彩、形象。事实上,对这部小说做出这样的理解显然也并没有太大问题。不过,这样理解作品,却也显然把这部小说的价值限定在了对一个特定时代的反映,而忽略了其对人性更为深刻的发掘。事实上,小说通过设置第二部分,即对小说第一部分中历史当事人的实地探访,和小说的第一部分一起,有效建构起了一个复杂的历史时空。在这个被拉长的复杂的历史时空中,人性的复杂性也被呈现了出来。
在“我”寻访二哥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二哥当年的同学赵宛民。赵宛民是二哥的同学,也是一起从河南走出的同乡。他们怀着报国志向主动来到新疆落户。在小说第二部分的叙述中,“我”所见到的赵宛民,是一个慈眉善目的长者,他同情二哥的遭遇,对那个时代也进行批判,同时也主动给予我很多帮助。赵宛民也对“我”讲过他和二哥的关系。在赵宛民的讲述中,他和二哥的关系良好,而且赵宛民对二哥也是称赞有加。这是当下时空中的赵宛民,显然,这是一个善良的,而且有着强烈正义感的长者形象。但是,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也曾经提到,二哥张书铭之所以来到库尔喀拉,在这个地方一步步开启他的悲剧人生,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原来的单位犯了错误。当年,张书铭从学校毕业之后,主动申请到新疆工作,被分配到了省交通厅。在省交通厅,章明和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组建了红山文学社。但是,不幸的是,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的这个文学社很快被定性为小团体,而且遭到批判。在这种高压局面下,一群曾经志同道合的同伴,开始互相揭发。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就是在这个时候到来的——他被他曾经深深相信的同学揭发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空中,揭发张书铭的,正是后来曾经热情称赞张书铭的赵宛民。
在叙事者后来找到的当时的历史资料中,非常清晰地写道:“赵宛民详细交代了文学社几次活动的内容,把责任推给了张书铭和另外一位同学。他说张书铭特别崇拜反革命集团里的作家,把某某的小说和某某的诗歌推荐给大家阅读。社友给北京的杂志投稿,都是张书铭提供地址。他为他们提供方格稿纸,帮他们到邮局寄发。”为了能让自己立功,他甚至不惜对曾经的伙伴恶毒攻击——“赵宛民材料里的一个细节让我禁不住心跳骤停:‘文学社最后一次聚会,大家传看报纸上登的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和编者按。张书铭上厕所,把这张报纸带去擦屁股了。’”赵宛民当年对二哥的这个揭发,显然非常恶毒,它已经远远超出了自保的意味,而更多带有打击别人让自己获利的特点。我们可以说,张书铭当年遭遇的坎坷,肯定是和赵宛民的揭发有关的。这就是历史资料中的赵宛民:他曾经受害,但他也曾经害人。那么,这个历史资料中的赵宛民和现在“我”所见到的慈眉善目的赵宛民,哪一个是真实的赵宛民呢?两个赵宛民,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呈现出不同的形象,这充分呈现了人性的复杂性。
在小说中,伤害章明最深的,显然应该是他前后两任妻子,因为他也在这两个人身上用情最深。小说中章明的第一任妻子——李梅,是在章明受到围攻的关头,突然反戈一击,背叛了章明的,而且她还嫁给了主持打击章明的领导老耿。小说以另外一个人物宋丽英的视角,描述了章明遭遇到李梅的背叛的经过。因为章明的不识时务,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无法承受这个压力的李梅背叛了章明,主动向组织靠拢了。而且,在李梅背叛章明之后,章明还不知情的情况下,老耿主持召开了批判章明的辩论会。所谓辩论会,不过是对一个批判对象进行集中打击的另一种方式而已。当别人揭发检举章明,或者和章明辩论的时候,章明显然早已做好了准备。“有时候发言人点名要章明回答质问,章明就在原地站起来回答。丽英……从上午到下午,她对章明的表现很满意,别看他平时不爱说话,可每次发言都很精彩,不但能说到点子上,还很文明,一句脏话也不说,一个脏词儿也不带。她满心为他高兴,深深为他自豪。”显然,章明的很文明,一句脏话也不说,背后隐含的是他对这辩论会的蔑视,或者说,这种打击对他而言,已经不是什么打击。他早已做好了准备。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辩论的高潮出现在晚上。一个娇小的女人手里拿着一摞东西走上台,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会场里顿时鸦雀无声。……从李梅走上台的一刻起,章明的脸变得惨白……丽英看见章明的手和腿开始抖颤,腮帮上的咬肌绷紧,整个脸扭歪了。”在这最关键的时候,来自曾经最亲密的爱人的攻击,给了章明最沉重的打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李梅对章明的攻击,不是敷衍了事,不是应付差事,而是毫不留情地选取了对章明来说最脆弱的点,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李梅把章明私下说的牢骚话、反动话一条条揭发出来,用革命道理分析、批判,这女人的口才不错,理论水平也很高……他把我们党的干部比成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大家看看,他对我们人民政权有多么深的仇恨,用心有多么恶毒……他不知道这女人啥时候把他的日记拿走了。她肯定把它交给老耿看过了,有问题的地方都折了页,现在可以有条不紊地一篇一篇读给大家听,一边读一边解释,再加上激烈的批判。” 显然,李梅对章明的批判,对于章明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从此时李梅对章明的批判来看,似乎她对章明没有爱,只有恨。但是,在叙事者“我”去寻访当年二哥的历史的时候,却发现小说中李梅的原型,即二哥的第一任妻子李春梅其实后来也悄悄帮助过二哥。二哥在下放劳动的时候,因为无法忍受艰苦的生活,曾经给李春梅写信,想让李春梅帮他说话,调回原单位。二哥的这个举动,在当时也可以算是严重的问题。如果李春梅举报二哥,那么等待二哥的将是更为沉重的打击。但是,李春梅没有举报二哥,而且还偷偷给他寄了五斤粮票。之后,在二哥失踪之后,李梅也积极去寻找二哥。显然,李春梅的这一切举动,都说明了她对二哥不是没有感情的。可是,既然如此,在当年对二哥反戈一击的时候,李春梅又为什么那么绝情?
显然,赵宛民也好,李春梅也好,以及书中其他很多人物,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中,都曾经深深伤害过二哥;但是,也正是他们,似乎又对二哥怀有感情。那么,哪一个赵宛民是真实的赵宛民?哪一个李春梅是真实的李春梅?帕斯卡尔曾经谈过人性的复杂:“当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会奇怪我们有病时怎么能做出那些事;但当我们有病时,我们就高高兴兴地服药了;病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再也没有兴致和愿望去进行健康所给予我们的但与疾病的需要不适合的娱乐和漫游了。”[2]63似乎,在不同的境遇下,人性会自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如果仅仅看二哥在特定年代的遭遇,我们似乎很容易就把赵宛民、李春梅定性为坏人。但是,如果把历史拉长,看到之后他们的举动,我们似乎又很难给他们贴上一个简单的坏人标签。毫无疑问,人性是复杂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模糊》用拉长的历史时空,给小说中的人性以充分的呈现空间,从而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关于人性可能性的思考。
二、环境、话语与人性的呈现
在《模糊》的上半部中,李梅在检举揭发章明的时候,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把人性之恶呈现了出来。作为章明曾经最亲密的爱人,李梅把章明所有对她说过的话,对其他人的讽刺等等,都说了出来,而且还把章明的日记给拿了出来,以现场批读的方式对章明展开批判。之所以说李梅在这时淋漓尽致地呈现了人性之恶,是因为,此时如果她是不得不检举揭发章明的话,她其实是不需要把章明私下给她谈论过的、在别人看来罪大恶极的私人言语完全揭发出来的,因为别人并不知道章明说过这样的话。从她当时检举揭发的坚决和彻底来看,似乎是要置章明于死地而后快。但是,在小说的下半部,我们发现,李梅的原型李春梅似乎对章明的原型——“我”的二哥张书铭,并无恶意,甚至还有感情。比如,在张书铭向她求援的时候,她并没有落井下石——把张书铭的这封信举报上去,反而悄悄给张书铭寄了五斤粮票。在张书铭失踪之后,她也积极去寻找张书铭。李春梅的女儿董红旗也对“我”说,其实李春梅对她原来的婆婆——张书铭的母亲很有感情。显然,李春梅检举揭发张书铭时候呈现出来的极端的人性之恶,并非来自她对张书铭,或者对张书铭的家庭的恨——她其实对这些人还是很有感情的。那么,李春梅的人性之恶的来源是什么?
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李春梅通过检举揭发张书铭,通过嫁给张书铭单位的领导,保证了自己的安全——她不再是一个被批斗对象的妻子,而是一个检举揭发者,进而成为一个革命领导的妻子。事实上,保护自己,显然也正是李春梅在检举揭发张书铭时表现出极端的恶的很重要的原因。阅读小说,我们也会很容易找到李春梅如此紧张地保护自己的原因——她的父亲曾经担任过伪职。在那样一个阶级斗争意识统辖一切的年代,她父亲的这个经历很容易给她的整个家庭带来灭顶之灾。显然,在恐惧中长大的李春梅,在那个特殊年代,要比那个一开始受了打击还坚持理想的张书铭成熟得多,当然,这也是她和张书铭矛盾的根源。因为自己出身不好,所以李春梅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显得积极向上。也许,直到嫁给单位领导——老革命老董后,李春梅才感觉到了安全。显然,恐惧,以及强烈的自保的愿望,会激发起人性深处的恶——只要是为了保护自己,一切的恶都是可以做的。在这里,环境是促使人性中的恶被激发出来的关键原因。当年赵宛民检举揭发张书铭,那种人性之恶的原初出发点,显然也是出于自保。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被动之恶,而不是主动之恶,或许,这也正是他们很容易忘掉自己过去的恶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是主动为恶的,所以,似乎也不需要为这个恶承担责任。
饶有意味的是李春梅的命运。在张书铭被批判的时候,李春梅突然反戈一击,通过检举揭发张书铭,保护了自己。此时李春梅的行为,是为了保护自己,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她的家人——因为一旦她被张书铭的事件牵连进去,她的曾经担任过伪职的家人毫无疑问会成为首先被打击的对象。在嫁给老董后,她把自己的爹妈、弟弟从河南老家接过来和她一起生活。显然,她通过背叛张书铭,嫁给老董,似乎获得了保护自己父母的能力,似乎让自己从恐惧中逃离。不过,在她嫁给老董之后,她还是没能保护好自己的父母。老董趁着清查盲流,把李春梅的父母、弟弟妹妹都交给了遣送队。两个老人被遣送回原籍后,连批斗带冻饿,很快就死了。也就是说,其实李春梅最终也没有保护好她的父母。老董之所以把李春梅父母遣送回原籍,是因为李春梅喜欢上了另外一个人——小于,而和他闹离婚。两个人的关系闹僵了。当然,这里有趣的地方在于,当李春梅喜欢上另外一个人,要和老董闹离婚的时候,她其实应该知道,老董依然有着毁灭她、毁灭她父母的能力——事实上,李春梅父母后面遭遇的悲剧也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同样是面对来自老董的压力,李春梅此时为什么没有原来和张书铭在一起时的那种强烈的恐惧?她此时为什么能直面来自老董的压力,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显然,李春梅前后表现出的差异,和她前后期所处的环境不同,所面临的话语压力不同有关。在成为老董的妻子之后,和老董成为仇人,李春梅虽然知道老董仍然有能力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她进行打击,但是在她生活的外部环境中,却并没有各种话语时时刻刻对她进行提醒或者强调,因此也无法让她恐慌。但是,在批斗张书铭的时候,她所面临的环境却不仅仅是来自老董一人的压力。当时的情况是:老董打击张书铭的意愿,已经化作了单位中几乎所有工作人员的意愿,并且通过这些人不断张贴出来的批判张书铭的大字报呈现出来。此时,张书铭和李春梅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来自领导的打压,而且还是无所不在的来自各个方面的强大的精神压力。这种无所不在的大字报,无所不在的强大的批判话语,无时无刻不在向李春梅暗示着之后可怕的处境:张书铭将会被批判,张书铭将会被斗倒,李春梅会被张书铭牵连,李春梅父亲曾经担任伪职的事情会被发现并且张扬出来……对抗这种环境,显然需要极大的心理定力。张书铭之所以还能坦然面对,更多的是源于他在某种程度上的无知。但是,一直对自己父亲身份极其敏感的李春梅,显然就无法承受这种来自环境的巨大压力了。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巨大的威压之下,李春梅心理崩溃,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父母,背叛张书铭似乎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无所不在的又似乎是漫无尽头的攻击性话语,似乎比真实的打击更让人无法承受。当年批判张书铭时候,李春梅人性中的恶,也正是在这无尽的攻击性话语的挤压之下,彻底迸发出来了。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性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存在,它和环境有关,和话语有关。
三、人性的弱点:遗忘,扭曲的记忆与对自我的原谅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特殊高压年代就是一个人性的试验场。在这个试验场中,人性中极端的恶与善都会迸发出来。这时候呈现出来的人性之恶,或者人性之善,都具有人性标本的价值。不过,人如何去面对自己曾经的恶,显然又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有趣的话题,而这个,似乎也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模糊》这部小说设置了一个拉长的时空,在完成了特殊年代人性的极端呈现之后,又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软弱。
当叙事者“我”刚见到赵宛民时,“我”的眼中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他热情善良,助人为乐,很热情地招待我。他谈起了他在“极左”年代所受的打击,但是有没有因为这打击而失去对生活的爱——他依然对生活抱有热情,而且现在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了。如果没有“我”得到的关于赵宛民的历史资料,显然,我们会难以相信这样一个人居然曾经利用恶毒举报别人来谋取自己立功。小说写到,赵宛民正在写自己的回忆录,而叙事者“我”也看到了他回忆录的第一部分。在这个回忆录的叙事中,赵宛民并没有对自身展开反思。那么,问题在于,在接下来的回忆录的书写中,在涉及红山文学社这段历史的时候,赵宛民会书写自己曾经冷酷地检举揭发同伴么?至少,在叙事者“我”看来,是不会的。“我猜想,赵宛民正在写的回忆录里,大约不会有这些内容。人的回忆录之所以不可靠,就是因为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在赵宛民这里,我们似乎根本无法看到任何的愧疚或者自责。他很干净利索地把自己曾经构陷同伴的令人不齿的事情从自己的脑海中抹去了。“我”见到赵宛民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热情、坦诚是真实的,而且,还力所能及地为“我”寻找二哥提供帮助。他似乎并没有担心我可能会找到他当年举报二哥的资料,或许,在他的脑海中,他已经把这一段历史剔除了。当然,在这里,也显示出赵宛民这个形象更值得深入反思的地方,即他在反思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反思自我。他用遗忘帮助了自己,彻底忘记了自己过往不堪的行为,从而在自己心目中塑造出自我的健康、善良的形象。
事实上,不仅仅是赵宛民用遗忘来保护自己。值得深思的是,叙事者“我”也展开了对自我的反思和批判。“一个亲人,当你失去他时,才会意识到对他亏欠了很多,此生无法弥补。这部书稿不仅唤起我对亲人的怀念,也唤起了我心底深深的愧疚。张书铭每次探亲回来,为什么我不能多花费点时间陪陪他,耐心听听他那些啰啰唆唆的倾诉?为什么不能多给他一点亲情,多给他一点温暖?我自以为对他够宽厚够仁爱,其实那只是一种怜悯和施舍。读那些荒唐的来信时,为什么我心里没有同情,只有嫌怨和不耐烦?以至于把他的失踪看作是我和大哥的解脱,还觉得对他已经仁至义尽?”小说中“我”的二哥张书铭是多年以前就失踪了的,但是“我”却没有想到去寻找二哥;而是相反,“我”已经忘记了生命中还曾经有过一个二哥,正是这部小说书稿,让我不得不重新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我”曾经有过一个二哥,他现在失踪了,而且,他失踪好多年,我也从来没有认真去找过他。为什么“我”会遗忘曾经饱经磨难的二哥,因为“我”曾经对他所经历的苦难极其冷漠,因为“我”曾经把二哥看作自己生命的累赘。所以,当听到二哥失踪的消息时,“我”本能的感觉是解脱。但是,“我”的良知又告诉自己,自己对二哥做的是不对的。于是,为了逃避自我良知的审判,二哥便被“我”遗忘了。
这种选择性遗忘,还可以扭曲记忆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小说上半部关于二哥历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任妻子小六的背叛,对于章明来说打击重大。章明怀着“右派”被改正的喜悦,披星戴月回家找妻儿报喜,但是看到的却是一个盲流已经成为自己这个家中的主人。然后,两个人就分开了,而这次妻子的背叛,显然也给了章明沉重的打击。我们当然可以给小六的出轨找出一系列的理由,比如章明作为一个书生,现实生存能力太弱,所以这个家庭需要小六承担太多的责任;比如章明长期在外面劳动,经常不在家里,所以,家里的重体力活儿需要有人承担,等等。我们可以对小六的出轨给予很多理解,甚至同情,但是,毕竟这无法改变小六出轨的事实。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在两个人的关系上,她是对不起章明的。那么,若干年后,历史中的小六,会如何看待章明,看待自己和章明的关系呢?
小说的后半部分,在叙事者“我”探寻二哥的时候,也找到了曾经的二嫂,上半部小说中小六的原型——叶玉珍。在见到“我”的时候,叶玉珍首先发起了对二哥的批判,说二哥无能,除了能在单位上班,什么也干不了;说二哥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需要她出面保护他……而且,在谈到两人离婚的原因的时候,她轻描淡写地说:“笨蛋,窝囊废,还是个小心眼儿!人家谁个女人打火墙?他连个火墙也不会打,我请人帮忙打火墙,他就说我跟人家有什么什么关系。……闹得像八辈子仇人似的,手里掂着铁锨,撵着跟我拼命。”显然,在这里,她把自己的出轨,对二哥的背叛,解读成了二哥小心眼。当然,言外之意即是,她是没有错误的,只是二哥误会了而已。而且,她把两人离婚的原因,推到了二哥身上,“他改正了,到库尔喀拉去上班了,我带着孩子去找他,他把箱子柜子锁上,像防贼一样防着我。户口、粮食关系都攥在他手里不给我,连饭也不管。我跑去找他们领导,他才给我饭吃。他上了班,有了工作,就不想要我们了,嫌我们拖累他,想离了婚再找个有工作、有工资的。”换言之,历史上原本曾经给予了二哥沉重打击的来自妻子的背叛、离婚,在曾经的妻子的话语中,成了二哥无能、小心眼,以及有意嫌弃妻子。叶玉珍自然是清楚历史的真相的,否则,也不会在“我”针对她对二哥的批判做出回击之后而哑口无言。人性的复杂在叶玉珍这里又呈现出来。对于这种状况,帕斯卡尔曾经有过一个有趣的说法——人对真理充满仇恨。他认为,人类的本性是爱自己,“其本性就是只爱自己并且只考虑自己”。然而,如果自己并不完美甚至充满错误,“他就要尽可能地摧毁他自己认识中的以及别人认识中的真理;这就是说,他要费尽苦心既向别人也向他自己遮蔽起自己的缺点,他既不能忍受别人使他看到这些缺点,也不能忍受别人看到这些缺点”[2]53。某种程度上,或许叶玉珍对二哥还心怀愧意,但是,她必须要有合适的理由来给自己和二哥的离婚做出一个解释;用这个解释,对自己,对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所交代。于是,在她的叙述中,她和二哥的关系,就完全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换言之,叶玉珍是通过故意扭曲记忆的方式,来有意对历史中自己不光彩的行为进行了选择性遗忘。从叶玉珍对二哥的抱怨,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性的另一面,即人总是在有意无意地修改着自己的记忆,从而可以让自己回避掉自己在历史中的难堪,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这个世界。人总是习惯于原谅自己。
其实,无论选择性的遗忘也罢,还是更加强调对自己的原谅也罢,背后折射的可能都是人性的软弱。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即人对自我无法面对的东西的有意无意地逃避。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人性的软弱。叙事者“我”是软弱的,所以,我有意无意地把二哥给遗忘掉了;二哥自己也是软弱的,他曾经那么勇敢,但是在生活的困境中,他给自己曾经深深痛恨的背叛自己的李春梅去信,希望她能帮助自己,甚至还向那个夺去自己妻子的人问好;小说中李春梅和二哥的女儿董红梅也是软弱的,虽然她是一个成功的女商人,虽然她因为丈夫出轨也愤而和丈夫离婚,但是她却始终无法放下对已经离婚的丈夫的爱,而甘愿成为前夫的提款机。但是,人性的这种软弱显然不应该成为人原谅自己的理由。在这部书的开头,叙事者说,中国人是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从赵宛民、小六这些形象,印证了作者的这个判断。但是,显然不仅仅如此。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仅仅善于忘记,而且还缺乏反思精神,缺乏自省精神。在反观历史的时候,他们都努力去指责别人,展示自己的伤疤,却都忘记了反思自我,批判自我。的确,在强大力量面前,人也许如同一棵芦苇,是柔软的、无力的。但是,人毕竟是会思想的芦苇。如果思想的锋芒从来不指向自身,没有对自我的反思,那么,永远就不会有人类自身的进步。
四、结语
显然,我们可以将《模糊》理解为对特定历史年代进行反思的一部小说。小说中对二哥的历史的叙述,毫无疑问能够达到这个效果——通过对二哥经历的阅读和思考,我们会反思这个时代的问题。但是,以这种方式看小说,显然也会限制作品意义的可能性。事实上,因为小说是不被授权的话语,所以,无论对某个时代的精神刻画是如何的深刻,也总不能将之作为历史来看待。小说的价值,尤其是伟大作品的价值,在于让每一个读者从中看到自己的人生,在于让每一个读者对社会、对人性有更多的思考。所以,我们显然也可以忽略小说与特定历史年代的对应,去观察、分析小说中所蕴含的一般性原则。那么,在这部小说中,除了对特定历史年代的反思之外,我们更能发现作家展开的对于人性的深入的思考——也正是在这样漫长的时空对比中,人性的多面性才能如此毫发毕现地呈现出来。显然,《模糊》是对历史的反思,更是对人性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