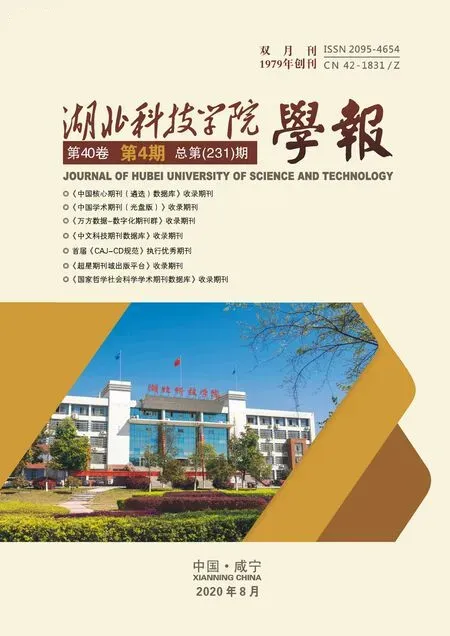“笼中鸟”的出走与回归
——简析《简·爱》中典型女性形象
2020-01-06邹毓菲
邹毓菲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简·爱》是英国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一部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作为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它不仅塑造了一个主体意识鲜明、敢于反抗压迫、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也从文本中的女性角色身上体现出了正在觉醒中的女性意识,反映了对女性自由意识的追求和个体存在价值的推崇。
纵观《简·爱》的研究历史,对《简·爱》的女性主义叙事的研究评论主要有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性意识、伯莎这一角色存在的合理性、简·爱所代表的女性反抗与权利意识、简·爱女性叙述的局限性等方面。如国外的学者、评论家有弗吉利亚·伍尔夫认为夏洛蒂·勃朗特代表了19世纪典型的中期愤怒、“受挫”的女性主义,桑德拉与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把疯女人伯莎看作简·爱心灵中的阴暗面,是她一直想抑制的另一个凶悍的秘密的“自我”,有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指出《简·爱》的帝国主义如何将“变成了一个偶像式的女性主义文本”,论文《我是一个怪物么——怪物阴影中的<简·爱>》以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为引探讨罗切斯特和与他相关的女人的关系,有南希·阿姆斯壮的《妇女的博物馆:<简·爱>》从叙事细节出发,认为勃朗特用从未有过的方式把家居环境与女性的权威联系起来[1];同时国内的学者、评论家有韦德三、吴静、夏郁芹、佟静、王慧英等认为《简·爱》反映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对当代女性有重要的启示和影响,也有王文惠从生态女权主义角度对《简·爱》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文本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和自然资源遭受男性压迫和掠夺的悲剧,表达了作者解放女性和自然、发展女性自我意识和两性完全平等和谐生存的理想。[2]
本文将从《简·爱》的结局出发,以女性的出走与回归为切入点来分析《简·爱》中的典型女性形象。历来对小说结局的批判大都认为此结局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且违反了现实主义叙事原则的“可能性”,但其实恰是这样的结局才能更好的反映出女性的两难处境,一边是为了个体的解放,为了平等的地位和应得的权力对男权社会做出反抗,一边却不得不为保留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认可的一席之地而顺从迎合。
如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演说的:“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出走反抗与回归家庭,是女性在觉醒后的必经的一个分岔路口,然而前途未卜如娜拉离家出走,《简·爱》中女性角色的出走与回归又有哪些意义呢?
一、“笼中鸟”的反抗与顺从
《简·爱》中的最典型的女性角色自然是女主人公简·爱。简·爱的人物形象所凸显出来的一个重要特质便是她的矛盾性。从盖兹海德到劳沃德到桑菲尔德再到沼屋,简·爱一直在激进与保守、叛逆与妥协之间游离,在“反抗——顺从——反抗”中来回波动,而且反抗的强度越来越低,顺从的时间越来越长,经历了一个从“反叛者”到“顺从者”的转变。这样的性格转变不能只简单地归为简·爱个人性格的不足,更多的是一种必然,因为简·爱始终无法摆脱一种对父权社会的服从性,所以她的性格变化呈现了一种“出走—回归”的模式。
简·爱的生活轨迹可以按照她的所在地分为四个阶段:盖兹海德时期与劳沃德前期、劳沃德后期与桑菲尔德时期、沼屋时期以及最后回到罗切斯特身边的芬丁庄园时期。前两个阶段的简·爱处于一种渐弱式的反抗状态,而后两个阶段则是一种渐进式的顺从状态。
当简·爱住在盖兹海德,她的首要反抗对象是盖兹海德的“小皇帝”约翰和她的里德舅妈,小说一开篇就表现出了简·爱骨子里的不顺从:面对约翰的压迫与欺凌,简奋起反抗,“你像个杀人犯——你像个虐待奴隶的人——你像罗马的皇帝!”[3](P15)一句直接喊出了简·爱对于约翰的不满与对抗,表达了她对自尊的维护;被舅妈关在红房子里时,她的反抗意识也一直在挣扎,“‘决心’也同样被鼓舞起来,催促着我采取什么奇妙的方法,从这难以忍受的压迫下逃跑——譬如像出走,或者,万一走不了的话,就永远不再吃不再喝,听任自己饿死。”[3](P18);甚至在得知被里德舅妈送往劳沃德时,她还直言不讳地向舅妈尖锐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愤恨。到了劳沃德,从简·爱与海伦的那一次谈话中,我们也能看出简·爱本性中的反抗精神:“当我们无缘无故挨打的时候,我们应该狠狠地回击;我肯定我们应该回击——狠狠地回击,教训教训打我们的那个人,叫他永远不敢再这样打人。”[3](P47)“有些人,给我不公平的惩罚,那我就不能不反抗。”[3](P47)从简·爱的行为和言语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在第一阶段的状态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不公正的对待等让她感到不平的事件就像一根导火索,可以瞬间让她变得激进愤慨。
而当简·爱经历了在劳沃德的八年生活之后,她逐渐变得内敛而沉稳,这和海伦与谭波尔对她的教诲以及海伦的突然死亡是紧密相关的。而随海伦逝去之后,谭波尔小姐的离开似乎也将简·爱难得的宁静也带走了,“从她离开的那天起,我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一切稳定的情绪,……全都跟她一起消失了。……我似乎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克己的人。……我已经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我的心已经把它从谭波尔小姐那儿借来的东西抛开——或者不如说,她已经把我在她身边所感到的宁静气氛带走了——如今,我恢复了我的本性。”[3](P65~66)简·爱感到从前的情绪又活跃起来,她认为自己保持平静的理由已经不再存在了,这便引发了她的第一次“出走”;“保持平静”一词用的耐人寻味,也许可以理解为简·爱在为了迎合他人而有意地压抑自己的天性,暗含了一种“反抗—顺从—再反抗”的意味,也许小说在这里就为简·爱随后对罗切斯特与圣·约翰的迎合埋下了伏笔。
初为桑菲尔德的家庭教师的简·爱在最初其实仍然对生活的平静感到乏味和不满,刚刚逃出劳沃德那样毫无起伏的生活的简·爱还留存着“反抗”的情绪,向往着有波澜的经历和不平凡的体验,她认为“说人们应该对平静感到满足,这是徒然的;人们总得有行动;即使找不到行动,也得创造行动。”[3](P83)可这样的不宁的心绪却被罗切斯特的出现打破了,与罗切斯特相爱的过程正是简·爱再次“反抗—顺从”的反映。最初简爱是对罗切斯特毫不畏惧的,第一次会面时她能“毫不拘束的坐下来”,认为罗切斯特“粗鲁的任性”使她“没有任何义务”,但随着简爱对罗切斯特的感情日益深重,她对于罗切斯特态度反而越来越惶恐,仅仅是在称呼上,“我的主人”出现的次数就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在决定要同罗切斯特结婚后,“每晚七点半”的会面中,简似乎在惹恼罗切斯特的行为中不断的确认罗切斯特对她的感情是否真实,恰好反映出了简的不安全感和身处父权社会中女性对于男性不自觉的依附性。在简不知不觉的顺从中的第二次“出走”是在她得知了伯莎的存在之后,毅然决然地拒绝成为罗切斯特情妇的举动,但这样一种离开附上了很浓重的宗教因素,也反映出简·爱本身的自卑,她认为自己缺少金钱与美貌,现在所谓的经济独立其实也是建立在做桑菲尔德的家庭教师的基础上的,如果她真的接受成为罗切斯特的情妇,那么她就不可避免地会沦为罗切斯特的附属品,而且简·爱在离开时是充满了不舍和痛苦的,这样看来,简·爱的第二次“出走”已经没有第一次那么强的反抗性了,反而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选择。
在沼屋生活的日子里,简·爱同两姐妹的交流与相处使得她的个性有所还原,但在与圣·约翰的相处中,简·爱依旧不可避免的经历了一个从平等到顺从的过程。简·爱意识到要讨圣·约翰喜欢,就必须“抛掉我的一半天性,扼杀我的一半才能”,但这种感觉带来的不是她对圣·约翰意志的反抗,而是她觉得拒绝圣·约翰的种种要求越来越困难了。为了让圣·约翰满意,她可以放弃学习自己喜欢的德语转而学习圣·约翰要求她学的兴都斯坦语;在圣·约翰要求他作为他的妻子一同前往印度传教时,尽管她拒绝了两次他的要求,但在最终却又选择了妥协,而摆脱这样一种妥协的结果的诱因不是她自己内心的意识而是罗切斯特超自然的呼唤,简·爱的性格变化到了这里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顺从性。
到了最后的芬丁庄园时期,“出走”的简终于因为“简!简!简!”的呼唤选择了“回归”,还是成为了传统的“房中的天使”。简在反驳罗切斯特对自己的否定的时候说罗切斯特是一颗富有生机的大树,“不管你要不要,你的根部周围都会长出花草,因为它们喜欢你的浓荫”[3](P317),简在在这样一种比喻中将自己比作了“花草”,也正是其心中对于父权的一种服从性在作祟。对于作者安排的这样一种“出走—回归”性格变化,可以理解为是在表现在当时的时代,女性始终难以摆脱父权社会对她们的束缚和压迫,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笼中鸟”的反叛与毁灭
《简·爱》中的第二个典型的女性角色自然是疯女人伯莎·梅森。与简·爱相异的是,伯莎从出场时便已经处于一个反叛的状态,在变化过程中也直接呈现出了“反叛——毁灭”的模式。作为被禁锢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是一个没有发言权的“被叙述”者,不同于简·爱以第一人称的正面叙述,她的形象几乎全都是由简·爱和罗切斯特从反面描绘出来的。
伯莎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通过简·爱的亲身经历反映出来的。首先便是她诡异的笑声和呜咽般的哭嚎,仿佛盘旋在桑菲尔德上空的无形鬼魅,为宁静的桑菲尔德凭空增添了一抹阴森;其次就是罗切斯特房间夜里燃起的大火和梅森先生受伤的那一晚,让这个诡异女人更添几分恐怖;最后是伯莎深夜潜入简·爱的房间撕毁了她的面纱之后,简·爱在对罗切斯特描绘场景时,描绘出了那张“野蛮的脸”——“又多又黑”的头发、“又白又直”的衣服、“没有血色”“又黑又肿”的脸、“红眼睛”……瞬间树立起了一个丑恶的女鬼形象。在读者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印象之后,又有了重婚败露后罗切斯特对简·爱“说惨”的“补充内容”:疯与放纵。为了在简·爱面前树立一个正人君子的模样,罗切斯特自然是对伯莎极力抹黑,通过他对简·爱的辩解,罗彻斯特塑造了自己受害者的形象:被父亲和长兄骗入婚姻,被疯妻子折磨,由此更衬出“邪恶”的伯莎对他这一懵懂青年的迫害,于是《简·爱》中的第二个典型女性形象就这样颠倒着、扭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罗切斯特那番情真意切的表白中,他曾说“梅森小姐在西班牙城以美貌著称”,而且“她那个圈子里所有的男人似乎都爱慕她”,单从这样的描述中来看,伯莎·梅森在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很有魅力的美人,那么一个美貌的少女,婚前是大家闺秀,婚后隐居偏僻的庄 园,怎么就成了“淫荡的妻子”、“纵欲的疯子”?只因为家中有精神病史,因为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母亲的忠实的女儿”吗?显然不可能。如果按照《简·爱》中本身的生活逻辑思考,伯莎应该不是像罗切斯特叙述的那样不堪。从罗彻斯特的表白中那些模糊的字句中,伯莎也许更像是一个被三万英镑出卖的少女,比如罗切斯特在讲到父亲为他筹划的这一门有利可图的婚事时,提到了结婚的对象是“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梅森先生的女儿”、有三万英镑陪嫁的伯莎·梅森小姐,而且说起父亲撮合他与伯莎的婚姻时只提她的美貌,未提她的嫁资;又如谈到老罗切斯特所做的调查时,说的是从梅森先生那儿打听到“他可以而且愿意给女儿三万英镑”,可在当时的英国,已婚妇女无权掌握自己的财产,结婚后一切财产归丈夫支配,直到1871年通过已婚妇女财产法,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4]梅森先生的三万英镑分明是给女婿不是给女儿的,罗彻斯特不可能不清楚。由此看来,伯莎所谓的“恶”可能只是罗切斯特“一言堂”的负面渲染的结果,而并非她本人的真实模样,婚后四年,罗切斯特的哥哥与父亲相继去世,他自言“现在我是够富的了”,那么在此之前四年呢?在罗切斯特还不足够富裕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容忍伯莎在放纵中疯狂吗?
从伯莎在桑菲尔德庄园的几次出现中可以推断出,伯莎的一举一动都是一个受迫害的女人渴望反抗与复仇的内心流露。深夜放火和梅森先生受伤的事件正好能反映出她对罗彻斯特的仇恨,而且梅森的受伤很有可能是误伤,她的目标应该只是罗切斯特,从罗切斯特带简·爱去看伯莎的场景也能窥见一二:“罗切斯特先生把我推到背后;疯子跳起来,凶恶地卡住他的脖子,用牙咬他的脸颊;他们搏斗着。”[3](P211)在当时的场景中,一共有五个人,简·爱、罗切斯特和跟随而来的三位绅士,如果伯莎只是纯粹的精神失常,她也许会不分对象的进行攻击,但是从伯莎每一次的暴力举动看来,她想报复的只是罗切斯特一人而已。此外,小说中还有一个细节,当医生为梅森包扎好伤口之后,梅森说伯莎说要把他的心里的血吸干,但闻言的罗切斯特却在发抖,“一种奇怪的明显的嫌恶、恐怖、憎恨的表情把他容貌歪曲得几乎变了形”[3](P154),从这里也能推断出罗切斯特其实心里知道伯莎真正仇恨的对象是谁。
但伯莎的这样疯狂的反叛却仍然不能达到她的目的,不能打破男权社会的牢笼,她的激进、她的仇恨在那样一个社会中只会被认为是异类,是怪物,就连一同生存在桑菲尔德里的所有女性,也只认为她只是罗切斯特疯掉的太太而已,比如当罗切斯特带领一行人去看伯莎的时候,“看管人”格莱斯·普尔对罗切斯特的描述是“有点要咬人,可还不残暴”,简·爱对她的描述更是“穿着衣服的鬣狗”。所以,想要吸干罗切斯特心里的血的伯莎,只能采取更加极端的办法来复仇,她最终仍是用火据了结了桑菲尔德这“罪恶的金钱的堡垒、男性统治的中心、女人的监牢和地狱”。在大火中,伯莎疯狂地站在房顶上,在雉堞上挥着胳臂大叫大嚷,像是获得胜利的呼喊,又像是终于解脱的哀嚎,当她从楼上一跃而下时,一个被压迫的女人的挣扎与反抗,就这样画上了句号。这便是伯莎毁灭式的反抗,她以同归于尽的方式,诉尽了自己内心的仇恨。
值得一提的是,用来禁锢伯莎的“楼”,是一个意味着束缚、防卫和幽禁的意象,象征着女性的生存困境:封闭的环境、非人的处境、个性的封锁与压抑,这正是女性在传统男权社会下生存困境的缩影,是男权文化统治的阴影。
三、“笼中鸟”背后的关系与渊源
女性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斗争的妇女拿起武器进攻凡尔赛是法国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的标志。随着《女权宣言》的发表,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群体也逐渐开始追问女性的自我地位与自我价值。这一时期科学、工业的迅猛发展促成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形成了男女平等观念的基础。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更多的女性参与了社会活动。但对许多女性来说,这并非一个适合生活的好时代,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为了维系生活而不得不选择辛勤工作。很多女性的主要选择则是家庭教师,夏洛蒂·勃朗特就有做过家庭教师的经历,从《简·爱》中不难看出这份工作并不能让女性得到真正的自由,反而可以体现当时英国社会中的贵族阶级和正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性格所具有的冷酷、自私、虚伪。
在女性写作崛起之前,男性作家一直是西方文学的中心和方向。经历两次妇女解放运动,女权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女性意识的崛起,女性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女权运动的开展使得女性作家将压抑在心中的不满和愤怒诉诸于笔端,以文字的形式向男权中心论发起挑战,她们的作品对传统女性形象和女性地位提出了异议,以全新视角重新审视女性地位。[5]
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根据弗洛伊德学说提出了“影响的焦虑”理论,这种影响的焦虑超出血缘关系上的父子关系,联系到文学史上的前世作家与后世作家,前世作家是后世作家效仿的模范,后世作家成名的必经之路就是超越前世作家,这种焦虑就是一种“影响的焦虑”。《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作者桑德拉和古芭根据这个理论又提出了一种男作家与女作家之间的相应关系,从一开始写作就被视为男性的事业而非女性的事业,作为想要挤进男性的领域去进行创作的女性作家来说,她们不得不面对男性作家一直以来创作的传统,因为男性已经在这个领域获得一种权威,所以女性作家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不敢去打破传统;可女性作家的自我意识如果想要得到表达的话,她们又必须去对抗、打破。这样看来,简·爱与伯莎不应该是两个在爱情中对立的女性角色,而是作者女性意识的分裂。
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伯莎·梅森这一角色的设立是一个微妙的文学策略。看似对立的甜美的女主角与咆哮的疯女人构成了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矛盾,但这样的对立实则男性作家对于女性刻板印象的一种体现,因为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要么是天使,要么是恶魔,而判定的标准则是她们是否符合男性的需求,肤白娇小又安静少言的简·爱自然是符合男性标准的“天使”,而高大粗犷、疯狂躁动的伯莎·梅森就必定是男性眼中的“恶魔”。所以夏洛蒂·勃朗特一方面是在模仿男性作家的一种模式化写作;另一方面是在这个模式之下去寻找天使与恶魔之间的相通性。这样的小说创作是女性作家自我意识的体现,而女性作家在体现自我女性意识的时候又畏惧于把妥协和对抗都放置在女主角身上,所以与女主角对立的疯女人的存在就必不可少。
总之,简·爱和伯莎·梅森都应该是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自我女性意识的一种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中的疯女人并不仅仅是女主人公的对手,或阻挠与干预她的人,她通常更有可能是作者的重影或替身(double),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焦虑与愤怒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