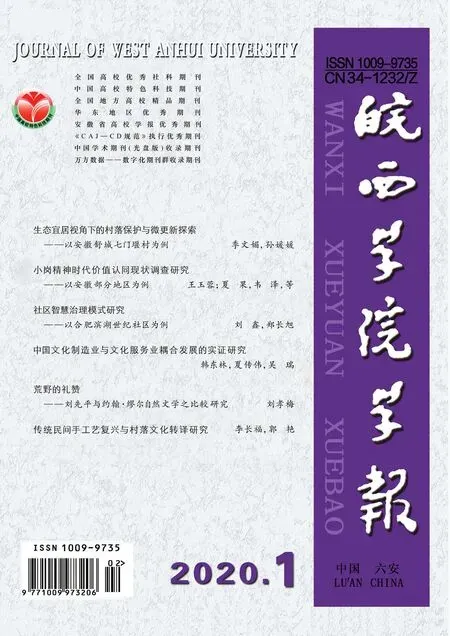卢曼社会系统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以刘勇军译《月亮与六便士》为个案研究
2020-01-02徐琳,龙翔
徐 琳,龙 翔
(桂林电子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翻译研究在20世纪经历了几次“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也就是研究角度的转变,无论是六十年代约翰·卡特福德(J.C.Catford)和尤金·奈达(Eugene A.Nida)进行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还是九十年代安德烈·勒菲勒尔(Andre Lefevere)和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倡导的文化转向(the culture turn)等,都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法。1972年,荷兰翻译理论家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在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的重要论文。该篇学术地位极高,堪称翻译学科的“奠基之作”[1](P92)。
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学界翻译的社会学理论逐渐被引入翻译研究,其中就有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论(Social Systems Theory)。卢曼在著作中,以社会学为信号,提出新的“范式转换”,帮助翻译研究开始进行社会学的转向(the sociological turn)。即使到目前为止,虽然学界对另一位社会学家布迪厄理论的翻译研究居多,但是随着卢曼系统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在翻译研究中对社会系统论的应用也如雨后春笋般增加。本文就以刘勇军翻译的《月亮与六便士》为例,对卢曼社会系统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探究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讨论其在翻译研究中的意义,以期为今后的社会翻译学研究提供启示。
一、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框架
德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卢曼接受了生命系统自我再生(autopoiesis)系统理论,将其借用到社会学,形成了社会系统理论。卢曼认为,系统包含各个子系统,系统是由事件构成的,而不是个体;而且摒弃“整体/部分”的传统区分,提出新的系统主导性区别“系统/环境”,超越了传统的研究范式。他的社会系统理论奠基之作《社会诸系统》于1984年在德国出版,之后翻译成英文于1995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2]。社会系统论全方位地探求各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在行使其功能上的成果,从而体现出一个社会系统的自我生产机制。
(一)“系统”的内涵
卢曼发展了带有后现代主义特点的认识论,完善了社会系统论:他认为由生命、意识和沟通(communication)①三种要素构成了三种“系统”——生命系统(肌体系统)、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他们既独立运作,又相互依存;既是自我指涉,又是自我生产的系统。他们具有封闭性特征,能自主地建构和运行自身的系统[3]。不过,在这三个系统中,卢曼关注的是社会系统和心理系统。卢曼以建构的手法,搭建了一个系统的框架,许多界限不明或模糊的现象有了新的划分。他认为,各个系统存在诸多子系统。社会是个动态的,流动的系统;它的子系统也是如此。社会系统功能的分化产生系统的复杂性,使各个子系统彼此依赖,彼此独立,在相互影响下实现功能。结构功能论学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一个系统先有结构的搭建才能有功能的出现;而卢曼则认为,先有功能后有结构[2,4]。由此看出,卢曼并不认同之前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产生的顺序与关系,于是卢曼对其师帕森斯的思想进行了部分否定与修订;因此,学界将卢曼在帕森斯基础上形成的新理论称为“功能结构主义”[5]。
(二)“自我再生”和“自我指涉”的系统
卢曼的系统理论重要的特点之一是自我再生(autopoiesis)。卢曼认为,社会系统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自我再生的系统。另一个特点与“自我再生”相关联,就是自我指涉:指个体凭借着自我再生操作(operation)②,可以将自己的内部因素同外部环境区分开来,从而凸显其主体性,以区别于其他社会系统[6](P37)。自我再生的系统通过自我指涉的方式内部封闭运作;也通过“异己指涉”(hetero-reference)的方式向周围环境开放并与之沟通。只有当外部要素或其他系统只提供一些信息或提示时,只有当系统确认并接受这些信息,并将其纳入自我再生的操作时,这些外部作用才会产生意义[6](P37)。自我指涉与异己指涉是自我再生系统维系内外部关系的方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自我再生在封闭循环中,也在环境影响下,持续循环进行下去。自我指涉体现了系统的排他性,异己指涉体现了系统的容他性,自我再生则体现了系统的延续性,从而体现了系统的丰富性。
二、社会系统论在刘勇军译作《月亮与六便士》的应用
《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作家毛姆成为世界级小说家的奠基之作。其作品以深刻的哲理性语言见长,在讥讽中潜藏对人性的怜悯与同情[7-8]。青年翻译家刘勇军翻译的版本,文字简洁平实,通俗易懂,于是本文选用他的版本作为研究。在译作分析案例中,译作位于研究的中心,译者则出现在翻译系统、源语言和目标语的交叉部分[9]。在翻译实践中,翻译自成一个自我运作、自我再生的系统;同样,也可以看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外部环境的影响通过系统的内部机制影响系统。在真实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处在交叉部分,通过选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从而在翻译系统中发挥作用。同时,该译作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体现了翻译系统的自律性(自我指涉)和他律性(异己指涉)的特点。
(一)翻译作为自我再生、自我指涉的社会功能系统
翻译系统具有自我组织,自我调整等特性,能够依靠自身与环境的互动以及自我运作建构它的体系,从而成为一个社会功能系统。卢曼认为,系统的开放是“封闭性开放”;系统的封闭是“运动性封闭”或“开放性封闭”。与社会系统一样,翻译的界定也是动态的,那么,刘勇军也把他的翻译看成一个自我指涉,自我再生的“开放性封闭”系统。换言之,把翻译过程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具有自创性的体系。这与安德烈·勒菲勒尔和苏珊·巴斯内特倡导的“文化转向”观点——翻译是原文的“再创作”,不谋而合。
Example 1
Source Text(ST): Rose Waterford was a cynic.She looked upon life as an opportunity for writing novels and the public as her raw material[7](P14).
Target Text(TT):罗丝·沃特福德平素有些玩世不恭,她会把生活当成小说的灵感,把芸芸众生当成她创作的素材[8](P18)。
译者将ST中“cynic”(adj.愤世嫉俗的),根据词义选择,选择翻译成了“玩世不恭”,更贴切罗丝的人物性格;把“looked upon life as an opportunity”中原文作者用了“look upon”表达了对生活“仰视”的态度,为了让译文既能体现上文的部分语言特色,又能更好地衔接下文,于是译者翻译成了“把生活当成小说的灵感”。译者把整个译作视作可以自我再生的系统,根据译文自身的特点以及人物特点,选择适合的词语,从而实现译文的“自我再生”。
(二)翻译作为社会的子系统
以卢曼的理论视角,翻译也可以被当成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且可以与其他的社会子系统互为环境。翻译的存在离不开周围的环境,尽管本身内部闭合运作,但却时刻保持与各子系统(环境)互动;同时,这样的互动也依赖于“观察”体制,“观察”促进两者的沟通。作为位于社会系统边界的子系统,翻译主要功能就是促进社会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的互动,从而增加社会系统的敏感性[2]。同时,翻译在系统中的边缘位置也决定了它的中介功能。当人际或代际沟通受阻或者个人内心发生冲突时,需要翻译的介入。该功能在根本上帮助翻译系统与其他子系统进行了区分[2]。
Example 2
ST:My engagements were few, and I was glad to accept.When I arrived, a little late, because in my fear of being too early I had walked three times round the cathedral,I found the party already complete[7](P15).
TT:我的应酬并不多,自然乐于接受这样的邀请。我到达时,还稍稍迟到了,因为我担心去得太早,就围着大教堂走了三遍。等我到达那里后,发现客人均已到齐[8](P18)。
译者把整个译作视作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利用翻译的中介功能,介绍源语言的文化。在西方宴会,客人过早到达,会使主人因准备未毕而难堪。尤其在原文中,作者与斯特里克兰太太刚刚认识不久,提早到达必然导致尴尬的情景。刘勇军不仅符合原文表达的意思,同时体现了翻译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与社会的子系统相互作用。
(三)翻译系统的自律性与归化
赫曼斯(2007)认为,翻译系统同时具有自律性(自我指涉)和他律性(异己指涉)[10]。根据翻译的自我再生特点,翻译系统的自律性尤为重要。在实际翻译实践中,译者将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拉近源语与目标语的距离。因为译作将成为目标语文化中的一部分,所以目标语将成为翻译研究中的内部研究对象。翻译的自律性体现了翻译系统的内部机制特点,这与翻译策略中的归化有相似之处。在本译作中译者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使文章更贴近目标语,更符合读者的文化背景与阅读习惯,从而更好地实现翻译的自我再生过程。
1.翻译系统的自律性
由于中英文在语法、词汇、文化和阅读习惯上的不同,译者在贴近原文意思的基础上,更加灵活地选择符合读者文化和阅读的目标语,从而体现了翻译系统的自律性。
Example 3
ST: Maurice Huret in his famous article gave an outline of Charles Strickland’s life which was well calculated towhetthe appetites ofthe inquiring[7](P3).
TT:莫里斯·于雷在他那篇著名的评论里简单地概括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生平,意在吊足好事者的胃口[8](P3)。
在TT中,译者将ST中“whet”(v.刺激,增强)翻译成了“吊足”;把“the inquiring”(n.爱打听的人,好奇的人)翻译成了“好事者”,这样的翻译,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也体现出了,在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生平感兴趣的人中,也不乏好事者的存在。这是翻译系统的自律性所使然。
2.归化策略
归化策略是指源语文化在目标语文本中尽量减少影响,甚至到不存在,即译文的语言和文化与目标语趋同。在某种程度上说,归化使译作更容易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在译文中,译者采用许多中文的四字结构,就体现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四字结构,或成语,或自由短语,是汉语独特的语言描写形式;其含义深刻,表现力强,体现了汉语的简明流畅以及音韵美等特点。作为归化策略体现的一种方式之一,译者在译作中也使用不少四字结构,从而为译文润色,也体现了译者的语言功底。
Example 4
ST: I do not speak of that greatness which is achieved by thefortunatepolitician or thesuccessfulsolidier...[7](P1)
TT:我所谓的伟大,与鸿运当头的政客或者功绩卓著的军人所成就的伟大并不一样[8](P1)。
Example 5
ST: She combined a masculineintelligencewith a feminineperversity, and the novels she wrote wereoriginalanddisconcerting[7](P14).
TT:她既有男性的聪明才智,又有女性的任性乖张,她写的小说匠心独具,令人心潮难以平复[8](P17)。
Example 4在TT中,译者将ST中“fortunate”(adj.幸运的)翻译成了“鸿运当头”;把“successful”(adj.成功的)翻译成了“功绩卓著”。Example 5在TT中,译者将ST中“intelligence”(n.智力,才智)翻译成了“聪明才智”;把“perversity”(n.任性)翻译成了“任性乖张”;把“original”(adj.首创的,原创的)翻译成了“匠心独具”;把“disconcerting”(adj.令人不安的)翻译成了“难以平复”。Example 4 和Example 5这样的四字格或成语翻译,符合汉字的表达习惯,属于翻译系统的归化策略,更好地贴近中国文化,易于读者理解;同时,也体现了语言的音韵美。
(四)翻译系统他律性与异化
翻译系统与外界环境进行沟通,产生了异化,从而促进翻译系统的发展。翻译系统他律性就是尽量保存原文的风格和特点,让读者适应作者,带给读者一种阅读原文的感觉,这与异化的翻译策略不谋而合。这种异化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服从源语,有利于将异质文化及相关概念引介到目标语中,实现强调异质文化价值的目的。
在姓名翻译上,译者体现了系统的他律性并运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我们要明确英文名和汉语名排序的差异:英文名是姓在后,名在前;中文名恰恰相反。在名字结构上,英文名分为三部分:名字,中间名和姓;中文名分为姓和名。刘勇军强调了异质文化的元素,通过音译的方式把它翻译出来。通过这种方式,他把源语文化的因素保留在目标语中,把异国元素带到目标文化中。下面是一个有关姓名翻译的例子:
Example 6
“Rose Waterford译为:罗丝·沃特福德,Charles Strickland译为:查尔斯·斯特里克兰,Richard Twining译为:理查德·特文宁,George Road译为:乔治·路德,William Morris 译为:威廉·莫里斯”[7-8]等。
这样的翻译,给我们增添了一种异国情调,使读者很容易对于文章传递的故事产生的背景、发展的情节产生信任感。这是一种翻译系统他律性与异化的体现。
尽管环境主要依靠翻译系统内部运行的规律来实现,也就是,他律要通过自律来实现。但是,在翻译实践中,翻译以一个系统的形式运作,于是译者通常同时使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为了追求翻译系统的内外平衡。
三、反思与总结
卢曼以建构主义的立场,从系统的视角观察与证明翻译系统的存在,扩展了翻译研究的研究领域。本文以卢曼社会系统论的理论框架,以刘勇军的译作《月亮与六便士》为例,讨论了其在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应用,探究系统论在翻译研究中的意义,为将来社会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参考与启示。
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翻译研究正在经历社会学转向,但是主要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王宏印指出,当前社会翻译学建设的薄弱环节:既不在于个案的微观层次,也不在于理论的宏观层次,“而恰恰在于中间层次,即利用或寻找扎实可靠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将其纳入典型的翻译活动,进行有效结合式的研究(不是综合研究,也不是资料和框架的分开研究”[11](P23)。此外,社会系统论中没有人的存在,也就是译者的存在。这一点和翻译的范式研究如出一辙,客观地避免了翻译系统中掺杂个人感情,但是也回避了译者的工作轨迹(trajectories)与工作倾向(tendencies)的主观差异性和多样性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这是理论中不可忽视的缺憾。
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框架已经具备,但是要将其纳入具体的翻译活动中,最好将社会学理论和翻译实践相结合。如何用,如何结合,是当前的问题。而且,如何将社会学的方法应用到翻译实践中,是否将实证研究引入到社会翻译学中,这些将是我们在未来讨论的内容。
注释:
① “Communication”在学界有多种译法,译为“交往”“交际”和“沟通”,本文中采用“沟通”这种译法。
② “Operation”在学界有多种译法,译为 “操作”或“运作”。本文中采用“操作”这种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