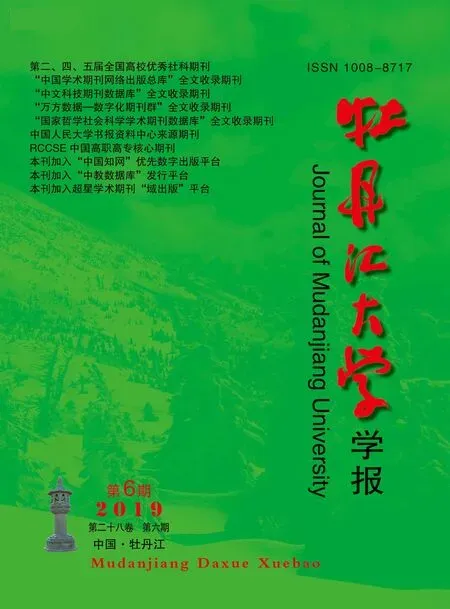场域、差异:晚清以来英美小说翻译规范的变迁
2019-12-29袁辉徐剑
袁 辉 徐 剑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晚清以来外国小说译介最直观的特点就是数量大、重译多。从译本形态上看,形成了晚清、民国、建国初期和新时期四个翻译历史场域,各时期译本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诉求与翻译规范变迁。
一、用夏变夷
小说译介开近代外国文学翻译的先河,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长文,倡导大规模地翻译外国小说以满足文学与社会的需要。
中国传统小说从语言上可分为文言和白话两种,从体裁上可分为笔记体、传奇体和话本体,上述两种语体三种文体是传统小说创作的基本规范。五四前的译者,多采取中国小说的传统规范翻译外国小说,比如鲁迅早期的翻译,就与后来很不相同。
鲁迅早年翻译《月界旅行》等小说均采用章回小说的体裁,形式上增添了中国章回小说独特的回目,在章回结尾,还常常补上解文诗句和收场套话,如第二回:
社长还没说完,那众人欢喜情形,早已不可名状……正是:莫问广寒在何许,据坛雄辩已惊神!欲知以后情形,且待下回分解。[1]
当时的小说翻译因为沿用中国传统小说的体裁,往往给译文增加了原文没有但由于体裁变化所带来的内容。另一方面,将原著原样装入中国旧小说的体裁里也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删减改易“用夏变夷”在所难免。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凡二十八章,例若杂记。今截长补短,得十四回。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体杂言庞之讥,知难幸免。”[2]我佛山人译《电术奇谈》,在附记中亦有类似表达。[3]这个时期用夏变夷最为成功的小说翻译家要数林纾。
“规范”本质上是社群的主流行为,具有稳定性,但也会受到挑战,当挑战主流翻译规范的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规范变化,曾经的主流翻译规范会被边缘化甚至消失,新的规范则开始成为主流。总体上看,晚清的翻译规范是在五四前后发生根本变化的,但不同文类的翻译规范则变化有早有晚,在晚清翻译规范发生根本变化前,已有一些对既成规范的“破坏者”。与林纾同时代的著名译者周桂笙就是小说革新的推动者,他通过外国小说的翻译为中国小说革新提供了借鉴的榜样。1903年他在《毒蛇圈》的译者序言中谈到中外小说体裁规范上的不同,解释他“照译”小说原作的原因:“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陈陈相因,几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此篇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著,其起笔处即就父母(女)问答之词,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元,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显然,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爰照译之,以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讥之。”[4]周桂笙指出中西小说写法的不同,对于国人来说,初读西方小说的安排,或许会觉得“突兀”混乱,细读则会发现其中的妙处与高明。他指出这是“欧西小说家之常态”,即西方小说的创作规范,周桂笙为了文学译介的目的,翻译时不再以中国传统小说的体裁为模板加以修改变化。
周桂笙的翻译实践,在晚清民初都还处于挑战传统规范的阶段,要扭转主流翻译规范绝非易事。一方面,成功的翻译容易被不断地复制,另一方面成功的翻译又会以读者期待的方式进一步巩固主流翻译行为。钱钟书在评价林纾的翻译时就曾说周桂笙的翻译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与林译相比,宁可读原文,也不愿读后出同一作品的‘忠实’译本,而且林纾译本里的不忠实或“讹”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外语水平低。[5]我们认为林译在当时符合大多数读者对小说的期待规范,是其译作深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晚清的翻译规范,主要还是体现了公众对译者翻译行为的期待,这种期待一方面延续了大众既往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也通过肯定那些符合大众阅读习惯的译本,进一步强化了翻译规范自身的约束力量。晚清时期各种文类的翻译基本上都依循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的样式,跳出小说翻译的范围看,“用夏变夷”的译法具有普遍性。
二、西学为用
民国时的中国社会恰好处在规范激烈冲突的时期,源自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的各种规范竞争社会体系的主导地位。文学和翻译的子系统也是如此。从规范论的视角看,晚清至民国同样存在三类不同规范,但它们在系统中的位置关系发生了变化。晚清国门未开之时,文学典范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古典文学。作为绝对强势的规范,其核心地位直至西方炮舰将国门打开之后才逐渐失去。五四前后是新旧规范的位置发生彻底变化的时期,中国文学的经典规范发生了新旧更迭,“西学为用”是这一时期的主基调,翻译导致中国文学产生三个方面彻变,一是语言形态,二是文体体裁,三是文学文类。中国文学规范系统的演变与重构,离不开翻译活动的参与。新规范的建构是个渐进的过程,翻译在其中不仅起到了触媒作用,还发挥了样板示范作用。作为中国文学规范的组成要素,外国文学翻译规范经历了由依循中国文学规范到中国文学规范与外国文学规范交织杂合,再到创制出现代翻译文学规范的过程。
规范的更迭演变是新旧规范相互竞争的过程,这种竞争表现为这一时期的小说译本既受新规范的影响,又有旧规范的痕迹,这是事物演变过程中的典型特征。以转型时期《维克斐牧师传》的译本为例,我们注意到,三十年代伍光建所译的《维克斐牧师传》(1931年出版),在语言上逐步摆脱文言的束缚,且非常“应时”地译出了一些欧化的句子,虽然还残存着一些文言,但总体上已经非常接近后一时期的语言特征。然而这个转变过程对伍光建先生而言似乎并非易事,我们以伍光建译本的章节标题为例加以说明。[6]
第一回 叙维克斐牧师家庭 这一家人面貌思想大略相同(老牧师闲享家庭乐)
第二回 家庭不幸 君子不为贫贱所移 (好辩论两亲家失和)
第三回 移居 幸福原是自召 (白且尔客店遇牧师)
……
原著的章节命名比较接近汉语小说形式,伍光建先生认为离理想的汉语小说标题仍有距离,于是在原标题后又自拟了一个标题。自拟的标题因循旧俗,沿袭了章回体小说的传统。这种译法是规范更迭时期典型的翻译杂合现象。旧规范是逐步退出的,新规范的确立也是个渐进过程,由弱小到分庭抗礼直至占据主导地位。《维克斐牧师传》于1958年曾经重新修订再版,新修的译本在译文标题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使用“回”目,而代之以“章”,删去了伍光建先生依据章回体小说传统自拟的标题,修改了部分标题的译文。
翻译行为受到多种力量的牵引,由于伍光建的译本经历了漫长的翻译过程,从小说体裁的选择上看,译者经历了纠结的过程,充分体现了译者从中国传统小说体裁切换到西方小说规范的艰难。
三、正本清源
建国初期翻译领域还存在很多乱象,政府加强了翻译工作的组织领导,强调文学翻译为革命服务、为创作服务,端正译风,提升翻译质量。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用严肃的态度对待翻译工作”的文章,1951年发表了毛泽东修订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奋斗”,1954年茅盾、郭沫若等又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发表系列讲话,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翻译规范的基础。其中既包含职业道德规范,也包含操作规范,并指明了为什么译、译什么、怎么译、译者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译,对这个时期的翻译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文学翻译规范开始再造,翻译界对翻译态度、译者责任感、译者修养和翻译技术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讨论。这些讨论旨在构建翻译的“责任规范”,为新中国的翻译规范明确了内涵,与前一时期自发调节翻译行为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在翻译“质量规范”的重建上,一方面对文学翻译标准中的政治化进行纠偏,另一方面强化了翻译语言的规范性。茅盾作了“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成为当时文学翻译语言规范的指导思想,他提出文学翻译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每种语文都有自己的语法和语汇使用习惯,不能把原作逐字逐句,按照原来的结构顺序机械地翻译过来,这种译文不仅在一般翻译中不该存在,在文学翻译中更不能容许。茅盾总体上表达了归化翻译的主基调,反对机械硬译的办法,赞同有限度地吸收外语的句法特点和有限度的汉语欧化,并认为适当照顾原文形式与保持译文是纯粹的中国语言,完全可能而且有必要。此外,译本选择上鲜明的阶级性也是建国初期翻译规范的特点。规范是价值观的体现,也反映意识形态的变化。新中国成立,文学翻译在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同时,也发挥了政治教化的功能。在译本的选择上,代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文学作品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进步文学作品,都是翻译出版的选择对象。翻译规范的阶级性变得更加鲜明。
在翻译规范得以整肃和重塑的情况下,外国小说的译介质量有了保障,组织性加强,乱译也得到纠正,修正了语言过度欧化的现象,汉语纯洁性也得到了保障。我们以《傲慢与偏见》两个时期的译本来说明这种变化,篇幅所限,仅取小说的一段译文为例。
王科一1955年译本:尽管班纳特太太有了五个女儿帮腔,向她丈夫问起彬格莱先生这样那样,可是丈夫的回答总不能叫她满意。母女们想尽办法对付他——赤裸裸的问句,巧妙的设想,离题很远的猜测,什么办法都用到了;可是他并没有上她们的圈套。最后她们迫不得已,只得听取邻居卢卡斯太太的间接消息。她的报道全是好话。据说威廉爵士很喜欢他。他非常年轻,长得特别漂亮,为人又极其谦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打算请一大群客人来参加下次的舞会。这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事;喜欢跳舞是谈情说爱的一个步骤;大家都热烈地希望去获得彬格莱先生的那颗心。[7]
董仲篪1935年译本:无论如何,背纳特太太帮助她五个女儿讨论此事使她丈夫满意背格累先生说的。他们以各种方法进攻他--用明显问题,冷静态度;但他闪避一切技巧,他们最后不得不接受二把手邻人路斯太太的消息。她的报告很有益。威廉先生喜欢他。他是很年轻,奇美极相配人,并且冠美一切,他意想第二次会聚同住很大团体。没什么再很可喜!爱好跳舞是发生恋爱一定的阶段;背格累先生的心蕴蓄住活跃的希望。[8]
王科一是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翻译家之一,他的译本在语言上适度回归了汉语语言规范,尊重原文的表达习惯,但不为原文的句法结构约束,在忠实原文和通达顺畅上取得了较好的平衡。译文与原文的对应性较好,既根据汉语语法的需要及时调整语言结构,同时也不对原文做随意的剪裁编排。董仲篪的译文从翻译方法看是以原文为导向的,语言结构比王科一的译文更贴近原文,总体上句子结构的欧化胜过词汇层面的欧化。董仲篪的译本在词汇风格上值得一提,有那个时代很多翻译的共同特点,保留了不少文言词汇的特征,形成一种比较独特的杂合的翻译语言风格,即用欧式的句子结构组织了一部分文言或浅近文言词汇,这算得上是当时欧化翻译的一个特点,在当时的翻译大家伍光建、梁实秋等人的翻译中都很常见,是影响较大的翻译规范之一。今天的读者或许更能够接受王科一先生的译本,原因是今天的翻译规范更接近王科一的译文。另外在人名、地名的翻译上,王科一先生的翻译更加炼字,音形义的结合更“雅”,这与五十年代对翻译标准的讨论不无关系。
四、百家争鸣
新时期的翻译实践,大致以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为起点。从翻译行为上看,这一时期的翻译规范有一些显著的变化。
首先,在初始规范上,涉及译本选择的翻译政策更加宽松,译者、出版社对译本的选择相对自由,文学、教育以及市场的力量是更直接的译本选择因素。译本的题材和选择范围都较以往扩大,更好地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英美文学翻译的地位大幅提高,成为文学翻译的绝对主流,这种情况与民国和建国初期不同。前两个时期,苏联文学的翻译始终占据这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新时期的翻译格局发生了变化,极左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减弱,中国翻译史迎来了又一次翻译高潮,展现了更为丰富的多样性。
其次,市场因素导致了愈演愈烈的重译行为。文学重译的合理性存在于场域变迁对重译本的需要,但是,改革开放后的翻译实践场域出现了大量的重译本,这些重译行为只有少部分是由内源性因素引发的,大部分翻译行为都受控于市场因素,甚至是纯粹的利益驱动。从加入版权公约国之前的普遍重译,到成为版权公约国成员后集中在经典作品上的重译,都很好地说明了市场因素对翻译行为翻译规范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翻译的历史实践场域不同,译本才可能产生较大的变化与差异,才能凸显译者的翻译风格。从内部逻辑上看,同一时期、同一历史实践场域,并不需要大量的翻译作品以几乎没有差异的形象同时登场。在国内的学术界,有很多学者反对重译,他们提出文学翻译完全可以有定本的观点,这种反对不无道理。翻译受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控制,资本趋利的特点极可能导致非理性翻译行为的发生。从翻译的组织性上看,这个时期翻译活动的自由度提升而宏观的组织计划性降低。
再次,编译改译的形式与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编译、节译、改译甚至改写的翻译行为流行于晚清时期。纵览现当代翻译史,总的趋势是编译、改译等翻译行为愈来愈少。在编译改译的案例中,晚清的林纾算得上是最成功的一个。林纾的编译、改译行为并不都是他和助手的语言能力不足而被动造成的,有时他是刻意而为。林纾的时代正值国门初开,国人对国外的了解,被动大于主动,林纾的编译改译,幅度大,文化与语言表达替换多,满足了归化的需要,更利于国人渐进地了解西方文化,是外国文学中国化的一条捷径。钱钟书认为这种方法仿佛做媒似的,能够“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姻缘’”[5]。回到当代,改译、编译并非不存在,只是呈现了新的形式:一是改译大多表现为由意识形态原因引发的删节;二是编译、改译、改写的目标读者群主要是青少年,作为外国文学素养的初级读物出现,这些作品的读者主要不是成年人,与林纾的时代已大为不同。随着全社会外语水平的提高,编译、改译在文学译介中的接受度也越来越低。
五、结语
总览过去一百余年外国小说翻译的译介出版,场域特征尤为突出,每个译本多多少少的都带有它那个时代的印记。在翻译规范更迭中,外国小说以差异化的形式实现了在中国历史实践场域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