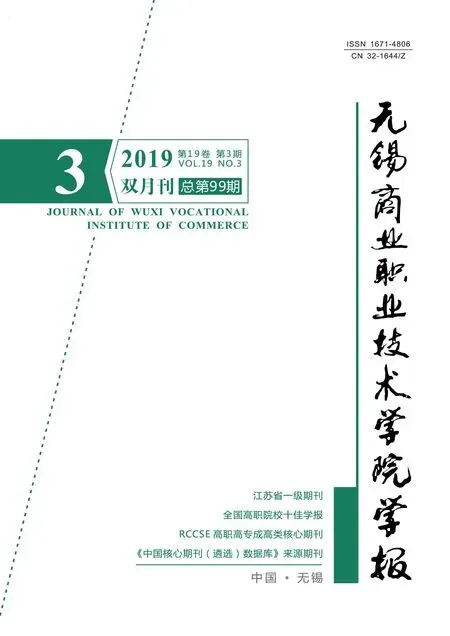接受美学视域下期待视野理论的阐释
2019-12-27温竹梅
温竹梅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0)
姚斯(Hans Robert Jauss),德国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接受美学的主要创立者之一。他构建的接受美学,试图找到一种新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这种新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更关注作品与读者接受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姚斯是从“期待视野”开始对此进行分析的。由此,“期待视野”便成为姚斯基本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他最重要的理论文章的“方法论顶梁柱”[1]340。
一、对期待视野概念的爬梳
“期待视野”一词最初并非姚斯首创,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都使用过“视野”或“视域”的概念。胡塞尔在分析主体体验时提到了“视野”,并从时间、空间两个角度来进行论述:从时间的向前、向后延伸中胡塞尔看出,在对新体验的期待与旧经验的重温中逐渐展开了主体的体验过程;从空间的“内视野”与“外视野”可以看出主体视野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海德格尔在胡塞尔的基础上将“视野”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前理解”。海德格尔认为“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做的无前提的把握”[2]176,而是“前理解”在起一定的作用。海德格尔的“前理解”超越其导师胡塞尔之处在于:“在胡塞尔的理论中视野只在相对于主体的意向性时才有意义,而海德格尔则打破了意向性的束缚,将其上升到指引主体认识、理解的高度。”[3]伽达默尔又在海德格尔的“前理解”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提出了“视域融合”。他认为,文本理解活动的本质就是不同视域的相遇过程。姚斯的“期待视野”正是在“前理解”与“视域融合”的启发下进一步提出的,不仅如此,姚斯还将其从哲学领域引入美学领域。
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列出了七个论题。其中,论题二、三、四便试图说明接受美学的中心概念——期待视野[4]。 论题二讲述的是“期待系统”,姚斯对此这样论述道:“从类型的先在理解、从已经熟识作品的形式与主题、从诗歌语言和实践语言的对立中产生了期待系统。”[1]28可以看出,姚斯所言的期待系统指的是读者所具有的对于文学体裁、形式与主题、语言的理解之和。论题三讲述的是“视野的变化”。姚斯认为:“假如人们把既定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新作品出现之间的不一致描绘成审美距离,那么新作品的接受就可以通过对熟悉经验的否定或通过把新经验提高到意识层次造成‘视野的变化’。”[1]31在姚斯看来,视野的变化是由审美距离造成的。论题四讲述的是“视野的重构”。姚斯认为,历史上对于一部作品的评判,“是一部作品之中所包含的意义潜势不断地展示,是作品在向理解性判断展示自身的历史接受中的现实化。作品在与传统相遇时,以具有一定制约性的方式获得‘视野交融’的性能”[1]34。所谓视野的重构,其实就是一种与传统认知相遇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姚斯虽多次提到“期待视野”,其著作中却并未对期待视野概念做出明确定义,这就给其他学者对这一术语的界定留下了广阔的阐释空间。
许多学者对期待视野概念进行过界定[3]。霍拉勃认为,期待视野是指“一个超主体系统或期待结构,‘一个所指系统’或一个假设的个人可能赋予任一本文的思维定向”[1]341。王先霈先生认为,期待是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5]193。杨守森先生认为:“在文学阅读之先及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在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读者这种据以阅读本文的既成心理图式,叫作‘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简称‘期待视野’。”[6]289由此观之,三位学者皆倾向于将“期待视野”定义为一种“先在结构”,即主体的种种先在的思维定向、先在体验、先在心理图式构成的一种“先在阅读期待”。从“先在结构”的意义上来理解“期待视野”,虽然把握住了“期待视野”重要的一面,即突出了读者的首要性和独立性,然而却忽视了读者与本文间的交流活动。相比较而言,陈长利的观点更为全面,他认为:“期待视野更加完整的含义应该是在‘先在结构’ 与‘体验建构’ 中互动生成。”[7]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说:“一部文学作品, 即便它以崭新面目出现, 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示自身,它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 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 随之开始唤起中间与终结的期待,于是这种期待便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这类文本的流派和风格的特殊规则被完整地保持下去, 或被改变、重新定向’ 或讽刺性地获得实现。”[1]29不难发现,“体验建构”才是姚斯构建接受美学的最本质的初衷:一种研究作品与读者接受之间作用的文学史。据此,对“期待视野”做出如下界定:期待视野是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读者的“先在结构”与文本意义的“体验建构”间互动生成的一种心理机制。
二、期待视野理论的形成过程
期待视野是一种心理机制,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创立的发生认识论中的认识结构为阐释这一心理机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参照。认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涉及“图式”“同化”“顺应”“平衡”这四个概念。本文即以皮亚杰的认识结构作为理论参照来分析期待视野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
图式,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础,与图式作用相似的是读者在阅读作品前存在的先在阅读期待。它是进行文学阅读的基础,在主体阅读前与阅读中起到一种指引或制约的作用,在它的伴随下,主体才具备能够对文学的形式、主体、类型、语言、风格等进行赏析评判的能力。如果读者不具备一定的先在阅读期待,文学作品的阅读就无法进行,期待视野也无法生成和发展。
皮亚杰认为,在认识过程中,同化是个体把客体纳入主体的图式中,所引起的只是图式量的变化;而顺应则是主体的图式无法同化客体,而所引起的是图式质的变化,这促进原有的图式进行调整,从而创立新的图式。与同化、顺应作用类似的是期待视野中读者的“定向期待”“创新期待”。
论及定向期待与创新期待,就绕不开审美距离。姚斯认为:“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熟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1]31在姚斯看来,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是由审美距离决定的。仔细思考后不难发现,审美距离不外乎出现如下几种情况:第一,审美距离在读者的先在阅读期待范围内,且远小于读者的先在阅读期待,这会造成一种阅读失望。第二,审美距离在读者的先在阅读期待范围之外,且远大于读者的先在阅读期待,这就导致作者创作出的作品可能是优秀作品也可能是非优秀作品。优秀作品因其远超同时代读者的期待而成为一种超时代作品,这会出现两种后果:一是被其之后的时代发掘,成为不朽之作;二是被淹没在浩瀚的文学作品中。而非优秀作品因其过于晦涩,使读者产生极强的抵触感。上述两种情况皆无法产生定向期待或创新期待。第一种情况,读者不愿意将作品纳入自己的审美经验中,所以此类阅读不属于定向期待,当然更不属于创新期待。姚斯本人也说过:“一部文学作品在其出现的历史时刻,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这种方法明显地提供了一个决定其审美价值的尺度。”[1]31可见,第二种情况下的作品也不在姚斯的审美距离论述范围内。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产生于第三种情况——审美距离与读者的先在阅读期待相差一定的距离。在读者的先在阅读期待内,产生定向期待;超出读者先在阅读期待一定距离,产生创新期待。
定向期待在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时体现出的是一种具有稳定性的、甚至有些惰性的无意识阅读习惯,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期待视野处于一种质的稳定中,因此不会造成读者阅读过程中产生不适感。定向期待带来的变化是一种顺势延伸,这种延伸可能唤起过去与之相关的一切审美经验,并在此过程中增加或深化了读者对于此类作品的理解,使其期待视野在量上有了新的调整。
创新期待则需要不断打破原有的惯性思维,重新调整新的视野,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与原有视野不同甚至相反的内容。阅读此类文学作品时,原有的定向期待会受挫,产生暂时的不适感,但这种不适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随着读者个人的经验世界的变迁,如生活体验、文化水平、时代精神等,读者的期待视野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缩短了与作品的‘审美距离’或对作品有独特的发现,期待视野也因之得到拓展和丰富”[8]。
皮亚杰认识结构中的“平衡”指的是同化与顺应之间的平衡,与之作用相似的是期待视野中的定向期待与创新期待间的平衡。在认识过程中,人习惯于“一方面以先在的心理图式去同化客体,同时又不断地变更、调节原有图式去顺应客体,只有同化没有顺应,或只有顺应没有同化,人的认识也就难以发生和发展”[9]。审美阅读中的期待视野也是如此。在审美阅读中,读者的心理常处于矛盾变化中:一方面,原有的阅读习惯使他以一种定势思维对文学作品进行审美选择和同化;另一方面,追求新颖的阅读需求使他寻求具有创新期待的作品。
通过上述分析得知,读者期待视野的形成其实就是读者审美心理的建构过程,由先在阅读期待作为基础,通过定向期待与创新期待两者间的对话交流,最终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的过程。这种动态平衡不断促使之前的旧平衡向新的平衡发展,而新的平衡又不断地向更新的平衡发展,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螺旋上升的动态发展过程。
三、对姚斯期待视野理论的反思
任何一个理论的提出均受其时代背景及作者个人思想的局限性影响,但这并不能否认这一理论在它所处的年代的积极意义,更不能否认它对后世的影响。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同样如此。因此,本文对此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反思,试图发掘出“期待视野”中有价值的方面,使其发挥应有的理论生命力。
姚斯期待视野理论存在的局限性,或者说其理论的消极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姚斯虽然看到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狭窄的文学期待视野,还应包括广阔的“生活期待视野”,可是在具体分析时,却忽视了生活期待视野,而将期待视野完全归在文学期待视野的狭小圈子之中,这便在无形之中割裂了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使其理论脱离现实生活的土壤,成为“无根之树”。如此一来,不但使其概念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还使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漩涡之中。第二,以作品、作者这两个方面来研究文学史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作者和作品都是相对稳定的因素,而读者却是极其不稳定的因素,从读者的接受角度来建立文学史便具有很大的难度。单从期待视野这一概念来讲,不同的读者所处的社会背景、成长的经历等都极其复杂,且相对不稳定,难以找到共同的本质。因此,从读者接受角度来重新建立文学史将是一项非常艰难甚至可以说是几乎难以完成的工作。第三,期待视野虽然是姚斯接受美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然而姚斯本人却并未对此做过明晰界定,这就造成了后来的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而难有统一定义。此外,审美距离作为解释期待视野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姚斯在论述的过程中也并未对其中的“距离”进行明确界定。究竟审美距离大产生的期待视野的效果好,还是相反。抑或这个距离应该划定在什么区域内才能产生出使读者愉悦或不适的期待视野,这些姚斯皆未详细说明。这些概念上的模糊性使得其他学者在解读姚斯这一理论过程中遭遇了一定的困难。
不可否认,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也存在着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积极方面。姚斯期待视野论述的可取之处,或者说是其理论的积极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姚斯以“期待视野”作为方法论构建起来的接受美学呈现出一种相对开放的动态发展特征。相比历史实证主义范式、古典人文主义范式、审美形式主义范式而言,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不仅关注文本,还关注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交流过程。此外,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关注文本与读者的关系,还关注读者的期待视野对于创作者的反作用。随着读者期待视野的拓展,新的期待视野又反过来对作者的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呈现出的这种开放、动态发展的特征影响了众多学者。在其之后的众多文学理论家皆从中汲取营养,如美国学者罗伯特·C.霍拉勃(Robert C.Holub)所言:“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传统批评家,从古典学者、中世纪学者到现代专家,每一种方法论,每一个文学领域,无不响应了接受理论提出的挑战。”[1]282第二,当代西方文论在研究的重点方面有两次历史性转移:第一次转移是将研究的焦点从研究作家的生平背景、思想发展等外部研究转向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的内部研究;第二次是将研究的关注点从作品文本本身的内部研究转移到作品外部读者的接受研究。姚斯的接受美学无疑在第二次转向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如今,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草根”作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容小觑的弊端。比如,很多作家为了赢得可观的收入而大量产出文学作品。而在这个以物质作为标尺来衡量一切的商品经济时代,它又逐渐在作家圈形成一种整体趋势。如此一来,越来越多的模式化、同质化的作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如果从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来看,创作的作品低于读者的先在阅读期待,这便会造成一种阅读失望,读者就不会继续欣赏此类作品了。因此,无论在什么时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将会提高读者的阅读期待,读者的新的阅读期待又会反过来对创作者提出新的要求。现在重提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对于文学批量化生产、读者的期待视野变得模式化的当下,具有极其重要的警示作用及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