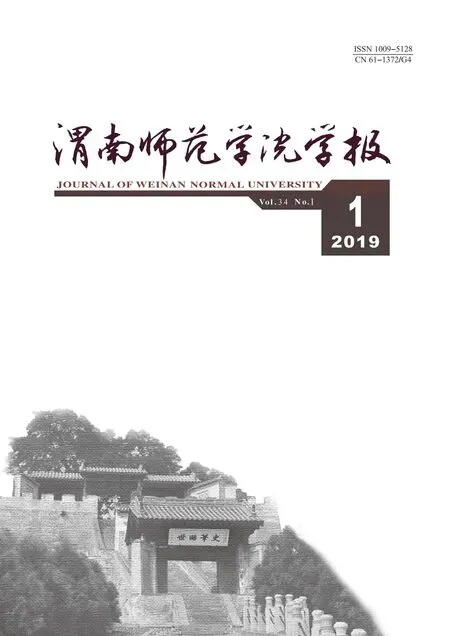21世纪以来《史记》“世家”研究述评
——兼论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2019-12-27周朋升周慧敏
周朋升,周慧敏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来,《史记》研究领域逐渐拓宽,研究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目前虽未见对“世家”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与综述,但从2000年至今,《史记》的研究成果显著,已出版著作30余部,其中大部分都对“世家”进行了详略不同的阐述。对“世家”进行研究的各类论文有120多篇。现对“世家”在史学、文学与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进一步提出研究展望。
一、《史记》“世家”的史学研究
学界对《史记》的史学研究可谓各抒己见,其中有关“世家”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世家”体例及“五体”关系的探讨;二是对“世家”定义的解读;三是对“破例”的分析。
(一)对“世家”体例及“五体”关系的探讨
《史记》五体结构是司马迁的伟大创造,随后“被封建王朝定为国史正体”[1]127,而学者多偏重于《史记》编纂方法的研究,如陈其泰从“应另换一副眼光读之”的角度分析“世家”历史编纂成就,认为司马迁创立“世家”这一体例的目的,一是解决了历史编纂所面临的难题,二是表彰在历史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各种人物。[2]张桂萍在《〈史记〉世家的编纂方法及其历史观念之民族特性》一文中指出,“世家”这一体例在《史记》中有其独特性,既有对先秦史著的继承,又有司马迁的独创,二者较好的结合显现出中国史学的一些民族特点。认为“世家”中有16个世家在写法上有共同点:强调国君的个人道德品行对国家盛衰的影响,在一国历史中反复穿插反映历史发展大势的代表性事件以及多记梦卜之言等,这是“世家”在树立列国形象时采用的主要编纂方法,体现了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历史观念,即道德批判与历史批评的结合,系天下存亡与弘扬人文精神的结合,天命与人事的结合。[3]不同于上述研究视角,张大可《史记研究》对“五体”题名进行明确解析,指出五体“各具笔法,自成系统,而又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不仅是一种史料的编纂方法,而且更是一种历史的表述法,反映了司马迁大一统的历史观”[4]193,但张先生对封为诸侯、又历传数代的赵王张耳、长沙王吴芮不立“世家”却未做解释。可永雪先生在《史记文学成就论衡》一书中把历代学者、史家对“五体”的评论进行梳理,做了简要说明。池万兴《史记与民族精神》一书指出“五体结构形象地反映了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5]271。此外,刘建民《〈史记〉五体的关联》一文论述《史记》的五种体例之间的关系,指出“本纪”只叙大要,提供统一的空间与纵贯的时间;“世家”“列传”“书”以“本纪”为纲要,拓展其记载范围,细化其记载内容。[6]
此外,肖振宇《〈史记〉类传及其撰写特点》一文,将《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进行分析判断,确定“类传”的概念,并以《外戚世家》和十一篇“列传”为例,指出其撰写特点。作者认为以具体人名命名的“合传”不属于“类传”。[7]针对“合传”是否属于“类传”的问题,笔者认为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史记》中《管蔡世家》《荆燕世家》《绛侯周勃世家》都是二人合传。而《外戚世家》一般都被认为是“类传”。其中的诸位女性,她们的身份都是“外戚”,事实上也是多人的合传;至于“列传”中的诸多合传,也都是侧重其某一方面的共通之处而合的。无论“世家”还是“列传”,都是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所以,争论到底是“合传”还是“类传”,一定要将之泾渭分明,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二)对“世家”定义的学术争鸣
尽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8]3319指出三十世家是辅佐君王的肱股之臣,就像众星环绕北辰一样。但赵生群在《〈史记〉文献学丛稿》中指出:“这段话概括了世家的部分内容,但不是全部。为国藩辅并不是世家的唯一要求,进入世家的也并不都是肱股之臣 。”[9]219即“世家不专指王侯传国”以及“王侯传国未必世家”[9]214-215,认为“世家专指王侯之家,是后人的理解”,“《史记》中‘世家’的内涵,是指某种事业后继有人。‘家’并非专指王侯之家,‘世’也不仅限于子孙相继”[9]215,并以《孔子世家》《陈涉世家》为例来阐释这一观点。赵先生除对“世家”进行阐释外,还对赵王张耳、长沙王吴芮不入“世家”的原因做了解答,论说简明而清晰。张大可《史记研究》一书认为“世家”之义有三:一是记诸侯列国史;二是载传代家世;三是“世家”与“本纪”同体,均编年纪事,因有别于天子等第而别名“世家”[4]196。杨光熙《司马迁的思想与〈史记〉编纂》一书认为,以“形势论”和“藩辅论”作为衡量“世家”的标准并不全面和充分,进而从“世家”的词源入手,指出“世家”即“世代相传袭之家”[10]187。郑慧生《“世家”解》一文认为“家”为宗庙,“世家”就是世世永祭之庙。[11]而叶永新在《“世家”为长祭不迁之宗庙说质疑》一文中则对此观点提出质疑,指出其缺乏字义上的根据,与《史记》“世家”情况多不相符,因而不能成立,认为“世家”标准具有多面性,但叶先生却未进一步撰文明确阐释。[12]蒋晓彤的硕士论文《〈史记〉三十世家研究》对“世家”释义有二:一是为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直接或间接地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股肢辅弼者”。二是因有别于天子而别名为“世家”。该文接下来分别对“三十世家”中破体为例的现象、“三十世家”中的疑案、“三十世家”的取材进行了考辨和研究。尽管众说纷纭,但毋庸置疑都肯定了“世家”传主在汉朝建立过程中的功绩。[13]
(三)对“破例”的探讨
杨光熙《司马迁的思想与〈史记〉编纂》一书对“世家”进行解释后,认为孔子、陈涉看似不合“世家”标准,但事实上“孔子虽无尺土之封,司马迁却显然受了汉代称孔子为‘素王’的影响,认为孔子以六艺传家”[10]187,而陈涉则是因为有首倡灭秦之功,刘邦、项羽实是陈涉事业的后继者,从这一点来看,陈涉当入“世家”。赵生群《〈史记〉编纂学导论》一书以若干世家为例进行题解,其中对颇有争议的《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戚世家》进行分析,指出司马迁有自己的体例标准。牟维珍、张黎黎在《〈史记〉三十世家“破体为例”发微》一文中指出,管蔡、孔子、陈涉、外戚是否该入“世家”,学界历来聚讼纷纷。文中通过对太史公的著书宗旨、编纂思想及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最后指出他们是完全有资格破体为例立“世家”的。这种破体为例既是为了褒显他们的历史功绩,也是司马迁创新精神的反映。[14]徐超《〈史记·陈涉世家〉与〈汉书·陈胜传〉对读札记》一文,分析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是如何看待“世家”之体以及陈胜入“世家”之事。[15]安丽红的硕士论文以刘知幾和章学诚关于《史记》五种体例歧异态度为研究对象,其中第二章叙述刘知幾、章学诚关于“世家”体例的歧异。刘知幾认为《史记》“世家”中多有破例之处,章学诚则认为“世家”体例合乎司马迁著史旨意,并不存在破例问题。对此,作者一一进行分析,认为刘知幾对司马迁《史记》“世家”破例的批评,是他囿于史体之名,不知变通的表现,也是他没有深刻理解司马迁著史宗旨的表现,更是他史识不如司马迁的表现,《史记》各种“破例”的出现正说明司马迁唯实不唯名,不拘泥于体例而懂得变通。[16]
总体来看,各位研究者对司马迁创造的容纳丰富历史内容的五体形式,尤其是对“三十世家”序列义例进行分析和总结,其研究已超过前人,并对后世“世家”研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史记》“世家”的文学研究
史学著作的文学性问题是古今学者一直关注的重点,其中对“世家”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既有对“世家”人物的评价,又有多种文学手法的运用,因后世文学对此多有吸收与借鉴,进而使《史记》成为古典文学艺术的巍峨高峰。
(一)对“世家”的人物评价
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来,对“世家”人物研究出现了一些成果显著的论著。这些成果既有将人物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分类研究,又有对单个人物的评价。
首先对“世家”人物的分类研究。杨燕起《十六诸侯世家论析》一文本着“拱辰共毂”的主旨,从著始分封之功效、重继承制之传统、昭诸贤能之德业、阐文化观之价值、显总时局之变化等五方面进行论述,从纵横双向阐释他们为大一统发展所做的业绩。[17]兰青青的硕士论文以“世家”“列传”中记载的西汉前期功臣为主要研究对象,按高祖、文景、武帝三个时期来分析功臣的命运。[18]杨燕起、兰青青二人均未对“世家”中唯一的女性描写做历史功过的评判。郑林、刘伟《史记新读》一书则从帝王之后、姜子牙的子孙们、吴越争霸、楚韵雄风、孔子故乡人、风悲水寒燕人歌、晋世豪杰、三晋风云、刘邦的左膀右臂、刘氏宗亲、粉黛三千为一人、寂寞的孔子、折翅鸿鹄等方面对“三十世家”进行整合后,对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和结局进行分析,词条式的内容既编排便于阅读,又便于对当时的政治斗争、社会变迁、人事炎凉与民间百态有通观的认识。单瑞永的硕士论文《〈史记〉人物美德研究》,将人物美德分为帝王之德、诸侯之德、臣民之德,又从中突出人性中的美德,并予以归类分析。但人物美德是一个很宽泛笼统的范畴,而人性是复杂的,只捡其美德论析不足以展现人物的完整性。[19]李鹏的硕士论文对《史记》人物出场与退场的类型、方式、出场艺术三方面进行分析,如结合孔子、陈涉、张良、陈平、萧何、曹参、周勃、周亚夫、勾践等相关世家人物进行分析论述,视角比较有新意,对《史记》研究富有启迪性。[20]
此外还有从性别角度将“世家”作为一个整体从不同层面的分析,如陈鑫的硕士论文《〈史记〉中的谋士形象研究》,通过对谋士着笔的繁简及最终的归宿来分析,指出其悲剧性,但对谋士悲剧性的分析略显不足。[21]除了对男性群体进行评价外,还有一系列论文分析《史记》中的女性群像、汉初政治女性等。《史记》以女子为中心的篇章集中在《吕太后本纪》和《外戚世家》,而对女性的分析主要针对后者。如王肖杰的著作《说史记:〈史记〉中的那些事儿》、李黎的论文《从〈史记·外戚世家〉探析后宫女子的命运悲剧》[22]、杨麟舒的论文《从〈外戚世家〉看〈史记〉的女性书写》[23]等,要么是从阶层的角度,要么是从努力抗争却无法把握命运和随遇而安、无为而达的角度分类,要么分析后宫女子或传奇或波折的人生。总之,对这些女性进行归纳,分析她们的地位、婚姻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的关系,指出女人间的勾心斗角关联政治的起伏,但无一例外地都指出她们的悲剧性与传奇性,对女性抱有尊重、同情的态度,体现了司马迁超前的历史观。
其次对“世家”人物个体的研究。当前对“世家”人物的个体研究,在深广度方面均有进一步拓展。尤为可贵的是从地域文化视角对“世家”人物进行解析,这在当前《史记》研究中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命题,最突出的成果是刘玲娣等著《〈史记〉中的河北人物研究》一书。书中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将《史记》中涉及的112位人物进行地域划分,有30多位是河北人,遴选其中最有影响的29位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六类,关乎“世家”的有第一篇“君王至尊”中的赵武灵王(《赵世家》)、燕昭王(《燕召公世家》);第三篇中“沙场枭雄”中的乐毅、第五篇“汉宫巾帼”中的诸位女子(《外戚世家》),就人物的生平足迹、历史贡献、社会地位与历史影响等展开论述,突出地域文化对于人物性格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意义,揭示其功绩与影响,以求在新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重新审视和进一步认识这些人物。张新科的论文结合《吴太伯世家》分析吴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区文化载入史册,指出先秦西汉时期吴人尚武好勇、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体现了《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24]刘晓娜着重探讨《史记》中记载的齐鲁历史人物及其精神风貌,来展现司马迁对齐鲁文化的继承。[25]崔凌榣的硕士论文《司马迁地域审美观研究》,以“货殖列传”“本纪”“世家”为例来探知南北地域审美意识的形成,但对“地域审美观”的概念阐释不够具体深入。[26]
除去地域文化视角,还有学者多维立体地解读“世家”中的人物。王肖杰的专著《说史记:〈史记〉中的那些事儿》对“三十世家”中的17个“世家”进行评价,如“理想悲歌”(《孔子世家》)、“智绝”张良(《留侯世家》)、“为自己而活”(《吴太伯世家》)、“云梦多奇人”(《楚世家》),等等。史冷金《煮酒论史:史记中的哲学与智慧》一书,对《宋微子世家》《齐世家》《赵世家》《楚世家》《晋世家》《魏世家》《越王勾践世家》中的传主进行评价,指出其处世的哲学与智慧。从已有成果来看,对“世家”人物的评价比较集中于孔子、吴太伯、张良等人。
学界对《孔子世家》从多侧面多角度来论析,侯文学[27]、林素英[28]、林宗昱[29]、张耀予[30]等撰文指出孔子其人、其人格魅力及对文化的贡献,其中刘志伟[31]评其是“素王”典范,而刘国民在《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司马迁〈史记〉二十讲》一书中评价他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32]66。而富有启示性和代表性的论著是陈曦的《〈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该书中编对《史记》中的人物实例进行分析,指出司马迁“有意夸大孔子的政治才干和在政坛的影响力,以此来深刻反衬孔子的悲剧命运”[33]116,并视孔子为“具有灵活处事能力的而不是生硬呆板的人,用大量佚事揭示了他不废原则、勇于权变的思想特征以及忍辱忘忧、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33]119。同时,对孔子出身的大胆描述,透视出司马迁不为贤者讳的“实录”意识,以及用于挣脱儒家教条的可贵精神。
陈桐生在文中对《吴太伯世家》进行了简要评论,指出司马迁将其置于“世家”之首是肯定太伯、季札的让国精神,并对吴国后期兴暴亡忽进行历史反思,在叙事上颇具匠心,再次体现太史公善序事理的杰出才能。[34]而徐兴海在其文中指出司马迁对太伯事迹进行充实完善,使得太伯形象更加完美、高大,更有政治家的谋略、胆识与气魄,其中寓含了司马迁对“义”、国家、文化等观念之认识。[35]韩兆琦在《韩兆琦〈史记〉新读》一书中对张良有专讲,说其是“黄老铸就帝王师”[36]147,写他助刘邦攘外安内的旷世之举和历史功勋,分析他受高人点拨的神奇谋略、最后写他自我防护、明哲保身的智慧。李悠罗的博士论文分别对游侠主题、成仙主题、帝王师主题进行溯源后,以《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故事为原型分析他在这三种主题中身份变迁的时代性特征,以及在戏曲、小说、诗文中的形象变化及其文化内涵。论述清晰,富有系统性。[37]欧阳清在其论文中重点分析了“被改造的张良”,对张良游侠、谋士、游仙三种形象进行分析,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张良形象历史变迁的原因。论述虽不够深入,但对张良分析也略有补充。[38]
综观学界对孔子、吴太伯、张良三人的命运、遭际多有不同意见,但对其品德、人格、才能、智慧方面的评价,皆是持肯定赞许的态度,这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个鲜明的、饱满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此外,还有对范蠡、周亚夫父子等人的评价。张文江文中指出《越世家》是对《货殖列传》中范蠡的补充,是为了脱离政治,通过经济而获得相对的自由。[39]韩兆琦、陈曦一文则认为司马迁笔下的范蠡有着汉初现实政治的影子、荒诞不近人情、信仰与实践脱节,进而指出司马迁对黄老思想及其鼓吹者的隐隐嘲讽。[40]王肖杰《说史记:〈史记〉中的那些事儿》一书对周勃周亚夫父子概括为“武夫从政”,指出周亚夫错在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最后死得很悲壮,却没有明确点出政治才能的缺乏、性格因素是其悲剧的又一原因。[41]99吕方《汉初社会流动个案研究——以〈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汉初社会流动个案研究为视角,结合时代变化对周勃父子跌宕起伏的人生进行分析,揭示其悲剧的原因。[42]《韩兆琦〈史记〉新读》一书认为周亚夫有大功,为人比较正直,最后却死得相当委屈,较之“世家”中的其他人物,司马迁对其寄寓了更多的同情。张大可《史记二十讲》一书,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评价周亚夫之死是西汉盛世时期的三大冤案之一,指出伴君如伴虎,专制体制铸造君王的绝对权威,才是功臣悲剧的根本原因,分析可谓中肯又一针见血。
(二)“世家”文学手法研究
目前,对“世家”文学手法进行研究的内容,散见于将《史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艺术研究的相关论著中。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一书,结合《楚元王世家》《陈涉世家》《陈丞相世家》等分析《史记》作为传记文学所进行的取舍剪裁。俞樟华《史记艺术论》一书,从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艺术结构、语言艺术三方面结合相关世家进行分析,如结合《魏世家》分析人物传记的完整性与集中性,结合《陈涉世家》《留侯世家》分析轶事描写的意义,结合《陈丞相世家》分析艺术结构,结合《留侯世家》《外戚世家》等分析语言艺术。安平秋、张大可、俞樟华《史记教程》中以《留侯世家》《魏世家》《外戚世家》等为例,指出司马迁对民间语言的吸收与提炼,进而展现《史记》的语言成就。杨树增《史记艺术研究》结合《孔子世家》分析想象与虚构及人物表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突出司马迁的爱奇;以《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等为例分析司马迁的艺术构思、人物塑造与艺术风格。杨先生给予《史记》以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巍峨高峰”[43]383。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衡》第四五六章,能结合吴太伯、孔子、陈涉、张良、晋文公、梁孝王等世家人物进行细致分析。总体来看,这几位学者对《史记》文学艺术成就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为广大后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厚宝藏。
论文方面,探讨具体文学手法的成果不少,有一些论述比较精到。如陈曦从“隐含叙述”的角度,结合“世家”“列传”的具体篇章进行寓言式叙述和移位叙述,并通过一字寓褒贬的手法进行反讽修辞,来表达司马迁不愿公开的叙述态度。[44]赵沛霖从神话视角对《高祖本纪》和《赵世家》中的神话进行审视,指出帝王天命神话的没落。[45]高志明的硕士论文在立足文本的基础上从文学语言和审美表现的视角进行分析。[46]而许勇强、李浩淼则指出“提顿之笔”是“世家”中的一种特殊叙事手法,其主要表现形态或直接系以国君的纪年,或用“是时”或“是岁”等语引出,可以确定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拓展叙事的空间,有利于读者在对历史事实全面掌握的基础之上窥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47]史常力则是以小见大,通过抓住《史记》的微小事件,关注其逐渐发展演变,最后成为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并肯定其是《史记》叙事中的“蝴蝶效应”,观点新颖,论述具体而翔实。[48]刘宁从立体叙事、宏大叙事、全知叙事等手法来论述《史记》的叙事风格。[49]曹西兰重点对《晋世家》的整体叙事风格、深层叙事逻辑、具体叙事过程进行了细致分析。[50]党艺峰以《宋微子世家》为探讨中心,从史料来源、结构与主导线索、建构叙事模式等角度解析一个历史学家的悲剧意识。[51]王振红指出司马迁运用“迭见法”重复记载人事的目的在于寄寓褒善贬恶之义,解决“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叙事难题,以及展现时代精神与历史的发展趋势,最终服务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52]张学成撰文指出,《史记》人物写心艺术分为直写法与曲写法两种。“直写法”意为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直接描写,关于此法,今之学者所述较多。“曲写法”意为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并不给予直接揭示,而是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予以巧妙地表现。张学成重在对“曲写法”中“空白法”写心艺术的分析,是作者发挥丰富的想象而进行的合情合理的虚构和加工。视角独特,很有新意,论述较深入。[53]
此外,美国学者倪豪士从行文的逻辑结构视角对具体问题予以探讨。他在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晋世家》中灵公杀宰夫、鉏霓不杀赵盾自己触树而死、郤克使齐等三个问题存在的逻辑矛盾,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进行分析。从一个外国学者的思维逻辑,通过引入不同的叙事文本提出自己的推断和假设。[54]8-17
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专门对“世家”进行文学性研究的内容不多,且多夹杂在对《史记》文学性研究的相关论著中,但都阐释得比较深入。相比而言,对此研究的论文则较多,多从细微处落笔,涉及面广泛,其研究角度和方法是对前人的一种补充和发展,进而对后学者有重要的启示性。
(三)“世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学界多将《史记》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其中间或引证“世家”篇章,因此,在相关论著中有关“世家”对后世文学影响的研究成果比较碎片化。相比较而言,各类论文对此问题的研究则比较集中突出,具体如下:
一是对“世家”人物取材研究。曾礼军《论唐代诗人对〈史记·留侯世家〉的接受》一文指出,唐代诗人结合自己的生平遭际对张良从不同角度发表自己或褒或贬的言论。[55]张艳艳的硕士论文《张良故事研究三题》,主要从小说、杂剧和传奇戏曲三个角度纵向来写后世作家对张良的接受。[56]董亭的硕士论文《“赵氏孤儿”故事流变考论》指出,“赵氏孤儿”故事最早见于《春秋》,丰富于《左传》,成型于《史记》,并将《左传》中的本事和《史记·赵世家》的故事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其逐渐扩大的现实意义。继之以元杂剧《赵氏孤儿》与《史记·赵世家》的记载进行对比,指出其在此基础上的流变。[57]李悠罗的博士论文《张良故事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主要以《史记》中的张良为底本,以时代为顺序写其发展变化,通过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来进行历时性展现。[37]陆殷殷《唐宋诗人对〈史记〉范蠡形象的接受——以史记咏史诗为探讨中心》一文,以唐宋两代诗人歌颂范蠡的咏史诗为切入点,表达对范蠡建立功业的称赞和对其功成身退的向往。[58]苏悟森的硕士论文《〈史记〉对先唐诗歌的影响研究》第三章探讨《史记》对先唐咏史诗的影响,主要是对“世家”“列传”中历史人物的吟咏和评价,体现诗人的态度。[59]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在论述明清戏曲对《史记》的接受与改编时,于“世家”偶有谈及,在此不一一论述。
二是艺术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论文方面,各位研究者都能结合“世家”中具体篇章论析其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如葛鑫从叙事角度论述《史记》对四大名著的影响[60];刘新生从比较与接受的角度指出《史记》“本纪”“世家”“列传”的叙事特点,并且在“史”的叙述中有浓烈的小说因素,并为后世小说发展提供借鉴。[61]刘金文指出司马迁创造性地运用“春秋笔法”处理材料、描写人物、传达道义,不但使《史记》中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并援引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戚蓼生等人对四大名著的评点,指出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其文学成就的取得追溯到《史记》,进而分析“春秋笔法”对后世史传文学及明清小说的影响。[62]张萍先后两次撰文,前文分析《史记》中的女性形象对《红楼梦》女性人物塑造有一定的原型意义,但对于二者的关联则不够紧密;后文分析《红楼梦》对《史记》写人艺术的继承,从“不虚美,不隐恶”、个性化的写人艺术、人物传记体式三方面予以探讨,指出《红楼梦》对《史记》写人艺术的借鉴。[63-64]此外还有研究者从写人、结构、艺术手法等角度指出《史记》对《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等的影响。如孙连云重点论述了《史记》与《儒林外史》的亲缘关系,该论文的第三部分论述《史记》的艺术手法对《儒林外史》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具体“世家”“列传”为例,从情节设计、人物塑造及叙事手法几个方面论述,指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的许多艺术手法都与史传作品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65]
三、《史记》“世家”的文献学研究
进入21世纪,《史记》“世家”文献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主要是针对一些具体问题结合历史学、考古学进行的文献校勘考辨研究。赵生群先生在《〈史记〉文献学丛稿》一书中指出“《史记》取材于诸侯史记”[9]133,太史公对各国史记原始材料的吸收完成对赵、魏、韩、齐、楚、燕等“世家”的记载。曹定云从《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推算出西周积年总数为274年,再次得出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4年的结论,并深信这一结论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66]毛远明撰文从历史角度考察,指出司马迁对田完、赵衰、赵盾的谥号有失于考索之处。[67]林小云在文中对卫康叔进行考证,结合《卫康叔世家》及《尚书·康浩》等的考察,认为康叔并未封于康,其始封为卫。“康”并不是国名,而是谥号。[68]王永吉撰文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为底本,以清代武英殿本对校,参考南宋黄善夫本等其他版本及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校正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世家”部分文字讹误凡19条。[69]赵生群指出“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各体与《左传》重叠之处甚多,《史记》三家注亦常称引《左传》,作者将三家注称引《左传》之文检校一过,并略加辨析考证,其中涉及“世家”的条目多达47条,对《史记》《左传》及其注释、校勘、标点具有较高参考价值。[70]于海芹[71]、李世佳[72]分别于2010和2015年撰文就《史记·楚世家》“鬻熊子事文王”进行考释,二人都认为“鬻熊子事文王”一语,可理解为鬻熊奉周文王为主而臣事之。崔富章撰文对《孔子世家》进行补正,指出《孔子世家》有讹误、失载、阙讹,并据《高祖本纪》《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儒林列传》以及宋本《孔氏家语》卷十孔衍上汉成帝书等传世文献,参照补正,并列出自孔子起十六代世次。[73]尉侯凯于2017年先后撰文两篇,前文对《史记》(修订本)仍然存在的倒衍讹夺现象进行勘误拾补共14则,涉及“世家”的有《梁孝王世家》《五宗世家》;后文进行校订二十六则,涉及“世家”的有《郑世家》《陈涉世家》《齐悼惠王世家》《留侯世家》,对进一步完善《史记》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74-75]
通过考古文献来阐释一些具体问题,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以论文居多。这些研究比较集中在《晋世家》所载世系与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的铜器铭文的比对上。美国学者倪德卫、夏含夷撰文指出,《史记·晋世家》所载晋侯世系与周礼昭穆制度相矛盾,据以推测献侯和穆侯的世系被颠倒,并进一步说明一系列中国古代年代上的问题。[76]中国学者贾洪波用晋侯墓地出土中所见晋侯名,来考证墓主年代序列及晋国早期的都城变迁。[77]秦蕊、吴坤撰文指出“桑下饿人”故事见于《史记·晋世家》,但通过对传世文献与汉画像的考辨,指出《史记》在撰写此则故事时候出现了杂糅的讹误,司马迁对故事的主人公姓名记载错误,其对故事的改写也有不合常理之处。[78]
还有结合文献记载、出土文献进行经济、行政区划方面的考察。霍有光的专著《〈史记〉与地学文化发微》,以别致的视角运用文献、考古、冶矿、经济等交叉学科,剖析从五帝至汉兴百年间的地学文化,探幽发微,如论证黄金文化,除引“本纪”“列传”外,涉及“世家”的有《赵世家》《陈丞相世家》《燕召公世家》等,并从黄金作为价值尺度、贮藏手段,用来馈赠、赏赐与悬赏,做器物、装饰品及随葬品等方面分析,可以说改变了以往研究者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此外,还有系列论文对此进行研究。如陆振岳先后撰文分析吴国建立的相关问题及“句吴”与“吴”的差别,并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进行论证,指出前者是“自号”,后者是国号。[79-80]刘振刚、张海涛撰文指出《外戚世家》中的窦太后是“赵之清河观津人”,是据汉初行政区划言之,这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81]刘万华指出梁孝王时期的梁国,经济发达、国库充足,并结合文献记载与近年来梁国文物考古情况,来分析《史记·梁孝王世家》所记载的真实性,以及梁国富足与强盛的原因。[82]柴国生认为《史记·外戚世家》“入山作炭”为“入山采煤”无疑,从考古发现反映出汉代洛阳及周边地区的规模化燃煤情况,以及汉代煤炭开采燃用技术的进步等因素综合来看,宜阳存在“百余人”的采煤队伍是与汉代社会发展和生产实际相符的。[83]通过这些研究,能够对汉代的政治、经济、生产等有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结合考古发掘,并与传世文献相参照进行研究,不仅解决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对书中的倒衍讹夺、一些名物、称号、世系等,从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角度进行明辨厘清,这是《史记》研究的重大成果。
除对“世家”进行史学、文学和文献学的研究外,涉及“世家”的研究还有王芳从伦理学角度探究《史记》的伦理文化,阐明政治与伦理的关系,并对写作主体司马迁的伦理价值观进行分析。[84]但对伦理学的阐释不够深入,在行文顺序上有倒置之嫌。金菲菲从律法角度对《史记·陈涉世家》中的“失期”进行分析。[85]师帅从建筑学角度认为《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中有大量宫殿建筑方面的描写,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还有重要的文学价值。[86]还有曲柄睿从档案学角度分析“五宗”“外戚”这两个世家的编纂,并指出档案的形态影响了史书编纂的面貌。[87]这些多样化的研究视角,是对“世家”研究成果的进一步丰富。
总之,21世纪以来,《史记》“世家”的成果蔚为大观,研究或注重理性分析,或侧重考据,或注重感发,有些研究能做到有理有据,言简意赅。但仍有不少研究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有些观点论述新颖,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但有些流于浮泛,不够深入。未来,对“世家”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尝试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来实现某些突破。“世家”中有大量关于战争、事件、人物心理等方面的描写,可以结合叙事学、心理学、军事学等理论视角进一步探究。二是应注重“世家”文化精神的研究,加强其与地域文化的结合。司马迁撰写《史记》前漫游地域之广、时间之长,可结合具体篇章对人物进行地理学、档案学、民俗学等方面的考察,进而对《史记》进行立体化构建,注重交叉学科的关系研究,使那一段历史及历史中人物、事件、民俗、制度等得以立体化呈现。而对历史人物的文化解读,要注意其历时演变与横向比较,避免过多地集中于对某几个人物的评价及共性研究,要注意对个体差异的论述。三是结合出土文献的发掘,加强对“世家”中涉及的人名、地名、时间、事件等做训诂、校勘、版本、目录、考据方面的研究,继续致力于重点难点问题的考辨,使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得以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