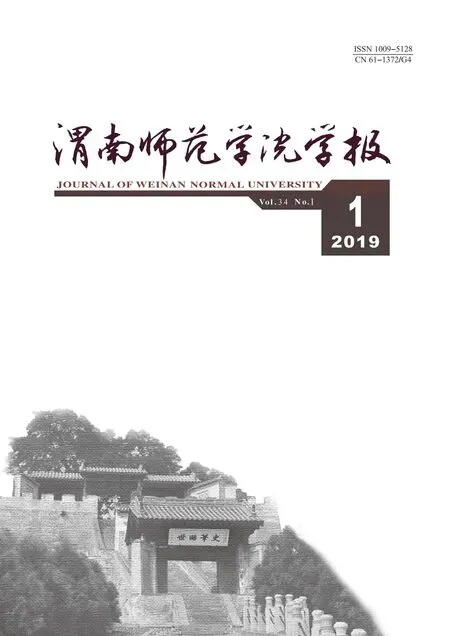《伯夷列传》与正史隐士书写
2019-12-27霍建波
霍建波,李 超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隐士文化是我国古代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与仕宦文化相对而言的,它曾对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人生抉择、心理状态以及文学创作均产生过重大影响。隐士文化的形成发展既是古代隐士群体活动的历史展现,更有赖于古代典籍的隐士书写传统。而在古代典籍中,传统正史无疑是其中最为可信的部分。本文即以《史记·伯夷列传》为中心,对我国古代隐士书写传统尤其正史隐士书写做全面扫描与简要分析。
一、《伯夷列传》之前的隐士书写
在《史记·伯夷列传》之前,我国先秦时期的典籍已有关于隐士的记载。这些记载虽不集中,也没有形成专题篇章,但却对《伯夷列传》以及后世的隐士书写传统有重大影响,也对我国隐士文化的形成有着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贡献。先秦典籍关于隐士的书写,以《论语》和《庄子》的篇幅最为可观,影响最大,也最具有代表性。《论语·微子》篇既最早提出了“隐者”一词,也记载了众多的隐士形象,如荷蓧丈人(见“子路从而后”章[1]195-196)、长沮、桀溺(见“长沮、桀溺耦而耕”章[1]193-194)、楚狂接舆(见“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章[1]193)等。
上述这些关于隐士的片段记述,在结构形式上都颇为相近。一是通过人物对话的方式来体现,二是具备较为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三是隐士的性格形象都很鲜明。这三段所记载的隐士形象,都具备强烈的避人、避世倾向,即使与世人(以孔子与其门徒为代表)偶尔有所接触,也会很快地再度疏离而去;同时,这几个隐士也都对时政或者孔子等人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批判。由此可知,他们尽管选择了避世隐居,其实仍然关注着社会现实,关注着时政人物,并未完全超脱人世之外。此外,《论语》记载的隐士,著名的还有《季氏》《述尔》《公冶长》等篇都提及到的“伯夷、叔齐”,《宪问》篇提及的“荷蒉”“晨门”“微生亩”等。除了直接记载隐士事迹,《论语》还载有孔子关于隐士思想的较为集中的论述,形成了儒家手段式的待时之隐,对后世隐士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2]42-45因笔者曾在其他论著中涉及,此不赘述。
《庄子》不但最早提出并界定了“隐士”[3]555概念,同时也有大量关于隐士事迹的书写内容,其中以《杂篇·让王》篇最为集中、详尽,其他如《内篇·逍遥游》《内篇·齐物论》《外篇·天地》《外篇·知北游》《外篇·秋水》《外篇·田子方》《杂篇·徐无鬼》等,也均有所涉及。《让王》一篇文章,共由十几个小故事组成,这十几个小故事几乎均是叙述或讨论古代高人隐士之事。如《让王》篇提及、《逍遥游》篇详细记载的尧“以天下让许由”[3]22-24,《让王》篇中的尧“又让于子州支父”,“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舜以天下让善卷”,“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王子搜“逃乎丹穴”“颜阖守陋巷”,列子“再拜而辞”子阳赠粟,屠羊说“居处甚贱而陈义甚高”,“原宪居鲁”,“曾子居卫”,颜回“不愿仕”,魏侔“隐岩穴也”,“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商汤拿王位“以让卞随”“又让瞀光”,伯夷叔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等等。[3]965-988这些隐士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慕权势,不贪名利,坚辞当权者的封赏,追求全生、个性独立与自由,希望过着“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3]966的无拘无束、不以外物损害生命的生活。其中关于伯夷、叔齐的记载,与《史记·伯夷列传》的关系最为密切,且为《伯夷列传》的撰写提供了基本的故事框架,可与《伯夷列传》对读。
除《论语》《庄子》之外,先秦典籍中叙及隐士之事的,还有《左传》《诗经》《周易》《孟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等。作为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左传》是解释、阐述《春秋》的。它和《春秋》一样,是为了记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而撰写的。至于其中记载到隐士,应该并没有很特别的用意。如襄公十四年记载的吴国公子季札辞让王位的事迹,就颇具隐士辞王、辞封的味道:“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4]202还有僖公二十四年提到的“不言禄”的介之推,也是一个隐士的形象。[4]75《诗经》中的一些诗篇描写歌颂了隐士,也对后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卫风·考槃》《陈风·衡门》等,均被后人明确认为是隐士诗。《周易》虽是上古的一部哲学著作,最初是为了沟通人神进行占卜而出现的,但笔者也从中解读出了较为复杂的隐逸思想:“《周易》的隐逸思想启发了儒、道两家,开启了先秦儒、道隐逸思想的端绪,对中国隐逸文化的形成、发展意义重大。”[2]37-42综上可知,先秦时期的不少典籍,均有关于隐士的书写,尤其以《论语》《庄子》体现得最为充分、突出。中国古代的隐士文化,由此掀开了神秘的第一页。
二、《伯夷列传》的隐士书写
先秦典籍中虽有不少关于隐士的书写内容,但却零散不成体系,且并非是专门为记载隐士而做出的有意识的行为。如《论语》的记载,分散在二十篇的不同地方。虽在《微子》篇中,隐士的事迹排列在一起,相对集中一些,但其前后的章节并非关于隐士。这与《论语》的编撰成书过程有关,作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集体创作,该书以推尊孔子为中心,其他人物、事件都是为了记录、衬托孔子及其思想而存在的。再如《庄子·杂篇·让王》篇,尽管通篇都是在记载和讨论隐士,但其本意是在说明道家的“尊生”“全生”、不以物害生之理,是在阐发道家顺其自然、无为养生的主张,并非是为记载隐士而撰写隐士故事。在我国历史上,真正为历史人物进行分门别类,并设立专门传记来记载隐士的,首推司马迁的《史记》。
在我国传统正史“二十六史”中,常常会开设隐士列传,记载这类历史中的特殊群体,并且总结探讨相关问题。一般认为最早设立隐士传的正史是范晔编撰的《后汉书》,如清代学者赵翼、王鸣盛等均持这种观点。现代一些学者往往在未做深入考察的前提下,直接认可了他们的说法,如高敏《中国历代隐士·序言》,马华、陈正宏《隐士的真谛》等。但是,通过细读《史记》《汉书》文本,则会发现二者不但对隐士评价甚高,而且已经具备了隐士传的雏形。
号称我国“史圣”的司马迁,继承并发扬了先秦的文化传统。他以古代圣贤为榜样,既具有著史的历史责任感,也有浓厚的平民意识,深为那些“名湮灭而不称”的“岩穴之士”感到惋惜,故他非常重视隐士及其价值取向的社会影响。《史记》“世家”一体共设立有三十篇,其中《吴太伯世家》位居“世家”首位。该篇讲述了吴太伯与仲雍主动辞让王位于其弟季历的故事,最后两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5]439。在篇末“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大大赞扬了他们:“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5]444为了“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5]994,即为了嘉奖、张扬太伯的高让之风,彰显其德行,司马迁才在三十篇世家中把《吴太伯世家》放在首位。
同样,《史记》“列传”一体设立有七十篇,记载隐士的《伯夷列传》亦位于众列传之首,这也是为了弘扬伯夷、叔齐等人的高风亮节:“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5]997论其人物事迹,伯夷、叔齐兄弟与太伯、仲雍兄弟在辞让王位、淡泊名利一事上,几乎完全一致。当然,《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仲雍兄弟的故事,总体看来还比较简略。而与之相比,《伯夷列传》则可以作为《史记》中雏形的隐士传了。
《伯夷列传》把隐士的产生与古代的禅让制联系在一起,首先记载了传说中许由的故事:尧帝要把帝位禅让给许由,许由不以为荣,反以为耻,于是就主动逃跑,做起了隐士。然后提及了夏末商初的卞随、务光,但语焉不详。通过《庄子·让王》篇,我们知道卞随、务光也是秉性淡泊、辞让王位的高士。他们不但不接受商汤的禅让,还都采取了十分激烈的反抗方式,最后两人都投水自尽,希望用清清的河水洗刷掉自己遭受到的诟辱。最后,《伯夷列传》详细记载了伯夷、叔齐二人的生平事迹: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5]635
在这段两百多字的传记文献中,司马迁综合了《论语》《孟子》中孔子、孟子对伯夷、叔齐兄弟的评论,以及《庄子·杂篇·让王》篇的相关记载,并依据其他史料,做了适当的剪裁和补充,为我们提供了伯夷、叔齐兄弟二人比较详尽的生平材料。如他们身为孤竹国国君继承人的身份,他们如何不愿接受王位、如何让位相继逃走,他们怎样劝阻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他们为什么跑到隐居首阳山隐居起来、且不食周粟,又是如何作诗言志、感叹自己生不逢时的,以及如何采薇而食,乃至终于饥饿而死的整个过程,描述得明明白白。联系该传开篇叙及的许由、卞随、务光,可知《伯夷列传》记载、探讨的乃是同一类人,那就是隐士。故认定《伯夷列传》是关于隐士的类传,是合情合理的;又认为《伯夷列传》是隐士传的雏形,那是因为题目并未点明是类传,如“隐士传”“隐逸传”“逸民传”之类,且传主之外的其他人的记载,也都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尽管还不算成熟,但这篇传记也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它在后人心目中已经被当做隐士传来看待了。党艺峰说:“《史记·伯夷列传》在隐逸文化叙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归纳了此前隐逸话语的基本语法规则,从而启示出中国古代历史学对隐逸文化的关注。”[6]3综上可知,作为《史记》雏形的隐士传,《伯夷列传》对后代隐士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此外,《史记》还书写了历史上一些非常有名的高人隐士,如张良、商山四皓和黄石公(《史记·留侯世家》)、老子和庄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东方朔(《史记·滑稽列传》),等等。
三、《伯夷列传》之后的正史隐士书写
《史记》之后,我国传统正史的第二部便是《汉书》。《汉书》与《史记》一样,也设有雏形的隐士传,那就是《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的前半部分。该篇开门见山就提到了先秦时期伯夷、叔齐,接着记载了汉代的六位隐士。首先便是商山四皓,他们隐居在商山深处躲避暴秦,西汉建立后曾出山辅保刘盈,稳定了其太子之位,建立了特殊的功勋;然后是郑子真、严君平,他们虽都不曾出仕做官,但在社会上均有很大影响,郑子真“不诎其志,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7]3057。严君平虽然以卜筮为业,但能够寓教于卜,劝人向善,以致当权者与他交往,却“不敢言以为从事”[7]3057。
记录了上述“近古逸民”的事迹之后,《汉书》开始正式记载王吉(包括其子王骏、其孙王崇)、贡禹、龚胜、龚舍等传主,他们均是班固所标榜的“清节之士”,自然也是本传的核心人物。这些“清洁之士”都曾出仕为官,不能算作一般意义上的隐士。但是他们从不贪图功名权势,且对官场根本没有多少好感,一旦现实使得他们不如意,便断然挂冠隐退。在他们这些“清洁之士”的身上,我们甚至可以依稀看到东晋大隐士陶渊明的影子。
本篇传赞总结全文,探讨了士人的出处问题,也堪称隐士文化的重要文献。传赞认为做隐士和做官“各得道之一节……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7]3097。综上,判定该传的前半部分是一篇隐士传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把这一部分独立出来,并且取个“隐逸传”“高逸传”之类的题目,就是一篇较为完整的隐士传了。正因为并未独立出来,故认为该传的前半部分与《史记·伯夷列传》一样,都是雏形的隐士传。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我国传统正史为隐士设立传记的做法,并非从《后汉书·逸民列传》开始,而是肇始自更早的《史记·伯夷列传》和《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徐复观曾指出:“由《史记》的《伯夷列传》到《后汉书》的《逸民传》的成立,对于守着这种生活态度的人们,给予了我国历史上应得的确定地位。”[8]191-192在这里,徐复观指出并肯定了《史记》作为隐士传的开创性贡献和重大影响。正是《史记·伯夷列传》的存在,乃至《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前半部分的出现,才启发了范晔,才有了《后汉书》的《逸民列传》,才有了我国正史中明确成熟的第一篇隐士传。
作为传统正史“二十六史”的第一部史书,《史记·伯夷列传》不但专门集中记载了隐士的事迹,而且体现出了对隐士以及隐士文化的高度重视;同时,又因为隐士这个特殊群体的社会价值观与对历代统治者统治秩序的积极作用,所以后代这些“奉旨”编撰的正史几乎都有专门的隐士传,并且在正史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为隐士立传的文化传统。由于古代对隐士的称呼五花八门,所以这些隐士传的具体名称在不同的正史中也并不完全一致。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在其他论著中提及,这里不便展开,仅仅把隐士传的名称罗列如下。它们是:《后汉书·逸民列传》《晋书·隐逸列传》《宋书·隐逸列传》《南齐书·高逸列传》《梁书·处士列传》《魏书·逸士列传》《南史·隐逸列传》《北史·隐逸列传》《隋书·隐逸列传》《旧唐书·隐逸列传》《新唐书·隐逸列传》《新五代史·一行列传》《宋史·隐逸列传》《辽史·卓行列传》《金史·隐逸列传》《元史·隐逸列传》《新元史·隐逸列传》《明史·隐逸列传》《清史稿·遗逸列传》。
从上面一长串“二十六史”所设立隐士传的名单中,我们足可窥见古代隐士传统的强大,亦可知隐士文化的绵延不绝。同时,这些都是明确成熟的隐士传,而不是像《史记·伯夷列传》和《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的前半部分那样,只能算作雏形的隐士传。而所谓明确成熟的隐士传,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传记题目能够看出是记载隐士的;二是开篇有序文或文末有传赞探讨隐士之事;三是正文集中记载多个隐士。以此为标准来考察“二十六史”,《后汉书》的《逸民列传》便是其中最早的一篇。
因为《史记·伯夷列传》的开创性贡献,使得传统正史“二十六史”中有二十一部史书(包括《史记》和《汉书》在内)专门为隐士设立传记,有十九种有明确成熟的隐士传。这些正史的隐士传不仅记载下了历史上数量众多的隐士的事迹,也为我们探讨古代的隐士文化保存下了真实可信的原始文献。由此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独具一格的隐士文化,稳定了传统史学甚至整个中华文化谱系中重视隐士的传统。这为我们今天探究传统文化,解读传统文人的心理状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