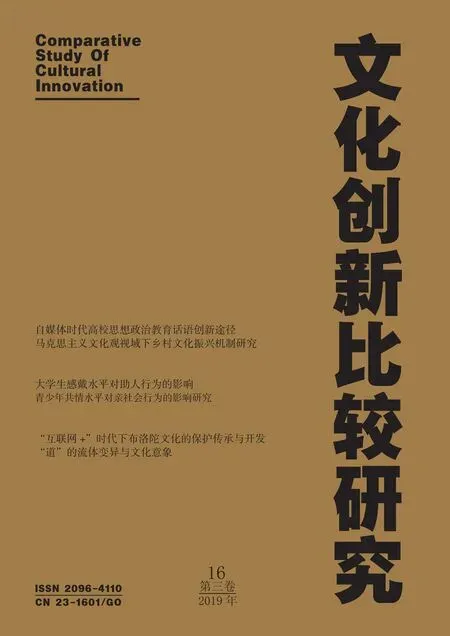略论儒家的道德观
2019-12-26郭金粘
郭金粘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037)
1 道德的本质意涵
道德是儒家的崇高概念,也是儒家教育中的底色问题,代表了儒家对知识分子最热切的要求与理想。金岳霖先生在《论道》中说道:“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的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1]。” 儒家经典《中庸》也强调:“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2]。”道的概念总是中国思想中最核心的概念与最基本的原动力,儒家的道德追求更偏重于人格理想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层面,例如君子之道,为师之道。《学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3],将君子的德性阐述的更具实用性,德是拥有万物的基础。可见德的观念是儒家的重要线索。道与德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合于道德。人的道德修养是儒家最重视的问题,是成人成圣的决定性因素。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认为自己所坚守的道所倡导的道德皆来源于周代。中国统一的制度与政治的创建始于周公,中国伦理社会的创立与社会伦理道德的主要精神的形成又源于其所定宗法。因此周公制礼作乐的深刻内涵即为了道德观念的确立,以维持伦理社会的正常运行,道德” 二字涵盖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之所在。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精神之特殊,或在其偏重道德精神之一端。[5]”中国文化中道德精神既非西方的宗教信仰,又非纯粹的思辨哲学,主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道德行为的内在道德精神最重要的特征是其内发性,是个人寻求其内心之所安的道德活动,而并非强迫或是压制,这种发于心的道德追求外在衍生为整个伦理社会的道德取向,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
2 道德的主要维度
儒家的道德内涵丰富、对象广泛,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对君王、 百官或是平民的道德教化都是必不可少,并以成人成圣为最终的道德旨趣。儒家的道德教育体系完善,涵盖了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方方面面,为世人的道德完善提供了可依循的路径。
《中庸》中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2]。儒家的开创者孔子述而不作,遵循周公所创造的礼乐制度,因此礼是儒家道德教育中的特有内容,区别于墨道法等诸子各家。儒家典籍中也多次提到“礼”的问题。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4]。在儒家看来礼制不仅关乎个人的道德品质亦关乎社会的稳定,所以礼治必不可少。荀子认为人一定要依靠师长的法度教化才能行为端正,社会得到礼义的引导才能有秩序。“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 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6]”教师是礼的化身,用礼来端正学生的品德,以正其心。
《孝经》开篇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7]。”孝是一切德性的根本,是教化产生的根源。从相对微观视角而言,孝是在家庭内部对父母兄弟的道德情感,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孟子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天下也。[8]”因而人子对其父母的孝最终体现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即道德的本质。儒家之所以把孝作为德性的根本,从更宏观的视角而言是因为孝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和谐,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4]”从为人臣的角度出发,一个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人自然不会犯上作乱,所以社会自然安定有序,而若使国家长治久安,自然是以君王力行孝道,推广至万民为根本,故武王尊为天子,周室始于武王,但必自屈为人子焉,尊文王为开国始祖,此所谓周公之礼。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4]。”因此孔子承继周公之礼,宣扬圣明的君王以孝治国,劝谏君王实行孝道,可见孝是儒家道德教化的根本。
《中庸》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2]。”朱熹认为此处的“一”解释为“诚”,这亦符合“自明诚谓之教”的道德教化理论。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因此在儒家孔子那里,圣人或君子最重要的道德品质[4]是“仁”,这也构成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体系。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4]。”孔子首先从祸福生死的角度给予“仁”崇高的道德定位,君子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违仁,继而提出仁的具体表现形式为遵循“忠恕” 之道,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可见孔子不仅仅限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更推己及人,关心群体道德,这也体现了儒家道德实现路径中的从个体到群体,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
3 道德的实践路径
无论是《中庸》所提到的“修道之谓教”“自明诚,谓之教”,或是《礼记》中“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相长”等儒家典籍都涉及教的问题,并且依据中国伦理社会的传统文化,儒家所谓的教必然离不开道德教育,更进一步说道德教育是儒家的核心内涵,一方面包括儒家自身的道德修养,另一方面则为对更广大民众的道德教化。因此儒家的道德实践路径有两条:一是指向自身的道德修养,将道德作为个体内心信仰与情感;二是促进社会良好道德风气的形成,将道德与社会的准则制度相联系。在儒家这两条道德的实践路径是相统一的,即所谓的“内圣外王”之学。如熊十力先生在《原儒》中明确指出“儒学总包内圣外王”[9]。当代大儒牟宗三认为所谓“内圣”者,“内在于个人自己,则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之谓也”;所谓“外王”者,“外而达于天下,则行王者之道也[10]。”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形成自然离不开每个个体内在道德品质的养成,个体内在的道德修养又受整体社会风气的影响,因此儒家从这两条路径出发,上下贯通,力图通过道德教化实现移风易俗,复兴周礼的宏大愿望。
儒家个人道德实践路径的核心是修身,即为“内圣”之道。《大学》中的“八条目”由内到外,层层深入地阐述了成为圣王的路径,其中修身是最重要的中间环节,《中庸》亦曰:“修身则道立”,可见修身是个人道德境界提升的重要因素。自然修身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儒家知识分子,故《大学》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人类无论阶层高下,在伦理道德层面享有平等地位,道德的要求不因等级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周代自君王至万民,自上而下皆以修身为本。君修其身而仁,则臣自敬。臣修其身而敬,则君自仁。子修其身而孝,则夫自慈。父修其身而慈,则子自孝[5]。修身自持是完善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并向群体道德转化的最佳途径。
儒家作为微弱的社会团体想要改变整个社会道德取向,明显看来力量太过薄弱,需要更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儒家群体道德的实践路径为出仕,孔子谓之“学而优则仕”,即为“外王”之道。《论语》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4]?”可见在孔子看来修身是必要的,但是君子修身的最终目的是安百姓,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儒家皆具有家国天下的道德情怀,孟子曰: “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0]。”在不得志的人生境遇之时修养自身道德,在有机遇之时看当天下重任,这是儒家所具有的道德情怀。
儒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已与周代宗法制社会迥然不同,周代各大宗小宗之间亲缘关系密切,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深远,上位者可以通过道德模范作用积极的影响下位者,可以维持整个社会道德体系正常运行。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套传统的宗法体系已经遭到破坏,政治脱离传统的氏族形态开始孕育新的社会政治形态大的诸侯国希望通过战争的形式歼灭吞并小的国家实现统治的目的。在这种社会纷争的背景下,儒家所推行的道德教化必然会受到重重阻碍,无论是以修身为本的个人道德实践路径还是以出仕为主的群体道德实践路径都似乎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但是正是古典教师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感化着世人,儒家的道德精神在新的社会意识形态下依然焕发着生机。儒家对于人类有着强烈的关怀或者说是人道主义的情怀,体现在对天下苍生的社会责任感,孔子人道社会的理想体现在“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4],孟子则体现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8]。总之古典思想中无不体现出对人类的关怀,这亦是一种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的集中体现,表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