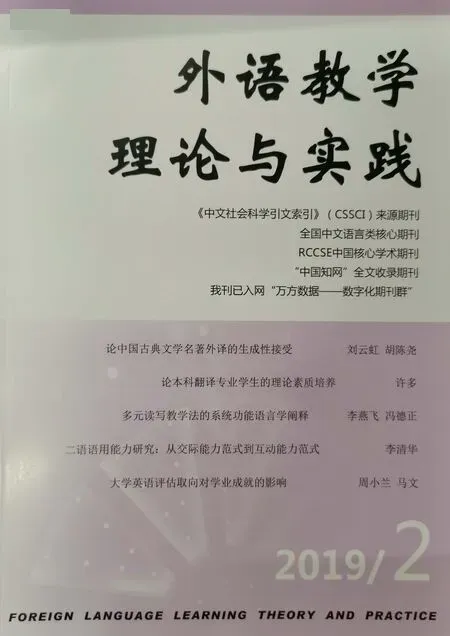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外译的生成性接受*
2019-12-21南京大学刘云虹胡陈尧
南京大学 刘云虹 胡陈尧
提要: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进程与时代背景下,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经由翻译在异域得到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但围绕翻译以及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仍存在需深入关注的事实与进一步澄清的认识。就根本而言,文学翻译是文本生命的生成过程,文学接受则是文本生命生成中的重要一环。同时,翻译始终面向读者,无论译介模式的确立,抑或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总是与读者的接受息息相关。据此,本文从文学翻译所具有的生成性本质出发,通过考察四大名著外译历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指出文学接受与文学翻译本身一样,始终处于不断更新与完善、不断丰富与发展的历程之中,并力求以历史、动态的目光深入揭示其阶段性、时代性与发展性特征。
一、 引言
2017年3月,瑞士译者林小发(Eva Luedi Kong)凭借其翻译的《西游记》首个德文全译本摘得“莱比锡书展图书奖”的翻译类大奖。从1914年德国汉学家最初的片段翻译至此,《西游记》在德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已走过了一百多年历程。这部耗时17年的译著一经出版便在德国掀起了一波“西游热”,也引发了国内学界和媒体对中国古典名著外译的进一步关注与思考。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媒介,翻译活动使中国的经典文学和传统文化得以走出国门,在世界文学之林延续其生命历程。然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的文学译介绝非一味的单向输出。正如不少学者所关注并探讨的,在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中华文化的传播中,重要的不仅在于如何“走出去”,更在于如何能更好地“走进去”,真正实现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在目前针对中国文学外译问题的诸多探讨、争议甚或质疑中,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不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文学整体“出海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也是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中一个迫切需要重视并解决的关键问题。
我们知道,译本的诞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完结,而恰恰是在“异”的考验中、在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与理解中翻译成长历程的开始。在《试论文学翻译的生成性》一文中,刘云虹曾就文学翻译的生成性本质进行了探讨,提出“无论就文本新生命的诞生、文本意义的理解与生成,还是就译本生命的传承与翻译的成长而言,翻译是一个由生成性贯穿始终的复杂系统,不断在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维度内寻求并拓展可为的空间,同时,翻译也是一个具有生成性本质特征的动态发展过程,以自身生命在时间上的延续、在空间上的拓展为根本诉求”(刘云虹,2017)。文学翻译是文本生命的生成过程,文学接受则是文本生命生成中的重要一环。同时,正如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翻译也始终面向读者,无论译介模式的确立,抑或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总是与读者的接受息息相关。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拟从文学翻译的生成性本质出发,通过考察四大名著外译历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做一探讨。
二、 从节译到全译: 文学接受的阶段性
翻译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行为,而是涉及两种语言与文化的再度语境化过程,必然遭遇来自语言差异性的考验,同时深受语言与文本之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就意味着翻译过程具有相当复杂的内涵,无论译者的“可为”空间,抑或读者的接受空间,都并非完全取决于主体层面,而是从根本上被限定在一个由时代因素所决定的“有限可能性”范围内。法国当代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其翻译研究中特别关注文学移植的不同形式和阶段,强调应在“文学移植”的总体理论下探讨文学翻译及其接受问题。在贝尔曼看来,文学移植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居于既定时代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集体规范以及读者的审美情趣、文化素养和期待视野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而这些因素无一例外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因此,他认为“异域文学作品首先有一个被发现、被本土读者关注的过程,此时它还没有被翻译,但文学移植已经开始;接着,如果它与本土文学规范之间的冲突过于激烈,它很可能以‘改写’的形式出现;随后,便会产生一种引导性的介绍,主要用于对这部作品所进行的研究;然后就是以文学本身为目的、通常不太完善的部分翻译;最终必定出现多种重译,并迎来真正的、经典的翻译”(Berman, 1995: 56-57)。这一观点揭示的正是文学译介与接受所具有的阶段性特征。
纵观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在海外的译介历程,它们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都大致经历了从节译、转译到全译的不同阶段。就《西游记》在德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而言,林小发的全译本诞生之前,《西游记》在德国曾先后经历了一个世纪漫长的节译、编译和转译过程。早在1914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就将《杨二郎》(YangOerlang)、《哪吒》(Notscha)、《江流和尚》(DerMönchamYangtsekiang)和《心猿孙悟空》(DerAffeSunWuKung)四篇译文收录进其编译的德文本《中国通俗小说》(ChinesischeVolksmärchen)中,这是德国汉学界对《西游记》最早的片段翻译。不可避免,卫礼贤的初次尝试中存在不少错漏,如他将原著中具有重要文学价值的诗词部分略去不译等。正如有学者在分析《三国演义》的英译时所指出的,外籍译者在客观上“会因为对相关中国古典文字、文学、文化领域知识的缺乏,在译介中与原著产生偏差”(许多,2017)。无论从翻译的完整性抑或译本的文学性来看,卫礼贤的翻译无疑距离理想的文学译介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我们应该看到,在20世纪初期,囿于汉语人才的短缺和相关研究的滞后以及中外文化间的隔阂,德国汉学界对《西游记》这样一部八十余万字的鸿篇巨著存在整体把握上的难度;普通德国读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十分陌生,尚没有形成有利的接受心态和开放的接受空间。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译者选取可读性强并具有代表性的故事情节进行编译,可以说既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能动选择,也是既定时代语境下的一种必然。这样的译介模式有利于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拉近读者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距离,为往后趋于完整与忠实的译介奠定了基础。
1947年,乔吉特·博纳(Georgette Boner)和玛丽亚·尼尔斯(Maria Nils)合译出版了《猴子取经记》(MonkeysPilgerfahrt),该译本转译自1942年出版的英译本《猴子》(Monkey),而英译本译者阿瑟·韦理(Arthur Waley)只选取了原著中的30回进行翻译,其篇幅之和不到整本著作的三分之一。1962年,原东德译者约翰娜·赫茨费尔德(Johana Herzfeldt)的节译本《西方朝圣》(DiePilgerfahrtnachdemWesten)问世,该译本依据的是《西游记》的中文原版与俄文译本,并附有译者序以及对原作者和小说历史背景的介绍。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西游记》译文在质与量两方面较之二十世纪初卫礼贤的译本已有显著进步,但删改和误译现象依旧存在,转译带来的翻译忠实性问题也不容忽视,如赫茨费尔德就在译序中指出了原著的文言诗词给译者在理解和阐释上带来的困难,并明确表示自己在译作中对原著的诗词部分进行了删减。
以上提及的节译和转译本应都算作贝尔曼所言的“引导性”翻译或“部分翻译”,其在德国的接受主要局限在少数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当中,并未真正步入广大普通读者的文学阅读视野,也因而未能产生实质性的传播影响。2016年由瑞士译者林小发翻译的《西游记》(DieReiseindenWesten)全译本由德国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该译本以中华书局出版的《西游记》原版为依据,后者则以清代的《西游证道书》为底本。林小发完整翻译了原著的所有章回,并最大限度保留了原著中的文言诗词及传达中国传统哲学与宗教思想的相关内容。此外,林小发还在译后记中附上长达18页的神仙介绍列表,并对小说中可能给读者造成理解困难的中国传统文化要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解读。林小发的全译本无疑是成功的: 初印的2 000册在短期内售罄,“过了短短五个月就准备印第四版”(宋宇,2017);德国《法兰克福邮报》将其列为最适宜作为圣诞礼物馈赠的书籍之一推荐给读者(孙玫,2016);此外,“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在线、《世界报》等亦对其进行了报道”(彭大伟,2017)。2017年3月,林小发凭借《西游记》的全译本一举摘得德国“莱比锡书展图书奖”翻译类的桂冠。从一部“被注视”的东方古典著作到成为畅销译著并荣获重要图书奖,《西游记》在德国的接受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
从《西游记》德译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译介与接受个案中不难看出,具有丰富内涵和复杂过程的文学译介活动必然经历一个迂回曲折的历程,需经由不同的历史阶段才能在不断接近翻译之“真”的路途中最终迎来“经典的翻译”。究其原因,中西方文化接受上的严重不平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其结果就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接受语境和读者接受心态两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具体而言,“当中国读者易于也乐于接受异域文学,并对阅读原汁原味的翻译作品有所追求甚至有所要求时,西方国家无论在整体接受环境还是读者的审美期待与接受心态上,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关注和熟悉程度可以说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刘云虹,2015)。不同文化间消除隔阂、相互沟通的历程是漫长的,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同样将经历从陌生、排斥到了解、接纳的过程。翻译是一种历史性活动,文学接受同样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因此,我们应从翻译历史观出发,充分把握文学译介与接受的阶段性特征,深入考察并理性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外译中客观存在的从删节、改译到全译的不同历史形式与阶段。
三、 “变形”与“新生”: 文学接受的时代性
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于其符号转换性。许钧曾就翻译的符号转换性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一切翻译活动都是以符号的转换为手段的”,而“经由转换的符号性创造,人类的思想疆界才得以拓展,人类各民族、各文化之间才得以交流与发展”(刘云虹、许钧,2016)。符号转换既指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也包括语言符号与音乐、绘画、图像等其他符号之间的转换。雅格布森从符号学观点出发对翻译进行分类,提出翻译可以在三个层面得到理论的界定,即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其中“符际翻译”的概念即指“非语言符号系统对语言符号系统做出的阐释”(Jakobson, 1963: 79)。相较于以单纯的语言符号为媒介的“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符际翻译将语言符号与各种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和阐释纳入翻译范畴内,拓展了翻译活动的形式与内涵。在当下的新时代,科学技术和新媒体高速发展,文学译介的手段与途径进一步丰富,同时新的翻译观念与新的审美需求也不断出现。例如有学者提出,在当前“读图的时代”,“图像的翻译与转换”已成为“当代翻译的一种形式”(王宁,2015),也有论者认为,“重视经典、长篇、大部头的对外译介,忽视不完整、不系统、跨界、短平快、消费性极强的文化信息的传播,‘严谨的输出导向’和‘活泼的需求期待’之间存在缝隙,导致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常常过于死板紧张,缺少灵活变通”(蒋好书,2014),等等。这一切都促使翻译的“新生”,文学作品的传播已不再囿于传统的纸质文本媒介,各种以“变形”为表征的符际翻译不断涌现,成为文学译介,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
《三国演义》在日本的译介、传播与接受便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个案。自江户时代传入日本以来,《三国演义》在日本先后经历了节译、改编和全译等译介过程,掀起了持续至今的“三国热”,成为一部真正走入日本大众视野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新的时代背景下,借助日新月异的高科技与新媒体,《三国演义》在日本的传播途径更加多元、传播形式也更加丰富,在相对传统的连环画、电视连续剧、歌舞伎等改编形式之外,动漫和电子游戏等更为新颖也更具时代特色的传播途径为作品生命在日本的进一步传承与延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众多由《三国演义》衍生出的动漫作品中,《最强武将传——三国演义》是耗资最多、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这部52集的动画片由中日合作拍摄,2009年亮相东京国际动漫展,2010年登陆东京电视台并占据每周日上午9点至10点的黄金时段。除了动漫领域,电子游戏在《三国演义》传播与接受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小觑。自1985年日本著名游戏软件公司光荣株式会社发行《三国志》系列游戏的首部资料片以来,该游戏截至目前(2018年1月)已有13部本传和多部外传。这一系列的历史模拟类游戏以《三国演义》《三国志》中的人物和故事为依据,并竭力“还原历史本源”:“为了人物头像等细节,制作人大量参考了中国明清的三国人物白描绣像、民国时期香烟盒等文献资料,在人名地理等方面也力求精确,加上卫星扫描的地图,严谨的各种历史资料的考据”(舒小坚,2011)。总的来说,新兴的大众传播文化与多元化的传播形式使《三国演义》这一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译介突破了传统的“从文本到文本”的限制,从而使其在日本传播与接受的广度和深度都得以进一步拓展。
如此的“变形”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外译中并不鲜见,《西游记》在英国的歌剧改编、《水浒传》在法国的连环画改编等都是颇为成功的文学译介与接受模式。2007年6月,华裔导演陈士争执导的现代歌剧《猴: 西游记》(Monkey:JourneytotheWest)“登上英国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的舞台,连演12场,常常爆满”(马桂花,2007)。该剧选取了《西游记》的九个回合,由中、英、法三国联合制作,融合了动画、灯光特效、武术、杂技等多重演绎方式,剧中音乐不仅有中国的传统乐器,还融入了电子音乐、打击乐等西方流行音乐元素,“为古老的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吹来一股现代风潮”(杨涛,2013)。演员的表演也颇具特色,“通过歌唱、武打和杂技,将《西游记》步步惊心的情节和气势磅礴的场面还原给现场观众”(同上)。《西游记》歌剧首映获得巨大成功,英国主要媒体纷纷给予高度评价。例如《观察家报》认为“无论是中国导演、英国作曲和造型设计、法国的指挥,都打破了常规,在一个陌生地区进行大胆尝试”(马桂花,2007)。在英国首演取得成功后,该剧“又在法国巴黎的查特莱剧院、美国斯波莱托艺术节及英国伦敦皇家剧院上演,并在巴黎查特莱剧院创造了连演16场并加演3场的历史纪录”(杨涛,2013);2013年7月,该剧“作为美国林肯中心艺术节的开幕大戏,亮相大卫·寇克剧院”(同上)。据央视网报道,“美国观众对这部改编自中国经典神话故事的摇滚歌剧表现出了相当浓厚的兴趣,很多观众散场后都争相在海报前留影纪念,不少人还模仿起剧中‘孙悟空’的经典形象,陶醉其中”(同上)。
2012年10月法文版《水浒》连环画在法国的出版同样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介与传播中颇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据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官网报道,法文版《水浒》连环画全套共30本,制作精良,面世后引发法国主流媒体的热切关注,“《费加罗报》称,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水浒连环画是一个动人心弦的新发现。《世界报》表示,‘连环画’是一种既富有创意又具启发性的形式,让我们在宋江起义故事中欲罢不能。”同时,该报道指出,“法文版中国传统连环画《水浒》首次印刷2 500套出版后一个半月售空,是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法国媒体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关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处,2013)。
不难看出,无论《西游记》的歌剧改编,还是《水浒传》的连环画出版,都是中国古典名著在海外传播历程中创新且颇有成效的尝试,其成功得益于生动多元的文本阐释与表现形式,同时也深刻展现了文学接受的时代诉求,促使古典名著的生命在当代接受中迎来崭新的绽放、实现最新的展开。这样的“变形”与“新生”无疑具有启发意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介与传播中,如何在传统的文本翻译之外,结合时代语境合理采用异域接受者喜闻乐见的鲜活方式引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进而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并“走进去”,形成中外文化之间真正的交流互鉴,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正如《猴: 西游记》导演陈士争所明确意识到的,“要想让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首先要用吸引他们的方式将其引进门。而音乐、动画、服装等视觉形象和国际语言都为来自不同文化的观众提供了较为宽泛的切入点,让他们在欣赏异域文化时没有陌生感和语言障碍,不分男女老幼都能接受这部中国传奇”(马桂花,2007)。
翻译始终与时代共生。总体上看,在新技术与新媒体空前发展、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日益丰富而多元的今天,文学译介与接受不可避免地体现时代特色、彰显时代诉求。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审美距离是决定文学作品被接受程度的重要因素。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在其出现的历史时刻,对它的第一个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这种方法明显地提供了一个决定其审美价值的尺度。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的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姚斯、霍拉勃,1987: 31)。如果审美距离过大,接受者便难以对作品产生共鸣,作品的传播和接受也将随之受到限制。就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外译而言,当下的异域读者早已远离古典名著诞生时的社会历史环境,而语言文化隔阂又使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被再度强化,这必然给文学接受造成巨大的困难。因此,关注审美期待与文学接受的时代诉求,在文学译介与传播中适当融入易于沟通中西文化、拉近审美距离的时代元素,赋予文本在新的历史时空得以“新生”的无限可能,以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在当前时代语境中更切实有效地走向世界,这在新时期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中既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也应成为一种理性的共识。
四、 “异”的考验: 文学接受的发展性
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经典文学著作在海外得到译介,翻译的重要性受到各界的空前关注,有关文学译介与文化传播的问题也引发了学界的普遍重视。在这一背景下,翻译方法和翻译忠实性问题成为学界探讨的焦点,其中不乏争论与质疑。有学者认为“连译带改”的翻译方法太不严肃,经“改头换面”而成的“象征性文本”无法展现真正的中国文学,只能导致对中国文学的误读、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因而也有悖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初衷。同时,也有学者和媒体以当下的市场销售和读者接受情况等为依据,对严肃文学与经典文学的译介提出质疑,对以忠实性为原则的翻译方法和翻译观念多有诟病。面对诸如此类质疑的声音和颇有争议的观点,如何立足于文化双向平等交流的立场,理性看待翻译忠实性原则与文学接受、文化传播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关系,这在推进中国文学译介,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古典文学名著外译中,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及的,翻译活动涉及两种语言与文化,受到文本内外多重复杂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语言的差异性、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两种语言文化间无法存在“完全对应的同时代性”(Meschonnic, 1973: 310)这一事实都决定着面临种种“异”的考验,翻译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而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但以历史的目光来看,任何既定历史阶段的要素都不是固化的,只要时代在演变,翻译所赖以进行的各种关系与各种条件就必然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无论关系的更新还是条件的积累,都将为翻译的发生与成长提供直接可能,促使翻译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接受环境、集体规范、审美期待等,伴随着翻译自身的成长,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也将面向自我与他者关系范围内的无限可能性,呈现出鲜明的发展性特征。
考察《红楼梦》在法国的译介,我们看到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法国走过了一条从陌生到熟悉、从误解到认同的曲折发展之路。法国对《红楼梦》的译介最早可以追溯到1912年法国汉学家莫朗(Georges Soulié de Morant)在其所著的《中国文学论集》中选译的小说第一章片段;其后,数位中法学者对《红楼梦》的部分章节进行了摘译;1957年法国翻译家盖尔内(Armel Guerne)根据德译本转译出版了《红楼梦》节译本;1981年由华裔翻译家李治华与法国妻子雅歌共同翻译、汉学家铎尔孟(André D’Hormon)校译的首个《红楼梦》法文全译本问世,至此,这部中国文化经典之作终于以完整的样貌进入法国读者视野。
伴随着从摘译、转译到最终实现全译的漫长译介历程,《红楼梦》在法国的接受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深化的过程。实际上,在首次摘译前,这部中国文学史上的旷世巨著就已得到部分法国作家和学者的关注,但他们对作品的理解明显存在某些片面乃至极端的观点。例如法国作家达利尔(Philippe Daryl)认为,“中国文学中有大量色情而淫秽的文学作品,这些叙事作品通常都配有彩色插图,其中最为流行的便是《红楼梦》(LesRêvesdelachambrerouge),其销量达到数百万册”(Daryl, 1885: 190)。将《红楼梦》理解为“色情而淫秽”的文学作品显然有失偏颇,但应该看到,在当时法译本尚未问世的情况下,达利尔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无疑是受到清代中国文人对《红楼梦》负面评价的影响。此后,多位留法中国学者或撰写文章,或出版专著,对《红楼梦》的故事内容、文学价值以及曹雪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加以详尽介绍,对促进作品在法国的传播与接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法国学界对于《红楼梦》的关注与理解也日益深入。例如1937年埃斯卡拉(Jean Escarra)在其著作《中国与中国文化》中将《红楼梦》评价为一部“著名小说”(郭玉梅,2012);1964年法国出版的《大拉鲁斯百科全书》第三卷认为《红楼梦》这部“极为成功的小说”“内容广泛,意趣横生,语言纯洁,充满诗情画意,心理描写也十分深刻”(陈寒,2012);20世纪70年代法国《通用百科全书》对《红楼梦》的把握则更为准确:“《红楼梦》既不是一部描写真人真事的小说,也不是一部神怪小说或自传体小说,这是一部反映18世纪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现实主义古典作品”(同上)。1981年,李治华《红楼梦》全译本的问世无疑对推动这部文学经典在法国的传播与接受具有决定性意义,法国书评专家布罗多(Michel Braudeau)在《快报》上撰写评论文章,认为“全文译出中国五部古典名著中最华美、最动人的这部巨著,无疑是1981年法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现在出版这部巨著的完整译本,填补了长达两个世纪令人痛心的空白”(郭玉梅,2012)。从“色情小说”到填补法国翻译文学史空白的经典巨著,《红楼梦》在法国读者眼中的形象发生了质的转变,这一“华丽转身”及其背后的曲折历程,一方面源自“异”的考验中翻译自身的成长与完善,另一方面也清晰地展现出翻译可能性不断拓展所实现的文学接受的深入与发展。
翻译是一个由一系列选择贯穿其间的过程,这种种选择都是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产物,既取决于译者对翻译活动的认识与理解,也与时代对翻译的需求及其为翻译提供的可为空间密切相关。而无论自律还是他律,都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必然在过去与未来、局限与拓展之间的连续发展演变中得以确立。因此,翻译无“定本”,文学接受对特定历史语境所带来的有限可能性的突破不是偶然的,而是持续而永久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复译应文学译介与文化交流的呼唤而生,其必要性体现在丰富理解、更新表达、增强时代气息以及满足读者不同审美需求等不同层面,但就其根本而言,复译所承载的乃是文本生命生成的一种内在需要。仍以《西游记》的译介为例,林小发的全译本首次将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完整且尽可能忠实地呈现在德国读者面前,无论就《西游记》本身的译介与传播而言,还是就中德文学与文化交流而言,这无疑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然而,有学者撰文指出,林译所参考的底本《西游证道书》是“一部删节评改本”,并非《西游记》的善本,认为“林小发译本采纳《西游证道书》的思想立意,不能全面、准确反映《西游记》的‘丰富性、多样性’文化内容”(竺洪波,2017)。这一质疑同样揭示出,翻译不可能有所谓的定本,“译本对于原作的生命‘馈赠’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而只能在不断延续与更新的过程中趋向原作生命之真”(刘云虹,2017)。文学译介与接受只有处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中才能推动文学作品本身意义的不断丰富,也才有可能实现文学作品生命的生成与延续。
中西方文化接受上的严重不平衡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接受语境和读者接受心态两方面存在的显著差距至今仍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基于此,就目前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外译而言,我们应认识到,在保留并传达作品中文化异质性与尽可能消除文化隔阂进而促进更为深入有效的文学接受这两者之间,需要某种程度的权衡与妥协。正如许钧所指出的,“在目前阶段,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译者在翻译中有必要对原著进行适当调整,使之在更大程度上契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期待视野”(许钧,2014)。而另一方面的客观事实在于中外文化间的相对关系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平衡状态正在不断得到改善,西方读者对异质文化的态度更加包容与开放,将不再满足于“改头换面”式的翻译,中国文学也将以更为“本真”的姿态走入西方读者的视野。莫言作品的主要法译者、法国汉学家杜特莱(No⊇l Dutrait)曾明确表示:“法国读者希望读到的是一部中国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适合他口味的文本”(刘云虹、杜特莱,2016)。因此,我们要充分意识到文学接受的发展性,以历史和开放的目光来看待目前文学译介中面临的挑战、遭遇的困难,避免将任何为“现阶段”需要而采取的翻译方法与策略模式化、绝对化,同时警惕功利主义的翻译观,从而将文学译介真正置于文化双向交流的长期目标和宏观视野下加以把握。
五、 结语
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不在于瞬间的绽放,文学的经典性必然在每一次当下的阅读、阐释与接受中历史性地生成。翻译是作品生命延续与传承的一种根本性方式,为作品开启其“来世的生命”。正如本雅明所言,“在译文中,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最新的、继续更新的和最完整的展开”(本雅明,2005: 5)。而从本质上看,文学翻译是一个由生成性贯穿始终的动态系统,以自身生命在时间上的延续、在空间上的拓展为根本诉求,永远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因此,在文学作品生命经由翻译而得以展开的生成过程中,文学接受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它与文学翻译本身一样,始终处于不断更新与完善、不断丰富与发展的历程之中。通过上文对四大名著外译中代表性案例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就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外译而言,无论译介、传播还是接受,都并非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的,而是随着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文本内外多重要素的演变,在不断减少与克服“异”的考验所带来种种翻译障碍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清晰的历史发展趋势: 从节译、改写到全译,从不忠实到相对忠实,从形式单一到形式多元。只有充分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外译的生成性接受及其具有的阶段性、时代性与发展性特征,才能以历史的目光,更加理性地把握翻译永远面向未来、面向其存在之真的生成历程,进而更加切实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