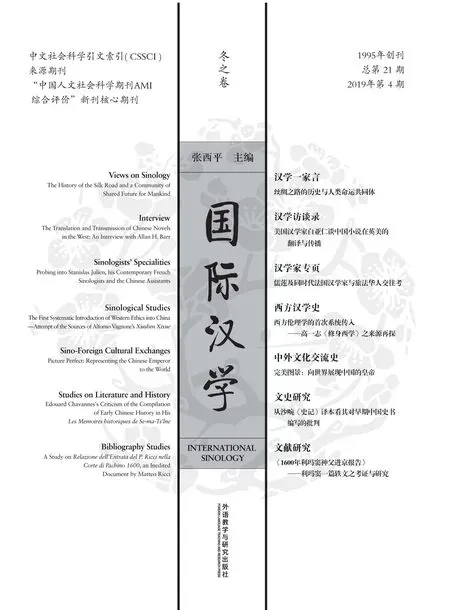英语学界中国文学教材中的《水浒传》管窥
2019-12-17王文强杨勇彪
□ 王文强 杨勇彪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中国文化形象在西方世界的塑造与传播有着现实的意义。英语学界的中国文学教材是文学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教材(文学史、文学概论、文学选集)的收录和改写是文学作品经典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而跨文化的文学教材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方式。”①江帆:《经典化过程对译者的筛选——从柳无忌〈中国文学概论〉对〈红楼梦〉英译本的选择谈起》,《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2期,第20—35页。然而,这种方式却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文化评论者、文学史编著者、翻译学者所忽略。
《水浒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作者施耐庵以其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和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创造出众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并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英雄形象。正是因为《水浒传》本身所蕴含的艺术价值,自1901年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问世至今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英语学界的中国文学教材始终保持着对《水浒传》的关注和评论,因此《水浒传》得以进入英美大学课堂,这对推动作品本身在海外的传播有着深远的意义,“高等教育的普及使文学经典化以最有力的形式表现出来。当出版机构与高等教育机构紧密而有力的合作时,经典化就是其最富有表现的典范。”②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s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p.22.《水浒传》出现在英美大学的文学教材中,这是最明显、最有效的经典建构形式,也让更多的读者接触到《水浒传》,大大提高了它的知名度。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1933年赛珍珠(Pearl S.Buck, 1892—1973)翻译的《水浒传》(All Men Are Brothers,1933)在美国出版后,在欧美风靡一时。“从中国杀将过去的这批梁山好汉, 一下子就蹿上了美国权威的每月图书俱乐部的排行榜。”③龚放、王运来、袁李来等:《南大逸事》,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230页。可见,赛珍珠的《水浒传》英译本在西方世界有着广泛的读者和较高的声誉。然而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教材却很少选取这个译本的翻译片段作为介绍《水浒传》的材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专业读者”对赛珍珠译本的质量并不满意。
依据英语学界中国文学教材对《水浒传》的相关介绍、评价和分析,我们认为,大体上可以将这段历史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早期、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三个阶段。
一、20世纪早期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中的《水浒传》
自19世纪下半叶,随着在华利益的不断扩大,英国政府需要更多通晓汉语并熟悉中国国情的“中国通”。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的汉学研究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涌现出一批一流的汉学家,并出版了大量具有影响力的汉学著作和译作。可以说这一时期英国已经取代了法国,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尽管《中国文学史》是翟理斯的个人著作,但我们仍然可以把它当作19、20世纪之际英国汉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翻译的总结性著作。
翟理斯是西方现代汉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与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和理雅各(James Legge , 1814—1897)并称为英国汉学“三大宗师”。他的《中国文学史》于1901年由伦敦的威廉姆·海涅曼出版公司(William Heinemann Publisher)发行。这本著作首次以文学史的形式,向英语读者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风貌,为传播中国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它基本上按照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把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分为八个时期。其中,《水浒传》被放置于第六部分的第三章“元代小说”中,并与《西游记》《三国演义》放在一起探讨。翟理斯认为中国小说题材可以基本分为四类:一是涉及篡权与诡计,二是涉及爱情与阴谋,三是涉及封建迷信,四是涉及土匪与暴徒。①Herbert A.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1, p.276.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作者当时所接触的原始资料有限,翟理斯的这部文学史存在着很多以偏概全、不符史实的论断。②例如,翟理斯将屈原的《卜居》《九歌》统称为《离骚》,实际上它们应该属于《楚辞》。再比如,他将《西游记》划为元代小说,实际上《西游记》成书于明代中叶。在对《水浒传》的介绍中,翟理斯首先简单地探讨了《水浒传》的作者和起源,然后用简洁的文字概述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这一章节,翻译为中文如下:
这部小说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章节,一个亡命之徒(swashbuckler)皈依佛门做了和尚。过了不久,他就难以忍受这种清苦的生活方式。有一天他烂醉如泥般地回到寺庙,这一丑行引发了轩然大波。第二次他又故伎重演,结果被众僧人关在门外。因为责怪山门下的金刚巨像不帮他开门,于是他把这巨像砸得粉碎。最后,他以放火烧寺来胁迫众僧人开了门。进门之后,他就醉倒在僧堂里,这时候从他的僧袍里滑出半条啃过的狗腿,于是他扯下狗肉直接塞进一个和尚嘴里,以此取乐。③Giles, op.cit., p.281.
最后,翟理斯高度评价了《水浒传》,他认为:“这部小说不仅生动形象,而且宏大壮丽,对人物的塑造可以说栩栩如生。虽说语言上接近于白话,然而这并不足以损害其经典的地位。”④Ibid.
二、20世纪60年代英语学界中国文学教材中的《水浒传》
“二战”爆发后,美国出现了大量与亚洲研究相关的教育研究机构。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对东方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中国诗歌与小说这两个体裁。然而,由于缺少这一领域最前沿、最全面的的研究资料,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对中国文学的阅读兴趣。”⑤Ch’en Shou-yi,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 Ronald Press, 1961, p.vii.20世纪60年代,相关研究机构数量激增,“十年之内,能够颁授东亚语言和研究专业学位的大学迅速增加到70年代初的一百零六所。”⑥于子桥、刘宁、唐奇芳:《2000年美国东亚研究现状》,《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3期,第135—141页。
在这一时期,亚洲研究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学者们开始深入探讨中国文学作品的背景信息、社会意义、普世价值,试图从深层次发掘作品的人文信息和史学涵义,这使美国的汉学研究从广度、深度、研究成果方面,都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面貌。另一方面,一些著名的英国汉学家离开本土,来到美国继续从事汉学研究,其中包括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1883—1956)、白之(Cyril Birch)、韩南(Patrick Hanan, 1927—2014)等著名汉学家,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中心逐渐由英国转移到了美国。这一时期,英语学界专业中国文学教材大量涌现。与美国相比,此时的英国汉学研究出现了些许滞后。这一时期,在英国本土发行的中国文学教材只出现了一部,那就是黎明(Ming Lai, 1920—2011)于1964年编写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64)。
1959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由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 1919—2017)主编的《东方经典文学探讨:通识教育中的亚洲文学与思想》(Approaches to the Oriental Classics, Asian Literature and Thought in General Education,1959),该著作是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论文集。在这部论文集中,梅仪慈(Yi-tse Mei Feuerwerker)撰写的《中国小说》(“The Chinese Novel”,1958)部分详细介绍了《红楼梦》《西游记》和《金瓶梅》这三部中国古典小说。然而,她却将《水浒传》故意忽略了。梅仪慈给出的原因是:
《水浒传》(赛珍珠将其译为All Men Are Brothers)这部作品在中国广为流传,深受中国人的喜欢。然而我很遗憾地在本文中将其忽略了,原因在于:现今的一些《水浒传》英译本,尽管译者在某些程度上翻译得非常认真,然而它们不仅不能充分表达这部小说的内涵,甚至可以说歪曲了《水浒传》的精神与气质。①Yi-tse Mei Feuerwerker, “The Chinese Novel,” Approaches to the Oriental Classics: Asian Literature and Thought in General Education. Ed.Theodore de Barr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184.
可见,梅仪慈对赛珍珠的《水浒传》译本质量并不满意。
1961年,美国波莫纳大学(Pomona College)教授陈受颐 (Ch’en Shou-yi, 1899—1977)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述》(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1961)由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Ronald Press Company)发行。林语堂作序时对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本著作将会保持其英语学界中国文学史权威之作的历史地位。”②Lin Yu-tang , “Foreword,” in Ch’en Shou-yi,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p.V.在本书第24章“早期白话小说”中,作者介绍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介绍《水浒传》的篇幅约为5页。书中讨论了《水浒传》的版本及其演变、作者和成书时间等问题。陈受颐认为《水浒传》的真正作者是罗贯中,而非施耐庵。他的依据是:
最早出现的《水浒传》(明高儒《百川书志》)中赫然写着“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然而,至于施耐庵何许人士、他是否与罗贯中生活于同一时期,这些问题我们无从知晓。因此,可能情况是这样的:施耐庵的原著是未能发行的手抄本,因为在罗贯中的《水浒传》以印刷形式发行之前,从未有人提及以印刷形式出版的《水浒传》。从当今流行的115回版《水浒传》的行文风格来看,即使是普通读者也能察觉出它与《三国演义》的相似性。③Ch’en, op.cit., pp.474—475.
同时,陈受颐认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与《三国演义》相比,“罗贯中的写作技巧明显更上一层楼。他笔下的人物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对艺术效果敏锐的洞察力让他在小说叙事情节的安排上炉火纯青。”④Ch’en, op.cit., p.475.为了证明这一说法,他选取原著第32回“宋江夜看小鳌山”中的两段作为论据。这部文学史还存在一个显著特征,除一小部分内容直接选取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翟理斯、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1881—1968)等西方知名汉学家的译文以及胡适、林语堂、吴经熊等中国学者的译作以外,文中绝大部分节选都是由陈受颐本人翻译,这其中就包括作者所节选的《水浒传》的上述章节。
1964年,伦敦卡塞尔出版社(Cassell & Company Ltd.)推出了黎明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该著作第13章为“明代小说”,作者首先详细介绍了白话小说的起源,其后分别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为例来介绍历史小说、冒险小说、神话小说和写实自然小说这四类中国古典小说题材。他这样介绍《水浒传》:
这部小说讲述了108个英雄好汉因不堪被当时恶劣的环境所压迫,而被迫在梁山泊落草为寇的故事。同当代惊险小说和西方小说一样,这部作品充满着活力。然而,除李逵、鲁智深、武松这几个英雄人物以外,作者对其他梁山好汉的刻画不够细致,他们中的很多人很明显是被作者生硬地拖进了36“天罡星”与72 “地煞星”中。另外,作者对吴用和公孙胜的塑造过于呆板……小说中还存在着一些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尽管有这些缺点,这部小说依旧在中国脍炙人口,中国人尤其喜欢武松、鲁智深、李逵这几个人物,因为他们一向爽直、冲动,喜欢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①Lai Ming,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London: Cassell & Company Ltd., 1964, p.294.
为了让读者体验这些英雄人物的性格特点,以此来加深他们对小说的理解,黎明选取了金圣叹70回本《水浒传》的第25回“供人头武二设祭”这一部分为例,译文采用的正是赛珍珠《水浒传》英译本的相关内容,可见他对赛珍珠译本的肯定。
自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汉学界先后出版了多个中国文学的英译选集,以文选的形式展现中国古典文学的面貌,为英语读者了解中国古典文学提供直接的门径。1965 年,白之编译的《中国文学选集:从早期至14 世纪》(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1965)由纽约“丛树出版社”(Grove Press)出版。他这样评论《水浒传》:“这部小说的情节精彩纷呈,对好汉的塑造更是生动形象……把《水浒传》当作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它来源于大众文化,小说中粗俗的白话、危险的信息都阻止了它成为严肃文学的可能性。”②Cyril Birch,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p.450.
在选材方面,白之指出:
在选集中,我们排除了那些用毫无生命力的英语翻译而成的作品或被毫无生气的学术所损害的译作,不管这些作品以前有没有发表过……我们当然希望选集具有适当的代表性,但是我们不会冒险让一位一流作家穿着不合适的衣服出现在读者面前。③Ibid., p.xxv.
由此可以看出,白之选择作品的标准主要是看译文的文学性与流畅性,故排除了在语言上具有高度准确性、但是可读性却不强的赛珍珠译本。白之选取120回本《水浒传》“智取生辰纲”的故事(14—16回),按照流畅通顺的翻译原则,由他本人亲自翻译。
1966年,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教授柳无忌(Wu-chi Liu, 1907—2002)编写的《中国文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1966)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出版。柳无忌在该著作中的第14章《民间史诗性的长篇小说》(“The Novel as Folk Epic”)中,详细介绍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作品。他指出:“如果说《三国演义》在情节建构上具有历史连贯性的话,那么《水浒传》之所以取得如此丰硕的艺术成就,其关键就在于作者对社会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m)的精致刻画上。”④Liu Wu-chi,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204.对于《水浒传》的创作手法和艺术特色,柳无忌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水浒传》把它的目的放在描写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事件和人物上。在这些精彩的故事里,每一个细节都丰富多彩、与众不同,作者用巧妙的艺术手法将这些故事组合成一部完整的作品。因此,这部小说在规模的广阔与内容的包罗万象上达到了某种统一性。⑤Ibid.
作者选取赛珍珠英译《水浒传》第23回“景阳冈武松打虎”和第43回“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作例子,对照和比较这两位英雄的英勇行为。他指出:“在这两个故事中,这两个英雄都显示出无比的勇气和高超的武艺,然而他们打虎的情景和方式却大相径庭,这种不同甚至表现在细微末节的层面上。”⑥Ibid., p.207.最后,柳无忌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进行了高度评价:
这两部作品在规模的宏伟和内容的深度上,可以与希腊和印度的史诗相媲美……几代艺术家把他们的生活经验、社会知识和创作才华都灌注到这两部小说中,这些因素让《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学丰碑。①Liu, op.cit., p.212.
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夏志清(C.T.Hsia, 1921—2013)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1968),在这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夏志清主要探讨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这六部中国古典小说。在本著作的第三章中,作者对《水浒传》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夏志清认为:
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至少在两个大的方面发展了中国小说的艺术性:一是对白话文体的大量采用;二是在精心塑造人物、巧妙铺陈故事时,大大摆脱了史料的束缚……《水浒传》以真实的日常生活为背景,细致地描绘出了江湖豪杰的英雄故事。与《三国演义》相比,它具有更加生动的现实主义特色。②C.T.Hsia, 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75.
此外,夏志清对《水浒传》里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阴暗面进行了深入的心理研究,如对武松在鸳鸯楼的野蛮滥杀,杨雄在翠屏山对妻子潘巧云的残忍虐杀进行解释和批判。为了更深入地探讨小说中的复仇主题,夏志清拿《水浒传》与冰岛传奇小说《恩加尔传奇》(Njal’s Sage,1960)做比较,他认为二者有两方面的不同:
一是这些传奇小说的作者是拥护和平秩序和正义的,而《水浒传》的作者则对正义态度模糊、对残忍的暴力行为津津乐道。二是《水浒传》存在着严重的“厌女”倾向,而冰岛传奇的作者们却把妇女的这种反叛性和复仇心看作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甚至对她们的泼辣和任性表示尊敬。③Ibid., p.76.
夏志清引用《水浒传》中的片段多达9处,这些内容的英译皆由他自己完成。需要指出的是,夏志清首次在英语中国文学教材中对《水浒传》中一些“好汉”精神世界的阴暗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海外汉学家对《水浒传》的评价。
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英语学界中国文学教材中的《水浒传》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与英语世界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日益扩大,这促进了新时期英美汉学研究的新发展。1987年,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汉学系教授浦安迪(Andrew H.Plaks)推出了自己的专著——《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1987),详细探讨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金瓶梅》这四部小说。1994年,由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1994)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进入21世纪以来,英美一流的汉学家合作成为主流,在文学史的编纂模式上逐渐由个人独著转向集体合作,先后诞生了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01)与《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10),这两部著作标志着英美的中国文学研究达到了新高度,它们对《水浒传》的研究更加全面、细致、成熟。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认为,反讽修辞艺术在明代小说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像稍后时期欧洲小说文体的情况那样,是一把具有两面刀锋的利刃:它一方面产生出一些主要用来削弱通俗文化对英雄人物的意向褒贬偏情的作品,与此同时,它又带有树立某种正面形象的必要含义。有关《水浒传》的内容被安排在著作的第四章。浦安迪指出:“《水浒传》对于扩大和丰富白话文学语言,并使之成为精湛的散文小说媒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尽管一般人误认为该小说用语纯属白话,但事实上作品是用各种不同层次文白杂用的措辞写成的。”④Andrew H.Plaks,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18.与夏志清认为《水浒传》着重反映中国传统心理状态的阴暗面不同,作者从本书的“反讽”手法出发,认为:
该小说的主旨既不盲目赞美梁山精神而忽视其不祥含义,也不一概否定绿林好汉所代表的一切,而基本上是持一种暧昧的态度……小说在描绘人们阴暗面的同时,也着力刻画了一批正面人物形象和理想观念,使读者对所描述的事件蕴意可以有一个均衡的了解。①Ibid., p.320.
作者以武松、李逵、鲁智深、宋江这些人物为例,对繁本《水浒传》特有的反讽手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拿一些具备“完美典范”的真正英雄好汉——林冲、秦明、朱仝、关胜、呼延灼、杨志作例子,指出他们被“逼上梁山”往往并不是像这个词语的通俗观念一样事出无奈,而是被宋江、吴用等人通过劫持或者阴谋陷害的方式强迫入伙的,这使小说更具有反讽的色彩。他得出的结论是:“小说作者通过塑造一系列体现中国传统英雄观念的正面人物,来抗衡前面这些主人公的阴暗面。”②Ibid., p.344.
关于《水浒传》的介绍出现在《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集》的第四部分“虚构文学”的“长篇小说”中,梅维恒选择《水浒传》第23回作为选译内容。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1945—1996)指出:“只要翻译文学在早期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经典化,新的选集就会接受这些正在出现的经典,并试图颠覆或者扩大这些经典。”③Lefevere, op.cit., pp.126—127.《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集》正是一部极力拓展文学定义并颠覆经典作品的选集。在对《水浒传》的选译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部文学选集不同寻常的“反经典”特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集对金圣叹点评文字的英译保留上,二是对新译者的选择上。就第一个方面来说,梅维恒选取“景阳冈武松打虎”这个章节,并细致地保留了金圣叹的文本点评,以斜体字标出,从而确保了译文的完整性。梅维恒解释了选择金圣叹点评本的原因:“在《水浒传》所有的点评本中,金圣叹点评版最为人所知。从这一章节可以看到,金的点评(括号内的斜体部分)形象生动、独具一格,它最大程度上提高了读者对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的鉴赏能力。”④Victor H.Mair,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997.
这部选集另一个“反经典”的重要特性表现在对新译者的选择上。梅维恒不同寻常地指出:“选集的第四个目的在于选择一些新译者的译作。我不想看到本选集重印那些经常被其他文学选集收录的翻译作品,除了选择一些经典译作,在此选集中,译者的译作必须要符合21世纪之交的读者的精神与需要。”⑤Ibid., pp.xxiv—xxv.梅维恒并没有从赛珍珠《水浒传》译本⑥截至1994年,英语世界已有三个《水浒传》英语全译本,分别为赛珍珠的All Men Are Brothers(1933)、杰克逊(J.H.Jackson)的 Water Margin(1963)、沙博理(Sidney Shapiro)的 Outlaws of the Marsh(1980)。中选择“景阳冈武松打虎”这一回合,而是选取并不知名的译者约翰·王(John Wang)的译文,体现了梅维恒刻意打破“经典”的编选动机。
201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梅维恒主编的另一重量级著作——《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为中国文学专业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尽可能地提供广博且可信赖的基本信息。编选者包括柯慕白(Paul W.Kroll)、施寒微(Hlwig Schmidt-Glintzer)、白安妮(Anne M.Birrell)、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等当代知名汉学家。关于《水浒传》的相关评论出现在第四部分“小说”中的第三十五章“章回小说”这一章节中。该部分由哈佛大学李惠仪(Wai-yee Li)撰写,作者认为《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存在着密切联系:“《水浒传》中的盗匪英雄,从姓名、绰号到长相、脾气,乃至于所用的兵器,都可溯源于《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二者都强调私人之间的结拜关系,重视‘忠义’和‘大义’。”⑦Victor H.Mair,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626.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三国演义》赞同儒家政治秩序和正统思想,而《水浒传》显然更认可建立在秘密社党的道义基础上的反政府或反文化心态,表达了对当下社会政治秩序的蔑视。”⑧Ibid., pp.626—627.作者对梁山泊“替天行道”的口号提出了质疑,她指出:
对此世界的进一步审查,暴露出并无更高尚的正义可言……快意恩仇,在此被提升为最高等级的正义,却实际退化为嗜血的欲望。总体来说,小说中存在着大量肆意、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行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好汉几乎以屠戮为乐趣。①Ibid., p.630.
201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该书由来自世界知名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主)的17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集体参与编写,如伦敦大学的贺麦晓(Michel Hockx)、哈佛大学的李惠仪、耶鲁大学的吕立亭(Tina Lu)、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Shang Wei)等。这本著作是剑桥大学出版社“世界国别文学史”系列的一种,自出版以来广受好评。有关《水浒传》的评论被编入孙康宜撰写的第二卷第一章“明代前中期文学”第三部分“中晚明之际的文学(1520—1572)”中,孙康宜介绍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三部作品,她认为这三部作品都经历了长期的民间口头流传以及文字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们都经历了“英雄主义的重写”(rewriting heroism),即“这些小说的作者在将早期的口头流传素材润色改造成一部精美通俗小说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新的英雄主义。依照这种英雄观,善恶的分界变得愈加模糊不清。”②Kang-I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Vol.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51.而英雄的观念在《水浒传》中更加矛盾,更有争议性。作者指出:
施耐庵描写这些英雄时,他本人的英雄观念有着很大的分歧,以至于这种矛盾特征会出现在他笔下的同一个英雄身上。这些“好汉”一方面坚决反对腐败的政府,并且坚守兄弟情义,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杀人施暴、冷酷残忍至极……这样的情节反复出现,对现代读者造成了深深的困扰。③Ibid., p.54.
我们发现,孙康宜“矛盾英雄观”的观点与夏志清对《水浒传》中这些梁山好汉的评价有着一致的看法,即“英雄之于恶魔,有时难以区分”。④Ibid.
结语
英语学界中国文学教材对《水浒传》评论、研究的整个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早期,集中体现在翟理斯于1901年在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对《水浒传》的介绍上。然而,翟理斯对《水浒传》的认识和了解仅限于一般水平,对它的介绍较为粗略、简单。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美国研究东亚文化的机构数量激增,高校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专业读者的阅读期待和需求促成了这一时期“专业中国文学史”的诞生。与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相比,它们对《水浒传》的介绍更为专业、系统、准确。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史在书写上呈现出鲜明的“合作”特点,这些中国文学史的参编者人数众多,由相关领域最为权威的海外汉学家执笔,其中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最具代表性。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文学教材相比,它们的学术性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可以说全面、细致、成熟地反映了中西学界对《水浒传》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