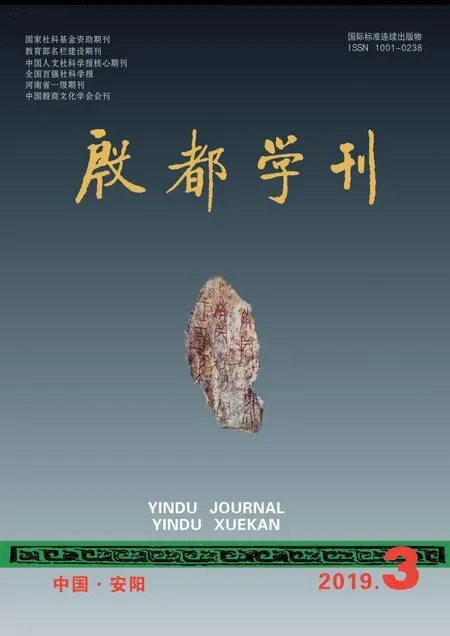法式善论体散文刍论
2019-12-16李艳丽
李艳丽
(1.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0;2.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法式善(1753-1813),蒙古正黄旗人,原名运昌,后依诏改名法式善;字开文,一字梧门;号时帆,又号陶庐,自署小西崖居士;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著有《存素堂文集》[1]、《存素堂文续集》[2]。由于同时代人多关注其“诗龛盟主”的显著身份及其诗作的杰出成就,而对其散文及笔记类作品往往重视不够,这也间接导致了其文名为诗名所掩的现象。其实法式善散文具有很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很高的文学成就,正如其友人吴锡麒所言,“其诗之见于世者,人得而信之;其文之未见于世者,人且闻而疑之”[1](吴锡麒序);又如刘锦藻所论,“虽无宗派家数,亦无愧古文家之正法眼”[3](卷二百七十七,经籍考二十一)。然而,关注其散文成就者毕竟为数不多,这应是法式善文学研究和民族文学研究之憾事。鉴于此,笔者有志于法式善散文研究,以期弥补法式善研究的一些缺憾。而本文则专选《存素堂文集》中以“论”名篇的散文,姑且称之为“论体散文”,笔者主要从文体学角度进行探讨研究,揭示法式善的思想主张及其散文章法手段等。法式善论体散文虽仅有8篇,数量并不多,但其成就绝不容低估。法式善的8篇论体散文中,史论2篇,人物论6篇。因为法式善本身并非史学专家,他以学者士大夫的身份,来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讹谬”[4](P43),因此,其论体散文能够突破史家传统和史书模式的樊篱,另辟蹊径,独出心裁,于是从论题主旨到篇章结构,再到行文抒写,都能够做到收放灵活,挥洒自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一
文以载道,自古而然。文章是思想的载体,作者的思想倾向会通过文章表现出来,因此法式善论体散文自然体现着其思想主张。分而论之,则有以下五点值得注意:
一是主张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思想是儒家学说的传统命题。但法式善生活的年代,却是“经世致用”思想逐渐淡出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乾隆末期吏治败坏,八旗子弟没落腐朽,社会矛盾丛生,乾隆帝却堵塞群臣挽救时弊之议,很多官员因此逐渐放弃了进言献策。但集学者、官员、文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法式善,却能不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仍然在自己的散文中,着眼于古今际会,历史变迁,治乱兴衰,将清初学者倡导的“经世致用”传承了下来,体现出一种救世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
法式善的这种由“经世致用”而“救世”的思想主要来自于顾炎武和李东阳[5](P56)。
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学者倡导“经世致用”并掀起了一股思潮,而且影响深远。法式善在《槐厅载笔》《陶庐杂录》[6]《存素堂诗初集录存》[7]中多次提及顾炎武及其《天下郡国利病书》,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顾炎武及其思想的崇仰之情。这种情感在其论体散文中,也表现得很充分。在《唐论》一文中,法式善提到了唐代君王因为没有做到“防微杜渐”,最终酿成大祸,这实际上也是在为清代统治者敲警钟:“故人皆谓唐之乱亡,由于方镇之跋扈;方镇之跋扈,由于宫掖之不肃清;宫掖之不肃清,其端皆起于太宗。太宗能以功烈盖父之愆,除乱致治,比隆汤武,可谓英主矣。至于以宫妾兴,以宦官废,未能逆睹,寻其终始,有足感者。防微杜渐,君子所以兢兢也哉”[1](卷一)。文章表面说唐,实则论清。法式善从根源上剖析问题,认为唐太宗虽然“以功烈盖父之愆,除乱致治,比隆汤武”,但由于早期对“宫掖”采取任由发展的态度,致使祸及几代,最终难免导致亡国。法式善希望清代统治者能够从中吸取教训,真正做到防微杜渐,从源头上杜绝那些危害政权稳定的现象,防患于未然,以保国家长治久安。
法式善的这种由“经世致用”而“救世”的思想,还与李东阳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式善对于明代前贤李东阳的敬慕,几乎时人无不知晓。查揆在诗中指出:“诗龛高会等无遮,载笔槐厅已满家。虾菜亭边闲得句,一生低首李长沙。”[8](诗钞卷九)法式善甚至将自己的诗龛就建于李东阳故居。法式善曾亲自寻得李东阳墓地所在之地——畏吾村,他在《明李文正公年谱》中还记录了自己发现墓地的全过程[9](卷五)。光绪年间《顺天府志》还写到法式善为李东阳修订年谱之事,“因采集各书编为七卷,前五卷唐仲冕校补,后两卷谢振定校阅,于东阳事迹搜采无疑”。大兴朱珪甚至称法式善为“西涯后身”,一时间这一称呼流传甚广,而法式善本人也很乐于接受这个称号。法式善一生写有关于李东阳的很多诗篇和文章,如诗有《西涯诗》《题白石翁移竹图后》等十余篇;文有《李东阳论》《西涯考》《西涯图跋》等数篇,就连“诗龛”十二像中也有“西涯像”。自嘉庆二年(1797)始,每年李东阳生辰,法式善都召集文友为东阳作寿诗,并时常向人索要“西涯图”及题图诗。由此可见,法式善思想、行为接受李东阳的影响之深,当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影响自然包括李东阳的经世致用思想。法式善曾亲自疏奏嘉庆帝“六事”,“己未春上疏,请旗人屯田塞外事,上以为违祖制,降官编修”[10](卷九),甚至落得个“照溺职列,一革职,以示惩处”的下场,而这种情况与戴殿泗《风希堂诗集·法时帆祭酒示西涯诗属和》中描写的李东阳当年“保全善类”与“条陈十事”的举动极其类似[11](诗集卷五翰苑稿)。再加之,致力于纠正明初台阁体书风的李东阳一直强调明理载道、经世致用,这与法式善的思想也是相似的。
二是坚持廉政为民。
清代中期,廉政为民思想还是主流,《渊涧类函》中就记载了相关内容:“景公问:‘廉政何如?’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其浊无不涂,其清无不洒。’”[12](卷三十地部八)类似的观点在《清经世文三编》《通鉴辑览》等文中也大量存在。法式善作为参与修撰《四库全书》的唯一一位蒙古族官员,对此必定非常清楚,理解甚深。法式善一生,经历两朝皇帝:乾隆和嘉庆。乾隆帝早年以励精图治、廉政为民而闻名;嘉庆帝在继帝位第二月,即颁布谕旨,杜绝了乾隆晚年兴起的进贡奢靡之风。可见,法式善的“廉政为民”的思想与时代风气也是密切相关的。
法式善《宋庠包拯欧阳修论》就很好地诠释了他的“廉政为民”思想:“然吾观宋庠循简以道自处,包拯直节著在朝廷。使人人皆效宋庠、包拯之所为,渐摩化导驯,至于一世再世。若徽宗狗马声色,穷边黩武,诸弊端有以杜其机于不萌,而九州四海隐受其福。固不少矣。”[1](卷一)法式善通过对宋庠、包拯 “循简直节”的肯定和赞扬,对宋徽宗“狗马声色”的严正批判,表达自己的“廉洁为民”思想。
三是推崇才德兼备。
在《宋论》中,法式善论及世人都知道要珍惜任用人才,但却不知道人才与人才之间是存在本质区别的,而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一个朝代的灭亡:“诸君子意在惜才,而不知才有可惜有不可惜;在用人,而不知人有可用有不可用。呜乎,是所谓忠厚之过也。”[1] (卷一)宋代统治者和历朝历代皇室一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在尽量网罗人才,且形成了所谓“人才盛世”。如宋庠、包拯、欧阳修、王安石等,全是治国安邦人才,他们的确推动了社会发展;但另外一些人,如章淳、蔡京、韩侂胄等,做的事情却是卖国求荣、祸国殃民,是他们加速了宋王朝的灭亡。为何如此?其实上述两类人都是人才,但是两者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一个“德”字上。显然前者是德才兼备的,而后者虽则不免有才却乏德。法式善在《姚崇论》中,开篇评价姚崇“德蕴于中而难知,才著于外而易见。姚崇盖才有余而徳不足者也。”[1](卷一)这至少说明,法式善在人才观上持有的是辩证法观点,“才”是国家考量人才的基础,但如果“德”有亏损,即使再有才华,也不可任用。
法式善的“才德兼备”观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中国传统的教育观本来就是“伦理”先行,德行为本。但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尤其重视与考试直接相关的内容,至于道德修养、纲常伦理就渐渐淡出了大众关注的范围,至少不是一些人首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人口口声声讲“仁义礼智信”,行为上却并不遵循,不去践行。这种情况发展到清代,变得更为严重。清代统治者其实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现象,曾提出了“崇实黜虚”的口号,号召人们以德为实,力图扭转士风日下的颓势,如康熙帝就曾撰《乡举里选解》一文,意在纠弊。所以,法式善结合社会实际,大力提倡“才德兼备”,这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四是强调个人的历史作用。
作为封建士大夫,法式善在论体散文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自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在论体散文中不止一次地强调帝王或个人在历史朝代发展更迭中的关键作用,甚至认为王朝的兴衰成败主要由某个个体主导。如他在《唐论》中指出:“自高祖至中宗,数十年中,再罹女祸。玄宗亲平祸乱,而复败于女子。宪宗志平僭叛,而不克终其业。穆宗以后,藉内竖拥立者且七君,国是又何论乎。顾人皆谓唐之乱亡,由于方镇之跋扈;方镇之跋扈,由于宫掖之不肃清;宫掖之不肃清,其端皆起于太宗。”[1](卷一)文中强调“女祸”在唐代历史上一再上演,最终造成了唐王朝的衰败。在法式善眼中,似乎封建统治者个人杜绝“女祸”与否就可以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了。显然,过分强调所谓“女祸”和个人决定论是不合适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封建帝王的确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绝不是全部作用,几千年人类社会的历史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13] (P98)唐朝后期统治者残酷盘剥百姓,荒淫无度,加之藩镇割据,使得百姓生活艰难,农民起义频发,最终导致唐王朝走向终结。显然,唐王朝的终结是统治者、起义军、藩镇各方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法式善的哲学史观出现了问题,是狭隘的,也是偏颇的。
二
文贵独创,有创见的文章能给人以启迪,才备受欢迎。论体散文以说理为要,重在剖析事理,论断是非,但说理观点的独创性则尤为重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曾谈到该种文体的“师心独见,锋颖精密”[14](论说篇)之特征 。这里所谓的“师心独见”,即指见解独到,不拾人牙慧。法式善论体散文的思想观点就有很多创见,很值得深入探究。这里拈出三点,略作阐释:
一是法式善论体散文中体现出的君子小人观。
法式善在《宋论》中,论述了宋朝的灭亡,不是因为小人,而是由于君子无法以果断的态度去除小人所致:“宋之亡也,不由于小人,而由于君子。不由于君子之不能容小人,而由于君子之不能去小人。其不能去小人,非有私也。大抵诸君子意在惜才,而不知才有可惜,有不可惜;在用人,而不知人有可用,有不可用。呜呼!是所谓忠厚之过也。……使数君子者本其学问、经济,而出之以果断,则宋之治,上媲唐虞,又何论汉唐乎?乃其于小人也,知之而不能除,能除而不能尽。”[1](卷一)其实,清初王夫之也写过一篇同题文章《宋论》,文章体现了清初思想界以史为镜所进行的深刻历史反思和批判。王夫之主要探讨君子小人的和同之辨以及对奸臣小人的批判,力赞宋太祖不论士的德行是否有“瑕疵”,都宽容待之的做法[15](卷一)。显然,王夫之的君子小人观仍是比较传统的。而法式善的“君子小人观”要较王夫之等人,立意要更深远一些。在法式善看来,君子小人的标准不是恒定的。他将批判矛头从小人转移到了君子上,与王夫之所论有了很大的不同,是一种矫枉,但并非过正。当然,也不排除在清代有论者与法式善有着相似的观点。如《易原就正》云:“小人恃势,而无忌惮,敢与君子战;君子则何以便轻身与小人战哉!盖小人之道,长极矣。君子之道,消极矣。至此不一,战则天道人道俱泯矣,其道穷也。”[16](卷一)《续资治通鉴》言:“盖君子小人,各有党类。先圣谓观过各于其党,不可不慎也。”[17](卷十一)但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人毕竟微乎其微,故而值得重视。
二是法式善论体散文对狄仁杰的评价。
历史上对狄仁杰的评价一直是褒扬的,这些评价主要出现在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除此之外,高适曾在《三君咏·狄梁公》中赞其:“梁公乃贞固,勋烈垂竹帛。昌言太后朝,潜运储君策。”[18](P2208)陈子龙赞其为一代贤臣:“臣闻唐臣狄仁杰,宋臣寇准、韩琦、富弼、范仲淹功名事业起于边圉。……庶朝廷用之者,既贤,而一代真才必有如狄仁杰、韩琦诸臣者,出为国家经略矣。议者犹以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强所不能,既坏其人,尤坏其事臣,谓不然夫所谓贤者,非默默株守之谓也。”[19](卷三百八十四)嘉庆年间官修的唐五代文章总集《全唐文》[20]中,全文收录了狄仁杰7篇奏折,足见对其勤于吏政、以民为本、持法严明、政绩突出的认可。
法式善本人也参与过敕撰《全唐文》,并在《校全唐文记》中记录了自己全程参与校对、编纂的情况[2](卷二),因此,历史上对狄仁杰的高度评价与肯定褒扬,他应该是了然于心的。但是法式善在《狄仁杰论》中对于狄仁杰的“卫身”“济变”之“心机”实际上是不赞赏的,甚至是有所非议的。从“其智足以卫身,其术实足以济变,其心实不足以对高祖太宗”一句,我们就能清晰感受出这一态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本人不认同《全唐文》对狄仁杰的评价,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足见其胆识与魄力。他指出:“幸而,易之从其说,而武后感悟,中宗得以复位,易周而为唐;不幸,而易之不从其说,而武后不感悟,中宗不得复位,亦将易唐而为周乎!仁杰其何所恃而为此?盖仁杰处其身于有利无祸之地,而隐忍迁就以为之。济,则己之功也,名也;不济,则时也,命也,己无与也。吾故曰:唐室之复殆有天焉。”[1](卷一)法式善认为狄仁杰有使自己处于“有利无祸之地”的心机,在覆周为唐的过程中,作用并没有那么大。
三是法式善论体散文对尔朱荣的评价。
法式善在《魏孝庄帝论》中将尔朱荣与韩信相提并论,并认为尔朱荣对魏庄的功劳超过韩信之于汉高祖刘邦。因此,他提出:“魏孝庄帝有负于尔朱荣,且甚于刘邦有负于韩信”的论断[1](卷一)。其实古代论及孝庄帝和尔朱荣的文章不少,《全唐文》就记载了尔朱荣“作乱”的全过程[20](卷一百六十一);乾隆朝官修的《通鉴辑览》对尔朱荣的评价倒是比较客观,功过均录[21](卷四十二)。但是,很少有人如法式善这样,将尔朱荣的评价提升至如此高度,居然将其与韩信相提并论,读来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世知汉高于韩信为寡恩,而不知魏庄于尔朱荣,其寡恩为尤甚!吾故表而著之,不然若荣者岂得与信并论乎?魏庄又岂得与汉高并论乎?”这种既能综观历史,又能横向比较,给长期以来评价不高的历史人物正名翻案的论述,实为罕见,而这恰恰体现了法式善论体散文师心独见的创作特色。
三
法式善论体散文不仅具有很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还体现出独具魅力的章法之美。下面就从立论精巧、持论公允、布局弘阔和收篇妙远等几方面具体分析:
首先是其论说的精巧。
刘勰认为论体文的立论模式要“归于余终,则撮辞以举要”[14](熔裁篇),意即用精炼言辞将文中主要论点或观点提出,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文中其他语句与举要之辞是从属、支撑的关系,也即陆机所说的“众辞”与“片言”的关系[22](卷警策篇)。对于论体文来说,开篇立论,提纲挈领,极其关键。论点的树立是论体文作者所应考虑的首要问题。“如果从效果出发,论体文创作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破坏性攻击,重在驳论;一类是建设性攻击,重在立论。”[23](P49)驳论模式重在推翻某种传统观点,“打破某种偶像和与其相应的思想上观念上的陈规旧律,他们的论作中充满激烈争辩的富有论战性的文字”[23](P49);立论模式重在建设新观点,虽有新的见解,但目的并不是与已有的观念发生冲突,而是在原有观念上锦上添花。
在法式善的8篇论体散文中,属于驳论文类的共有3篇,即《宋庠包拯欧阳修论》《李东阳论》《郑鄤论》;属于立论文类的共5篇,即《唐论》《宋论》《北魏孝庄帝论》《狄仁杰论》《姚崇论》。下面分别就驳论类和立论类各举一例予以说明法式善论述模式的特点。
(1)关于驳论的。法式善在《宋庠包拯欧阳修论》首段说明包拯对宋庠的评价以及欧阳修对包拯的评判均不高:“……包拯之论宋庠也,谓‘秉衡轴七年,殊无建明,少效补报,而但阴拱持禄,安处以为得策。’欧阳修之论包拯也,谓‘取其所不宜取,岂惟自薄其身,亦所以开诱他时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二臣之论,皆是也。”[1](卷一)第二段,法式善开始批驳包拯和欧阳修的言论,确立自己的观点,即宋庠有道,包拯直节:“然吾观宋庠循简,以道自处;包拯直节,著在朝廷。使人人皆效宋庠、包拯之所为,渐摩化导驯至于一世再世。”[1](卷一)然后就此展开论述,认为宋庠、包拯其实是大家应该效仿的对象,人们可以以此杜绝很多弊端。
(2)关于立论的。法式善论体散文中,立论文章很值得称道。如《唐论》开篇的立论:“唐之得天下也以争夺,而其失天下也亦以争夺。其兵之兴也以宫妾,而兵之废也以宦官。观于此天人感召之机盖不爽矣。”[1](卷一)用“天人感召之机”来解释唐王朝“天下之得失”与“兵之兴败”。开篇之论似乎在说明“唐亡”与“唐兴”都是天命所为,表面上看貌似老生常谈,但实际上,读者更应关注立论中“争夺”一词,这个词具有深刻涵义,意思是说:唐代得天下,其实并不光彩。最终也因此被人抢夺基业,而丢掉天下。因此,石韫玉评论该文说它“立论宏通”[1](卷一),陈用光评曰“立论亦极有精采”[1](卷一)。
其次是持论的公允。
所谓持论公允,是指文章立论公正,评论公允,分析符合事理。很多人评论法式善论体散文,大都认为其“持论平允”。法式善能够做到这一点,当与他一直潜心学习欧阳修散文笔法尤其是史论、政论文章的笔法有关。吴锡麒曾评论法式善诗文:“论时帆之诗,而以为摩诘;论时帆之文,而以为庐陵。”[1](吴锡麒序)法式善的《唐论》《宋论》就与欧阳修的《五代史官者传论》《朋党论》持论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持论平允,阐明己论,援古事以阐析疑义,论得失而重理,卓然自立,不露锋芒。如评价唐朝时,作者没有一味地赞扬和贬斥,而是深刻地分析出其得失天下均由于“争夺”;文章不是把唐高祖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客观看待他对于隋朝灭亡、唐朝建立的作用。《宋论》中一改自古以来的贬小人、扬君子的态度,公允地论说了君子如不能去小人,那么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不良影响更大。
再者是其布局的弘阔。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布局、格局的术语颇多,如“器”“识”“襟抱”“量”等,不一而足。黄庭坚曾说“一丘一壑,自须其人胸次有之,但笔间那可得”[24](P43),阐明了作者的胸襟决定文章的布局这一观点;沈德潜的《说诗晬语》也提到“第一等襟抱作第一等文章”[25](卷上)。从文章布局上论,可分为“弘阔”和“偏狭”两类。弘阔,指文章结构布局合理、严谨,内容丰富,文意深远;而偏狭则相反,指文章格局狭小,内容单一,立意肤浅。虽说法式善散文篇幅短小者居多,但这并不损害其文章布局的弘阔。也就是说,布局弘阔与否主要取决于内容之丰、层次之多和文意之深,与篇幅长短的关系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法式善论体文的布局都可以看作是“弘阔”之类。如《唐论》立论之后,将唐高祖与朱温类比,进一步述说二人极其相似的发迹史——均以“争夺”开始,都是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不断招降纳叛,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从而建功立业。然后,文章转折至“然高祖创业三百年,而朱温旋败,后之论者,终以盗贼归之,何其遭遇不同耶!”[1](卷一)这种论断何其独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过往正史中那些以成败论英雄的论断之偏颇。表面上看,法式善是在为后世常以“盗贼”名之的朱温鸣不平,实则是在以“争夺”之实归于唐高祖李渊。能大胆说出一代开国之君抢夺天下的事实,法式善勇气可嘉,见识更非凡。接下来,作者综观唐史,列举数例(包括高祖、中宗、玄宗、穆宗及其后面的七位国君),来验证论点中“兵兴之源”——宫妾(或女祸)以及“兵废之源”——宦官(内竖)的恶劣影响。列举完之后,追根溯源,还是将祸患之源头归于唐太宗:“顾人皆谓唐之乱亡,由于方镇之跋扈;方镇之跋扈,由于宫掖之不肃清;宫掖之不肃清,其端皆起于太宗。”[1](卷一)直至这里,作者表面上都是在围绕“天人感召”的论点在阐释兴衰更替,读者似乎感觉到一种神秘的力量笼罩着唐代,并使其走向灭亡。但是,文章最后一句话,却有更深层的含义,将文章的思想高度又进一步提升了:“太宗能以功烈盖父之愆,除乱致治,比隆汤武,可谓英主矣。至于以宫妾兴,以宦官废,未能逆覩寻其终始,有足感者。防微杜渐,君子所以兢兢也哉。”原来,作者真正的意图是提醒今之君子学会“防微杜渐”,而不是一味地陷入“天人感应”之机中无法自拔,毫无作为。如果从源头就杜绝危害,国家就能良性发展下去。整篇《唐论》,共276字,篇幅虽小,但可容纳百川,结构简单却极其紧凑,其体不可不谓之弘阔也。
最后是其收篇的妙远。
法式善论体文的结尾总给人一种悠深妙远之感,这一特点集中表现在《宋庠包拯欧阳修论》《唐论》《狄仁杰论》这3篇文章中。这里仅以《宋庠包拯欧阳修论》为例。文章开篇论述:历史上,包拯曾弹劾宋庠懒政,欧阳修曾弹劾包拯判案不公,有失偏颇,包拯和欧阳修的评论皆有道理[1](卷一)。接下来作者笔锋陡转,“然吾观宋庠循简以道自处;包拯直节著在朝廷。使人人皆效宋庠、包拯之所为,渐摩化导驯至于一世再世。”[1](卷一)作者认为宋庠一切循简,以道自处,而包拯以直节闻名,假使人人都来学习此二人之所为,良好风气则可以风行百世。这充分说明,法式善并不同意之前包拯和欧阳修对于同僚的弹劾。然后,作者再将文意推至更为深入的一层:“以君子而攻君子,人皆谅其用心之无他;而受其攻者,每甘心引咎,以至于畏首而畏尾。呜呼!攻之者过矣!善论世者,虽贤如拯与修之言,亦必取而折夫中。”[1](卷一)作者认为,因为双方都是君子,即使君子相轻或彼此攻击,人们也都不认为攻击者是为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公家,被攻击者也都会选择隐忍接受,不去反驳。在此,作者阐述了一个深刻观点——“攻之者过矣!”提醒那些“善论世者”,即使具备欧阳修与包拯那样的人品、德行,在评论别人时仍要切记“折中”,不要只盯着别人的一件错事或小过失不放,要从全局看,要看其主流。而最值得注意的是结尾一句:“不然,章惇小人之尤者也,而胡为逆知端王之不可立哉?”意即:否则的话,章惇那样的小人,怎么会预见端王不能立呢?章惇其实与文中所论人物没有丝毫关系,而且史书上多以“小人”目之。可是,作者却能看到章惇所具备的优长、对历史的贡献。文章在结尾处加了这么一处“闲笔”,貌似“节外生枝”,实则为深化全文,卒章显志。所以孙星衍评价该文“结处每能放宽一步,得妙远不测之神,而无节外生枝之累,此是得古人三昧处”,的确抓住了本文的精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