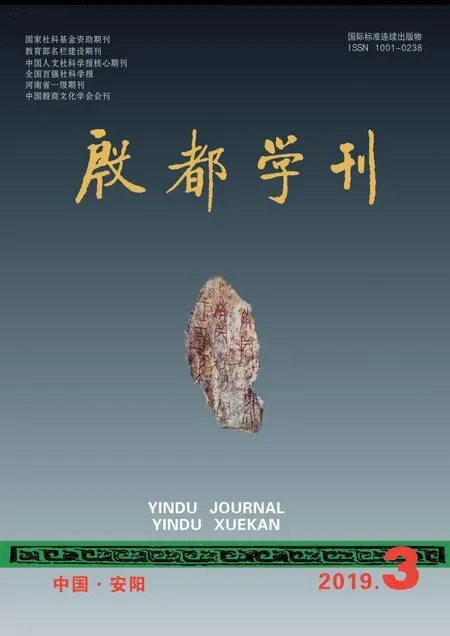朝鲜金泽荣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与接受
2019-12-16王成
王 成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金泽荣(1850-1927),字于霖,号沧江,亦号云山韶護堂主人,“韩末四大古文家”之一。1905年流亡到中国江苏南通,后加入中国籍,在中国生活了22年。有《韶護堂集》传世。金泽荣曾在张骞创办的翰墨林印书局任编辑,编辑刊行了朝鲜著名文人朴趾源《燕岩集》、申纬《申紫霞集》、黄玹《梅泉集》、李建昌《明美堂集》等文集。金泽荣宗法秦汉、唐宋散文,“于文好太史公、韩昌黎、苏东坡,下至归震川”[1](P407),其文“或者议政,或者论事,观点鲜明,有雄辩的气势”[2](P1324)。
金泽荣对司马迁《史记》非常推崇,其《杂言六》云“读司马史则可以知后世之史皆死史也”[1](P323),高度评价了《史记》的史学价值与地位。《杂言四》“太史公之文,便是诗”[1](P320),从文学的角度赞扬《史记》。鲁迅曾评价《史记》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是从史学、文学两个角度进行论述的。
金泽荣在评价他人时,总是把司马迁《史记》作为标尺,在论述他人文学渊源时也常常追溯到司马迁《史记》,这在金泽荣的文集中随处可见。如:
欧阳公文力,摹史迁神韵,然而无史迁长驱大进之气力,故终近于弱。古今善学史迁者,惟昌黎、东坡、震川三人。[1](P320)(《杂言四》)
《孟子》七篇,波澜之文也,韩昌黎学之,若欧阳永叔,虽学太史、昌黎而气力不足,不能似之,止于婉宕而已。自茅坤推欧为学太史,自后之文人靡然从之无异辞,亦一可笑。与其谓欧为学太史,毋宁谓苏文忠为学太史,苏文如《方山子传》之类,岂非真太史之遗韵乎?[1](P324)(《杂言八》)
世多以为震川学庐陵,非也,震川是专主太史公,而旁及昌黎、东坡、南丰者,故能朴实、能虚非、能长驱大进。[1](P320)(《杂言四》)
焉、哉、乎、也、之、而、故、则等语助字,虽似乎俚,而至妙之神理,实在于是。《尚书》《周易》之文罕用此,用之自孔子始,而司马史尤多用之。[1](P320)(《杂言四》)
《平准书》云“先是往十余岁”,《太史公自序》云“唯唯否否不然”,既曰“先是”而又曰“往”,既曰“否否”而又曰“不然”,今人能为此否。[1](P320)(《杂言四》)
《大学》“君子先慎乎德”以下三节,连下“是故”二字,真非今人情量之所及也。盖此法自先秦多有之,止于史公,而班固不能尔,况又益后于固者乎?[1](P320)(《杂言四》)
贾太傅文气魄之雄厚,机轴之变动,未必远让史迁。[1](P320)(《杂言四》)
引文概而言之,道出了以下一些信息:欧阳修学习司马迁《史记》,但没有学习到《史记》“长驱大进之气力”,说明《史记》文章充满了气势。与其说欧阳修学习司马迁,莫不如说苏轼学习司马迁,苏轼《方山子传》之类,有《史记》列传的神韵。古代文论家多认为归有光的文章是学习了欧阳修,金泽荣指出归有光是“专主太史公”,又兼习了韩愈、苏轼、曾巩等人,所以为文“能朴实、能虚非、能长驱大进”。金泽荣指出司马迁《史记》多用焉、哉、乎、也、之、而、故、则等语助词,这些语助词看似俚语,司马迁却运用得很巧妙,取得“至妙之神理”的艺术效果。“先是往十余岁”(《平淮书》)与“唯唯否否不然”(《太史公自序》)两句,金泽荣认为用词存在重复现象,“既曰先是而又曰往,既曰否否而又曰不然,今人能为此否?”金泽荣指出《大学》“君子先慎乎德”以下三节接连运用“是故”二字,这一用法源于先秦文学,止于司马迁,班固也无法做到。《尚书》、《周易》文章晦涩难懂,《论语》文章简约易懂,司马迁学习《论语》的简约风格创作了《史记》,写出了“疏荡高洁神韵”的文章。贾谊与司马迁可作一比。
金泽荣还通过评价李建昌《伯夷列传批评》传达出对《史记》中记述的伯夷叔齐故事的见解:“李凤朝《伯夷列传批评》,谓子长自以纂述一部史记,进退千古人物,如孔子春秋之权,自处于青云之高士,其说诚妙矣。”[1](P498)但他认为李建昌并没有分析透彻,所以他做了进一步分析。司马迁对孔子的尊崇,“一行必视为法,一辞必视为经,赞之以至圣,尊之以世家,与董仲舒雁行立”[1](P498)(《题李凤朝〈伯夷列传批评〉后》),并且尊孔子为师,“作其私淑弟子”[1](P498)。许由让天下出于黄老之言,而尊崇儒家思想的司马迁“历举六艺诗书及孔子之说以辨之”。所以说,“《史记》一书始于斥许由,以贵重史家之地位,终于正获麟,以拟圣人之经”[1](P498)。《题李凤朝〈伯夷列传批评〉后》这篇文章是金泽荣阅读李建昌《伯夷列传批评》后的个人体悟,是对李建昌观点的补充。
金泽荣同时指出修史即要像酷吏断狱案一样,能明辨事非曲直,能以信笔为之,如此,“方可以主史笔而定天下之是非”[1](P498)。所以在编撰《韩史綮》、《校正三国史记》、《韩国历代小史》等朝鲜历史书籍时,金泽荣积极向司马迁《史记》学习,采用“实录”法进行撰写。
《东史辑略序》一文交代了编写《东史辑略》的目的、过程以及指导思想。金泽荣指出,历代通史都存在繁复的弊病,这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不便易的,“自春秋以降,世愈下事愈繁,一代之史,非数十百卷,不足以尽记其事,人之从事于史学者,聪明既有所难给,而其初学之情,尤在于便易”[1](P430)。所以宋代江贽取司马光《资治通鉴》,删存大要,首尾赅通,成《少徵通鉴节要》一书。曾先之编撰《十八史略》,取材的史书自司马迁《史记》至欧阳修《五代史记》,是对十八种史书的节略。金泽荣有感于朝鲜本国初学史学者“所读本国史略,苦无善本”,所以他取材朝鲜本国历史,“据徐氏《东国通鉴》、俞氏《丽史提纲》、安氏《东史纲目》、洪氏《渤海世家》,以及乎日本之史”[1](P430),仿照曾先之《十八史略》,起自檀君止于高丽朝,“其所辨明,以疆域为主,多采丁氏疆域考说,而间亦附以私见”[1](P430),总11卷,名《东史辑略》。在付梓之前,金泽荣有感于史家之职责,“更取《三国史》、《高丽史》及《通鉴》等书,以证正修润,随润随出,以既厥事”[1](P430)。流亡中国后又对此书做了修改、补充,更名为《韩国历代小史》。
《韩史綮序》一文指出朝鲜王朝时期社会、政治存在诸多弊病,这就需要一部信史来真实地进行记录,以待后人学习、借鉴。金泽荣认为高丽时期和中国两汉时期相类,“风气尚能宽大”[1](P256),所以出现了郑麟趾撰写的《高丽史》。该书奉王命而修撰,体例仿中国正史,记载了高丽王朝的事迹。但朝鲜朝时期与高丽朝相比却有很多不同,“韩则不然,风气之狭隘,为历代所未有,动触忌讳,手足莫措”[1](P256)。朝鲜朝时期政治环境恶劣,自燕山朝开始,“史狱之惨,史笔摧挫”,史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成了无史之国度。即便民间有纪录者,也存在着“述而不作,俚而不雅”[1](P256)的问题,无法让人信服,做不到以信史传后世。作为一名朝廷史官,不能袖手旁观,使五百年间的君臣上下,“一切污隆得失之迹,归于烟雾之晦暝,灰烬之荡残”[1](P256)。并且,朝鲜朝时期朋党之争持续不断,互相攻击、倾轧,“四党分立,各持其论,圣于东者狂于西,忠于南者逆于北,纷纭错乱,莫执其一。虽其间或不无自命公正者,而积习之擩染,终未易脱之尽矣”[1](P256)。金泽荣庆幸自己没有卷入党争,能保有辨断是非的本心,能有自己的认知,所以撰写《韩史綮》。《韩史綮》以《大东纪年》、《国朝人物考》、《梅泉野录》三部著作为依据,考虑到修史需要严谨,金泽荣又参阅《燃蔾记述》、《党议通略》、《山南征信录》以及其他书籍。他采用的原则是:“采于纪年人物考,以补缺正误。顾英祖以下之事,不资记录。而但资于士大夫之游谈者,尚或有年月模糊之叹,故别列于右,以俟更正。”[1](P256)
司马迁撰写《史记》,实录是其最大特色,班固评价司马迁《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也以孔子继承人自命,说他撰写《史记》就是要彰显《春秋》等经典著作的本意,使后人更好地立身行事。司马迁还想通过《史记》揭示历史变迁、变化的规律,总结“变”的历史经验教训。
金泽荣在编写朝鲜历史典籍时践行了司马迁的史学观,《韩史綮》充分体现了实录精神。《韩史綮》共6卷,主要记述了朝鲜朝时期23王、2帝、2废主,历519年之事,该书“大张汉司马迁论史之意,而在书间论事品人,无论是君王或布衣,邦国大事或民事,堪论处,皆锋利,直抒心胸”[3](P141)。该书不仅在纪事时有评论,还专门设有“论曰”51条。《韩史綮》的实录精神主要体现在对统治集团的残暴、荒淫的揭露:
太祖高皇帝康献王,李姓,名旦,字君晋,初名成桂。其先全州人,屡徙为咸兴人。高丽东北面兵马使子春第二子也。母懿思,王后崔氏。屡立战功,致位将相,弑二王,篡恭让位。在七年。[4](卷一)
世祖之杀姪、杀诸弟以盗君位,万世之大恶也。叔舟请婢端宗妃,又万世大奸大恶之尤也。[4](卷一)
(世祖)残其骨肉,如屠羊豕,犯万世之大恶而不知其非。[4](卷一)
仅3例就足见金泽荣直书史实、不假文饰的实录精神,比司马迁《史记》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书出版后,韩国学界、政界反映强烈,也从侧面证明了其实录的价值。
《韩史綮》1918年由翰墨林印书局刊行后流入朝鲜, 开始引起那些抱有忠君思想的传统儒家学者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这是一部“耳不忍闻, 口不可言” 的史书, 其根本上违背了《春秋》“为尊者讳”的史法, 而以侮辱君王为能事。1923年刊出了赵愚植、柳寅永、崔万植等125人的连名抗议书《略辨韩史书》,辱骂金泽荣是寓佣于翰墨林印书局中的“一种妖怪孽芽”,“彼素以巧黠文字名”, 《韩史綮》一书“诬蔑君父、凌辱先贤”, 是“国家之乱贼, 儒门之叛卒”,要求南通翰墨林书局“摈屏于无父无君之地, 勿使污染华夏, 并火其书, 勿令惑人耳目”。1924年同时出版了两本《韩史綮辨》, 儒林总部推出的孟辅淳本, 有101位韩国学者参与发起对《韩史綮》的攻击, 该书罗列出《韩史綮》有违背“春秋大义”;诬毁后妃;诋斥先贤;党私之论;好谈阀阅;将檀君开国置于半信半疑之间;讥评韩人忠君爱国习性共七大罪状。结论是该书“不可以为史也, 亟付之火, 勿污人眼可也”。太极教本部出版的李炳善本, 参与围剿的京城绅士253人, 地方绅士1253人, 在该书末《讨史贼金泽荣文》中,把金泽荣斥为“枭獍不若”的“罪大恶极”者, 指责《韩史綮》“肆然加诬蔑于我列朝”、“辱说我先后”、“恶骂我先帝”、“大恶我英祖”、“夷狄我太宗”、“篡逆我太祖”、“侮毁我先贤”, 号召国人“同声声讨”,“遍告遐迩使人人鱼加严诛, 以伸春秋大义”。[5](P416-417)
韩国儒士学者们抗议、谴责《韩史綮》,主要是认为《韩史綮》违背了《春秋》为尊者讳的原则,揭露统治者的夺权、倾轧,对朝廷的朋党乱争等毫不留情,这恰恰是《韩史綮》最大的价值所在。《韩史綮》敢于直录实事,不假文饰,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张謇《韩国历代小史序》云:“故国禾黍之悲,耿耿不忘于君之心,于是始终李氏朝鲜之事,成《韩史綮》,居数年,以其书合之于前所作《韩国历代小史》为一书。以仿虞书冠尧典之义。……金君叙一国三千二百余年事,可观可怨可法可戒者略备矣,谓以供人观怨而法戒。”[6](P260)
《新高丽史序》一文也透视出金泽荣在著史书时对实录精神的遵循。郑麟趾奉王命续编《高丽史》,记载高丽王朝事迹,价值颇大,但也招致很多非议:“君子谓之非史,何也?夫人能正其身,然后乃能正人之不正。如麟趾者以韩端宗之大臣,叛附世祖,首建杀端宗之议,此其余狗彘之所不食也。况其史于讳亲之外,又多有稗陋荒谬之失者乎?”[1](P450)除此之外,郑麟趾《高丽史》中“本纪”谬误之处更多,“芜拙太甚,不成其章”、“不加剪裁陶镕”,“以本纪言之,如高宗三年契丹之难,但书小捷而不书金就砺之大捷。十八年蒙古之难,但书龟州被围而不显出朴犀之名。太祖所创延庆宫,非子孙之所敢改名。而仁宗纪,以改为仁德宫书之。忠肃王纪,杂入高宗时事六七行。以列传言之,崔允仪谀于毅宗,为台官所论斥,而其传谓之论事慷慨,文益渐以不附德兴君,被窜交趾,而其传谓之附德兴”[1](P450)(《新高丽史序·附说》)。上述情况大量存在于郑麟趾《高丽史》中。同时,高丽时期也是朝鲜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
惟高丽一代之事,有可以光耀于百代者四焉。高丽太祖以英雄之才仁义之资,为天人之所付戴,以正得国,并于三代,此其一也。田柴之科,规模乎周之井田唐之租庸调,以之制禄,而兼以厚其兵力,摧破劲敌,动十数万众,此其二也。用人惟取才德,而不问其地阀,由胥吏而致位卿宰者,往往有之,西汉宽大之政,不能胜之,此其三也。东邦之文风,始于新罗末世而仅仅焉,高丽承而王之,鸿工巨匠,前后如麻,在中国之宋世。而能操三唐之声律,而比其季则韩欧之文,程朱之学,亦出焉,此其四也。夫合东邦历代而言之,新罗、高句丽、百济质胜文而多勇,其犹日之初升乎,韩文胜质而多伪,其犹日之高舂乎?至于高丽,具彼四美,文与质俱胜,则日之方中是也。[1](P450)
高丽时期这一段历史值得书写与铭记,因为“可以光耀于百代者四”,金泽荣一一作了阐释。基于此,金泽荣下决心重新修正高丽史。他非常看重取材、史料的准确,在修订时,“引徐氏《东国通鉴》之文,以救其疏;引《公羊》、《谷梁》、《春秋》之义,以通其讳;加入释志、儒学、文苑、隐逸、遗民、日本等传,以苴其漏”[1](P450)。
综上可见,金泽荣对司马迁与《史记》的推崇、学习,贯穿其文学批评与史学著述始终。金泽荣的古文文学批评追根溯源时往往追溯到司马迁与《史记》,指出他人在学习《史记》中的得与失。在编撰《韩史綮》、《校正三国史记》、《韩国历代小史》等朝鲜历史著作时,金泽荣努力践行司马迁《史记》的“实录”精神,大胆对统治阶级进行揭露与批判,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朝鲜朝后期著名诗人、散文家李建昌(1851-1898)评价金泽荣是“文有史才”[7](P173),金泽荣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