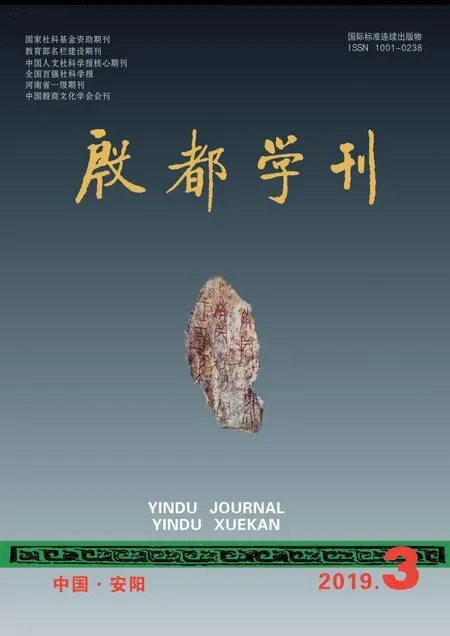元代中华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及文学史意义
2019-12-16任红敏
任红敏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元朝按照中原王朝的体制,建立了继唐宋之后中国的一个正统王朝,忽必烈以《即位诏》颁行天下:“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1](P65)即明确了元朝的正统地位。元朝如同立足中原的辽、西夏、金等一样,宋、辽、金、西夏对峙时期,当时辽、金欲进入中原,两朝君臣均自称契丹族和女真族本是炎黄之后,在族源上亦属于华夏一脉,自然认同中华文化的正统地位,以继承中原王朝身份承袭为中华正统,接受中华文化,推行汉法,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中原地区乃是“农桑为天下之本”,进一步推进农耕经济的发展,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理学正式成为官学,成为元朝的统治思想,文化方面,如绘画、书法、雕塑、音乐、文学艺术等,依然沿着唐宋两代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可以说在元代这个华夷一体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文化积淀、族群规模等方面的差异,中华文化对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影响既深且广。关于中原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严文明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论述:“整个中国的古代文化就像一个重瓣花朵,中原是花心,周围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里圈花瓣,再外围的一些文化中心则是外围的瓣。这种重瓣花朵式的结构乃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因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中国文明的历史之所以几千年连绵不断,是与这种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与民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2]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元代文化是其中延续的一环,又是极富特殊性的一段,特殊性指的是元代多元文化特色,草原游牧文化、西域商业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在大元统一政权之下,文化迅速交流而融合。蒙古草原文化处于统治地位而起主导作用,西域商业文化也是整个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传统中原农耕文化历史最为悠久,文明程度最高,辐射力最强,依然是元代文化的主干。
在中原地区,依然是汉文化处于强势的主体地位并沿着其固有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雍古族士人马祖常从语言认同上表达了各族人民对“中原汉音”的接受和认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偏气之语,不相通晓,互相憎恶。惟中原汉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于习说。”[3](P752)要实现各种民族真正的文化融合,必须依托中原汉文化,以四方都能接受的“中原汉音”为交流互动的文化基础进行。当然,元代疆域之广大,是超越前古的,中原文化影响的区域,自然也是超越前古的。戴良序丁鹤年诗集也说:
昔者成周之兴,肇自西北。西北之诗见之于 《国风》者,仅自邠、秦而止。邠、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系之列国,以与邶、鄘、曹、桧等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西北诸国,若回回、吐蕃、康里、乃蛮、维吾尔、也里可温、唐兀、天竺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其去邠、秦盖不知其几千万里,而其为诗,乃有中国古作者之遗风,亦足以见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变,虽成周之盛,莫及也。(《鹤年吟稿序》)[4](P238)
元建立之前,西域商人已经随征旅陆续进入中原,元统一全国之后,更有大批西域人定居中原各地,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许多西域知识分子人刻苦研读儒家典籍,正如陈垣先生所说:“盖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不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5](P132)他们吸取中华文化营养,与汉族文人学者交游学习,逐步形成元代所特有的西域文士群体。元初畏兀儿人廉希宪、阿鲁浑萨里,康里人不忽木,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均是精通儒学的名士,而且也身体力行,鼓倡儒学。北魏拓拔氏后裔元明善“自少负才气,盖其得于天者异于人,而又浸淫乎群经,搜猎乎百家,以资益其学,增广其识,类不与世人同。”[6](卷19)《元复初文集序》其后,有戴良《鹤年先生诗集序》文中所提到的西域文学家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剌、余阙、高克恭、康里巎巎、泰不华、雅琥、聂古柏、斡玉伦徒、伯笃鲁丁、三宝柱等人,均是文学领域享有盛誉的名士。还有葛逻禄人诗人廼贤,唐兀氏孟昉、张翔,均工于诗文,西域人沐仲易不仅“工于诗”,而且“尤精书法”[7](P109)。西域诸民族认同中华文化,在元代文学和文化各个领域出现了一大批名士。元代可谓各类西域色目人才济济,名士辈出的一代,文学家、艺术家、儒学家、史学家、天文学家、翻译家、星相家、建筑师、航海家等灿如繁星。除此之外,尚有辽宗室后裔契丹人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诗文兼擅,以及耶律季天、耶律柳溪、移剌迪、移剌霖、述律杰、石抹宜孙等契丹名士,女真士人徒单公履、夹谷之奇、乌古孙良祯、兀颜思中、兀颜思敬、完颜东皋、浦察景道、浦察善长、李直夫、奥敦周卿等均是元代名士。
作为居于统治地位的蒙古族,虽然在文化上处于主导地位,由于其本身是一个以较单一的游牧狩猎文化为特色的草原民族,文化和相对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相比较,处于落后的状态,蒙古族对各种宗教和文化又有很强的包容性,很容易接受中华汉文化。很多蒙古人很快发现了学习汉文化,精通儒学的好处。当蒙古族入主中原后,为了保持本族的统治地位,蒙古族统治者实行了四等人制,蒙古人作为元朝的国族自然居于首位,元代政权中首先依恃的是蒙古人,其次是色目人,“皆以蒙古人与西域人参用之”,元代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的最高长官一律由蒙古人充任。部分蒙古人出于对汉人统治的需要,或者出于对汉文化的仰慕,在移居内地之后,开始学习汉文化并研习儒学。元代任职中书、行省平章政事等中央和地方的显位要职官员好多是精通儒学的蒙古族儒士大夫,他们熟知汉文化又有汉地管理经验,和汉族士大夫文人自由交往。
很多蒙古、色目人由于文化上认同而采用汉式姓名与字号。“由于蒙古人在政治上居于主宰,而汉人在文化上则占优势,汉人采用蒙古名者或为接近权力源头的宫廷近臣,或为冒充蒙古人身份而谋求一官半职的猎官之徒;而采用汉式姓名之蒙古、色目人则皆系汉化较深者。”[8](P687)元代东迁西域各族,久居中土,对中原华夏文明耳濡目染,衣食住行等都受到影响,有的改用汉姓,有的改用汉名,华夏礼仪文化以及立身处世之道均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如江浙进士家铉翁由于受到中国传统礼俗的感染,“修孔氏之业,读文公之书”[9](卷6《送家铉翁序》)。清人赵翼曾云:元代“自有赐名之例,汉人皆以蒙古名为荣,故虽非赐名,亦多仿之。且元制本听汉人学习蒙古语,惟其通习,故汉人多以蒙古语为名,一时风会使然也。”(《廿二史札记》卷三〇“元汉人多作蒙古名”)如果说汉人改用蒙古名字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或为了谋求利禄,那么,这时东迁西域诸族人和蒙古人改汉姓名则纯粹是“慕效华风,出于自愿,并非有政府之奖励及强迫,而皆以汉名为荣。”[5](P95)于是东迁西域各族人之请字请名者触目皆是。东迁西域人有取表字者,也有采用汉姓者,如高克恭、马九皋、吴惟善、沐仲易、马易之(即迺贤)、虎伯恭等。(1)参见任红敏:《北方草原文化及西域商业文化对元杂剧创作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6年第1期。元人安熙言:“近世种人居中国者,类以华言译其旧名而称之,且或因名而命字焉。”(《御史和利公名字序》)[10](P531)如元末诗人丁鹤年,曾祖阿老丁,祖父苫思丁,父亲职马禄丁,至丁鹤年乃取先人名中汉译末字为姓,其子孙后代遂成丁氏。阿鲁丁,取其祖父玉速阿刺之“玉”为姓氏,称玉元鼎。亦不刺金者,取汉姓名为金仲达;札马鲁丁,取汉姓名丁慎之。
元朝在建立之初便带有明显的民族掠夺性,当年元军南下攻宋之时,“财货子女则入于军官,壮士巨族则殄歼于锋刃;一县叛则一县荡为灰烬,一州叛则一州莽为丘墟”[11](卷23《民间疾苦状》),官兵大肆抢掠,嗜杀成性。在政策制定上元朝统治者也是倾向于本民族的利益,把国家公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人显然是享有更多特权,色目人其次,南人最为低贱(2)元朝的法律还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知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元史·刑法志四》)如此不公正的待遇自然会引起中原汉族人的不满,在元代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元杂剧有不少作品正是元代这个特殊时代人民不满情绪的宣泄及反抗精神的反映。,元政府中的军政大权,基本由蒙古和色目人把持,整个元代,民族对立的情绪一直存在,彼此存在着隔阂,也有斗争。但是,在元代这样一个大一统王朝之内,居住于长城内外的各族人民相互杂居共处,多元文化并存,更多的是文化间的沟通和融合。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大,人口的迁移,因战争军旅屯驻,或立国之后戍守、仕宦等因素,蒙古族的军队、官吏常常是“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姚燧《千户所厅壁记》)[12](P94)。元朝廷为了屯田及巩固统治的需要,曾由政府下令迁徙大批汉人、南人到西北、东北等人烟稀少的边塞地区。还有,大批回族人通过军政或者农商或者手工业者散居全国各地,“以士兵、工人、技师、官吏、武将等各种身份……移居到中国的回回人约在100万以上”[13](P467),各民族之间杂居相处,各族人民接触频繁,相互依存,“不同的民族之间只要接触多了,必定有文化融合的结果。”[14]各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互相影响,各族之间的文化融汇交通。
蒙古和西域人东迁中土与汉人杂而居之,习染华风,逐渐习惯了按照汉人的行为准则办事,接受中原的伦理道德观念。“由于汉地环境影响,蒙古人皆改采汉人敛葬方式。”[8](P696)在丧葬等礼制方面也多遵从汉俗。虽然元政府规定各依本俗:“国家以风俗为本,人道以忠孝为先”[15](卷30《礼部卷之三·禁治居丧饮宴》),汉族传统的五服和守丧等仪制得以保留并影响了蒙古西域文人和官员,对此,元政府允许汉人官员实行丁忧制度,却不认可依照汉人的丧葬礼制。如成宗大德八年(1304)发布命令禁止蒙古、色目官员父母丧亡丁优:“三年之丧,古今通制。今后除应当的怯薛人员、征戍军官外,其余官吏父母丧亡丁优,终制方许叙仕,夺情起复不拘此例,蒙古、色目人员各从本俗。”[15](卷10《吏部四·职制一》)仁宗朝再次重申强调:“官吏丁忧,已尝著令,今后并许终制,以厚风俗。朝廷夺情起复,蒙古、色目、管军官员,不拘此例。”[15](卷10《吏部四·职制一》)对于蒙古、色目人在丁忧礼制上效法汉俗的现象,一些蒙古、色目官员建议以剥夺官职来惩罚:“致和元年 (1328)夏四月己亥,塔失帖木儿、倒刺沙请‘凡蒙古、色目人效汉法丁忧者,除其名。’”[16](P185)但是蒙古和色目人采用汉族礼俗的现象已经无法禁止,“然流风所被,莫之能御也。”[16](P185)文宗于“天历元年(即致和元年)十二月戊午,诏蒙古、色目人愿丁父母忧者,听如旧制。”[16](P185)汉族人素来讲究忠义、节烈的伦理道德,这自然也影响了蒙古和色目人。
收继婚一直是蒙古等游牧民族持续的一种婚姻方式,在元代法律重要的渊源之一,即蒙古族第一部成文法典成吉思汗《大札撒》里有规定。统一全国以后,尽管元统治者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法律形式限制其他民族采用收继婚,但仍在法律中保留了蒙古本族收继婚俗,保护蒙古族固有的文化。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笔记中有此类记录:“顾世之名门巨族……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匹之念已萌于中者。”[17](P225)皇妃、公主和官宦妇女改嫁和收继的情况很普遍,如:克烈部王汗有孙女脱忽思哈敦,是拖雷的妻子,拖雷死后,脱忽思哈敦又为其子旭烈兀所收;元世祖女囊家真公主先嫁纳陈之子斡罗陈为继室,斡罗陈死,“改适纳陈子帖木儿,再适帖木儿之弟蛮台”[18](P2073);浙东廉访使脱脱赤颜“其生母何氏本父之妾,而兄妻之”[1](P768)。当蒙古族等草原游牧的婚姻习俗影响中原汉族婚姻时,汉族的习俗和文化观念也会影响他们。在《元史·烈女传》中记载了只鲁花真、别哥伦氏、贵哥、卜颜的斤、阿不察、脱脱真等蒙古族女性的贞烈行为。如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乃武宗、仁宗之姐妹,文宗之岳母,受汉族贞节观的影响,“早寡守节,不从诸叔继尚,鞠育遗孤”[1](P246)。雍吉剌氏脱脱尼,美貌善女工,年二十六时夫亡寡居,公然抗拒蒙古族的国俗收继婚,“前妻有二子皆壮,无妇,欲以本俗制收继之,脱脱尼以死自誓。二子复百计求遂,脱脱尼恚且骂曰:‘汝禽兽行,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见汝父地下?’二子惭慎谢罪,乃析业而居。三十年以贞操闻。”[1](P4495-4496)《元史·列女传》里还记载有这样的事例:“只鲁花真,蒙古氏。年二十六,夫忽都病卒,誓不再醮,孝养舅姑。逾二十五年,舅姑殁,尘衣垢面,庐于墓终身。至元间旌之。”[1](P4489)她们的表现已经和汉族贞节烈女并无区别,受到中原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已经不再遵从蒙古族旧俗,否定本族收继婚俗。一些蒙古、色目女子受汉族贞节观的影响抗拒收继及改嫁,《元史·列女传》有不少蒙古、色目贞烈女子,且有朝廷表彰其志守节事的记载。
元末至正十五年(1355)大斡耳朵儒学教授郑晅曾建议:“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1](P921)但是,汉族官员提出的蒙古统治者改变婚俗的建议,没有得到元廷的支持,说明了一点,有元一代,元朝廷坚持不同族群在礼仪上各依本俗。
元代多民族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与民族格局,在汉、西域色目、契丹、女真及蒙古草原民族融合的基础之上产生了文化认同,他们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认可、认同,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必然很容易取得汉族人民对他们的认同,正因为其他民族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所以才能形成元代的多民族融合。正如姚大力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文章中所谈到的:“华夏或者后来的汉民族很早就认为,华夏文化是一种普世适应的文化。华夏与周边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不是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一种普世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文明与半文明、乃至非文明之间的差异。这样,在前近代的中国人看来,所谓‘夷夏之辨’表面上是族类或种族的差异,实际上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差异。蛮夷如果提高了文明程度就可以变成华夏;相反,华夏的文明如果堕落,他们也会变成蛮夷。……由这样的立场出发,华夏民族的文化归属感超越了它的政治的或族类的归属感。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至上主义的传统把汉文化、而不是国家或族类(即种族)作为忠诚的对象。只要能够坚持‘用夏变夷’的文化策略,那么从政治上接受蛮夷的统治也是可以的。”[19]在国家高度统一,多民族各地域文化融合的情况下形成了多种族、多文化、多风俗并容的“大元气象”,即为元代文化的多元性。此为“文化的大一统,大元朝文德远被,文化学术的多元相容”[20](P18)。
正因为元代中华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这种文化的包容,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而且多族文人共同创造了元代文学的辉煌,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近代史学家陈垣在20世纪初就已经对元代诗文成就做出了充分肯定:“(元代)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明人蔽于战胜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王夫之夕堂永日诸论外编,谓胡元诗人贯云石、萨天锡、欲矫宋诗之衰,而膻气乘之云云,其一例也。”[5](P132)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来看,元代文学是不容忽视的,与汉、唐、宋相比之下,元代文学有元代文学的辉煌和特色,元代诗文作家中也有大家出现,作家群体由多民族文人构成,诗歌和文章的风格与题材均有新的开拓,并呈现多样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