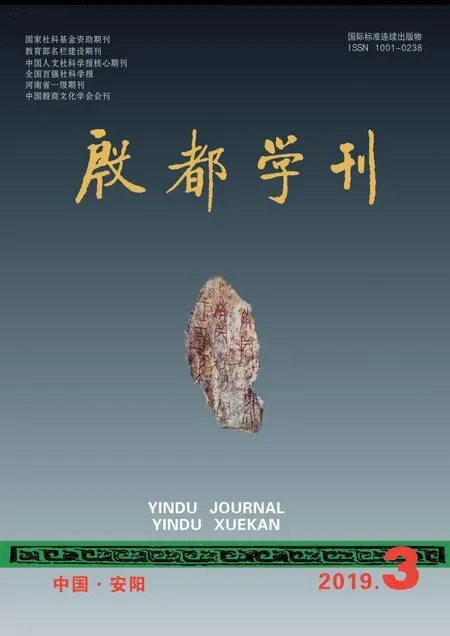元儒吴澄对“游”的多维度阐释
2019-12-16吴竺轩
吴竺轩
(复旦大学 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433)
吴澄(1249-1333),字幼清,晚字伯清,号草庐,江西抚州崇仁人,元代著名的理学家,与许衡并称“北许南吴”。作为连接宋、明理学的重要人物,吴澄在学术上的贡献自是有目共睹,但是对于他理学成就的偏重研究,掩盖了他在文学上迸发出的闪光点。吴澄的百卷文集中包含了许多他关于文学的思索与探讨(1)关于吴澄现存文集的优劣比较,可参见方旭东所著《吴澄评传》的附录二《吴澄文集版本源流考》一文,在此文中作者总结说:“现有版本中,以宣德版为最早,然其仅有之全本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取阅不易。而四库本在卷次编排上沿袭宣德本,且已有影印本,较容易取得,故四库本可作为研究参考版本。”(《吴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68页)本文所引文献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都以四库本为出处,不再赘述。。笔者在阅读吴澄文集的过程中发现,“游”作为一个关键词在其文章中高频率地出现,与通常认为的“游”作为人类活动之一种的单纯意义不同,吴澄笔下的“游”含义非常丰富,并成为一个媒介,勾连着作者理学思想与文学主张的两端,是理解吴澄何以基于自己的理学修养来构建其相对应的文学观念的有效切入点。本文试以吴澄对“游”的多重含义划分入手,通过分析“游”背后所蕴藏的理学渊源以及它在吴澄文章语境下与诗文创作的关系,以此来探求理学家吴澄笔下的理学与文学所发生的交互影响,即他的文学主张是如何从理学思想中衍生发展出来的。
一、吴澄文章中“游”的多重含义
王素美先生在对吴澄的理论思维方式进行概述时,首先就提到吴澄在推理论证中所运用的最基本的两种方法——划分和分类。“划分是明确概念全部外延的逻辑方法,吴澄在其理论创新的整个过程中使用划分的标准明确概念,能准确地划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与此并行,他还准确地运用分类的方法”[1](P18),并且,“吴澄运用划分方法准确地运用了一次划分、二次划分、三次划分和多元划分”[1](P18)。总的来说,吴澄善于在论证的时候使用划分以及与之并行的分类方法,将某一概念分为几种情况分别进行阐释,在几种情况下又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划分,彼此之间相互照应,组合起来就是对这个概念最完整的解释。如果不以现代的哲学术语予以描述的话,吴澄的这种做法其实源于传统程朱理学中“理一分殊”的思维模式。“理一分殊”最早出现在程颐对于张载《西铭》的解读中,其后经过多位宋儒的补充,在朱熹处集其大成,朱子将“理一分殊”的应用范围从程颐最初所讲的道德领域扩散为处理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原则[2]。以接续朱子思想自命的吴澄,在思考问题时也自然继承了“理一分殊”的思维模式,并将它运用得炉火纯青,其文章中对“游”的多重含义的阐释即是典型的例证。将“游”作为目标概念,吴澄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从三个相对独立的角度对“游”作了较为全面的剖析解读。
其一,以时间为依据,“游”可分为“古代之游”与“今世之游”:
自王政衰陵夷,至于春秋,至于战国,生民涂炭,孔孟抱济世之具而时不用,圣贤不忍恝然忘天下于是乎历聘环辙,而当时洁身避世之士犹且非之,倘无圣贤救世之心而游焉,则其非之也,又当如之何哉?七雄以力相并吞,冀得权谋术数之流,不爱高爵厚禄,以招致游士。游士因得肆其意以傲世主,然孟子比之妾妇,则其可贱甚矣。汉晋隋唐以来,游者不得如战国之盛,宋之季,士或不利于科举而游,入事台谏,则内外庶官畏之;出事牧伯,则郡县庶民畏之,虽不能如战国之士立跻显荣,而挟其口舌中伤之毒,亦可要重糈于人。若夫游于今之世,则异是。上之人无所资乎尔,下之人无所畏乎尔,于身既不可以骤升,于财又不可以苟得,叩富儿门,随肥马尘,悲辛于残杯冷炙之余;伺候公卿,奔走形势,侥幸于污秽形辟之地,不过如子美、退之所云,其可哀也夫。而好游者诿曰:“吾之游,非以蕲名,非以干利,将以为学焉尔。”是大不然。[3](卷四《收说游说有序》)
吴澄以古与今为基本条件划分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游”,为了更详尽地说明每种情况下“游”更细微的差别,又进行了二次划分。同样是古代之游,孔孟为救世而游四方,游士为求私利而走各处。今世之游中,游于富贵之门的求利,奔于权势之家的图名,其中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其二,基于主体的不同,“游”又可分为“君子之游”与“世俗之游”:
太虚以颖敏之资,刻苦之学,善书工诗,缀文研经,修于己不求知于人,三十余年矣。口未尝谈爵禄,目未尝睹权势,一旦而忽有万里之游,此人之所怪而余知其心也。……太虚肯如是哉?书必钟王,诗必韦陶,文不韩柳班马不止也,且方窥闯圣人之经,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讵敢以平日所见所闻自多乎?此太虚今日之所以游也。[3](卷三十四《送何太虚北游序》)
世俗之游者曰为名为利而已。[3] (卷六十一《书嚣嚣序后》)
吴澄盛赞表弟何中“以颖敏之资,刻苦之学,善书工诗,缀文研经,修于己不求知于人,三十余年矣”,俨然一位极具修养的君子模样,与世俗之人有着本质的差别。可见行为主体的不同也是决定“游”含义不同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三,当目的有所区别时,“游”则可分为“为道之游”与“为利之游”:
圣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非博见于外,虽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闻寡见,不免孤陋之讥,取友者一乡未足而之一国,一国未足而之天下,尤以天下为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渊明所以欲寻圣贤遗迹于中都也。然则士何可以不游也。而后之游者或异乎是,方其出而游上国也,奔趋乎爵禄之府,伺候乎权势之门,摇尾而乞怜,胁肩而取媚,以侥幸于寸进,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岂有意于行吾志哉!岂有意于称吾职哉!苟可以寇攘其人,盈厌吾欲,囊橐既充,则扬扬而去尔。是故昔之游者为道,后之游者为利,游则同而所以游者不同。[3] (卷三十四《送何太虚北游序》)
在此段论述中,吴澄以“所以游者不同”明确区分了为道而游与为利而游两种不同情况,对前者明显持肯定欣赏的态度。
虽然以上述三个标准分别讨论的时候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将它们聚在一起就会发现三种情况并不能完全相互剥离,它们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大致形成了两条关于“游”的连贯路径,“古代之游”通常为“君子之游”,以求道为目的;“今世之游”多半是“世俗之游”,以名利为追求。前文已经提到吴澄对“古代之游”进行了二次划分,虽然能更完整地说明概念包括的各种可能性,也使得它与“君子之游”有矛盾之处,两个集合不能百分之百相交,故而这是两条略显粗疏的脉络。吴澄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各个划分标准之间存在的交叉问题,所以他有意避免了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使用两种同等级的标准阐释“游”的概念,使得单独看待三个不同标准下吴澄对于“游”的阐释的时候,不会出现明显的龃龉。有趣的是,吴澄对于这两条约略的线索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情感态度,使得我们可以将“游”的不同层次的含义作为切入点以进一步剖析吴澄理学思想与文学主张的交互作用。
二、吴澄对“游”的预设条件
对于“游”在不同情况下的论述,吴澄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倾向,基于前文总结的两条约略的路径,他赞赏前者,批判后者,其中原因何在呢?这涉及吴澄划分“游”的不同标准背后潜在的条件性预设。但在正式分析预设条件之前,我们还必须对“游”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只有明白了为什么“游”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才能理解吴澄为何称赏某些特定的“游”。对于某事或物合理性的确认,是吴澄文章论述中绕不开的逻辑起点,只有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对于它更具体的讨论才成为可能。合理性最直接也最有效的获取方法就是从历史中寻找依据,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古为鉴——要么在过去的书籍中找到依据,要么在过往的人身上得到认同——吴澄在证明“游”的存在时,两方面均有所体现,下面将分别论之。从儒家经典中寻找依据,对于一个理学家来说是最有说服力的做法。吴澄于诸经中对《易》最为精通,他对于“游”的论证也以《易》为基础展开。“《易》坤下巽上之卦为观”[3](卷十《解观伯中字说》),“观也者,坤地柔顺卑下之民仰视九五阳刚中正之君也,然观之初曰童观,观之六二曰窥观,童者,盖如婴孩童稚之观;窥者,盖如妇女窥觇之观,所观狭少而所见不能以广大,是何也?初与二在下,远于九五也,夫至广大者,天也,戴盆而观之,坐井而观之,岂能见天之广大也哉?以下观上而远于天位,何以异于戴盆坐井而观天乎?若观之六四则切近九五矣,故其繇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然则观盛治者宜近不宜远也。”[3](卷二十五《送徐则用北上序》)《易》的观卦中有一繇辞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观国之光”换种表达就是游于国都,吴澄敏锐地发现了“游”与“观”在特定条件下的同义性,将“游”等同于“观国之光”,顺理成章地从经典中获得了“游”的合理性。“观国之光”对于吴澄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支持行为正确性的理论依据,在虞集为吴澄所写的行状和危素所撰的年谱中,都不约而同地记录了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请吴澄出仕的理由,即以观国之光邀之(2)《虞集行状》:“二十三年,程文宪公奉诏起遗逸于江南,至抚州,强起先生,以母老辞。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无一观乎?’”(见《吴文正集》附录)《危素年谱》:“(二十三年丙戌八月释服)程文宪公以江南行台侍御史承诏访求遗逸,有德行才艺者即驿送入觐。冬,程公至抚州,命郡县问劳迎致,强公出仕,力以母老辞。程公曰:‘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公诺之。”(见《吴文正集》附录),吴澄在自述中也是如此说明(3)卷五十四《题程侍御远斋记后》:“余既从公观光上国,又将从公而南。”。可见从经典中获得的合理性对于一个理学家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除此之外,古代圣人的行为则为“游”的合理性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资证。“然夫子,大圣人也,适周而问未问之礼,自卫而正未正之乐,征夏殷之文献而必杞之宋也,况下乎圣人者乎?览不厌其广也,识不厌其博也,见闻不厌其多也,不广不博不多则不无孤陋之讥,予其敢禁子之游乎?”[3](卷二十七《送陈中吉序》)圣人虽然生而知之,但“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非博见于外,虽上智亦何能悉知也”[3](卷三十四《送何太虚北游序》),从这个角度来说,“游”的存在确实具有一定意义。
既然“游”的合理性已经得到论证,那么为何吴澄对于不同的“游”又存在明显的态度差异呢?比较他对不同情况下的“游”的褒贬,其背后或许有某些暗藏的评价标准在发挥作用,即何人可游?何时可游?吴澄在论述中分别从主体和时间两方面对“游”作了条件预设,从而推导出他真正欣赏的“游”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为了更好地说明预设的条件,笔者各选取了一段吴澄反对与支持的“游”以供比较:
子之年方壮,质甚美,宜及时而勉学,以成身,以悦亲,苟如是,朋友亲之,党里敬之,长老喜之,子弟孝之,推其余又可以如世俗之人取爵禄,顾不此之为而为,今之行,子计左矣。[3](卷二十七《送陈洪范序》)
庐陵陈植,延祐四年江西省所贡士也,试礼部罢归,益厉其志,读书为文不休,或告之曰:“子之学,学于古者也,士贵通古而通今,盍亦学于今乎?”于是将游四方以历览山川,遍识人物,过予道其行之意。[3](卷二十七《送陈中吉序》)
这两段材料分别针对不同对象而作,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直接可以比较的切入点,但细读吴澄对两人的描述可知这两位年轻人最本质的差异在于他们的个人修养上。吴澄肯定了陈植“读书为文不休”的做法,认为其人已经“学于古”;但在对陈洪范谆谆教导时则劝诫他应该及时勉学。措辞的差别暗示出他们个体修养之不同,一个已经具有相当的学养,而另一个则还未窥得初学之门径。在其他吴澄所支持的远游中,均可以发现闲笔套话似的对于远游者个人修养的描述,如称“黄孚文中尝学于予”[3](卷三十一《送黄文中游京师序》),夸何中“窥闯圣人之经”[3](卷三十四《送何太虚北游序》),隐藏于这些“套语”背后的是吴澄心中对于“游”的主体的个人修养的条件预设,即一个人要对于圣人之书有所涉猎,对于圣人之道有所了解。这种预设条件的产生不难理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人修养使得人具备了基本正确的价值观,当其外出游历时才不会被乱花迷眼,偏离了自己的方向而一无所获。故而吴澄对于那些不具备此条件的年轻人提出的希望是:“当以朱子所训释之四书朝暮昼夜,不懈不辍,玩绎其文,探索其义,文义既通,反求诸我,书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实用其力,明之于心,诚之于身,非但读诵讲说其文辞义理而已。”[3](卷二十七《送陈洪范序》)“游”以增广见闻直接关涉理学家的格物致知之论,但吴澄对于读书和游历两种格物致知方法显然有所区别,正如方旭东先生解释的那样,“对外部事物的了解几乎都可以说与伦理有关。但是,与伦理的相关又有直接与间接之分。相对而言,程朱一系的格物工夫更重视读书讲学”[4](P118),“与程朱相同,吴澄也强调读书时学者的入门工夫,他说:‘明明之法不一,读书为入门,亦其一也。’此外,他也认为对物理的探究不是为学先务之所急,如他曾为学者讲解有关宇宙生成原理,时人颇有热心于斯者,或传录以去,或逐节画而为图,有见于此,吴澄特意告诫说:‘此特穷理之一端尔,人之为学,犹有切近于己者,当知所先后也。’”[4](227—228)基于读书工夫和探究物理的先后顺序,吴澄很自然地在作为探究物理手段的“游”的前面预设了读书工夫,这种预设条件的产生背后其实有深刻的理学渊源。
在“游”的时间选择上,吴澄传记资料里的另一个小细节为我们理解他预设的时间条件提供了线索。按照年谱的记载,元至正二十三年当程钜夫以观国之光征得吴澄同意后,吴澄立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归白游夫人”,虞集在行状中也特别写明“母夫人喜其行”。之前吴澄以母老为由推辞程公的邀约,其后虽然出仕但不过几月就以母老辞归,通过征得母亲或者说家中长辈的同意之后才能出行成为吴澄对于“游”预设的时间限制。他在劝阻士人出游时曾说:“道修于家可也,既仕而驱驰王事,则有四方之役,处士而离父母、去妻子,栖栖奔走,将何求哉?”[3](卷二十六《赠道士黄平仲远游序》)以不能侍奉父母作为主要理由来论证出游的不合时宜,看起来似乎颇为空泛,而吴本人以母老辞官,按照我们通常对于古人的理解,这更像是为官不得意的借口。但作为一个讲求真知实行的学者,“孝”对于吴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曾在多篇文章中对“孝”进行讨论,将“孝”区分为“世俗之孝”和“君子之孝”,世俗以身居高位、显荣父母为孝,君子之孝则以亲身侍奉左右为孝[3](卷二十七《国学生李黼泗州省亲序》)。关于孝与仕的矛盾性,吴澄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侈录如下:
古之仕者三,后世行可之仕几于无,而际可之仕亦或鲜矣,大率皆公养之仕也,夫既日公养则有亲者,凡以为其亲而已,养不便不仕可也,盖人之大伦五,父子其首也,孝于父斯可移于君,自非贵戚大臣身系社稷安危,膺托孤寄命之重,不得不以公义夺私情,苟守一官一职去就繇已,而诿曰委身为国,不顾其私,虽曰不贪荣,吾不信也。余犹记数十年前仕而少亏于子道,清议不容,不以人类比,数坐是终身沦废者有焉,而窃怪海宇混同以来东西南北之相去地理辽绝,有违其乡而仕远方者,于其亲也,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十余年而不一省,不惟安否之问,甘旨之供阙,至有畜妻抱子、新美田宅于它所而其亲自营衣食,自给繇役于家,窘穷劳苦而莫之恤,老矣而无欢,或不幸永诀而不相闻,甚者闻而不奔,又甚者匿而不发,饮食衣服、言语政事扬扬如平时,噫!是岂独无人心哉?[3](卷三十一《送李文卿序》)
在吴澄看来,若非担任特别重要的官员,一般类型的出仕都不能与孝亲相比,亲身侍奉父母是身为人子的应有之义。可见他以母老婉拒并非通常的推脱之辞,而是受到从心到身都力求做到的孝的影响。正如他当年出仕首先征得了母亲同意才成行一样,在他所支持的远游中,如果家中父母健在,他都会特别提及征得父母同意这个细节,弟子夏友兰游历京师时,吴澄称“幼安白慈亲愿观国光,亲许,遂趋京师”[3](卷七十四《元将仕作郎赣州路同知会昌州事夏侯墓志铭》);而家中长辈已逝,无亲可侍奉同样也为出游创造了时间条件,他赞同徐则用北游,正是因为徐氏自述说“在家已无亲可事矣”[3](卷二十五《送徐则用北上序》),这些都表明吴澄在个人出游的时间选择上确实预设了条件。
个人修养的要求和出行时间的限制共同发挥作用,最终决定了吴澄对于不同情况的“游”的差别对待,只有明白了这两个预设条件存在的理据,才能更好地理解吴澄文章语境下对于“游”的阐释,也才能透过“游”这个外在的行为去探求其背后蕴含的更深层的吴澄的理学思想。
三、吴澄对“游”的效用分析
吴澄在为弟子黄孚出游所撰赠序中提到“《易》曰:‘出而有获’”,此可作为吴对“游”之效用的概括。出游则必有所收获,那么所得为何呢?前文已提到以目的作为划分标准,“游”可分为“为道之游”和“为利之游”两种,吴澄显然称赏前者,摒弃后者,但“道”是一个包揽甚广的大概念,“为道之游”的“道”到底指什么呢?吴澄在文中数次提及“游”对增长见闻的作用,“士之贵乎多见多闻也,尚矣。……居则有过从,出则有交游,于郡县山川靡不遍览,于政教风俗靡不周知,所以通今也”[3](卷二十八《送曾叔诚序》),更具体一点说,闻见包括“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等各个方面,这些都需要游历于各处才能获得,但为什么吴澄会将游所得之闻见归于“道”之一端呢?这涉及理学传统中对闻见之知的看法:“夫闻见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又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3](卷二《评郑夹漈通志答刘教谕》)闻见是得之于外的,它虽然属于格物致知的一种而被纳入理学家所认可的“道”的范围,但却不能对一个人的秉性产生直接的影响,“闻见得之于外,如果没有反诸身心、见诸实行,也就是说凝为德性、化为德行,那么,他终究不过是口耳之学,而非真知。”[4](P116)游历所得的闻见之知必须反身于我,经过自我的内在转换成为德性之知后,才能对一个人的本性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故吴澄认为“游”的效用并不局限于闻见之知的获得,作为对于个人修养的极为重视的理学家,他显然希望“游”能达到更高层次的效果。所以在《送徐则用北上序》一文中,吴澄在称赏徐氏以解读《易》的方式为出游寻找合理性之后,他又补充说道:“子通经术,闲时务方,当强仕往近天子之光,其可。观之上九曰观其生,观其生者,自观一身也,上九远处一卦之外物外人也,他无所观,唯自观其身而已。子年鼎盛宜在近而观于国,予年衰耄宜在远而观其身。”此处吴澄以自己为例表示从观卦中获得合理性的“游”,其最终目的是要反身于我,如果说增广闻见是一个“博”的过程,那么之后向“约”的回归则是更高层次的追求,“虽然既广矣,既博矣,既多矣,有反诸约之道焉,未广未博未多而径约,则不可也。子其行哉,俟他日之广博而多,当为子指其所谓约者,于斯时也,不出户而知天下,而何事乎游?”[3](卷二十七《送陈中吉序》)最后一句结语对理解吴澄关于“游”的整体态度尤为重要,在他看来,“游”永远只是一种手段,不可能成为最终目的,当游历所得的闻见之知经过反身于我的过程,进而发见出本来就存在于我心中的德性之后,“游”作为一种手段的必要性也就不复存在了,故曰“何事乎游”。
理解了“游”的直接效用和最终目的之后,当我们去看待吴澄对于“江山之助”的反驳的时候,才能真正明白他驳斥的理据所在。“江山之助”最早出现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然屈平所以能够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刘勰在此处将屈原的创作归功于江山风物,其后随着历代文人对“江山之助”概念的丰富和发展,其含义主要有两个面向:一是从创作动机角度阐说,认为江山之景能够引发创作冲动从而产生优秀的诗文;二是从作品风格角度解释,以为江山之景有利于作者文学风格的形成。吴澄对于“江山之助”的接受显然是针对后者,即针对人们普遍认可的江山风物能够对某一作者创作的诗文的风格发挥直接影响的观点进行辩驳。在吴澄看来,江山之助的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司马子长世掌文史,父子授受而负杰然不羁之才,虽使终身不出门户,亦自有此雄健之笔,岂得于游哉?谓子长因游而有史者,谬也,信其说者,惑也。”[3](卷四《收说游说有序》)不同于大家普遍将司马迁的《史记》创作归功于他游历四海而得江山之助,吴澄认为影响其创作的关键要素一在于司马家世代的文学积淀,二在于司马迁的才气过人,与江山之助毫不相关。为了更好地理解吴澄的辩驳依据,我们不妨对吴澄文学思想中关于诗文创作要素的讨论略作分析。他在《元复初文集序》一文中集中谈到了这个问题:“非学非识,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气,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备,文其能以纯备乎?”[3](卷十九《元复初文集序》)在吴澄看来,文学创作的要素有四,主要分为两组,学与识为一组,才与气为一组,在诗文创作中“理为之主,气为之辅”[3](卷二十二《吴伯恭诗序》),主与辅又分别与两组要素对应。概括而言,前一组主导的是诗文创作的内容,因为有学识的积淀,使得作品中有理作为支撑。后一组影响的是诗文外在的风格,“韩子之论文,谓气盛则言之短长,声之高下皆宜。夫诗与文之有资于气也,尚矣。翰林侍读学士李仲渊心易直而气劲健,其为气也肖其人。……盖其平日淹贯古今诸名家诗,芳润熏渍乎肝脾,英华含咀乎颐辅,藏蓄既富,而气质盛又足以驱役左右之,俾效供给,而各职其职,非若孱懦之帅拥兵百万而拙于调用,故出乎喉吻,溢乎毫端,与名家诗人之态度声响无一不似。”[3](卷二十二《李侍读诗序》)吴澄认为诗文肖其人,一个人的个性气质如何,就会创作出相对应风格的文学作品。所以综观吴澄的文学创作论可以发现其中完全没有江山之助存在的空间,尤其是影响作品风格的一端更是一个人天生的秉性在发挥作用,所以普遍认为的江山之助对于作品风格的直接影响在吴澄的文学主张中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再者,前文已经论及“游”只能作为一种手段而不能成为最终目的,它所提供的闻见之知如果不能反身于我经过自身的内在转换,就永远只是口耳之学,对于个人气质秉性没有任何实质的影响,那么游历于江山自然也就无法对受到个人气质主导的作品风格发挥直接的作用。吴澄对于江山之助的反驳虽然表面看起来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但以“游”作为实质的江山之助却成功勾连了吴澄关于“游”的一系列理学思考,从而将吴氏思想中理学与文学的交互关系巧妙地呈现了出来。
在吴澄的文集中,高频率出现的“游”被作者从不同角度作了详尽的阐释,以时间、主体和目的作为划分标准,明显表现出他对于“古代之游”、“君子之游”和“为道之游”的欣赏态度,其背后暗藏着他对于“游”的预设条件,只有当个人在学养方面有所成就并且征得父母同意之后,这样的出游才值得肯定。从结果来说,“游”永远只是一个手段而不能成为最终目的,故而它不能对一个人的德性发挥直接的作用。有鉴于此,在吴澄文学主张中的个人气质秉性影响作品风格的前提下,江山之助的说法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本文以“游”为媒介勾连理学与文学的两端,希望能够展现出吴澄的理学思想是如何对其文学主张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