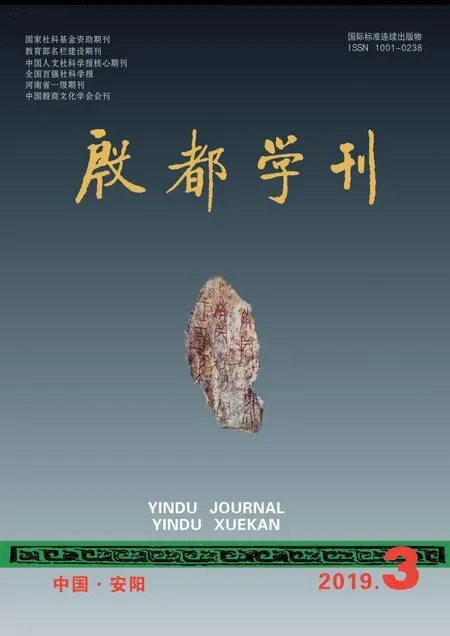“使气为戏”与晚明曲学的嬗变
2019-12-16石超
石 超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中国古代文学中以气论文的思想起源很早,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气论观一直未被引入戏曲创作和批评领域,或者说,虽然在戏曲创作和批评中一直贯穿着这种气论观,但没有曲论家进行过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在徐渭之前,几乎没有曲论家将文气论与戏曲批评相结合,只有朱权的《太和正音谱》中略有提及,书中言:“且如词中有字多难唱处,横放杰出者,皆是才人栓缚不住的豪气。然此若非老于文学者,则为劣调矣。”[1](P23)徐渭是将“气”论思想引入曲学领域的重要人物,关于这一点,苏涵已有专文论述。本文认为,徐渭不仅充分认识到元杂剧中饱含的生命之气,而且自觉地进行体认和养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气论观,并以此为指导,进行戏曲创作和评点,凭借对生命之气和真性情的推崇,使自己的作品和评点之作在晚明广受欢迎,对后世戏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元杂剧中的“苍莽雄宕之气”
元杂剧的创作过程中一直贯穿着“苍莽雄宕之气”,可以说这种郁积之气是元杂剧精神力量和艺术生命的本源。杂剧家可能并未意识到胸中郁积的跌宕之气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也没有形成自觉性的自我体认,但到明代中后期时,这种气慢慢被曲论家们发觉和重视,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赞赏和推崇。如徐渭《南词叙录》中说:
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迂徐绵渺,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2](P245)
在徐渭看来,北曲是灌注着一种气的,这种气“使人神气鹰扬”,足以鼓动人心,带有某种宣泄的味道。袁宏道也有同样论述,《徐文长传》中云:
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3](P1342)
到明中后期时,这种豪达意气已经被厘定为元杂剧固有的特质,甚至成为明人渴慕的对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明代前中期的剧坛缺少这种生命之气,使元杂剧中的气至此被涂上了孤绝的色彩。近人王国维和吴梅对这种生命之气也是亲睐有加,推崇备至。《宋元戏曲史》中云:
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4](P98)
《中国戏曲概论》亦言:
至就文字论,大抵元词以拙朴胜,明则研丽矣。元剧排场至劣,明则有次第矣。然而苍莽雄宕之气,则明人远不及元,此亦文学上自然之趋向也。[5](P154)
正是由于元杂剧抒发了作者胸中郁积的跌宕愤懑之气,是至真至纯的表达,所以才被王国维推崇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成为后世杂剧难以企及的高峰。亦如李渔所言:“凡做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而后鬼神效灵。予以生花之笔,撰为倒峡之词,使人人赞美,百世流芳——传非文字之传,一念之正气使传也。”[6](P12)元杂剧中贯穿的这种生命之气不仅成为一代才人的精神写照,也使这些作品因“苍莽雄宕之气”的灌注而成为永恒。
元杂剧中之所以能灌注如此强烈的生命之气,与杂剧作家的生存境遇是密不可分的。元代统治者是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的,这在中国历代上还是第一次,身份的差异使汉族文人与元朝统治者无法实现心灵上的认同,他们之间永远都有一种无法消除的隔膜感。再加上元朝实行等级森严的四等人制度,使江南文人无法进入统治权力的中心,后来更是一度废除科举,封闭了知识分子读书致仕的唯一途径,使他们报国无门,只能或是混迹江湖,郁郁而终,或是别寻他路,寄托余生。正如明正德时进士胡侍《真珠船》中所言:
盖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尽其国人为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如关汉卿入太医院尹,马致远浙江行省务官,宫大用钓台山长,郑德辉杭州路吏,张小山首领官,其他屈在簿书,老于布素者,尚多有之。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7](P182)
大部分的元曲家都是“沉抑下僚,志不获展”,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这与元朝广阔的疆域和雄胜的武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国运的强盛并未带来文人文化上的自信,或者更确切地说,元杂剧中并没有体现出国运昌隆的繁盛之气,俯拾皆是的反而是作家的愤懑不平之气。左东岭认为:“元王朝以气运论的确是博大雄迈的,但这博大雄迈不是文人的好运而是噩运,因此也支撑不起他们的心灵世界。”“之所以会造成诗文与时代的脱节,是由于汉族文人与元蒙朝廷之间无法消除的隔阂,即作为诗文创作主体的汉族文人尤其是江南文人,永远无法进入权力的中心,因而他们也无法将自我个性的伸展与朝廷疆域的广大有机结合起来。”[8]因为在杂剧作家的心灵深处没有与元朝廷达成一致,这种离异状态使杂剧作家无法建立起文化上的自信,将自身创作和政治相勾连,像盛唐那样以高昂激情赞颂国运昌隆,他们更多地只能是排遣和宣泄心中的抑郁之气和生不逢时之感,所以元杂剧中饱含“苍莽雄宕之气”。
可以说元杂剧中灌注的“苍莽雄宕之气”是曲家不自觉的行为,他们并未认识到气论观对于杂剧创作的影响,更多地仅仅只是因为现实的境遇使自己志不得伸,于是郁积难平,不吐不快,只需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奔泻而出即可获得动人心魄的阅读直感,并无理论层面的指导。
二、徐渭的“使气为戏”
徐渭“尝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3](P1341),其实,未被提及的曲才是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西陵澄道人《四声猿引》中云:“宁特与实父、汉卿辈争雄长,为明曲之第一,即以为有明绝奇文字之第一,亦无不可。”[3](P1357)清初邹漪亦言:“明南北剧不下数百家,唯徐文长《四声猿》称独步。”可知徐渭在明代剧坛独树一帜,《四声猿》更是广受欢迎,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其曲亦多奇绝之气。
(一)徐渭的气论观
一般认为,“气”在作者主观层面就是指作家的精神、气质和个性,既有先天的秉性和才气,又有后天的道德修养和受社会条件影响形成的精神个性。从这一角度而言,徐渭剧作中的气与元杂剧中的气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元杂剧中灌注的“苍莽雄宕之气”是一种无意识行为的话,那么徐渭的“使气为戏”就多少带有一些自觉和自我体认的味道;元杂剧中的气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奔泻而出,体现出人之性情的至真至纯的原始状态,而徐渭所言之气则是为扭转明代前期剧坛的理学之气,转而向内心求“真”,有刻意为之的倾向。
徐渭的气论观与其命途多舛的生命轨迹是相联系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社会的不平和命运的不公造就了郁积胸中的强烈的生命之气,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3](P1343)
除了生命轨迹与元曲家相似外,徐渭的文气论还与他豪放不羁的性格相关,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让他对气的认识与元曲家有了本质的不同,即徐渭对气有了自觉性的认识。他在代人所作的《石顶浮图记》中云:
予尝谓人处天地间,而气与之通。气有温凉寒暑浊清忻惨和沴,凡此诸祥与诸不祥,并从人口鼻肤孔,荣于藏府,乃始浇漱志虑,储于心胸而发挥于事业,与饮食衣服功用大相等,盖一吞吐服习间而灵蠢系之。[3](P604)
除了自觉性的体认之外,徐渭还将“治气”与“治心”联系起来,对于养气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其在《治气治心》中言:
凡人之情,养之于闲,则始可期于猝,炼之于缓,则始可责其效于临时。夫以七尺躯壳之中,充塞之物,与吾一寸之灵,素不相知而不相得也。平居荒其养,而卤莽其炼,一旦有事而使之,而期之,辟之豪奴之于乍主,孰听之而孰从之哉?古之将多矣,无不治其气与心,而其治气与心,无不养之于闲,而始责期于猝,炼之于缓,而始求其效于临时。……古之言将者,儒与将一也。儒与将一,故治气与治心一也。今之言将者,儒与将二也。儒与将二,故治气与治心,鼓且决者以属之将,而不鼓且决者以属之儒也。惜也,以孙子之才,其于心与气也,能知治之矣,而不知一之也。何也?心主气,气从心一也。[3](P892-893)
此文以“气”、“心”相结合来论将,并与孙子之法相比较,可谓见解深刻,虽不是直接言明气论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但对气论的认识亦是精深而独到的,特别是将“情”、“气”与“养”相结合,不仅是自觉体认的表现,更体现出养气的重要性。文中指出,如若无气,“一旦有事而使之,而期之,辟之豪奴之于乍主,孰听之而孰从之哉?”这种积聚内心的充盈之气与文学创作是相通的。由此也说明,与元曲家相比,徐渭对“气”已经开始了自觉地体认,不仅已经认识到北曲“以气入曲”的特质,并且自觉地将这种气论观引入到自己的戏曲创作与批评中。此外,还将“气”与“情”相连,表现出对生命之气和真性情的推崇与激赏。
(二)“气实使文”与戏曲创作
徐渭的戏曲作品主要是杂剧《四声猿》和理论著作《南词叙录》(1)笔者未将《歌代啸》列为徐渭的作品,是因为袁宏道、陶望龄等最早的徐渭研究专家都对该剧作者存疑,而目前又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为徐渭所作,所以姑且存疑。,关于《四声猿》的创作时间,早在明代时就有不同意见,王骥德和孟称舜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根据王骥德《曲律》的记载,四剧创作于不同时期,《玉禅师》是早年戏笔,其他三剧稍晚。今所见《四声猿》最早的版本是万历十六年龙峰徐氏梓行本,则该剧创作应不晚于万历十六年。《南词叙录》是嘉靖三十五年徐渭客闽时所作。这些著作中灌注着生命之气与徐渭的个性气质,与其生命轨迹是息息相关的,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其生命之气的自然流露。正如黄汝亨在《徐文长集序》中所云:“按其生平,即不免偏宕亡状,逼仄不广,皆从正气激射而去,如剑芒江涛,政复不可遏灭”。[3](P1355)正是这股“不可遏灭”之气,使徐渭的戏曲创作和评点迥异于时人,在明代剧坛上独树一帜。
1.不拘于声律规范和格式俗套
关于戏曲的声律规范问题,沈璟和汤显祖之间有一场大争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的汤显祖是步了徐渭的后尘,他们都将抒写真情和生命之气作为戏曲之根本,亦如凌廷堪《论曲》绝句所云:“四声猿后古音乖,接踵还魂复紫钗;一自青藤开别派,更谁乐府继诚斋。”[9](P408)这种气在两人的作品中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声猿》中,不协音律的地方随处皆是。吴梅在校勘《四声猿》时说:“《狂鼓史》……[葫芦草混]一曲,系合[油葫芦]、[寄生草]、[混江龙]三牌,从来词家,并无此格。”[10](P420)对此,周贻白也曾进行过具体的指认:“如《渔阳弄》一剧,为仙吕宫的全套北曲,他在套中却用上一个[葫芦草混]的犯调。《翠乡梦》的北曲联套很规矩,但两出都用的是双调,曲调也大体相同。《雌木兰》第一出用仙吕宫北曲,联套亦为旧规;第二出却—开首便连用七支[清江引],接着用[耍孩儿四煞]带[尾声]作结。这形式,也是前此所未有的。《女状元》五出,皆为北曲,但第五出连用三支[半叫鹧鸪],更为少见。其为有意创新,断然无疑。”[11](P738)曾永义也曾列举《四声猿》中犯律的地方,认为“杂剧中像他这样不守律的,可以说绝无仅有了”。如《翠乡梦》中[新水令]常例应后接用[驻马听],[得胜令]前用[雁儿落],而《翠乡梦》[新水令]后用[步步骄],[得胜令]前用[江儿水],这都是有悖元曲常例的。(2)上述观点参见周群、谢建华:《徐渭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310页,在此为谢。《四声猿》虽未协律,但丝毫不影响接受者对其称赏,如祁彪佳评《翠乡梦》时说:“迩来词人依傍元曲,便夸胜场。文长一笔扫尽,直自我作祖,便觉元曲反落蹊径。”评《女状元》时说:“南曲多拗折字样,即具二十分才,不无减其六七。独文长奔逸不羁,不骫于法,亦不局于法。独鹘决云,百鲸吸海,差可拟其魄力。”[13](P141-142)只有沈徳符对其有所诟病:“北杂剧已为金元大手擅胜场,今人不复能措手……唯徐文长渭《四声猿》盛行,然以词家三尺律之,犹河汉也。”[14](P647)可见,《四声猿》的不守声律,明代时就已有了不同的看法,但从各自的描述看,《四声猿》在晚明的盛行却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不守声律外,徐渭的戏曲创作还突破了传统的格式俗套,同样以“自我作祖”的勇气,为适应戏曲的发展大势将南北曲的融汇之风进一步发扬光大,这突出表现在南杂剧的开创上。南北杂剧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曲调的不同,即一南一北。南北曲融合之势在贾仲明、朱有燉的作品中就已初现端倪,至徐渭时渐成风气。就曲调而言,《四声猿》夹杂南北之音,没有统一的宫调,《雌木兰》和《狂鼓史》用北曲,《女状元》则用南曲,《翠乡梦》则是南北合套。就折目而言,《四声猿》也没有遵守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惯例,《狂鼓史》一出,《翠乡梦》二出,《雌木兰》二出,《女状元》五出。就唱法而言,《四声猿》也没有遵守金元杂剧每一折由正末或者正旦独唱的范例,四剧中都没有一个主角独唱到底的,如《狂鼓史》先由生独唱,再分旦、生和外独唱,末尾合唱。就故事情节而言,《四声猿》杂剧写了四个故事,彼此互不相涉,完全是互相独立的故事,徐渭以此合为一剧,以主体精神统摄,而不靠情节贯穿,在杂剧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打破既有格局的剧作,使《四声猿》在明代剧坛上特立独行,不仅没有被当作文坛异类受到口诛笔伐,反而是被广泛地推崇,即便是对此颇有微词甚至是进行诟病的正统文人,也不得不承认徐渭在晚明剧坛的影响力。这种创作方式之所以能受到广泛地推崇,关键就在于剧作富于奇绝之气,而这又恰恰是明代前中期剧坛所缺乏的,可以说徐渭以奇绝之气入戏,突破前期剧坛理学之气的藩篱,成为当时剧坛的一抹亮色。
2.用本色语言“写其胸膈”
本色与当行问题在明代剧坛上也是一桩公案,就本色而言,徐渭的看法是较具代表性的,他“关于‘本色’的论述,实为后来这场大争论的前导。”[15](P353)徐渭的“本色”论是以求真为先导的,要“无今人时文气”,即要求唱词、宾白自然天成。《南词叙录》是十分推崇本色语的,书中云:“《琵琶》尚矣,其次则《玩江楼》、《江流儿》、《莺燕争春》、《荆钗》、《拜月》数种,稍有可观,其余皆俚俗语也;然有一高处:句句是本色语,无今人时文气。”又云:“或言‘《琵琶记》高处在《庆寿》、《成婚》、《弹琴》、《赏月》诸大套’,此犹有规模可寻。惟《食糠》、《尝药》、《筑坟》、《写真》诸作,从人心流出,严沧浪言‘水中之月,空中之影’,最不可到。如《十八答》,句句是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2](P243)可见,徐渭肯定的不是“犹有规模可寻”的诸大套之作,而是“从人心流出”的本色之语,即人之真性情最真实的表达。
语言的真和内容的真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以自然天成的语言,才能传达最真实的性情,如果多是精工雕琢之语,则往往陷入云山雾罩的泥潭,无法体认其中的真情。除了言辞的自然天成外,徐渭还要求作品内容表现人之真性情。他之所以推崇南戏,很大层面上也是因为南戏是人之真性情的自然表达。在编《选古今南北剧》时,亦是以此观念为指导,“人生堕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戏,拈叶止啼,情昉此已……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而南北剧为甚。”[3](P1296)徐渭对真性情的推崇并不只限于曲学领域,而是推及到整个文学艺术范畴,《胡大参集序》中云:
然予窃怪之,今世为文章,动言宗汉西京,负董、贾、刘、杨者满天下,至于词,非屈、宋、唐、景,则掩卷而不顾。及叩其极致,其于文也,求如贾生之通达国体,一疏万言,无一字不写其胸膈者,果满天下矣乎?或未必然也。于词也,求如宋玉之辨,其风于兰台,以感悟其主,使异代之人听之,犹足以兴,亦果满天下矣乎?亦或未必然也。[3](P907)
《肖甫诗序》中亦言:
古人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是以有诗而无诗人。迨于后世,则有诗人矣,乞诗之目多至不可胜应,而诗之格亦多至不可胜品,然其于诗,类皆本无是情,而情设以为之。夫设情以为之者,其趋在于干诗之名,干诗之名,其势必至于袭诗之格而剿其华词,审如是,则诗之实亡矣,是之谓有诗人而无诗。[3](P534)
作品无“情”即没有生命和灵魂,“则诗之实亡矣”,徐渭将抒发真情作为创作的不二法则,并贯穿到所有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也是针对当时文坛的师古崇法之风而来,认为拟古之法多是得其表,而未师其心,即未得古人创作之三昧。必须以本色语言“写其胸膈”,才能“使异代之人听之,犹足以兴”。这一看法在师古崇法时期,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以气论戏”与戏曲评点
徐渭的戏曲评点本一直真假难辨,其间夹杂诸多赝笔难以确认,但根据其弟子王骥德的记载,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确证的内容。王氏《曲律》言:“先生好谈词曲,每右本色,于《西厢》、《琵琶》皆有口授心解。”[16](P168)可知徐渭是评点过《西厢记》和《琵琶记》的,特别是《西厢记》的评点本影响较大,据储著炎统计,“‘徐评本’《西厢记》,现知存留7种,各本转相因袭,评批内容基本相同。”[17]综观现存之“徐评本”,以《西厢记》较多,评点内容亦可通过王氏所记得到印证,所以这里主要讨论《西厢记》中徐渭的评点思想。
王骥德曾言:“先生居与予仅隔一垣,就语无虚日,时口及崔传,每举新解,率出人意表。人有以刻本投者,亦往往随兴偶疏数语上方。故本各不同,有彼此矛盾,不相印合者。余所见凡数本,惟徐公子尔兼本,较备而确。今尔兼没不传,世动称先生注本,实多赝笔,且非全体也。”[18](P143)根据王氏的描述,徐尔兼本是“较备而确”的“徐评本”,可惜不传。王氏《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亦有很多徐氏的评点之语,王氏自言“余注自先生口授而外,于徐公子本采入较多”,可知此本中的徐评之语是最真实可信的。
除了在戏曲创作中推崇表现真性情外,徐渭在戏曲评点中亦是如此。他之所以对《西厢记》较为推崇,便是认为《西厢记》是人间真性情的流露,诚如其在《西厢序》中所云:
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众人啧啧者呴呴也。岂惟剧者,凡作者莫不如此,嗟哉,吾谁与语!众人所忽,余独详,众人所旨,余独唾。嗟哉,吾谁与语
通过“本色”、“相色”对比,意在说明自然天成的重要性,最终指向的则是真性情的流露。在评点过程中,徐渭不但对描写男女情欲的文字大加赞赏,对猥亵之词也不避讳,甚至还推崇备至,将其作为追求真性情的充分体现。如《西厢记》卷一第一套中:
[后庭花]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这步香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见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面。刚那了一步远,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神仙归洞天,空余杨柳烟,只闻鸟雀喧。[18](P29)
徐渭评点道:
衬残红二句,只应上白怎生便知他脚小意,休提眼角以下,又推出一层意,慢俄延以下四句,正脚踪儿将心事传也,刚刚打个照面,正眼角儿留情处也。栊门指莺莺进去之门,言其形之纡徐系恋,及门而举步差远,复打个照面而传情无已也。[18](P31)
这是张生和莺莺初次见面的情景,在男女问题比较保守的时代,徐渭对于莺莺的解读却是“眼角儿留情”、“纡徐系恋”,可谓处处传情,但毫无忸怩造作之感,表明他对于男女间的自然真情是充分认可和尊重的。徐评中处处彰显出这种特色,即便是猥亵之语也不回避,还刻意点出,推崇一番。如卷三第一套中:
[仙吕赏花时]针线无心不待拈,胭粉消香懒欲添。春恨压眉尖。若得灵犀一点,姐姐敢医可这病恹恹。[18](P69)
徐渭评点道:“此极亵之词,却用得免俗。”[18](P71)作出这一泼辣而犀利的点评是极需勇气和魄力的。此句本是书中的隐语,徐渭却解读成大家闺秀对于情欲的渴慕,而且是以推崇和赞赏的语气,无疑起到了“宣淫”的效果,而这也正是徐渭赞赏和推崇真性情的结果。
徐渭的戏曲创作和评点都是在其气论观的指导下进行的,对于生命之气和真性情的推崇,使他的戏曲创作往往突破常规,直指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展现自然天成的状态,而不拘于声律规范和格式俗套。对于评点而言,则往往发人所未发,肯定内心真实情欲的流露,哪怕是猥亵之语,依然是内心激荡的生命之气的展现。正是由于徐渭的戏曲创作和评点中,饱含着这种生命之气,才使其与正统文人格格不入的剧作和评点之作广受欢迎,也正是由于明代前中期的剧坛缺少这种气,才使晚明曲风在徐渭的影响下为之一变,由“理”的维度慢慢转向“情”的维度。
三、“使气为戏”对晚明曲学的影响
虽然气论观与曲学结缘较晚,但作为文学正统的诗、文却一直氤氲在文气传统中。明初古文家宋濂不但以气论文,言“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19](P481)还自觉秉承传统的“文气”观念,注重养气,《文原》中言:“为文必在养气。气与天地同,苟能充之,则可配序三灵,管摄万汇,不然,则一介之小夫尔。……气得其养,无所不周,无所不极也,揽而为文,无所不参,无所不包也。”[19](P1404-1405)宋濂提倡的这种气与元代气运论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元曲家的气更多带有个体化色彩的话,那么明初的这股气则与政治联姻,赋予了集体化、社会化的印记。亦如左东岭所言:
随着宋濂、刘基、王祎等浙东文人集团的介入现实政治以及朱明王朝的建立,文坛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即元末以杨维桢为首的吴中文人集团的文坛中心地位转移到了浙东文人集团手中,而文学思想中的“气”论也从主体之“气”转换为作者主体之“气”与客观景象相结合的气象论。这是一个从个体化情感到社会化情感、从批判宣泄到歌颂鼓吹、从超然审美到政治关注的过程。[8]
正是受这股创作之风的影响,使明初的剧坛与政治联姻,鼓吹道学以致多理学之气,其间固然是有明朝廷的引导和限制,但更多地还是内心缺少充盈之气,陷入拟古师法的怪圈。
(一)明初剧坛的理学之气
以戏曲论教化的观念,元代时就已出现,如夏庭芝《青楼集志》中云:
“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杂剧”则不然,君臣如:《伊尹扶汤》、《比干剖腹》,母子如:《伯瑜泣杖》、《剪发待宾》,夫妇如:《杀狗劝夫》、《磨刀谏妇》,兄弟如:《田真泣树》,《赵礼让肥》,朋友如:《管鲍分金》,《范张鸡黍》,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又非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之“院本”所可同日语矣。[20](P7)
“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在元代时就已成为杂剧的既有之意,进入明朝后,戏曲中的教化观点有增无减。开国之初,朱元璋就极力推崇《琵琶记》中的教化观,后继的朱棣更是以律令的形式对其进行规定:
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21](P347)
正是由于戏曲在民间广受欢迎,统治者才赋予了戏曲沉重的教化责任,不惜以小道之学承载大道之理,即使是皇室、大儒、宰辅,也纷纷染指戏曲,以此宣扬教化。朱权《太和正音谱》强调“盖杂剧者,太平之盛事,非太平则无以出。”要求戏曲“以饰太平”,讴歌“皇明之治,”“以歌人心之和”。朱有燉也说“使人咏歌搬演,亦可少补于世教”。邱浚《五伦全备记》的《副末开场》更是阐发了一整套戏曲教化纲领。当有人指责他以理学大儒之身留心此道时,他是很不高兴的,但因戏曲在宣扬伦理、教化民众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却也愿意为之。后继的邵灿强调“今即古,假为真,从教感起座间人。传奇莫作寻常看,识义由来可立身”。《香囊记》第一出“沁园春”词中云“因续取五伦新传,标记紫香囊”,表明本剧承继了邱浚的道统思想,下场诗亦云:“忠臣孝子重纲常,慈母贞妻德允臧。兄弟爱恭朋友义,天书旌异有辉光。”
在这股“理学之气”的影响下,教化剧遂成当时剧坛的主流,《香囊记》被许多正统文人吹捧为“正人心、厚风俗”的“大雅”之作,广泛流传。对此,也有许多曲学家提出了批评,如王世贞批评邱浚《五伦全备记》是“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烂”[22](P34)。徐复祚亦言此类剧作“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南词叙录》则犀利指出:“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甚于今。”[2](P243)这些批评都直陈这股理学之气的弊端,徐渭甚至认为“南戏之厄,莫甚于今”,表明这种以道御戏的方式亟待转变。
(二)晚明剧坛的求“真”之气
夏咸淳认为:“明代士林心路经历了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分别呈现出沉寂、振奋、飞扬三种状态。始而袭宋而崇理,继而慕古而尚气,后则趋俗而尊情。”[23](P179)一般认为,晚明是“尊情”的黄金时代,而这股“尊情”思潮是受到了陆王心学的影响,李贽、徐渭、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人极力鼓吹原本蛰伏于“理”之下的“情”和个体的感性欲望,并将其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突出情感的个体性和先验性。由此而论,徐渭则处于由“尚气”向“尊情”转变的关键阶段,“可以说,万历年间文艺启蒙运动在高潮时期所耕耘的美学土壤,到处都留下了徐渭辛勤开拓的痕迹。”[24]也正是由于徐渭的积极创作和实践,才使明初剧坛的“理学之气”慢慢向求“真”之气转变,即剧作家由对政治化、社会化情感的关注转变为对个体化情感的关注。
与元曲家相比,明代剧作家的身份和地位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据罗锦堂统计,明代有杂剧作家101人,传奇作家317人,合计418人;除去既作杂剧,又作传奇的相重者23人,共有作者395人。其中有藩王、大学士、尚书、卿、侍郎等显宦,而进士及第者至少有30人,至于品味低或终身未仕的名彦宿儒,更是难以计数。[25](P201-227)这些从事戏曲活动的“名彦宿儒”无法体会元曲家的悲惨命运,胸中自然缺少愤懑之气——虽然康海、王九思等也有抒怀写愤的剧作,但由于缺少生命之气,并未产生广泛的影响。《四声猿》的出现打破了剧坛多年沉寂的状态,这股奇绝之气在当时广受欢迎。徐复祚云:“余尝读《四声猿》杂剧,其《渔阳三挝》,有为之作也,意气豪侠,如其为人,诚然杰作。”[26](P243)孟称舜评价《四声猿》说:“文长《四声猿》,于词曲家为创调,固当别存此一种。然最好者《祢衡》、《木兰》两剧耳。……挝鼓骂座,千古快事。此剧语语雄快,俨然如生。昔太史公状巨鹿之战,令人神王气慑,与此可以并观”。[27](P590)
在现今流传的近10个版本中,“新安尤峰徐民梓行,西山樵者校证”的版本就刊刻于徐渭在世时,万历、崇祯间的刊本尤多,目前尚存就有6种。汤显祖在读了《四声猿》后曾语卢氏李恒峤云:“《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28](P169)《四声猿》的流传使短剧创作渐成风气,如汪道昆效法《四声猿》的形式创作《大雅堂四种》,程士廉创作了《小雅四纪》,沈自征的《渔阳三弄》直接取材于《四声猿》中的《狂鼓史》,表达文人怀才不遇的苦闷。这种体式至清代时形成了叶承宗所谓的“效四声猿体”。除了形式层面的模仿外,书中体现出的那种精神气质的影响更为深远,《四声猿》不仅成为抒怀写愤的杰出代表,更是禀乎天道,追求至纯至诚的真性情的无上范本,它依托真性情的表达,昭示出生命之气的巨大力量。这些后继者们从欣赏书中的奇绝之气入手,进而模仿创作,将求“真”思维贯穿到自己的剧作中,在追求真性情的过程中慢慢褪掉理学之气。
除了创作上的影响外,徐渭的曲学观念还通过戏曲评点得到了传播,早在王骥德时代即言“世动称先生注本,实多赝笔,且非全体也”,可知“徐评本”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前文已言及“徐评本”对真性情的推崇和激赏,这种看法在明朝是不乏知音的,许多人都对“徐评本”《西厢记》赞赏有加,诸葛元声《〈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序》曰:
今以南调释北音,舍房阔态度而求以艰深,无怪乎愈远愈失其真也。吾乡徐文长则不然,不艳其铺张绮丽,而务探其神情,即景会真,宛若身处,故微辞隐语,发所未发者,多得之燕趋俚谚谑浪之中,吾故谓实甫遇文长,庶几乎千载一知音哉。[29](P117)
“不艳其铺张绮丽,而务探其神情,即景会真,宛若身处”无疑是对徐渭戏曲评点思想最恰当的概括,而这种看法也得到了印证,澄园主人的《〈徐文长先生批评西厢〉叙》亦云:
评《西厢》者不一人,或摘字句,或揽肤色,独青藤道人别出心手,略其辞华,表其神理,使世真知《西厢》之妙,共目为古今第一奇书者,道人之功也。[30](P651)
徐渭留给后世的评点文字虽然不多,但都是“出人意表”的腑肺之言,这种真性情的流露使“徐评本”和《四声猿》一样受到广泛推崇。从创作到评点,徐渭一以贯之的是对生命之气和真性情的推崇,这种独树一帜的方式犹如一股春风吹进明代剧坛,一扫前期的理学之气,使后期的剧作慢慢向求真的道路演进。
综上所述,在从元代向明代过渡的过程中,看似平静的剧坛其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内在之“气”而言,大致经历了“苍莽雄宕之气——理学之气——个体生命之气”的演进过程,对“气”的认识也从无意识状态转变为有意识的、积极的体认。而在整个转变过程中,徐渭“使气为戏”的观念产生了重要作用,他的戏曲创作和评点使明代剧坛从前期的“理学之气”慢慢向“个体生命之气”演进,在求“真”的道路上与“尊情”思潮相契合,共同成就了晚明剧坛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