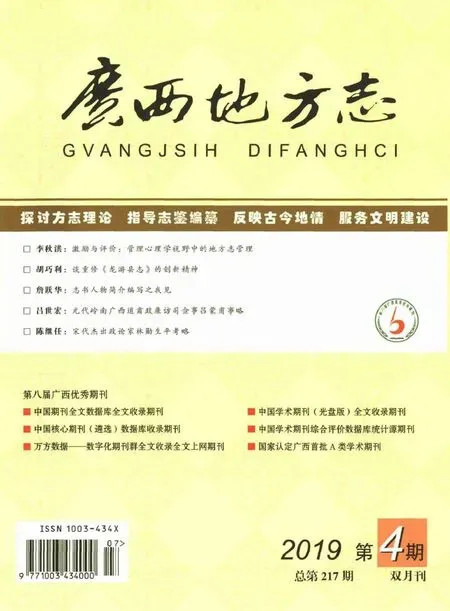南宁市博物馆藏部分碑刻选介
2019-12-15黎文宗
黎文宗
(南宁市博物馆,广西 南宁 530219)
2016年,随着新馆的正式开放,南宁市博物馆陆续将分散于北宁街库房、邓颖超纪念馆库房、粤东会馆临时库房等处的各类文物分批搬迁至新馆库房中。2018年底,存放于粤东会馆的碑刻作为最后一批文物被集体搬迁至新馆库房中。这批碑刻是南宁市博物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历次文物调查过程中,从南宁市市区各处陆续征集而来。由于早期缺乏对此类碑刻文物来源的登记、入账,这批碑刻基本上没有留下明确的入藏时间和征集地点,其内容更是缺乏记载。为此,笔者于2019年3月开始对这批碑刻进行整理,共发现清代石碑7块,民国石碑2块,年代不详的石刻1块。现将各碑简单介绍如下。
一、清代碑刻
(一)清康熙三年《重修城隍庙碑记》
碑高162厘米、宽82厘米、厚10厘米,圆首,四周阴刻一圈缠枝牡丹花纹,碑额楷书横题“重修城隍庙碑记”七个大字,碑文亦作楷书,题为:
山川岳渎之灵曰神,□□□□□之章曰□,□□□□犹翕河言山川之灵答时周之命令也,其尤为人□□□而亲民者,如城有城隍,里有土□,岁□旱涝,系树□之丰歉,御灾捍患,□疠夭扎之不□,应苍黎□祷灵爽□焉,神之□也,赞乎治矣。□□□庙貌□以牲□以然□□□□□福祸所刑赏□□□□□□之谓乎?邕州界控交南,□对□□,官守所寄,□□要地,而□□□宁为细,故所考之,先时水患浸城□,触仓库,突寺观,一郡□□,如遇兵寇。郡侯率士民祷祀,祈神乎雷怒,雨注穿穹,裂地而下,□□□□宇而鼎□□□重建神庙。时□□交蛮溪洞□□皆在上浣,奋写若□□□□飘屋,俄顷,而□斯□□壅疏漫,保护生灵□神功伟矣。至明□万历□□乃□□旱,民不聊生,时郡□齐洁祷于神祠,□□自责,甘雨随至,阖郡呼天罗拜,因复重修,庙貌更新,□□神之凭灵于其□也,□□奉上帝之命令,为一方生民福至,神之干旋造□□□有功于其土,则在神之自为之,虽帝□能自督之也,至天之降罚,虽天主之,而神能救护,天□□不□□不容此一方民而忍于其罚之重,此神之心即天之心也。我朝鼎定以来,邕城几回兵燹。余初至,□地萧凉之状,触目□忍,而仰瞻神宇,则栋摧瓦落,思欲即用民力,□则□雨阳初调,而□□□□□也,□□□□则风雨不蔽,乃捐俸资,稍葺其橅□瓦灰之败坏者,而辉□之尚未遑也。嗣外至庙门、二门、两□、两庑、□□、寝堂,内神室簾幕、仪像衣冠、藩幢、供案及诸地狱□□种种,朱碧辉煌,粉采炫烂,厕所□□□□□□□□□乃告成工。然非皆余力也,计官府之捐俸者十之五,土民之输诚者十之一,□□□□□□十之三,而属员之助作木、砖、灰之数,亦居其一焉。鸠工庀事,不至劳民力,以费民□□□□□□之人,未尝一出于勉强。噫!岂非神之灵爽有以感之欤?抑人之诚于求福之心,亦□于一时耶?乃三载时和,渐称丰乐,瘴烟不起,商旅安吉,寒燠不忒,民无疾病,其亦神致之欤?嗟乎!神之有功于其土者,若此其□□报祀之典,而泄泄焉视之也哉。因是簪笔而志之,而重新于不替,俟后之君子也。
落款下,位于碑左下角,还有两列小字,已模糊不清,可辨者有“塑□□□兆,□□□”。
此碑是虞宗岱于康熙三年(1664)重修城隍庙时所题刻,内容主要是赞颂城隍神的灵显,并述及重修城隍庙的起因、经过,表彰捐资众人之绩。虞宗岱,浙江人,进士,康熙元年至康熙四年(1662—1665)任南宁府知府[1]。虞宗岱重修的城隍庙为南宁府城隍庙,此庙最早可追溯至宋代所立的苏忠勇祠,以供奉苏缄为城隍,庙址在原邕州衙署旧址,即今之红星电影院一带[2]。据嘉庆《广西通志》载,南宁府城隍庙“元至元间重建”,“明洪武初至嘉靖间重修”,清代又经过多次重修,其中康熙年间仅见“康熙十二年,知府韩章、通判顾鼎植重修”[3],缺载康熙三年虞宗岱捐修一事,此碑所载,正可补方志之遗缺。又碑文中“故所考之,先时水患浸城□,触仓库,突寺观,一郡□□,如遇兵寇。郡侯率士民祷祀,祈神乎雷怒,雨注穿穹,裂地而下”,所载内容与元代张良金《城隍庙碑》中提及的“壬午水患”的描述相类似,张良金所载为“雷怒雨注,水乃穿窦而入,裂地而出,一郡汹汹,如遇兵寇”“宁江门水灌城……触仓库,突寺观,翻屋庐”,故虞宗岱描述的“先时水患”即元代至元壬午年(至元十九年,1282)水患。碑文中还提到明万历年间因干旱无雨,民不聊生,郡民齐到城隍庙中求雨,“甘雨随至,阖郡呼天罗拜,因复重修”,再次重修了城隍庙,而这次重修同样不见于史料所载。
(二)清嘉庆元年《捐助布施厘头碑记》
原碑已残,仅见上半部分,方首,碑宽82厘米、厚10厘米,碑文楷书阴刻,碑首题为“捐助布施厘头碑记”,全文为:
署理广西左江总镇、世袭骑都尉,又世袭云……
署理广西左江兵备道、南宁府……
广西馗纛营都阃府……
前任上思州正堂、升任刑部直隶司员外郎……
特调太平府江州州同、宜……
南宁府宣化县迁龙司……
大丰合记捐厘头银壹千叁佰贰拾肆两贰钱、大丰永记捐厘头银壹千壹佰柒拾柒两壹钱、恒升合记捐厘头银捌佰肆拾柒两玖钱玖分、大有纯记捐厘头银贰佰捌拾壹两肆钱陆分、公顺合记捐厘头银贰佰伍拾叁两壹钱柒分、永盛合记捐厘头银贰佰叁拾伍两叁钱肆分、生生□记捐厘头银壹佰零壹两伍钱柒分、秦三□行捐布施银壹佰两正、韩三成行捐布施银肆拾两正、兴顺何记捐厘头银叁拾玖两捌钱……天□泰记捐厘头银叁拾柒两贰钱……□□□记捐厘头银叁拾叁两捌……杨云盛号捐厘头银叁拾壹两……万顺宏记捐厘头银叁拾两……□川□记捐厘头银贰拾玖……
嘉庆元年……
碑文主要记载了嘉庆元年(1796)南宁部分商行布施、捐助厘头银的情况和金额。厘头银,也称厘头金,是在国家财政体制外设置的捐收,实际上是地方官吏的“小金库”,多被用于弥补上解亏空、官场交际开支或补贴官吏生活等。这种厘头银一般多是对地方商行铺号等抽取,还美其名曰“厘捐”“布施”。捐施的数额、抽厘的比例并不固定,但按照之后推行的厘金制度判断,早期的厘头银抽取比例或为值百抽一或值千抽一,具体仍待考证。仅从此碑所附各商铺捐厘的数额,可以看出当时南宁商行之兴盛。
(三)清道光二十一年柳际清重修宣化县城隍庙碑记
此碑在多次搬迁过程中已破碎为多块,且部分缺失,已难以拼合,目前仅落款部分较完整,碑高115厘米、厚8厘米,碑文楷书阴刻。原碑残缺严重,碑文已难窥全貌,今从民国版《邕宁县志》中补录如下:
稽诸载记,八腊之祭,首列水庸,盖城隍之祀古矣。若芜湖县庙,建于赤乌二年,则为建庙之始。他若《北齐书》郢城有城隍神祠,隋五行志、梁武陵王纪有祭城隍事。逮唐,则李阳冰、张说、张九龄、杜牧,或说或文,皆班班可考。南宁为古邕州地,按《宋史·苏缄传》,缄知邕州,蛮入寇,城陷,其家三十六人自焚。后交人谋寇桂州,行数舍,见大兵从北来,呼曰:“苏城隍领兵来报怨。”惧而引归。
邕人为缄立祠,则以人为神,尤为灵异昭著矣。宣化县城隍庙在府庙右,旧祀刘讳初,以公创筑城垣,有功德于民也。夫苏公以死勤事,刘公以劳定国,皆与古祀典合,则二公以血食斯土也固宜。庙创于乾隆乙酉,前宰胡君位铸始建数楹,厥后周君世英、万君廷莘相继修葺,规制未宏,历数十年而倾圯立见矣。余道光丙申冬来莅兹邑,入庙瞻拜,怵惕于心,慨然为修复计。比年来,人和岁丰,水旱疫病之不作,狱讼盗贼之无多,皆神之灵,有以默相之也。爰捐廉以为之倡,并劝诸同志及绅士、商民,筹金为助,鸠工庀材,一新轮奂,而于……鼎建之,前为大门,列戏台,中为大厅,后安神座,最后建高楼祀神,后并为寝室。较从前奉神后于右偏则尽善也。其间碑文联额,凡夙有于庙者,一仍其旧,而丹漆一新。经始于庚子之冬,毕事于辛丑之秋,工甫竣,适余奉权篆湘源之檄,都人士以余倡始其事,请序于余,余喜其庙之落成,乃援笔而为之记。至劝捐督工,辛勤劳勩,则少□胡君序谦为功实多,例得附记于末云。①参见民国《邕宁县志》。另,《邕宁县志》引此碑文时,与原碑文略有出入,如“城隍之祭古矣”的“祭”在碑文中为“祀”;“郢城有城隍祠”脱“神”字;“梁五陵王纪”中的“五”实为“武”;“乾隆丁酉”实为“乾隆乙酉”;“狱讼盗贼之潜消”中的“潜消”当为“无多”;“鸠工庀材”后脱“一新轮奂,而于”,其后似乎仍脱字,因此无法与县志“鸠工庀材而鼎建之”上下句衔接。
此碑残缺严重,但根据残存的碑文及《(民国)邕宁县志》中所录全文,柳际清重修的这座城隍庙是宣化县城隍庙,是有别于南宁府城隍庙的。南宁府城隍庙是由苏缄殉国后邕州士民为其所立的忠勇祠演变而来,供奉苏缄为城隍[5]。而宣化县城隍庙则“在府庙右”,供奉首建邕州城垣的刘初为城隍,且其历史只能追溯到清乾隆乙酉年(1765),时年宣化县知县胡位铸(晋江山阴人,副榜,乾隆二十八年任宣化县知县[6])于府城隍庙之右另行购地,建起了县城隍庙,其后的知县周世英、万廷莘②周世英,史料缺载。万廷莘,江西南昌人,举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任宣化县知县。相继修缮,直到柳际清时,再次对其进行重修。在今南宁市兴宁区派出所内还存有一通《重修县城隍庙碑记》,记载了1901年沈世培、周颂声等重修宣化县城隍庙的起因、经过[7],其中内容也可与柳际清碑所载相互印证。
(四)清道光年间告示碑
此碑已残,仅存上半部分,系以青石板刻制,宽75厘米、厚9厘米,方首,碑文楷书阴刻,左首题为“告示”,右正文残存文字为:
署宣化县正堂、候补分府、加五级……
贡生周建纶、廪生陈金、生员雷体琨……本县城隍庙日久,庙宇倾颓,兹蒙仁宪及前任柳主同助廉金,并饬……矣。前柳主在邑,备悉宣化县风……神灵,于功竣之日,柳主至庙上匾……分庙□沥扫庙宇,启闭门户,方……遵谕雇庙祝,数年,已经章程……必有好事者更改章程,难免僧……禀,伏乞仁宪俯准,乞批泐石……神人均感戴无既矣。为此切赴……远,为此示,仰该生等知悉,即……门户洒扫洁净,务使庙宇肃……控,以凭挐不贷,各宜凛遵……
道光二……
从碑文判断,这块碑应是当时宣化县署对县城隍庙管理问题的裁定、批示。碑文中提及的周建纶为道光甲午年(1834)岁贡生、陈金为道光丙午年(1846)岁贡生[8],雷体琨史料无载,应仅为县学生员,未获功名。三人或为此批示涉及的原讼人。碑文残缺下半部分,根据现存的告示内容,大致可推断此次纠纷主要是由宣化县城隍庙的管理问题引发,因此负责审理的县令批复明确规定管理县城隍庙的庙祝需遵循前定章程,“沥扫庙宇,启闭门户”等,并泐石公示。
此碑落款仅见“道光二……”但据碑文提及“蒙仁宪及前任柳主同助廉金”捐修事,此“仁宪”为宣化县令,“柳主”指柳际清,其曾于道光十六年出任宣化县知县,并在道光二十一年对县城隍庙进行重修。由此推知,此碑年代当晚于道光二十一年,应在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1842—1849)之间。又,碑首署“宣化县正堂”中的“县正堂”指知县,而道光二十一年后出任宣化县知县的是山西安邑人李天钰[9],因此,此处的宣化县正堂为李天钰。
(五)清华云善堂捐资碑
此碑已残,且被人为裁切掉四周,仅存碑心部分。现存残碑为长方形,长70.5厘米、宽50厘米、厚6厘米,碑文楷书阴刻,残存文字为:
……衰意惨□石□心,本堂同志……给牌,免其亲临,逐日督工,挑粥□□派送,由是年……此流离之众倏因饥火焚心,浑身冷汗,颤颤若惊……有所依食,而夫妻子女免受割离之悲,奚敢云博施……羊肆舞,秋初则旱魃为灾,米珠薪桂,人心惶恐,又……百方筹捐赈济,仿照前章办理。随荷官啇仁长大力……公所,办事善友勇于义务,不受惠、不留膳,每日咸集……际,日计七千有奇,携儿绷女,捧碗提篮,人虽蜂踊……道宪何、余观察,郡侯黄太尊轸念民灾,派丁弹压……之仁感动上苍,甘霖大降,夏至后早稻登场,杂粮……馑之后,贫民谋食艰难,往往有抱疾不治,僵伏道傍……妇孺,非择地另立,未为尽善。如是众志成城,复集数……为小小规模,经禀明地方官悬示晓谕,举凡赠医……门而入,永无阻善之路,将见仁政日兴,善门日广……
……壹百两正……壹百两正……壹百大员……壹百大员……银柒百大员……银伍拾两正;周严捐银伍拾大员,黄敦仁捐银肆拾两正,唐德仁捐银叁拾两正,雷福奎捐银叁拾两正,钟广铭捐银叁拾两正,周详庆捐银叁拾两正,萧永清捐银贰拾壹两七钱四分正,梁举麟捐银叁拾大员,阳朝光捐银叁拾大员,梁颛永捐银叁拾大员,邓朝澍捐银叁拾大员,梁文韬捐银叁拾大员……
叁拾贰号共捐银玖佰伍拾伍两肆钱贰分正。一支买善堂医所价银伍佰捌拾两正,一支中人总甲利是银壹拾壹两捌钱伍分,一支税契银贰拾陆两陆钱捌分壹厘,合共支银陆佰壹拾捌两伍钱叁分捌厘。除支,余银叁佰叁拾陆两捌钱捌分贰厘。此余款拨入癸卯、甲辰二年施药剂公用支讫。
此碑残缺严重,从残存的碑文判断,其内容主要是记载和彰显灾害发生时众人捐资赈济并建立善堂的义举。原碑缺失落款,年代不详,但碑文捐资情况中多有捐“大员”者,此“大员”即银元(俗称大洋),而银元源于欧洲,在明末才传入中国,清乾隆末年才有铸行,晚至光绪以后才大规模铸造,故可断定此碑年代应在清末。又碑文提及“道宪何、余观察,郡侯黄太尊轸念民灾”,其中郡侯、太尊均是对知府的尊称,则“郡侯黄太尊”当指南宁府的黄姓知府,而“道宪何、余”中的“道宪”是对道台的一种尊称,应指驻守南宁城的左江兵备道道台。考查有清一代的官员,同时期任上为黄姓知府、何姓和余姓道台的,仅见光绪朝南宁府知府黄英采(进士,光绪二十八年知府)及与其同期的左江兵备道何照然(二十八年任)、余诚格(字寿平,安徽望江人,进士,二十九年任)[10]。另,碑文中还有“余款拨入癸卯、甲辰二年施药剂公用支讫”的记载,而黄英采、何照然、余诚格三人在任期间的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十年(1904)的干支正好是癸卯、甲辰。由此推测,此碑的年代应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前后。
清光绪二十九年前后在南宁城中修建的善堂仅见“华云善堂”一家。据民国《邕宁县志》记载,华云善堂“在城西内马王庙巷。光绪季年,壬寅、癸卯之交,岁大饥,慈善家捐资购米平糶,复煮粥以救饥民,又假府城隍庙为赠医施药之所,多感未便,乃购今地建堂,一切经费,俱由各善士临时筹捐。”[11]华云善堂在马王庙巷,即原新宁路东一里,位置大概在今西南商都至悦荟广场一带。华云善堂建立前,正值南宁城一次大规模饥荒爆发,此时正是“壬寅、癸卯之交”(1902年秋至1903年春),与碑文所载“秋初则旱魃为灾”及“夏至后早稻登场”才缓解饥荒的记载吻合,干支也能对应。华云善堂最初是由“慈善家捐资购米平糶,复煮粥以救饥民”,这也和碑文“百方筹捐赈济”“随荷官啇仁长大力”“挑粥□□派送”的记载相同,后来因为“多感未便”“非择地另立,未为尽善”,“乃购今地建堂”。碑文中所有捐资者均为个人,不见商号铺店,也和史料所载“一切经费,俱由各善士临时筹捐”对应。综上可知,则此碑应是华云善堂创立时所立的捐资纪事功德碑。而且碑文中明确记载善堂建于饥荒之后,即“壬寅、癸卯之交”以后,则其具体年代应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
值得一提的是,碑文中还提到“利是银”,即现今常说的“红包”,如今操白话的老一辈南宁人仍习惯此称,可见“利是”的说法至迟在清末的南宁即已出现。
(六)清同治十一年《重修魁台码头碑记》
此碑已断为两截,系以石灰岩质青石刻制,碑为长方形,高110厘米、宽72厘米、厚8厘米,楷书阴刻,碑首题名“重修魁台码头碑记”,正文分序言和捐资名录两部分,其中序言题为:
尝思名区以培植而弥彰,胜地以增□而愈久,况神祠之依据开敞高昂,而庙宇所式凭□行正大。我古城口衣锦坊、兴庆坊、锦□坊,前建三界高祖古庙于高坡之上,为一乡之保障,护境以平康,固所谓地杰神灵,居高驭下者也。建时筑一魁台,东西为阶级,以上而庙之□□,尤称雄壮,登拜者亦便于步。□□日以倾圯,遂□庙貌孤高,岁时展祀,登涉维艰。爰集各坊,共议捐金重修,现已落成,视前者尤为坚固高厚,所有乐捐芳名泐石以志,为创此举者□□,以为后之随时培植增修者先导云。是为序。
序后是捐资名录,落款作“同治拾壹年岁次壬申仲夏月穀旦立”。
此碑刻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其内容主要记载当时捐修魁台码头事。魁台码头,实际上是三界庙前的一个石阶平台,因临江,兼有码头之用途,故名。史载三界庙“在仓西门外三界坊街。旧日为商界聚会议事场所,面临大江,与天妃宫近,今为第二国民学校”[12]。三界坊,即今壮志路,三界庙则在壮志路4号一带。清代三界庙周边一带商会、会馆众多,分布着粤东会馆、安徽会馆、两湖会馆、新会书院等,商界聚会时,常借三界庙作为议事场所。
(七)清告示碑
此碑已残缺,目前仅见下半部分,宽78厘米、厚10厘米,以青石刻制,碑文楷书阴刻,残存文字为:
……南莞会馆即不准其开载乎?本爵阁部堂驻□南宁……官,此时榱楣、钟鼎尚能一律整齐,否则不但钱粮无……迨,叠控不休,该府县左右互袒,终无定断。适足启□……剖断此案,惟当以康熙、雍正、乾隆各年间由单为……于南莞二邑商民经管,宣化绅民不得妄思觊觎……系建庙在前,设立会馆在后。府县开载:天妃宫……化县速即出示晓谕,南莞二邑商民毋许将庙门……报赛,有欲进庙拈香展敬者,管庙人不得拦阻……官究治。其庙门匾额,饬令遵奉现在……祠内所供徐、杨二公之木主,虽系该商报本……稽考,乃为设主崇奉,殊属越礼犯分,应饬该……庙前本有圩市,合郡民人俱赴此贸易,历来……前该县给示驱禁,实属偏袒孟浪,嗣后仍令蹟不敢躁践吵闹,便足以尊崇庙貌,何至……南莞与宣化民人皆吾赤子,何容丝毫偏袒……祠设主易匾、驱市,乃其愚妄错谬之处,经……断,则必将为首之绅民及教唆之讼师李……木主撤毁,任听本地民人入庙烧香,赴……此批泐石永远示遵,并取具碑摹详送……日批示。
此碑上半部分已缺失,但从残存碑文判断,此碑应是宣化县商民与南海、东莞二邑商民因天妃宫及庙门前圩市的经营、管理问题而产生矛盾,由此“叠控不休”,最后诉至两广总督处,由总督定断并颁布告示后泐刻。碑文中的“本爵阁部堂”,指两广总督;南莞会馆,即南海、东莞会馆的简称,亦称二邑会馆,“在城西三界坊街(今壮志路),广东东莞、南海商民所建”[13];天妃宫则“在仓西门外沙街(今解放路),向为敷文书院产业”[14];南莞会馆与天妃宫相邻,且天妃宫庙门前有圩市,故常有二邑商民到此贸易,并渐而占用了天妃宫,由此引发了此次诉讼。最初,宣化县、南宁府衙署都难以定断,多有偏袒,以至双方都不满意,这才告发至两广总督处。两广总督最后判定,允许南海、东莞商民在天妃宫前圩市自由经营,二邑商民也不得阻拦本地民众进入天妃宫烧香。此碑缺失年款,但碑文有“以康熙、雍正、乾隆各年间由单为(准)”的记载,则其年代当在乾隆以后,或在嘉庆年间。
二、民国时期碑刻
(一)民国二十四年《义塚》碑
此碑以大块且厚重的青石板刻制而成,碑高127厘米、宽76厘米、厚12.5厘米。碑为方首,上部以双线阴刻出一个长70厘米、高28厘米的开窗,内楷书阴刻有一段序言。序言下的石碑主体部分有楷书阴刻“义塚”两个大字。序言主要记载此义塚的由来,其右上角已残缺,残存文字为:
……本堂……所其有无……报告亦皆为之……月为之祭扫,使不致……法至善也。由此西行数……为托子岭,原有本堂义地凡七十余塚,此即本堂创置义塚之所,后乃渐为扩大至马鞍岭,计已八百余塚矣。民国甲戌夏,因政府开筑战壕,凡附近路线左右坟茔均令迁移,同人等往来番间,见白骨纵横道左,业已集资募人收拾,概移至旧义地掩埋,约三百余塚,并立碑纪实,以毕此举矣。乃至旧历十一月,复奉政府命令,马鞍岭西侧二百余塚及托子岭之七十余塚均须迁葬,同人等急为觅地,乃东行数里至官塘村后,土名长岭者,村人均谓此宜作善堂义地,乃共议以应迁之新旧茔域共四百余塚,移厝于此,共立一大墓,名曰‘新义塚’。其大塚下,左右侧有韦氏一墓,缘施主韦芳鸿者,老而乏嗣,愿将其遗产约值二千金,捐赠本堂,用为义举,同人等不忍湮没其善而不彰也,爰以数百金除办理韦翁身后事外,并葬翁于义地,特立一墓于左侧,其右侧二墓则翁之令子及若媳也。事竣后,爰述其厓略,勒石以纪其详,俾世之君子知同仁等区区恻隐之私忱,庶不负本堂名命之义云尔。
民国廿四年乙亥二月十七日同仁善堂谨立。
根据碑文所载,这块义塚碑乃是同仁善堂于1935年在南宁市西郊的官塘村长岭上所立。同仁善堂,“地址在兴宁路西一里(即旧银狮巷),前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立,办理赠医施药,年终施赈济孤贫米粮,积有铺租为常年经费,办事员三十人”[15]。民国甲戌年(1934),经历了蒋桂战争失败的新桂系政府开始推行自治建设,并加强了一些军事设施建设。这一年的夏天,新桂系政府在南宁以西开挖战壕,沿线的一些坟茔被挖开,将白骨弃之道旁,同仁善堂即拣拾这些白骨移至托子岭原同仁善堂义塚之地埋葬,共计有三百多座坟茔。但仅仅几个月后,新桂系政府再次扩修战壕,同仁善堂原位于托子岭、马鞍岭的四百多座墓葬又被迫迁移到官塘村长岭上安葬,并取名“新义塚”。此外,碑文中还特意记载了一位因无子嗣而捐出身家的施主韦芳鸿的事迹,以彰显其义举。
(二)民国二十七年芬振然建屋题记
此石刻系以青石刻制而成,长62厘米、宽18厘米、厚8厘米,正文四列,共48字,楷书阴刻,题为:
振然建造此侧门厦屋,以为永远,自贮傢俬什物。芬振钧世代出入,顺手关门,两无异言。爰勒石为记。
民国廿七戊寅年十月廿一吉刻。
从铭文判断,这块石刻是1938年芬振然为避免与其兄弟芬振钧的房屋产权纠纷而泐石,以标明自己对所建房屋的所有权。这块石刻是当时南宁民间房屋所有权纠纷的一个重要见证。
(三)年代不详石刻
仅1块,即“八卦符箓纹石刻”。此石刻系以邕宁本地常见的红色细砂岩凿刻而成,石刻呈方形,边长35厘米、厚4厘米,细线阴刻,刻纹较浅。石刻四周,按文王后天八卦排列顺序分别刻有“巽、离、坤、兑、乾、坎、艮、震”八个卦象。石刻中部的上离下坎两卦之间,还阴刻有一道符箓。符为上中下结构,符头题有“敕令”字样,符窍依稀有“土九……急急”之字,疑为安土镇宅之符。推测此石可能是建筑房屋时砌于墙体上、用以镇宅挡灾的符箓石,作用与石敢当类似,或属于石敢当之一种。此石无年款,具体年代不详,但南宁保存的建筑大多系清代民国时期所建或重建。又目前所见南宁周边利用本地所产红色细砂岩为建筑材料或石碑材料的,多集中在清末民国时期,因此,此石的年代大抵在清末民国时期。
三、结语
南宁市博物馆收藏的这批碑刻虽多残缺、文字漫灭,难以辨识,但从残存的碑文中,我们仍然能够了解到清代民国以来南宁的一些地方历史。此次发现的十块碑刻中,清康熙三年《重修城隍庙碑记》、清道光二十一年柳际清重修宣化县城隍庙碑记、清道光年间告示碑都与城隍庙的历史有关。南宁城内的城隍庙在解放初已不存在,其历史多不为人所知。民国莫炳奎在《邕宁县志》中曾分列有“府城隍庙”和“县城隍庙”两座城隍庙,而在此前的志书中则没有记载“县城隍庙”,故多有地方学者疑此记载有误。柳际清碑和道光年间告示碑的发现,不但确证了“宣化县城隍庙”的存在,更为我们了解县城隍庙的历史提供了一些帮助。清代华云善堂捐资碑和民国二十四年《义塚》碑分别涉及华云善堂、同仁善堂两大民间慈善机构,是清末民国时期南宁地方慈善事业的重要见证。当时的慈善事业“皆系救济一般穷黎而设,如施衣、施粥、施药、施棺各种”[16],有地方官办和民间筹办两种,而以地方慈善人士捐资筹办为主,较知名的民间慈善机构除了华云善堂和同仁善堂,还有保爱善堂、仁爱善堂、华明善堂、平南善堂、蒲庙善堂、福生医院、普济留医院、红十字会等。而清中期的两块告示碑、民国二十七年芬振然建屋题记则是清代民国时期南宁地方民间纠纷、诉讼的一个缩影。清中期的两块告示碑涉及地方公共服务资产的纠纷,分别由县城隍庙的管理和天妃宫的经营管理问题引起,最后都是经过诉讼后由官方予以裁定,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诉讼形式、法律裁定等都有一定的意义。芬振然的题记则与私人房产纠纷有关,是芬振然用于界定与其兄弟芬振钧房屋产权的一个物证。清同治十一年《重修魁台码头碑记》是清末民间捐修码头以便通行的一个历史见证。清末民国时期,南宁两岸码头林立,商贸兴盛,而魁台码头即三界坊(今壮志路一带)周边民众捐修的一个小型码头,见证了当时邕江两岸码头、商埠的兴盛历史。清嘉庆元年《捐助布施厘头碑记》是清代南宁地方官府对商行铺店收取厘头银的历史见证,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南宁商业的兴盛程度。而八卦符箓纹石刻以极具道教文化特色的八卦和符箓纹为图案,反映出民间常见的安土镇宅、挡祸消灾的祈福心理,很可能属于一种独特的石敢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