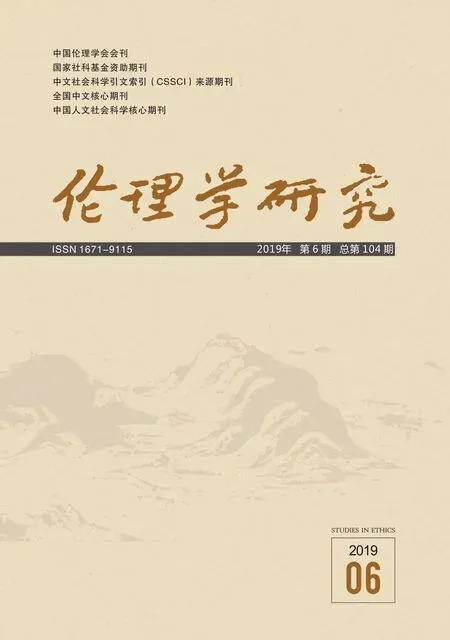周海门良知观辨析
2019-12-14阮春晖
阮春晖
周汝登(字继元,号海门,1547—1629)是晚明重要心学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其列入“泰州学案”。对于良知心体的肯认,周海门显与王阳明遥相呼应,不过,在周海门的良知意域中,良知之体表现为“无”之深微本质,良知之用从顾及整体规模细化为注重当下与偶然,良知自我呈发的力量以“现成”的样式得以强化,其意涵集中表现在“无物而物在”“手持足行是道”和“自我现成”三个命题所构成的逻辑序列中。
一、无物而物在
1592 年,海门与许孚远(字孟中,号敬庵,1535—1604)会聚南京,就无善无恶之旨展开辩难,敬庵以“九缔”示之,海门以“九解”复之。在“缔三”中,敬庵认为人心如太虚,太虚之中存有“中”“极”“善”及仁义礼智信之“所以为天下之大本者”[1](P431)。针对此说,海门回复曰:
说心如太虚,说无一物可着,说不杂气质,不落知见,已是斯旨矣。而卒不放舍一善字,则又不虚矣,又着一物矣,又杂气质,又落知见矣,岂不悖乎?太虚之心,无一物可着者,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实有所以为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则是中与太虚之心二也。太虚之心与未发之中,果可二乎?如此言中,则曰极,曰善,曰诚,以至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等,皆以为更有一物而不与太虚同体,无惑乎?无善无恶之旨不相入,以此言天地,是为物有二,失其指矣。[1](P431)
在“人心如太虚”这点上,海门与敬庵观点一致。但敬庵说“人心如太虚”,是要给理留下存放的空间,而非纯粹的真空无物。胡居仁有类似说法:“若以为真空无物,此理具在何处?”[2](P42)朱熹在答及“太虚何所指”时,亦说“他(张载)亦指理,但说得不分晓”[3](P2534)。由此而言,“心如太虚”之意在朱学一系里,主要的是从虚实视角而言,心为虚为次,理为实为主,理优先于心。对比地看,海门说心如太虚,是从本体视角而言,“本体只是太虚”[4](P1442),既是本体,心就是天下之大本,不必再另立“中”“极”“善”之所谓大本者,否则就是“中与太虚之心二也”。因此,在天地太虚这一层次上,海门说心体无物可着,实际上是指良知心体排斥了善、诚等道德性规定,从而表现为良知心体之无善无恶、无念无识。
这里有一细节:善、诚等作为天之“大本者”,敬庵以为它们皆是物,在海门的回复中,也没有反对敬庵此说。然则善为物否?我们不妨宕开一笔,来看看阳明如何说。阳明心学的异出,据阳明自称,是基于朱子“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之弊而发,故阳明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不过,在何者为物的问题上,当时学人有不同看法,阳明曾针对弟子王纯甫的提问,有如下回答:
善即吾之性,无形体可指,无方所可定,夫岂自为一物,可从何处得来者乎?故曰受病处亦在此。纯甫之意,盖未察夫圣门之实学,而尚狃于后世之训诂,以为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须从事事物物求个至善,而后谓之明善,故有“原从何处得来,今在何处”之语。[4](P175)
纯甫亲炙阳明,但此前受朱子之学影响较深,“未能动静合一,而遇事辄有纷扰之患”[4](P175),曾多次问及善从何处来、今在何处。阳明为解其所困,亦曾数次致其书信,此语即出自其中。阳明指出纯甫之问是将善看成是事事物物各有之善,将善分说了,故有来去之分。而在阳明看来,善作为人之本性,无形体无方所,它始终内在于人性之中,无所谓从何处来、今在何处,因而不能将之定为实有之物。照这种说法,阳明和海门之说似有不同,实际上在海门思想中,由于已将良知心体视为绝对存在,敬庵再另立善、诚为大本,则被视为与良知有二的外物,是头上安头之见。因此海门在这里所说的善,其实就是阳明批评纯甫所持的事物分有之善。另者,阳明此文段写于正德癸酉(1513),距1527 年“四无”论的提出尚有较长时日,从早年“以善说性”到晚年以“无善说良知”,其思想流程有变化,于海门而言,以“无物”指绝对良知而不讲良知之善,也正好可以回应阳明晚年思想义理的变化。
“无一物可着”是从本体上说良知,那么,发用上的良知又是如何呈现?来看海门对《中庸》之“不诚无物”的解释:
无射问:“本来无一物,又曰不诚无物,何?”先生曰:“本来无一物,即是诚。”曰:“如何不诚无物?”曰:“如耳无物然后聪,有物则听而不闻,不成耳矣;目无物然后明,有物则视而不见,不成目矣。推而到酬酢万事,若有一物,便颠倒错乱,事不成事,此之谓不诚无物。”[1](P499)
朱熹这样解释“不诚无物”:“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所得之理既尽,则是物亦尽而无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而君子必以诚为贵也。”[5](P34)朱熹以为,天下之物皆有其理,如以诚求之,就能得其理,进而识得此物,如此逐一扩展,则理能尽,物亦能尽,此是诚而有物;如不诚,则物之理不能尽,物亦不能识,是为“不诚无物”。显然,朱子是从求诸事物的外在工夫路径来解释“诚”的含义,“诚”是获得“实理”的重要条件。海门则以“本来无一物”释“诚”,这种解法在阳明后学中不乏其人,如焦竑“本来无物者,即《中庸》未发之中之意也”[2](P830)即是其例。海门所说的无物,是诚之本体的本有状态,本体不沾滞具体物事,其本有特征才会呈现出来,如耳不滞于声则能辨其声,目不滞于物则能识其明。由此引出另一疑问:海门既然主张心之体无善无恶,为何又立带有道德含义的“诚”为良知心体?事实上,无论是阳明还是标示“四无论”的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8—1583),他们所提之无善无恶,并非善恶双泯,而是指良知心体尚未启动、未与物接时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状态,也即阳明所说的“无善无恶者理之静”[4](P33)。在这种情形下,“诚”就是无善无恶,不着一物,等同于太虚,在不另立道德本体的前提下,我们既可讲“本来无一物,即是诚”,也可说“本来无一物,即是中,即是极”,因为中、极、诚、太虚在此种意义上是同质同序的概念。既然良知心体在本体层次上表现为“无一物可着”,海门以为,在形下发用层面上自然也是“无物”,即无着于物,如此方能与阳明所说的“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者”[2](P165)相应。海门说耳有物而不闻,目有物而不见,“推而到酬酢万事,若有一物,便颠倒错乱,事不成事”,便是“着物之用”与“无物之体”的不谐,这在海门看来实为“不诚无物”。比较朱熹与海门两说,不难发现,“无物”作为“不诚”之结果,两人看法一致,但这种结果在朱熹表现为对事物条理的不识,而在海门则表现为事物本质的不显。此外,在对“诚”的理解上,二者亦有殊异。朱熹将诚视为认识事物、达观天理的条件,而海门则将之以本体视之,其本质在“无”,在心体的无滞碍。由此可以看出,海门并没有否认《中庸》之说,而是基于自身学术立场,借语发挥,重点强调了诚之“本来无一物”的意义,以此来解释“不诚无物”之结果。
故而海门讲良知心体之无,并非排除善恶,而是不拘执于具体的善恶,心之体“作为价值绝对的原在,乃超越于经验价值世界中的任何相对价值形态,既超越于任何‘善的’,同样也超越于任何‘恶的’”[6],惟其如此,方能呈现出良知“无物”的本质。但在阳明那里,一则上根之人难求,二则阳明自己也力图避免陷于“异端”的指责,故阳明以“三有”来确保“一无”的成立,从有归于无,复还本体。王龙溪则突破这一限制,以“无”来界说良知之体,并以意、知、物皆无善恶,在形式上将阳明“四句教”划归为整体的“无”,在内容上淡化意、知、物的工夫作用,以此阔显心体之无的本体特性。置于儒释关系之中,尽管龙溪之学在形式上带有佛氏成分,但他仍言“吾儒之学,自有异端,至于佛氏之家,遗弃物理,究心虚寂,始失于诞”[7](P14),可见在他看来儒释之间依然有着分隔。海门论良知之无,紧承龙溪语意,又特别转出两点:一是将良知之无的本质与《中庸》相融,不再避开“异端”之嫌;二是消除了良知之体从有到无的过渡痕迹,不再以“有”来释“无”,良知之无直接决定了万物之有的真实性与道德性,认识万物之有当先确立心体之无,从而明晰地将“无”视作良知的深微本质。
由于良知之本质在“无”,良知才有“无不知”的强大能量。海门谓:“良知无知无不知。”[1](P536)“无知”指向良知之体,“无不知”指向良知之用,良知体用观便在海门之“无”的双重界说中得到确认。这种言说方式尽管带有玄妙或禅理的成分,然在着意于良知本质方面,却也具有强化的功效。除“无知无不知”外,海门还有许多诸如“无能之能”“无味之味”之类的话头,这些关于良知之无的说法,其依据都和良知的深微本质有关。也正是在这层语意上,“无物便是物在”[1](P495),因为坚信良知本体之无物,才有现象界之“物在”;反之,没有现象界的“物在”,无物之物也难以成立。当然,海门的“无物便是物在”,不单单是从“无”立个良知,主要的是基于良知的深微本质,从而确立起对于良知的信仰,表现为从良知切入却从无处立根基的独有成相。良知为有,其体却为无,要在有无之间确立起良知的信仰意志,这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2](P178)的学术氛围之下,显得迫切而必要。
二、手持足行是道
海门认为“无物而物在”,一个现实问题是,生活世界的“物在”究竟如何表现,且良知本体的不可执滞,不容拟议,也终究要通过实践主体将之下贯为经验世界的“手持足行”,形上良知之道与手持足行之经验的体用关系如何构成,也是需要回答的。海门谓:
盖视听行持,本来是道,所以非者,只因着些私心故耳。心苟不着,浑如赤子,则时徐行而徐行,时趋进而趋进,视即为明,听即为聪,率其视听行持之常,何所不是而复求加哉?明道云:非礼勿视听言动,积习尽有功,礼在何处?故学者但防其非而已,无别有是也。若心已无非,更求一般道理,并疑见在之视听行持,皆以为未是,则头上安头,为道远人,性学之所以不明,而工夫之所以反害也,可不辨哉
“视听行持”也可说成“持行”“手持足行”“手揣足行”“视听言动”等,是晚明学者常用的口语词汇。狭义而言,该词指的是目视、耳听、手持、足履等具体动作;广义地看,则泛指经验世界中的种种实践行为。很多情况下,这些具体动作被视作人之自然能力的表现,生活实践被看成是获取物质资料的多种手段,与道德因素关联不大。不过,置意于心学系统,由于良知对物事所具的统制性,加之良知的道德主体地位,因而生活世界里的多样行为便带有道德的成分,手持足行就转意为“当视则视、当行则行”,显示出良知在道德行为上的普遍规定。其实这种思想自孔孟以来就有之,然孔孟之“应当”,是在“礼”范围内的一种约束,视听行持如有逾矩,则为“不当”,因而视听言动实际上会产生“应当”与“不当”两种结果。海门说“视听行持,本来是道”则将之归约为一种结果,认为所有行为俱是“应当”,即“有道”。这一转变的内在契机是心“不能着些私心”,需做到“无物”,如此方能“时徐行而徐行,时趋进而趋进”,也才能将生活中的实际行为纳入到良知的道德标准之内,从而表现为多样的“物在”形式。
“手持足行是道”之说与杨时(字中立,号龟山,1053—1135)有关。龟山有言:“尧舜之道曰孝弟,不过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日出而作,晦而息,无非道也。譬之莫不饮食,而知味者鲜矣,推是而求之,则尧舜与人同,其可知也已。……圣人所谓性与天道者,亦岂尝离夫洒扫应对之间哉?”[8](P439)这是把人的自然能力和日常生活实践视作道的体现。杨时力行二程之道,但他也主张“凡形色具于吾身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反而求之,则天下之理得矣”[8](P439),以形色等外在事物置于自身,反身求之,则事物之理自现。龟山如此言说,明显又带有心学特色,故朱熹对此持强烈批评意见:“桀纣亦会手持足履,目视耳听,如何便唤做道?若便以为道,是认欲为理也。”[3](P1340)显然,朱熹是将手持足履、目视耳听之类的日常行为视作欲的表现,是有待“理”纠正的对象。海门针对朱熹此说,进一步言及:
晦翁云:“龟山言,饥食渴饮、手持足行便是道。夫手持足行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视耳听未是道,视明听聪,乃是道也。不然,桀纣亦会手持足履,自视耳听,如何便唤做道?”嗟乎,此正学问一大关键处也。夫世有一种恣情任欲之人,冒昧承当,则晦翁之言不可忽,但执定晦翁之言,彼赤子持行而已,不知其他,将亦不得为道乎哉!”[1](P427-428)
依海门之见,对于恣情任欲之人,因其心不纯,其行不道,朱熹之说于此是成立的,但对于良知纯净之人,如仍以这种方式质疑其言行,则是对道的误解。我们也不妨这样理解:如没有道德矩制,即便有手容恭、足容重之礼态,也可能是一种伪道德,如此便不能判明其行为所承载的道德价值;再者,目视耳听的对象如是道的存在,以此陶染目视耳听者并使其归之于道,其实这也是道的表现;另外,如笼统地将饥食渴饮、手持足行一概视之为非道,道与非道的界限便会变得模糊不清,这实际上有损于对道的向往和持有。但是,当聪明恭重本含伦理之情、道德之义,已区别于自然本能式的饥食渴饮、手持足行,在此种情况下再任由良知发散流行,则又有可能导致另一种“恣情任欲”。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1557—1627)对此就有看法:“呜呼!一则曰而已,再则曰而已,又曰不知其他,不知他字何所指,必欲借赤子以抹杀聪明恭重道理,何也?不知聪明恭重道理是天生来,自赤子时已完完全全的,只是尚浑含未露,如何便抹煞得他?如此立论,是又为恣情任欲者开一自便之门也。”[4](P40)这是少墟批评海门未见聪明恭重等行为所含之理,也不于手持足行中求得此理,而是将手持足行直接等同于天理,以此夸大这些行为的道德等级,这在少墟看来是“又为恣情任欲者开一自便之门”。其实,龟山讲“饥食渴饮、手持足行便是道”是基于圣贤这一前提而言,朱熹和少墟是从“物物皆含理”来确定聪明恭重之为道,而海门则基于“体用之全”将日常手持足行等意于良知心体的道德之善,三者微有不同。如果我们把圣贤看成是纯善良知的代名词,那么在设定道体之善这一前提进而演绎出手持足行所具的道德质地方面,海门与龟山有异曲同工之处,故陈来先生说“在排除外物的研究上,他(龟山)的倾向与格心说的立场是一致的”[10](P112),由此亦可见出理学与心学的某种思想对话。
在体用关系问题上,阳明曾谓:“盖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4](P20)这里的“体”指实体与本质,是事物存在的内在依据;“用”指发用与流行,是“体”的外在显现。未发之中作为“体”,有发而为已发之和的趋势及能力;已发之和作为“体之用”,是基于未发之中这一“体”的发散及呈现。台湾学者林月惠认为阳明的体用观表现为四个层次:“良知本体”之体用(显示良知本体的超越性与能动性)与“本体与工夫”之体用(彰显本体与工夫之合一),此为直接的体用关系;“良知与闻见之知”之体用(着意于主/从、本/末的从属关系)与“良知与七情”之体用(着眼于二者的相互转换),此为间接的体用关系[11]。由此可推显出阳明体用观的多重意蕴。总体上,我们仍可将阳明的体用观纳入到主宰与流行、先验与经验、形上与形下、道与器等构成的逻辑序列中,前者突出良知内具的充盈动力源特质,后者扩显出在内动力源促发下形成的心理意识层级和各种实践行为,由此形成心学中的“彻上彻下之道”。也就是说,良知具有自我存在、自我推扩的道德动力系统,用以保证其自身的独立运行,并提供施发于外的品质担保。在阳明,体用关系表现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作为体之用的“事事物物”含涉较广。至海门,则将“事事物物”窄化为“手持足行”,尽管语意范围有变化,然在体用关系的处理与安排上,海门无疑与阳明有应和,其基本内容也与阳明相对应,有关阳明的体用观其实也适用于海门的相关理论,如良知之“无”为体、为道、为先验、为形上,手持足行为用、为器、为经验、为形下,体用之间相互贯通,相互显明。
横向地看,阳明的“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致良知”带来的结果,“致”的工夫套路仍然得到足够重视。阳明弟子心斋,为避免出现“凡涉人为,皆是作伪”[12](P5)之困境的出现,曾私下和欧阳德(字崇一,号南野,1496-1554)论及“良知致”[12](P73),主张因任良知之自然,不必着意用力,以百姓日用间“爽快应答,不作滞泥,不生迟疑”[12](P86)来指点良知,因而有“百姓日用是道”之说。海门之“视听持行即是道”可简意为“是良知”,因良知纯善,在道德主体带动下,生活世界的一切行为都是良知本性的显出。从“致良知——良知致——是良知”,良知之体以递进的方式不断被强调,使得良知之用也以不同形式得以展开。与海门“视听持行即是道”之说类似,罗汝芳(字惟德,号近溪,1515—1588)亦有“捧茶童子是道”之言,指“童子日用捧茶是一个知,此则不虑而知,其知属之天也”[13](P45)。两说都强调当下行为所呈具的道德意义,但近溪之说在于突出眼前的瞬间灵明顿悟,带有较强的机缘指点特性;海门所言“手持足行”,则将阳明和心斋的良知“整体之用”细化为注重当下行为的道德呈现。在对“当下”的运用上,海门也把近溪的“瞬间性当下”转变为“连续性当下”,将眼下发生的行为联结起来,构成手持足行式的连续行为实践,以此显明良知心体之“无”在“物在”上的特殊表现形态。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在阳明后学中,他们对良知作为“千古学脉”自无疑义,但对于良知的本质内涵、存有形态以及由之而来的良知流行之用,都存在着种种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良知学的理论视域。
三、自我现成
海门以“无”定良知之体,并非否认良知之“有”的维度指向;认为手持足行是道,也并非以当下事为取代良知天理,而是意图从“我”之视角来新构良知的另一重理论面向——自我现成,以此回答良知主体与实践主体的自我定位问题。
自我现成与现成良知有关。“现成良知”作为一独立用语,出现在王龙溪和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1504—1564)的相关辩驳中。龙溪以“见在良知,与圣人未尝不同”[7](P42)之语,指罗念庵在对良知本体的把握上,“未免于矫枉之过”;念庵则以“世间哪有现成良知?良知非万死工夫断不能生也,不是现成可得”[14](P697)之反驳,认为王龙溪将良知作现成看,而不知下致良知的工夫,终会导致“茫荡一生有何成就”。观王、罗之辩,王龙溪的基本立场是:良知是现成的,无需再以万死工夫生出良知;良知现成且圆满地存在于每一个体,圣凡无别,个体只需固良知、复良知并循良知即可。这一立场和主张工夫实践的罗念庵显然有别。在王、罗之辩的带动下,此后围绕良知是否现成的话题,王门内外众多学者都有往来辩难,海门的自我现成观便是其中之一。海门指出:
《易》云“自强不息”,《书》云“能自得师”,《诗》云“自求多福”,《记》云“射者各射己之鹄”,孔子云“见过而内自讼”,颜子云“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曾子云“皆自明”也,子思云“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这“自”字、“己”字、“我”字,孟子学问渊源从此得来,真千圣一脉。[1](P483)
海门列出儒家经典以及孔颜等人论及与“我”相关的话语,意在表明关于“我”的思想由来有自,尤其点出孟子学问渊源由此而来,含有圣学不断相传的意味。海门称赞孟子之学乃“千圣一脉”,固然是肯定孟子的学术归属,更重要的是将传承孟子之学的后人也融入到整个圣学宗传体系之中,从而解决自身学术来源的合理性和学术传承的正当性问题。我们知道,良知学从语意源头看,与孟子提出的“良知”直接相关,确定孟子的学术地位,也就为良知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权威依据。这一论证意识在心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延续,海门自不例外。不过,海门于此的思考重点是在揭点“自我”的来源问题,以此担保在论述“自我”时既是合理的,又是正当的,故海门又言:“孟子认得头脑清,处处言‘我’字、‘反’字、‘身’字、‘约’字、‘己’字,最堪悟入。”[1](P477)这样,海门就从孟子之学中找到了其学依据,言“我”“己”或“反”也成为海门良知之学的重要特色。
“自我”的思想渊源问题得以解决,“自我”道德品性如何,这是海门在论述“自我”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涉及到在良知之体为无的情况下自我主体的设定问题。来看一段对话:
问:“见知闻知,岂真无所见所闻得之前圣者乎?”先生曰:“若谓前圣有什么可令后圣见、后圣闻,若谓后圣有所见于前圣、有所闻于前圣,皆是不知圣人者也。自古圣人无有一法与人,亦无有一法从人而得。见者自见,闻者自闻,知者自知而已。”曰:“如此,何以谓之圣圣相传?”先生曰:“圣圣正相传自见自闻自知,同归于宗,如水合水,非真有物可相授受之谓也。”[1](P478-479)
在问者看来,决定圣之为圣的主要依据,在于圣人的见闻知识要多于常人,圣圣相传的主要含义也在于经验知识的相互传授。很显然,这种观点是以见闻多少、知识多寡等外在因素作为区分圣凡贤愚的唯一标准,进而以识取德,以外代内。海门对此有异议,认为是否为圣贤的关键在“自见自闻自知”。当然,这里的“自见自闻自知”,不是自我闻见于知识经验,而是吾人对自我主体的反察与确认,体悟良知心体的湛然明净,回复到良知虚无的状态,能复于此并一于此,便是圣贤。海门对此十分自信:“故曰此天地之所以为大,盖言仲尼也,以天地与仲尼对待言之,不知仲尼者矣。虽然个个人心即仲尼,与我分别言之,又不知我者矣。仲尼即天地也,我即仲尼也,一也。学者须于此自信。”[1](P459)由是观之,海门设定良知之体为无,并非去除对善的追求,而是让世人摒弃各种具体工夫形式,因为“我之圣贤”本为现成,只以反观自我的方式恢复良知之善即可,从而确立起自我在良知系统中的道德主体地位。
“自我”道德主体地位得以确认,涉及到的另一问题是,“自我”的社会角色和实践事为还需阐明,以便回答“自我”在生活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海门谓:
乾坤一身而已。无极太极,是称父母。吾为天地立心,吾之气塞于两间。民吾肢体,物吾皮毛。大君吾之元首,大臣吾之手眼。天下之疲癃残疾、鳏寡孤独,皆吾身之痿痺而疾苦也。存吾昼作,没吾夜熄也。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我外无物也;程子曰我在天壤间,直是孤立,我无有对也;周子言立极在我,天地日月四时,鬼神不能违也;邵子谓肯把三才别立根。诸语皆同一旨。[1](P453)
这是海门针对弟子“《西铭》之乾坤与《易》之乾坤有何不同”之问时所作的回答。海门认为《西铭》的“乾父坤母”说,“只是庶官庶民,听命处多,主张处少”[1](P453),也就是缺少自我独立、自我主张的成分,缺乏实践主体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因此海门以“我”为中心,将乾坤万事纳入吾之身心之内,从天地之立到天下之作,无一不在“我”的范围之内,以此确立起实践主体的社会角色和实践担当。这样,一个高大“我”的形象便挺立在海门的思想系统之中,良知内在现成的能量被极大突显出来。在海门语录中,还有多处议及“我”的地位和作用,如“《论语》一书,将孔子言‘吾’字、‘我’字处类观之,甚妙。如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曰‘何有于我’,曰‘是吾忧也’等,不知凡几见于篇,其精神全归自身,此是旨要”[1](P485)之言,将孔子论“我”的话语视为学习的“旨要”;对于谢上蔡所说的“我要有便有,要无便无,天下事无一不由我”,海门认为“于此须断然信得过”[1](P484),显示出自我处理天下事的社会实践主体意义,现实自我取得了与良知同等的至上性和圆满性,良知主体的内在能量被极力显发。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海门论“我”说“吾”,并非推出极端自我主义而逾越于道德矩矱之上,而是有道德标准对之进行衡量和规约:
学问不可悬空立论,须于言下就体入自身。即今说良知,就看我只今问答,是良知不是良知;说不睹不闻,就看我只今问答,是睹闻是不睹不闻。密密自察,方有下落,若只泛泛论去,言自言我,自我又欲等待他时体验,则愈论愈支,如说食不饱,竟有何益。[1](P487)
这一道德标准便是良知,而且良知对“我”的指引和认定是当下即时的,这就提醒“我”在从事具体的实践活动时,需时时以良知为轨则,如此才能完成实践主体的道德任务,否则便会陷入自我空谈或自我张狂,这是海门对学人的警示,也是我们在谈论海门“自我论”时要注意的细节。
因此,海门所说的“自”“我”或“己”,具有圣贤般的道德品性,也能够自作主张、独立完成天下之事,具有道德的完满性和实践上的巨大能量。“自我”也并非工夫所生的对象,而是工夫行为的施发者、导引者与裁判者,其自身是自足的、现成的,无需经过外在工夫的雕琢与洗涤。在心学内部,主体之己我虽然一再被强调,但在阳明时,依然特别突出“若不用克己工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现,私欲亦终不自现”[5](P23),而海门则以“圣我无别”和“无事不由我”的豪言壮语,以更为张扬的方式将自我主体地位极力抬升,发出了“自心满足,世界满足,不干世界事”[1](P446)的响亮口号,格外凸显了“自我”自足现成、高扬超拔的一面。此点正如冈田武彦所言:“海门的现成论之所以成为明显的简易直截之说,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强调自我的现成。虽然他是继心斋、近溪之后而提倡自我(自心)现成论的,但此论在他那里却有登峰造极之感。他以为‘己即圣’,而以自我为现成,为此,他不容一刻拟议推寻,只要求直信自我,并以此为圣学第一义谛。”[15](P187)在海门思想中,良知具有强大的自我呈发能量,并以自我现成这种致思理路,使得这种能量显得尤为丰盈主动,现成良知之辩得以多维度展开。不过也需指出,自我现成对“信不及”者而言,仍未免有玄虚茫荡之处,也可能将本体与工夫、良知之先验性与自我之现实性并成一团,使之难以分疏,这对于主张工夫进路的晚明学者而言,自有其异议处。
海门的良知观,表现为由良知之体、良知之用、良知之我所构成的三维架构。体用自是一源,良知之我则涉及海门良知体用观中道德主体和实践主体分别含蕴的道德品性和道德能量,用以论证在良知之体为“无”的语意背景下,良知系统依然保有的道德有效性。这种良知观,在思想定位、核心构成和作用流行等方面,与阳明之学的基本方向相符,这对于阳明学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海门以“无”说良知,带有释氏成分,在儒学内部难免受到误解或辩难;手持足行是道,以当下即时行为直接与良知本然相联,此说固然凸显了良知的崇高与威严,但同时也忽略了中下根之人与良知相接的中间环节;把自我当现成,使得目标与现实、本体与工夫之间的区别变得难以界定,也可能使得自我朝着极端方向发展。然而,我们也不能说这意味着良知的解体,毕竟良知的三维架构能够自成一系,而且在由无转有、由有转实等方面,海门也设置了由此及彼、由彼返此的谆谆诫语作为掐紧之处,如“于此自信”“防其非”“密密自察”等,显示了海门对可能出现“良知不明”现象的警醒,这也是我们在探讨海门良知观时应注意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