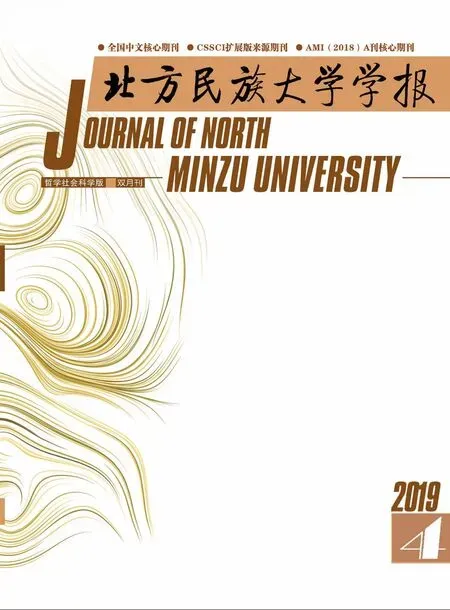曹元弼与黄以周学术异同考论
2019-12-05李科
李 科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乙酉,曹元弼(1867~1953年)通过南菁书院甄别考试,进入南菁书院,并从黄以周(1828~1899年)问学。王欣夫所撰《吴县曹先生行状》云:“乙酉,调取江阴南菁书院肄业,从定海黄先生以周问故。”[1](522)在曹元弼入南菁书院的前一年,即光绪十年(1884年)甲申,其从兄曹元忠(1865~1923年)已入南菁书院从黄以周治经学,曹元弼所撰《诰授通议大夫内阁侍读学士君直从兄家传》云:
光绪甲申,以第一人补博士弟子。督学瑞安黄淑兰师器异之,咨送南菁书院肄业,从定海黄元同师受《诗》《礼》、群经。[2](435下)
曹元忠入南菁书院后,住院学习。与曹元忠有所不同,曹元弼入南菁书院后并非住院肄业,而是“从定海师质正诸大义,不久即归”[2](435下),因此,其从黄以周问学的时间其实比较短,不及其从兄曹元忠。但是曹元弼从南菁书院归后,在与曹元忠及南菁同学,如张锡恭(1858~1924年)、陈庆年(1863~1929年)、王仁俊(1866~1914年)等论学的过程中,亦多闻黄以周之学。《诰授通议大夫内阁侍读学士君直从兄家传》云:“兄止宿南菁有年,每假旋,相就论学,各举心得相证,往往不谋而合。”[2](435下)又云:“迨弱冠后,兄每自南菁归,与余及故执友王虞笙大纶,考辨经史,纵论古今得失之林,天下治乱兴衰之故,其味醰醰,其芬郁郁,其声洋洋,古人所谓渐离击筑,旁若无人;高凤读书,不知暴雨者,真未足喻其乐也。”[2](437下)
《纯儒张闻远征君传》言曹元弼在南菁书院结识张锡恭后,“函书往来,商榷经义,君每至江阴,恒过余,纵论学术,别同异,明是非,必求惬心当理而止”[3](143)。因此,虽然说曹元弼从黄以周问学时间较短,但是在日后与曹元忠、张锡恭等长期受教于黄以周的南菁同学交流论学的过程中,也多与闻黄以周之学,并且从后来曹元弼的学术实践看,其学术思想也确实受到黄以周的影响,但是在奉持黄以周之教的过程中,因来自于其他方面学术思想的影响,其思想也发生了不少变化。
黄以周承其父黄式三(1789~1862年)之学,治学以礼学最为精审,而曹元弼在入学南菁书院之前,既在其父母授读之下,由《诗经》进而研习礼学,同时又问学于同县管礼耕(1848~1887年),在礼学上颇有造诣,尝欲重疏《礼经》,并撰《仪礼正义订误》《仪礼注疏后校》及《礼经纂疏长编》,后删定成《礼经校释》一书。从表面上看,曹元弼与其师黄以周皆精礼学,似乎学术上当多有相同之处,但是从曹元弼后来所著诸礼学著作及相关论说来看,其学术虽受黄以周的影响,但与黄以周不尽相同,其中颇有微妙之处。黄以周对曹元弼最大的影响是以经为本,实事求是,汉宋兼采的治学观念,二者的学术相通之处在此,但是二者学术最大之不同也正是从此而出。
一、黄氏父子治学态度与方法
清初,顾炎武反思明亡教训,在学术上提出“经学即理学”的观点,并在治学方法上提出由小学以通经学的考据学方法,嗣后经胡渭、阎若璩,至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发扬而汉学大兴,同时,治学方法上的汉宋学之争也逐渐兴起,至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出,在义理上驳斥朱子,汉宋学之争遂由学术方法之争演变为义理之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汉宋学之争一直是清代学术的一个焦点。黄以周之父黄式三对汉、宋之分却颇不以为然,黄式三在《汉宋学辨》中认为,“经无汉、宋,曷为学分汉、宋也乎”[4](73),因此认为判汉、宋为二而各守专家者为自欺欺人,如《易释自序》云:
自治经者判汉、宋为两戒,各守专家而信其所安,必并信其所未安,自欺欺人,终至欺圣、欺天而不悟,是式三所甚悯也。[5](2)
因此,主张以经学为本而会通汉宋,实事求是,如《汉宋学辨》云:
儒者无职,以治经为天职,荀子所云不求而得之谓天职也。儒者诚能广求众说,表阐圣经,汉之儒有善发经义者,从其长而取之;宋之儒有善发经义者,从其长而去之。各用所长,以补所短,经学既明,圣道自著。[4](73)
又《读顾氏心学辨》云:“天下学术之正,莫重于实事求是。”[4](311)黄以周亦承其父之观点,坚持以经为本,实事求是,汉宋兼采。首先,黄以周对读古经注,虽然强调明家法,但是反对墨守家法,而要以经为断,实事求是,如《释锾锊》云:“学者读古经注,宜知家法之异同,而定以经恉。”[6](338)又如《礼书通故》中讲:“阿注违传,近时说家法之大弊,深可慨也。”[7](740)而在清代乾嘉以来,学术最大之家法即执汉、宋门户,对此,黄以周持汉宋兼采之说,如《读〈汉书艺文志〉三》云:
凡解经之书,自古分二例:一宗故训,一论大义。宗故训者,其说必精,而拘者为之,则疑滞章句,破碎大道;论大义者,其趣必博,而荡者为之,则离经空谈,违失本真。博其趣如《孝经》,精其说如《尔雅》,解经乃无流弊。《汉志》合而编之,乃所以示汉世读经之法,惜今之讲汉学、讲宋学者,分道扬镳,皆未喻斯意。[6](387)
自乾嘉以来,汉宋之争外出现了调和汉宋之说,不外两途:一则“训诂宗汉,义理宗宋”[8](2),将汉宋两分之,但“汉儒未尝不明义理,宋儒未尝不精训诂”[8](2);一则取汉宋之学相似处而比类附会,如陈澧认为“汉儒、宋儒之学多有同者”[9](179),所撰《汉儒通义》《东塾读书记》即多取汉、宋,尤其是郑、朱相似之处以为类比,往往弃其大体绝异者。虽然黄以周强调汉宋兼采,但并不持此两种调停之说,且对此调停之说加以批评,如《南菁书院立主议》云:
今之调停汉、宋者有二术:一曰两通之,一曰两分之。夫郑、朱之说,自有大相径庭者,欲执此而通彼,瞀儒不学之说也。郑注之义理,时有长于朱子;朱子之训诂,亦有胜于郑君。必谓训诂宗汉,理义宗宋,分为两截,亦俗儒一孔之见也。兹奉郑君、朱子二主为圭臬,令学者各取其所长,互补其所短,以求合于圣经贤传,此古所谓实事求是之学,与调停正相反。[6](661~662)
由此可见,黄以周所谓的汉宋兼采与其父黄式三是一致的,即于汉、宋不论在义理还是训诂方面,都各取所长、互补所短,而不是于训诂宗汉而义理宗宋,或取汉宋相类之说以为调和。在黄氏父子看来,只要以经为本,实事求是,就不必株守一家一说,凡可以通经明道者,不论汉、宋,皆可采择。黄氏父子的汉宋兼采是以经为本,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在汉学和宋学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黄氏父子用以经为本,实事求是,汉宋兼采的原则指导治经,因此,其学术研究能够做到“有宗主而无门户”[10](424)。细读黄氏父子之著,其所宗非一家,汉学以郑玄为宗,宋学以朱子为宗。黄氏父子之所以宗郑玄、朱子,不仅在于“三代下之经学,汉郑君、宋朱子为最”[11](164),又在于两家不立门户,能网罗众说,实事求是,而不拘家法。黄式三以为“宋儒之能汉学者莫如朱子,而汉儒之能启宋学者,岂非郑君欤?”[4](74)虽然宗郑玄、朱子,但是亦不曲徇其失。如,黄式三《论语后案》虽然认为“《论语》注之传者,朱子为醇,天下之公言”[12](709),郑玄之注“当时尤贵”[12](710),但亦能于“古今儒说之荟萃,茍有裨于经义,虽异于汉郑君、宋朱子,犹宜择而存之”[12](711)。又如,黄以周于礼学宗郑,所宗者非郑玄家法,而是宗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7](2721~2722)的通儒之学,因此,其撰《礼书通故》,正法郑玄不专一家之义,而网罗众家,兼采其长,如《礼书通故序目》云:
昔者高密笺《诗》而屡易毛《传》,注《礼》而屡异先郑。识已精通乎六艺,学不专守于一家。是书之作,窃取兹意。以为按文究例,经生之功;实事求是,通儒之学。或者反以不分师说,为我诟病,甘作先儒之佞臣,卒为古圣之乱贼。惴惴自惧,窃有不敢。[7](2722)
对黄以周这种通人之学,在当时之评价亦如郑玄在东汉,有混淆家法之讥。如与曹元弼往来密切之费念慈,即谓黄以周《礼书通故》“有极精到处,惜无家法”[13](372)。
二、郑玄家法与实事求是
正是秉持着以经为本,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黄以周在南菁书院立下了“多闻阙疑,不敢强解;实事求是,莫作调人”[14](602)的规矩。曹元弼在问学黄以周时,黄以周亦尝将以经为本,实事求是之旨谕之。《复礼堂述学诗》卷九《述礼总义》云:
先生诲人不倦,因才设教,元弼尝侍坐,承间言“治经当以家法为主”,先生正之曰:“治经当以经为主。”元弼由此不敢以株守旧说为遵家法,务由注以通经,不强经以就传,深推诸家离合异同之故,归于按之经而合、问之心而安。久之,乃益知郑义之不可轻议。[15](卷九,5a)
吴地学术自惠栋以来,多讲求汉师各经家法,曹元弼在其父母授读群经之下,由《诗》及《礼》,渐及群经,又在与吴地学者往来论学之间,逐渐形成了治经专守郑玄家法的特点,故而其谓黄以周“治经当以家法为主”。从前面论述可知,黄氏父子在经学上反对墨守家法,主张以经为主,实事求是,于各家学说各取所长而补其所短。因此,针对曹元弼之说,黄以周答以“治经当以经为主”,即以经为主,实事求是,而融汇各家之长,不株守旧说。事实上,曹元弼亦赞同黄以周以经为主的实事求是的治经之法,因此,在黄以周答以“治经当以经为主”后,自言不敢墨守旧说,而“由注以通经,不强经以就传”。但是因为曹元弼对郑玄家法已经先入为主,因此,在其以经为主,实事求是的治经过程中,得出了“郑义之不可轻议”的结论,即曹元弼本黄以周之训以治经,恰好证成了其谨守郑玄家法的合理性。当然,曹元弼从黄以周以经为主,实事求是之方法而得出“郑义不可轻议”的结论还受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如云:
又目击世趋,以陵跞先儒为饰智惊愚之术,疑经非圣,犯上作乱,实由此阶。是用大为之坊,深塞祸源,说字宗许,说经宗郑,说理宗朱,非徒沿袭其说,必求实得于心。先生往日尝以“力挽时失”许之,惜所著各书,不及就师训定也。[15](卷九,5a~b)
在曹元弼看来,一方面,因为经注以郑玄为最精、小学以许慎为最精、性理以朱子为最精,所以,“说字宗许,说经宗郑,说理宗朱”是符合实事求是之旨的;另一方面,因为郑玄之学“中正无弊”[15](卷首,13b),许慎《说文解字》“九千文字归忠孝”[15](卷一四,7b),朱子“明道立教,百世所宗”[15](卷三,57b),出于正学术以正人心,深塞乱源的致用目的,所以“说字宗许,说经宗郑,说理宗朱”。不过,曹元弼也顾及“说字宗许,说经宗郑,说理宗朱”可能有沿袭旧说、墨守家法之弊,因此强调其“必求实得于心”,且以黄以周“力挽时失”之许来说明自己并非为了沿袭旧说,而是为了“大为之坊,深塞祸源”的致用目的,但黄以周所谓“力挽时失”,也未必全是对其学术的评价,更多的还在于对曹元弼著作致用意义上的评价。
因为曹元弼在问学黄以周之前,即受到了吴地学术讲究家法风气的影响,形成了对郑注的坚守,从而导致其在贯彻黄以周以经为主,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的过程中,不仅证成了坚守郑氏家法的合理性,而且对其师黄以周的著作亦有所误解。例如,《复礼堂述学诗》卷六《述礼总义》云:
元弼少肄业南菁书院,从院长黄元同先生问故。先生承太夫子敬居先生式三家学,博通群经,尤邃于礼。作《礼书通故》,仿许君《五经异义》之例,类聚典文,博采众说,条分缕析而折衷之,朴学潜研,真积力久,多发前人所未发。其于郑义,虽申订互见,然遵守实多,引申尤善,且有相违而适相成者。元弼撰《周礼学》,于封建、军制、庙祧等,皆因先生说而推详之,不揣固陋,间有弥缝,亦先生赞辨前贤之义,虽下己意,实本师法。[15](卷六,4b~5a)
曹元弼以为《礼书通故》乃仿许慎《五经异义》之例,此点符合黄以周著作之实[注]黄以周《礼书通故叙目》自言:“儒说之异同,别汇一编。迟之数年,乃仿戴君《石渠奏议》、许君《五经异义》,裦集是书。”见黄以周著,王文锦点校,《礼书通故》第五〇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713页。,但是对其中驳正郑玄之说,曹元弼则多加弥合。黄以周驳郑之说,如前引《序目》所言,正是效法郑玄之学不专守于一家,实事求是的做法,对郑注之依违,以经为断,实事求是,故申订互见。《礼书通故》中遵从郑玄之说的固然多,那是因为黄以周通过考据,以为郑注多合于经旨,故从郑说,而对郑说不足或误说处,则或申或订。但是曹元弼于黄以周申郑订郑之外,特强调其“遵守实多”,且认为黄以周申订郑注时“相违而适相成”,实际上都是从守郑氏家法的角度去审视黄以周此书。黄以周作为其问业师,于礼不当驳斥,然又以其师多申订“先师郑君”,所以曹元弼有此弥合之说。曹元弼所谓其《周礼学》于封建、军制、庙祧等多本其师黄以周之说而间有弥缝,大概亦如此,惜其《周礼学》今未见流传,不得考其详,然从《复礼堂述学诗》卷四《述周礼》尚可见相关论说。如关于军制,云:
夏、殷及周初,诸侯大国百里。周公制礼,则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而书传通谓之千乘之国。夫以公侯四五百里计,六十四井出一乘,可也。若百里而出千乘,则十井一乘,其虐甚于丘甲,民何以堪,先王之制岂其若是?黄先生以周《礼书通故》,以《逸周书》《司马法》与《周礼》相推校,乃知古二十五人为一乘,周以七十五人为一乘,乘法截然不同。又《周礼》畿内诸侯大国不过百里,其乘法与古同,而与外诸侯异。又以征调之法,为出赋之法,故《司马法》论军乘二法,人数多少迥异。郑注分别引之。元弼《周礼学》引申师说甚详。[15](卷四,39a~b)
黄以周于《礼书通故·军礼通故》考古军制之人数与乘数,其先据《逸周书·武顺解》及孔晁注,《周礼》以为“故车以二十五人为一乘”[7](1613),考以《司马法》所载之车乘之制,以为“《司马法》所言乘制,实仿《周书》,特其所用人数较古为多耳”[7](1614)。在此基础上,黄以周进一步辨《采芑》“其车三千”与《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之郑笺所言军制的问题。《诗·采芑》曰“其车三千”,郑笺以为“三千”为“三千乘”,云:
方叔临视此戎车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师扞敌之用尔。《司马法》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乱,羡卒尽起。[16](910下)
郑玄据《司马法》以七十五人为一乘,乃都鄙计井出车之法,则三千乘为二十二万五千人,远超天子六军之数,故以为周宣王承幽、厉乱后,南征荆蛮之国,不仅发六军正卒,而且羡卒尽起。黄以周以为“周初军制,自以《武顺解》‘四卒成卫’为通制”,因此推考郑笺,以为:
启行元卒,古亦谓之元戎:其人五伍二十五,古亦谓之一乘。天子六军,七万五千人,以元卒五伍计之,得三千乘。《采芑》所咏,正六军正卒之数。顾王出征不靖,非特羡卒不尽起,即正卒亦不尽用。而诗人意在夸美,故举六军正卒言之尔。抑亦玁狁素强,遂尽起六军与?又案:天子六军之制,七万五千人。有合前开、左右闾三卒言之者,其车千乘,如注疏家所言是也。有专以元卒五伍言之者,车三千乘,如《采芑》诗所言是也。其诸侯三军之制,用武王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之法,军百乘,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则大国千乘有公徒三万,如《鲁颂》所言是也。诸言各有所指,宜分别观之。若牵而缠合,无一可通矣。[7](1614~1615)
这里,黄以周根据《武训解》所载车乘的人数,以为“其车三千”正合六军正卒之数,并且认为天子出征讨乱,不仅羡卒不尽起,即便正卒亦不尽起,诗人意在夸美,否定了郑玄据《司马法》解《采芑》“其车三千”以七十五人为一乘及羡卒尽起之说。关于《采芑》“其车三千”的兵制问题,金榜曾详加辩驳,其后陈奂《诗毛氏传疏》承其说,皆与黄以周同。究其实,当以黄以周说为近理。又《诗·大雅·棫朴》“六师及之”,郑玄以为:
周王往行,谓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为师。今王兴师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礼》。《周礼》:“五师为军,军万二千五百人。”[16](1107下)
黄以周以为:
天子国制六军,其出征只用六师,不尽发正卒,不足则征诸诸侯,故《诗》述天子之军皆曰六师。《常武》为宣王亲征,亦惟曰“整我六师”,则《棫朴》诗言“六师及之”者,非殷末之制有异《周礼》之故矣。《周礼》以制军言,《诗》以出征言。[7](1615)
郑注以为《棫朴》“六师及之”之“师”为“二千五百人”之师,而非六军,乃殷末之制。事实上,郑玄此笺,孔疏即有疑惑,认为“军之言师,乃是常称,不当于此独设异端”[16](1107下),然出于疏不破注的原则,最后为调和之说,以为“当是所注者广,未及改之耳”[16](1107下)。黄以周则认为,以军制言,天子备六军之制,以出征而言,则只用六师,所以《棫朴》“六师及之”并非是殷末之制与《周礼》不同,而是所言对象不同。观黄以周之意,在于说明郑笺于两处言兵制时分别引《司马法》与《周礼》之不同,属于申订郑注,疏通经义,但并不强调郑注于两处一引《司马法》、一引《周礼》的合理性。但是曹元弼在肯定其说的基础上,特别提出郑笺于两处分别引之,而不及郑笺之误,其言外之意即认为黄以周所考证的军制问题,事实上,郑玄在笺《诗》注《礼》时已经明白,所以“郑注分别引之”。换言之,曹元弼是从宗郑的角度来看待黄以周关于军制的考证的,而对黄以周订郑之说不置一词。由此可以推想,其《周礼学》所谓“因先生说而推详之”,本“先生赞辨前贤之义”而于其师说“间有弥缝”,亦当是对其师申述郑玄之说而推详,对其师订郑之说而弥缝。由此可见,黄以周以经为本、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已经形成谨守郑玄家法观念的曹元弼而言,实际上更促成其宗郑。所以曹元弼在晚年述及黄以周之学时,黄以周变成了说礼以郑义为宗,如云:“院长定海黄元同先生尊闻行知,触类变通,由后师之说,以深探先师硕意,以为汉代经师家法不同,而莫纯于高密郑君,宋代理学宗派不同,而莫正于新安朱子,说礼皆一以郑义为宗”[3](144)。
三、宗郑、经世与汉宋兼采
黄以周父子强调以经为本,实事求是,因而在汉学、宋学的问题上持汉宋兼采的态度。这一点对曹元弼有很大影响,但是曹元弼在本其师说的过程中又有变通。与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一样,曹元弼亦持汉宋兼采的态度,如云:“学者勿争汉、宋门户,但当择善而从,兼得先儒之益,以明圣人之教,斯善矣”[15](卷三,57a~b)。又云:“学者自少读朱子《集注》,闳意眇指,未必深窥,当更溯源注疏,参酌群言,乃知紫阳采择之精,而汉、宋之不容强分门户。”[15](卷一三,26a)
可见,曹元弼亦赞同黄氏父子汉宋兼采,择善而从的治学原则。同样,曹元弼于汉学和宋学中亦标举郑玄与朱子,与黄氏父子认为“三代下之经学汉郑君、宋朱子为最”[17](217)一致。如,曹元弼认为“历观古今百家,以为郑君、朱子集经学、理学之成”[15](卷首,15a)。但是曹元弼的汉宋兼采和并宗郑玄、朱子,事实上相对于黄氏父子来说又有很大的变异。
首先,曹元弼认为,汉学、宋学前后一贯,宋学之主流与汉学是一致的。如云:
学者多争汉学、宋学之别,然《周易》《尚书》,乃魏、晋人翻新作伪,排弃古训,非宋儒之咎。《春秋胡传》,亦有为而作,说虽偏颇,非故立异。汉、宋殊致,惟论《诗》《书序》及《诗·郑》《卫》诸篇,千虑一失,早有定论。至礼,则司马、程、张、朱子皆确守注疏,而紫阳尤笃信高密。其背经任意反注违例者,乃安石一派耳,后人岂可尤而效之。[15](卷六,55b)
在曹元弼看来,汉宋之别,于《周易》,是因为王弼、韩康伯等违异汉儒旧注而翻新造成的;于《尚书》,是晋人排弃汉儒之说而造伪《书》及伪《孔传》,降及宋代而与汉异,其实并非宋人所为,所以不当于此二经以咎宋儒。于《春秋》一经,曹元弼认为《胡氏春秋》是有为而作,“多感慨时事之论”[15](卷一〇,83b),并非故意标新立异。而于《礼》,司马光、二程、张载、朱子皆确守注疏,而朱子尤其笃信郑玄礼注,且背经反传的只有王安石新学一派。因此,汉宋实质上的分歧在《诗序》《书序》的存废和《郑风》《卫风》的淫诗问题。在《易》学上,曹元弼亦认为宋儒多通《易》义,且有功汉《易》。如《周易郑氏注笺释序》云:
宋濂溪周子、明道程子、横渠张子通论《易》义,旨深言大。伊川程子因孔氏《正义》,而实以精理,用功至深,多与汉儒暗合。……康节邵子究极理数,所传河、洛先天之说,后儒或力攻之。然河图即天地五十有五之数,为生蓍立卦之本;洛书即《易纬》太一行九宫之法,与“帝出乎震”一节用异而位同。北周卢仆射说明堂,已目此数为龟文。先天加一倍法,与《太玄》合;八卦分阴阳,与《参同契》合。盖立卦已备,比六十四卦阴阳之画而观之,以起消息,推刚柔之事,与虞氏之法同源而分流,要之河、洛先后之名,不必深求,其法则确有所由来也。晁以道始考《周易》古本,东莱吕氏为之音训,而《汉志》《易》十二篇,《魏志》称郑本《彖》《象》不与经连而注连者,至是乃复其旧。此三者穷理极数,考文之事,朱子兼之,作《本义》《启蒙》。尝曰:“《易》之为象,必有所自来。顾今不可考,则姑阙之。”盖自王弼以来,古学尽亡,师传歇灭,且千年欲一旦而丛棘尽辟,豁成大涂,斯固难也。他若朱子发考古义,王伯厚辑郑注,杨诚斋论政治,及诸有道名儒,笃学精研,历元迄明,撰述益多,各有心得。[18](卷首,26b~27b)
关于《尚书》,宋人对辨定伪《书》、伪《传》,辑考郑注,亦颇有功。曹氏云:
至宋吴氏棫、朱子始质言古文孔传之伪,元吴氏澄、明梅氏鷟继之。宋王氏应麟始搜采群书,辑郑注遗文,国朝惠氏栋得其孤行传本。或以为出自定宇,托诸伯厚者,必不然也。[19](452)
至于礼学,在曹元弼看来,自郑玄以至于朱子,再传至于江永,更是无汉宋之分,前后一贯。《复礼堂述学诗》卷四《述周礼》云:
伊川、横渠并尊《周礼》,而朱子礼学,直绍郑君,故治礼无汉学、宋学之分,在实事求是,体心践履,以达之天下而已。[15](卷四,59b~60a)
并且,曹元弼认为宋儒于郑氏礼学之传承与复兴,亦颇为有功。如《礼经纂疏序》云:
宋初,聂氏崇义作《三礼图》,据旧图为本,考正疑讹,申释隐滞,近唐儒精实之学。景德元年,吕蒙正等上邢昺、孙奭等所校定《仪礼疏》。其书见于今,为疏本之最古者。其后儒臣多敦崇古学,横遭憸人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非圣无法,天下愤之。南渡后,张氏淳据当时所存各本,校严州所刊《仪礼》经注,作《识误》,有功此经。而朱文公以上贤纯徳,绍郑君于百世之上,知治乱天下之必本于礼,而《仪礼》为礼之本经,《周官》其纲领,《礼记》乃其义疏,深忿安石遗本宗末,博士诸生于仪法度数之实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上疏乞修《三礼》,不果行。晚乃与弟子编《仪礼经传通解》,取十七篇经文,分章附记,全录郑注,节引贾疏,经所不具,以记补之,别立门目,以类相从。凡各经传记、史志有及于礼者,靡不毕载。自定家、乡、学、邦国、王朝诸礼,而以丧、祭二礼属弟子黄氏幹。黄氏成《丧礼》,于《祭礼》未及精专修改,复以其书授弟子杨氏复,杨氏别成《祭礼通解》。盖礼书若此之难也。文公弟子又有李氏如圭,与修《通解》,别撰《仪礼集释》,阐发亦多。自文公作《通解》后,郑氏礼学复兴,文公尝称郑注《三礼》大有功,叹为大儒,又于宋孝宗之丧得郑注“天子诸侯之丧皆斩衰无期”一条,深服郑君,以为其说足以补经定制。盖高密紫阳,易地皆然。嗣有岳氏珂刊《三礼》郑注,魏氏了翁撰《九经要义》。[20](444~447)
在曹元弼看来,朱子在礼学上不仅直绍郑玄,其撰《仪礼经传通解》,创通大法,至清代马骕、张尔岐、吴廷华、江永、徐乾学、秦蕙田等学者的礼学著作,皆沿袭朱子之法。因此,朱子对清代礼学的复兴功不可没,如云:
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厘析经文,每一节截断后一行题云:“右某事。”较贾疏尤简明。……此朱子之大有功于《仪礼》者。至国朝而马宛斯《绎史》所载《仪礼》,张稷若《仪礼郑注句读》,吴中林《仪礼章句》,皆用朱子之法。江慎修《礼书纲目》因朱子《通解》而编定之,固宜遵用其法。徐健庵《读礼通考》,秦文恭《五礼通考》亦皆分节,自朱子创此法,后来莫不由之矣。[21](577下~578上)
首先,由上所引曹元弼关于汉宋兼采及宗郑玄与朱子之说,可以发现,其中依然贯穿了曹元弼坚守汉学,尤其是郑玄家法的痕迹。曹元弼之汉宋兼采及宗朱子,是以宗汉宗郑作为基础而会通汉学宋学的。虽然黄氏父子在汉宋学问题上也以郑玄为主,但是并不强调郑学家法,尤其不墨守郑说,其著作中驳郑注之误者甚多。而曹元弼在郑玄和朱子问题上,则坚守郑君家法,不容稍有异议,于朱子亦加尊崇,而于郑、朱相异之处,则多以郑为归,此例在《礼经校释》《周易郑氏注笺释》《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孝经郑氏注笺释》等著作中比比皆是。
其次,曹元弼的汉宋兼采有非常明显的经世目的。曹元弼与作为纯粹学者的黄氏父子不同,其先后受东林学派以来的顾炎武、冯桂芬、黄体芳及东塾学派、张之洞等人的影响,同时又身处晚清,关切时局之危,故其于历代经学尤其注重其中的经世功用。正是因为这种对经世致用的关注,曹元弼在汉宋兼采的观念中融入了浓厚的经世思想。曹元弼认为,秦火之后,汉儒发明经训,阐明王道,至汉武帝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遂开汉四百年经学政治之盛”[15](卷首,8b)。虽然汉儒“所讲者仁义,所守者圣法,天秩民彝,同归一致”,但是经分今古,且一经又有各家,如《易》有施氏、孟氏、梁丘、京氏、费氏;《书》于今古之外,又有大小夏侯、欧阳三家;《诗》有今文齐、鲁、韩与古文毛四家;《礼》有“大小戴、庆氏不同”;《春秋》有公羊、谷梁、左氏三家之异;因为“文字、训义、名数之属,各习其师”,甚至“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党同妒真,不求至是”[15](卷首9b)。至东汉末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15](卷首,9b)。至魏晋天下大乱,玄学清谈之风兴起,破坏礼法之事甚多,但“圣人之道不绝,惟郑氏礼学是赖”[15](卷首,10a)。降及六朝时期,虽然中原分崩,迭经战乱,但是其间“礼议义疏,精研经义,辅翼名教”,至河汾之学兴起,“佐唐贞观之治”[15](卷首,10a)。在曹元弼看来,经学盛衰关系天下治乱,而东汉以后至唐,天下能够拨乱世而反诸正,正在于汉儒之阐明经训,尤其是郑玄及历代研习郑玄《礼》注者之辅翼名教。而自唐末五季之乱后,宋儒继汉儒而阐明经义,尤其是朱子绍郑玄而集宋学之大成,重开治世之后,一直到明亡而大彰儒效,则其功多赖宋儒,尤其是朱子。曹氏云:
秦火之厄,先王之法尽灭,故汉儒务发明经训,以兴王道。五季之衰,人心陷溺已极,故宋儒务阐扬义理,以觉民迷。自宋初敕邢昺、孙奭等校补经疏,儒学蔚兴。而濂溪、明道、伊川、横渠诸贤,以躬行心得,穷理尽性之学,为人伦师表。朱子集其大成,极毕生之力,作《四书章句集注》,穷性道之奥,严诚伪之辨,判义利之界,明邪正顺逆之分。宋末以来家弦户诵,明代用以取士。而三纲四维,凡民皆知,尽忠蹈仁,志士接踵,气节之盛与东汉等。《周礼》师儒,以道得民,其效大彰明较著矣。然周、程、张子之学,实皆自熟读注疏,博学反约,含咀英华而出。朱子尤覃研群经,服膺郑君礼学。其于国家治乱,民生休戚之实,无不讲求有素。[15](卷首,11a~b)
清初,顾炎武反思明亡教训而揭起“经学即理学”之义,强调由小学通经,通经以致用,遂开清代考据实学一派。虽然乾嘉考据学多以经史考证为务,不甚讲求经世致用,但是在曹元弼看来,这是博极古义而精发圣言,使七十子至汉儒之绝学得以昭炳,为通经致用奠定了基础。同时,清代之理学名臣如汤斌、陆陇其、张伯行等继承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学,而佐清廷辅治。中兴名臣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之戡定太平天国之乱,在曹元弼看来更是通经致用,博学达政的典范。曹氏云:
亭林顾先生当贞元之会,愍恻当世,大振颓风。其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为主,实握经明行修,通经致用之要。自文字、训诂、声韵、名物、度数、礼乐、刑政,性与天道,微言大义,以及郡国利病,山川险要,士风民俗,细无不包,大无不举,而处心光明正大,廓然有斯人吾与吉凶同患之意。虽耿耿孤忠,系心先代,皦皦大节,不事二姓,而著书立言,中正平实,绝无过激险怪之论,贻患来世。学派既开,英儒宏彦,翕然宗之,式古训,讲实学,以求儒效。
恭逢景运中天,列圣郅治,御纂钦定诸经,同符尧、舜、周、孔,彝教迪民,洪化育才,经师大儒,云会星联,承流宣风,修学兴道。于是《易》有惠、张、姚氏,《书》有江、孙、段、王,《诗》有二陈、马、胡,《礼》有江、戴、金、张、凌、胡,《春秋》有惠、顾、孔、陈、钟氏,《孝经》《论语》《孟子》有阮、刘、焦氏,《尔雅》《说文》有邵、郝、段、桂、王氏,群经通义有阮氏、陈氏,皆博极古义,精发圣言。自七十子以至汉儒,千载垂绝之学,一旦昭炳光明。而汤文正、陆清献、张清恪诸公,以理学名德,光辅圣治;曾文正、胡文忠、左文襄诸公,以博学达政,底定中原。[15](卷首,11b~13a)
因此,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曹元弼认为汉学、宋学亦前后一贯而有益于治道,因此,持汉宋兼采之说。这是曹元弼不同于其师黄以周之处,但曹元弼仍然是以学术上的实事求是为前提的。通经致用的目的是拨乱世反诸正,然学术之正邪关系到人心之邪正,而人心之邪正关系到天下治乱与生民祸福,曹氏云:
学术正则人心正,而人才皆用于忠孝仁义,经文纬武,以造天下莫大之福。学术乱则人心乱,而人才皆趋于悖逆诈伪,贪暴残杀,以贻苍生无穷之忧。[15](卷首,6b)
因此,要通经以致用而使天下归于郅治,而使生民相生、相养、相保,则必须正人心,而正人心则须正学术,正学术之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原本经义,实事求是,而不能背经反传。曹元弼认为汉儒,尤其是郑玄,继七十子之后,实事求是,阐明经训,得学术之正,经明行修,所以能够开四百年经学政治之盛,历魏晋六朝之乱而维持圣道不坠,并开唐贞观之治。经历唐末五季之乱,宋儒能够继汉儒之学,“以躬行心得,穷理尽性之学,为人伦师表”,尤其是朱子直绍郑玄之学而集宋儒之大成,开宋以后数百年之治,以至于晚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诸人。这一维持世教的过程,既强调实事求是,又以汉儒尤其是郑玄为核心。因此,从经世致用角度的汉宋兼采而言,曹元弼亦在其中贯穿了坚守汉儒,尤其是郑玄家法的原则。
四、结 语
综上可知,曹元弼入学南菁书院,问学于黄以周,在以经为本,实事求是及汉宋兼采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方面,曹元弼虽然汲取了黄以周之教,但是又受其自身既有的宗汉宗郑思想,以及来自于前辈、家族、乡邦、时贤和晚清经世思想的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从而形成了不同于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的学术特点,在以经为本,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下证成了其坚守汉儒,尤其是郑玄家法的合理性。因此,曹元弼的汉宋兼采,在学术上是以郑玄家法为核心的汉宋兼采。同时,其在学术之外,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论述汉宋兼采。虽然曹元弼问学于黄以周的时间很短,且对黄以周之说奉持不坚,多有变异之处,但是黄以周以经为本、实事求是及汉宋兼采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还是对曹元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著述方面。所以曹元弼在具体著述中虽然坚守郑说,但能够博采他说而赞辩之;虽然强调经世致用,但不流于以经议政的穿凿,能够以实事求是之态度确求经义。正如其《复礼堂述学诗》卷三《述诗》言其一生著述之旨曰:“我不忍先王先圣教民相生、相养、相保之道,从此败坏而不救,沦亡而不反也。是用深考汉学之源流,会通宋学之精义,平心实事,正本清源。群言淆乱质诸圣,天下之动贞夫一。”[15](卷三,71b~7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