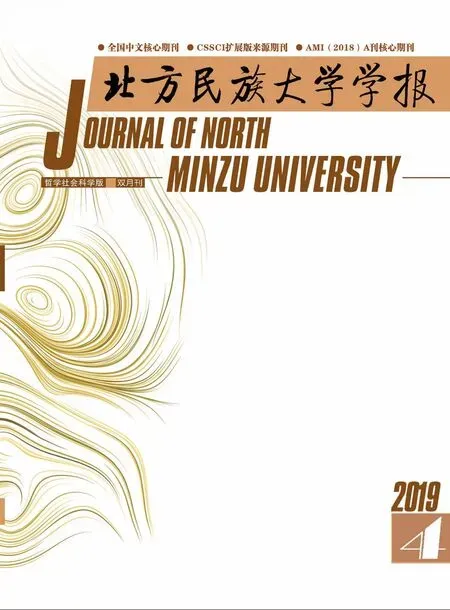唐代巡幸起居制度研究
2019-12-05张琛
张 琛
(1.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2.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所谓起居制度,“是指以下对上的一种探视和问候的制度”[1],这种探视和问候,往往以问起居的形式来完成。问起居的形式虽多,但唐代问起居的相关内容只限于臣下对皇帝及皇室其他成员而言,如太上皇、皇后、太子等[2]。巡幸是指唐朝皇帝离开京城到地方的巡视活动,巡幸起居的形式也限于臣下向皇帝的问起居。现存的唐史史料并没有将问起居作为制度进行专门论述,起居制度散见于史料中,零星而分散,使得起居制度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杜文玉、谢西川的专文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对唐代的日常起居、巡幸起居、外官起居等起居形式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述,还指出了起居制度的影响[2]。此外,杜文玉注意到了内殿起居与中枢决策的关系[3],胡戟、刘后滨注意到了起居仪[4](229),这些研究也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尽管如此,作为起居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巡幸起居制度在起居形式及起居人员、起居表及制度变迁等方面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笔者不揣浅薄,爬梳史料,对巡幸起居制度进行了再研究,希望使相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一、巡幸起居人及巡幸起居形式
唐制:
凡车驾巡幸及还京,百官辞迎皆于城门外,留守宫内者在殿门外,行从官每日起居,两京文武职事五品以上三日一奉表起居,三百里内刺史朝见。东都留司文武官每月于尚书省拜表,及留守官共遣使起居,皆以月朔日,使奉表以见,中书舍人一人受表以进。北都留守每季一起居。[5](114)
上述起居制度规定了车驾巡幸期间,问起居人员的构成及问起居形式。其人员构成主要由行从官、京师留守官、地方州刺史、东都及北都的留守官组成。其实不唯如此,史料中还有皇太子、公主、宗室皇亲等人问起居的记载。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太宗征辽发定州,“皇太子奏请飞驿递表起居,又请递敕垂报,许之。飞驿奏事,自此始也”[6](587)。唐太宗征辽东,皇太子李治在定州监国,要向远在高丽作战的李世民问起居,这是皇太子问起居的例证。唐高宗巡幸洛阳,皇太子李显在长安监国,曾向唐高宗奉表起居。
《文苑英华》卷六○五《皇太子请起居表》载:
臣某言:今月某日,起居舍人某至,伏承圣躬顷稍不安,今已痊复,手舞足蹈,庆跃兼深。臣闻孝于事亲,为子之方已极;恭于奉上,为臣之道则先。臣自违侍轩墀,已淹时序。周储故事,一日三至于寝门;晋室旧仪,一月五朝于左阁。今之望古,臣独何人?日者沥胆陈祈,焦心觐谒。伏惟天皇以关河镇重,监守务殷,睿旨冲邈,未垂矜亮。今既十月筑场,三农事隙,特乞暂息恩召,俯念丹诚,遂以起居,假以时月,得晨拜旒扆,遂臣私情;则暮辞阙庭,在臣无恨。不胜恋慕之至,谨遣某官奉表陈请以闻。[7](3137)
该起居表的作者是崔融。《旧唐书》卷九十四《崔融传》载:“崔融,中宗在春宫,制融为侍读,兼侍属文,东朝表疏,多成其手。”[8](2996)崔融曾是唐中宗的太子侍读,帮助唐中宗起草表疏,可以说明《皇太子请起居表》中的皇太子即唐中宗李显,问起居的对象则是唐高宗李治。“伏承圣躬顷稍不安,今已痊复,手舞足蹈,庆跃兼深”,说明唐高宗在巡幸期间得了一场病,后来康复了。“自违侍轩墀,已淹时序”,说明唐高宗在外巡幸的时间非常长,太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父亲了。“今既十月筑场,三农事隙,特乞暂息恩召,俯念丹诚,遂以起居,假以时月,得晨拜旒扆,遂臣私情”,说明唐高宗巡幸地距离长安较远,唐中宗要在讲武和农事的间隙才能去见唐高宗。又,李显是在永隆元年(680年)八月被立为皇太子的,说明唐高宗这次巡幸的时间当在永隆元年八月以后。据此可以推断唐中宗的奉表起居发生在唐高宗巡幸洛阳期间,时间是永淳元年(682年)四月丙寅至永淳二年(683年)十二月丁巳之间,这次巡幸时间长达289天,且长安至洛阳,路途遥远,要在讲武或农隙期间才不影响生产,巡幸洛阳期间,唐高宗患有严重的头痛病,一再推迟封禅中岳大典,后来被侍医秦鸣鹤治愈,与前面考证相合。据此,崔融《皇太子请起居表》也可以作为皇太子向巡幸皇帝问起居的例证。
公主也是问起居之人。《唐代墓志汇编》永淳025载:
贞观初,圣皇避暑甘泉,公主随傅京邑,载怀温情,有切晨昏,乃□□表起居,兼手缮写。圣皇览之欣然,以示元舅长孙无忌曰:朕女年小,未多习学,词迹如此,足以慰人。[9](703)
墓主是唐太宗的女儿临川公主,根据墓志,临川公主死于唐高宗永淳元年五月,春秋五十有九,可以推断她生于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贞观初年也就七八岁的样子。年幼的公主向在甘泉宫避暑的唐太宗上起居表,可作为公主向巡幸在外的皇帝问起居的例证。
宗室皇亲等也是问起居人。《旧唐书》卷一百七《凉王璇传》载:
东封年,以渐成长,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于夹城中起居,每日家令进膳……天宝中,庆、棣又殁,唯荣、仪等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于外坊,时通名起居而已。外诸孙成长,又于十宅外置百孙院。每岁幸华清宫,宫侧亦有十王院、百孙院。宫人每院四百,百孙院三四十人。又于宫中置维城库,诸王月俸物,约之而给用。诸孙纳妃嫁女,亦就十宅中。[8](3271~3272)
“东封年”即开元十三年(725年),因为这一年的十一月,唐玄宗封禅泰山。自开元十三年始,十六王宅制度正式建立,通名问起居成了十六王宅制度的一部分。“每岁幸华清宫,宫侧亦有十王院、百孙院”,说明这种制度适用于皇帝巡幸地,可作为亲王皇孙向巡幸在外的皇帝问起居的例证。
唐制对京师留守官、东都留守官、地方州刺史的问起居形式均有明确规定,行从官的问起居形式仅规定为“每日起居”,具体形式缺乏说明,需要进行考察。《旧唐书》卷七十四《刘洎传》载:
贞观十九年,太宗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康。洎与中书令马周入谒。洎、周出,遂良传问起居,洎泣曰:圣体患臃,极可忧惧。遂良诬奏之曰: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诏问其故,洎以实对,又引马周以自明。太宗问周,周对与洎所陈不异。遂良又执证不已,乃赐洎自尽。[8](2612)
唐太宗巡幸定州,侍中刘洎、中书令马周、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人均是行从官。“洎、周出,遂良传问起居”是指刘洎与马周入谒出,褚遂良得以传问起居,这种传问起居也是以入谒的形式完成的。因此,可以断定入谒起居是行从官问起居的一种形式。
叩头起居也是行从官问起居的一种形式。刘瑕《驾幸温汤赋》载:
开元改为天宝年,十月后兮腊月前。……百官叩头而起居,四夷搕额再拜。亦曾见没量时来游猎,不得似这回最快。既而到温汤,登会昌,历严帐,巡殿堂。[10](2~3)
刘瑕《驾幸温汤赋》记载的是唐玄宗驾幸温汤的场景。“百官叩头起居”之“百官”,指的是行从官,“四夷搕额再拜”中的“四夷”也是指行从人员,问起居的形式也是叩头起居。可见,叩头起居也是行从官问起居的形式,是以跪拜皇帝的方式完成的。
二、巡幸起居表
“起居制度作为国家的一种典章制度,是指下对上的一种探视和问候的制度。”[1]巡幸起居表的内容表现为臣下对皇帝的探视和问候。武则天巡幸长安,富嘉谟《起居表》曰:
臣某言:伏奉车驾以今月二十二日西至长安。臣闻咸秦奥壤,河洛旧区,王者是宅,因时顺动。故睿情载伫,西眷邦土,玉轫金根,天旋云被。皇舆凯入,在藻知归。臣忝葭莩,谬膺垣翰,尹京靡托,陪銮遂阻,紫宸渐遥,丹慊空积。伏惟祁寒在侯,辇路逶迤,法驾就跸,圣躬多祜。然后辟天陛而临旧都,巡卜征而考元吉者也。无任悦豫之至,谨遣某官奉表以闻。[7](3159)
武则天从洛阳出发,预计到达长安的时间是“今月二十二日”,具体年月不详。《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富嘉谟传》载:“长安中,累转晋阳尉,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8](5013)直到武则天长安年间,富嘉谟才具有上表问起居的资格,故武则天这次巡幸长安的时间当在长安元年(701年)之后。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在洛阳称帝后,只在长安元年回过一次长安,因此,富嘉谟《起居表》的时间当为长安元年,《新唐书》卷四则将时间具体到了十月壬寅[11](102)。故《起居表》中的“今月”也就是十月。十月壬寅是十月二十三日,与“今月二十二日”的记载不一致。武则天诏令巡幸长安,打算十月二十二日到达,路上耽搁一天,十月二十三日才到,也属正常。
“故睿情载伫,西眷邦土,玉轫金根,天旋云被”,是说皇帝因怀念旧土才驾幸长安的。武则天晚年在“立子”和“立侄”的问题上一直处于摇摆之中,直到圣历二年(699年)才决心立自己的儿子李显为皇太子。为了稳固李显的太子之位,增加与李氏子孙的情感交流,武则天决定巡幸长安。“臣忝葭莩,谬膺垣翰,尹京靡托,陪銮遂阻,紫宸渐遥,丹慊空积”,富嘉谟对于自己因公务不能扈从皇帝驾幸长安深为自责。“伏惟祁寒在侯,辇路逶迤,法驾就跸,圣躬多祜”,则是富嘉谟对皇帝的问候,希望皇帝注意身体,因为当时已经是农历十月下旬了,天气非常寒冷,对于已经七十八岁的皇帝来说是非常辛苦的,这是富嘉谟《起居表》的主旨。
唐德宗车驾幸梁州、洋州,于公异代李晟上《起居表》,表文如下:
臣某言:自中使至,伏奉手诏后,行在所未有人至。伏以巴梁既远,信使全希,路有豺狼,时当否塞。东征西怨,彼虽幸于南巡;捧日望云,臣独瞻于北极。伏惟陛下以重慎为意,以社稷为心,每于寝膳,必尽颐摄。况朱明启夏,小暑届时。曾观蜀汉之风,小异函秦之气。尚衣侍膳之分,莫敢侵官;资父事君之诚,空思入面。违奉既久,涕恋无从。不任之至。[7](3159~3160)
于公异所代之人当为李晟。《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于公异传》载:
于公异者,吴人。登进士第,文章精拔,为时所称。建中末,为李晟招讨府掌书记。兴元元年,收京城,公异为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肃清宫禁,祗奉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德宗览之,泣下不自胜,左右为之呜咽。既而曰:不知谁为之?或对曰:于公异之词也。[8](3767)
泾原兵变之后,直到兴元元年(784年)李晟收复长安,于公异一直是李晟的掌书记。掌书记掌“表笺书翰”[12](8169),具体为“朝觐、聘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号令、升绌之事”[12](8480~8481)。兴元元年,李晟收复长安,命令于公异为他露布行在。据此可知,《起居表》也是于公异代李晟所奏。
“自中使至,伏奉手诏后,行在所未有人至。伏以巴梁既远,信使全希,路有豺狼,时当否塞”,是指唐德宗经历奉天之难后,逃至梁州、洋州的事情。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开赴河南战场的泾原士卒在途经长安时发生哗变,京城空虚,唐德宗仓皇出奔到奉天。哗变士卒拥戴朱泚为帝,并围攻奉天城。十一月,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千里赴难,解了奉天之围,但被宰相卢杞所间,与神策军矛盾逐渐激化,遂与朱泚潜联合,德宗被迫再次南迁梁州。朔方军叛,奉天城内朔方将士本李怀光旧部,德宗惧为内应,仓促南奔梁州,扈从者主要是宦官所统的左右禁军。德宗一行进入骆谷后,适逢霖雨,道途泥泞,六军溃散,很多卫士亡归朱泚。唐德宗的安全没有保障,引起了李晟的担心。“东征西怨,彼虽幸于南巡;捧日望云,臣独瞻于北极。”当时,李晟屯兵东渭桥,为李怀光所阻,不能救驾,只能遥祝皇帝平安。“伏惟陛下以重慎为意,以社稷为心,每于寝膳,必尽颐摄。况朱明启夏,小暑届时。曾观蜀汉之风,小异函秦之气。尚衣侍膳之分,莫敢侵官;资父事君之诚,空思入面。违奉既久,涕恋无从。不任之至。”不仅关切皇帝的安全,还对皇帝的饮食起居进行关注,希望皇帝以重慎为意,以社稷为心,善自珍摄,表达了对皇帝的忠心和惦念,这也是该《起居表》的内容主旨。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起居表都表现为对皇帝的探视和问候,还有一些起居表的内容为述职。羊士谔《代人行在起居表》曰:
臣某言:臣以菲才,亲奉昌运,受藩隅之重任,效犬马之微诚。惟君知臣,特受恩奖。夙兴夜惕,荣惧积中。臣某中谢。伏以租税之殷,江乡为重;闾井之化,水旱是虞。臣职在分忧,期于富庶。宣陛下雨露之惠,令获小康;守朝廷刑赏之规,敢思中立。条赋敛以办集,除疾苦而均安。闭合斋心,仰思元造。窃以圣慈广被,每念遐方。臣忝守官,合具闻达。[7](3159~3160)
行在乃是皇帝的驻跸地,是指天子外出巡幸居止之处[13](371)。羊士谔《代人行在起居表》可视为巡幸起居表。羊士谔,新旧《唐书》无传,《全唐文》辑前代文献附一小传,曰:“士谔,泰山人。贞元元年进士,元和初官监察御史,擢户部郎中,出为资州刺史”[14](2741)。该记载过于简单,经历也语焉不详,代写人难以考究。“臣以菲才,亲奉昌运,受藩隅之重任,效犬马之微诚,惟君知臣,特受恩奖”,据此可以判断,代写之人的身份是地方官,而且是任命不久的地方官。该官员自受命以来,“宣陛下雨露之惠,令获小康;守朝廷刑赏之规,敢思中立。条赋敛以办集,除疾苦而均安”,职在清身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民、恤狱讼、均赋役,取得了物质生产丰厚,百姓安阜的局面。这种巡幸起居表显然是地方官述职问起居的一种形态,更多的是展现政绩,以赢得皇帝的欢心。
三、巡幸起居制度的变迁
关于唐代巡幸问起居制度,《唐六典》《唐会要》《大唐开元礼》《新唐书》等史籍均有记载,且差异较大,这反映了巡幸起居制度的变迁。
《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载:
凡车驾巡幸及还京,百官辞迎皆于城门外,留守宫内者在殿门外,行从官每日起居,两京文武职事五品以上,三日一奉表起居,三百里内刺史朝见。东都留司文武官每月于尚书省拜表,及留守官共遣使起居,皆以月朔日,使奉表以见,中书舍人一人受表以进。北都留守每季一起居。[5](114)
《唐会要》卷二十六《笺表例》载:
(开元)十一年七月五日敕:三都留守,两京每月一起居,北都每季一起居,并遣使。即行幸未至所幸处,其三都留守及京官五品以上,三日一起居。若暂出行幸,发处留守亦准此并递表。[6](589)
《大唐开元礼》卷三《杂制》载:
凡车驾巡幸,每月朔,两京文武官职事五品以上,表参起居。州界去行所在三百里内者,刺史遣使起居。若车驾从比州及州境过,刺史朝见,巡幸还去京三百里内刺史,遣使起居。[15](32~33)
《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一》载:
皇帝巡幸,两京文武官职事五品以上,月朔以表参起居;近州刺史,遣使一参;留守,月遣使起居;北都,则四时遣使起居。[11](1194)
《唐六典》卷四的记载基本是开元七年(719年)的唐令[16](403),为方便文中叙述,以开元七年唐令为代称。《唐会要》所载是开元十一年(723年)唐令,以开元十一年唐令为代称。《大唐开元礼》成书于开元二十年(732年),可看作开元二十年及以前形成的唐令,则以开元二十年唐令为代称。《新唐书》成书于宋代,是宋人在唐代遗存资料的基础上精心加工而成,是对唐代巡幸制度的总结。考校诸书,巡幸起居制度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确了行从官的问起居制度。开元七年唐令规定行从官问起居的时间是每日一起居。开元十一年唐令、开元二十年唐令均没有行从官问起居的制度性记载,大致是沿袭了开元七年的唐令。前引刘瑕《驾幸温汤赋》“开元改为天宝年,十月后兮腊月前”,说明唐玄宗巡幸温汤的时间是天宝元年(742年)十月到十二月期间,《旧唐书》将时间明确为天宝元年十月丁酉至十一月己巳之间[8](216)。“百官叩头而起居,四夷搕额再拜”,说明行从官起居制度在天宝元年仍得到了很好的坚持。这种制度坚持到何时,难以确定,宋人修《新唐书》时并未将其列入其中。
二是地方州刺史问起居制度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所经三百里内刺史朝见起居制度的断层。开元七年唐令规定所经三百里内,以刺史朝见的形式问起居,这一制度坚持到何时难以判定,但这一起居形式更多的是对古礼的遵循和发展。《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载:“先天二年,玄宗讲武于新丰。‘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诣行在。’时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猎渭滨,即召见,帝曰:公知猎乎?对曰:少所习也。”[11](4383)引文“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诣行在”的故事,难以判断源于何时,但可以证明,玄宗正是援引此故事,才将身为同州刺史的姚崇召至行在的。这说明早在先天二年(712年),开元七年的唐令已经在执行。开元二十年唐令则规定皇帝巡幸三百里内刺史遣使起居,所过州境刺史朝见。朝见起居得到了保留,但限于所过州境的刺史。开元二十年唐令虽然打破了“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诣行在”古礼的要求,但是保留了“所过州境刺史朝见”的制度,也符合“天子巡狩,诸侯待于境”的古礼要求。另一方面,地方刺史遣使起居制度的发展。开元二十年唐令规定的皇帝巡幸三百里内刺史遣使起居,这种制度得到了很好的坚持。兴元元年(784年)二月,唐德宗移幸梁州。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派行军司马樊泽“奉表起居”。乾宁三年(896年)七月,李茂贞大兵压境,昭宗欲往太原李克用处避难。车驾行至渭北,华州节度使韩建遣使奉表起居,请暂跸华州。可见,直到唐末,皇帝巡幸,地方长官奉表起居的制度仍在执行,故宋人将其总结为“近州刺史,遣使一参”[11](1194)。
三是留守官问起居制度的完善。开元七年唐令、开元十一年唐令均记载东都留守每月一起居,起居形式是遣使奉表起居。开元七年唐令记载较为详细,如问起居者不仅限于东都留守,还包括东都分司官,起居表在每月初一由中书舍人转呈给皇帝等。至此,东都留守巡幸起居制度得以完善。北都留守每季一起居在开元七年唐令、开元十一年唐令中均有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条》“北都留守每季一起居”,不存于开元七年令[16](403),是开元十一年以后的唐令。因为开元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唐政府改太原尹为留守[6](1401),真正意义上的三都留守才算出现。开元十一年唐令记载北都留守遣使起居,使得北都留守巡幸起居制度得以完善。京师留守每月初一起居则见于开元十一年唐令。因此,宋人在总结时,概括为“留守,月遣使起居;北都,则四时遣使起居”[11](1194)。
四是两京文武职事官五品以上问起居形式的变革。开元七年唐令为每三日一起居,开元二十年唐令规定五品以上每月朔上表参起居,《新唐书》并没有沿袭开元七年唐令的记载,完全承继了开元二十年唐令的记载。可视为两京文武官职事五品以上问起居形式的变革。
综上,巡幸起居制度是建立在礼制基础上的典章制度,具有明确高下尊卑的等级特点。巡幸起居中,皇太子、公主、宗室皇亲、在京官员等都要定期向皇帝问起居,起居内容集中在对皇帝的探视和问候,起居形式有叩头起居、遣使起居、通名起居等,这些都是君尊臣卑的反映。除此之外,巡幸起居制度还具有政务运行的特点,前引羊士谔《代人行在起居表》,问起居者向皇帝述职,介绍自己的工作成绩,以引起皇帝的注意,是政务特色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