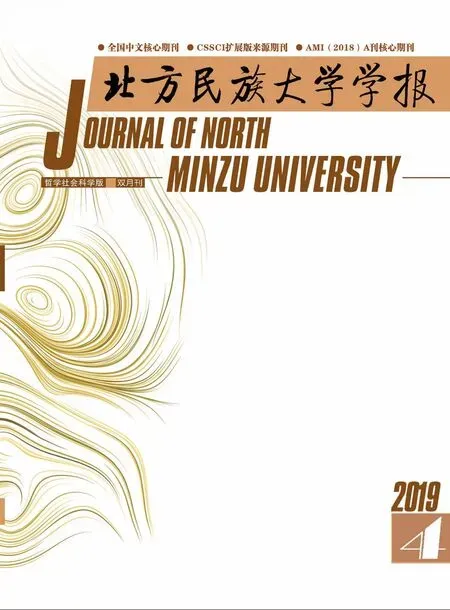乡村女性的人生困局
——论马金莲小说中的女性生存状态
2019-12-05海晓红
海晓红
(北方民族大学 学报编辑部,宁夏 银川 750021)
“历史上的中国,女性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和基本品格,处于历史边缘而沉沦于历史地表。1949年‘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新思想让大多数中国妇女走出了家庭,却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作为女人的‘女性’,一步步演化为‘男人’,强调‘男女都一样’,颠覆了性别歧视,让女性与男性拥有了同等地位,但同时也否定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群体的存在。”[1]1978年以来,这一趋势逐渐发生变化,城市女性开始探索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和发展路径,而对于乡村女性,这条路还很漫长。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偏僻地区,女性仍旧被束缚于家庭,在旧式的轨道上中规中矩地扮演着家庭妇女的角色。宁夏女作家马金莲的文学创作较好地描摹了西部乡村女性的生存状态。作为一位长期生活于西北农村地区的作家,马金莲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系列关于乡村女性的故事,阅读其文字,可以深切地感触到作者温情的目光、隐忍的态度中观照的乡村女性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本文从村落遭际和城市想象等维度切入研究对象,从社会学角度阐释马金莲小说创作中乡村女性的生存状态,以期为新时代背景下乡土文学批评提供一些启示,为乡村女性的发展提供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学界对于马金莲创作的研究大多围绕乡土、底层、死亡、信仰、“80后”等关键词展开,这些成果又多围绕两条学术理路展开:一是结合作家生平经历,围绕创作主题、美学特征、地域文化、族群文化等展开论述;二是以其他“80后”作家或相同题材创作者为参照,讨论马金莲创作的独特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个。
一是从地域文化角度考察作家乡村经验、精神信仰、底层立场和文化观念的养成。难能可贵的是,学者们在分析马金莲小说创作特点的基础上,也指出了其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即具有怀旧色彩的乡土书写与严峻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无法磨合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其创作囿于诗意家园的消失和消失的不可抗拒性之间的惶惑、无奈中[2]。
二是将马金莲的小说创作放置在新时期以来的底层文学视域中进行考察,认为马金莲创作的底层性具有异质性的一面。有学者就指出,主流的底层文学将写作重心放置于挖掘底层的现实苦痛,借助物质生活的困窘为底层伸张正义,与此不同的是,马金莲以抒情笔调诗意地描摹底层生活,与物质生活的贫穷相比,艰难岁月里的那份诗意才是其作品彰显的核心[3]。
三是将其与其他“80后”作家加以对比,认为与大多数“80后”作家将创作重心落在商业文化的漩涡里不同,马金莲的创作扎根于土地,从日常生活伦理出发,彰显了具有普世价值的人间光辉,用温情的笔触书写了一个善良淳朴的乡土世界[4]。
四是以欲望化写作为参照,认为马金莲的创作是“根源于爱的乡土童谣”。她以独特的生命意识,用平实的语言书写了宁夏西海固山区人们的家长里短、农事更替、婚丧嫁娶,在琐碎的文字中隐含着自己的情感积淀、生命体验,彰显出对于生命的悲悯情怀[5][6]。
总体来说,关于马金莲创作的研究成果讨论最多的是其主题中的苦难意识,从女性角度切入其创作的成果也有一些,但大多数属于轻描淡写类,目前,尚未见到全面探究其作品中女性生存状态的相关研究成果。另外,纵观马金莲的作品,女性在其中占有很大篇幅,且是其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形象之一,女性角色已经成为其小说构思的支撑所在,而乡村女性的遭遇、困惑、品质客观上彰显了传统文化背景下普通乡村女性的生存状态,对这类女性形象的全面考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对乡村女性生存状态的探究不仅是对作家创作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乡村女性深入了解、进而使其成为反观现代乡村女性生存现状的一面镜子。另一方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群体的发展进步对于推动家庭、乡村乃至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从文学意义上看,马金莲笔下的女性勤劳却隐忍、顽强却安于当下、心怀忧虑却不挑战陋习、期待爱情却停滞不前、向往自由却选择留守,这一群体矛盾性格的文学呈现客观上表现出这样一种精神风景,即对于家以及家的承载地——乡村由深情而至绝望或希冀有所改观的心理轨迹,她们的遭际及现实生存状况从侧面表征着我国西部乡村几代女性勤劳保守的生存状态。
二、乡村女性的村落遭际
“村落既是一个空间单元,又是一个社会单元。”[7](3)在村落中,乡村女性经历着栖居、立足、安身和立命的不同人生阶段,“妇女做女儿时,依托父亲而获得在父姓家族、村落‘栖居’的资格,获得归属和生命的体验;出嫁之后,依托丈夫在夫姓村落‘立足’,从而获得夫姓家族、村落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并依托丈夫体验自身的存在意义;亡夫之后,儿子便是妇女的依靠,是妇女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来源,并且所有的农村妇女只有完成传宗接代、依托儿子才能在夫姓家族、村落‘安身’,以之为最终归属;等到妇女年老,儿孙绕膝,完成了毕生任务,也就实现了人生的‘立命’,并在儿孙为她准备的体面的葬礼上完成最后的归属。”[8](30)因此,客观上,乡村女性的生命轨迹是清晰的,她们按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理念过日子,这是一条看似清晰的人生道路。但是,从另一角度看,主体性之于她们,是一个模糊甚或不存在的概念;人生之于她们,意味着长大、结婚、生育、离世,她们是一个为了活着而不懈劳作的群体。《长河》中的“我”对人生的想象仅止于村庄女子的生命轨迹:像每个村庄里的女子一样,长大、成熟、变老,“等这副身躯老成了一把干柴才会离开世界。这是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要走的路,除非半途遭遇不测,才能将这一常规打乱”[9](19)。所谓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一件遥远的事情。由此,我们看到马金莲笔下不同年龄段的乡村女性都在随父栖居、随夫立足,终而在乡村安身、立命的轨道上经年不变。
首先,乡村女性在随夫栖居中安身度命。在《长河》中,伴随着四季流转的是个体生命的无常,这其中,女性的命运常常与男人相关,比如伊哈媳妇,她嫁给伊哈时,是一个“脸色粗红”的女人,随着伊哈“口唤”,伊哈媳妇改嫁了。令村民们深感意外的是,她居然改嫁到了川道里一户家境还不错的人家,于是,村庄里的女人开始感叹伊哈媳妇有福气,苦尽甘来,然而当伊哈媳妇再次出现在村庄里时,只带给孩子几个馒头就匆匆离去了,“之后女人们议论说看她那笨笨的吃力样儿,八成有身子了”[9](10~11)。这里,女人的存在映衬着一个男人之于家庭的重要性,而她的离去,客观上表征着川道里另一个男人的存在,以及她为其传宗接代的事实。小说中,没有正面出现的男人是一个真正的存在,而正面出现的乡村女人却是为了烘托男人的权威,以及女人所扮演的劳作、生育的角色。在《绣鸳鸯》中,爷爷的骂声不绝于耳,每当天气干冷、刮西北风时,他就喜欢骂人,“骂奶奶是个邋遢婆娘,炕席上落有灰土!骂我父亲火烧得不旺;骂牲口圈里那头黑驴肚子不争气,老是下驴驹子,连一个骡子驹儿也不下,配种时明明用的是儿马嘛,还花了钱呢;骂小叔叔放羊不经心,满山洼赶着羊群胡逛呢,游荡一天羊的肚子不还瘪瘪的吗?骂这鬼天气,好好儿的刮啥风,害得他的老沙眼又犯了……”[10](3)这里,爷爷是家庭威严的表征,无论他怎样“骂”,奶奶都选择无声地顺从,奶奶和其他人的隐忍无度,使得爷爷更加任性。这里,男人的权威无限扩张,而女性在逼仄的空间里隐忍度日。
其次,在家庭及村落的无形压力中默泣。关于这一点,集中地表现在马金莲一系列以死亡为主题的小说中。在马金莲看来,活着或者死亡,都只是无尽生命长河中的一瞬。于是,生命无常便是乡村女性经常需要修炼的人生功课。面对亲人的离世,乡村女性通常的做法是,在葬礼上失声痛哭,而在日常生活中,她们选择默泣。在《长河》中,面对唯一的儿子的离世,“马云会的女人哭晕了”[9](17)。在《赛麦的院子》中,男婴的降生和离世是赛麦母亲命运的福音,也是她的最大苦痛。男婴的降生和离世在改变家庭氛围的同时,也改变了赛麦母亲的命运,他的离开之时即是母亲的大悲之际,从此,“母亲的哭声像夜半游荡的孤魂,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然响起”,面对来自家庭和村落的无形压力,“母亲极力想撕破这张要命的令人窒息的巨网”[9](65~66)。葬礼上的痛哭及其他失态行为都是在世者,尤其是母亲大痛大悲的表现,而日常生活里对于痛苦的消解方式则是暗夜里一个人的默泣。无疑,痛苦的双重表达方式客观上呈现了乡村女性身心俱疲的现实处境,而“令人窒息的网”不只是男婴离世的悲痛,更包含着曾经经受的压力以及接下来还必须面对的各种困境。
再次,在传宗接代的“自然使命”中负重前行。在农村,血缘的传递是通过男性后裔完成的,生儿子意味着祖宗牌位前的香火永不间断,香火不断就意味着这一宗族能够传宗接代[11](65),女性并不在血脉传递的序列中,因而,在家里的位置并不明确[8](47)。因此,当赛麦母亲生下一个又一个女孩时,赛麦爷爷的神情是萎靡的,显出“受了挫折的样子”,对于别人眼里“懂事”“惹人疼爱”的赛麦姊妹们,爷爷表现出冷淡、不屑的态度,在“不过是几个毛头女子”的话语中,有着明显的蔑视轻贱。如果爷爷的冷淡是出于接续香火层面的考虑,那么,赛麦父亲的表现则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面对“生不出儿子”的境况,他选择“拍拍屁股”出走。在赛麦的世界里,父亲是一个好吃懒做、不顾家小、一无是处的男人,但就是这样一个男人,母亲义无反顾且毫无悔意地跟随着。在《马兰花开》中,马兰的父亲也是类似的男性形象,赌博成性、恶习满身、毫无责任感等是其典型特征。由此,我们看到,马金莲笔下的乡村婚姻生活中,女性极少表达自己的主观意愿,男性承担的责任是模糊的,而其权力似乎是无处不在的。
最后,在婆婆及其他女性的围观中隐忍度日。在传统家庭中,婆婆是一个特殊的人群,“是在男人的权力下讨生活,逐步取得了局部的权力和地位,然后摆出一副‘统治者’的姿态,帮助男人实现女人的统治,她们是男性的同谋和共犯”[12]。在《马兰花开》中,婆婆对于马兰和嫂子是一种无形胜有形的力量,她所在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对儿媳妇的掌控,而儿媳妇们则在她的掌控下生儿育女、伺候老人,稍有不妥,婆婆便会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教训”。如果说婆婆常态化的教训已经使儿媳妇们产生了心理疲劳,那么,家庭之外熟人社会里女性同伴的围观则在无形中给予乡村女性致命的“嘲笑”。面对赛麦母亲又生一女儿的现实,本家二奶奶显得分外兴奋,在赛麦家出出进进无数次,喜形于色,她的儿媳妇们生的都是儿子,于是,她似乎有了“笑话”别人的理由,在她看来,应该一一休了她们,“世上女人多的是”。由于没有生育男孩,赛麦的母亲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夜里,她翻来覆去,感叹命运悲苦[9](48)。而在周围人眼中,赛麦的母亲就是一个“笑话”,理由则是她生出了七个女儿,也没有生出儿子[9](48~49)。由此,生男生女不只是传宗接代层面的事情,也关乎家庭的面子,不光女人脸上“不好看”,“觉得矮人一截”,其公公婆婆也会觉得“低人一等”[9](49~50)。于是,乡村女性理所当然地成了被议论的对象。对于乡村女性而言,她们一边自责,一边充满了无力感;而对于长辈,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生男孩的渴求以及由于未能生男孩的某种苛责和无法言说的纠结。
三、乡村女性的城市想象
成长于农村的马金莲对乡野生活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她的大多数作品取材于一个名为扇子湾的地方,留守农村、心向城市是其笔下大多数乡村女性的生存状态。比之于孙慧芬笔下乡村女性强烈的“出走”愿望,马金莲笔下的乡村女性更加保守,城市之于她们,仅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城市在别处,它始终与想象同行。也正因为此,以城市想象为参照,乡土文化对于女性的深层影响和城乡二元结构中乡村女性的困惑、矛盾在马金莲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突出表现。
首先,在马金莲的小说中,城市想象意味着小家庭的团圆。它不同于大多数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城市想象,即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种完全不同于乡村的生活方式、一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尤其是在广大乡村女性的想象中,进城意味着命运的转折和崭新生活方式”[13]。在马金莲笔下,城市表征着一种家庭生活方式,即一家团圆的幸福日子。“向城而生”的女人大多是已婚女性,她们之所以“向城而生”,主要是因为那里有她们的丈夫,这种特殊的牵挂和依赖成为她们想象城市的重要基点。在乡村女性心目中,比之于穷困的现实生活,分居两地更加难以忍受。一方面,分居意味着“守活寡”。《大拇指和小拇尕》《马兰花开》《鲜花与蛇》等作品都在传递一个信息:那些留守乡土的女性在日复一日的劳作后经历着巨大的寂寞和孤苦,农闲时节或农忙休息时段,她们的心里满载着对丈夫的思念。另一方面,分居意味着缺乏妥靠贴心的男性平衡婆媳、妯娌关系。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婆媳、妯娌关系对乡村女性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她们是乡村女性日常生活是否愉悦的关键影响因素。在马金莲笔下,婆婆表征着规矩,她掌握着支配儿媳妇的权力。因此,马兰们一面按照婆婆的要求、暗示或示范行事,一面在心底暗暗做着自己的打算。妯娌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乡村女性在大家庭中的地位,而地位的高低不仅受其原生家庭财富、丈夫地位高低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是其自身能力的显示。但也有例外,比如《马兰花开》中,马兰的娘家并不富裕,父亲是个赌徒,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过着穷苦日子,马兰对家务一窍不通,但是她有文化,且个性温顺,因此,颇得婆婆喜欢,也是其嫂子心事的倾听者,由此,她得以在婆家安稳度日,但是日子久了,也会有一些的矛盾浮出水面,这时,丈夫就会成为抚平她心理褶皱的“熨斗”,但是丈夫隔三岔五外出打工,马兰不得不为此不时地调整自己的姿态,以适应婆媳及妯娌关系的变化。
其次,金钱是城市想象的重要构成之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金钱成为影响乡村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关键因素。《大拇指和小拇尕》讲述了一个疼痛的故事:哈蛋一年中的多数时间都在外打工,家里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哈蛋媳妇的身上。虽然男人每月都会寄钱回来,但是终究只能满足日常花销而已。面对日益增多的挣钱机会,哈蛋媳妇终于耐不住寂寞,想出去挣钱,可是孩子无人照看,她先后带着孩子外出干活儿、将孩子锁在家里或放在窖里,然而不幸降临了,孩子在经历了暴晒、电击等灾难之后,最终,蛇钻进了孩子的嘴里,悲剧发生了,悲剧留给人们的不只是孩子离世的苦痛,更有新时代农村女性无力也无法迈出家庭的现实矛盾,以及金钱给人带来的伤痛。《富汉》讲述了王牛子家靠挖煤发家的故事,在该作品中,所谓“富汉”,如同王牛子手里的气球,膨胀起来,无人能及,憋下去时,仅看到王牛子哇哇大哭的嘴巴。如同学者所指出的,乡村文化的脆弱之处在于,“一条项链、一方头巾,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却奏响了乡村文明崩溃的序曲,冷却了传统价值伦理的脉脉温情”[14],金钱之于乡村文明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城市之于乡村女性,仅止于守望,她们始终未能走出长久生活的安全区——乡村。诚然,“在中国当代发展的情景下,农村成为她们想要挣脱和逃离的生死场,而不是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空间’”[15],然而,马金莲笔下的乡村女性始终留守在乡村,这与其说是保守、胆怯,不如说是对自身责任的认知使然。在《鲜花与蛇》中,怀孕的阿舍期盼着外出打工的丈夫尔萨的归来,当每日的期待变成一个又一个豪言壮语之后的“匆匆离去”时,阿舍只能以乡民不屑的某些年轻媳妇的抉择安慰自己。作者描述道,也有一些“不安分”的年轻媳妇不愿意留守,希望跟随丈夫外出打工,这样不仅能够专心“拉扯娃娃”,“给男人做饭”,也能挣到一份工资,“好歹一家人是团圆的”[9](193)。而事实上,阿舍之所以安于现状,不是她不想走出乡村,而是她对自身所处位置进行判断后做出的选择。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提出了学理性的解释:“女人心中的宿命观念、男权意识、依附品质使女人放弃了自己把握命运的权力,女人把自己当作花瓶、摆设、劳动工具……起着滋润男性的作用。长期的非主体感,使女人愈来愈模糊了自我认识、愈来愈认同罪劣观念、是应该在苦役式生存与依附中赎罪的对象”[16]。因此,在阿舍的心里,照顾公婆、种地、生育等事务是其理所当然的责任。同样,《马兰花开》中的马兰借助于自己不屑的外力(嫂子)试图出走,终而在家庭责任、丈夫的说服、公公婆婆的威慑等多种力量的合谋中“出走失败”。《鲜花与蛇》中的阿舍也是如此,她老老实实地在乡村留守,可是她何尝不想出去呢?作者如是写道:“她的内心是渴望出去的,一来和丈夫早晚守在一起,二来见见外头的大世面”[9](193)。传统文化和文化惯习的共同影响,使乡村女性将心底真实的渴望深藏,她们本能地行使着家庭女性的角色。于是,“出走”被搁置,“希望”流产,留守成为她们余生的常态。在这个意义上,马金莲笔下的乡村就是生活本身,其地域环境、文化生态等共同制约着乡村女性的日常生活。
四、余 论
乡村女性的文化是直面现实的文化,无论面对多大困境,她们选择的初衷始终是最根本、最直接的生存问题,而较少考虑精神层面的因素。因而,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马金莲笔下的乡村女性忙着耕作、忙着生孩子、忙着伺候老小,她们的姓名被隐没或忽略,人们理所当然地称呼她们为“某某的女人”或者“某某媳妇”,她们的生命之重主要表现为乡野日常生活的消磨、朴素平庸日子里的寂寞、生“儿”不能的焦虑,以及乡村文化制约而不自知的烦闷。她们的人生之旅是从父家向夫家位移的过程,她们的行为举止是乡村戒律的传声筒。乡村之于她们,是难以走出的安全区;城市之于他们,则意味着一种全然不同的生存方式。然而,在她们的生命哲学里,“出走”意味着“被说”,固守则意味着贫穷、孤独、无趣,但是她们宁愿在贫穷里挣扎,也不愿或无法走出乡村。究其原因,大多缘于文化水平对其个性和命运的影响、传统乡村伦理观念的束缚、乡村女性的主动依附和被迫依附[17],以及主要活动于社会场域,缺乏自我成长的独立空间,使其对自身发展缺乏规划。
马金莲的文学创作忠实记录了现代化背景下处于乡土一隅的女性生存状态,其创作能够直面乡村女性的生存困境,对这一群体生存状态的书写丰富、丰盈了当代文学的女性形象图谱,而且,其创作提供了一种想象乡土的视角和方式,即以女性视角审视静默无声的乡村,以女性的隐忍彰显乡村发展现状。作为女性作家,马金莲天然具备的细腻、善感、体察入微等能力,使其作品往往显现出较多的柔软、细腻和温润,同时,其细腻敏锐的感知和捕捉能力,为女性在与整个世界的坚硬对抗中提供了坚韧温婉的立足点[18]。但是其在女性生存状态书写中的不足也是较为明显的,比如,女性日常生活的平面化书写,对乡村女性文化心理的种种痼疾等缺乏必要的批判,而往往包含着乌托邦的想象。如同陈晓明所指出的,就当今女性作家仅有的“女性意识”而言,主要是在个人经验范围内的自省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话语的副产品,因而,多少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品难免生活面狭窄,无力与现实对话[19](90)。这是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马金莲的作品也同样存在。我们相信,以马金莲的文学天赋和勤奋,一定会在未来的创作中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