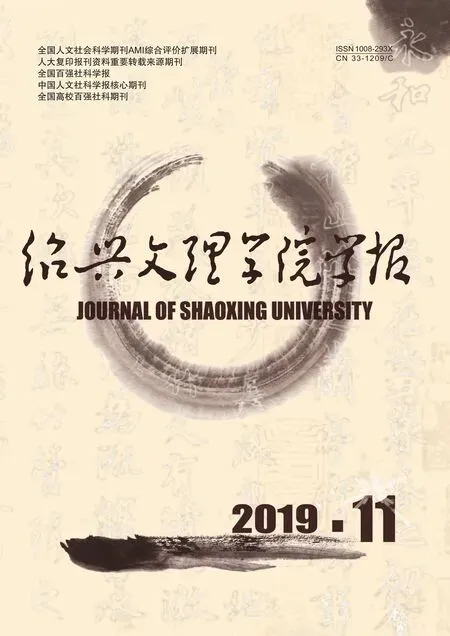传承与发展
——从《水之嬉戏》看印象主义钢琴演奏技法
2019-12-04李柯
李 柯
(武汉音乐学院 钢琴系,湖北 武汉 430060)
钢琴演奏技法是随着钢琴这件乐器的不断演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钢琴作品的内容要求而进化和发展的,钢琴300年既是一部乐器史,同时也是一部演奏史。从文艺复兴时期键盘乐器技法的萌生,至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的未臻完善,再到浪漫主义时期的日趋成熟,钢琴演奏技法已经由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孩成长为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而在印象主义音乐中,各种新鲜、极富效果的演奏技巧更是层出不穷,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由此,本文拟以拉威尔的《水之嬉戏》为例,用肖邦的两套共二十四首钢琴练习曲作为参照,从本源上将两者的技巧特点加以对比,以求揭示印象风格的钢琴作品中演奏技巧之丰富,并阐明完美达成这些技巧的要点。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主要就纯技术性技巧(即以手部技巧为主的手指、手腕、手臂技术)进行探讨,而把触键法、踏板法等更加广义的演奏技法另作专文论述。正如法国钢琴之母玛格丽特·隆(Marguerite Long,1874—1966)所说:“5个手指的机械训练对我来说是一把打开一切技巧之门的钥匙”;也如一代宗师、伟大的奥地利钢琴家、作曲家、钢琴教育家卡尔·车尔尼(Carl Czerny,1791—1857)所指出的:“一个人越能掌控整个键盘,就越能轻易地洞察任何音乐作品并从中获益。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对演奏者来说,没有什么是比训练有素的灵活、轻盈、流畅的手指更为必需和重要的素质了[1]”——手指技巧确实可称得上“是钢琴演奏中最重要的领域[2]”!
一、纵论
众所周知,拉威尔的这首《水之嬉戏》是印象派作曲家所写的一系列描写“水”的作品中的第一首。1901年,当拉威尔在他和他的好友们组织的“叛逆集团”的聚会上向伙伴们首次介绍《水之嬉戏》这首杰作时,伐尔格(Faque)——叛逆集团成员之一,这样写道:“这是陌生的一种火热的感情,波浪的汹涌和细腻表情的结合,从来还没有人能达到这个境界。”事实上,这一作品的出现,把钢琴这个乐器的表演技术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拉威尔给真正的技巧家提出很复杂的任务:他要求他们不用一般吸引听众的办法而敢于使用以前禁止的音区,试图揭示钢琴恶魔般强大的力量[3]。
(一)借鉴与继承
乐曲一开始就显示出了精致的技巧:手指既要伸张又要保持稳定,右手要极为平均、流畅,各手指的音色和力度要均匀,且要在极弱的连贯中保有一定的通透性。见例1。
它同肖邦的作品第十号练习曲的第一条(以下均为简称)有着完全相同的技术课题,所不同的是10之1要求触键结实而有气魄,这里却要求柔和而轻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较弱的力度层次上对于力度与速度的控制往往比在较强力度层次中更难,因此对于演奏者来说它无疑更具有挑战性。
肖邦的黑键练习曲(10之5)素来以其“珠落玉盘”般的独特效果,演奏者在黑键上如闲庭信步、挥洒自如的高难度演奏技巧而闻名于世。他的作品10之7则专注于双音同时下键的精准性、手指伸张动作的迅速与放松以及大跨度伸张技术的发展。而在《水之嬉戏》中,拉威尔恰到好处地融合了以上几种技巧。见例2。


这里应注意右手手指不要抬得过高,而是贴近键盘,手指手掌应该尽量撑开。手腕完全放松,让手自由迅速地移动,以便弹奏相距较远的双音时击键准确稳定,同时还要兼顾音乐的轻巧与优雅。
印象风格的钢琴音乐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大量出现大跨度的和弦及琶音。这主要是由于作曲家们为了将传统的和弦功能减弱到最低限度,注重使用了各种不同结构的七和弦、九和弦或更大跨度的和弦;广泛运用了各种色彩性和弦,如在七和弦上附加其它的音,并籍以这些音域宽广的和弦来表现广袤而宽旷的空间,体现自己悠远而精致的乐思。见例3。
这个急速进行的跨度达12度的分解和弦音型有着与肖邦10之11同样的技术课题——手指伸张技术的发展。在肖邦的练习曲中,它的表现形式为轻快、自如的琶音,在这里则是迂回进行的分解和弦。因此,它对于手指大跨度强有力的急速触键以及手腕在做快速、连续的回转动作时的放松与自如的要求是更高了。
在肖邦的作品中,10之2是一首以右手3、4、5指弹奏半音阶而闻名的技巧艰深的练习曲。然而,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困难症结在于,如何把手的肌肉活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起主导作用,另一部分仅仅是伴随的。对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技术课题,《水之嬉戏》中也有类似的体现,甚至表现得更为复杂。见例4。


这里,右手出现了连续的快速二度双音琶音,它将手的肌肉活动分为了三个部分(25之3的结尾处亦有类似技法),且都处在极弱力度层次上的敏锐的控制之中。通过对生理解剖学的了解,我们得知我们的手的2、3、4、5指是以所谓“肌腱”相连接的,其中任何一指的动作都必然会牵扯其它各指,而此处肌肉活动的划分恰恰违背了手的自然生理机制,三个部分分别由1、2和3,以及4和5指分组独立进行敏捷而平稳的运作,同时还要兼顾跨越于右手之上的左手八度旋律的完美音色,其难度可想而知。特别是到了乐曲的尾声处,织体由先前的十六分音符变为三十二分音符、音域跨度由一个八度扩展到两个八度,技术上的要求就更高了。
八度和弦技术是一种从古典主义中后期开始逐渐得到重视的钢琴演奏技巧,到了浪漫派,特别是晚期浪漫主义时期,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舒曼的作品第7号《C大调托卡塔》,肖邦的作品53号《“英雄”波兰舞曲》,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六首、《诗与宗教的和谐》第七首《葬礼》、超技练习曲《英雄》《旅游岁月》(第一集)《瑞士游记》之5《暴风雨》以及他的歌剧改编曲《费加罗的婚礼》等一系列作品中,均有八度和弦技术的辉煌表现。而在印象风格的钢琴音乐中,虽然也不乏八度和弦这种技巧,但却绝少出现长时间、高强度的段落,这大概是由于印象主义作曲家们对于音响色彩的别样追求以及与浪漫主义相比审美情趣的截然不同所造成的吧。见例5。
这里出现了与肖邦的25之10完全相同的技术课题。演奏者应专心于八度和弦的连奏,在随波逐流般的韵律中控制好手腕的动作,务求手指在和弦间衔接的连贯性及旋律声部的明确。此外,尽管是极弱的力度,八度和弦的三个音仍需绝对整齐地弹下去,要小心控制,稍有疏忽便会破坏音乐的淳美意境。

接下来的技术课题是有关震音的演奏。通常,我们所见到的震音奏法都是以虎口,即拇指与食指之间为分界,用拇指(以右手为例)弹奏震音的下方音、用二至五指负责其它各音,这当然就很符合我们手的生理构造。而在这里,拉威尔要求我们向自身的局限挑战,用1、2指演奏双重震音的下方双音,用3、5指演奏双重震音的上方双音。见例6
例6:

这样,它就产生了类似于肖邦练习曲10之2的特殊课题,如何把手的肌肉活动划分为两个部分,使之不致相互牵连,进而达到急速的独立运行便成为了演奏者所要克服的首要困难。
在肖邦的练习曲10之8中,我们会遇到钢琴演奏技术中的一个主要课题,即拇指的下转动作。而在下面的例子里,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与之看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的演奏技巧——小指的上转动作。见例7。
这是一个快速上行的经过性乐句,它的织体主要为和弦与音程的交替级进,而不是单纯的单音线性进行。其中,小指在黑键和白键上连续作了六次上转动作——这一点,又与肖邦的10之2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应力求小指上转动作的轻巧柔顺,避免乐句旋律线条的断裂,确保和弦或音程中各音的平稳触键,亦不应人为地减慢速度。当然,这一切的完美达成与手腕的积极配合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有人想从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音乐中探寻到一丝印象风格的气息的话,那么,我推荐他去听听“牧羊人的笛子”(肖邦练习曲25之1)。舒曼曾对此曲作过如下评论:“艺术家(指肖邦)的妙手轻巧地拨弄琴弦,绘编出一幅多采的音响图案,……降A大调练习曲(25之1),与其称它为练习曲,毋宁称它为诗[4]。”现在,当我们把它与《水之嬉戏》中一个梦幻般存在的片断加以比较时,你就会发现它们无论是从音乐的意境、还是演奏的技巧上都是那么惊人地相似!见例8。

旋律的极富歌唱性、小指所单独承受的繁难任务(下键沉稳而含蓄、音色清新而悠扬)、相距甚远而又异常迅速地分解和弦以及音乐所要求的诗意朦胧的气氛,这一切,都无不显示出完美的技术对于完美的音乐形象的表现是多么至关重要。

本章节所要讨论的最后一个纯技术性课题是琶音的演奏。关于这种演奏技巧,在肖邦的练习曲25之12中有充分的表现。在那首作品中,如波涛潮水般汹涌的强力琶音是音乐的主要织体,它的显而易见的困难是准确地弹奏琶音并突出其中作为骨架的有力的旋律线条;而另一个较隐蔽的困难则是要避免由于弹奏琶音所用的指法(如作品开头处右手用1、2、5、1指弹奏四个音一组的上行琶音)需要手的不断转位而产生的不恰当的重音,这一要求就与下面的例子颇为相似了。见例9。
在这个片断中,右手琶音的结构对演奏技巧的难度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它要求右手的2、3、4、5指分别弹奏大小七和弦中的#C、E、#G、B这四个音。这就要求演奏者有良好的手指间距,手腕要更加灵活并与手指动作相协调。由于这段琶音是在较弱力度层次上的快速流动,因此,演奏者必须十分注意力量的控制,保证手指弹奏力度与速度的绝对均匀。只有这样,才能完满地营造出拉威尔所期望的效果——让左手如歌的旋律在右手温暖湿润的晨雾中轻轻飘散。

(二)创新与拓展
以下四种演奏技巧是肖邦的两套练习曲所没有涉及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拉威尔在对音乐表现技法的选择上不但勇于创新,也是完全遵循了其艺术审美情趣并以音乐形象的表现为前提的。
这里包含了两种演奏技法。第一种是双手协同交替弹奏强力的长时间和弦震音。它要求演奏者的大臂极为放松和稳定,小臂与手腕要配合默契,手指、手掌保持稳固的击键姿态,由小臂的上下挥动带动手腕来完成演奏。这时,如何解决好大臂的松弛与小臂及手、腕部的相对紧张之间的矛盾,如何正确地贯通和传送力量,以及怎样才能协调好双手在高速进行中的密集配合,便成为演奏者所要认真思考进而去解决的问题了。见例10。

紧接震音之后的,是一种被认为在印象主义风格的钢琴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技巧——滑奏。我们知道,在李斯特之前,钢琴作品里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过滑奏这一技巧(贝多芬的“华德斯坦”是一个例外),是李斯特创造性地把它运用于《匈牙利狂想曲》第十五首《拉科齐进行曲》以及《第一梅菲斯托圆舞曲》等一系列作品之中。而在德彪西、拉威尔等印象主义大师的手里,这一技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各种滑奏形式不断产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钢琴演奏技法的宝库。这里,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如:左手白键的单音上行滑奏《水妖》、右手白键的单音上行滑奏《烟火》、左手黑键的单音上行滑奏《水妖》、右手黑键的单音上行滑奏《烟火》、左手白键的单音下行滑奏《烟火》、右手黑键的单音下行滑奏《水之嬉戏》、右手白键的三、四度上行及下行滑奏《小丑的晨歌》、左右手密集接应的黑键上行滑奏《水妖》,以及双手黑白键结合的滑奏《大圆舞曲》(La Valse双钢版)等等。
关于滑奏的练习,玛格丽特·隆指出:它(指滑奏)很困难、很危险,并可能使手指遭到损伤。拉威尔本人也认为,如果弹不好双滑音,宁可用单滑音,重要的是要给人迅速滑行、一闪而过的印象。然而,完美滑奏的音响效果具有如此诱人的魅力,正如人们屡次所提到,德彪西在其《雨中花园》里正是受到《水之嬉戏》中这个闪闪发光的经过句的启发,我们当然更应该努力去掌握它了。
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在钢琴音乐的创作上,拉威尔较多地发展了李斯特的传统,而德彪西却明显地体现出肖邦的气质。从下面这个例子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支持这一说法的依据。见例11。

这是一组下行的、左右手自低向高密集接应弹奏分解和弦的快速经过句,它属于炫技性演奏技法,在李斯特的歌剧改编曲《弄臣》等诸多作品中均出现过类似的技巧。在《弄臣》中是为了模仿竖琴高音区温暖而朦胧的音色,而在这里,拉威尔意图通过这一技巧表现一种波光粼粼、流水潺潺的声光效果。演奏时不仅要让由三十二分音符组成的七连音均匀、顺畅地从指尖流泄出来,还要留意表现每组分解和弦的最低音——如果将这些音符连接起来,你就会发现一条隐藏的减七旋律线条。而如何利用拉威尔提供的这种和声背景,在轻巧急速的进行中去创造出令人心旷神怡的音响效果,这就是摆在演奏者面前的主要课题了。
在《水之嬉戏》中,还有一种演奏技法被高频率地使用——双手交叠、交错演奏技巧。见例12。
在这个炫技性的、几乎覆盖整个钢琴键盘音域的经过句中,要特别注意双手与身体的协调配合,要在瞬息之间调整好身体与手的姿态,以便能清晰、快速而又均匀准确地奏出那一串串密集的三十二分音符以及左手在黑键上的跨越式大跳和弦。同时,拉威尔还要求我们在几乎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从极弱(ppp)一下子冲到极强(fff),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这样迅急而大幅度的渐强,是需要很好的手臂与全身的调控能力以及强大的手指支撑力才能完美实现的。

此外,这个片断还包含了另外一种技术课题——跳跃技巧。这种技术对于演奏者整个手臂的柔顺、协调、爆发以及精准性都有较高的要求,它在钢琴作品中的应用也比较广泛,表现形式多样化。在肖邦练习曲25之4、25之9,李斯特超技练习曲《狩猎》《梅菲斯托圆舞曲》No.1等很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而这里的特殊困难在于,由于在钢琴的中高音区,左手始终处于极不自然的位置和姿态,以极快的速度、在很难控制的黑键上进行跳跃弹奏;同时,演奏者还要顾及左右手的交错问题以及急速渐强的力度控制问题,真正是展现了钢琴恶魔般强大的力量。
二、结语
通过以上对拉威尔的钢琴作品《水之嬉戏》与肖邦的二十四首钢琴练习曲中存在的纯技术性技巧的对比,我们发现,除了关于多声部即手指不同层次音色的控制(10之3、6;25之7)及节奏上独立性的训练(10之10、25之4)不在本文讨论范畴之内,只有三度、六度双音的演奏技法(25之6、8)没有在《水之嬉戏》中出现。而其它技巧,如左手伸张技术的提高(10之9)、手指均匀、快速、有力的一般性或基础性技术课题的练习(10之4、12、25之11)、八度触键技巧的改善(25之9)等等这些在《水之嬉戏》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拉威尔亦在本曲中展现了更多新奇而耀眼的钢琴演奏技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拉威尔在其印象风格钢琴曲的第一作《水之嬉戏》中,充分继承了古典及浪漫主义钢琴音乐中的演奏技巧,并将自己的艺术风格与审美情趣融入其中,以此产生了更新、更富效果、更具挑战性的钢琴演奏技法,为复兴在李斯特以后毫无作为的独特的钢琴技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3]。
当然,印象主义钢琴音乐中的精妙技巧决不仅只这些。在德彪西的《前奏曲》中[5],我们可以看到快速向下滑行的三度《帆》、八度和弦连续大幅度跳进与剧烈的力度起伏对比的《原野上的风》、连续快速蠕动上行的三度《向皮克威克先生致敬》、双手持续快速的交叉演奏《三度音程的变化》以及《烟火》中李斯特式魔术般技巧的展现;而在拉威尔的《镜子》[6]套曲以及《夜之妖灵》中,则表现出了比《水之嬉戏》更加复杂的钢琴演奏技法,如震音与同音反复相结合的持续快速演奏、左手持续快速极弱的同音反复、同音反复与双音滑奏的密集接应、同音反复与手指大跨度伸张的混合处理、左右手大跨度和弦高强度快速交替进行以及大二度双音的半音阶快速经过句等等。其中,由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技巧性手法,钢琴套曲《夜之妖灵》中的《幻影》被认为是自《水之嬉戏》后钢琴技术发展中新的高级阶段。正如钢琴家基尔·马尔舍克斯(Gil Marchex)所说的,“要弹上一整本练习才能掌握这种新的钢琴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