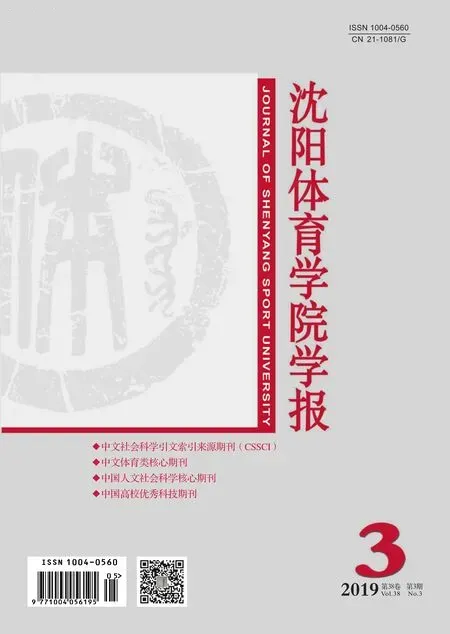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生秩序逻辑及其参与社会治理路径
——基于对桂西的田野调查
2019-11-24王晓晨乔媛媛蒲玉宾崔永胜
王晓晨,乔媛媛,蒲玉宾,崔永胜
(1.玉林师范学院 体育健康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2.沈阳体育学院 武术与舞蹈学院,辽宁 沈阳 110102;3.国家体育总局 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科宣部,北京 100061)
2018年1月19日,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联合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深受各民族群众的喜爱,在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流交融,提升各族人民体质健康水平,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有着挖掘其多元价值,进而服务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必要。换言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携带着强大民族文化基因、蕴含着丰富民族文化故事、有着多重民族记忆和严重族群认同的身体文化,欲在新时代、新思想、新矛盾、新目标的今天、在“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国家意志和政治诉求中焕发蓬勃生机、赢得可持续发展态势,就必须积极地站在国家与民族的高度,成为服务社会的参与者和奉献者。与此同时,学界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进展的归纳中又指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与社会现实问题联系的相对较少,对当代社会存在的价值功能研究相对匮乏。”[2]因此,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有哪些属性可以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做出贡献?其固有的秩序逻辑与价值又有哪些?又有哪些恰切的手段和路径保证其秩序功能得以施展?本研究认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体实例来梳理其文化的内生秩序逻辑,厘清其在未来社会治理中秩序建构的着力点与路径就极具现实意义。
1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无论是检视著名史学家黄现璠主编的《壮族通史》(1988年),还是梳理著名壮学家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1997年,上中下三卷),更抑或是精读壮族研究学者李富强、白耀天的《壮族社会生活史》(2013年,上下卷),都能看出在我国自秦汉大一统以来的国家治理发展进程中,中央对桂西民族地区的治理实践经历了不同的关系模式。首先是朝廷与民族地区治理结构的整体性与多样性并存、天下一统与怀柔羁縻共生,如秦、汉、唐对桂西的羁縻政策与羁縻制度、宋元明对桂西的土司制度以及明清以来的“改土归流”等;其次是近代以来国家主义视域中中央对民族地区管理的内地化,如民国旧桂系与新桂系在广西政坛的更替实现了从“桂人治桂”到“建设广西、复兴中华”的变迁;新中国成立后现代统一国家内的民族区域治理,统一与自治结合、民族与区域兼顾,践行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治理格局。这三种关系模式渗透着数千年来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重要传统和宝贵经验,其中注重差异性前提下的尊重民族地区传统基层自治文化当属首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如何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不容置疑,“强化民族地区社会主体民主参与、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建构、政府服务理念转变以及社会法治体系建立”[3]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进一步聚焦,欲达此目的操作路径上,就需要“充分发挥民族地方文化多样性优势,调动各民族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让各民族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真正成为内源式的现代化,这才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明智选择”[4]。即欲实现合法性与效率完美结合的善治,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依然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一脉,当然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况且面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当代传承与发展的困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有必要在服务于社会中求发展。因此,在双赢的发展契机与语境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寻求突破而有所作为就提上了日程。
2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生秩序的不同维度
英国人类学家费思在其著作《社会组织要素》中指出:“如果认为社会是由一群具有特定生活方式的人组成的,那么文化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并进一步强调“文化就是社会,社会是什么,文化就是什么”[5]。从中不仅看到文化与社会的共生共存关系,也看到了文化之于社会秩序生成的基本理路。正如赫德利·布尔所指出的“秩序是指导致某种特定结果的格局,一种旨在实现特定目标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6],那么文化即社会中人群遵循的精神价值、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在潜移默化中往往发挥着价值导向、道德示范、文化认同、关系调适、社会整合等治理作用。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主要是以身体活动为方式的文化,同样有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内生秩序功能,在社会的发展中影响和建构着相应的社会秩序。
2.1 价值导向的秩序影响
“价值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特定现象,它存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和价值紧密联系,追求价值实现不仅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目的、意义所在,还是人们积极活动的最终动因。”[7]由价值建构的价值观对社会中个体的思想、行为以及主观能动性的调动都起着主导作用。众所周知,不同于军事、法律、政治对社会管理过程中具有的强制性,文化的社会治理就是通过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而从内而外的转化过程。因此,由文化中价值导向所产生的社会秩序无疑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效果影响最为深沉和执拗,只不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价值导向的表达更为直观、鲜明、纯正罢了。桂西“龙舟、舞狮、秋千、跳蚂拐、踩风车、芦笙舞、竹杆舞、背箩筐、独竹漂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它们背后大都隐含着自然力崇拜,体现着敬畏自然、爱护生命的价值追求。”[8]笔者与课题组成员为聚焦具体项目的价值导向,在教育部人文课题基金的资助下,在2018年春节后对被誉为“壮族蚂拐文化第一村”的广西天峨县六排镇纳洞村的蚂拐舞又一次进行了调研,发现蚂拐舞有着祈求雨水、生殖隐喻等主要的价值导向。壮乡作为稻作文明的发源地,其农业的丰歉与气温和雨量息息相关,而在气象科学极不发达的时代,在观物取象与农耕经验的直觉思维中往往根据蛙鸣来判断天气变化。正如人类学家弗雷泽所说:“青蛙和蟾蜍跟水的密切联系使它们获得了雨水保管者的广泛声誉,并经常在要求上天下大雨的巫术中扮演部分角色。”[9]于是在蚂拐崇拜中建构的蚂拐舞首先是为了祈祷风调雨顺,保佑农业的丰收,正是这种价值诉求导向了壮人保护稻田益虫的社会规则。壮族妇女农秀英告诉我们:“我们这的人都非常尊敬和喜欢青蛙,许多地方不准杀青蛙。大人看到小孩乱捉青蛙会制止,还要‘la’(壮语,意为严厉斥责)孩子们。我们在田间劳动,看到青蛙要小心绕行。”至今,东兰、田东、田阳等地仍然禁止捕杀青蛙,个别村落有禁止吃青蛙的习俗。这种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导向,以及对大自然的尊重,在蚂拐舞中的“祭蚂拐”“葬蚂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蚂拐舞还有生殖隐喻的价值导向。“蛙类代表着女性的生殖象征。蛙的大腹,象征着母性怀孕的体态;蛙卵的繁多,更为那些盼望有众多子嗣的人们所倾慕。蝌蚪,一方面和象征着女性生殖器官的贝壳中的软组织相类似,又和男性的精虫有点相近,更容易被古人看作是阴阳交泰的感生物。”[10]整个蚂拐舞表演过程中,由两位女性站在祭台击鼓指挥以及对歌中成对男女通宵达旦唱情歌的环节,都凸显壮族妇女显赫的社会地位以及生殖崇拜中母系氏族社会遗风的展示。蚂拐舞中呈现的生殖崇拜对壮人的生育观有着严重影响,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也对社会治理带来不小的冲击。纳洞村蚂拐舞传承人向宝业告诉我们:“以前壮人一个家庭育有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孩子很正常,由于兄弟们多而去别家上门入赘的大有人在,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观念也在淡化。”同样,侗族抢花炮有着“求福、求子、求财”,壮族抛绣球包含着“求偶、交友、娱乐”,苗族拉鼓有着“追怀祖先、彰显宗族力量”等的价值导向及丰富意涵,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文化价值导向中的内生秩序对社会治理都有着型塑与指引作用,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2.2 道德示范的秩序规训
道德示范隶属示范教育,往往是基于蕴含较大道德价值的人或事的展播,将道德规范和道德愿景人格化、具体化,以摸得着、看得见的生动案例来对人们道德观影响的过程,极具说服力、感染力和教育效果。置身其中的示范客体人群,在深受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的规训下,就会建构一种基于共同认知的道德观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机制下的社会秩序形成的事例,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不胜枚举,其道德示范往往通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参与人员资格的审查来彰显。如课题组在对百色西林的壮族舞春牛调研中发现,舞春牛的参与者一般由德高望重的艺人出面挑选,对象是那些遵规守法、敬重长辈、头脑灵活且能善歌善舞的村民,道德表现不佳者不予考虑;三江县林溪乡侗族抢花炮中的“还炮”仪式中,只有那些被认为社会形象好、生活令人羡慕、为人让人尊重的族人(家庭表现上首先是父母长寿,命运较好;通过诚实劳动致富、遵纪守法,无赌博、酗酒等不良嗜好),才能担当还炮之人。这种重德敬贤的资格衡量过程充斥“见贤思齐见不肖而内醒”的诉求,对基层社会秩序的建构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其实道德示范在这些人员选拔过程中彰显的内生秩序尚算一般,其强烈的道德示范往往在仪式中。
以瑶族传统社会价值和生活实践的“自然实体”为主要内容的瑶族“还盘王愿”仪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内含长鼓舞、舞草龙、瑶歌、上刀山、下火海等瑶族民俗活动与传统体育文化的“还盘王愿”祭祖仪式在展示瑶族非物质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处处彰显着权威和威望存在下的内生秩序功能。涂尔干认为“将仪式看成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而其中的‘神圣/世俗’的关系和行为被看作二元对立的基本社会分类”[11],沿此逻辑,以点带面地审视“还盘王愿”仪式中作为神圣表征的师公和世俗代表的祭品酒,就可以窥见仪式中对道德高扬下的秩序内生。2016年笔者和课题组在桂林恭城瑶族自治县调研中,发现“还盘王愿”仪式中的师公,往往是由瑶族德高望重的、经过专门传承的男性来担当。仪式结束后,这些“师公”回归村寨,上山砍柴、下地种田,过着同其他族人无异的日常生活。但当问到瑶族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如何看待师公蒙老爹时,村民盘长龙说:“老爹德高望重,具有法力,肯定和我们不一样。”也就是说仪式的神圣色彩和“师公”神人相通的“使者”身份,使得平时生活中师公的道德魅力得以放大,对族人生存空间中的社会秩序有着积极影响。与此同理,在盘王祭礼“许愿”“还愿”环节中不可或缺的祭品——酒,也有着通灵祖先盘王品德、表达祖先英雄崇拜的效果。参与仪式者可以在仪式中共同举杯,也可以酩酊大醉;饮酒的过程不仅是瑶族特定社会传统建立、明确人际关系和朋友的过程;也是通过酒的迷幻效果来实现在神圣与世俗的交换中对祖先的缅怀。此时的酒犹如莫斯《礼物》中所说的“总体呈现体系”[12],其具有祖先道德权威的民族标志表达建构了浓厚的瑶族文化社会秩序。
2.3 文化认同的秩序生成
认同是指人与人对共同或相同的事物进行接受和赞同;文化认同[13]是指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不言而喻,文化认同不仅是规范熟人社会的普遍存在,而且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有很多种,调研发现这些衍生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渐次形成的文化传统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都有所体现。如壮族蚂拐舞的文化源头是蚂拐崇拜,侗族抢花炮的心理诉求是请神灵赐福添丁,苗族爬坡杆的精神内涵是追怀古代英雄孟子佑,而瑶族“长鼓舞”则充溢着颂扬盘王功德的始祖崇拜意蕴。实践表明,在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中“任何一种法律,倘要获得完全的效力,就必须使得人们相信,那法律是他们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则不能不诉诸人们对于生活的终极目的和神圣的意识,不能不依赖法律的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最能够表明这一点的乃是传统”[14]。其实传统就是共同认同的文化,正如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与其说是文化在控制人、奴役人,倒不如说人在利用文化和顺应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也就是以身体活动方式来体悟这种文化与传统,在无声中建构着社会秩序。
2018年广西“三月三·民族体育炫”期间,笔者和课题组在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富禄乡的“抢花炮”活动中,发现人们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看似一片混乱的抢花炮,总是给人一种秩序的写意。比如抢花炮的出队总是以村寨为单位:抢炮的人数多寡、抢跑人群的能力大小,以及游炮中花样多少、人数多少、芦笙声音分贝高低等,都在隐喻着村寨力量的强弱。因此,壮侗苗瑶等群众在节庆期间,无论离家有多远、工作有多忙、加班的补贴有多高,他们大都置之不理而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在精神栖息的场域中代表村寨参与各种活动。同时,村寨的寨佬与头人在群体中有着强大的号召力,由其组织的以“抢花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赛更是像仪式中反日常的能量宣泄,狂暴之后留给社会的是井然有序。因此,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视域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文化认同以其凝聚了族群力量、强化了集体意识的“机械团结”而建构了相应的社会秩序。
2.4 关系调适的秩序再造
关系调适往往相对于关系冲突,而文化场域内的关系冲突往往与民族日常生活中的惯习息息相关。布迪厄指出“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是一种依靠行动者自身努力或经由他人灌输而来的行动的产物,并通过个体或者集体的生活史被身体化与内在化”[15]。因此,不同文化样式凝练出的群体或个体“惯习”是不同的。不同“惯习”置身同一场域中时就会有冲突,当然这种冲突也是场域的动力之源,可是要可持续“共处”下去就必须进行关系调适。传统民族地区的社会交往伦理指向往往是以“亲近性”为基础的道德内核,“家庭单位和村民内部的主流交往方式凝聚着共同的民族记忆和村落认同感,民族契约和乡村生活要求从一开始便成为大家遵守的行为规则”[16],但随着剧烈的社会转型造成的社会分化加剧、利益群体形成以及社会关系复杂,使得不同社会成员间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增多,家庭代际冲突、邻里关系淡漠、村内关系分散化等社会交往矛盾凸显。而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为表征的集体活动,在此背景下又有着释放群体或个体生存与生活压力的“安全阀”功能而具有关系调适功能和用途。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以身体为载体,在身体的能量释放中也宣泄了敌对和不满情绪;敌对双方在体育比赛的场域中也彼此进行了心灵的沟通,众多基于缺乏碰撞的误会也得以真相大白,相互理解之后换来的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消解。例如,与格尔兹深描下的巴厘岛斗鸡非常相像的广西融水苗族斗马活动就有此功能。斗马中的“选斗”(选马)、“走堂”(示威)、“相斗”(争斗)等环节,与苗族男人的地位之争存在着一种隐喻。随着斗马决赛中两匹马凶狠的撕斗,强弱立刻可见端倪:斗败者颓然出场,获胜者披红戴绿,苗族村寨之间、宗族与宗族之间的矛盾、竞争也暂时得到缓解,斗马俨然成为恩怨宣泄的通道和途径。正如2016年笔者和团队在融水香粉乡的那坡会调研时,斗马协会会长梁光明所言:“看着是马斗,其实是人斗;斗马由原来的爱情之争变成现在的男人雄性之争、经济实力之争。”置身斗马现场,能直观深刻地感受到斗马人群的这种情绪波动。埃利亚斯在其《文明的进程》中指出,对暴力的使用态度是一个群体或民族的文明标志。此时的斗马虽是民族体育活动,但已成为暴力消解的载体和象征,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下的村落与村落、宗族与宗族、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调适起到了不可小觑的秩序再造作用。
2.5 社会整合的秩序凝聚
当代社会随着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运动的扩张,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在价值观念、利益分成、阶层地位上出现了急剧变迁,原本“大杂居,小聚居”特征中有着相对一致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认同的稳固地区秩序,也开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与转型。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将这种“合久必分”的社会分化与新秩序重构,看成是实现社会良性循环的基本范式。但是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难以承受当前的社会分化的激烈程度,以至于社会由于震荡而出现稳定问题,呈现出亟待建构新的社会整合力量的趋势。而社会整合在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看来,是“社会不同要素、部分结合为一个统一、协调的过程”[17],意即在化解个体之间的矛盾和隔阂、协调社会各要素、调适社会关系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与功能。时至今日,“我国正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整合机制呈现出阶段化、差异化特征,而探究不同民族以及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社会整合,尤其是要重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实现社会整合”[18],方能可持续地建构良好社会秩序。
涂尔干指出:“如果不能定期维护和重申那些可以形成社会统一和人格的集体情感,社会就将不复存在。因而,必须借助庆祝仪式、聚会、集会和会议、教育等形式,重塑人们的共同情感,将人们紧密地围拢在一起。”[19]少数民族体育作为民族地区最传统的文化资源,在体育活动开展中增加了社会成员的交流机会,促进了价值认同,消除了感情隔阂,消解了文化误读,提升了社会道德,有着无可替代的社会整合作用。不仅如此,笔者在对桂西少数民族体育多次调研中发现其体育活动过程以及发起体育活动的村落组织在社会整合中也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壮族的蚂拐舞、侗族抢花炮、苗族拉鼓舞、瑶族祭盘王等活动,其经费由寨老会、理事会等体育活动组织牵头募集。然后在村落公共场合中比较显著的位置对活动的收支细节进行张榜公布,接受众人的监督。族人在对这些传统体育活动认同的基础上,纷纷为相关体育活动出钱出力。这其中就产生了秩序再确认,比如张榜公布名单的排序,往往基于赞助份额的多少;体育组织的建构往往基于族中个人的威望与权威。体育活动举行的过程也是对相关人员社会地位排序的梳理和强化。与此同时,这些民间体育组织除了本然职能,还衍生出调解矛盾的社会整合功能。2016年,笔者和团队在对天峨县纳洞村蚂拐舞进行调研中获悉,村民宅基归属纠纷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蚂拐舞协会利用其影响力主动出面调解,最终有效消解了族员矛盾,强化了社会整合。
3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内生秩序功能的施展路径
文化社会学认为:“文化的产生是社会功能的需要,其本质在于维护社会规范,形成社会秩序。”[20]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反映少数民族精神面貌、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身体文化,既然在价值导向、道德示范、文化认同、关系调适、社会整合等方面有着圭臬秩序的价值,那么梳理出促使其在当前改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健全民族地区公共安全体系中发挥最大秩序价值的路径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3.1 利用展演机会,彰显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内生秩序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传统村寨社会中维系民族团结的重要媒介。无论节庆、民俗,抑或是个人红白喜事等活动,少数民族体育的一次次展演与玩味都是于一次次地促使个体社会化的同时增强集体意识和强化族群认同,有着凝聚族众、万流归宗的向心价值。从文化结构事象来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包括的器物、制度、精神3个层面都有着规范社会的秩序价值。比如蚂拐舞中耕牛、犁、耙是稻作文化的器物表征,身着金冠黑袍的师公及其仪式中的言行是制度文化的比附,铜鼓、蚂拐图像指的是精神层面的图腾文化;再如笔者和团队在河池南丹拉者村调研壮拳文化时,发现壮族武术的器具、服饰、仪式、动作等都折射着壮拳文化结构中的内生秩序。这些基于文化本体的结构逻辑彰显,对置身其中的族众均有着无形氤氲、循循善诱、逐渐建构契合其民族文化范式社会秩序的作用。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要在文化层面上发挥建构社会秩序的效果,还是要切实抓住各种展示平台和机会,多次和长期展演,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效果才会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3.2 组织竞技比赛,扩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内生秩序
以赛促传承、以赛促发展的实用方针,强调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弘扬同样需要竞技比赛这个有力杠杆。赛事不仅能引起更多人关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更多的项目开展与学习机会、更多的项目基层组织建构,而且赛事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民族体育文化的饕餮盛宴与狂欢叙事。正如符号人类学家特纳对仪式的象征符号解构与抽离一样,其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更像一个大的“仪式”。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展开的过程,也就是其中“信仰的、伦理的、道德的等各种事关社会规约的象征符号”[21]对置身其中的族众实施象征教育的过程。象征人类学指出,这些族员,尤其是运动场景中那些逃离社会现实进入“阈限”的族员个体往往通过从类比、隐喻和联想等方式中汲取文化符号影响,在身体活动的体验中宣泄情感不满、建构社会安全阀,从而形成有秩序的言行,融入社会。笔者和团队目睹过南宁宾阳炮龙节中群龙叩首、民龙共舞时的人山人海,也看到了比赛中“炮声不停,龙舞不止”的为民祈福以及最终点燃龙骨架促成“化龙升天”过程中族众的如痴如醉。情感的宣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在这些赛事活动一并得到了实现。因此,少数民族体育赛事为其内生秩序的社会建构提供了契机。
3.3 强化体育组织,延伸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内生秩序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组织除了组织民族间体育活动的职能外,同样也有着消解社会矛盾、整合民族团结等服务社会治理的功能,然而其作为典型的草根体育组织,往往具有非政府行为性、非营利性和临时性。换言之,少数民族体育组织在缺乏有力的制度、经济、物质保障的情况下,往往不够稳定和无法持续存在。已有研究将其按构建模式大致分为主体独立型、宗教依附型、权力渗透型、资本联姻型4个类型[22]。这些类型虽有宗教、乡村权威以及外来资本的支撑,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冲击,也存在着有活动临时搭建、无活动就自然闲置甚至解散的状况,存在着组织不够坚实、不能持续发挥组织功能的情形,不利于除本职职能外的社会治理功能的延伸和施展。因此,在基层的社会管理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扶持已经形成的民间体育组织,使之不断地强根固基。在此方面,被誉为“壮拳第一村”的宜州合寨村的壮拳组织有着典型的示范意义。笔者和团队2018年5月在合寨村调研中发现,由第二代壮拳传承人蒙国栋、蒙胜凤和第三代传承人蒙承顺、蒙国伦、蒙光新等建构的壮拳组织,在村里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力支持和扶持下,不仅传承了猫狮运动、土壮拳技术体系,而且以其组织的影响力,有力地消解了村中的邻里矛盾、村与村之间多年来的积怨,并劝解了几次箭在弦上的械斗,有效地发挥了民间体育组织的作用,营造了和谐社会。
4 结语
“西方治理理论已引入我国多年,然而却不能在我国扎根,只在形式上敷衍应付,社会治理实践中仍问题重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治无教。”[23]因此,国家顶层设计层面提出了大力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实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的时代号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虽然只是少数民族的身体活动方式,但却内蕴了历史人文、宗教信仰、民俗艺术等诸多内容,无论社会教化、社会治理维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都有着张扬社会规范、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文化软实力。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逻辑下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思考中,应该具有和强化深挖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义理、发挥其文化治理功能的自觉,让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在融合中实现民众向善、社会和谐、国家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