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的现实与困境
2019-10-08史宇
史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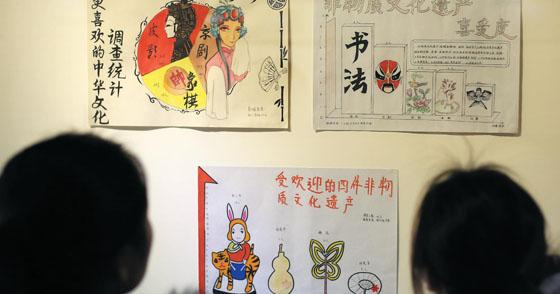
在我国8500万残疾人口中,有108.7万残疾儿童少年。由于行动、视觉、听力以及智力等障碍,这些孩子不能正常接受教育,或者不能进入普通学校就读。这就需要特殊教育的方式,帮助他们实现受教育的权利。然而,特殊教育的发展遭遇诸多壁垒。特殊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在现实中“风雨飘零”,他们也成为了一群反向飞行的“候鸟”。
两种境遇
中国的特殊儿童,境遇往往大相径庭。
佳佳是一名先天小儿麻痹症患者,小时候父母经常带着她四处求医,但佳佳还是要与轮椅终身为伴。好在佳佳生活在医疗条件发达的大城市,她的父母也都是国企员工,经济收入稳定。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佳佳顺利地在普通教育体系内完成学业,现在已经保送到名校攻读硕士。
不过,像她一样幸运的女孩也许并不多见。据统计,中国每年有100万到120万名婴儿出生时带有缺陷,平均每30秒就有一名缺陷儿降生。但这些带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去哪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称,中国每年大约10万名儿童遭到遗弃,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身患残疾。
另外一个故事中,有一对姐妹花,分别叫豆豆和丁丁。姐姐大两岁,是特殊儿童,妹妹是普通孩子,很是聪明可爱。到了这对姐妹该上学的那年,父母拿出全部积蓄,在济南一所以素质教育著名的小学旁边买了学区房。5月份,办完手续迁完户口,姐妹俩参加了小学入学面试。
然而等来等去,周围的邻居陆续收到了小学入学通知书,豆豆和丁丁却没有收到。她们的父母急了,到处打听,学校给出的回复是因为他们5月份才买房迁户口,所以没有被录取。可事实是小区里比他们买房还要晚的邻居都收到了入学通知书。
后来学校里一位熟人告诉他们,学校不想接受姐姐,可如果只收了妹妹而拒收姐姐,可能会被投诉,于是——学校连健康的妹妹也一起拒收了。父母想了各种办法,到处求人,最后的结局是——学校接受了妹妹,拒绝了姐姐。条件是父母签订保密协议,保证不能到处反映,更不能找媒体报道。父母在协议上签了字,从此,姐姐失学在家。
妹妹入学后,因为学校迫使姐妹分开,开始排斥上学。她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也不肯吃小饭桌,要求父母每天四次接送她。家里还有一个辍学的姐姐,这让父母痛苦不堪。仅仅上了一年,因为厌学,妹妹也退学了,追本溯源,她的罪过只是因为她有一个脑瘫的姐姐。
向记者讲述这个故事的另一位特殊儿童家长发出喟叹:特殊儿童这个群体,就像一群候鸟,只能朝着相反的方向飞翔。当普通孩子的家长拼命攒钱买房,削尖脑袋想进名校的时候,这个群体却像一股逆流,拼命往郊区甚至农村,往人流少、教学质量差、环境差的学校里塞,因为那样的学校才有可能容下他们的孩子。
歧视与隔离
据中国残联数据,中国8500万残疾人士中,有超过1500万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其中有1200万人就在农村。他们没能实现就业,也没有条件接受教育,只能靠家庭成员供养、低保金和社会救助勉强度日。
经济条件上的困难,只是特殊儿童遭遇教育困境的原罪之一。
因为残障儿童是有特殊需求的病人,那么出于各种考虑,普通学校有理由拒绝残障学生,将他们推向特殊学校。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中国6-14岁学龄残疾儿童有246万人,在校的残障儿童中能接受全纳教育的比例仅为51.8%,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达到了90%左右。
在特殊学校里,特殊儿童没有机会和没有残障的儿童相处,造成了另一种隔离。同时,由于特殊学校数量不多,且远离残障儿童的住处,大部分儿童必须住在学校,远离家人和朋友,同样不利于残障儿童的成长。
已有研究表明,有残障和没有残障的学生在一个无差别、没有排斥的环境下共同成长,可以得到更好的学习成效。普通教育系统应当充分无障碍地向特殊儿童敞开大门,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愿望很难实现。特殊儿童除非能证明自己能适应学校的物理环境,否则可以被拒绝入学。
而在高等教育领域,歧视同样存在。假如残障学生克服各种困难通过高考,他们要进入高等学府,还必须通过体检,普通高校存在拒绝某些残障学生的情况。目前,在中国8500万的残障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只有94万人。也就是说,100个残障人士中,只有一个人上过大学。
然而,随着平权运动的推进,残障人士的权益亦引起了更多关注。观念意识上的改变,以及强大的儿童福利制度的支持,让残障儿童权益得到了更多保障。在这方面,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做出了許多示范,证明其可行性。
在日本,残疾人又被称为“障碍者”,残障儿童除了能享受一般残疾人的福利政策外,还能享受到其他一些特别的优惠。譬如在医疗方面,先天缺陷儿童的治疗费用由特殊儿童补贴承担,医疗费全免,免除了父母的后顾之忧;后期的康复治疗,如领取助听器、义肢等残疾人用品,家长的自费比例也只有一成。
在教育方面,日本各地区都设有专门针对残疾儿童的“特别支援学校”,确保残障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而残障儿童到普通公立学校就学,学校亦不得拒收。残障人士想接受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也不设体检,只要能力达标,就能上学。其他诸如就业、出行、生活照顾等方面,亦有事无巨细的优惠条例。
改变从“教师队伍”开始
8月27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八次常委会专题会议上,张海迪作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办好特殊教育》的发言。
她重点提出了“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亟需改进的一些问题”,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特殊教育的现状。
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是特教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2018年全国有特教学校2152所,在校生25.54万人,专任教师5.87万人,师生比差距较大。特教教师不仅要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有的还要承担随班就读指导和为重度残疾学生“送教上门”等工作,编制少、人手紧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送教上门”只能安排在双休日进行。
再者,特教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据统计,全国第一学历为特教专业的仅占30%,其他都是由普通学校转岗而来,还有不少还是“冗员”转岗而来。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问题更加突出。最近中国残联相关部厅去佳木斯桦南县特教学校调研,那里33名教师中,13人是学特教的,占比39%;湖南省平江县特教学校50名专任教师中,11人是特教专业的,占比22%。
一些特教专业毕业生宁愿留在大城市不稳定就业,也不愿去艰苦地区担任特教教师。比如,北京顺义区的学校反映招不到北京联合大学特教专业学生。由于没有要求师范院校普遍开设特殊教育必修课,普通学校以教师不懂特殊教育为由拒绝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现象时有发生,成为制约融合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特教教师队伍的结构也需要调整和完善。张海迪表示,从近几年统计数据看,特教对象中盲、聋残疾儿童不断减少,孤独症、脑瘫、中重度智力和多重残疾学生明显增加,有的培智学校75%的学生都是孤独症儿童。但是,国内目前只有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开设了孤独症专业。从需求看,康复治疗学、教育康复学、应用心理学中,拥有孤独症教育课程的毕业生供不应求。
特教教师难度高、压力大,待遇普遍偏低。1956年,国家出台了特教津贴制度,当时按全部工资的15%计算。1985年工资改革时改为“基本工资”的15%,只占全部工资的6%左右,起不到吸引人才的作用,而且,中高等特殊教育的教师还不在享受津贴范围内。尽管陕西等省将特教津贴比例调到“基本工资”50%,但仍有大部分省份以“上面没有政策”为由维持原比例,因此,完善顶层设计势在必行。
历史视域下的特殊教育
封建制度下的“特教”
中国古代,相传在舜的时期,就曾经安排特殊个体与健全人一起在部落进行学习,一起接受生活习俗和劳动教育的教育。古代先民的教育主要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进行,并未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
在后来的封建历史中,特殊教育成为了教育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有关记载几乎成为了空白。对于残疾人的特殊教育,宫廷官府中设置的特殊机构数量下降,但特殊教育在民间却得到了发展,逐渐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一种情况是残疾人普通教育,将残疾人同健全者一起进入家塾、村塾进行学习。还有一种情况是残疾人的职业教育,它是指残疾人在社会事件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生理情况学习某种技能,如算命、卜苎、音乐,典艺、杂技等,目的是为了生存。关于这一部分的记载,多出自各朝各代的野史,文人小说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特殊教育的情况。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特殊教育,尤其是残疾人教育虽然起源很早,在周代就以辉煌的成就走在世界特殊教育的前列,但是特殊教育事业和其他学科一样,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无论是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还是特殊教育的立法与发展渐渐地同西方世界拉开了差距。
封建思想观念阻碍了特殊教育的发展。特殊教育是封建等级观念,取代了之前的朴素平等唯物观念,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一观念随着西学的传入而逐渐被打破。
“特教”与资本主义印记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支配时,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殊教育正在高速发展,随着近代启蒙思想的提出,一些人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要通过教育的手段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一时期涌现出不少特殊教育的理论和著作。
作为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洪仁玕所作的《资政新篇》里有不少关于社会改良的意见。在这本书里洪仁玕提出了借鉴西方的教育经验对我国的残疾人实施教养和教育:“兴跛盲聋哑院。有财者自携资斧,无财者善人乐助,请长教以鼓乐书数杂技,不致为废人也。”通过教育使得他们能够习得谋生的手段,不至于被这个时代所抛弃。
《资政新篇》所提出的对于未来社会的种种设想,最终由于太平天国的覆灭而未能得以实施,而其公平、公正的朴素人文主义精神和相对先进的特殊教育理念,是近代系统思考和开展特殊教育的肇始之作。
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十分欣赏各国在教育事业上的处理办法,他认为即使是盲人、聋哑人、孤儿及罪童,也要和正常人一样,一起接受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国人无一弃材。实现国无不学之人,则贤才不胜用的良好局面。郑观应的思想里,已经蕴藏着全民教育的雏形了。
率先将西方的特教理论在中国落地实施的,是一群来华的传教士。他们以救济的名义来关注特殊人群,因此有比较明显的慈善性质。1874年威廉·穆瑞在北京创办的“瞽叟通文馆”是我国建立最早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也是北京唯一一所视障教育学校。
20世纪上半叶,国民政府也曾颁布过《教育部官制》《国民学校实施细则》《学校系统改革案》等一些对于特殊教育的细则,明确了教育最高行政主管部门对特殊教育承担管理义务,在对盲校的师资配置方面,有着十分具体的规定。
但回头来看,这一时期的特殊教育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痕迹明显,一些思想观念直接复制或者去照搬西方,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并不深。
新时期的求索与发展
为了规范与促进特殊教育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教育部根据特殊教育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具体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特殊教育教学与管理的指导意见。各项特殊教育及学校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与颁布,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方向与路径,并为特殊教育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1951年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这份文件作为新中国教育体制纲领性文件,对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即“各级人民政府并应设立聋哑、盲目等特种学校,对生理上有缺陷的儿童、青年和成人,施以教育”。要求各级政府都应设立聋哑与盲目类学校,这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
相对于过去特殊教育自由无序的发展状态,新中国首次将其作为各级人民政府的一项工作要求而提出,从根本上奠定了特殊教育政府办学的新走向,其历史意义无疑是突出的。在此政策的积极推动下,新中国的特殊教育事业得到快速的发展。至1965年,中国大陆地区已经建立了盲聋类学校266所,在校人数高达22800余人。
随后的几年里,有关特殊教育的法律纷纷颁布,如1956年6月《关于聋哑学校使用手势教学的班级的学制和教学计划问题的指示》、1956年7月《关于聋哑学校学制和教学计划问题指示中的若干有關问题的补充说明》、1956年11月《关于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经费问题的通知》、1957年4月《关于聋哑学校口语教学班级教学计划草案的通知》,以及1957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好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的几点指示》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殊教育的国际开放与交流日益增多,开始探索打破隔离教育的实践模式,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融合教育方式,即随班就读。这种实践探索的路径,得到了有关教育部门的肯定与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