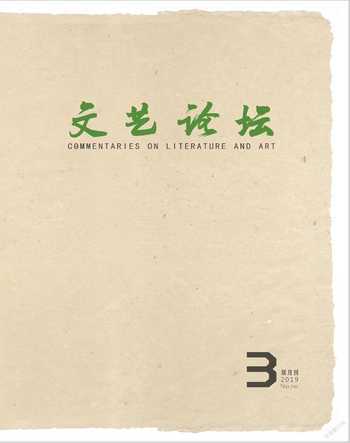主持人语(二)
2019-09-10佘晔
佘晔
李洱是我的老朋友,先是校友系友,后是朋友。说来话长,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钱谷融教授门下攻读硕士研究生,李洱先我一年进华师大,不过他是本科生,等级不一,辈分似乎落差更大,虽然我们年龄相近。可能也因此,当年我们见面不多,并不熟悉,后来连啥时认识的情景也完全忘记了——李洱好像和我说过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但我很怀疑那是他作为小说家的天性想象出来的。等到我们有经常见面的机会了,李洱就总称我“吴老师”。我很不习惯,心想这是否就是我们以前比较生分的缘故?否则为什么见到格非他不说是“格老师”或“刘老师”呢?后来发现,大凡见到大学里当老师的朋友,他多数会称老师,我的理解这是他对一种职业身份的礼遇。格非在他心目中首先还是小说家吧,据说是格老师陪他把自己的一篇小说送到《收获》去的。这个细节虽是日常,但也近可窥见李洱小说的一点特征,比如他的《花腔》和《应物兄》,教师人物不少,或者说像教书匠喜欢掉书袋的人物语言口吻很多。也可以说,李洱是很在乎一个人的文化身份的,人物身份的知识性在他就是一种象征,这个世界可以由此深入,反言之,小说的世界可由此展开,这决定了他的小说叙述形式。这其中是否有些他个人的传记原因,我不得而知,但作为一种李洱叙事的文化心理研究路径,我以为是可以探讨的。不过暂且打住,留待别人后续。也许中国作协机关并非李洱的久居之地,哪天他也会像格非毕飞宇一样去当大学老师的。作家想当大学老师,其实也是一种病,这几年这种病已经成了传染病,也是中国式一流大学建设的特色。
话再说回去,我们各自毕业后也并不常见面。见面无非是在一些文学会议上,北京河南上海几地吧。也许是校友的缘故,也许我很欣赏他的小说,也许他看过我的某篇文章,也许我们偶然谈起过共同心仪的那位华师大女生?反正每次见了彼此会有一种亲切感,好像彼此本来就该是朋友。有几次我对李洱的急智口才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一年敬泽兄领衔的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在许昌举办,李洱地主在会上照应,那是世纪初吧,我们都还年轻,口无遮拦,李洱充分展现了他口若悬河的演说技术和知识能量。他的演说不以声高或气势取胜,而在声调、节奏、面部表情、内容的起承转合,再配以手势、身形,引人入胜,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不得不进入他的语境。而且你知道的,不管是正经谈小说,还是插科打诨,或是臧否人物、讲述时闻,他都能引经据典,藏谐于庄,庄由谐出,一如《花腔》《应物兄》。李洱就是一个在小说里过日子的人,或者说他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像在写小说一样。另一次蒙他高看,母校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华师大作家群的散文集,里面约请李洱一本,出版社说最好每本都由作者请本校朋友写个序。李洱想到了我,给我机会验证一下我们的友情。于是我立即把他的文集全都读了一遍,但还没落笔写序,就听说这事恐怕很难进行下去,也就延宕着一直没写,听候消息。果然,不知何故,这套书终于没能出版。我对李洱抱歉地说,如果这套书出版了,那就是我耽误了你的书,我的序一直没写出来。李洱给我的这次机会,就此成了我欠他的一笔债。而且不是普通的文债,一开始就内含了道德意味。至今差不多还要加上十几二十年的利息。
和李洱的交往故事可以说很多,终于到了他出版了《应物兄》。一两年前在北京听他讲过《应物兄》出版前的惊险经历,那时或许还没有小说的定名,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的不同版本,这里我就不复述了,总之,经历十几年琢磨曲折的《应物兄》注定是要面世的,否则李洱一定活成或堕落成行尸走肉了。现在,他为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人生划上了第一个句号,此前种种只是逗号。此后如何就再说了。《应物兄》以篇幅巨量著称,但一本书出版未久,批评文字已经多过本书,这恐怕也是近几年里的唯一个案。就此而言,李洱或《应物兄》成就了自己的世界。套用流行的俗话,这叫做一个现象级的事件。本来作为老朋友,我想请李洱移驾南下金陵,分享一下新书的阅读快感。没想到是他谦虚还是真的太忙了,半年过去回我说,还是不去了,各地活动也取消了不少。我想可能他对这类活动有了审美疲劳,翻来覆去讲同样、差不多的话,总有倦怠感了吧。就在我邀请他的几次对话中,他问了一句:“小说你看了吧?”当时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我的看与否显然不是他想得到的全部回答,但我的回答也显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简单回答的。看过了,怎么样呢?大家都说了这么多了,还有什么需要、或能再说的呢?正好,《文艺论坛》给了一次再说的机会,刊物约我上半年筹组一个《应物兄》批评专辑的稿子,我也终于有了还债的机会。这就要说到我对《应物兄》的看法了。
我把《应物兄》读成一部当世的寓言之作。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这样说过。寓言之作的要义是以出世的精神写出俗世的故事而成就入世的关怀。我也是这样来看庄子寓言的。寓言性决定了《应物兄》的思想境界和审美趣味。说它写的是俗世的故事,它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日常,但寓言性的故事显然并非现实,而具有了超现实的结构和走向,比如农夫与蛇的故事,既是日常的,却又非现实。所以太实际落实地读这样的书,在故事理解和修辞上恐怕就会陷于误读。出世的精神既是指作家的思考思辨,更多是指他的想象,他的想象在于如何摆脱故事的世俗面,不失故事的真切性而具有空灵超然之思,这在叙事上同时也就提出了一个修辞美学上的挑战——写在实处,归于哲思。这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庄子寓言的美学。这种美学对一个作家而言就是他的文学观和世界观。这样的作家不纯是一个写故事的人,也不是一个高蹈玄思的世外哲人,之所以要以出世的精神写出俗世的故事,根源仍在他的入世情怀。李洱写出了《应物兄》,仅在于表面上像庄子一样用恣肆放荡的文辞写一个寓言以显示自己的博学或叙事才华?或者像农夫与蛇一样写一个简约生动又能充分阐明道理的小品?或者犹如伊索寓言体现俗世高人的智慧?能写俗世故事就能成为小说家,能以俗世故事体现入世关怀就是一个出色的小说家,能以出世精神写出俗世故事而不失其入世关怀的内衷情怀,就是杰出的小说家。这么说下去的话,古代小说就会想到了《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部书堪称大俗大雅趣味的以出世精神写出俗世故事而不失其入世关怀的杰作。我不敢说《应物兄》就在金红两书之间,但李洱的企图和野心或就在此。为什么要谦虚呢?《应物兄》实际就是想挤在金红两书间成为一部当世寓言之作,或一部写尽了荒唐的荒唐之书。我以为李洱真的得了金书红书的神髓。庄子生也太早,文字不足以敷衍作长篇吧。
我的话暂且说到此为止。这个小辑的主角是四篇文章的作者,我只是捧场的。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师范大学师生关于《应物兄》的讨论,这让我想起了我和李洱在大学读书时的文学生活,那时我们讨论《人生》《爱是不能忘记的》,现在讨论《应物兄》。時代不同了,角色轮替,谁能始终站在舞台上呢?《应物兄》会比他的作者活得长。这是我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