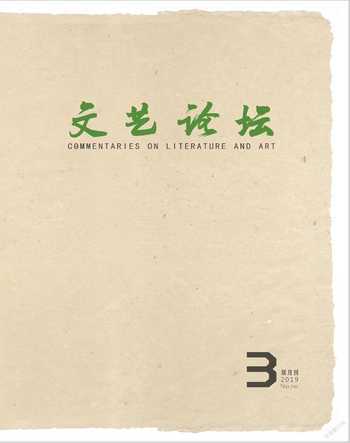融时代命运于小人物的书写之中
2019-09-10王春林
王春林
摘 要:作为一部人物群像式的长篇小说,何顿的《幸福街》所真切书写的,就是1950年代初叶,在新的时间开启之后半個多世纪的时代与社会变迁。小说最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集中体现为作家不仅把时代和社会的巨大变迁非常巧妙地嵌入到了一批普通民众人生命运的书写之中,而且二者之间达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水乳交融程度。
关键词:时代命运;社会变迁;人物群像
放眼当下时代的中国文坛,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活跃着那么多可谓是海量的作家,但严格来说,大约可以被划分为这样不同的三类。一类作家,是创作实绩与自己的声名大致相符,另一类作家,是获得的声誉明显大于自己的创作实绩,还有一类作家,则是创作实绩突出地超过了自己的声名。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这里所具体关注的湖南作家何顿,就毫无疑问属于最后那一类创作实绩远远超过了所获得世俗名声的实力派作家。从1990年代初期,一直到2010年前后,在相继发表了包括《我们像葵花》《就这么回事》《生活无罪》等一系列以作家的出生地长沙为故事背景的小说作品,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之后,何顿的小说创作开始发生某种重大的题材变化。他的关注点,由充满鲜活气息的城市现实生活,逐渐转移向那些已然逝去日久的既往历史岁月。具体来说,作家忽然对抗日战争那一段历史发生了极其浓烈的探究表现兴趣。这样也就相继有了《湖南骡子》《来生再见》《黄埔四期》这样三部姑且可以被命名为“抗日三部曲”的长篇小说。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部既带有鲜明史诗性特点也带有深切反思色彩的,以当年的国军抗战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黄埔四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一直到现在都无法出版单行本,但依照我个人的一种理解与判断,《黄埔四期》应该是一部具有文学史意义的重要作品。我相信,伴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我的这种判断,应该可以得到未来文学史的充分证实。最近一个时期,在抗日题材的书写告一段落之后,何顿的创作兴趣又转向了同龄人所走过的人生道路。虽然从其中肯定难以找出明显的自传性因素来,但因为主要以同龄人为关注对象,所以,在作家新近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幸福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12月版)中,多多少少都会渗透有作家个人的一些生长经验,却是顺乎逻辑的一件事情。尽管说在这部不仅带有突出的散点透视特点,而且时间跨度超过了半个世纪的长篇小说中,出场人物众多,差不多达到了四五十位,但认真地检视一下,就可以发现,活跃于文本中的主要是两代人。除了作为人物主体而存在的,与何顿自己年龄相仿,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叶的这一代人之外,另外就是作为他们父母辈的上一代人。
或许与作家所采用的散点透视方式紧密相关,阅读《幸福街》,我们的首先一个判断就是,这是一部人物群像式的没有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假若一定要为这部作品寻找一位主人公,那么,这个主人公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被看作是作为故事发生地的这一条“幸福街”。这条被何顿征用为小说标题的幸福街,并非古已有之,而是1949年之后出现的新生事物之一种:“幸福街原先叫吕家巷,一九五一年新政权给街巷钉门牌号时,将它改名为幸福街。最开始大家都不适应,好好的吕家巷,怎么就变成幸福街了?有人以为钉门牌号码的人搞错了。出面制止道:‘同志,你们搞错了,这里是吕家巷。’那些人回答:‘没错,以前叫吕家巷,从现在叫幸福街了。’吕家巷的住户觉得这太荒唐了,不情愿道:‘为什么要改名?’那些人答:‘新社会新气象,叫幸福街好。’既然是新社会为之,大家就禁了声,但幸福街的居民着实花了几年时间,才渐渐接受这个名字。”请原谅我在这里引用小说开头的这么长一段文字。之所以如此,乃因为这样的一种开头设计,对我们理解这部作品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小说开头的重要性,曾经有论者写到:“开头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也。尤其在《红楼梦》这样优秀的作品中,开头不仅是全篇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能起到确定基调并营造笼罩性氛围的作用。至少,如以色列作家奥兹用戏谑的方式所说:‘几乎每一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用这根骨头逗引女人的狗,而那条狗又使你接近那个女人。’”“假如《红楼梦》没有第一回,假如曹雪芹没有如此这般告诉我们进入故事的路径,假如所有优秀文学作品都不是由作者选择了自己最为属意的开始方式,或许,我们也就无须寻找任何解释作品的规定性起点。”①同样的道理,何顿《幸福街》的开头方式,看似寻常,其实也暗含有进入并理解这部作品的某种玄机。首先,幸福街原来为什么叫吕家巷,虽然叙述者并未做明确的交代,但只要联系后文,我们就不难认定,其实,吕家巷的命名,恐怕与那个住在幸福街一号的前地主兼资本家吕家有着难以分割的内在关联。“幸福街一号的前主人姓吕,吕家于一九四九年前在黄家镇有大片良田,且经营着大米厂和三家米铺,划阶级成分时,是地主兼资本家。”而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后来的幸福街一号,也就是当年的吕公馆。在1949年之前那样一个私有神圣的时代,能够拥有巨大的资产,是一件特别重要且充满荣耀的事情。大约也正因为由于吕公馆驻足于这条街上,所以这条街才被叫作了吕家巷。就这样,假若我们可以把吕家巷的命名理解为那个曾经的民国时代的象征的话,那么,后来被强制性改名为幸福街,就可以被看作是刚刚到来的一个新时代的象征。但千万请注意,街道的这种更名,并非出于本街住户自身的意志,而是新政权强力意志的一种推行结果。借助于街道的“更名”如此一种开头方式,作家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不管你顺应也罢接受也罢,时代的强力意志都不可违逆与阻挡。不管你情愿与否,正如同吕家巷的被改名为幸福街一样,一个全新的社会和时代就这样到来了。我们都知道,也就在差不多同样的时候,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同时也是诗人的胡风,曾经充满激情地歌咏道“时间开始了”。如果我们从小说是一种时间的艺术这一点来考量,那么,何顿笔下的吕家巷被强制更名为幸福街,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一种历史时间和社会时间的新的开启。就此而言,作家在《幸福街》这样一部以街道为具体命名方式的长篇小说中,所真切书写的,就是在新的时间开启之后超过半个世纪的时代与社会变迁。只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何顿不仅把时代和社会的巨大变迁都非常巧妙地嵌入到了一批普通民众人生命运的书写之中,而且二者之间也达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水乳交融程度。
作为一部人物群像式的长篇小说,《幸福街》中的很多人物形象都给读者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比如,那位小说开篇不久就已经出场的林阿亚的父亲林志华。林志華给我们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一位很有几分桃花运的幸运儿形象。作为五十年代的“个体户”,作为幸福街上一位凭借高超理发手艺谋生的年轻人,因了自身的风度翩翩,最终赢得了周兰这样一位师范学校毕业的漂亮姑娘的芳心暗许。然而,这个时候的周兰肯定想不到,等到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再度到来的时候,自己竟然会因为丈夫林志华的被认定为国民党特务而对当初的这种婚姻选择而悔煞肚肠:“周兰老师特别恨,要知道当年她走进这处遍地古树的古镇,在迎宾路小学安顿下来时,好几个青年都追她,其中一个还是区里的干部,如今那干部调到县水电局当了副局长。可她却糊里糊涂地选择了林志华!上个月,林志华被定为国民党特务,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周兰老师并不相信林志华是国民党特务,说林志华有资产阶级思想,她还是会默认。但那个年代十分荒诞,很多事情的处理都有些出人意料。还有更惊奇的事情,婆婆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据说婆婆说了一些有逆当时政治大气候的话,也被判了刑。”关键在于,好端端的,林家怎么会遭此劫难呢?问题出在婆婆私藏着的一支手枪上。那么,手无缚鸡之力的婆婆,又为什么要藏一支在和平时代毫无用处的手枪呢?却原来,林志华的父亲,曾经是孙传芳手下的一个连长,后来被国民党收编后,曾经以团长的身份参加过著名的淞沪会战,并在战斗中打死过很多日本鬼子。尽管说这位曾经的抗日战士早在1947年就被病魔夺走了生命,但婆婆却把这支早已锈迹斑斑的手枪一直保存下来。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这能丢的?这是你公公的遗物,你公公曾拿着这把枪打死过很多日本鬼子呢。”丈夫逝去,妻子不管不顾地非得把丈夫的遗物作为一种念想保留下来,这本身是人性温暖的极好体现。熟料由于遭逢了一个政治畸形年代,由于邻人陈兵的带头抄家,他们一家三口全部被带走做进一步的审查。最后的结果,除了周兰被放回家之外,林志华和母亲分别以国民党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羁押收监。
林志华因被认定为国民党特务出人意料地被羁押收监倒在其次,更令人感到莫明惊诧的一点是,身在狱中的林志华,到头来竟然会把曾经的妻子周兰也诬陷为国民党特务。却原来,在林志华被判刑入狱之后,生性懦弱,在生活中需要有男性呵护关心的周兰,经过差不多长达一年之久的犹豫彷徨后,为了自己,也为了林阿亚,终于下定决心和林志华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周兰根本就没想到,就在办理离婚手续的过程中,自己的美色却意外地惊艳了凭借不正当手段窜上权位的区革委会严副主任。面对着心态霸蛮、手段凶狠的严副主任,周兰虽然一再抗拒,但还是无可奈何地成为了他身份不公开的姘头。就这么担惊受怕、被逼无奈地过了一阵子姘头日子之后,因为工作调动的缘故,周兰不仅结识了芙蓉路小学的彭校长,而且还两情相悦地达成了结婚的意见。既然要与彭校长结婚,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那就必须中断与严主任(严副主任此时已经升任为严主任)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周兰一反抗,就必然要触怒严主任的威权。这样一来,也就有了林志华诬陷周兰行为的生成。严主任因为周兰执意要摆脱自己而恼羞成怒,他的部下,那个一贯以整人为乐事的刘大鼻子便巧妙地利用林志华的嫉恨心理,诱导他在狱中以口供的方式诬陷周兰为自己的同党,为国民党特务。林志华锒铛入狱后,妻子周兰不仅拒绝前来看望他,而且还不顾一切地和他办理了离婚手续。周兰的这种无情决绝,让身陷囹圄渴望温暖的林志华倍感伤心:“他每天晚上望着铁窗外的天空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妻子那么有情有义而周兰却如此薄情?每当他看见两个已婚犯人的妻子送来肉或猪油或香烟时,他馋得要命,这种恨就会加深一层。恨,一层层加深,累积多了自然会反弹,因为不是在炎热不堪就是寒冷无比的牢房里,如果不想泄恨的事就没事可想了。机会是刘大鼻子提供的。”林志华原初被迫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本就是被刘大鼻子们屈打成招的一种结果。但人性的吊诡之处在于,在他痛恨刘大鼻子的同时,却把更多的仇恨指向了前妻周兰:“但他更加无法容忍前妻尚未与他离婚就跟别的男人上床!这不是不道德的问题,是无视他的存在,是背叛!”正是在如此一种极端仇恨心理作祟的情况下,“他恨恨地大声道:‘我揭发,周兰是我发展的国民党特务!’”一个男性的嫉恨心理,竟然可以达到如此一种地步,细细想来,的确让人倍感震惊不已。对于林志华这种严重被扭曲的不正常心理,何顿还借助于叙述者之口有着更进一步的揭示:“在监狱里关了几年的林志华,思想已长了霉,犹如树根上长了有毒的蘑菇。他一想到周兰与另一个男人交欢,就嫉妒得眼睛充血!”
在那个充满荒诞色彩的年代,既然已经有了林志华的口供,刘大鼻子们也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把周兰硬是作为国民党特务判处了十年徒刑,如果不是周兰自己坚决不承认,不是后来幸运地遇上了市里下来视察工作的那位年轻领导,那周兰还真有可能冤枉地在狱中被关押十年时间。周兰的不幸与幸运之外,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林志华在诬陷周兰后的自我了断。当然,林志华的如此一种自我了断,与他的生性有着内在的紧密关联:“他不是一个有话就说出来让大家分享的人,事实上他是一个精于计算、暗中独占好处的在黄家镇长大的小男人,这种男人太防范别人了因而内心是关闭的,想问题总是往一个死角钻,极容易悲观。这种抑郁和悲观的情绪发展到次年春天,就发展出问题来了。有天,他忽然感觉自己相当愚蠢,想自己被他们利用了。他想一定是他们想欺凌周兰,周兰不从,就利用他的话加害周兰。他们煽动起他强烈的嫉妒心,让他在嫉妒心的指引下充当了帮凶。‘我真是糊涂啊,怎么当时就没看到这一层呢?!’”就这样,由于他那过于狭小的心胸,当他终于认识到自己被人利用而产生了强烈的悔恨心理之后,他竟然在牢房里上吊自杀了。认真审视林志华这一人物形象,一方面,何顿的确不失精准挖掘出了他的人性深度,无论是他的心胸偏狭,还是他那无以自控的嫉妒心,抑或还是他后来的悔恨交加,都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莎士比亚笔下的奥塞罗。我们注意到,在《幸福街》中,叙述者曾经借助于陈漫秋和黄国进之口,专门讨论过奥塞罗的杀妻悲剧。黄国进认为:“奥塞罗太自负了,也太容易被人骗了,智商不高。”而陈漫秋则认为:“是奥塞罗的嫉妒心太重了,这种人头脑不清醒,因嫉妒心导致他人格分裂。这是他杀死妻子苔丝狄梦娜,自己又悔恨地自杀在苔丝狄梦娜身边的原因。这个悲剧是人物性格造成的。”两相比较,当然是陈漫秋的看法更具合理性。事实上,与其说这种看法是属于陈漫秋的,莫如说更是属于何顿自己的。虽然说具体的故事情节并不相同,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笔下的这位林志华,还真是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奥塞罗的。但在充分肯定林志华别具一种人性深度的同时,我们却也必须看到时代与社会在其人生悲剧过程中的巨大投影。毫无疑问,若非遭逢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那么,林志华和周兰就极有可能幸福而又平静地度过他们平庸的一生。从这个角度说,林志华的悲剧,就既是性格的悲剧,同时也是时代与社会的悲剧。
再比如,高晓华这个后来陷入到精神失常状态的“宣传宝”。作为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高晓华的引人注目,是从他伴同女友黄琳一起上山下乡做知青那个时候开始的。具体来说,那个时候的高晓华,是一个拥有远大志向的理想主义热情高涨的时代青年。在对知青农场倍感失望的情况下,高晓华毅然辞去副场长职务,组织了十几位可谓“志同道合”的知青,决心另外创办一个新的经济上独立的小农场。高晓华的理想主义精神,从他对准备加盟小农场的女友黄琳的询问过程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高晓华当着十六名男女知青的面说:‘你能做到互助友爱吗黄琳?’黄琳答:‘我能做到。’高晓华问:‘你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吗黄琳?’黄琳答:‘我能。’高晓华说:‘我们要做无私无我,一切都是大家的,包括父母寄来的钱物,你能做到一切都交公吗?’黄琳想他们能做到她就能做到,答:‘我能。’高晓华说:‘还有一条最重要,我们决定三年不回家,你能做到吗?’黄琳答:‘我能做到。’高晓华对她的回答很满意,说:‘小农场是我们大家创办的新型集体,我们每个人都是新型集体中的一员,我们都要有集体荣誉感,都要有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尽管说此后的一系列事實,充分证明高晓华的这些想法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在他这些极其切合于那个时代主体导向的想法中,理想主义精神的存在,却是无可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实际上,也正是在与黄琳的关系中,高晓华陷入到了某种肉身与精神的分裂状态。一方面,性欲强烈的他,特别贪恋黄琳的肉体,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口口声声强调:“黄琳,我觉得肉体之娱是低级的,我们是人,是有思想的,我们要做思想领域里的崇高者。”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是,并不只是高晓华一个人,其他很多类似的具有理想主义特质的人物那里,在那个特定时代,也往往会陷入到如此一种灵与肉的分裂与冲突状态之中。其他方面的自私或许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克制,唯独本能的性欲无法自控,难以操纵自如。一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是,具有精神受虐倾向的高晓华,一直到精神失常变身为“宣传宝”之前,都处于这种灵与肉的分裂和冲突状态之中。
一般来说,在那个不正常的畸形年代,如同高晓华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也都会生成某种可谓是生气勃勃的野心:“高晓华的幼年是在后院的桃树、梨树和橘树、柚子树下长大的,少年时他常常爬到树上眺望,就把自己眺望成了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好强、勇敢,视别人为刍狗,渴望自己某一天能成为操纵他人命运的人!”一方面,受制于那个时代所谓集体主义理念的规约,另一方面,也与他内心深处一种出人头地的强烈权欲紧密相关,到后来,等他进入镇陶瓷厂并成为厂里的团支部书记后,才会出于对改革开放、对厂长的强烈不满而上书上级机关告状。面对现状,“他深感悲哀。他想一个人过,回到知青林场,边耕读边学习,他喜欢那里的树木和那里的阳光,但嫉妒心和旺盛的情欲却让他离不开女人。如今这社会不是他想要的,当年大家都有一股不怕吃苦的热情,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现在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奖金少了几块钱都在厂里闹,吃不得一点亏。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改革开放释放了人的私欲,导致了人人都盯着利益。”唯其因为如此,他才会恨恨地说:“现在哪里还像搞社会主义,分明是搞资本主义。”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一点是,高晓华对自私心理的仇恨,竟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学生时代就有理想,就有要使全人类变得毫无私欲的乌托邦精神,但自从他创办的小农场不欢而散后,他对人性充满了质疑,觉得很多人都变肮脏了,变坏了。他其实是有高瞻远瞩的,很想找几个科技人员,发明一种激光机器,可以直接伸进人的大脑里刮割,把人们大脑里的自私病菌剔除掉,让人人都活得纯洁、健康。”他的如此一种试图使用机器剔除人的自私心理的想法,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英国作家奥威尔的长篇小说《1984》。这种思想的可怕处在于,它很容易成为滋生极权的土壤。但正如同你已经预料到的,思想一直停留在过去时代的高晓华,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肯定会因其思想言行的格格不入而被日新月异的生活所抛弃,必然会成为时代与生活的落伍者。受到如此严重失败感的长期困扰,久而久之,高晓华的精神失常,自然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一种必然结果。从一种无法自控的嫉妒心理出发,高晓华不仅对妻子黄琳的男友宋力大打出手,而且还使得宋力彻底丧失了性能力。这样一种打人致残的行为,给他带来的是长达七年之久的牢狱之灾。
等到高晓华终于从监狱中走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彻底精神失常,变成了一个身穿旧军装,在街头用喇叭大声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宣传宝”:“他真是高晓华!她的心都碎了,想不到曾经跟着她一起在学校里造老师反,后来又随她下乡当知青、鼓动十几名知青与他办小农场的,曾经是那么精明、勇敢、执着且身怀抱负又不顾一切追求她的高晓华——她的第一任丈夫,竟成了这么一个人!她呆立在他身旁,他好像不认识她了,没看她而是对着喇叭大声背《纪念白求恩》‘……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和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她感慨良多,辛酸、难过和可怜等都有。他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原来同事们嘲笑的街上的‘宣传宝’(“宝”字,在湖南话里有傻的意思),竟是与自己离婚多年的高晓华!他彻底疯了。”正因为黄琳不仅曾经是高晓华的妻子,而且还从内心深处深深地崇拜并爱过他,所以,面对已经变身为“宣传宝”的高晓华,她才会感到特别痛心,难以接受。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高晓华是何顿在《幸福街》中刻画塑造的最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之一。很大程度上,高晓华的悲剧质点,在于与时代和社会的严重错位。当社会已经告别以“政治”为核心的运动时代,进入一个以“欲望”为核心的经济时代之后,高晓华的思想却一直停留驻足在既往的那个时代。之所以会是如此一种情形,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在于那个时代恰好是高晓华精神成长的关键时期,另一方面,更加不容忽视的,恐怕却在于高晓华个人的主体精神结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很多他的同龄人却都没有变成“宣传宝”。归根到底,高晓华的变身为“宣传宝”,所充分说明的,正是那个不正常的畸形时代在其精神深处的嵌入之牢固。
虽然是一部以散点透视方式完成的人物群像式的长篇小说,但相比较来说,何顿的关注点,恐怕还是更多地停留在了何勇、林阿亚、张小山以及黄国辉他们几位一九五八年生人身上。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他们几位身上,也同样有着来自于时代与社会的巨大投影。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是何勇和林阿亚。如果说我们此前分析的林志华与高晓华,以及稍后要展开分析的张小山与黄国辉,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更多是所谓负能量的话,那么,何勇和林阿亚身上所携带的,就更多是一种以善良为核心的所谓正能量。自幼一起长大的何勇与林阿亚,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一对男女青年。一方面,是父亲和奶奶的被捕与判刑,另一方面,是母亲周兰的被牵连入狱三年多时间:“林阿亚成了只可怜的小猫。父亲、母亲和奶奶被带走后,她害怕得缩成一团,好像天塌下来压着她一样,让她有一种快窒息的感觉。她想他们家一下子就变成坏人了,她怎么活呀?”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不是周边的邻居,尤其是何勇他们一家的积极帮助,孤苦伶仃的林阿亚,恐怕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度过少年时期这一场突如其来的人生劫难。等她到了可以上初中的年龄,由于家庭牵累的缘故,“本来是没初中读的,开学一个星期了,她被那个年代的学校排除在外。”在那个时候,慨然出手帮助林阿亚的,依然是何勇那位善良无比的母亲李咏梅校长。很显然,如果没有李咏梅校长的帮助,林阿亚小小年纪便辍学在家,那她后来在历史发生重大变迁后,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由丑小鸭变成大天鹅,不可能考上复旦大学的。到后来,高考制度恢复之后,已经追随心仪的男友何勇做下乡知青的林阿亚,一门心思想要参加高考。没想到,由于主管报名工作的区文教卫办公室主任刘大鼻子利用她的家庭出身问题从中作梗的缘故,唯一一个没有拿到准考证的,就是林阿亚。值此关键时刻,同样是何勇通过母亲找到了已经成为区革委会主任的黄迎春,在黄迎春的强力干预下,方才获得了参加高考的权利。到这个时候,自然也就应了那句“祸福相依”且互为转换的老话,虽然林阿亚打小一直到此时此刻都可谓劫难不断,但等到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时候,她反而因被冷落时的刻苦学习而因祸得福,最终在高考中取得了好成绩,一举考上了复旦大学这样的名校。与她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那位一直都情投意合的男友何勇。由于父亲是大米厂厂长,母亲是校长,根正苗红的何勇,从小一直到高考失败的时候,都可以说是顺风顺水。然而,等到参加高考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把学习当回事的何勇,即使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都无济于事了。
毫无疑问,假若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那么,早已两情相悦的何勇与林阿亚他们两位,恐怕也就顺理成章地结婚成家了。现在的情况是,他们不仅天各一方,而且身份地位也形成了极明显的差异。一个是黄家镇上的普通民警,另一位则不仅在大上海读名牌大学,而且大学毕业后又进一步深造读了研究生。尽管说他们曾经是那样地志同道合两情相悦,但到了这个时候,客观的状况已经致使他们不可能再有共同的精神语言可供日常交流。怎么办呢?他们各自都陷入到了矛盾的心态之中。林阿亚的内心苦恼,集中通过她和大学同学乔五一的通信而表现出来:“他和何勇不同,何勇是她的发小,属于青梅竹马,如果不是她上了大学,她和何勇恐怕都有小孩了。乔五一是她的大学同学,有思想有追求,而且……也帅。”实际上,当林阿亚在心目中把何勇与乔五一做这种不自觉比较的时候,她的情感天平已经在不知不觉地向乔五一那边倾斜了。其实,林阿亚的内心纠结,集中在是否应该知恩感恩进而报恩的问题上。依照一般的民间伦理,既然何勇尤其是何家,当年在她无奈落难之时,曾经倾全力相助,那么,不管此后身居何种高位,林阿亚都不应该忘恩负义,她都应该心甘情愿地嫁给何勇,做何家的儿媳妇。然而,在一种现代的层面上来说,正所谓“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男女之间的婚姻结合,必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事实上,乔五一给出的建议,就是以这种现代婚姻观念为出发点的:“你既然不想面对他就离开他,你丝毫不要背负感情和道德上的债务,那些债务可以用别的方式偿还,但不要把自己的一生都献出去,不要勉强自己,因为你和他不在一个层面上了,即使结合到一起也不会幸福。”由此可见,隐身于林阿亚的自我纠结背后的,其实是民间伦理与现代爱情观念之间的一种尖锐冲突。就这样,在经过了一番内心的自我挣扎后,林阿亚最终还是理性地遵从了内心的情感律令,选择了对何勇的远离。而自感到与林阿亚的各方面差距越来越大的何勇,尽管内心里满满地都是对她的迷恋与爱慕,到最后,在父母朋友的规劝下,他所作出的选择,也是对林阿亚的无奈放弃。尽管我们很难设想,假若何勇与林阿亚真正结合后会是一种什么情况,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其实心地都特别善良、正直的何勇与林阿亚,在做出了理性的选择,分别成立了各自的家庭后,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我们都知道,文学创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人性无关,但需要强调的一点却是,所谓人性,既包含了善,也包含着恶。一方面,文学创作固然应该有对于恶的深度透视,我们前面专门分析过的林志华与高晓华,更多地就是其内心深处的与恶相关的负面因素,但在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也应该有对于善的张扬与表现。而且,在很多时候,要想富有说服力地把人性之善表现出来,很可能比展示人性之恶的难度还要更大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说,何顿能够在《幸福街》中,通过何勇与林阿亚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把他们内心深处的善良与正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在何勇与林阿亚的身上,也同样有着时代和社会的深度嵌入。林阿亚之所以能够在遭受一系列人生劫难后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正因为她很好地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而何勇,虽然没有如同林阿亚一样凭借高考获得人生的重大转机,但在他那平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人生道路上,却也同样有着对时代与社会发展趋向的契合与顺应。
如果说何勇与林阿亚属于那种中规中矩的好人形象的话,那么,张小山与黄国辉他们两位就毫无疑问属于那种最终走上了人生歧路的迷途者形象。因为他们不仅都出生在一九五八年,而且也都家住幸福街的缘故,所以,张小山、黄国辉与何勇、林阿亚他们不仅从小就是很好的玩伴,而且也在共同成长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林阿亚不仅身为女性,而且很早就考到上海去读复旦大学,姑且忽略不计,作为少年时的好友,张小山、黄国辉他们两位与何勇的渐行渐远,是从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之后慢慢开始的。先让我们来看张小山。或许与其生性的敏锐、机巧有关,张小山其人,在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曾经一度扮演过引领风潮的弄潮儿角色。眼看着有人在幸福街上开了一家个体小商店,心眼一向活泛的张小山坐不住了,决定筹集资金去做生意:“三个人喝了几巡酒,说了些互相勉励的话后,张小山说:‘我去了趟广州,发现广州那边开放多了,做什么生意的人都有。’黄国辉问:‘你准备做什么生意?’张小山说:‘我打算先做点小玩意生意。’‘好,是要从小事情做起。’何勇鼓励他说。”就这样,在两位好友的鼎力支持下,张小山的生意开张了。从最初的墨镜与打火机,到后来的收录机,再到后来的良友、希尔顿等外烟,张小山的生意可谓步步为营越做越大。在其原始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决定顺应时势,租用竹器厂的礼堂办一个红玫瑰舞厅:“红玫瑰舞厅在千年古镇上诞生了,不亚于晴天霹雳。”由于切合了那个时代年轻人时尚心理的缘故,红玫瑰舞厅的开办可谓大获成功,仅仅是到了当年年底,就已经赚了十多万。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张小山自我创业的巅峰时刻。面对着满面春风的张小山,何勇不由得感叹他是一个有能力谋划未来的人。但张小山自己给出的却是另外一种说法:“我父亲死得早,遇到困难我都得靠自己解决,就学会了动脑筋。”他们之间的情谊在某种意义上堪比“刘关张”的何勇、张小山以及黄国辉三人中,之所以是张小山一度成为引领风骚的个体户,除了思想活跃与丧父的孩子早当家这两点之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在被镇竹器厂开除后,他所面临着的,已经是一种生存的绝境。就此而言,他的自我创业行为,很是有一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但谁知张小山不仅贪心不足,而且还特别贪恋女色,到后来,等到他自信满满地在县城又创办了一个名为“红彤彤”的舞厅的时候,虽然舞厅的客流量依然爆满,但最终却因为他与县剧团一位姓杨的名角儿发生私情,并引发其丈夫李军的报复行为,舞厅不仅被付之一炬,他自己也终因无法偿还相关债务而被迫锒铛入狱。自此一劫后,虽然也还有过几度起伏,当就整体趋势来说,张小山的人生就走上了一条每况愈下的下坡路。其间,尽管已经出任了驼峰山乡派出所所长的何勇旧情不忘,先后设法安置了张小山与黄国辉这两位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但张小山却恶习不改,仍然坚持组织并参与六合彩的地下赌博活动,最终还是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无业游民。到最后,也还是在他的强力怂恿下,一贯有勇无谋、徒有一身蛮力的黄国辉,才和他一起铤而走险入室盗窃。虽然他们一开始并不打算杀人,但在被大毛认出之后,无奈杀人灭口,就此而走上了人生的末途。后来,叙述者曾经非常巧妙地借人物杨琼之口,对张小山与黄国辉的杀人事件作出过这样的评论:“黄国辉下岗后,只知道玩,宁可饿肚子也不去做事。张小山一天到晚跟那几个鬼打麻将,输了钱,又想赢回来,结果越输越多,把他几年前赚的钱全输光了,那还不饥寒起盗心?”紧接着,杨琼又说:“我们这代人受的教育,你们是知道的,没有什么文化又都好面子。我曾多次劝张小山,要他做点小生意,他听不进去,放不下面子。”何勇补充说:“杨琼说得对,张小山最要面子。黄国辉在街上瞎混了几年后,人变懒惰了,也好面子,我曾经想帮他,问他愿不愿意来派出所打扫卫生,工资虽不高,但至少可以让他活得好一些,他居然嫌找个工作丢脸。”毋庸讳言,以上这些人物对张小山与黄国辉的议论,肯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作家何顿的看法。但依我所见,在承认以上观点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同时,却也更应该看到,幸福街上同样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一个阶级斗争的时代走过来的一代人,为什么只有张小山与黄国辉他们两位最终步入了人生的歧路。从根本上说,张小山与黄国辉人生悲剧的酿成,恐怕也还得在他们自身寻找原因。一方面,所谓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极大地刺激了他们內在的贪欲,但在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却又缺乏实现人生欲望的合理手段。二者发生激烈碰撞的最终结果,自然也就是他们入室抢劫杀人行为的酿成。从这个角度来说,张小山与黄国辉的悲剧,固然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与他们各自的主体心理结构紧密相关,但与此同时,却也明显包含有时代与社会的因素在其中,可以说是时代与社会的悲剧。
反复阅读何顿《幸福街》后,我想,我特别认可胡平与李建军他们两位对这部长篇小说所作出的评价。胡平说:“《幸福街》描述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幸福街的时代变迁,以及街上两代人数十年间的命运遭际,真切还原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几乎所有细部上,都是经得住检验的,成为‘历史的书记’。”②李建军说“我觉得这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因为现在整个当代创作,流行一种非历史化,跟现实严重脱节的现象,很难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活历程,而《幸福街》深刻地还原了时代的风貌。”③文本的事实的确告诉我们,《幸福街》是一部真切还原了时代与社会风貌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但在承认以上观点合理性的同时,我也还愿意有所补充。那就是,《幸福街》不仅真切还原了时代与社会的风貌,而且还进一步地把时代与社会的精神都深深地嵌入到了一众小人物跌宕命运的书写之中。
注释:
①张辉:《假如<红楼梦>没有第一回》,《读书》2014年第9期。
②胡平语,参见《幸福街》封底,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③李建军语,参见《幸福街》封底,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