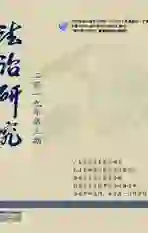评仲裁庭关于国际法中历史性权利的裁决
2019-09-10王军敏
王军敏
摘要:在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将菲律宾第1、2项诉求定性为涉及《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推断中国对超出《公约》允许海域外的“九段线”内海域的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提出了专属历史性权利。在查明《公约》第298条“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等条款含义时,仲裁庭对国际法中的历史性权利作出解释、对中国南海权利主张进行推断并作出裁决。西方一些学者高度评价仲裁庭对历史性权利的裁决,认为是对国际法中历史性权利问题的权威解释和裁决。然而,研究表明,仲裁庭对历史性权利的解释、裁决存在着瑕疵:第一,历史性所有权仅指沿海国对海域的领土主权,不能用于指对陆地的领土主权;第二,仲裁庭对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推断值得商榷;第三,仲裁庭推断中国对超出《公约》允许海域外的“九段线”内海域的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提出了专属性权利,将这种权利主张定性为非专属历史性权利,并按照其要件判断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有效性,错误地适用了国际法规则。
关键词:历史性所有权 中国南海权利主张 非专属历史性权利
DOI:10.16224/j.cnki.cn33-1343/d.2019.03.012
2013年1月,菲律宾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将中菲南海争端提交《公约》规定的强制仲裁程序。在2014年3月30日的诉状中,菲律宾向仲裁庭提出了15项仲裁请求。其中,诉求1:中国南海海洋权利主张,不能超过《公约》允许的范围;诉求2:中国主张对“九段线”内南海海域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历史性权利”违反《公约》,在超出《公约》允许范围的情况下不具有法律效力。在2015年10月29日《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中,仲裁庭认为,对于菲律宾第1、2项诉求管辖权的最终裁决取决于中国历史性权利的性质,以及它们是否属于《公约》第298条规定的“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争端”,从而排除仲裁庭对菲律宾诉求1、2的管辖权。因此,仲裁庭将菲律宾诉求1、2的管辖权问题推迟到与实体问题一起裁决。在2016年7月12日裁决中,仲裁庭不仅对中菲南海历史性权利争端作出裁决,而且最终以裁判方式阐明了当代海洋法中的历史性权利问题。克里夫(Clive)非常赞赏仲裁庭对历史性权利问题的裁决,认为仲裁庭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井然有序、合乎逻辑,法律上是可接受的。然而,仔细分析仲裁庭关于历史性权利问题的裁决,它在历史性所有权的适用范围、非专属历史性权利及其构成要件等问题上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历史性所有权仅及于海域,还是包括陆地?
关于历史性所有权的意义,仲裁庭指出,虽然该术语的通常意义已经暗含一个所有权概念,但是,应该在国际海洋法演变的特定背景下理解“历史性所有权”概念。在研究了1930年海洋法编纂会议、1951年渔业案、1956年国际法委员会对条约草案的评述《历史性海湾备忘录》《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历史性水域法律制度》《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和《公约》关于历史性所有权的规定,分析了国际法院在卡塔尔诉巴林案、大陆架案(突尼斯诉利比亚)对历史性所有权、历史性捕鱼权的意见之后,仲裁庭强调:“在海洋法中,存在着对源于历史性过程的各种权利用语的可认知用法。‘历史性权利(historic rights)性质上是一般性的,可以指一国可能享有的、如果缺少特定历史性情势那么根据一般国际法规则通常不能产生的任何权利。历史性权利可以是主权,但也可以是更为有限的权利,如捕鱼权或者通过权(right of access),即不及主权的权利主张。相反,‘历史性所有权(historictitle)专门用于指对陆地或海域的历史性主权(historic sovereignty to land or maritime areas)。‘历史性水域只是指对海域的历史性所有权的表达法,通常将其作为内水或领海对其行使国家权力的海域……。最后,历史性海湾只是一个国家将其主张为历史性水域的海湾。”
可以看出,仲裁庭澄清了先前对海域的历史性权利主张使用的那些模糊不清、并且经常混用的各种习惯用语的含义,如历史性权利、历史性所有权、历史性水域或海湾等,并且强调:历史性权利性质上是一般性概念,外延更大,包括历史性所有权和非专属历史性权利,如捕鱼权或者通过权;历史性所有权所涉海域被称为历史性水域,历史性水域是内水或领海,这取决于沿海国将所涉水域作为内水或领海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性海湾是历史性水域的其中一种。应该说,这是仲裁庭对国际法中历史性权利习惯法规则的认定、解释和权威确认。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仲裁庭关于历史性所有权专门用于指对陆地或海域的历史性主权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历史性所有权仅指对海域享有领土主权,不包括对陆地的所谓“历史性主权”。
(一)从历史性所有权概念的演变看,它仅指对海域的领土主权
国际常设仲裁院在北大西洋沿岸捕鱼案中提出“历史性海湾”概念后,学术机构、国际会议在界定领湾时,均将虽不符合其提出的领湾标准但所谓“历史性海湾”视为领湾,这些海湾不受编纂性条约的影响,仍然属于海湾沿岸国所有。后来,从事海洋法编纂工作的国际会议、国际机构注意到:具有类似于历史性海湾地位的海域不限于海湾,也存在于其他沿海水域,如海峡、河口湾、群岛内水域等。哈佛大学国际法研究院《关于领海研究草案》在规定历史性海湾的同时,意识到可能存在着以历史性理由主张更宽的领海。在渔业案中,国际法院判决挪威对不具有海湾特征的其他海域享有历史性所有权,认为挪威有权根据历史性所有权主张4海里领海。《历史性海湾备忘录》得出结论说:“历史性海湾理论是普遍适用的。不仅对海湾而且对不构成海湾的海域,例如,对位于群岛内的水域以及群岛和毗邻陆地之间的海域主张历史性权利;也可以对海峡、河口湾和其他类似水域主张历史性权利。存在着日益将这些海域说成是‘历史性水域,而不是‘历史性海湾的趋势。”
受渔业案判决影响,1958年海洋法会议在讨论领海划界规则时意识到,相邻、相向国家领海划界在适用中间线或等距离线原则时,可能存在着特殊情况或者相关国家以历史性所有权为根据主张不同领海宽度的情况。因此,会议讨论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所有权等问题时,开始使用“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历史性水域”表达法,促请“联合国大会对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历史性水域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并将这些研究结果分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1958海洋法会议通过了4个海洋法公约,其中《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7条第6款规定:“上述规定应不适用于所谓‘历史性海湾。”第12条第1款规定:“如果两国海岸彼此相向或相邻,两国中任何一国在不能达成相反协议的情形下,均无权将其领海延伸至一条其每一点都同测算两国中每一国领海宽度的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的中间线以外。但如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有必要按照与本款规定不同的方法划定两国领海的界限,本款的规定不应适用。”这样,国际社会第一次在普遍性国际公约中明确承认了历史性海湾、历史性所有权在现代海洋法中的地位。1962年,联合国秘书处向联大提交的《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历史性水域法律制度》重申:“虽然‘历史性海湾是对海域享有历史性所有权的典型例子,但似乎原则上对不是海湾的其他海域也存在著历史性所有权,如海峡或群岛间海域,或者一般地说对可以构成国家海域领土一部分的那些所有海域存在着历史性所有权。”
可以看出,公法学家、学术机构说明“历史性海湾”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时,最初将其说成是内水、领土一部分,国际法院将其定性为国家对所涉海域享有历史性所有权。虽然联合国秘书处在《历史性海湾备忘录》中使用“历史性权利”表述法,但从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以后,国际社会倾向于使用术语“历史性所有权”,来表明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历史性水域的法律地位,即国家对所涉海域享有主权,是沿海国的内水或领海。而且,从“历史性所有权”的提出、确立过程看,历史性所有权限于沿海国对毗邻海域的主权,如海湾、海峡、群岛内海域、沿岸岛屿与海岸间的海域,等等,从来没有说是对陆地领土的主权。
(二)从时际法规则看,对陆地的历史性主权并不意昧着现在仍享有主权。相反,对海域的历史性所有权意味着这些所有权仍然是有效的
胡伯法官在帕尔马斯岛案中指出:有关发现和取得领土的国际法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当事方也承认,一個法律事实必须按照与之同时的法律,而不是按照关于该事实的争端产生时或解决争端时的法律予以判断。在具体如何适用时际法规则时,他指出:“至于一个具体案件,在先后连续不同时期适用的几个不同法律制度中究竟应适用哪一法律制度的问题(所谓的时际法),必须对权利的产生和权利的存在这两者作出区分。产生一个权利的行为受该权利产生时所适用的法律支配;按照同一原则,该权利的存在,换句话说,该权利的继续表现,也应当依循法律的演进所要求的一些条件。”因此,根据16世纪的国际法,即使西班牙能够通过发现取得对帕尔马斯岛的领土主权,但后来没有通过有效占有来保住它的主权,特别是关键日期即1898年割让时,西班牙已经丧失了对帕尔马斯岛的领土主权,因此,美国不能根据《巴黎条约》从西班牙取得对帕尔马斯岛的领土主权。可以看出,对陆地领土争端来说,即使一国按照领土取得时的国际法,取得对某一领土的主权,但没有按照国际法演进的要求表明、强化其领土主权,特别是在争端产生时的关键日期已经丧失了领土主权的情况下,该国仅仅援引历史性主权是不够的。换句话说,历史上曾经取得的领土主权只表明领土在历史上的法律地位,不代表领土在当下的法律地位。在解决领土争端时,领土主权取决于争端产生时即关键日期时的时际法、事实、行为,不取决于历史上曾经取得的领土主权。
在海洋法中,历史上没有形成有关领海基线的一般国际法规则,或者一直模糊不清,存在争议。因此,国家社会在编纂领海基线一般国际法规则时,不是无视一国对海域的历史性所有权,而是将其作为编纂性条约确立的一般规则的例外,使历史性所有权继续存在。正如联合国秘书处在《历史性海湾备忘录》中指出的:“限制沿海国将海湾海域主张为内水一部分的企图与现状有冲突。存在着海域面积相当大,但完全为沿海国所有的海湾——在这种情况下,领海因此应该从所涉海湾的湾口处向海测算。因此,为编纂的目的,存在着两种可能选择:允许这些情况作为一般规则的例外继续存在;不论其事实上的地位如何,将拟议中的一般规则适用于所有的海湾,不考虑它们。后者是专横的,如果在实践中适用将导致国际困境。”
对陆地领土的历史性主权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相反,对海域的历史性所有权一般作为适用编纂性条约规定一般规则的例外,能够继续存在。因此,从国际法中的时际法规则以及领土法和海洋法的特点看,历史性所有权不包括对陆地领土的历史性主权是适当的。
(三)从《公约》的谈判过程、规定看,不允许对陆地的历史性所有权
海底委员会向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提交了需要编纂的海洋法问题清单,其中“历史性水域”包括在第二项目“领海”下。在海洋法会议上,第二委员会负责领海问题。在1974年第二期海洋法会议上,许多国家建议保留《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关于领海制度的规定,其中,在讨论领海宽度问题时,菲律宾又提出了历史性水域问题,建议:“领海包括以历史性权利或所有权为由、并且实际上被它作为领海一部分的那部分海域;公约规定最大领海宽度不应适用于被任何国家视为其领海的历史性水域;在批准本公约前已经确立了比本条规定的最大领海宽度更宽领海的任何国家不应受本条规定的最大宽度限制。”印度尼西亚建议:“历史性水域权利主张不应包括陆地领土或者已经置于另一国家主权或管辖权之下的水域。”第二委员会在第二期会议结束时通过了《第二委员会工作文件:主要趋势》。《主要趋势》第二节“历史性水域”综合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提案,包括两个条款:“第2款:领海包括以历史性权利或所有权为由、并且实际上被视为领海的那些海域。第3款:历史性水域权利主张不应包括陆地领土或者已经置于另一国家主权、主权权利或管辖权之下的水域。”
但这些条款在随后进行的非正式谈判中没有被保留下来。在1975年第三期会议上,作为非正式协商结果提出的统一案文出现在《非正式单一协商案文》第二部分的第9条,其中第6款规定:“上述规定不适用于所称的‘历史性海湾,也不适用于采用第6条规定的直线基线法的任何情形。”在1976年第四期会议上,哥伦比亚建议将第1款和第6款合并,并取消第6款关于直线基线的规定,同时建议加一条关于历史性海湾的界定以及沿岸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历史性海湾的规定,但该建议未被采纳。最终通过的《公约》关于领海宽度的第3条规定:“每一国有权确定其领海宽度,直至从按照本公约确定的基线量起不超过12海里的界限为止。”关于历史性海湾的第10条第1款规定:本条仅涉及沿岸国属于一国的海湾;第6款规定:上述规定不适用于所谓历史性海湾,也不适用于采用第7条所规定的直线基线法的任何情形。因此,虽然《公约》没有明确规定“历史性水域权利主张不应包括陆地领土”,但会议谈判过程表明,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对历史性水域的历史性所有权不应适用于陆地领土。
从《公约》第298条第1款(a)项规定看,一国可以书面声明的方式将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排除适用公约规定的强制程序。当然,公约生效之后发生的这种争端,经争端当事方请求,应提交公约规定的强制调解程序。但是,如果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争端“必然涉及同时审议与大陆或岛屿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有关的任何尚未解决的争端”,就不应提交这一程序。因此,如果按照仲裁庭的意见,历史性所有权包括对陆地的历史性主权,那么,该款后半部分不应多此一举,仍然规定“……与大陆或岛屿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有关的任何尚未解决的争端”,不应提交这一程序。实际上,仲裁庭在这一问题上是前后矛盾的,例如,仲裁庭指出:公约起草者知道这一用法,因此《公约》第298条提到的历史性所有权是指基于历史性理由对海域的主权主张;这与《公约》其他地方唯一直接提到该术语的第15条是一致的,即历史性主权对领海划界的影响。
总之,历史性所有权仅是对海域的领土主权,不能是对陆地领土的历史性主权。在这一点上,仲裁庭的裁决显然与有关历史性权利的习惯法规则不符。
二、仲裁庭推断的中国南海权利主张:是非专属历史性权利吗?
关于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性质、含义,仲裁庭推断中国对超出《公约》允许海域外的“九段线”内海域的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提出了专属历史性权利主张,并将这种权利主张定性为非专属历史性权利。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仲裁庭对中国南海权利主张性质、含义的推断是有疑问的,将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定性为非专属历史性权利是根本错误的。
(一)仲裁庭对中国南海权利主张性质、含义的推断
2006年8月25日,中国援引《公约》第298条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声明,对于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等争端,不接受《公約》规定的导致有拘束力的强制程序。在《管辖权和可受理性裁决》中,仲裁庭裁决菲律宾诉求1、2不涉及海洋划界争端。接下来,仲裁庭着重考虑菲律宾第1、2项诉求是否属于“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从而排除仲裁庭对菲律宾诉求1、2的管辖权。在阐明了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含义后,仲裁庭试图查明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主张的性质、含义。
仲裁庭认为,尽管中国从未明确其主张的历史性权利的性质或范围,也未曾明确其对九段线含义的理解,然而,根据“九段线”的演变过程,中国2009年5月7日、2011年4月14日照会,外交部发言人一系列表态,可以确定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性质、含义,即中国明确将“九段线”与其声称的“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主张联系在一起。并且,根据中海油《2012年中国海域部分对外开发区块公告》、中国对菲律宾位油气区块招标的反对和交涉,以及中国“关于南海海域伏季休渔的通告”等国家实践、行为,仲裁庭认为,中国的确对超出《公约》允许海域范围外的整个“九段线”内海域、海床和海底的油气资源和渔业资源提出了权利主张。同时,基于中国明确声明尊重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中国1996年公布了围绕海南岛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仲裁庭推断中国没有将“九段线”内海域视为领海或内水。
仲裁庭得出结论说:中国以历史性权利为根据对超出《公约》允许海域范围外的“九段线”内海域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提出了权利主张,但不认为那些水域是其领海或内水的一部分。@根据对《公约》第298条“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含义的解释,仲裁庭认为,中国对南海水域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不是《公约》第298条规定的“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因此裁决对菲律宾诉求1、2有管辖权。
裁决对菲律宾第1、2项诉求有管辖权后,仲裁庭转向处理这些诉求涉及的实体问题。仲裁庭认为,《公约》规定了——并且限定了——一个能够将海域或海床任何部分主张为国家管辖海域的全面海域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超出《公约》允许范围外的“九段线”内海域生物和非生物资源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性权利不符合《公约》。
关于菲律宾提出的中国南海权利主张没有满足历史性权利的标准问题,仲裁庭认为:历史性权利的形成过程,《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历史性水域法律制度》做了较好梳理,即要求提出权利主张的国家连续行使其声称的权力以及其他受影响国家的默认;尽管研究报告讨论了对历史性水域主权的权利形成过程,但是,历史性水域仅仅是历史性权利的一种形式,该过程与对不及主权的权利主张是一样的。仲裁庭进一步分析说,就中国对超出《公约》允许海域范围外的“九段线”内海域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历史性权利而言,中国历史上在南海的航行和贸易以及在领海外的捕鱼,代表着行使公海自由。二战前,对领海外海床的使用也是任何国家的自由,尽管作为一个实践问题,有效使用的技术能力只是近年来才出现的。因此,为了确立对“九段线”内海域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历史性权利,有必要表明中国从事了背离公海自由的活动,并且其他国家默认了这一权利。实践中,为了确立中国对超出《公约》允许海域范围外的“九段线”内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专属性历史性权利,必须证明中国历史上寻求禁止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国民开发这些资源,并且这些国家默认这种禁止或限制。在仲裁庭看来,这种权利主张不能得到支持: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历史上曾在领海外管理或控制南海捕鱼。对于海床,仲裁庭没有看到能够被限制或控制的任何历史性活动,相应地,不存在历史性权利的根据。1996年《公约》生效后的几年里,中国也没有取得超出《公约》允许海域范围外的权利或管辖权。《公约》通过以来,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4条提到了历史性权利,但是没有明确这种权利的任何内容,使其他国家知悉所主张的权利的性质或范围。对“九段线”内海域主张权利的范围随着中国2009年5月7日照会才开始逐渐明确。自那时起,中国的权利主张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反对,不存在默认。固仲裁庭裁决:《公约》规定中国、菲律宾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不得超出《公约》规定的国家管辖海域范围;中国对超出《公约》允许海域范围外的“九段线”内海域的历史性权利或其他主权权利或管辖权在超出《公约》规定的中国海洋权利的地理和实体限制的意义上没有法律效力。
(二)仲裁庭对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性质、含义的推断值得商榷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采取了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严正立场,只是通过庭外法理斗争,从法理上阐明仲裁庭没有管辖权,没有就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所涉及的实体问题发表意见,也没有对菲律宾诉状、陈述中有关中国“九段线”权利主张的推断作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庭以菲律宾对中国“九段线”权利主张的解读、与中国有关的行为和事实为依据,对中国“九段线”权利主张进行推断,断言中国以历史性权利为根据对超出《公约》允许海域范围外的“九段线”内海域生物和非生物资源提出了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但没有将上述海域主张为领海或内水。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仲裁庭对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推断是有瑕疵的。
1.仲裁庭推断中国南海权利主张性质、含义所依据的事实值得商榷。
菲律宾、仲裁庭均根据中国2009年5月7日照会推断中国对超出《公约》允许海域范围外的“九段线”内海域生物和非生物资源提出了历史性权利。实际上,学术界在解读这份照会时并非没有不同看法。例如,叶强、蒋宗强认为,1948年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时,中国对所有岛型地物主张主权,而不是海洋管辖权;中国2009年照会的措辞表明它符合《公约》:“根据现代海洋法,中国基于领土主权对某些海域享有海域管辖权。这就是中国对南海诸岛主张主权、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主张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原因。”
另外,就拿仲裁庭援引的三项事实和行为来说,如果说中国农业部休渔令、中国外交部与菲律宾的交涉能让仲裁庭作出上述推断的话,那么作为国有企业的中海油发布的中国海域部分对外开发区块公告,能否作为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国家实践,令人存疑。
2.关于“九段线”的性质、含义,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存在争论。
关于“九段线”的性质、含义,主要有四种观点:岛屿归属线说、海上疆界线说、历史性水域说和历史性权利说。共同点是均认为中国对“九段线”内的所有岛、礁、沙、滩等及其附近海域享有主权,不同点是对于“九段线”内海域的法律地位存在着存在分歧:海上疆界线说认为线内海域是中国内水;历史性水域说认为线内海域为中国领海或内水,但没有区分“九段线”内哪些海域是内水,哪些海域是领海;历史性权利说认为中国对线内海域享有历史性权利。多数学者赞同历史性权利线说。但究竟有哪些历史性权利,学术界仍存在着不同意见。
例如,邹克渊教授先后发表3篇有关中国“九段线”历史性权利的文章。他在2000年的文章中认为:“断续线的法律概念和含义仍然存在争议,但是一般认为该线表明对线内岛屿的所有权,当然,术语‘历史性权利可能意味着多于此。”在2001年的文章中,他认为:1998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4条可以解释为意指中国主张历史性权利的某些海域超过了200海里范围;中国的权利主张是一种“具有温和性主权的历史性权利”,包括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之外海域的主权权利,即为开发该区域自然资源的目的是专属性的,但不及完全主权。在2012年的文章中,他认为,2009年5月7日照会表明“……中国官方第一次使用u型线捍卫其南海的权利主张。”并且将该线与1998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4条联系起来,指出:“一般认为该节与中国对u型线内南海海域的权利主张有关。然而,没有使用术语‘历史性水域,中国机智地选择更为灵活的术语‘历史性权利。这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即其历史性权利主张等同于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不同于主权”。李金明、李德霞认为:“1998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没有解释术语历史性权利的精确含义,但我们可以想象它与南海断续线内海域的历史性权利有关。”洪农研究员主张,中国在“九段线”内的历史性权利是捕鱼权、航行权以及资源开发的优先权,不是主权。在高之国法官和贾兵兵教授看来,“除公约赋予的那些权利之外,根据《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4条,中国在‘九段线内对捕鱼、航行以及勘探和开发资源可以主张历史性权利。”贾宇研究员认为,中国琼州海峡、南海诸岛附近和群岛内的水域是中国的历史性水域,中国享有历史性所有权;南海成为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或将所涉区域的渔业资源置于其专属性的主权权利之下,或者当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些群岛国适用群岛制度将所涉海域变为群岛水域时,中国在群岛水域内享有历史性捕鱼权;基于历史上的航行活动而取得的历史性航行权,以及根据《公约》的航行制度,例如穿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群岛国的群岛水域的航行权、穿越马六甲海峡等过境通行权,都属于中国应该享有的历史性航行权;“与其说南海断续线代表了——除其他外——中国在南海的大陆架及对大陆架非生物资源的权利,不如说这种权利直接来源于《公约》。作为缔约国,中国在南海的大陆架及相关权利是《公约》赋予缔约国的权利。”金永明研究员认为,中国南海断续线是岛屿归属及资源管辖线,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分为两类:基于海洋法制度下的水域和历史性权利下的特殊水域,中国在基于历史性权利下的特殊水域中享有各种优先权:对其中海洋的各种资源进行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之优先权利;保护与保全环境之优先权利;科学研究之优先权利;航海、航空交通管制的权利,甚至管制周边国家相关航行活动。同时,他也意识到,由于一直以来中国政府未对断续线内水域的某些权利(例如,航海、航空管制权)予以管制,将会是争议的焦点。笔者主张,中国对“九段线”内那些距离较近、密切相关、可视为一个整体的群岛或列岛间的水域享有历史性所有权,这些水域是中国的历史性水域,是中国的内水,中国有权用划定连接这些群岛或列岛最外缘各岛和各干礁的最外缘各点的直线基线作为领海基线;当“九段线”内海域与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重叠时,中国在上述海域享有历史性捕鱼权。
在南海问题上,台湾地区与大陆具有共同的历史根据——U型线或南海断续线、“九段线”。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在讨论制定海洋法时,对u型线的法律性质曾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应将u型线内水域主张为中国的历史性水域;另一种观点认为,u型线画得很随意,缺乏坐标,不可能在海上定位,很难确定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但起草的“中华民国领海和毗连区法草案”第3条最终规定,断续线内水域为中国“历史性水域”。1993年3月10日《南海政策纲领》强调,“南海历史性水域界限内的海域是中华民国管辖下的海域,中华民国拥有海域内的所有权益。”将u型线内水域主张为历史性水域,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俞宽赐、孙建明、宋燕辉、俞剑鸿等学者认为,主张历史性水域的国家,必须对所涉水域长期、有效行使权力、有效管辖,并且得到其他国家的默认;历史性水域是权利主张国的内水或领海。并且认为,中国1948年以来没有将u型线内海域作为内水或领海行使国家权力,因此不能将其主张为历史性水域。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放弃了原先将u型线内海域主张为历史性水域的观点,在“立法院”二读时删除了“历史性水域”的规定。1998年1月21日“中华民国领海和毗连区法”没有关于u形线内水域为历史性水域的规定。与此同时,多数台湾学者将历史性水域等同于历史性权利,因此,也不认为中国对u型线内水域享有历史性权利。在一份1999年“外交部”声明中,台湾当局抗议菲律宾占领南沙群岛中的榆亚暗沙(InvestigatorShoal)、簸箕礁(Erica Reef)、将黄岩岛划在菲律宾领土地图内,并且提到南海是“中华民国的水域(abody of wat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但从2009年开始特别是近年来,台湾当局的有关声明逐渐符合《公约》,例如,针对马来西亚、越南联合外大陆架划界案,台湾当局2009年的声明对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及其周围水域(surrounding waters)及其海床和底土主张权利。当然,这取决于对“周围海域”的解释。2014年以来,美国要求台湾当局澄清或放弃断续线,遭到了台湾学者、媒体的反对和谴责。尽管如此,台湾当局只是重申其对南海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島和东沙群岛及其周围水域(surrounding waters)的权利主张。换句话说,尽管台湾当局没有放弃断续线,但也没有重申该线。在解释“周围水域”时,逐渐解读为是对符合《公约》海域的权利主张。在2014年9月1日的“中华民国南海领土南海史料展”上,马英九在致辞时表示:第一,1947年宣布“南海诸岛位置图”时,除领海外,尚未有其他海域主张与概念,暗含是对线内岛礁而不是对其中水域的权利主张;第二,关于南海的海洋权利,遵守陆地统治海洋原则,即海域权利主张必须源于陆地。在罗伯特看来,马英九致辞以及11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以更加明确符合《公约》的方式阐明台湾当局的南海权利主张。早在民进党上台前,民进党政策执行主任、“驻美代表”吴钊燮扬言,台湾应该表明:在根据太平岛所有权确定领土权利主张时遵守《公约》特别是第121条,坚持航行自由原则。固实际上,民进党上台后,并没有如之前预料的,明确将领土权利主张限于实际控制的岛屿、放弃断续线。但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后,蔡英文当局表示仲裁裁决完全无法接受,其结果没有法律拘束力,并宣称:“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主权属中华民国所有,中华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相关海域享有国际法及海洋法上的权利。”可以看出,台湾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经历了变化。上世纪90年代,台湾当局除对南海诸岛主张主权外,曾试图将断续线内水域主张为历史性水域,学术界研究发现,中国没有将断续线内海域作为内水或领海行使国家权力,不符合历史性水域的要件,致使台湾当局最终放弃了将断续线内水域主张为历史性水域,但我国台湾地区某些学者将历史性水域等同于历史性权利,实际上也不再提出历史性权利主张了。2009年以来,在美国要求台湾当局澄清、放弃断续线以及南海仲裁案的背景下,台湾当局强调断续线是对线内岛礁而不是对其中水域的权利主张,开始逐渐按照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阐明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
从国际上看,对“九段线”的性质、含义也存在着不同看法。例如,针对马来西亚和越南联合外大陆架划界案、越南单独外大陆架划界案,中国政府2009年5月7日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声明和标注“九段线”的地图。此后,越、菲、印尼等国多次在联合国、东盟等国际场合,以外交照会、大会发言等方式,否定或反对中国的“九段线”权利主张。2011年6月20日,新加坡外交部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澄清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范围,并强调新加坡作为主要贸易国,对可能影响南海航行自由的事件都极为关注。2014年2月5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作证时敦促中国“澄清或调整九段线权利主张以便使之符合国际海洋法。”国外一些学者,如巴里维恩、哈西姆加拉尔等认为,中国“九段线”权利主张不符合国际法,另一些学者,如许通美认为,中国的主权主张不明确,如果南海断续线是岛屿归属线就同《公约》一致,否则违反《公约》。弗洛里、皮埃尔、罗伯特等认为,从地图本身、标注背景、中国国家实践、官方和学者表述看,中国的“九段线”权利主张存在着诸多模糊之处。美国在《海洋界限——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中认为,中国“断续线”权利主张有三种可能解释:对线内岛屿的主权主张;国界线,即意在表明中国与邻国的海上边界;历史性权利主张,即将断续线内的水域视为中国的“历史性水域”或者对其享有“历史性权利”。美国断言:“除非中国澄清:断续线权利主张仅仅是对线内岛屿以及这些陆地按照体现在《公约》中的国际海洋法产生的国家管辖海域的权利主张,否则,中国的断续线权利主张不符合国际海洋法。”
可以看出,仲裁庭无视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国内对“九段线”权利主张的不同观点,国际社会对“九段线”性质、含义各种可能的研究结论,仅凭菲律宾的解读和中国极为有限的国家实践,断定中国对超出《公约》允许海域范围外的“九段线”内海域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提出了专属性权利主张,其推论难以令人信服。实际上,仲裁庭在这一问题上也是心虚的:一方面,仲裁庭意识到“中国从未明确阐明其主张的历史性权利的性质或范围,也从未阐明其对‘九段线含义的理解。”又如,“当事双方的争端是否涉及到历史性所有权,这首先取决于中国对南海的权利主张的性质,其次取决于例外的范围;应该由中国来确定其海洋权利主张的范围。”另一方面,它对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推断并不十分肯定:“实践中,为了确立对‘九段线内海域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专属历史性权利(the exclusive historic rights),即中国目前似乎主张的……”因此,仲裁庭对中国“九段线”权利主张的性质、含义的推断,是否准确,是有待验证的。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九段线”权利主张并非如仲裁庭推断的,那将意味着菲律宾虚构了中菲南海历史性权利争端,仲裁庭只是对假设性中菲南海争端作出了裁决。
(三)即使按照仲裁庭对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推断,这种权利也不是非专属历史性权利
笼统地说,国际法中的历史性权利是指国家对某些海域的权利,这种权利既可以是领土主权,被称为历史性所有权,也可以是非领土主权性质的权利,被称为非专属历史性权利。历史性所有权源于沿海国对某些沿海水域的“远古占有”,或者以违反公海自由原则的方式对沿海海域的领土取得,历史性所有权往往作为适用编纂条约规定的一般规则的例外使国家继续享有这些权利。历史性所有权所及的水域被称为“历史性水域”,即意味着这些水域是沿海国的内水或领海的一部分,历史性水域包括历史性海湾、多国历史性海湾、邻接海岸的其他沿海水域、群岛间水域以及比国际公认的领海宽度更宽的领海水域,等等。非专属历史性权利主要包括历史性通过权和历史性捕鱼权。历史性通过权是指在内水的无害通过权,即其他国家在那些由于适用直线基线的效果使原来并未被认为是内水,但被包围在内成为内水的水域享有的无害通过权。历史性捕鱼权是某些国家根据公海自由原则在先前为公海海域,但由于沿海国扩大领海宽度、设立专属渔区或专属经济区变为国家管辖海域而取得的非专属历史性权利。历史性通过权、历史性捕鱼权均是非领土主权性质的权利,是非专属历史性权利,这种非专属历史性权利被有些学者称为逆向的历史性权利。
如上所述,根据有关行为、事实以及中国照会,仲裁庭推断中国对超出《公约》允许海域范围外的“九段线”内海域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主张专属历史性权利。在确认中国没有将“九段线”内海域主张为内水或领海后,仲裁庭裁决中国“九段线”权利主张不是历史性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庭想当然地将其推断的中国对超出《公约》允许海域范围外的“九段线”内海域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专属历史性权利定性为一种历史性权利。众所周知,国际法中的历史性权利除了包括历史性所有权这种专属历史性权利外,剩下的只有历史性通过权和历史性捕鱼权这种非专属历史性权利。在将中国“九段線”权利主张推断为专属历史性权利的同时,又将其归属为非专属历史性权利,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三、非专属历史性权利的构成要件问题
仲裁庭推断中国对超出《公约》允许海域范围外的“九段线”内海域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提出了专属历史性权利,自相矛盾地将其定性为非专属历史性权利,并进一步阐明国际法中非专属历史性权利的构成要件,然后根据这些要件来判断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有效性。
仲裁庭指出:“国际法中历史性权利的形成过程,在联合国秘书处1962年发表的《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历史性水域法律制度》做了较好梳理,要求提出权利主张的国家连续行使其声称的权力以及其他受影响国家的默认。尽管研究报告讨论了对历史性水域主权的权利形成过程(见第225段),但是,历史性水域仅仅是历史性权利的一种形式,该过程与对不及主权的权利主张是一样的。”在仲裁庭看来,非专属历史性权利即历史性通过权和历史性捕鱼权,与对历史性水域的历史性所有权的形成过程、构成要件是一样的:权利主张国长期、连续行使其声称的权力;受影响国家的默认。然而研究表明,国际法中非专属历史性权利的构成要件并非如仲裁庭所说。实际上,非专属历史性权利的形成过程、构成要件不同于历史性所有权的形成过程、构成要件。
《历史性海湾备忘录》讨论了历史性海湾的构成要素、取得历史性所有权的要件。《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历史性水域法律制度》研究表明,公法学家、国家实践、司法裁决一致认为,历史性所有权的构成要件包括:权利主张国对所涉海域长期、连续行使国家权力,形成一个常例;其他国家的默认。应当说,这两个法律文件专门讨论了对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历史性水域的历史性所有权问题,没有研究非专属历史性权利问题。那么,历史性所有权的构成要件能否适用于非专属历史性权利呢?
(一)非专属历史性权利
编纂性条约规定历史性所有权的目的,使沿海国历史上一直对海湾或其他沿海水域享有的领土主权不至于受编纂性条约规则的影响,而是作为适用编纂性条约规则的例外使沿海国继续享有领土主权。作为一种理论,这种权利被援引在其他场合: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在讨论直线基线问题时提出了历史性通过权问题;耳关合国第二次海洋法会议在讨论扩大领海宽度、设立专属渔区问题以及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在讨论专属经济区时提出了历史性捕鱼权问题,在讨论群岛国群岛水域时提出了传统捕鱼权问题。
1.历史性通过权。
在渔业案中,基于挪威领海划定制度、历史性所有权,国际法院判决挪威有权划定领海基线,基线向陆一侧水域为挪威内水。英国曾辩称,构成国际航道的那些海域应该并入领海而不是内水,外国船舶应享有无害通过权。在对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领海制度条文评述中,英国又提出了因适用直线基线而成为内水的那部分海域的无害通过权问题。国际法委员会在讨论领海制度时,也涉及这一问题,起草的《领海法(草案)》第5第3款规定:“在确定直线基线的效果使原来认为领海或公海一部分的区域包围在内成为内水,则在这些水域一直通常用于国际交通的情况下,沿海国应该承认第15条规定的无害通过这些水域的权利。”委员会认为,这一原则,“可以称为在特定种类的内水中无害通过的历史性权利原则”。最终,海洋法会议通过的《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5条第2款规定,“如果按照第4条确定直线基线的效果使原来认为领海或公海一部分的区域被包围在内成为内水,则在此项水域内应有第14条至第23条所规定的无害通过权。”《公约》第8条第2款规定,“如果按照第7条所规定的方法确定直线基线的效果使原来并未认为是内水的区域被包围在内成为内水,则在此种水域内应有本公约规定的无害通过权。”
《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公约》规定的内水无害通过权被称为历史性通过权。仔细分析历史性通过权的构成要件可以看出,国际社會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这些海域在适用直线基线制度前是领海、公海的一部分,或者并未视为内水,其他国家在这些海域享有无害通过权或公海自由,只是由于直线基线的效果才使这些海域变成了内水。在这种情况下,规定历史性通过权是对其他国家既得权的承认,当然,这种基于领海无害通过权或公海自由基础上形成的既得权是非专属性的,因此,这种历史性通过权也应该是非专属性的。
2.历史性捕鱼权。
在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讨论沿海国扩大领海宽度、领海外设立专属渔区问题时,葡萄牙、美国等国要求沿海国应尊重其他国家主要是远洋捕鱼国家在上述海域的捕鱼利益或历史性权利。在联合国第二次海洋法会议上,加拿大重申其建议,沿海国有3海里领海外加9海里专属渔区,沿海国应该尊重长期从事捕鱼活动的外国渔民的权利。在吸收新西兰提出的历史性捕鱼权在确定期限内逐步消失建议基础上,美国、加拿大相互作了让步后向会议提交了联合提案:各国可以有6海里领海,外加6海里的渔区,沿海国在渔区内享有专属捕鱼权,但1958年前5年内在12海里渔区从事捕鱼活动的国家,仍享有从1960年起10年内在该区域继续进行捕鱼的权利。古巴代表指出:“其国民已经在公海一个区域从事传统捕鱼活动的国家可以说对该海域取得了时效性权利,这些权利可能比沿海国的权利分量更重——例如,在沿海国国民没有或很少在该区域从事捕鱼活动的情况下,并且在沿海国国民捕鱼不可能影响当地鱼量或可捕量产量的情况下,这种观点更有说服力。”美国赞同在从海岸起的6至12海里之间的区域保护外国人的历史性捕鱼权,条件是外国捕鱼量不允许增加,并且增加捕鱼量专属于沿海国。加拿大反对将历史性捕鱼权永久化。哥伦比亚、波兰、南斯拉夫、挪威等国家支持加拿大建议案。澳大利亚虽然支持美国的建议案,但批评其在历史性权利框架下处理其他国家的捕鱼权问题,认为它可能对所涉权利的法律性质造成混乱,指出:“根据一般国际法,所有国家均有权在公海的某些区域内捕鱼,远洋捕鱼国家目前所行使的捕鱼权利就其性质来说曾经是并且一直是完全合法的,并且现在的有效性不取决于它们行使捕鱼权的期限。”针对海洋法会议对历史性捕鱼权问题的讨论,鲍威特指出,援引历史性权利理论和“逐步撤出期”的理由都不在法律范围之内,并且实质上“找到一个妥协的期限,以便使沿海国在不远的将来取得专属捕鱼权,与此同时,使远洋捕鱼国家对其产业作必要的调整。”然而,一些学者并不这么认为。菲茨莫里斯分析说,这些国家(常常是远洋捕鱼国家)不仅仅是在行使公海自由,而是通过其国民或船舶取得某种利益,即该海域对其捕鱼船来说应该是可继续进行的(当然是在非专属的基础上),应该得到沿海国的尊重。的确,根据公海自由原则,包括远洋捕鱼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均享有公海捕鱼自由,各国国民通过所属国也当然享有在公海上进行捕鱼的权利。那么,实践中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势,即一国国民长期以来一直在特定海域从事捕鱼活动并且它们或其所属国均无意将所涉海域据为己有,但能够在非专属的基础上对该海域的捕鱼活动具有优势地位,甚至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而其他国家的渔民也常常尊重该国国民在该海域的优势地位甚至垄断。既然如此,可以说其所属国通过其国民对所涉海域的渔业资源形成了既得权,即这些区域的渔业资源对该国来说应该是继续可得到的。应该指出的是,这种通过其国民取得的历史性捕鱼权是非专属意义上的权利,不是领土主权。因此,应该承认这些国家的历史性捕鱼权。
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确立的专属经济区制度是对专属渔区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既然如此,国际社会在解决由于沿海国扩大领海宽度或在领海以外设立专属渔区而产生的历史性捕鱼权问题也应该为新确立的专属经济区法律制度所借鉴。虽然《公约》规定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生物资源享有主权权利,但这种权利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限制,即沿海国应决定其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可捕量及其捕捞能力,在没有能力捕捞全部可捕量的情形下应通过协定或其他安排准许其他国家,包括其国民惯常在专属经济区捕鱼的国家捕捞可捕量的剩余部分。可以看出,历史性捕鱼权在专属经济区中的法律地位已经不同于其在专属渔区中的法律地位:①法律性质不同:沿海国在扩大领海宽度或设立专属渔区时,一般承认其他国家的历史性捕鱼权,并对这种历史性捕鱼权作出某种安排,如享有历史性捕鱼权的国家在一定期限、海域内继续享有这种捕鱼权;在专属经济区制度下,历史性捕鱼权已经不再被承认为一种权利,只是在沿海国没有能力捕捞可捕量的情况下,才考虑许可其国民惯常在专属经济区捕鱼的国家(包括其他国家)继续在该海域内捕鱼,换句话说,只是考虑因素之一。②法律根据不同:在专属渔区或沿海国扩大了的领海内,其他国家从事捕鱼活动的法律根据是历史性捕鱼权;在专属经济区中,其他国家继续在该海域内捕鱼的法律根据是沿海国与这些国家签订的协定或其他安排以及沿海国依公约所承担的“……促进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最适度利用的目的”的义务。③援引历史性捕鱼权的国家、条件不同:在专属渔区或扩大了的领海内,不管可捕量如何,援引历史性捕鱼权的国家均有权参与捕鱼;在专属经济区法律制度下,只有沿海国没有能力捕捞全部可捕量、存在可捕量剩余部分的情况下,其国民惯常在专属经济区内捕鱼的国家才能参与捕鱼,而且其他国家,如区域的生物资源对其有重要性的国家、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该分区域或区域内发展中国家及曾对研究和测定种群做过大量工作的国家,都可以参与沿海国专属经济区捕鱼。总之,根据《公约》,在专属经济区制度下,历史性捕鱼权不再视为一种权利,只是沿海国在准许其他国家获得专属经济区内可捕量的剩余部分应考虑到的因素之一。
(二)非专属历史性权利的形成过程、构成要件
从历史性通过权、历史性捕鱼权等非专属历史性权利的历史背景、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可以看出,非专属历史性权利的形成过程、构成要件,并非如仲裁庭所说的与历史性所有权的形成过程、构成要件一样。就非专属历史性权利而言,这些权利原来是领海的无害通过权或者公海自由,国际社会、某些国家在行使这些权利过程中形成了既得权益,即这种无害通过权或者捕鱼自由对国际社会、某些国家来说应该是可继续享有的。因此,如果一定要说非专属历史性权利的形成过程或构成要件,至少应该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只是在海域地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提出了非专属历史性权利,例如,因使用直线基线的效果使原来并未认为是内水的区域包围在内成为内水,则在这内水中应有公约规定的无害通过权;因沿海国扩大领海宽度、设立专属渔区、专属经济区,将公海一部分变为国家管辖海域,其他国家可主张历史性捕鱼权;因群岛国划定群岛基线将一部分公海海域变为群岛水域,应承认直接相邻国家在群岛水域内某些区域内的传统捕鱼权利和其他合法活动。
第二,非专属历史性权利原来都是国际法承认的权利,是某些国家行使這些权利过程中在非专属基础上形成的,不是领土主权,是非专属性权利。
第三,历史性所有权是沿海国向国际社会主张的权利,而非专属历史性权利是国际社会、某些国家向沿海国主张的权利。
因此,仲裁庭关于“行使国际法允许的自由不能产生一个历史性权利”“历史上在领海外航行和捕鱼不足以构成历史性权利产生的基础”等论断是错误的。实际上,正是中国在南海海域特别是“九段线”内“更为频繁的捕鱼活动的证据”,才使在“九段线”内海域与其他南海周边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重叠时,中国有权在上述海域主张历史性捕鱼权。
总之,仲裁庭推断中国对超出《公约》允许海域外的“九段线”内海域生物和非生物资源主张专属性权利,这种权利主张不是国际法中的非专属历史性权利。按照仲裁庭的裁决,中国通过2009年照会才开始明确对“九段线”内海域权利主张的性质、范围,如果这样,只能按照有关单方行为的习惯国际法规则来判断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有效性,而不是按照国际法中的历史性权利判断其有效性。德根认为,国际实践和实在法一直承认国家据以取得新权利的某些单方行为。这种单方行为主要包括占有无主地、时效、历史性所有权以及《公约》规定的沿海国单方行为。按照仲裁庭对中国“九段线”权利主张的推断,这种权利主张既不是对无主地的先占、历史性所有权,也不是《公约》规定的沿海国单方行为,因此,这种权利主张的有效性只能按照时效来判断。仲裁庭将其推断的中国南海权利主张定性为非专属历史性权利,按照它想象的非专属历史性权利的要件来判断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有效性,显然是错误地适用了国际法。
四、结论
综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国际法中历史性所有权的含义是特定的,仅指沿海国对海域的领土主权,所及的水域被称为历史性水域,是沿海国的内水或领海;历史性所有权不能用于指对陆地的领土主权。
第二,仲裁庭推断中国对超出《公约》允许海域外的“九段线”内海域的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提出了专属性权利,其推断值得商榷,毕竟中国尚未明确其南海权利主张的性质、含义。
第三,仲裁庭将其推断的中国南海权利主张定性为非专属历史性权利是错误的,按照非专属历史性要件判断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有效性,错误地适用了国际法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