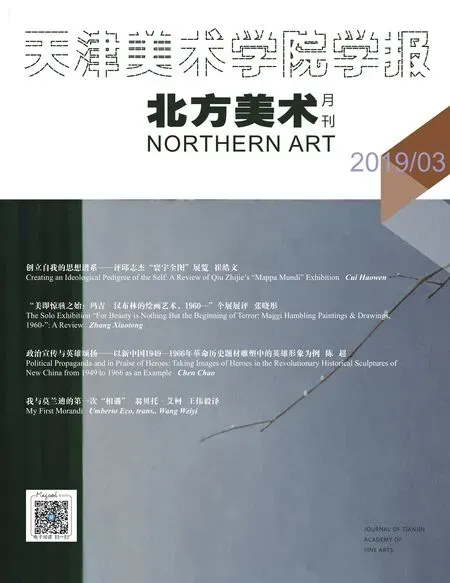北朝佛教刻经隶书的意义与影响
2019-06-14段为民DuanWeimin
段为民/Duan Weimin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佛教文化的传播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佛教刻经就是其中一种非常典型、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传播形式。这种形式把佛教经典教义同中国的刻石文化结合在一起,加以中国书法的独特的审美效果,使得佛教刻经在中国书法史、中国佛教文化史上都有特殊的意义。
一、北朝佛教刻经隶书的意义
北朝佛教刻经隶书书法,采以特殊的载体——刻石,成功地融篆、隶、楷三法于一体,加上其所依托的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共同融汇成个性鲜明的北朝佛教刻经隶书,成为书史上绝无仅有的书法形式。
北朝时期,特别是北魏时期,魏碑书几乎独擅天下,隶书、篆书等都非常衰落。从艺术角度看,这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因而北魏时期,就有人尝试突破魏碑的单一笔法一统天下的局面。《郑文公碑》是其中非常成功的作品,包世臣赞其“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也”。[1]《郑文公碑》的融合是以魏书为本,参以“篆势、分韵”,而北朝刻经隶书则是以隶书为根基,结体采用隶书的纵势,表现出一种宽博之气;笔法上则以篆书的含蓄圆浑为主,辅以隶书特别是像《石门颂》一类隶书的灵动。赖非先生说:“它们的书者能在不违背隶楷转变总规律的前提下,以隶势为基调,用篆书的行笔法,来避免笔画中虚现象,又在恰当的地方揉进楷书的起收笔法,对那些飘而不实的笔画进行了根本性改造,将滑向低谷的隶书重塑成一种新的形象。”[2]262-263
北朝泰峄山区的大字榜书刻经,堪为中国书史之宏构。北朝佛教大字刻经,尤其是以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四山摩崖等为代表的山东地区大字刻经,在大字榜书方面不仅有开拓之功,更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清代人对北朝榜书刻经不吝赞美,极为推崇,其原因在于榜书的难作。康有为说:“榜书,古曰署书,……作之与小字不同,自古为难。其难有五:一曰执笔不同,二曰运管不习,三曰立身骤变,四曰临仿难周,五曰笔毫难精。有是五者,虽有能书之人,熟精碑法,骤作榜书,多失故步,盖其势也。”[3]854(图1)[4]作榜书,不仅要有熟练的技巧,更要有一种气势,刘熙载说:“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为书。”[5]北朝刻经榜书虽字大盈尺,但是浑穆雍容,气韵高绝,“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绝”[3]855。

图1 邹城尖山刻经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蓬勃发展,书法美学得到空前的繁荣,出现了大批书法理论和批评著作,人们的审美意识更加独立发展,在创作中自觉地“寓性情、襟度、风格于其中”。佛教的广泛传播,带动了佛教刻经的巨大发展,而佛教刻经的书者,有许多出自于释门,如北朝刻经的领袖人物僧安道一,“道鉴不二,德悟一原;匪直秘相咸韬,书工尤最”[6]。这些人既通佛理,又精书法。因此,他们的审美意识之中,以书法参佛法、以佛法运书法是一种最高境界。万事万物,穷其根源,通于一理,书法与佛法又何尝不如此呢?“书法亦犹佛法,始于戒律,精于定慧,证于心源,妙于了悟,至其极也,亦非口手可传焉。”[3]846
佛教刻经书法,尤其是摩崖刻经书法,充分体现出了“佛即是字,字即是佛”。日本立正大学桐谷征一先生论及岗山刻经时说:“从山顶沿山谷而下,散布着约30余块巨石刻经,刻有《观无量寿经》和《入楞伽经》,每石多则数十字,少则仅一字。一眼望去此处如同诸佛聚会的曼陀罗(文字即佛),为修行者营造了在岩石边冥想,与诸佛同在的环境。”[7]书者凭借极大的宗教热情和超凡脱俗的艺术天赋,以超然的心态,用舒缓的用笔,写出的线条和结构与世俗习尚迥异,转折圆缓,少见方折,不露锋芒,用笔的提按顿挫,都深藏于浓厚的篆、隶之意的笔道中,舒迟伸展中倾注着超脱的澄净,凝重含蓄里呈现出虔诚的信念。结字宽博疏放,静穆平和,不入北魏藩篱,不涉险奇怪诞,似欹侧还端庄,似散逸还浑凝,似精神还冲淡,恰似得道高僧,雍容大度,器宇非凡,创造者试图表现的是博大精深的境界,给受众以精神、心灵的洗礼,“佛法之信仰,佛典之庄严,北齐信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祈祷震荡群山,直到今天仍回响在我们的心中”[8]。
二、北朝佛教刻经隶书的影响
沙孟海先生说:“北碑结体大致可以分‘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两个类型,过去也少人注意。”[9]114赖非先生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翻阅大量的出土资料,我们的印象却是,北朝早期的作品‘斜画紧结’,晚期的作品‘平画宽结’,‘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是北朝书法两个阶段的特征。”[10]
北朝刻经书法,也经历了由“斜画紧结”到“平画宽结”的阶段,由于大量的刻经是从北齐中后期开始的,所以绝大部分的刻经处于“平画宽结”的阶段,刻经书法的体势平正,布白疏朗,不同于北朝前期魏书的欹侧的体势。
这一阶段在书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上承魏晋,下启隋唐。这时出现的平正体势是向唐楷进化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唐楷无论从笔法到结体都是紧承这一阶段的,因此,在北朝书法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北朝佛教刻经书法,对后世的书法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沙孟海先生在谈到北碑对隋唐的影响时说:“《张猛龙》、《根法师》、龙门各造像是前者(斜画紧结)的代表。《吊比干文》《泰山金刚经》《唐邕写经颂》是后者(平画宽结)的代表。后者继承隶法,保留隶意。前者由于写字用右手执笔关系,自然形成。这样分系,一直影响到唐宋以后。褚遂良、颜真卿属于后者,欧阳询、黄庭坚属于前者。”[9]114论及隋代真书,他认为有四种面貌,其中,“第三,浑厚圆劲一路。从北齐《泰山金刚经》、《文殊经碑》、《隽敬碑阴》出来,以《曹植庙碑》、《章仇禹生造像》为代表,下开颜真卿”。[9]115从沙孟海先生理出的体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齐而至隋、唐的楷书发展脉络。
欧阳中石先生在分析水牛山刻经时说:“《水》(即水牛山《文殊般若经》)字的用笔及结构应该说更接近了唐楷。有人说《金》(即泰山《金刚经》)字是颜真卿字的源头,其实说《水》字与颜字似有渊源更为确切。”[11]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是碑(水牛山刻经)虽简穆,然较《龙颜》、《晖福》尚逊一筹,今所见岗山、尖山、铁山摩崖,皆此类。实开隋碑洞达爽闿之体,故《曹子建碑》亦有(水牛山)《般若经》笔意。”[3]834
到了清代,考据学盛行,也是金石学极盛的时代,金石学者精于鉴别,考证严谨认真,收集资料丰富,研究范围广泛,占北朝石刻相当数量的佛教刻经当然也是被广泛关注。这种考据学风一方面给书法家们提供了大量的新鲜的书法资料,供他们取法借鉴,另一方面,这些材料为书法家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使他们视野大开,“经过乾嘉时期金石学在研究考证、资料方面的有力支持和一批敢于标新立异的书家的实践,碑派书法兴灭继绝、遣文返质的指导思想,以俗代雅、与古为新的审美追求,以及崇尚古厚朴拙的创作原则均已形成”[12]。许多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把目光投向六朝墓志造像之属,加以碑派理论大家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极力鼓吹,寂在深谷、僻处山林、长久无人问津的北朝碑版大放异彩,北朝佛教刻经书法也备受世人瞩目。王学仲先生认为,郑板桥曾取法于北朝刻经,他说:“清代郑板桥,学书不主一家,但隐约露出黄(庭坚)书痕迹,其杂糅真、草、篆、隶,在郑未必自觉,但他在山东任县官多年,云峰及山东书僧石刻,不可能未入其目,他的独特书风,也极可能于岗山石刻中寻其仿佛。”[13]清末书家李瑞清,自称“余每作大字,则用此石(指经石峪《金刚经》)”。
自20世纪90年代起,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省书协等先后举办了三届中国北朝摩崖刻经书学讨论会,北朝佛教刻经隶书受到了越来越大的重视,它的书法价值、它的文化意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去追求、研究。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称赞“佛教徒处在理性思维的高级阶段”,“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有效的,只有东方的佛教徒和希腊人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快适应并融入东方文化中,进而对包括书画、诗文、建筑等各种艺术形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性空思想与当时的玄学文化相互融合,这种审美倾向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书法,北朝佛教刻经隶书正是融佛教文化与书法艺术于一体的典范,尤其是第二类型的隶书,它采用隶书的体势,取其宽博端庄,采用篆书的线条,取其含蓄静穆。它平淡高古,雍容恢宏 ,气息淳厚,意境清远,铁山《石颂》中赞其“精跨羲(王羲之)诞(韦诞),妙越英(张芝)繇(钟繇);如龙蟠雾,似凤腾霄”[2]113。北朝佛教刻经隶书以其特有的形象与内涵,独到而全新的表现形式与文化意义,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