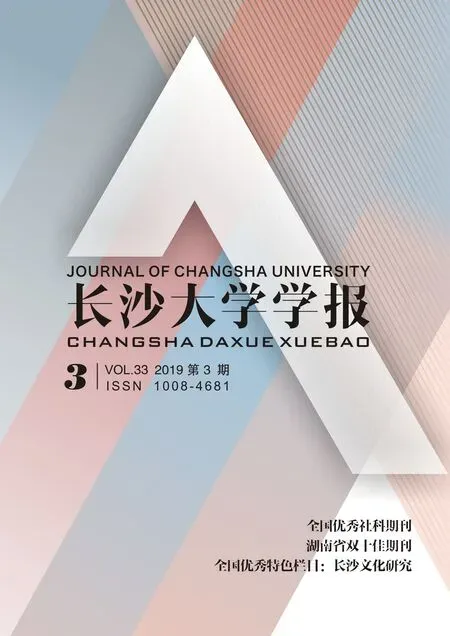名实之争:论中国古代童话的自发性
2019-05-20范丽
范 丽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湖南 长沙 410016)
中国古代虽没有童话之名,却有童话之实。在中国古代存在众多的童话作品。不过,事实上,要从众多古代文学作品中无一遗漏地、轻松地将童话作品辨别、挑拣出来,却非易事。而且,以前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中国古代有无童话之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童话具有自发性的特点,中国古代是童话的自发时代。因此,本文在试着说明中国古代存在大量童话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中国古代童话的自发性。
一 童话及童话的特征
何谓童话?在探析古代童话的自发性之前,我们需要对童话的概念有个清晰的认识。早期学者对童话的认识还比较笼统。比如孙毓修创办《童话》刊物时就认为童话是除教科书外的儿童读物,主要供儿童课外阅读,内容包括文学读物、知识读物、历史读物、科学读物等诸多内容。五四时期,周作人认为“童话最简明的界说是‘原始社会的文学’”,并将童话分为“纯正童话”(源于传说,分为根据想象来解释自然和解释人事为主的两种形式)和“游戏童话”(非源于童话而具有娱乐功用的,分为动物谈、笑话和复迭故事三类)。
这些对童话的认识都不够清晰,比较笼统。而事实上,时至今日,对童话的看法依然既具有不清晰性,又具有确定性。不清晰性表现在不同的书、不同的学者专家对童话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和界定。比如:
在《辞海》中,“童话”一词是被这样定义的:
“儿童文学的一种。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来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生活,增进儿童思想性格的成长。一般故事情节神奇曲折,内容和表现形式浅显生动,对自然物的描写常用拟人化手法,能适应儿童的接受能力。”[1]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童话”一词是这样解释的:
“儿童文学的一种体裁,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来编写的适合于儿童欣赏的故事。”[2]
蒋风在其著作《儿童文学概论》中说:
“童话是儿童文学中的一种重要的样式,也是文学中的一种特殊的样式。它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用符合儿童的想象力的奇特的情节编织成的一种富于幻想色彩的故事。”[3]
而韦苇在《韦苇与儿童文学》一书中,对童话作了如下一系列界定:
“童话是以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存在的荒诞性与真实性和谐统一的奇妙故事,是特别容易被儿童接受的,具有历史和人类共享性的文学样式之一。
童话是以‘幻象’为一岸,以‘真实’为另一岸,期间流淌着对孩子充满诱惑力的奇妙故事。
童话是一种以幻想为特征的荒诞故事来引起儿童共鸣的艺术假定。
童话是符合儿童想象方式的,富于幻想色彩的奇妙故事。
童话是以幻想滋养人类精神的故事家园。
童话是被故事逻辑所规范的童梦世界。”[4]
由吴其南主编的《儿童文学》一书,对“童话”的界定为:
“童话是一种以非生活本身形式塑造艺术形象并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其主要特点是文学性、虚拟性、儿童性。”[5]
黄云生在其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一书中则指出:
“童话,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也是儿童文学最基本最重要的体裁之一,它是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虚构故事。”[6]
陈蒲清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童话小史》中给童话的定义是:
“童话,是一种适合儿童心理特点的幻想性强的故事。这个定义揭示了童话有三个特性:一是故事性,二是幻想性,三是适合儿童心理特点。”[7]
这些对童话的解释和界定已经有很多了,但还不是全部,这足以说明童话这一概念的不清晰。有些概念一开始就将童话划定为儿童文学的一种体裁。这种概念不能说是错,却是面向现代童话的,是在有了儿童文学这一概念和学科划分后,对儿童本位有着清醒认识后才有的概念。因此,这样划定童话,童话这个概念就只能面向现代童话了。也因为在童话的概念上存在着这些不清晰性,从而也导致很多人无法从定义下手,去寻找中国古代童话,从而得出中国古代并无童话的结论。
当然,这些对童话的解释和界定,相对于孙毓修、周作人等早期学者对童话概念的模糊认定又是很清晰的,而且在不断接近本真了。事实上,透过这些不同的表述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众多定义中清晰的内涵,那就是童话概念中最实质性的东西,通过这些实质性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很好地去界定、寻找、欣赏和评判古今童话。那么,什么又是童话最实质性的东西呢。童话是要以儿童为受众的故事,而且这种故事是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这一点就可以确定童话必须是能易于被儿童接受的,适合儿童的、具有幻想性的故事。这就确定了童话需要具备的三个实质性的特点:故事性、幻想性和适合儿童心理性。这样来看,前面所提到的诸多定义中,大都切中了童话的这三个实质性的特点。不过有些表述比较诗意,比如韦苇教授的;有些表述比较繁复细致,如《辞海》;有些定义则比较通俗、简单,比如陈蒲清教授的。
二 中国古代的童话形式
中国古代有没有童话?答案是肯定的。虽说中国古代没有童话这一说,但童话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只不过这些童话在当时并不以童话的名目出现,而是混杂在各种民间故事、传奇、志怪、志人小说当中。像《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列异传》《神仙传》《齐谐记》《续齐谐记》《幽明录》《酉阳杂俎》《夷坚志》《聊斋志异》等这些书籍中,就有很多童话。陈蒲清教授早在1993年出版的《历代童话精选》一书中,就从中国古代的62种典籍中选出了120篇优秀童话。这些童话都具备童话的三大实质性特点,它们本质上就是中国古代的童话。以《叶限》为例,它其实就是中国版的《灰姑娘》故事。
《灰姑娘》先由贝洛收录进《贝洛童话》,后格林兄弟又将它收入《格林童话》中。它是一篇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经典童话。而事实上,早在我国古代的秦汉之前,就有一个与之相似的童话在民间广为流传,到唐朝的时候,段成式把这篇童话收录进了《酉阳杂俎》一书中,它就是《叶限》:
南人相传,秦汉前有洞主吴氏,土人呼为“吴洞”。娶两妻,一妻卒,有女名叶限,少慧,善淘金,父爱之。末岁,父卒,为后母所苦,常令樵险汲深。时尝得一鳞,二寸余,赪鳍金目,遂潜养于盆水。日日长,易数器,大不能受,乃投于后池中。女所得余食,辄沉以食之。女至池,鱼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复出。
其母知之,每伺之,鱼未尝见也。因诈女曰:“尔无劳乎?吾为尔新其襦。”乃易其敝衣,后令汲于他泉,计里数百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鱼,鱼即出首,因斫杀之。鱼已长丈余,膳其肉,味倍常鱼,藏其骨于郁栖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复见鱼矣,乃哭于野。忽有人发粗衣,自天而降,慰女曰:“尔无哭,尔母杀尔鱼矣!骨在粪下。尔归,可取鱼骨藏于室。所须第祈之,当随尔也。”女用其言,金玑玉食,随欲而具。
及洞节,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远,亦往,衣翠纺上衣,蹑金履。母所生女认之,谓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觉,遽反,遂遗一只履,为洞人所得。母归,但见女抱庭树眠,亦不之虑。
其洞邻海岛,岛中有国名陀汗,兵强,王数十岛,水界数千里。洞人遂货其履于陀汗国。国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减一寸。乃令一国妇人履之,竟无一称者。其轻如毛,履石无声。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锢而拷掠之,竟不知所从来。乃以履弃之于道旁,即遍历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叶限,令履之而信。叶限固以翠纺,蹑履而进,色若天人也。始具事于王,载鱼骨,与叶限俱还国。其母及女,为飞石击死。洞人哀之,埋于石坑,命曰“懊女冢”。洞人以为媒祀,求女必应。陀汗王至国,以叶限为上妇。
一年,王贪求,祈于鱼骨,宝玉无限。逾年,不复应。王乃葬鱼骨于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为际。至征卒叛时,将发以赡军。一夕,为海潮所沦。
成式旧家人李士元所说。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怪事。
这篇《叶限》故事性很强,想象奇特丰富,在主题、人物、情节安排,甚至细节处理和最后的结局等方面,都与《灰姑娘》相类似,况且,它最早记录在我国唐代的《酉阳杂俎》一书中,比最早记录在《贝洛童话》中的《灰姑娘》早了八百多年。从表1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二者的异同。

表1 《灰姑娘》与《叶限》比较
如果我们能承认《灰姑娘》是一篇不折不扣的经典童话,那《叶限》肯定也是。不只有《灰姑娘》和《叶限》相类似,清代黄之隽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而记录的《虎媪传》也与《小红帽》这个童话故事非常类似,是典型的“兽外婆”型童话故事。事实上,在中国古代还存在众多脍炙人口的童话故事,比如《白水素女》《阳羡书生》《李寄斩蛇》《千日酒》《扶余王》等,它们与《灰姑娘》相比,与欧洲的其他童话相比,毫不逊色。只是在我们古代,没有人把这些童话单独列出来,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整理,也没把它们叫作童话罢了,这也导致了一些人误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童话。
也许有人说:“中国古代童话缺乏儿童本位观念,算不得是真正的童话。”但正如王泉根在《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一书中所说:“从世界文学史的范围看,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只是在近代社会里才诞生的。”[8]西方也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才有了儿童本位观念的童话。《灰姑娘》这样的经典童话也是在有儿童本位观念之前就出现了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没有儿童本位观念,就否认《叶限》是童话,更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国古代有童话作品。
三 中国古代童话的自发性
中国古代的童话还处在童话的初级阶段,是完全自发的,它与完全自觉的现当代童话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没有专为儿童创作的、以儿童为本位的作家作品
从目前我们搜集到的古代童话作品来看,大都混杂在一些民间文学作品中,以及志怪、志人小说和传奇故事中。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志怪、志人小说和传奇故事等,它们都是专属于成人文学领域的,是提供给成人阅读的作品,而不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因而作者在创作这些古代童话作品时,也不可能考虑到儿童的需求和接受心理,做到以儿童为本位,专门为儿童去创作这些作品。但因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渗入了一些适合儿童心理特点、易于被儿童接受和喜欢的因素,使这些作品具备了童话的特点,成了儿童喜欢的童话作品。
不过,在前面已提到,没有儿童本位观,这并不是中国古代童话的专利,事实上,欧洲也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才有儿童本位观的。但正如不能因为没有儿童本位观,就否认欧洲古代没有童话一样,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古代没有童话。
(二)中国古代没有专门为儿童创作童话的作家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文学长河中,一个个名垂千古、为人称道的大作家,成就了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的辉煌。但是,众多的作家当中,我们却找不到一个专门为儿童创作童话的作家。
从古代作家的创作动机来看,中国古代的文人进行创作,无外乎以下几点动机:第一,抒情言志,表达自己的内心意愿和情感,为自己立言等。第二,给领导阶层进言、献策,并给自己谋求仕进的机会,或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或对当局进行讽刺,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失望。第三,怀才不遇,转而移情山水,寄寓鬼神等。总之,古代作家们进行创作,都是从自身出发,从成人的角度和目的需求去进行创作,而不是从照顾孩子的童心出发,去专门为孩子们写作的。偶尔有家训、家书之类的作品出现,也是本着教育后代、培养封建接班人和光耀门楣的想法和目的去写作的。带着这样的目的和想法所创作的家书、家训自然不可能成为童话。虽说偶尔有些作家从成人的角度和目的出发,写出了孩子们喜爱的童话,但那都是不自觉创作的。而且这些童话,也基本上只是作家众多作品中的一两篇而已。所以,在中国古代,是没有专门为儿童创作童话作品的作家的。
(三)没有专门针对童话创作和批评的理论著作
中国古代有众多的文学批评理论及著作,在郭绍虞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中选入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论文(含论诗诗)就有55种,其中先秦5种,两汉4种,魏晋南北朝5种,唐8种,宋10种,金1种,元2种,明9种,清11种。比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叶燮的《原诗》、刘熙载的《艺概》……这些文学批评理论著作对中国古代出现的各种诗、文、赋等文学体裁及各种文学现象以及文学批评本身都有批评。然而,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童话理论批评却久久未能真正地生长发育起来。虽历史上有过关于童谣来源的“荧惑星说”,有李贽的关于创作的“童心说”,但这些都不是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去进行思考和批评的,更不是针对童话创作去进行批评的。在我国古代,找不到专门针对童话创作和批评的理论著作。
(四)作品的呈现形式不利于儿童阅读
文言文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写作方式,它作为古代文学流传的主导方式,也就决定了那些接受教育很少,理解能力和知识水平有限的儿童群体是不可能读懂或完全读懂那些文言作品的了。虽然古代也有一些“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作品,但相对于儿童那有限的知识水平和欣赏层次,这样的作品也大都只能束之高阁,拱手让给成人去品味了。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绝大部分儿童是文盲,他们根本无法接受学校教育和基本的文字教育,这样,他们根本不可能看懂那些文言文作品了。因而这些作品也没法广泛地被儿童接受并在儿童群体中大量流传。听成人讲故事是儿童知晓并接受它们的主要方式。夜间,围炉夜坐或在星空下纳凉,或大人忙活的间隙,听大人“讲古”是儿童接受这些作品教育的最常见的场景。古书中也有不少有关这种场景的记载。这种传授方式一方面受限于大人所知晓的故事的多寡,同时也受制于他们的说话水平和思想观念。因而能传授的故事是相当有限的,而儿童能从中听到的真正的童话故事就更不多了。
(五)没有让作家自觉创作童话的时代土壤
我国古代,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伦理教育是建立在忠孝仁义的基础上的,是必须绝对服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伦理的。这种封建教育,一方面是父辈的无上权威,以致“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另一方面,这种教育也绝不可能以理解、尊重儿童的心理特点、精神个性和独立人格为出发点,恰恰相反,是以损坏儿童的独立人格为代价的。在“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桎梏下,儿童是只可能处在被漠视、被支配、被要求绝对服从权威的地位的。而对他们的教育,更是把他们当作“小大人”来看,用成人的方法和知识来对他们进行灌输,从而培养出他们心目中所期待的“顺民或忠臣孝子”。在这种封建教育大背景下,儿童的精神特点和独立人格是完全不被尊重和理解更谈不上重视的。当然,在这种封建土壤中,也不可能有作家作品是在以儿童为本位的前提下去专为儿童创作的。这种封建的时代土壤,一方面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童话自发性的一个特征和表现,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是导致中国古代童话一直处于自发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童话的这些自发性特征,也导致古代童话中夹杂着一些不利于儿童阅读的因素,比如大多数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是让孩子感到比较害怕的精怪和鬼魅,一些故事情节也比较血腥、恐怖,在一些故事中还宣扬了因果报应、成仙得道、门第尊卑观念等众多封建思想。这些都是创作者从成人的角度出发创作并受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影响的结果。不过,虽说夹杂了这些不利于儿童阅读的因素,整体来说,中国古代的童话,童话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根据童话的本质特征,我们去检视、去整理那些古代文学作品,便能从各个时期的作品中挑出大量童话来。
总之,正因为中国古代童话的创作有以上诸多自发性特点,因而可以断定中国古代处于童话创作的初级阶段,童话的自发性特征相当明显。也正因为中国古代童话具有这么明显的自发性特征,从而导致众多童话作品没有得到流传和好好保存。这些古代童话与现当代处于自觉时代的童话创作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在很长时间内,现当代的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童话,当然也就很少有当代学者对中国古代童话去进行研究和评判了。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童话,犹如一座尚未被完全发现并开发利用的童话宝库,它期待着我们去关注它、研究它、开发它、利用它。我国当代早期的童话作家,有过从我国古代童话中吸取营养的经验,像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葛翠琳的《野葡萄》、洪汛涛的《神笔马良》都是脱胎于中国古代童话的优秀之作。而从2003年底开始儿童文学创作的汤汤,则以一系列带有浓郁古代童话气息的鬼童话,让儿童文学界惊艳。还有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她的新作《南村传奇》更是融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故事于一炉,通过舍身石、少年和蟒蛇、狐狸女婿及花神丁婆婆的美丽幻想故事,描绘了一个桃花源式的美好家园。相信,在这些作品的带动下,在不断发现并挖掘中国古代童话宝库的形势下,这样充分从中国古代童话甚至整个古典文学的宝库中吸取营养的上乘之作,将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