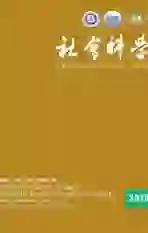中国古礼的象类原则与象征思维
2019-05-15曹建墩
摘要:中国古礼是一完整的表意体系或象征体系,礼乐文化通过象征建构了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则与价值规范。比象天地阴阳五行的象类原则是建构礼仪制度的重要方式,它为古礼的正当性赋予了神圣的终极依据。古人对于礼乐象征意义的诠释,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将礼乐与人的诚敬、仁爱之情及伦理道德相联系,礼乐符号成为仁爱之情与“德”、“政”的象征,由此形成“以象比德”、“礼以象政”的诠释模式。礼乐符号的深层象征意义构成了中国古礼的精神传统。古礼的象征思维方式对古代中国的政教方式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礼;象类;神圣性;德;象征
中图分类号:K892.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9)05-0163-09
作者简介:曹建墩,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开封475001)
导言
中国古礼是借助礼物与仪式表征意义的符号体系。传统礼学认为,礼有本有文,文乃是为表示意义而制作的符号体系,一般称为“礼数”、“礼文”等,均属于“象”的范畴;本乃是礼的本质规定,指礼乐符号的象征意义,一般称为“礼义”。清代王夫之说:“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①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指出,在仪式中,情绪和动机与形而上的概念缠绕在一起,它们形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②。礼是以象喻义的完整表意系统③。礼仪是人们表达情感、人生观、价值观的一种重要符号,也是社会的表象或象征模式,因此礼仪是认识一个民族精神意识最好的文本。
一、礼仪的神圣来源:古礼的象类原则
礼是依据一定原则建构出的文化系统,其中象类原则是一项重要原则。“象类”一词,首见于《左传》。《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雷震电曜,天之威也。圣人作刑戮以象类之。”雷震电闪是天发威之象,令人震恐,圣人于是效法比拟这些天象制作刑罚诛戮,以威慑犯人。古人将这种比拟方式称为“象类”,它包含有:一是对天地万物之象的模拟,二是用以类比类的类比推理方式来行事。“象类”或称为“比象”。《国语·周语中》:“服物昭庸,采饰显明,文章比象。”韦昭注:“比象,比文以象山龙华虫之属也。”《左传·桓公二年》:“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杜预注:“车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虚设。”所谓“不虚设”,指礼象有形而上的天道依据。
象类原则体现在古礼的方方面面。譬如周代郊祀中很多是以象类原则来建构礼仪制度。《周礼·春官·大司乐》载,祭天礼仪于冬至日在南郊圜丘举行:圜丘祭天,效法天之圆;冬至日,取象于阳气生。《礼记·郊特牲》:“兆于南郊,就阳位也。”南郊为阳位,天为阳,于是遵循象类原则就阳位祭祀天阳。此外,祭天用的玉币、牲牢、尊俎、乐舞、车旗之属,亦各以象类。《礼记·郊特牲》说:“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乘素车,贵其质也。旂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天子身穿的衮衣上绘有日月星辰,旌旂上画龙为章兼设日月,是比拟天象;天子首所戴衮冕有璪十二旒,所建之旂十二旒,都是比象天道的十二时辰和十二月;乘素车,“扫地之象”,象天之质朴;祭天时“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总之,郊祀祭天遵循法则天象的象类原则。
在祭祀中,鬼神形象、所用祭牲与玉器也遵循五行象类原则。《国语·晋语二》载:“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西方为白色之象,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西方神蓐收的颜色和其所主方位亦有神秘的象类性。《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周代藏冰之礼曰:“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北方对应黑色,五行为水,北方神为玄冥司寒,故据象类原则,藏冰时用黑公羊和黑黍祭祀司寒神。《周礼·地官·牧人》载祭祀用牲:“凡阳祀,用骍牲毛之。阴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无论阳祀、阴祀、望祀,牺牲必须是纯色,望祀时牲色与方色象类。《周礼·春官·大宗伯》载祭祀所用玉器:“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各方所用玉器的玉色与方色象类,各象五行。
古礼中,空间位序也遵循象类原则。在《仪礼》乡饮酒礼中,设有主、宾与介,也具有象征意义。《礼记·乡饮酒义》阐发道:“饮酒之义,立宾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设介僎以象日月,立三宾以象三光。古之制礼也,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四面之坐,象四时也”。主宾之位在堂上尊位户牖之间,主人位在阼阶上,体现出对宾的尊敬。而《礼记》不仅将宾主等人的位置与天地、日月、三光对应,而且将其座位与四时相互对应,属于典型的以人事比擬天道的象类思维。
以象类原则建构礼仪制度,数字是一重要的环节。宋人蔡沈指出:“欲知礼不可以不知数,数者,礼之序也,分于至微,等于至著,圣人之道,知序则几矣。”蔡沈:《洪范皇极内篇》卷一,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9页。在古礼体系中,各级贵族的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礼器等使用都有规定的礼数,《左传·庄公十八年》云:“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礼数成为等级链条中各级贵族“名位”的象征符号,它实质上是运用数字序列使政治等级结构序列化,所谓“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大戴礼记·朝事》)。另一方面,礼乐体系中的数字具有沟通天地人的神秘功能与象征意义。如数字“三”“六”“十二”,《国语·周语下》说乐律“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即使用这类数字乃遵循天道之举。古礼中有“礼成于三”的原则,譬如礼仪行为有三让、三揖、三辞(《大戴礼记·朝事》);丧礼有三年之丧;卜蓍有不过三次的规定(《礼记·曲礼上》);礼有“天地君亲师”三本(《荀子·礼论》),等等。三的意义,《史记·律书》谓:“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礼记·三年问》云:“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则于人。”使用三应来源于对天、地、人三才的比象。另,《周礼》非常崇尚数字六。例如:天子之礼相配以六为数,有六方、六色、六玉等(《周礼·春官·大宗伯》);祭祀有六牲,膳食有六牲、六畜、六兽、六禽(《周礼·天官·冢宰》);饮食方面,王馈食用六谷,饮用六清(《周礼·天官·冢宰》);巫术方面,占卜有六龟(天龟、地龟、东龟、西龟、南龟、北龟)。六,取象于天地四方,这些实是比象天地四方、阴阳五行构建的系统彭林:《周礼的主体思想与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63页。。至于数字十二,古礼中使用它象征十二月,如《礼记·深衣》载周代深衣“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左传·哀公七年》说:“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天数以十二为大,为不可逾越之数,故多为周天子使用的礼数。
古人推天道以明人道,古礼的象类原则中,主要是以天地之象为比拟效法的对象。古人认为礼源于天地之道,如《礼记·礼运》曰:“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东周时期,阴阳五行思想渗透进礼仪制度,阴阳五行成为象类原则的重要理论基础。《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夫禮,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礼是建立在天地之道基础上,是天经地义的。君臣与夫妇、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等人伦准则都是取法天地之道:君臣上下尊卑,效法地之有高下;夫妇内外有别,效法阴阳刚柔;父子兄弟婚姻等伦理,取象于天明;人事之运作,顺从四时之道;国家制定刑罚监狱威慑百姓,乃是效法雷电天象;政治上温和慈祥的措施,乃是效法上天生长万物之德。这种推天道以行人事的诠释,表明礼乐行政是对天地之道的比拟效仿,遵循着象类原则。这与《礼记·丧服四制》所言“凡礼之大体,体天也,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意义相同,均言礼乃是效法天地之道。
古礼中象类原则具有深层次的礼制功能。由于天是世俗王权的终极来源,因此效法天道在先秦以至后世,都是国家政治运作的首要大事,如《尚书大传》云“道正而万事顺成,故天道,政之大也”,《大戴礼记·诰志》谓“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因此君王必须知晓天道,从天道推衍人伦之道,“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国语·周语下》)。天道虽然深邃不可测,但“天事恒象”(《左传·昭公十七年》),常以天象昭示给人类,因此,礼仪中象类原则就具有特定的功能。首先,它为礼乐体系提供了终极性的理论依据,也即为礼乐制度的合法性赋予了天道依据,古礼也因此具有了神圣性。其二,“天垂象而圣人则之”,取法效仿天之象,乃圣王所专擅。在政治运作中对天象模拟效仿的象类原则乃是顺天的方式。《汉书·郊祀志》云:“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郊祀中的象类原则,可以彰显君权的神圣至上性,并以此向天下宣示君权的独尊。其三,因为天道与人事吉凶祸福有神秘的联系,君王法天道行人事,可以凭借象征体系沟通上天,获得上天的佑助,从而实现天人秩序的和谐如《国语·周语下》云:“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
象类原则体现出中国古代的象征思维方式。中国哲学主要是用“象征”的方式来表达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通过想象、联想、比拟来沟通感性符号或概念和对象世界的联想边凤花、纪兴:《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类型和基本特征》,《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易·系辞上》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也者,像也”,即以此物来比拟形容彼物,其实质就是以有形之物表达无形之理,“立象以尽意”、“托象以名义”皆是此意。象征思维的认知过程便是“立象以尽意”。象是能指,意是所指。古礼中的象类原则,即是对认知客体现象的直观比拟。
二、古礼的仪式与象征
古礼的象征体系可以分为表层符号象征与深层的象征意义两种。前者是外显的、可视可察的象征符号。彰显礼义的符号有“礼物”与礼仪两类,前者是宫室、车马、服饰、礼器等名物度数;后者是仪式中周旋揖让、盘旋辟退等行为动作。深层象征体系,是内隐的、不易观察的,它是符号所隐喻的观念形态,它往往是一个政治或文化共同体共同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伦理道德准则等。
表层符号有礼器、辞令、乐舞、体态符号、仪式等。“礼物”是古礼中彰显礼制精神的物质象征符号。《左传·隐公五年》:“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轨,乃是礼仪法度;物,指显示文采之物。政治秩序与规范要依赖物来彰显,君主的任务即是制定规范,用物来规定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使各等级的人安守其位。其中,礼器是周礼体系的重要物质形态符号,《左传·成公二年》说:“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君之所司也。”礼器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符号,“器以藏礼”,不同等级贵族所用礼器,其颜色、礼数等均有严格的规定。
体态符号是人行礼时的容止、仪态的规范,如登降上下、盘旋辟退、周旋揖让、颜色容貌、声音辞气等。贾谊《容经》云:“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颜色声气,各有宜称,所以明尊卑,别疏戚也。”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0页。《礼记·曲礼下》:“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体态符号的不同表征身份尊卑贵贱的差异。体态符号也是人际交往中情感的象征符号,具有多种象征意义。
下面重点分析礼仪的深层次象征意义。
其一,仪式秩序象征政治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的伦理价值观。仪式本身就是秩序的象征,并通过仪式来强化这种秩序。下面以周代觐礼为例说明。朝觐礼作为一种政治礼仪,其核心是确定君臣上下的尊卑关系,仪式乃君臣尊卑关系的象征。《仪礼·觐礼》记载诸侯觐见周天子时:“侯氏入门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周代天子宗庙大门中央设有一短竖木称为闑。闑西为门左,宾客从此进门;闑东为门右,主人从此进门。由于诸侯是臣子,不能作为宾客而与天子分庭抗礼,故出入君门常从闑东,象征诸侯的臣属身份。觐礼中,诸侯奉献玉挚以及述职时均是“入门右”。又周礼规定,当授予物品时,若两人尊卑身份不等,则卑者将礼物“奠而不授”,不能亲自授给尊贵者。觐礼中,诸侯坐下将玉圭奠于地上,然后再拜稽首,也是奠而不授,用的是臣礼,象征其身份为臣,卑于周天子。
另如,周代饮食以及祭祀等礼仪中,牺牲被宰割的骨体有尊卑之别,不同的牲体各自被赋予尊卑贵贱的意义,成为贵贱尊卑等级秩序的象征。在礼仪中,地位尊者食用贵骨,卑者食用贱骨,骨体使用成为参与礼仪者身份尊卑贵贱的象征符号曹建墩:《周代牲体礼考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仪式是浓缩的象征形式,不仅是社会政治秩序的象征,而且还集中体现了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如婚礼中有夫妇同牢共馔、合卺而酳的仪节,《礼记·昏义》解释道:“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虽然夫妇之间并无血缘关系,但由于妻将为“社稷主”、“祖先后”,所以夫妇要相敬相亲,以情義相固来达到琴瑟和谐的目的。共牢而食、合卺而酳,即象征夫妇一体,相亲相爱。另如婚礼中“婿亲御授绥”之仪,婚礼中,夫婿授新妇车绥并亲自驾车环绕三圈,《礼记·郊特牲》解释说:“敬而亲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此仪节象征夫妇之间相敬如宾,相亲相爱。
其二,礼以象政,礼仪是政治之象。古人认为,礼乐皆可以观政,乃是为政之象。下面以祭祀为例说明。馂礼是祭祀之后食用神灵剩食的礼仪。《礼记·祭统》论曰:
是故尸谡,君与卿四人馂。君起,大夫六人馂,臣馂君之馀也。大夫起,士八人馂,贱馂贵之馀也。士起,各执其具以出,陈于堂下,百官进,彻之,下馂上之馀也。凡馂之道,每变以众,所以别贵贱之等,而兴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见其脩于庙中也。庙中者,竟内之象也。
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原始社会中,祭祀之后的祭肉往往被礼仪参与者所分享,以接受神力Catherine Bell, Ritual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108.。中国上古时期祭祀后的祭肉也被认为神灵已赋予其特殊的神力,能为人带来福祉,故归胙礼又称为致福。馂礼本来是具有宗教意义的一种仪式,但经过人文化之后,它除了象征尊卑贵贱差等,还有施惠于参加典礼者的象征意义,成为“施惠之象”。馂礼是君主仁政的象征,因为人君恩泽充沛才能施惠于百姓,故《礼记·祭统》云馂礼“可以观政”。
祭祀之后君王赐予祭肉也是仁政的象征。《礼记·祭统》云:“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贵者取贵骨,贱者取贱骨;贵者不重,贱者不虚,示均也。惠均则政行,政行则事成,事成则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为政者如此。”有德的君王将祭肉颁给下层百姓,乃“惠下之道”,也是仁政的体现。君主若能施惠于庙内,则能普施于一国内,因此“庙内之象”为“竟(境)内之象”。在这里,颁祭肉礼仪成为君主施行仁政的象征。
其三,仪式是情感的表达方式。传统礼学认为礼乃是缘情而作,如《礼记·坊记》、郭店简《性自命出》都有“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的说法。礼乐的内在依据为人的内在本然之情,即人之所以为人的仁爱之情。上博简《孔子诗论》简文云:“其言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隐志必有以喻也,其言有所载而后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干也”,“离其所爱,必曰吾奚舍(予)之,宾赠氏(是)也。”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隐志”,即内心之情志。人际交往若无币帛挚物则无以表达内心之情,故先以币帛为挚通情致意,然后再交往。否则即是不以礼而交,容易导致人的轻慢之心。简文“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是说宾客礼仪中百姓以币帛赠贿乃发自于内心的诚敬之情,是人性自然而然的表现。玉帛作为礼物符号具有象征意义,具有表达爱敬等情感的功能。总之,仪式符号作为一种表达性符号,可以表达礼仪参与者的情感,所谓“礼以副情”,“礼章情”是也。但是,在古礼体系中,更多的是将人的自然情感通过礼乐的裁节而实现向道德情感的转换,使人的内在之情外发时符合伦理规范的“义”。因此礼文是对人情感的合理裁节,是人情之节文,是要使过者与不及者都回到中和之境,它使外发之情符合天理,从而实现人情与天理的合一。因此,礼仪与情感表达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礼以章情”与“礼以节情”两种方式。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在《象征之林》中将仪式描述为一系列的象征符号,指出仪式象征具有两极性、浓缩性和符号的统一性等特征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这对我们分析中国古礼的象征体系很有启发性。中国古礼发展到周代,已形成了成熟完备的体系,这一礼仪体系已经超越了原始礼仪,被赋予了道德人文等意义,具有整体性、系统性、规范性和统一性、公共性等特征,成为周代华夏族群共享的象征与意义的集体文本。综合以上对仪式象征的考察,古礼体系的象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特征:
其一,浓缩性。维克多·特纳指出:“单个的象征能够同时代表许多事物,它是有着多重含义的,而不是只有单一意义。它所指代的事物并不都遵循同样的逻辑顺序,因为它是从多种社会经验和道德标准中提升出来的。”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1页。礼仪具有强大的叙述能力,是“符号的聚合体”,具有多重意义,既表达有复杂的情感,又象征道德伦理以及政治秩序等意识形态,从而构成了意义丛体。比如祭礼,《礼记·祭统》阐释云:“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祭祀中不同的象征符号在仪式中具有不同的象征,符号组合象征不同的价值观以及社会秩序,形成多层次的意义丛。祭祀仪式是浓缩的象征形式,蕴涵了礼的基本精神,涵括了周人的道德、伦理准则,统摄了周人亲亲、尊尊、贤贤、男女有别的价值观念,是父子、君臣、上下尊卑秩序的浓缩象征。
其二,公共性。仪式符号所表现的意义和仪式符号的指涉,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社会和人所赋予的,经过社会规约性之后便固定下来,具有了“公共性”。因为礼仪符号的象征意义在政治文化共同体内具有公共性,所以春秋时期鲁国叔孙豹出使晋国,晋侯设宴招待他,当“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礼仪具有公共性,这也是统一国家的礼仪体系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其三,变异性。当代符号学研究表明,象征符号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也会形成多层次的重构。礼仪象征具有变异性,仪式符号重组之后会产生新的象征意义。
其四,人文性。与西方文化人类学所探讨的仪式(ritual)相比,中国古礼象征缺少神话,或者说不需要借助神话建立象征体系。即使是宗教祭祀,也经过改造注入了道德精神而具有人文特质曹建墩:《从“以德事神”至“尽心成德”——两周祭祀观念之嬗变》,《孔子研究》2009年第3期。。而且古礼象征符号的所指多是人文意义上的道德,参下面论述。
三、以象比德与礼乐象德
古礼的成熟形态是周礼。周代礼制精神核心是德,礼与德二者犹如表里关系,礼乐秩序确立也意味着德治秩序的确立。德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宗教祭祀到婚丧嫁娶、宴饮游戏,无不践行着德的价值理念与原则。
(一)“礼物”象德
玉器在早期中国属于神圣之物,是沟通天地鬼神的法器,也是奉献给神灵的祭品。周代则“以玉比德”,玉礼器成为德之象征。如《考工记·玉人》说:“琬圭九寸而缫以象德。”
古礼中往往以玉圭、玉璋等瑞玉作为朝聘礼的挚(类似于当今社会的见面礼),来表达行礼者内心的诚信之情。《礼记·郊特牲》云:“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玉圭象征信义之德。以瑞玉作为朝聘、觐见时的礼器,体现了周人尚德的文化心理。《礼记·聘义》云:“圭璋特达,德也。”也就是说,玉圭、玉璋等挚是君子之德的象征。此外,朝聘礼中享献是用束帛加璧,也具有象德的含义,《礼记·郊特牲》解释道:“束帛加璧,往德也。”往德,即往归于德之义。总之,古礼中,圭璧加以束帛是主要的礼币,象征着诚信之德。
周人崇尚文德。在西周王朝尚文之风的背景下,车马、服饰、佩玉成为贵族阶层展现威仪,别贵贱等威的象征符号。《国语·周语中》说:“服物昭庸,采饰显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顺,容貌有崇,威仪有则,五味实气,五色精心,五声昭德,五义纪宜,饮食可飨,和同可观,财用可嘉,则顺而德建。”服饰可以表明功绩,色彩可以显示德行,纹饰可以比拟物象,仪节可以序次尊卑,礼容具有尊严,威仪具有法度,肴食的五味充实气志,器物的五色净化心灵,乐舞的五声昭示道德,礼仪的五义纲纪人的行为,饮食可口,情谊可观,酬礼可嘉,法度得以推行而道德得以建立。关于礼物象德,《左传·桓公二年》有精辟的阐述:
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
古礼通过礼仪和礼器等礼象来表征某些特殊的意义,“礼物”之形状、颜色、度数等,皆蕴含着深刻的意义。有形的“礼物”都是德的象征符号,反过来也可以促进人的德的建立。
(二)仪式象德
礼的节文仪式也是德之象,最鲜明的体现是“威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释云:“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据此可知,威是周代贵族外在服饰、容貌、仪态、言行举止等所体现出的威严气质,在周人看来,威是具备君子德性人格之后所呈现出的一种精神气质,这种气质可以令百姓产生一种敬畏之感。仪是人视听言动等身体展现出的符合礼仪规范的仪态、举止等,故书称为礼容,关于礼容的礼学门类称为容礼。“有仪而可象”,有两层含义:一指仪具有象征意义,象征君子之德,即所谓德行可象,君子之威由其德而来,百姓的敬畏其实是对君子之德的敬畏;二,可象之仪乃是可以为百姓效法的圭臬,礼象具有纲纪百姓的政治功能,即《国语·齐语》所言的“设象以为民纪”。仪式、节、度、数等外在符号,也包括社会政治秩序的人伦准则,其共通性的象征意义乃是周人所大肆宣扬的德。
另如飨礼,也具有象德之义。《左传·成公十二年》云:“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飨礼形式上的象征意味很浓,它体现为:牲体采用体荐而不吃,有几而不用,爵中充满酒但不饮,这些仪规象征着恭敬与俭约。飨礼食物也尽量要求物品完备,也具有象德之义,《左传·僖公三十年》记载:“王使周公阅来聘,飨有昌歜、白黑、形盐。辞曰:‘国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则有备物之飨,以象其德;荐五味,羞嘉谷,盐虎形,以献其功。吾何以堪之?”足见飨礼仪式是一种象德意味很浓厚的礼仪符号。
如学者指出,在周礼体系中“礼—程式、节文、仪态等——就是德的表象,反之,礼则是德的社会意象”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8页。。
(三)乐以象德
在儒家乐论中,乐是与德联系在一起的。《礼记·乐记》云:“德音之谓乐”,即乐必须有内在的道德精神内涵,《礼记·乐记》云“乐者,通伦理者也”,“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是德外显于乐、舞、歌的艺术形式,故《礼记》有“乐以观德”之说。
在先秦乐论中,“乐以象德”是重要的观念。如《礼记·乐记》说“乐者,所以象德也”,“乐章德”。《左传·文公七年》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是说歌乃是德之表象。春秋时期,吴国季札观乐,皆以德論乐,云“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当季札观看舞蹈时,也是以德论舞,“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幬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可见乐舞皆象征德,乃德之象。《礼记·乐记》提出:“夫乐者,象成者也”,“乐以象成”即“乐以象德”,象征功德成就。作为乐组成部分的舞蹈,是以不同的体态符号表征道德意义,如《礼记·乐记》所说:“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乐象德,故可以观乐而知德,这是周代贵族阶层的流行观念。
乐从属于礼,是具有道德意味的象征符号。从乐的生成上,乐以象作;从功能论上,以象章德;乐之象与德是一体两面,具有互动关系的一对范畴。
综上所论,礼是一个象征系统,其意义是由各种象征符号所体现。古人对于礼象的诠释,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将礼仪与人的真挚情感(如诚敬、仁爱、哀戚等)及伦理道德联系起来,仪式符号成为仁爱之情与德、政的象征,由此形成“以象比德”、“礼以象政”的思维与诠释模式。在古礼体系中,礼乐符号逐渐抽象化、道德伦理化,成为道德伦理的象征,礼乐符号的深层象征意义是“德”这一周代思想的核心观念,“德”是礼乐文化体系中统一的具有支配性的理念,这也是中国古礼象征的特质。
四、古礼象征思维与礼乐教化功能的实现
当代象征人类学研究表明,象征符号不仅是意义的载体,而且会参与或促成社会活动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古礼借助具体的符号,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规范和整合。下面主要探讨下礼仪象征与教化的关系。
实现礼仪教化功能的一个重要方式是礼仪表演。如学者指出,古代的礼乐体系就是将“尊尊”、“亲亲”等抽象概念物化为可观的外部形式,把观念上的等级意识通过不同的物质形式隐含地表现出来,见之祭祀对象、祭品、服饰、丧葬等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乃至最细微之处,使人与人之间的高低贵贱、亲疏远近通过外在形式一望而知夏静:《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5页。。礼仪符号乃是德之象、人伦之象与情感之象,具有直观性、容易明白等特点。而且,相对于语言符号的封闭性,象征符号的象征意义更为强大。如朱熹说:“言之所传者浅,象之所示者深。”朱熹:《周易本义》卷七,苏勇校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礼仪的象征意义比语言符号的表意具有更强的表达功能,因此礼仪的教化效果远比空洞的语言说教更加有效。《礼记·仲尼燕居》说:“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禮记·文王世子》:“是故古之人,一举事,而众皆知其德之备也。古之君子,举大事必慎其终始,而众安得不喻焉。”即指出礼仪作为象具有深刻而又直观的表意功能,可以确保礼乐教化的实施效果。
因为礼乐之象浓缩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则与价值观如《礼记·乐记》说:“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观象就成为推行礼乐教化的重要方式。所谓乐教,就是通过乐舞这类可观可感的表演形式,正确引导人的心志,“修乐以道志”,激发人内在的道德情感,从而实现对人的道德教化。先秦社会,当举行丧礼、乡饮酒礼、射礼等典礼时,常有宾客观礼之举。所谓观礼,就是对仪式表演的观看体察,这是对礼仪象征意义的内在体验的过程。仪式符号是一种公共符号体系,它可以对人的心灵产生积极作用,参与礼典或观礼者可以获得情感共鸣,从而激发人内心的道德情感,转化为合乎道德伦理的社会行为。《礼记·檀弓下》说:“以故兴物”,故指礼乐,也就是说礼乐可以唤起、提升内心的道德情感。《礼记·檀弓下》又云:“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当人身处特定的墟墓、社稷、宗庙等礼仪场景中,目睹礼乐符号,会提升自己内心的道德情感,这就是礼乐教化的效果。
古礼的象征思维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教化模式,形成了重视“身教”、“法象”的教化传统。徐干《中论·法象》:“夫法象立,所以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仪。……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义存,仁义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为法象。”孙启治:《中论解诂》,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1页。身教重于言教,这种仿效“法象”的身体政治乃是西周、春秋以来政治思想中的一贯思维。例如《诗经·大雅·荡》云:“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云:“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君子的威仪乃是百姓效法的圭臬,君子法象立,则百姓归之如流,此即《礼记·中庸》“君子之道本诸身”这一宗旨。欲教化百姓,关键在于执政者具有良好的德行,身体力行,做出垂范。若执政者举止容态遵循礼道,则百姓有准则可效法。《孝经》曰:“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对于这种重视身教的典范政治的功效,《礼记·乐记》阐发道:“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礼乐教化的根本在于执政者要具有“一德”、“恒德”,而君子的恒德与外在符合礼仪规范的身体符号是一体之两面,法象乃君子恒德之符表,德乃君子身体符号之灵魂。君子有内在之恒德,外则行礼如仪,如此才可以使民信之、从之并乐意效法之,从而达到敦化民俗,使民德归一的目的。总之,礼乐符号因其象征丰富的德性意义,具有直观性,可以对百姓进行教化,这也使政教更具有可操作性。
结语
综上论述,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中国古礼是一完整的表意体系或象征体系,体现出古人的象征思维方式。其中,象类原则是礼仪建构的重要原则,它法则天地之道,以天地之象为比拟对象,为礼赋予了神圣的终极依据,强化了古礼天经地义的正当性。中国古礼体系象征有表层符号与深层次的象征意义两种。礼乐之“象”象征着政治社会秩序,由此形成“礼以象政”的象征模式。古人“以象比德”,在古礼体系中,礼乐符号逐渐抽象化、道德伦理化,成为道德伦理的象征,“德”是礼乐文化体系统一的支配性的观念,这也是中国古礼象征体系的特质。礼仪符号的深层象征意义构成了礼的精神传统,古礼的象征思维对传统中国的教化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陈炜祺)
Analogical Principles and Symbolic Thinking in Ancient Chinese Rites
Cao Jiandun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ritual is a complete ideographic system or symbolic system. It construct ethical principles and norms of social values of ancient society by means of symbol. It is the key way to construct ritual system by analogy with the universe, Yin Yang and five elements, and it has given the sacred ultimate basis for the legitimacy of ancient rites. In the course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rites and music, one obvious feature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itual music and people's sincerity, benevolence and ethics. The symbols of rites and music become the symbol of benevolence and “Virtue” and “politics” and become an interpretive mode. The deep symbolic meaning of ritual symbols constitutes the spiritual tradition of Chinese ancient rituals. The symbolic way of thinking of ancient rites exert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the pattern of politics and cultivation in ancient China.
Keywords: Ritual; Analogy; Sanctity; Virtue; 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