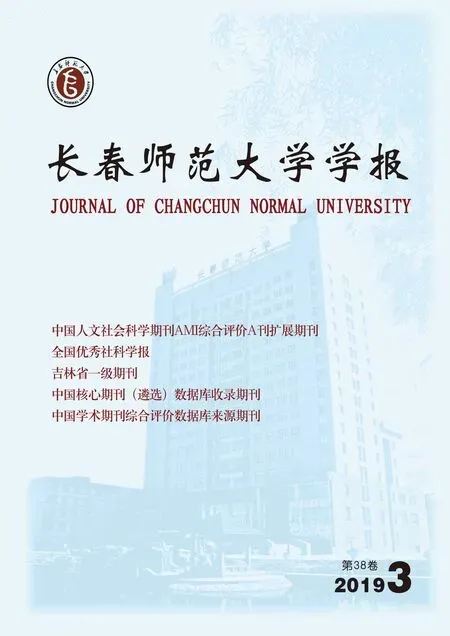三苏论管仲之评析
2019-03-22管成学荀长春
管成学,管 恕,荀长春
(1.北大资源学院,北京 100097;2.北京大学 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3.吉林大学莱姆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管仲作为春秋第一名相,深受孔子的称颂:“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今受其赐,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苏洵、苏轼、苏辙都写有《管仲论》,专门论述管仲其人其事。他们所议论的角度不同,表现方法各异,但对管仲都给以高度肯定,并指出他的不足之处。
一、苏洵论管仲
苏洵论管仲,主要见于他的《管仲论》(见于《嘉祐集》卷九)。
(一)全面肯定管仲的功绩
苏洵充分肯定了管仲相齐的功绩,在《管仲论》开篇就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戎翟,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叛。”[1]
苏洵在《管仲论》中又说:“彼桓公何人也?顾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桓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1]苏洵认为桓公是一个沉湎声色的君主,因有管仲为贤相,竖刁、易牙、开方这样三个以声色讨好君主的小人并不能乱政,不能影响齐国之富强;管仲一死,齐国不久就大乱了。
苏洵看到了管仲辅佐桓公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没有管仲的谋略,齐国是不能走向民富国强、称霸诸侯、一匡天下的。
(二)尖锐批评管仲不注意培养接班人
苏洵对管仲的批评有失公允,我们也略作辩析。
苏辙引用其父苏洵论管仲之言说:
《传》曰:“管仲病且死,桓公问谁可以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何如?’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刁何如?’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祸作。”“夫世未尝无小人也,有君子以间之,则小人不能奋其智。《语》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举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 矣。’岂必人人而诛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无以御之,何益于事?内既不能治身,外复不能用人,举易世之忧,而属之宋襄公,使祸既已成,而彼宋人以干戈正之。于乎殆哉!昔先君之论云尔。”[2]
苏辙引用苏洵论管仲之言,批评管仲在病危之际,面对桓公问其逝后何人任相,只说易牙等三人不可用,并没向桓公推荐良相。批判曰:“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无以御之,何益于事?”[1]
每读苏洵之文,则心生疑惑。以管仲之一世英明,面对他与桓公所创之伟业,怎能不选择接班人呢?
近读《诸子集成》,发现两条史料,可纠正苏洵所论之偏颇。以就正于致力于苏学的专家们。
管仲临终时,齐桓公问鲍叔牙可否任相,管仲作了如下回答(被韩非子记于《十过》):“鲍叔牙为人刚愎而上悍。刚则犯民以暴,愎则不得民心,悍则下不为用,其心不惧。非霸者之佐也。”谈到隰朋时说:“其为人也,坚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坚中则足以为表;廉外则可以大任;少欲则能临其众,多信则能亲邻国。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3]鲍叔牙对管仲有大恩,但管仲并不任人唯亲,而是以国家的利益为重,认为鲍叔牙不可任相。管仲推荐了隰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
管仲对鲍叔牙和隰朋谁可任相的评论,被管仲的后学们记载于《管仲·戒》中,与《韩非子·十过》所论大同小异。在《管仲·戒》中,管仲谈到鲍叔牙时说:“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谈到隰朋时说:“朋之为人,好上识而下问。臣闻之:以德予人者,谓之仁。以财予人者,谓之良。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国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必则朋乎!且朋之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门,居公门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举齐国之币,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4]
管仲病危时,桓公问及谁可任相一事,又记于《庄子·徐无鬼》:“管仲有病,桓公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谓)[讳],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管仲曰:‘公谁欲与?’公曰:‘鲍叔牙’。曰:‘不可。其为人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治国,上且钩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将弗久矣!’公曰:‘然则孰可?’对曰:‘勿已,则隰朋可。其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勿已,则隰朋可。’”[5]
以上三则史料明确告诉我们:管仲不像苏洵、苏辙说的那样,仅仅否定了易牙等三个媚君的小人而没有推荐贤相。他以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重,否定了自己的恩人鲍叔牙,而推荐贤相隰朋。
管仲是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思想至今福泽着神州大地,弘扬管仲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当仁不让的职责。
二、苏轼论管仲
苏轼论管仲不同于苏洵,苏洵没有经历苏轼的坎坷。苏轼像管仲一样胸怀忠君爱民、致君尧舜的雄心壮志,想使积贫积弱的北宋政权走上富国强军之路。但是,刚愎自用的宋神宗不肯采纳他的意见,又听信李定、舒亶、贾种民等的诬告,逮捕、贬斥了他。所以,他更能理解管仲让沉湎声色的齐桓公接受他的改革,谈何容易啊!苏轼给管仲以更多的理解,对其评价也更加全面和准确。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既不见容于新党,也不见容于旧党,饱尝宦海沉浮之苦。政治上的挫折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所以,他的思想比较复杂,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对各家各派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因此,他对管仲的了解和评价是非常全面中肯的。
苏轼论管仲的文章比较多,除了《论管仲》《管仲分君谤》《管仲无后》等三篇外,还有《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思治论嘉祐八年作》等文章。
(一)苏轼《管仲论》专论《管子》的军事思想
管仲辅佐齐桓公,希望刚刚从动乱中稳定的齐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管仲是怎样组织和培训这支军队的呢?苏轼研究了《管子》的“七法”“九变”“兵法”等军事著作,又与《司马法》、周代军队编制相比较,得知管仲的军队编制和军队训练的独特之处。《司马法》曰:“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为奇,其余七以为正。四奇四正,而八阵生焉。”周代兵制和《司马法》讲的是阵法,追求的是守卫和不败。
苏轼在《管仲论》中,盛赞管仲“简而直者”“有所必胜”的战法。“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谓截然而易晓矣;三分其国,以为三军。五人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乡长人。三乡一帅。万人而为一军。公将其一,高子、国子将其二。三军三万人。如贯绳,如画棋局,舒畅洞达,虽有智者,无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简一,而民有余力,以致其死。”“由此观之,不简而直,不可以决胜。深惟后世不达繁简之谊,以取得败亡,而三代什伍之数,与管子所以治齐之兵者,虽不可尽用,而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于简而直者以之决战,则庶乎其不可败,而有所必胜矣。”
苏轼认为管仲改变周代和《司马法》推崇阵法、用以固守的军事思想,采用简而直的“决战必胜”的策略,是其军事思想的重大贡献。
(二)苏轼《管仲论》阐述道德与史论
1.坚辞子华之请以弘德
苏轼在《管仲论》一文中引用的第一件史实是管仲劝齐桓公坚辞郑太子华有违周礼之请求,训以弘德之辞,以扬周道。
郑太子华言于齐桓公,请去三族而以郑为内臣。公将许之,管仲不可。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苟有衅,从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率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公辞子华,郑伯乃受盟。
苏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辞子华之请,而不违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
2.不违曹沫之盟以守信
曹沫者,鲁将也。与齐战三败北。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曰:“齐强鲁弱,请还侵夺之城”。桓公当众许之,曹沫归其座。其后,桓公怒,欲违其盟。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授,不如与之”。于是,桓公听管仲谏,尽复侵鲁之地。
齐桓公让出的是侵鲁之城,而得到的是天下信誉。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召集诸侯会盟,确立了齐国的霸主地位。
管仲辅佐齐桓公,以道德与诚信征服诸侯的政治理念,得到苏轼的高度评价,称赞为“盛德之事”。
3.“七人为万世法者”言史论重在当世
苏轼在《管仲论》中说:“吾读《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为万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为万世戒”。
“七人为万世法者”,乃桓公、管仲不废田敬仲,欲以为卿;楚成王知晋之必霸,而不杀重耳;汉高祖知东南必乱,而不杀吴王濞;晋武帝闻齐王攸之言,而不杀刘元海;符坚信王猛,而不杀慕容垂;唐玄宗用张九龄而不杀安禄山。
这七个可谓万世法者的历史人物中,苏轼首推管仲。苏轼认为齐景公不用繁刑重赋,虽有实力雄厚、野心勃勃的田氏,也无法取代齐国。所以,后世论史者认为管仲不该以田敬仲为卿的评论是不公平的。其他六人也是一个道理,从吴王濞到安禄山,在没有他们反叛的证据时,不能以传言或疑惑杀人,即史论重在当世,惩罪杀人,必须有实证。
4.“八人为万世戒者”言不以成败论是非
“八人为万世戒者”是:“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晋文帝以卧龙而杀嵇康,晋景帝以名重而杀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杀王彧,齐后主以谣言而杀斛律光,唐太宗以谶而杀李君羡,武后亦以谣言而杀裴炎。世皆以为非也。此八人者,当时之虑,岂非忧国备乱,与忧元海、禄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败为是非也。”
苏轼所强调的是史论不能以成败论是非。成功者依然会做错事,汉景帝总体上应该是一个好皇帝,但他逼死周亚夫的过错是不可原谅的,必须受到批判。苏轼《管仲论》留给我们的史论标准是值得称颂的。
三、苏辙论管仲
苏辙的《管仲论》主要继承了父亲苏洵的观点,责怪管仲没有举荐贤相。苏辙在《论语拾遗》《冯道》《策问十六首》等史论中也对管仲多有褒贬,在此择其精要,给以评析。
(一)钦佩管仲大节无亏
苏辙与苏轼都批评管仲的奢靡生活、聚敛财富,认为管仲的品德不符合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标准。但是,苏轼以忠臣为君“掩过”、“分谤”为由,替管仲辩解。他以自身的经历深知管仲要改变齐桓公沉湎声色的享乐是不可能的,所以认为管仲“三归之家,树塞门,有反坫”,是为了“分君谤”,以掩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之过。苏轼在《管仲分君谤》中说:“管仲之爱其君亦陋矣,不谏其过,而务分谤焉。或曰:“管仲不可谏也”。苏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谏而不听,不用而已矣。”[6]
苏辙与苏轼不同,认为管仲大节无亏。苏辙论人大胆立异,能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评价历史人物,在《冯道》一文中说: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从而相之;晏婴与崔杼俱事齐庄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婴伏尸大哭,卒事齐景公。
苏辙认为,议论冯道的人应该多一些宽恕。他深知仕途的凶险,认为冯道日日与暴君骄将相伴,不仅能够自保,而且能有益于社稷,确实是不容易的。他甚至把冯道和管仲、晏婴相比,认为他虽功不过管仲,却无愧于晏婴。
(二)以治国论管仲之才
苏辙在《进策五道·第四道》中高度评价管仲的治国之才。他列举管仲劝齐桓公忍曹沫持刃之辱、信守退还侵鲁之城、赢得诸侯的信誉为证。当齐桓公因为怪罪少姬而攻打蔡国时,管仲“责苞茅不贡于周室”,以尊王之大义代替泄私人之愤,既解决了问题,又使诸侯归心于齐。
苏辙在《论语拾遗》中指出:“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许之矣。然而三归反坫,其心犹累于物,此孔、颜之所不为也。使颜子而无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将造次颠沛于是,何三月不违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礼,死而五公子之祸起,齐遂大乱,君子之为仁,将取其心乎?将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相人,以颜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几无后患也夫!”[7]
苏辙还称颂管仲“臣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他认为在非常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进行各种改革时,管仲能够公平果敢地处事,尽管不能不得罪一些人,但都是为了齐国的强军富民,所以能使得天下归心、君臣相得。可见,苏辙非常肯定管仲的政治才能。
(三)批评管仲没有考虑到他与桓公死后的齐国兴衰
苏辙对管仲的评价深受其父苏洵的影响。与苏洵一样,苏辙认为齐国的没落与管仲不无关系。但是,他认为管仲的失职不仅仅是没有除去桓公身边的三个小人,更重要的是没有精心为桓公作身后计。在《管仲论》中,苏辙指责道:
管仲身有三归,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为非,此固適(嫡)庶争夺之祸所从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与桓公为身后之计,知诸公子必争,乃属世子于宋襄公.夫父子之间,至使他人与焉,智者盖至此乎于乎,三归、六嬖之害,溺于淫欲不能自克,无已则人乎!《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四方且犹顺之,而况于家人乎?[8]
苏辙和苏洵一样,都在分析史实方面比较深刻,都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苏洵认为功有所由起,祸有所由兆,所以把齐国大治归功于鲍叔牙,把齐国大乱归罪于管仲。苏辙在分析管仲临终之言后,认为小人存在是齐国后来大乱的主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自身的问题。他认为,管仲和桓公有共同的缺点,那就是“溺于淫欲而不能自克”,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自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委托给外人宋襄公,怎能不导致齐桓公死后诸子争权,死而不得葬的悲剧结局呢?
苏辙叹息道:“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无以御之,何益于事?内既不能治身,外复不能用人,举易世之忧,而属之宋襄公,使祸既已成,而后宋人以干戈正之。于乎殆哉!昔先君之论云尔。”[8]
我们已批评了苏洵论管仲中的偏颇之处。苏辙再引先君论,而忽视了管仲推荐隰朋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