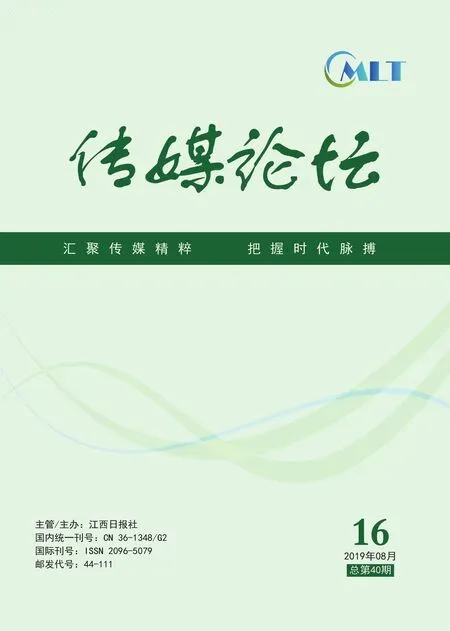日本科幻的美国化难题
——以《攻壳机动队》为例浅析美式科幻电影的改编困境
2019-03-20王子川
王子川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2019年,美国科幻电影《阿丽塔》上映,5月,制作人卡梅隆在接受采访时表明了票房收入远未达到预期,7月,二十世纪福克斯宣布重新考虑电影续集拍摄的可能性。这是近年来美国科幻电影在改编日本科幻作品时又一次遭遇的失败。随着本土科幻创意的衰减,许多美国制片方试图通过购买日本科幻作品版权为电影提供改编文本,《攻壳机动队》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但超高的原著人气和庞大的电影制作成本并没有实现电影的成功,对《攻壳机动队》的改编暴露出了美国科幻电影的改编困境。突出的问题是,《攻壳机动队》没有继承发展原作的思想灵魂。美国科幻电影发展的轨迹以及相伴随的人本化趋势,决定了它注定不可能还原那些超前而思辨的哲学思考,更无法在电影形而上的领域产生新的突破。就如同电影中义体承载人的思维一样,它不过是一个年长但前卫的壳承载着更加老迈的思想罢了。
一、从整体思考到个体认知的认同难题
东方国度普遍拥有漫长的历史与长期的强大,这使得他们的文化能够跳脱出现实世界的困扰从而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这使得苏轼能够从整体世界天地的角度思考个人问题。也使得日本《源氏物语》能够从对个人际遇的悲演进到对自然天地更替的悲。它们作为早期的整体性思考,已经为《攻壳机动队》(日)的视域拓展提供了较高的基础。
美国与此不同,这个无时不在为开发生存而埋头苦干的国家标榜的是实用主义,而拒绝思考与自己无关的东西。体现在美国科幻电影中就是科技对“我”这个个体的影响。在原版影片中,2029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高速进步,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边界日趋模糊。人类可以用机器来替代部分身体,来获得能力的强化和生命的延长;在剧情设定中,很多人在脖子后面装备了与整体云世界信息相连的输入端口,个体演变为整体信息系统的终端。主人公“公安九课”的少佐是其中最先进也最复杂的个体,她保留了人体的大脑,采用机器的身躯。原版将少佐的迷茫表现在因为站在整体世界的角度解读个体,而发出如苏轼一般蜉蝣的感息,进而传达对世界的态度。但在美版中,少佐对亲情、友情,维护公平正义,发扬英雄主义的兴趣都比思考“我在世界中是谁”的兴趣要大很多。它的关注核心事实上是人本的,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这种人本的关注点来自于漫长的美国科幻电影史。如果刨除《月球旅行记》这些早期科幻性质电影的话。从早期科幻电影《太空探险2001》到经典科幻时代的代表作品《异形》《侏罗纪公园》《哥斯拉》,再到新世纪以来,反映生态思想的科幻影片如《金刚》《生化危机》《喜马拉雅》《猩球崛起》等,科技对人类的影响是美国科幻电影唯一不变的主题。看起来这些电影既有关于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也有对科学技术无节发展的批判,甚至在后期幻想了人类命运的终结。有人说这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这其实不过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衍生。
西方研究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指人类相较同力场其他生命视自己为高等生命,自认为能够决定包括动物、植物等地球上一切已知生命和一切非生命的存在。现有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早在人类文明产生初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就已然存在。西方科幻电影中对人类命运的悲哀展望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其实立足点还是对人造成了什么后果,目的还是促进人的发展,而非脱离人类视角以一种理性的态度认识社会,这也是造成美版《攻壳机动队》沉湎于关注网络犯罪、义体对人的影响等小格局而放弃深入原版唯精神世界等世界观的主要理论。这种“人本”思想最终导致了大视野退化回小格局。
二、从自然性到人性的思考难题
美国科幻电影另一个突出的趋势,就是片中的非人一定要具有人行和人性。这种趋势从《ET》中外星人带有部分人性和人的行为,到近期“超级英雄”系列人行角色找寻回归人性的故事。美版的《攻壳机动队》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原版中少佐同时具备机器性和人性,在这中间的挣扎与迷茫是引发观众形而上思考的动因。其中一段台词来自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解释了影片的唯精神世界观,它说道:“生命是存在在信息洪流中的一个质点,DNA对生命而言,就像人类的记忆一样,独特的记忆造成了独特的人……而我则是诞生在信息中的生命体。”在原版作品中,这是最打动读者的部分,也创造了一种对于人与机器的关系的富有韵味的描述。而在美版中,这种韵味消失了,变成主角直白地和机器划清界限的无意义感情宣泄:“人性是我的美德”。简单而粗暴的价值判断使影片失去了哲学探讨的空间,原著中构建的平衡可发展格局退化为单一价值观导向,丧失了它的科幻意义。
事实上,美国科幻电影在叙事和人物塑造的这种人本性可以追溯到好莱坞“经典叙事”。好莱坞编剧认为,英雄对应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领域的“自我”,而这个形象如果想要成功,就需要让观众产生一种共情。观众对人物的认同往往来自对动机的认同,首先要为英雄设计一个观众可以认同的动机,之后再让英雄随核心事件一同成长。这其实非常符合好莱坞的叙事套路。但是这种套路并没有能够拯救剧情,反而硬生生引入诸如复仇、亲情等无关枝叶,削弱了原著对“我”的哲学性解读。
在原版中,主人公有很多赤裸的画面,在原版对机器性描述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认知隐含的寓意是对主人公来说,机器身体是衣服一样的存在,只是一个“壳”。裸体突出了身体的机器性和自然性,强调了自我和本我的对立关系,它并非只是作为别人的观看物,同时也是属于自我存在的见证对象。但是由于美版对少佐自然性和人性的剥离,这种裸露最后只成了恶趣味者的福利,不在具备它的情感宣泄作用。
由于本片根本就没有营造出少佐身上机器性与人性的对立和均衡,而是以好莱坞科幻片一以贯之的“人本位”创作思路,为本片迅速确定了剧情走向和主流价值观,从而使它一开始就变成了纯粹的爆米花电影。最关键的是,它回避了一个根本的问题:除了“意识”,“身体”本身是否具有属性?历史的本质是时间在个体行为上的反映吗?个体作为历史时空的载体,当它开始接受一个全新的“意识”时,它们之间存在形而上的冲突吗?这些问题本是探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和形而下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我们在电影里看到,随着记忆被植入大脑,意识和身体竟然无缝对接。或许导演根本就不想在这个命题上继续下去。包括最后一个镜头少佐用身体毁灭坦克本应是全剧的高潮,但由于电影根本没有能够展开关于存在的探讨,自然她身体的破碎就只好如前几次一样再去缝缝补补了。影片的精神震撼彻底丧失了,留下的全部是导演让观众得到的生理刺激。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承认,两种文化对存在的不同认知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片哲学思辨的力度。在日本神道教中,人们信仰八百神,至于这八百神到底都是谁却没有公论。这些神祇存在我们周围,却和《攻壳机动队》中的网络一样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日本文化也可以接受形而上的设想,比如德川家康就一直坚称世间是由大道统领的。但在美国,即使是宗教信仰也是向未降世的天主祷告,形而上的哲学探讨本就少见于美国影片中。
三、结论
从美国科幻电影发展的历史来看,在电影中注重人本人性思想的宣传一直是他们标榜的,这甚至影响了美国科幻电影中的人物设置和剧情安排。但另一方面,科幻电影中的人本与人性很大程度上却是不科幻的表现,带来的后果就是电影灵魂的丧失。尤其是在改编日本科幻作品的过程中,美国科幻电影往往会陷入这种文化困境,对于原作品武断的工业化加工和生硬的西方文化移植,最终让电影失去了新意与深度,并在传播过程中增加了壁垒,最终导致了电影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