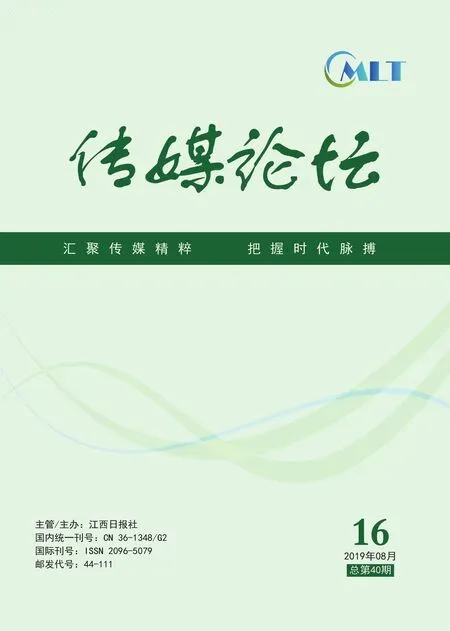论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都市文化及电影改编
——以《倾城之恋》为例
2019-03-20魏书鹏
魏书鹏
(西北民族大学,甘肃 兰州 730124)
20世纪40年代,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主要时期,也是她小说风格形成的成熟期。张爱玲小说被普遍认为雅俗互动的特性,相对于小说思想内涵与美学艺术上的雅,其俗的表现之一是都市文化的书写,加上小说文字极具“电影感”的特征,给予了影视创作者改编影视的可能性。
小说中,张爱玲不厌其烦地描写了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李欧梵在《苍凉与世故》中评价说这个主题在她作品中占有主要地位,因为在她笔下,“它们代表了都市生活中的一种‘文明的节拍’,充满了五光十色的刺激,这就是她所熟悉的上海。”①她所书写的上海都市文化脱离了时代洪流中民族与国家的宏大主题,而是日常生活的真实与逼仄,人物的一言一行与动态心理都依借着物质意象来表现,反映出她对世俗人生的深刻体验,折射出一种苍凉的阅世哲学,这是张小说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因此,从文本语言到视听语言,上海都市文化的可视化呈现至关重要,一方面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时代氛围,一方面通过都市生活的描绘,将小市民群像真实地展现,传达出张爱玲作品对人性的透彻的凝视。
20世纪80年代的“张爱玲热”吸引了一批港台导演的影像化改编,目前已上映播出的电影有五部,分别是许鞍华导演的《倾城之恋》(1984年)、但汉章导演的《怨女》(1988年)、关锦鹏导演的《红玫瑰白玫瑰》(1994年)、许鞍华导演的《半生缘》(1997年)和李安导演的《色戒》(2007年)。因导演的个性差异与地缘文化的影响,影片中上海都市文化的呈现各有风格。本文将以许鞍华导演的《倾城之恋》为分析例证,并参照其他导演的影片呈现进行对比,通过文本和影片的细读与比较,在还原度和二次创作效果的维度上探析,总结出电影创作中的亮点和遗憾,为文学影视改编提供一些参考路径。
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影视改编的维度,论述小说改编影视的可行性和挑战,指出张爱玲小说最关键的改编原则;第二部分先从文本语言的维度,梳理小说《倾城之恋》中关于上海都市文化的意象和空间场景,解析它们在作品中的隐喻和象征意义,再从视听语言的维度,比较许鞍华改编影片中对上海都市风情的呈现,并引例其他导演的改编电影,指出许改编的缺憾之处;第三部分为全文的结语和未来展望。
一、文本改变影视的可行性和挑战
张爱玲小说素有“纸上电影”之称,体现在她小说中具有影视特征的“视听意象”和“现代手法”上。“视听意象”就是以物质或声音意象来表现人物心理、性格、形象,布设周遭环境,推动情节发展。如弄堂、公馆、老洋房、电影院、舞场都是张小说中惯常出现的空间场景,用以暗示时代环境、烘托时代氛围;月亮、旗袍、镜子、中式或西式家具等意象常用来影射人物内心,隐喻人物命运;胡琴声、电车声、马车蹄声、小贩叫卖声等市音常常巧妙自然地渲染出人气和生活气息。
“现代手法”是张爱玲创作小说的“影视技法”,表现为“蒙太奇”的镜头语言效果:用一连串利落有劲的动词构建出空间场景,整个语言的叙述一气呵成,仿佛有一个镜头在眼前由近及远或由内及外展现出了一幅画面。《倾城之恋》中有一段白公馆堂屋的描写:门掩上了,堂屋里暗着,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籍,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拖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这段一百多字的文字精简凝练,几乎每个小分句都有一个动词或方位词,表现着物像的具体状态和颜色、光影效果,三言两语便真实地再现了内堂布设。
电影是一种视听语言,因此镜头是通过视觉和听觉体验讲故事,重在对人与物的表征再现,色彩、光线、声音是电影表达的重要元素,而张爱玲在创作小说时运用的这些技法给予了影视创造者很大改编的空间,为文本语言到视听语言的转化架构了桥梁。
文学和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表达媒介,表现方式和呈现效果都迥然不同,在小说中出色的心理描写和上海时代氛围再现却成了电影呈现的难题和挑战。文字语言的魅力在于能用精湛的文字功底准确地引导、提示读者,为读者构建出人物的心理历程并留有读者想象的空间,而电影语言的表现需要读者基于演员的表演联想,往往演员的表演素养决定了诠释的效果,极可能使观众陷入不知所以的观影体验,因此在心理描写的影视化呈现上极考验导演的功力;小说中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再现,张爱玲是基于自身的地缘文化优势书写的,她从对上海和上海人的生命体验中将都市的时代氛围和小人物精神面貌深刻地再现,而不同地缘身份的导演,对上海都市文化的体验往往是有距离感的,会让影片中的上海都市风情呈现出个人特色,最终必须经受观众的考验。
二、从文本到荧屏:都市文化的影像化呈现
写于1943年的《倾城之恋》是一个双城传奇,张爱玲颠覆了中国传统寓言中红颜祸水的故事,而是以倾覆了一座城的历史背景成全了一段爱情。在小说中,张爱玲以上海人的身份分别书写了上海和香港的都市文化,虽然重点情节设置在香港,但只是围绕着香港浅水湾酒店发生,并未深入香港生活和文化的核心领域,这由于张爱玲是以上海人的身份来看香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双城故事其实是借助香港的历史环境书写了一个上海情调的传奇,因此本文所要探析的“香港舞场”将归入在上海都市文化范畴中,具体原因如下两点:
其一,从客观的历史环境来看,20世纪40年代香港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与当时的上海有着不解之缘。1937年“七七”事变,大批上海舞女和经营夜总会的商人南下香港,为香港的舞厅带来了更加浓郁的“海味”;上海在1932年兴建了颇具规模的“百乐门”,随后香港在1945年出现了同名“百乐门”舞厅,足见香港舞厅文化的发展深受海派娱乐的影响,可以说上海海派文化的南下重构了一部分香港。因此,窥探彼时的香港文化,往往依借并对比20世纪30、40年代上海的海派风情,尤其是在香港故事中40年代的“舞场”,追根溯源,是上海舞场文化的移植品。
其二,从张爱玲与香港的个人情缘来看,香港是相对于上海(本我)的“她者”。张爱玲在1939年入读香港大学文学院,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国,1943年创作了《倾城之恋》,因此此时在张爱玲眼中的香港,是一个相隔两年的回忆,是以异域人的身份完成的想象。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坦露:“我为上海人写了一部香港传奇……写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查看香港的。”这段自白再次印证了张爱玲依借香港这个“非道地中国”②书写了上海情调的传奇。在小说中,也随处可见上海世界的影子,如“大中华”上海菜馆,仆欧们的上海话,范柳原对白流苏穿旗袍模样的想象等等。
(一)白公馆
上海传奇的白公馆是一个旧中国的文化遗物。这里处处充溢着古老腐朽的气息——“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式”,“玻璃罩子,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坏了,停了多年”,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这里一天天衰落并永恒地颓败着——白四爷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上下旧楼梯总是“吱吱格格一片响”,“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在张爱玲的眼中,白公馆有着日常生活气息却也是死一般的压抑与沉寂,楼梯拥挤狭窄,内堂昏暗凄冷,老物什透着噬人的阴森冷气,仿佛要将人的灵魂永远禁锢在老宅中。
这是一个传统封闭的中国空间,也是张爱玲原生家庭的影射,她在《私语》中忆及幼时居住的公馆:“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③她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融入小说创作中,冷静真实地再现20世纪40年代上海都市人的日常生活现状。
布设奢靡浮华的白公馆,看似体面实则衰颓虚空,在张爱玲笔下,成了人物心理物化的对象,内心的情绪依托着老物什具象化。白流苏观望着这个破落的老洋房公馆,她惊恐地发现自己已然活成了老宅中的一件旧物什。玻璃罩子中的珐琅自鸣钟,机括坏了多年,停滞的时间阻隔不了白公馆的腐朽没落,潜藏着一种反讽意味,白流苏的心也在这尘封的老家具的浸染中变得迟滞黯然;金色寿字团花仿佛浮在半空中,虚幻缥缈,白流苏的人生就像这些虚飘飘的字,落不着实处,看不见底下的光亮;镜子前的白流苏摇曳生姿,和着白四爷的胡琴声,她为自己表演了一出伶人的戏,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流苏无法挣脱生活这部戏剧的枷锁,她在无尽的孤独和无望中顾影自怜。
许鞍华对上海故事的处理,带有香港人即异域人看上海的生疏感。电影的前三分之一是白公馆的故事。影片中的白公馆内部布设家居自然,且有一定的年代感,较好还原了白公馆破落腐朽的气息。许鞍华多采用移镜头和长镜头,景别多中景、全景,在全知视角上展示人物关系、人物走位,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人物的心理表现。徐太太在房间安慰白流苏的情节,许鞍华采用了声画分立的技巧,徐太太劝告白流苏“找个人才是真的”,之后画面是三个长移镜头,从白公馆的堂屋移到屋外再承接到流苏的手部特写,弥补了人物对话时画面的单调,同时许鞍华似乎有意地展现了白公馆由内及外的衰颓势态,配上凄苦的二胡声,将白流苏的艰难处境烘托而出,为流苏积极与范柳原的交往埋下伏笔。
在小说里,张爱玲以白流苏的主观视角观望了堂屋里书箱、紫檀匣子、珐琅自鸣钟、对联,以蒙太奇的影视技法过渡意象,再以对联上“虚飘飘”的字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处境,引出了一长段的心理描写,情绪有层次地递进,耐人寻味。许鞍华采取了“物人对照”的镜头语言,徐太太走后,第一组镜头从白流苏的视角切到一副祖宗画像,从全景推到近景再到特写,之后切回白流苏的正面全景,白流苏走向镜头,若有所思;第二组镜头从白流苏的正面画面切到玻璃罩中的珐琅自鸣钟特写,玻璃罩上反射出流苏的上半身,此时流苏依旧在沉思,几秒后流苏的身影淡去,镜头切到流苏的手部特写;第三组镜头从流苏揉搓手巾的手部特写向上移到面部特写,流苏垂着眉眼做思索状,镜头随着她的视角切到朱红对联的黑字特写上,之后切到流苏哭着跑走的画面。这三组画面分别选用了画像、珐琅钟、对联三个意象对照流苏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影射流苏的心理活动,将文字中有声的心理描写转化成镜头上无声的意象影射,这种尝试实则是将主动权交给了演员,诠释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演员的演技。遗憾的是,女主缪骞人的长相过于硬朗,与白流苏传统温润的古典美气质不太符合,并且表演缺少感染力,眼神也显得空洞呆滞。以白流苏在白家苦熬多年的韧劲和与范柳原对峙爱情的聪慧,她虽内心苦不堪言,但有心想打破这种困局,因此眼神中既有对自身命运的哀伤和青春逝去的恐惧,也有一股不甘心的狠劲,而不是全然缪骞人式的软弱无措、木讷无语。
同样是“物人对照”的镜头语言,关锦鹏在《红玫瑰白玫瑰》的电影改编中诠释得更贴切自然。他在影射红玫瑰王娇蕊、白玫瑰孟烟鹂的性格形象与心理动态时,采用变形的画面构图、有别的光影变化。用不规则、多样式的线条,暖调色彩的墙砖和淡黄色的光线影射王娇蕊的热辣奔放,勇敢自信;用规整单一、构图简洁的白墙砖和冷色调影射孟烟鹂的传统保守、含蓄内敛,并且物像与人物融合在画面中,自然地烘托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而不是物与人分离,通过目光在意象上的落及与之构建关联,生硬的物化人物心理。
电影中白公馆里人物与人物的关系与走位,近乎是一出舞台剧的表演,尤其在中景和全景的镜头中,眼神等微表情都淡化处理了,难以感受到个体小人物的心理状态。在改编电影《红玫瑰白玫瑰》中,振保兄弟二人与王士洪见面时,关锦鹏设置了具有纵深感的中近景镜头和虚化处理,突出主要人物,王娇蕊出场后,甚至只单独让振保或娇蕊入画,更加突显主次,并用了眼神和手部的特写表现人物的心理,构图时让人物占满空间,使得画面狭小拥挤,烘托出暧昧的气氛。因此丰富的蒙太奇技法可以让人物关系层次分明,人物的心理得到饱满体现,而许鞍华导演的处理显得平淡仓促。
(二)旗袍
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开始盛行,它不仅是上海时代文化的象征,还构成了上海女性形象和精神的重要部分,张爱玲在《更衣记》中这样说道: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袄”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在小说中共有三处对旗袍的描写:第一处是宝络相亲时特制的累丝衣料旗袍;第二处是白流苏与范柳原初见之后的月白蝉翼纱旗袍,第三处是在停战后白流苏回到家拾起的一件蜜合色衬绒旗袍。三处旗袍的描写虽着墨不多,却在恰当的时分映射出人物的心境,同时显示出张爱玲对旗袍服饰的偏爱。范柳原说白流苏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女人,想象她穿着旗袍跑在森林的模样,可见白流苏的旗袍形象是推动二人情感深入的重要存在。
许鞍华在电影中着重了旗袍的视觉存在,电影中的白流苏共穿过近二十件旗袍,在烘托人物形象、影射人物心理时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白公馆时,白流苏穿过的三件旗袍都是极素的样式,直到她坐上去香港的轮船,才穿了一件带有紫色条纹的款式,这种对比暗示了她在白家寄人篱下的处境。在香港与范柳原相处期间,流苏换了十几套颜色丰富的旗袍,隐喻着流苏的生活有了希望和光彩,同时许鞍华借旗袍的更换代表暗示日子的变化。近二十套旗袍大多以素色为底色,配有浅色系的条纹,与电影柔而缓的叙事基调相一致,是许鞍华个人风格的体现,电影也荣获了第二十五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服装设计。
(三)电影院和舞场
20世纪30、40年代,电影院和舞场是上海风行一时的娱乐消费场所,其中电影更是张爱玲生命中重要的精神文化,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评论道:“她的这种个人爱好潜入了她的小说,构成了她小说技巧的一个关键元素。在她的故事中,电影院既是公众场所,也是梦幻之地;这两种功能的交织恰好创造了她独特的叙述魔方。”张爱玲的成名作《第一炉香》中,姑妈梁太太的私人宅院在葛薇龙看来,“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在1943年发表的《倾城之恋》中,电影院是男主人公安排见面的场所;写于1947年的小说《多少恨》,在开头部分细致地描绘了电影院,称之为“最大众化的王宫”,这反映了电影院在上海已经成了公众娱乐的普遍方式。
1927年中国电影院达到106家,分布于十八个大城市,上海就占了26家;1933年,著名的大光明影院开张;“三十年代末,上海已经有了三十二到三十六家影院”。④本土电影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电影成为上海人新的生活习惯,同时电影院作为相对封闭、幽暗的环境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现代上海人逃避高压生活、寻求个体精神独立的空间场所。正如三奶奶所说的徐太太的猜想,范柳原将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安排在电影院,“坐在黑影子里,什么也瞧不见”,“要把人搁在那里搁个两三个钟头,脸上出了油,胭脂花粉褪了色,也可以看得亲切些。”范柳原身为父亲在外的私生子,独自生活在国外多年,环境促使了他善于斡旋、伪装的面目,电影院是范柳原和白家众人第一次正式见面的场所,他在相对私人的空间中更方便思虑筹划、稳重行事。同时电影在此处隐喻了范柳原和白流苏的爱情,理想化、虚无化,彼此都带有表演的成分。
20世纪20年代早期,第一批舞厅在上海开张;到了30年代,舞厅成为上海城市环境的一个标志,不仅是精英阶层,小市民阶层也经常出入舞厅,成为上海日常娱乐生活和社交的一部分。张爱玲在《谈跳舞》的散文中认为:“就普通的社交舞来说,实在是离不开性的成分的。”第一次的舞场会面,范柳原便对白流苏说了许多“她一句也不相信”的、“对女人说惯了谎”的话,没有直接的跳舞描写,但从白流苏的心理活动中足可见当时气氛的暧昧,范柳原那情场老手的油滑一面。第二次在香港舞场二人都在用漂亮的话语斡旋,谨慎试探对方,攻占心理,显示出他们各自精明算计的心思,同时再一次将暧昧的情感升华。
电影中关于上海电影院和舞场的场景,许鞍华完全依照着小说,通过三奶奶的一句话带过了这个情节。对于小说而言,这种技法能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间,且张爱玲的文字语言已然烘托出了上海的时代氛围;但是电影作为视觉语言,需要通过镜头画面建构人物形象,布设时代环境,而许鞍华略去了二人第一次情感交锋的场面,使得范柳原的形象和性格构建不够饱满,二人的动机和目的没有交代和过渡,导致在香港故事中第二次跳舞场景显得过分亲密突兀。
李安改编的《色戒》有心地设计了“电影院”这个意象,在影片中每次“电影院”放映的电影或展示的电影海报,都在暗示着人物的命运走向或时代环境。据李欧梵在《苍凉与世故》中考证,《色戒》中出现的电影院情节直接引用了三部电影的片段,这三部电影都是与小说背景同时期的影片,李欧梵认为,“李安用老电影来‘重现’老上海的都市文化面貌,并从而反映片中人物的心态,因此使得改编后的情节和气氛更为多彩多姿,这就不简单了。”⑤
范柳原与白流苏在第一次见面时便跳了交际舞,白流苏成功“给了他们一点颜色”,可见二人在舞场的亲密接触使得流苏与白家人的关系充满火药味,许鞍华将交锋高潮放到了香港饭店的舞场中,然而也是在“顶古老的舞场”中的一次上海情调的表演。整个舞场的色调和光线处理得极为温暖浪漫,许鞍华采用了一个将近两分钟的长镜头跟着二人的舞步摇曳、旋转,二人近距离地浓情蜜语,气氛达到前所未有的暧昧,整个世界仿佛都剩下这对才子佳人,最终似乎要将观众迷醉在这温柔乡中。
在小说中,张爱玲只书写了二人跳舞时的对话,许鞍华设计了许多浪漫元素,使得故事的爱情情调成为主要基调,加上电影删掉了原著中实则苍凉的结局暗示——“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所以纵观许鞍华对小说的改编处理,她的爱情情调盖过了本该是主基调的人生“苍凉”感,使得故事偏离了张爱玲的小说内涵和主题,成为一部失败的改编电影。许鞍华后来也承认道:“《倾城之恋》最大的教训,是我没抓住作品的精神,那个作品的精神其实是很西方、很讽刺的,而不是缠绵的大悲剧。”
三、结语
综合上述对上海都市文化的细读和比较,许鞍华导演改编遵循的最大原则就是爱情基调,这正是她对小说的最大误读,她遵循着原著人物的出场顺序和场景变化,却没有真正遵循和领悟小说的精神内核和主题意义,导致原小说的苍凉基调淡化,失去了电影应有的光彩和价值。
在上海时代氛围的再现上,许鞍华显然不如后期对香港地域的深刻体验和考究,她以异域人的地缘身份,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再现变成了“布景和道具”,没有生动的烟火气,“更谈不上情调”。正如李欧梵在《苍凉与世故》中所言:“也许,这种情调非身历其境或真有亲身经验的人是拍不出来的。”
从20世纪80年代诞生了第一部张爱玲小说改编电影以来,有两个奇特的现象一直存在。其一,目前对张爱玲小说进行电影改编的导演都是港台身份,内陆导演在电影领域的涉足基本空白,只有少量艺术价值不高的电视剧作品,大抵由于张爱玲和她的作品带有政治敏感性。但是笔者认为,张爱玲小说的改编难点和重点依旧是基于爱情叙事下关乎人性和生命的苍凉主题,而改编者大可将政治和历史因素进一步消解,如果内陆导演能以上海人的地缘身份对张爱玲小说进行改编与创作,这将呈现出与港台导演不一样的叙事风格和影视效果,或许能更接近张爱玲上海人写作的心境。
其二,尝试改编过张爱玲小说的导演,在改编的风格上都不约而同进行了温情化处理。许鞍华将《倾城之恋》中男女主人公的算计彻底沦为爱情套路,最终成全了这对深情款款的乱世佳人;在《半生缘》中,许鞍华弱处理了小说中姐夫强奸曼桢的细节,姐夫从主观故意变成喝醉后的“失手”,并删去了曼桢嫁给姐夫与其生活再离婚的情节,淡化了情节的张力和人性的丑陋;关锦鹏在《红玫瑰白玫瑰》中立足于佟振保的男性视角,对他的形象性格和行为动机都赋予了一些合理和同情的意味,淡化了小说中张爱玲以女性视角对佟振保的反讽情感;《色戒》中李安让王佳芝和易先生产生了真正的爱情,二人在真爱的感召下都暂时忘却了对方身份的危险性,各自奉献了一份真心。
这些导演的改编与张爱玲的不同之处在于,张爱玲受自身家庭环境的影响,从小看尽人性的冷漠与亲人间的算计,在写作中赋予每个人的行为动机都是现实而世俗的;而以上导演却将人性处理得更温情、更英雄主义,消解了张爱玲小说的“不彻底”“苍凉”意味,让人物形象满足了大众心理对虚构故事的美好想象,与现实环境保持了距离,因此改编后的故事弱化了普通人的日常传奇,多了一种英雄主义的传奇,满足了消费时代大众对文艺作品的心理渴求。
基于大众文化市场的语境,导演给改编电影适当添加一些个人风格和温情化处理都是可取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上海时代氛围透射出世俗人性和苍凉的生命体验,将风格化、温情式的外衣作为电影的点缀,充分发挥导演的才华和创造力,不再只是机械地复制小说,而能让小说可视化后使得大众产生新的启示和回响。
注释:
①李欧梵.苍凉与世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5.
②李欧梵.苍凉与世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98-99.李欧梵将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中“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的“华美”,引申为:“华美——是一种非道地中国(或上海,其实在张爱玲眼中上海就是中国)而极富东方主义色彩的华美。”
③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④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⑤李欧梵.苍凉与世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