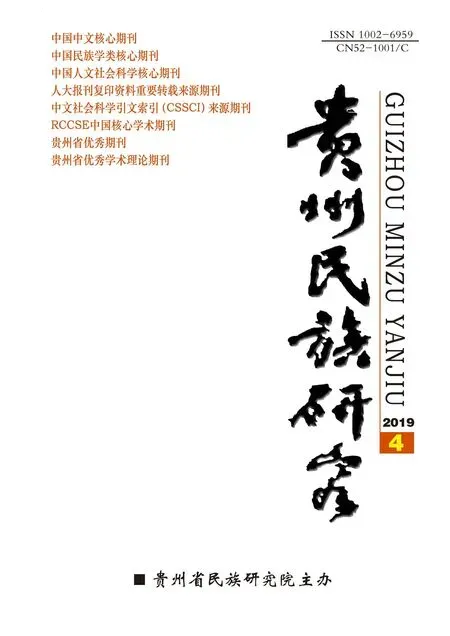清宫太监喇嘛考
——兼谈内廷藏传佛教仪式与信仰
2019-03-17郎丰霞
郎丰霞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目前学界对清代太监群体或制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太监的管理与惩处、防止阉宦专权、个别宦官事迹考等,成果相对单一且薄弱。本文拟在细化太监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能够兼及丰富今人对清宫宗教仪式与信仰的认知。关于此专题,罗文华《乾隆时期宫中内监僧制度考》[1](以下简称“罗文”)一文实为奠基之作,但因清宫档案史料的庞杂、分散,且长时间以来一直未及整理公开或出版,迟迟难以取得进展,近两年相关档案史料的接续开放与出版,惠及学林。笔者亦得以承借东风,细化、订补前人研究的同时拟对清宫文化史进行探讨。但终因史料不足征,尤其是顺治,康熙时期档案无着,有些问题仍待进一步挖掘,现仅据所见略陈己见,以祈方家。
一、太监喇嘛安设之若干情形辨析
清宫太监喇嘛始设于何时?清宫中设置过太监喇嘛的地点有哪些?学经太监安设于何处?等等,此类问题或模糊不清或探讨不详,下文将尽力辨析之。
清宫内廷以宦充僧之例,沿自前明,又有所增损。明朝历代帝王多行优礼藏传佛教之策,永乐帝更为刊印藏文佛经而特设番经厂,后明世宗嘉靖帝虽因笃信道教,荒废藏传佛教事务致番经厂岁渐倾圮,隆庆、万历朝终能及时缓解对蒙政策,笼络蒙藏、刊赐番经,葺修番经厂,诵经、法事不辍[2]。“本厂内官,皆戴番僧帽,穿红袍黄领黄护腰,一永日或三昼夜圆满。”[3]番经厂充喇嘛太监、首领者十余名,皆为临时兼差,遇万寿圣诞、元旦等节唪唱经咒、大作法事,平日仍为主供服侍内廷之太监,未成定例,大不同于清代逐渐制度化的太监喇嘛职设。
据史书所记来看,清宫内廷太监和尚始设时间与线索较清晰,应该在顺治朝。此与顺治帝崇信禅宗、礼遇禅师有关,曾特命玉林通琇等在万善殿弘法,供三世佛并选老成太监剃发为僧,唪经焚修。[4]然太监喇嘛之始设情形、早期情况则不甚清晰,现仅据档案史料做合理推测。
首先,清仍明旧,保留番经厂、道经厂、汉经厂、大西天经厂的基本设置包括内监僧,隶属礼部管理[5],清早期太监喇嘛大概源出于此,而非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始设之中正殿。康熙时于经厂附近建修嵩祝寺作为章嘉呼图克图的驻锡寺庙,因番经厂、汉经厂皆地近嵩祝寺,雍正十二年初(1734年)议修嵩祝寺、番经厂时,曾将番经厂居住之太监喇嘛移居大西天。可见此前至少番经厂常住有太监喇嘛。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时番经厂与嵩祝寺一同修理,但其并未被嵩祝寺完全兼并,“仍照旧式修理作两所,旁开便门行走相宜”,[6](册12,p.188)乾隆时期,番、汉经厂旧址才逐渐改建成三寺格局。考档案、碑记具体改建过程为:乾隆十年(1745年)十一月,汉经厂逐渐归并嵩祝寺。[6](册33,P.52-50)乾隆二十三年 (1758年),命建造智珠寺同时修理法渊寺,[6](册53,P456-452)可知此时法渊寺已建且准备改建智珠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命修理嵩祝寺、法渊寺等,[6](册94,P293-284)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二月,又命总理工程处等整修嵩祝寺、智珠寺。[6](册139,P64-58)第二年,重修三寺完成后,乾隆亲撰《法渊寺碑记》,据碑记内容亦可知三寺与前明经厂的承继关系[7]。其次,至于慈宁宫,据档案所见亦有长时间的太监喇嘛安设,从孝庄太皇太后崇信藏传佛教来看应该有较早安设太监喇嘛的可能性,但笔者所见慈宁宫太监喇嘛安设情形的记载已到乾隆时期。
清宫设置过太监喇嘛的地点除了番经厂、慈宁宫、中正殿、大西天、宝相寺、永安寺、圆明园清净地外,还有静宜园弘光寺、静明园圣缘寺,[6](册47,P.553、560)且据更为详细的档案分析来看,多处地点的设置过程与情形有待更正。
北海永安寺不仅有较早的太监喇嘛安设,并且也是主要的学经太监设置地点之一,负责调补遗缺太监喇嘛。雍正元年(1723年),孝恭仁皇后梓宫奉移之日永安寺等四寺曾请喇嘛诵经,乾隆十二年(1747年),和硕礼亲王请旨大行皇后梓宫奉移援例唪经事,因永安寺住有太监喇嘛而移至雍和宫,可见永安寺太监喇嘛安设应在雍正朝或乾隆初期。[8](P255)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永安寺有太监喇嘛十名,[6](册47,P608-606)乾隆迄嘉庆十九年(1814年)之前,永安寺太监喇嘛人数基本维持在六至十名之间,期间或因病故、患疾不愈裁退为民等情调补、添裁者为常例[9]。嘉庆十八年(1813年)十一月,总管内务府议裁永安寺、大西天太监喇嘛,二处殿座交奉宸苑管理,唪经之需拟交喇嘛印务处,太监喇嘛八人内三人脱去僧衣拨进当差,其余五人调拨中正殿[10]。
慈宁宫向为太皇太后、皇太后所居并经多次修缮添建,乾隆时已建修为宗教气息浓厚的慈宁宫一区,包括英华殿、大佛堂、慈荫楼、咸若馆、宝相楼等,兼设太监喇嘛与太监和尚。正因慈宁宫与太后崇佛之举关系密切,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孝圣宪皇太后去世后,慈宁宫太监喇嘛归并中正殿,慈宁宫此后再无太监喇嘛安设,似成定论。其实不然,至少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慈宁宫仍见有安设副首领太监喇嘛一名,太监喇嘛五至六名[11]。
太监喇嘛主要来源于学经太监,其中经文唪诵熟习者,需经总管内务府奏请由呼图克图授戒披剃穿黄,方能添补太监喇嘛,且学经太监之安设地点不止永安寺一处。乾隆十二年(1747年),永安寺既安设有学经太监,[6](册42,P160-159)中正殿、慈宁宫、永安寺遇有太监喇嘛缺出,例由永安寺学经太监内拣选挑补。[6](册115,P400)其中,大西天经厂额设之太监喇嘛照万善殿太监和尚例,向由礼部行文招募年幼太监咨送内务府选补[12];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奏准亦由永安寺学经太监内充补,与他处划一[13]。据档案来看,嘉庆元年(1796年)至嘉庆十四年(1809年),学经太监主要安设地点为中正殿和永安寺,嘉庆十五年(1810年)二月份增设大西天常设学经太监三名;[14]嘉庆十六年(1811年)至十八年(1813年),三处安设之学经太监互有调动,至嘉庆十八年底,彻底裁撤永安寺、大西天太监喇嘛并学经太监,拨派清净地当差;[10]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始,学经太监常设地改为中正殿与清净地;道光元年(1821年)始,统归中正殿一处,同年底将中正殿四名学经太监尽数调补为太监喇嘛[15]。道光十四年(1834年)迄光绪朝,学经太监虽多有久悬未补等情,但中正殿尽力维持一到两名的额设以备充补[16]。
其他地点,如长春园宝相寺,乾隆年间就安设有太监喇嘛,但无首领与副首领职,常年设有太监喇嘛三名左右以应差事,之后随着喇嘛人数的递减,道光十七年(1837年)遭彻底裁撤,清宫太监喇嘛安设地仅剩中正殿与清净地[17]。中正殿至少乾隆初年已有太监喇嘛安设,[8](P221)常着亲王管理中正殿事务,且乾隆以来中正殿念经处一直作为清宫太监喇嘛的调补、管理中心,喇嘛层级设置最为完善,咸丰十年(1860年)圆明园遭英法联军劫掠后,同治元年(1862年)将清净地太监喇嘛六名尽拨中正殿[18],清末太监喇嘛无人充补,内廷各差不得不委派外庙达喇嘛承应,宣统二年(1910年),仅剩中正殿首领太监喇嘛曹瑞清一人[19]。
二、角色与境遇:太监喇嘛制度化设置的背后
清宫太监喇嘛群体设置逐渐制度化、常态化的表现有如下几点:一、不同于前明临时兼差番僧之内监,而为逐渐专业化的职业喇嘛,主要由学经合格的学经太监受戒、披剃与穿黄后成为太监喇嘛;二、有严格的职衔与钱粮等级、额设与升补程序、违禁犯罪惩处规定等,并载入宫中与内务府则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三、分布于更为广泛的皇宫禁苑之中,佛事活动更为频繁与日常。
“伊等虽是喇嘛,究系太监”[10]一言,体现了清宫太监喇嘛所扮演角色的实质。清朝汲取前明阉宦之祸旧训,置太监事务管理于内务府的严格控制之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内务府更是将礼部对太监的收录、选用之权,收归己有。据档案来看,其多数来源于包衣三旗各管领下人,年龄、体貌、公费钱粮等项专档存记;他们学习唪诵的佛籍经典多为基础常用篇目,如《无量寿佛经》《药师经》《吉祥天母经》《护法经》等。
太监喇嘛长期住庙焚修念经,除负责本处洒扫、看管等差使外,还须承应宫廷各处的唪经、道场所需。遇有久病不治、耽误差使者,不仅全行裁退其每月所食钱粮米石,且给为民执照,令其自谋出路[20]。若已为太监喇嘛而发现学艺未成者,则惩其剥黄,并交总管太监补挑宫内下贱或繁重差事[21]。首领太监喇嘛、太监喇嘛有维护、看管本处财物之职,若疏于防范导致宫物丢失被窃等,轻则革职、罚俸,重则杖责甚至发遣[22]。
太监喇嘛虽会因承差唪经或参加佛事礼节而得赏项等物,但总体来看,其月食钱粮与一般太监无异。首领太监喇嘛食三两钱粮,太监喇嘛食二两钱粮,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内务府奏准:“太监喇嘛、太监和尚著照宫内太监等得给公费,不必给与菜蔬口分,其外边喇嘛和尚仍照旧给与。”[23](册4,P86)“首领太监喇嘛每月得给公费大制钱七百文,太监喇嘛每月得给公费大制钱六百文,移咨广储司转行得给。”[23](册4,P278)
太监喇嘛设置逐渐制度化的背后,是来自内务府机构的严格管理与监督。对于违禁犯罪者,内务府通过剥黄、勒令还俗、发往铡草、枷号、杖责、减食钱粮、分拨外围,甚至发遣为奴等则例规定,实施严格管控。乾隆十五年(1750年),永安寺学经太监王炳自述因畏难学经、管教严苛,怕受责打而初逃,经管辖番役处缉拿归案,内务府依太监违制例,判其发往翁山铡草一年,年满发往热河当差,减食一两钱粮。[6](册37,P489-487)乾隆十七年(1752年),永安寺学经太监马进忠同因逃走,后因害怕而自行投回,内务府以太监出逃例,鞭八十、发往热河,减食一两钱粮。[6](册42,P160-157)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总管内务府奏请更定惩治逃逸太监条例,若系初次逃走太监,情罪轻者,仍照旧例发往吴甸铡草一年,期满交总管太监等分拨外围当差;二次逃走者,即发往黑龙江给索伦为奴。[6](册68,P304-297)至于其他情形,如妄求呈控、不安本分、援结外朝等,更是从重治罪。对于缉拿出逃太监喇嘛之事,不仅内务府番役处要严行访稽,刑部、各该旗等需一体遵行严缉,被缉者的体貌、年岁、穿戴等项一并开列、相互知会。[24]
众所周知,清代宫廷太监额数不仅明显少于前明,且常处于缺额状态,尤其是清后期。乾隆十六年(1751年),曾令将太监额数定为三千三百名,但从实际人数来看,往往不及定数,太监喇嘛人数更是不断递减。鉴于此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清后期对于太监喇嘛违禁犯罪案例的惩处力度有所缓和、减轻。例如同治二年(1863年),中正殿太监喇嘛刘来安等二人皆初次逃走被获,罚责六十板、枷号后,仍移送中正殿原处当差;同治三年(1864年),刘来安二次逃走被获后,仍罚责板、枷号后,移送原处当差,减食赏银。[25]尽管如此,清廷仍然保持安设太监喇嘛的定制直至清末,这提醒我们不可忽视其在清宫体制运作中的制度化意义。
三、清宫内廷的日常仪式与信仰
有学者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中正殿念经处的建立,标志着宫廷内藏传佛教活动的制度化。”[26]笔者以为,中正殿的建立仅为宫廷藏传佛教活动制度化的开端,此后宫中办造佛像与喇嘛念经等事务及管理才逐步展开。康、雍以来,尤其是乾隆时期,清宫藏传佛楼、殿、堂不断添建完善,慈宁宫区、中正殿区、宁寿宫区、建福宫花园区等,包含多处藏传佛楼建筑;养心殿、养性殿、寿康宫等暖阁内,亦皆设有佛堂;圆明园、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内,更是佛香四溢。与之相呼应的,是一系列宗教仪式、活动与礼节的逐步开展,如喇嘛唪经、拈香礼佛、造像经卷、唐卡绘画、放乌卜藏、燃灯法会,以至于本论太监喇嘛的常态化安设等等,这些特征不仅仅是清朝控驭蒙藏政教策略的外延表达,更是清宫内廷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场景与元素。
由前述可知,以太监喇嘛的身份与角色而言,虽不可能在清宫宗教活动与仪式中扮演主角,但却在清宫内廷频繁的宗教活动中扮演着基础角色;也恰恰是因为这种沿至清末的“日常”,为我们揭示藏传佛教在清宫中的宗教文化意义提供了窗口。
从清代皇室的起居注册、园囿档案、帝后生活等档案史料可以看出,拈香、礼佛、唪经等宗教仪式,已成为清帝及皇室成员参与的日常活动,因皇宫内苑外庙喇嘛不便经常出入,太监喇嘛遂成为承应各差的必备人员。清宫定例每年十二月初九日,中正殿都会举办送白伞盖大回避巴苓礼节,皇帝会亲诣中正殿并于坛城前拈香,管理中正殿事务大臣率呼图克图、喇嘛等在御前跪递舞恰尔转查克苏穆,[27]转查克苏穆毕,太监喇嘛等需将舞恰尔查克苏穆送出昭福门外,接下来呼图克图、喇嘛等完成撂巴苓、唪吉祥讃经等环节,仪式结束。[28]总之,凡皇帝亲诣拈香各佛堂殿座,皆需太监喇嘛预先恭备内廷唪经,记录拈香日期、香支数目等事。
唪经以祈祥、祝寿或纪念等事,是清宫中举办最为普遍且频繁的宗教仪式之一,太监喇嘛则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每年正月初一,中正殿太监喇嘛于中正殿唪吉祥天母经成为常例。[23](册4,P164)并且,中正殿太监喇嘛一并承应养心殿、九洲清晏、碧云寺等处的念经差使。雍正以后,养心殿日益成为融皇帝起居、理政、礼佛等功能于一身的日常处所,每年正月、二月、四月以至十二月中的多日,太监喇嘛都会在养心殿佛堂唪经,直至宣统年间终行不辍[29]。圆明园殿、思恩室等处按期放乌卜藏、唪经亦由太监喇嘛完成。[23]宫中其他地点,如慈宁宫、毓庆宫、储秀宫、钟粹宫等,或因曾为龙居之所,或因主人的崇信,常着太监喇嘛唪经。[29]如嘉庆二年(1797年),着首领太监喇嘛等在毓庆宫后殿安佛唪沐浴经、长寿经、乌卜藏经等。[30]永安寺、大西天等太监喇嘛安设地,皆有唪经常例。[31]
太监喇嘛虽以服侍内廷唪经、应差为主,自身并无高深佛学修养,但也不乏虔诚信仰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进京朝觐,参观完各宫殿佛堂,“回到丹杂康孜林殿后,应管事太监喇嘛为首的各位太监的请求,摩顶传授《白伞盖佛母陀罗尼经》。”[32]其他宗教仪式礼节中也会有太监喇嘛的身影,如参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恭递丹书克仪注等。[33]
四、结语
本论的写作初衷,不仅在于厘清与考察清宫太监喇嘛群体设置的相关史实与变迁历程,也在于以小见大为我们了解清宫宗教活动与信仰提供一种视角。众所周知,清宫宗教文化丰富而多元,以坤宁宫祭、堂子祭为代表的萨满文化追述着满洲最初的群体记忆与身份认同;汉地佛道文化也曾在顺、雍等朝的清宫中迎来了发展的小高峰;至于藏传佛教在清宫中的深远文化影响,则经常被“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的政治口号牵引而去,忽视宗教、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互通。藏传佛教文化对于清宫内廷的重要影响,由本文或可见一斑。多元宗教、文化的兼容并包亦是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最好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