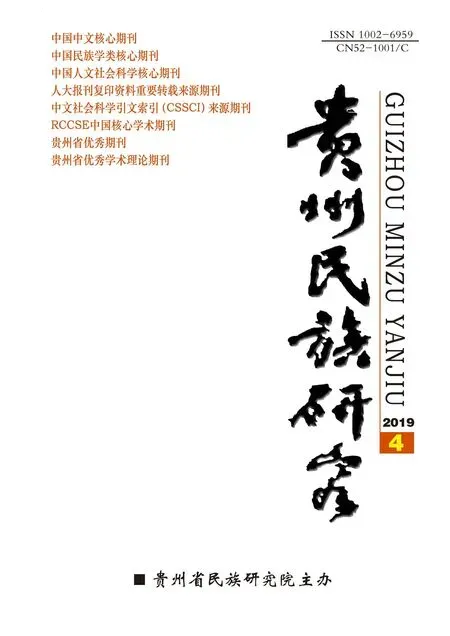改土归流与地方社会转型
——以明清之际川东威远卫的置废变革为例
2019-06-04张洪滨郭声波李大海
张洪滨 郭声波 李大海
(1.暨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632;2.中山大学 历史系,广东·珠海 519082)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廷倾全国之力发动播州之役,次年又对播州实施改土归流,力图将原杨氏土司辖地改为明王朝直接管控的普通郡县。此次改流包含“复郡县”“设屯卫”“设兵备”“设将领”“急选调”“丈田粮”“限田制”“设学校”“复驿站”“建城垣”“顺夷情”“正疆域”等方面的内容,[1]坚持“今既改流,自当纯用汉法”[2],意图将播州地区全面改属流官体制。这其中“复郡县”和“设屯卫”两项内容尤为重要。复郡县意在促进土司地区由“间接行政区”向直接行政区转变。设屯卫意在开屯养兵,借以巩固播州改流的政治成果。实际上,关于威远卫的设置还有更为广泛的意义。明中期以后卫所系统面临衰败的危机,汉兵战斗力亦大不如前,明廷在边疆地区开始吸纳和征用大量土兵驻守藩篱。万历二十九年设置的威远卫即是一个汉土军民混杂并居的卫所。播州平复后,明廷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地方土目势力,并将他们连同异地留守兵士一起编入新设卫所进行管控。这就导致了改流以后地方土客势力的不断争斗与冲突,渐而也促进了播州土民的“汉化”。借用郭声波教授提出的“圈层结构理论”,明王朝对播州的改流旨在打破地理空间中固有的政区圈层结构,实现边缘区的民族自治区向政治中心区的内迁。[3](P12-13)换言之,改土归流的目的在于改变原先的土司世袭体制进而转化为封建州县流官体制,而明清之际播州地区的社会变迁过程正是这一行为的具体展现。本文的论述正是基于以上理论,将威远卫的历史沿革分为初创、衰变、蜕变三个时段,分别加以论述。
一、初创:“双重政区”与土流之争
(一)县卫混置的“双重政区”
万历二十九年明廷在遵义白田坝设威远卫,隶四川都指挥使司,是谓川东威远卫(以下均称威远卫)。史载:“议于白田坝建置一卫,设立指挥、千户等官,安插官军,立屯防御,卫名候钦定。”[2](卷358,P6686-6687)之后万历皇帝赐卫名“威远”。
威远卫设置的目的在于“安插官军,立屯防御”,此主要是针对参加平播之役留镇地方的士卒。关于留镇士卒的具体人数,史书记载颇有疑义。按总督李化龙的善后方略,预设前、后、中、左、右五所共五千兵士,[1](卷6,P255)但道光《遵义府志》(以下均称《府志》)载:“威远卫,在(府)治左,前、后、中三所”[4](卷7,P167)。可见,威远卫的设置并未完全依照李化龙的设想。
威远卫在设置之初仅有三个千户所,共计兵丁三千余人。随后又有许多土著兵民不断划拨至卫所辖下,壮大了威远卫的实力。根据《府志》卷十二所载可参透其大略。史载:
自平播设府后,所属一州四县复业旧民、入籍新户,除正安州土州同、土州判二员,威远卫指挥等官及务川民杨瑜等,各于正安、遵义、仁怀拨置田粮成丁外,实在田丁一万四千五百四十一,地丁二万八千八百三十三,共四万三千三百七十四丁口。万历二十六年[笔者注:应为万历三十六年]攒造,除绥阳、桐梓、真安仍旧外,五属实编共三万五千四百零一丁口。[原注:《孙志》]
遵义县:自平播设县后,旧民、新户成籍,除卫官折俸田丁外,实在田丁六千六百二十四,地丁三千二百三十一,总共九千九百五十六丁口。万历三十六年从实编造,总四千四百零一丁口。
……
仁怀县:自平播设县后,旧民、新户成籍,除卫官折俸田丁外,实在田丁一千九百三十四,地丁一千九百四十三,共三千八百七十七丁口。万历三十六年清造减丁不减银,止余一千三百五十八丁口。[4](卷12, P271-272)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丁口统计制度与明代实施的一条鞭法内容有关,即“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5](卷78,P1902)。可见丁口统计是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此法简便易行,“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根据引文所述年代,其丁口数据应是遵循了一条鞭法制度统计出来的。播州改流后将遵义府辖境所属旧民、新户统一登记造册,这自然包含了许多战后留驻该地的外籍将士。引文中第一次丁口统计数字当是指万历二十九年各州县的丁口数目,此时军、民一体,还未完全分开造册。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遵义、仁怀二县黄册所载丁口数目发生巨变(注:遵义府其他州县丁口数目基本未变),其原因是军、民户口已分属兵、户二部,当需分别造册。换句话说,在威远卫设置以后,遵义、仁怀二县逐渐于辖区内部拨出部分土地、人口划归到卫所名下,将原先部分田丁、地丁转化为屯卫丁或卫所丁。因而,笔者得出结论:“卫丁数目=第一次统计数目(军民总丁口)-第二次统计数目”(民籍丁口)。因而万历三十六年威远卫实有丁口8074,遵义、仁怀二县剩余丁口5759。
威远卫之丁口数目远大于遵义、仁怀二县之丁口数目,县署流官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屈于被动地位。之所以造成“卫重县轻”的局面,是因为明廷将更多的人口、田地编入到屯卫之中。平播战争期间,总兵官吴广率军由合江而发,大军行至播西仁怀县境,“陶洪、安村、罗村三寨土官各出降,他部来归者数万,广择其壮者从军”[5](卷247,6408)。战后当地从征人员均领照复业,而各里之土民亦多被安插至各屯服役。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前后,又有一批土目向明廷献土,他们均得到了朝廷的封赏。史载:“播州平后建设屯卫,以土官舍军功及献土一事,分别改授职级,填补新卫。”[2](卷486,P9153)此次献土事件是在万历三十六年攒造黄册之后,预示着又有部分土地和人口由遵义、仁怀二县划入卫所名下。由此不难发现,威远卫是一较典型的准实土卫所,其附廓于遵义、仁怀二县构成县卫混置的“双重政区”。由于资料所限,笔者无法查证威远卫屯田在遵义、仁怀二县各里之具体范围,因而只能大体标出威远卫的总辖区,如下图所示。李新峰指出:“同城实土卫所的总辖区,存在平等分享和主客共享两种情况,介于彻底混杂和明确分区两种极端情况之间。”[6]不可否认,遵义府辖下县卫政区的设置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县卫共享的情况,但更需认识到,由于卫所辖区内土目势力依然强大,县署流官政权实际管控范围非常有限。

遵义府辖区示意图(1601年)
(二)土客冲突及其由来
随着卫所、军屯的不断扩充,遵义、仁怀二县治下土地、人口逐渐减少。加之当地存在诸多土目豪强,新生流官政权的发展步履维艰。如改流之初的“仁怀设县风波”,即是因为土城里袁氏豪强的阻挠而被迫将仁怀县城选在县北四塞之地留元坝(今赤水市老城区)。时留元坝人烟较少,交通多有不便,作为县治所在极为尴尬被动,因而仁怀县早期官员皆将迁移衙署一事当作立县治民的头等大事。
除去土客势力的博弈,下层汉土军民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平播后许多外来将士留驻遵义、仁怀二地,起初他们与土民对面而居却又不相来往,形成汉土夹杂却又泾渭分明之怪象。仁怀市合马镇罗放收藏《罗氏家谱》(1984年石印本)记载了播州之役后仁怀地方的社会状况,即“土人自治,以安边邻。异地军士,屯堡戍守。军务既战,平时耕耘。土流兼治,政归明君”[7](P57)。所谓土人即是当地旧民,他们多依附于各里之土目豪强,形成较强大的家族势力。在此情况下,明廷逐渐将地方土民连同田地一起划拨至威远卫辖下,让汉土军民共同参与耕作和训练,这样就打破了汉土分立的局面。当地土人在与客民的接触中逐渐被汉风俗感染,其本身好勇仇杀的秉性亦逐渐退化,致使二十年后播州军民“归马放牛以来,武备渐弛,反为诸土司所轻”。[8](卷58,P2707)
二、衰变:屯田受毁与土目失势
天启元年(1621年)发生的奢安之乱对于西南地区来说无异于一次大洗劫,而遵义地区因邻近永宁、水西遂成为受战火蹂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史载:“(天启)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西贼攻遵城,各逃性命,贼恣意掳掠,地荒人绝,千里无烟。”[4](卷40,P912)遵义克复后,其地“田荒民散、斗米数金,僵殍在道”。[4](卷40,P911)面对当下窘境,府县官员“奉行撤屯归民”,[4](卷40,P914)将遵义县内的屯田分给战后流民,任其耕种。如此以来威远卫减损田地、人口过半,仅剩仁怀县十屯之地。关于此“十屯”之名称及具体位置今已很难考证,以笔者参阅地方史料来看,当有毛坝、吴马、后山、河西等屯。除河西屯位于今赤水、习水二县(市)赤水河以西地区外,其他大部分屯区位于当时仁怀县南境。经过奢安之乱,威远卫除去减损大量屯田以外,其内部还发生了三处明显的变化:
(一)威远卫移治仁怀生界
威远卫在奢安之乱期间因屯田被毁、军民流散不得已于战后采取撤屯归民之策,而卫所军屯实仅余十屯之地,主要分布在仁怀南部地区,这就导致了威远卫治所(遵义白田坝)与屯田辖地的分离。在此情况下威远卫需要寻找新的治所,仁怀生界坝遂成为卫治西迁的目标。从地理环境上讲,生界坝地势平坦,位于“十屯”当中,且紧临赤水河畔,与遵义府城相距不远,是卫治迁徙的理想选择。
关于威远卫迁治生界坝一事,史书并无明确记载,只能详加考探。首先是对于“生界”一词的解读。清康雍年间仁怀县训导陶淑李有《设仁怀县议》一文,其言“生界虽系陆路,然小山环绕,势若星罗”,[9](P48-49)又说“仁邑之钱粮若干两,上三里居其半,乃环拱于生界”,又言“夫生界,威远卫故地,宜因其名设一威远县”。“生界”原指生苗所居、未经开化之地。而陶氏文中所言“生界”,实际指“生界坝”,即为有众多山丘环绕的一块平地坝子,在今仁怀市鲁班镇生界村一带。入清以后,生界地区作为威远卫腹地,逐渐发展为县南最富庶之所。陶氏所言“宜因其名设一威远县”暗指此地曾为卫治所在。可见,威远卫在奢安之乱平定后迁治到仁怀生界坝,并拥有了一片比较明确的独立辖区。但此时威远卫仅余一所十屯,实际上相当于一独立的“守御千户所”。《府志》所引《陈志》(清初遵义令陈瑄所纂,成书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为《康熙乙丑志》[4](卷首,P2)载,“(威远卫)置军一千二百名,更班赴府防守”,[4](卷26,P570)正是卫所衰变的直接体现。由于威远卫迁离府城,因而需要派兵轮值守城。
(二)开辟生地
明清之际仁怀县幅员辽阔,含今赤水、习水、仁怀三县(市)之地,实有人口应不止3877之丁口。在当时之仁怀县土目、夷民较多,又有不少苗蛮生地未经开辟,这其中许多人口应该没有计入官方黄册。而天启年间奢安之乱的发生则为明廷根除西南边患、开辟新疆创造了机遇。天启三年(1623年)六至八月间,明军自古蔺、土城两次大胜奢军后趁势南下,一举荡平了奢氏全境,并收回了奢氏长期控制的仁怀西南部地区。[10](卷7,P210、237)此后,竹坝、盐井、九仓、茶园等地皆改由威远卫管辖。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这些新设屯地的出现,威远卫才有了继续保留的需要。
(三)土目失势
仁怀县位于遵义府西境,是明廷防御奢、安二土司的屏障,战乱发生后成为奢军首要攻击的目标之一。史载:“泸州、江安、纳溪、合江、南溪、兴文、长宁、遵义、桐梓、仁怀、绥阳、綦江等府州县并威远、泸州二卫,或为逆贼门户,或与蔺土相邻,悉被攻陷。”[10](卷1,P28)此时,遵义、仁怀二县土目豪强或依附于明廷,或投靠于永宁,皆被卷进了这场战乱之中。在攻陷重庆后,奢崇明又从永宁分兵攻略周边地区,先“擅杀威远卫百户刘训等全家,又欲挟迫土城千户袁见龙兄弟”[11](295)。袁氏豪强本为仁怀第一旺族,势力强盛,但因“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见龙与加衔守备雷安民援辽阵没”,导致家道中落。奢、袁两家历有争斗,崇明叛乱后又纠集播土各土目“立应龙族人杨维新为兴国君,将土城袁氏杀戮殆尽”。除土城袁氏外,其他土目豪强亦在战乱中遭受重创,另有部分倒戈者因战后被政府通缉而被迫隐姓埋名或流落他所。土目失势为流官统治区域的扩大消除了障碍,这在无形之中促进了流官政权的扩展。
三、蜕变:人口集聚与社会转型
威远卫在移治仁怀“生界坝”后实际上变成一个独立的屯田千户所,除卫治是改设以外,其辖下人口、屯田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战后收编了大量的奢氏余党及部分“夷众”,许多参与平叛的外籍军士亦留驻当地。据考证,当有黎民、龙井刘氏,梅子坳汪氏,喜头史氏,二合正觉寺罗氏,三元硐吴氏等家族因戡乱而留镇地方。[7](P59-63)明末威远卫在后期的发展中以生界坝为中心,通过开荒屯田,吸纳流民等方式,加速了对县南生界的开发。崇祯末张献忠率军入川,全蜀为之震动,时“流寇入川,屠戳生民殆尽,惟遵义远在荒徼,幸免毒手,附近之人以为乐土。惊魂丧魄者络绎不绝,蜂屯蚁聚于斯”。[4](卷43,P1018)当此之时,遵义地区俨然成为明末战乱的“避难所”。
明末川民沿赤水河上溯南迁,至茅台村登岸陆行,即到达仁怀南境。此时生界连绵沃土,呈现欣欣向荣之象。有江津人卞运昌,明末廪生,“甲甲避地[乱]因家仁怀之生界”,[4](卷34,P782)后成当地旺族。卞氏一族人才辈出,落业生界坝后,其门中“进士1人,举人2人,贡生7人,廪生、庠生20余人”。[7](P76-77)卞氏族人皆饱尝诗书之士,其后世中多有置私塾、义学者,传教乡邻,德泽一方。此外,生界后田陈氏一族亦为当地文教事业做出了贡献。陈氏先祖以荩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三月随清军入遵义,而后落业仁怀生界。为培养子女,陈以荩从遵义府杨柳街请来蔡建学在家设馆授教。[7](P69)
相比于留元坝,生界坝一隅在交通及区位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仁怀南部地区的崛起。首先,留元坝偏居县境西北,“距府西八百里”,[4](卷3,P87)官民往来需十二日之久,不便于民亦不利于官。生界与府治相距百余里,府卫两地官民往来频繁,商贸为之兴起。其次,仁怀县幅员辽阔,“广约四百里,袤约六百里”,[4](卷3,P87)留元坝作为县治所在很难达到控驭全境的效果。此时生界的崛起正在起着一“副政治中心”的作用,这为日后仁怀县治南迁打下了基础。再者,生界坝是仁怀陆路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其北接茅台渡口,东连遵义,西可至大定、黔西,是川盐入黔的必经之地。因而,生界能够发展为仁怀最富庶之地,并非历史的偶然。
入清以后威远卫旋被裁撤,但生界繁荣之象已成事实。康熙初期“仁邑之钱粮若干两,而上三里居其半,乃环拱于生界;下七里居其半,乃环拱于土城”,[9](P48-49)生界之富裕已在土城、留元坝之上。正因如此,县令罗缔才提出于生界坝、土城二地分设威远、仁怀两县的提议。至雍正八年(1730年),“移贵州遵义府粮捕通判驻仁怀县旧城,其仁怀县署改驻生界地方”,[12](卷98,P307)次年又“题准移县治亭子坝”,[9](P11)这才实现了对仁怀政区的调整改良。在此过程中,生界坝虽没能发展为县治驻所,但却为仁怀县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做出了铺垫。从此,仁怀县一分为二,并由土流并治时代过渡到完全流官统治时期。
另一方面,由于县治南迁,原生界地区“土人”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土人”原指仁怀县改流以前的旧民,其来源非常混杂,改流之初一度不被编入黄册。但由于县治的变动,原生界地区的“土人”成为流官政府直接管辖的县民,其政治身份得到了认可。
四、结语
明末播州改流有着极深远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帝国晚期西南地区的社会发展趋势,是王朝势力入主西南边疆的前奏。同时又要承认明末改流的不彻底性,仍然保留诸多土目豪强。此后随着明末清初西南时局的不断变化,土目势力渐被铲除,新生流官政权也愈加强大,这为西南边疆的稳定与发展带来契机。在此背景下,仁怀县治的南迁并非只是政治中心的转移,更重要的在于流官政权的扩大以及统治方式的变化。威远卫的创置看似简单不符常规,但却举足轻重,是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保障。从实际效果来看,威远卫的政治变迁促进了播州地区由军政向民政的转变,不但发挥了临时政区的过渡作用,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二次改流危机,同时还促进了生界的繁荣,此成为播州改流的最大惊喜。可以说,改土归流绝不仅仅是政治层面上的制度变迁,也包含了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民族身份认同与转变等方面的变迁内容,是王朝实现边疆地区“内地化”的重要手段之一。[13](本文撰写得到暨南大学短期出国访学项目资金支持,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