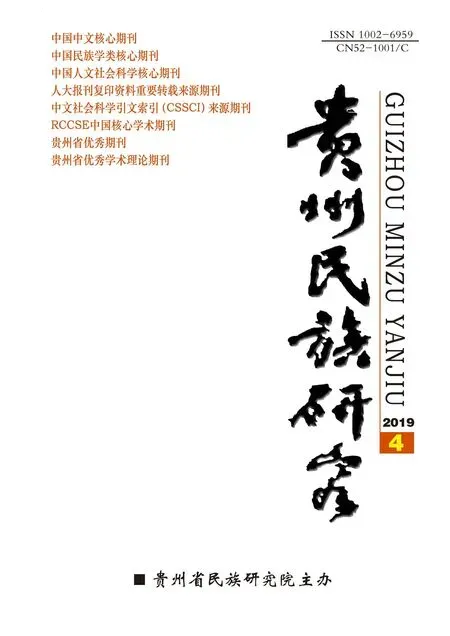贵州台江苗族家庭语言政策调查研究
2019-06-04王莲
王 莲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贵州财经大学,贵州·贵阳 550025)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作为国家重要语言资源,由于使用活力总体上正在发生显著的下降[1],对其保护、保存和抢救是新时期中国语言文字工作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区别于国家语言规划或学校、社区等公共领域语言规划,家庭作为语言保持和转用的重要场域,更适宜考察隐形语言政策,也意味着在语言政策研究中容易被忽视[2]。笔者在梳理家庭语言政策文献时发现国内少数民族家庭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为数甚少,已有成果描述性研究远多于实证研究,理论知识与实证性经验都有待系统建构。
贵州台江县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8%以上,享有“天下苗族第一县”美誉,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大部分家庭成员都是苗语、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使用者,担负着苗族语言与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基于家庭语言政策理论,以家庭为单位,对台江县苗族家庭语言现状展开深入调查,分析了苗族家庭内部的隐形语言政策与家长语言态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儿童语言文化认同的影响。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Spolsky 提出语言政策由语言实践(language practice)、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y)和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三个要素构成。语言实践是人们在语言方面所表现的实际行动。语言意识形态指人们赋予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语言变体一定的价值和地位。语言管理可以影响语言使用者,从而使它们改变自己的语言实践或语言信仰[3],三者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独自一体,对家庭领域的语言政策研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这个政策模型指导下,Curdt-Chritiansen研究发现加拿大华裔父母的语言意识形态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密切关联,父母的教育背景、移民经历和文化性格也是影响家庭语言政策的主要因素[4]。Schwartz将家庭语言管理分为两种实现路径,一是外部社会语言环境支持,二是在家庭内部传承家族文化和培养儿童母语惯习[5]。冲突下的语言意识形态是牵引家庭语言政策变化发展的核心要素,子女的能动性对家庭语码选择和家庭语言意识形态会产生持续反作用力[6]。对此,国内也有研究证实子女并不是被动的语言接受者,父母的语言意识直接影响孩子对某一语码的掌握和使用,但会随着儿童自身的语言意识增强逐步消弱[7]。家庭语言政策往往受到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双重影响,家庭内部因素,如父母的语库、教育背景、职业及家庭成员的结构,也会在家庭语言政策中发挥关键作用。笔者认为,家庭内、外部因素与家庭语言实践、家庭语言意识形态与家庭语言管理之间并非均衡作用,而是各有侧重[8]。因此,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提出如下三个研究问题:第一,台江苗族家庭中的语言实践现状及发展变化如何?第二,家庭语言意识形态是否与家长语言价值认知、苗语能力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第三,家庭语言管理受哪些因素影响?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展开,辅以质性访谈,答题和访谈对象均为苗族家长,他们的母语均为苗语。问卷调查分三步进行,首先,基于对家庭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专家和苗族家长的访谈内容确立问卷维度与题项;其次,在30名苗族家长中进行预测,根据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对不合格题项进行了删除或修改;最后,进行问卷正测。本研究设计了“台江苗族家庭语言政策问卷”,问卷包括四个维度:家长基本信息、语言意识形态、语言实践、语言管理。调查在贵州台江县2 所幼儿园和3所小学展开,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总发放问卷900份,有效问卷814份,问卷有效率为90.4%。其中母亲478人,父亲336人。按子女受教育阶段分类,幼儿园组289人,小学组527人。问卷主要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语言意识维度答案选项从完全不同意(1分)到完全同意(5分),语言管理维度答案选项从从没做过(1分)到一直都做(5分)。问卷三个子维度内部一致性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语言意识形态0.793,语言实践0.768,语言管理0.755,表明该问卷各测量部分信度均处于可接受范围。数据运用SPSS18.0进行描述性统计。为深度挖掘家长的语言态度,半结构式访谈选取了接受过问卷调查的20位家长,采用单独访谈的形式进行。所选样本中父亲和母亲所占比例基本均衡,调查对象以幼儿园和小学生家庭为主,孩子社会化程度低,家长对孩子语言教育的态度和行为较有代表性。
二、结果与分析
(一)家庭语言实践现状及发展变化
在家庭环境下,家庭成员之间语言使用的状况复杂,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父母之间使用语码均存在差异,语码交替使用情况也很常见。父母对孩子使用时间最长的语码是普通话,约为46%,其次是苗语,占39%,方言为15 %。约44%家长跟子女兼说苗语和普通话,其次17%家长兼说方言和普通话。孩子对父母使用时间最长的语码是普通话,约占55%,其次是汉语方言,占33%。苗语约占12%。约35%子女跟家长兼说苗语和普通话双语,其次25%子女说普通话单语。
通过访谈了解到,子女的苗语听说技能明显低于父辈是一个普遍现象。大多数孩子对苗语的掌握处于勉强听懂但口语表达困难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双方使用苗语或汉语方言沟通,但面对孩子的时候,会用普通话替代苗语或方言,只有极少部分家长坚持对子女说苗语。国家关于“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的语言管理措施确实促进了本地人口普通话能力的显著提高。然而,由于政策解读不全面或其他客观原因,只重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而忽视对本民族语言文字保护的“矫枉过正”现象也时有出现。在台江县,幼儿园是孩子语言变化的重要分界岭,普通话侵入式教育使孩子语言使用发生接触性演变,他们会逐渐抗拒说苗语或方言,从而打破以苗语或方言交流为主的家庭语言结构,向普通话使用靠拢。作为教学语言,普通话在小学和中学校园全面普及,名副其实成为通用语广泛应用在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中,加上当地城市化进程中受到汉文化的极大影响,孩子对普通话的价值认可和情感认同在日益增加,而对苗语表现出不感兴趣,不愿意学的态度。与此同时,父母通常会选择不干涉或顺从迁就孩子的语言选择。虽然台江县的小学校园近两年陆续开展了“苗族文化进课堂”系列活动,并取得成绩。但开设汉苗双语课程和苗文选修课程还非常艰难,校本教材编写、师资保障、经费来源也都存在匮乏短缺。
家庭中孩子使用苗语的比率过低的另一个原因是家长对子女的普通话教育愿望降低了苗语的可供性,祖辈成为孩子学习苗语的重要媒介。调查发现当祖父母作为稳定家庭语言成员时会加大苗语在家庭内部使用比率,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与祖父母交谈均是苗语单语使用率最高,超过85%。就有被调查家长坦言一直对孩子说普通话或汉语方言,孩子的苗语是跟家里老人学会的。祖父母往往在保持本族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家庭语言或继承语言方面起到关键作用[9]。台江家庭的祖父母通常只会苗语,不会说普通话,少部分会说汉语方言,祖父母与孩子接触时间越长,苗语输入量越多,孩子习得苗语的可能性越大。孝道文化在苗族家庭伦理规范中占据核心地位,也是促进孩子习得苗语的重要原因。听不懂祖父母说苗语被认为是不尊重长辈的表现。然而,特定交际空间内的多种语言接触必然产生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之间的竞争,功能上形成区分,最终苗语被局限于有老人在场时的家庭内部交流语言,普通话成为父母在特定场合下与孩子交流或对孩子进行教育时选用的家庭教育语言。因此,苗族家庭语言使用情况既受到国家语言政策、地方语言政策和学校语言政策等外部环境影响,也与子女的语言习得、父母语言选择、家庭成员组织结构密切相关。
(二)家庭语言意识形态
孩子在语言社会化过程中会伴随家长的语码变化,这样的语言实践受到了家长语言意识形态的支配。笔者认为,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可具体表现为理性价值评价,如“苗语很有用”“孩子说好苗语和说好普通话一样重要”,和情感价值评价,如“苗歌好听”“苗语听上去很亲切“。调查数据显示,70%的父母认为苗语和普通话对孩子一样重要;89%的父母认为孩子有必要掌握和使用苗语;81%的父母认为应该跟孩子用苗语交谈;60%的父母认为苗语不会影响说普通话,不确定是否影响占22%。概言之,过半的父母都赞成苗语对孩子的成长跟普通话一样重要,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长为双语使用者。一方面,语言是家庭情感联结和文化身份认同的最重要的形式,家长对苗语的价值认同体现了家庭语言意识形态中的认知情感态度。一位家长说道“不会苗语,孩子回老家就没法跟亲戚交流。既然是苗族人就要会一点(苗语),不然会被别人笑话,被瞧不起”。家长表示苗语具有象征性意义,说苗语代表自己是本民族群体中的一员。对他们而言,苗语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还传递着苗族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信仰。
另一方面,语言理性价值评价涉及语言的实用性和社会声望。Bourdieu在对资本的分类中提出个人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10]。期望孩子掌握双语的家长认为,孩子说普通话和本族语双语代表一种文化资本,可以和更广泛的人群交流,拥有更宽阔的发展前景。比如,苗语听说能力被列入当地政府某些岗位招聘条件中提高了苗语的社会资本价值。一位受访家长提到“政府基层工作岗位招聘条件其中就有会说苗语,因为下乡工作需要用苗语跟村民沟通啊,会说苗语还是很重要,所以我经常鼓励他多跟老家亲戚说苗语”。当情感价值认知与理性价值认知发生冲突时,语言情感评价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家长们在语言选择时会更看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由于苗族没有系统的语言文字,方言苗语、次方言和土语各种语言变体词汇差别较大,同一土语也存在诸多语音变异。即使相邻的两个苗族县城也或许会出现苗语发音不同,沟通困难的情况。苗文读本的匮乏使得苗语教育只能以听说训练为主。在苗文推广度不高,在实际口语交流中语用受限的劣势下,苗语的生存空间受到汉语严重挤压。因此,家长认为苗语局限于特定的交际空间,仅能满足家庭成员之间交流需要。还有部分家长认为家乡话会阻碍普通话标准发音,在家里孩子也应该少说“土话”,多讲普通话,这也加剧了苗族家庭对苗语和汉语方言的语言偏离。
(三)家庭内部因素对语言意识形态的影响
为进一步解释造成家长语言意识形态差别的原因,本研究对语言意识形态与家庭内部条件,包括家长苗语听说能力、家长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和家长职业展开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如下(表1):

表1 语言意识形态与家长苗语听说能力、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家长职业的差异分析
以上数据显示,家长苗语听说能力、教育背景、家庭月收入与父母的职业类别均对语言意识有显著影响,F值分别为6.984,5.620,4.174 ,4.214,p<0.01。家长个人的语言学习经历是左右对子女语言教育决策的关键因素。统计数据显示,苗语水平越高和大专学历以上的家长,对孩子掌握与使用苗语的愿望更强烈,对苗语的认同感更高,也更支持对孩子进行汉语和苗语双语教育。苗语水平高意味具备辅导孩子苗文的知识能力,能从自己的学习经历中找到传授孩子苗语的方法,更容易与孩子学习苗语的经验产生共鸣。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积累的文化资本丰富,多能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灵活选择和语言转码,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相比,陪伴孩子过程中的教育投入方面会更占优势。学历水平高的家长语言态度普遍更开明,正如本科学历的小学王老师所言“我觉得苗语不会影响说普通话,孩子的普通话发音比我还好。多会几门语言也是为了交流方便,英语也很重要”。家庭收入方面,样本数据显示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这个区间为分界岭,而语言意识形态在4000元月收入以下的家庭与4000以上的家庭中均没有明显的变化。这表明,当经济资本达到一定水平,就不再是苗族家庭语言意识形态的关键影响因素。收入极度拮据的家庭对普通话的认同度高,对苗语认同度低,原因或许是普通话社会声望高,这部分家长把说普通话视为孩子未来阶层上升的语言工具。父母职业分类方面,职业属于“政府公务员”“教师”“公立事业机构人员”“解放军官员”类别的家长语言意识形态与其他类别的家长语言意识形态存在明显差异。前四种类别的家长更熟悉国家在民族地区的语言管理政策,受教育程度和社会权利地位也比其他类别的家长高,容易构建积极家庭语言意识形态,访谈中也表示非常重视子女双语能力培养。
(四)家庭语言管理及影响因素
家庭语言管理是家长在家庭内部实施,对语言实践或语言意识形态进行干预、影响或修正的具体行为[11]。研究发现,家庭语言管理与语言意识形态呈现离散现象,即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互动中朝不同的方向发展。语言意识形态和信仰可能是家庭语言政策潜藏的力量,但后者未必都会转化为实践[12]。当问及“鼓励孩子在家说什么话”时,排首位的是普通话,占47%,其次是苗语,占44%; 对问题“在家亲自教(或者请人教)孩子学习苗语”,约48%人表示一直都做或经常做,18%人从没做过;对问题“要求孩子收看苗语电视节日或音频栏目”,只有12%人表示经常做,40%人从未做过。虽然大部分家长在语言意识形态调查中对本族语的价值评价很高,但在实际家庭语言管理中却把普通话排在第一位。当问及“是否会干涉孩子的语言选择”时,大多数家长都表示很难坚持。究其原因,一位受访家长说道“在家会要求他说简单的生活苗语,像‘吃饭’‘洗脸’这样的表达。孩子也会说简单的苗语,只是不喜欢说而已,平时学习也忙,就没有刻意去教(苗语)”。访谈还了解到苗族家庭有男性主导家外、女性负责家内的传统习俗,通常情况母亲陪伴子女的时间往往多于父亲,语言管理的机会更多,在家庭语言管理中的母亲的角色往往更占据主动和优势。
语言能力是影响父母进行家庭语言管理的基本条件。苗语能力强的父母更支持子女在家多使用苗语,其次是普通话,方言排在最后。苗语能力差的父母结果恰好相反。家长苗语水平与培养孩子苗语能力的家庭语言管理正相关。积极的语言管理行为还表现为坚持教孩子苗语词汇、给孩子说苗语故事、唱苗歌、带孩子收看苗族电视节目和参加苗族文化活动等。积极的家庭语言管理者与子女交流中语码转换活跃,善于用苗语替代普通话或方言教孩子苗语词汇与句法表达,注重培养子女日常生活中使用苗语的习惯。归根结底,家长自身的双语能力,以及与子女坚持采用语码转换的交际行为是语言管理成功的两个重要条件。
三、结语
Fishman 认为语言“自然代际传递”是语言维持的关键因素[13]。基于台江家庭语言现状和上述发现,研究提出苗语的自然代际传递呈递减趋势。台江苗族家庭第一代祖父母多数是苗语单语者;第二代父母是苗语兼通汉语者,苗语听说认知依旧保持语言活力;第三代子女是普通话使用者,部分兼通苗语,苗语听说认知远不及父母,苗语在这一代身上已表现出严重衰退。虽然苗语在家庭域中仍有一定使用率,但第二代到第三代总体呈现出苗语和汉语双语平衡向“亲”普通话、“疏”本族语的方向流动。此外,苗族家庭语言意识形态与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存在分离现象。虽然大多数家长表达出传承苗语的意愿,以及少数民族身份的认同,但在家庭语言实践中对普通话的评价却更高,在家庭语言管理中家长表现出向子女语言选择妥协,共同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这也佐证了孩子在家庭语言政策中具备能动性的观念。因此,笔者认为,苗族家庭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不完全受家长的语言意识形态支配,社会其他层面的语言管理意识和行为会左右家庭语言意识形态的发展。在家庭空间内传承苗语固然重要,但苗语的实用价值需要在更大的社会空间获得认同,方能本质上提升台江人对苗语的保护意识,减缓它的衰亡速度。